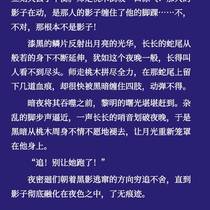*点击就看银杏智斗大反π
*没斗过
五声乌鸦叫过,侧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当值的小太监对银杏略一点头,示意她快些进去。
夜已深了,司徒京却尚未睡下。宫中起火,他自然不能安寝,见银杏风尘仆仆赶来,脸上尽是不悦。
“你究竟有何要事,非得在此时禀报不可?”
乌鸦叫是司徒京和她约定好的暗号,以五声最为紧急。银杏没有像往常那样跪下说话,而是站直了身体,强迫自己直视司徒京的眼睛:“在下有要事奏报,但还请大人将家父之事据实以告,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想必此事非同小可,竟然让你有胆子威胁我了,”司徒京冷哼一声,“究竟何事?”
“我必须要先听到家父之事。”
“跪下!”司徒京大喝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只是这宫里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站着和我谈条件?”
银杏不跪。她直视着他,强迫自己用最平静的口吻说道:“皇上死了,是我杀的。”
她期待着司徒京那张千年不变的面具轰然碎裂,她想看到他惊愕,迷茫,甚至恐惧的神情,但司徒京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冷笑了一声:“哦,如何杀的,说来听听?”
银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她可是杀了皇上!那是皇帝,天子,九五之尊,不是路边的野猫野狗,宫里的宫女太监,是皇上!
她咬紧嘴唇让自己冷静下来,再一次问道:“当年家父平白受冤,我一家蒙难,幕后究竟何人主使?”
司徒京沉默片刻,终于开口:
“你父亲林海舟,曾是前朝内阁大学士的幕僚。”
也许是因为自己所言之事关系重大,司徒京终于还是松了口,却只说了一句便停了下来。
“然后呢?”银杏急切地问道。她终于抓到一丝父亲蒙冤的线索,不能就这样错过!
“我已经给出了我的诚意,现在你该说说陛下是怎么死的了,”司徒京挥手指了指一旁的座椅,“坐。”
银杏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荒谬:仿佛她杀了皇帝,才有资格在司徒京面前坐着说话。
银杏从头讲述起这漫长的一夜。她跟随汝阳公主离开桃花宴,一路来到佛堂,面见了太后,公主又被皇上召见,不料那昏君竟想拿她作人牲!眼见姚小娥危在旦夕,银杏哪里顾得上那么多,抄起桃花枝捅进皇帝心口,那昏君当场就没了气息,可桃树却在他的尸身上生长起来,甚是可怖!
此后小娥托她传信之事,却不便与司徒京说,银杏便按下不表。好在她在混乱中寻到二皇子,将信交给了他,只是来不及把详情与他说明。
司徒京神色未变,淡然道:“这便是你和我谈判的筹码?我知道这些又有何用,应当把你这个弑君的刺客拉出去斩首才是。”
“宫中火起,太后生死未卜。然而我与公主面见太后时,她曾讲起一桩宫中秘事。”
这便是银杏最大的倚仗。此等机密之事,司徒京不可能不想知道。
司徒京却反问道:“我无意参与立储之事,也从未卷入朝堂斗争,宫中秘事与我何干?”
那你要我去做二皇子的眼线,难道真是让我去吃白饭的?银杏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道:“那就把我处死好了,反正我死了,秘密就和我一起被埋进土里了。”
司徒京冷笑:“据你所言,此事汝阳公主也知晓。皇帝一死,她也脱不了干系。等她和你一道关进天牢,我倒要看看她的嘴是不是比你的还要硬。”
……银杏真恨自己多嘴,为何要说汝阳公主也知晓此事?她本想以此事作为筹码,可司徒京终究还是技高一筹。罢了,即便被处死,死前杀了那昏君,也算是死而无憾!
门外突然有人禀报,司徒京示意银杏藏在屏风后面,走出门去,片刻后他关门落锁,皱眉对银杏道:“你父亲的事我所知不多,但我有所耳闻,新帝即位后,大学士一派便被清算,而幕后主使便是枢密使庆春泽。”
被突如其来的收获冲昏了头脑,银杏没去想为什么司徒京突然改了主意,急切地问道:“此事当真?”
司徒京点头,慢条斯理地说道:“现在,你可以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吧?”
这个漫长的夜晚仍未结束。司徒京说她不能再留在宫中,甚至不能再留在城内了。银杏乔装一番,趁桃花和大火带来的混乱还未平息溜出了宫,回望却见参天桃花,不禁一阵胆寒:自己将那桃树枝捅入皇帝胸口,是不是无意之间犯下大错?
“姑娘,快走吧。”一旁的侍卫低声催促道。
司徒京竟然大发善心,派人护送银杏出城。只要出了京城,便可去往江南避避风头。大概是皇帝已死的消息尚未从宫中传出,出城的路格外顺利,天光大亮之时,银杏便已与那侍卫一同策马奔驰,远远离开了桃花笼罩的京城。
行至一处荒地,银杏说想歇息一会儿,两人便下了马,找了处背阴的地方坐着。
“唉,城里怕是要出大乱子了……”
侍卫感叹道。
银杏沉默不语,突然提膝撞向侍卫腹部,趁侍卫吃痛倒地,拔出他腰间宝剑,飞身上马,扬长而去。
司徒京哪会发什么善心,他肯留她一命,必然是因为她还有用处!她再不想像枚棋子那样受他摆布,她要拿回自己的名字,拿回自己的剑!
银杏策马扬鞭,将层层叠叠的桃花甩在身后。
*点击就看小小剑客被搓扁揉圆
*就算只写了一根头发丝也要响应
“杏儿,杏儿……”
“醒醒,该起了。”
仿佛从水底艰难地浮上水面,银杏从梦中醒来了。方才梦中的所见所闻消散大半,只留下强烈的愤恨,大概是又梦到从前。
她艰难地坐起身子,眼前的女子对她温柔一笑:“总算醒了,快起来吧,可别误了时辰。”
银杏揉了揉眼睛,只觉得眼眶湿漉漉的,似乎有泪痕,暗道不妙。她试探着向女子发问:“小葵姐,我刚刚可曾说了什么?”
“没有,”小葵笑道,“就算你说了,也只是梦中胡言而已,当不得真。”
小葵姐一直对她多有照顾,料想就算自己真的说出什么,她也不会四处乱说。再说,梦里的话谁会当真?银杏放下心来,手脚麻利地梳洗打扮。自打做了掌设,活计也没比从前轻松许多,虽说不必像寻常宫女那样整日地清扫,却也要四处奔走,忙碌得很。
也许是这样的生活使她逐渐麻木,潜藏的愤怒才会在夜晚喷涌而出,提醒她去做那件必做之事。
我没忘,银杏想。有朝一日,她将化身利剑,刺穿那昏君的心脏,为父母,为家族报仇——然而她已许久没摸过剑了。
入宫数月,银杏这把剑早已不似先前那般锋利。
一开始,她舍弃了自己的名字。
听闻花鸟使将至,县丞家中小姐出逃,王家上下兵荒马乱,生怕落得抗旨不遵的罪名。赶来追回小姐的下人抓错了人,银杏就这么成了王杏儿,被县丞死马当活马医地带进了府。
若是能进宫做妃子,得手的机会要多少有多少!银杏成了替身,花鸟使来时,她竭力出演大家闺秀,实则琴棋书画样样稀松,只有竹笛勉强吹得像样。纯秋端坐屋内,仔细观瞧,面色不改,直到把钱袋拿在手里掂了掂,嘴角才上扬几分:宫里这样的姑娘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可有了银钱做砝码,天平的一头便沉沉地压了下来。
于是王杏儿入宫。
入宫前,她舍弃了自己的剑。削铁如泥的一把好剑,在当铺只不过值碎银几两。她打算用这银钱用来上下打点,好让她有机会面圣,可她姿色平平,又无过人才艺,这面见皇上的机会哪里轮得到她?她成了尚寝局的小小宫女,整日清扫宫中,没有一刻得闲。
若她真是王杏儿,此刻免不了怨声载道,但银杏是不叫苦,也不叫累的。她七岁习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并非什么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因此极快地在宫中安定下来。
唯有一件事让她不快:几位宫女见她干活麻利又不善言辞,总是将她的功劳揽去。起初她忍气吞声,后来便忍无可忍。她没了剑,却还有拳脚。脸上的巴掌火辣辣的疼,打她的人被她一脚踢翻在地,半天都没能爬起来。
这事原本交由掌设处理就好,谁料那日司徒京目睹这场争执,冷着脸将银杏带来问话。银杏忍不住叫屈:活都是我做的,可她们上下嘴皮一翻,就全成她们的了!
司徒京轻哼一声:既然是你做的,为何无一人替你作证?说罢便让银杏一干人等领罚,银杏罚得最重,挨了几下板子,好几天没能下床走动。
小葵姐一向关照她,特地来给她上药。她一边叹息一边说:过刚易折,过刚易折呀……咱们女人要像水一样,不管什么沟沟坎坎都能趟过去才好,你说对不对?
银杏赌气道:得罪了司徒公公,我看我也没几天好活了。
小葵姐笑道:我看未必。你卧床这几日,她们几个忙得焦头烂额,公公一向心细如发,该知道谁是实打实做事的那个。
银杏一想到那天司徒京的冷言冷语,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要是真那么心细如发,就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地罚我!
小葵姐苦口婆心道:司徒公公是在提点你呢!你这性子的确是该好好改改了。
改?如何改?银杏向来只知道怎样把剑磨得更锋利,却想不到有一日,她得把剑变钝才能过得下去。
忍气吞声只会让这些人更嚣张,一味讨好又像热脸贴冷屁股,银杏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她还在琢磨着如何去做,就又惹上了麻烦。宫里丢了几样摆设,宫女们众口一词,说是银杏拿的。司徒京不由分说,把银杏拉去打板子,要打到她开口为止。这次打得更重,但银杏愣是半句求饶也不说,硬生生地挺了过去。
司徒京冷笑:好一个硬骨头,你不怕死吗?
银杏咬紧牙关,狠狠地瞪着他:不是我做的,我死都不认。
好!司徒京拍起手来,吩咐手下将银杏带走看管起来。银杏以为自己要被下狱,却没想到司徒京派人为她治伤,一养便是半月。期间司徒京来过一次,说了些话,险些没把银杏气死:我早知此事不是你所为,那日罚你,一是为了服众,二是为了磨磨你的心性,要你日后做事圆滑些。过刚易折的道理你可懂得?我可是相当器重你啊。
银杏不懂,也不想懂。器重?又没给她银子,也没给她差事,板子倒是挨了两顿,若是宫中人都是这么器重人,她宁可受冷落。
她没想到,伤好之后银子和差事都来了。银杏和小葵一起成了掌设,八品的女官怎么也比宫女强上几分。那几个欺辱她的宫女已经不知去向,听说是偷了东西,与太监销赃时被逮个正着,如今尸体大概已经被丢在乱葬岗了。
银杏愣愣地摸着手中的银钱,心想司徒京倒是真没说谎,他的确是器重自己的。
成了掌设之后,倒是没怎么有人找她的麻烦。银杏卖力干活,只闲暇时琢磨屠龙大业:宫中守卫森严,偷溜进皇帝寝宫简直是天方夜谭。若是自己精通琴艺舞艺,就能趁着宫宴下手,早知如此,自己学什么剑,应该学舞,学唱曲才对!若是去求司徒京,让他给安排个皇帝跟前的差使,自己也好有机会下手,但司徒京又凭什么答应自己?
想来想去,都是些没用的办法。皇帝就在宫中,一想到他仍高坐龙椅之上,银杏的胸中就如同烈火焚烧:就是他害自己家破人亡,凭什么他还能活在世上?
也许是那火烧得太旺,终有被识破的一天。
你不是王杏儿。司徒京在她面前负手而立,平静地说出让她胆寒的话语。她此生从未感到如此恐惧,司徒京是如何看穿自己的?莫非是先前他问过几次家世,自己的回答出了破绽?可她早已与王家人串通妥当,想来不会有问题才对。她跪在地上冷汗直流,料想自己的死期就在今日。不对,这不对!她的剑呢?她就算是死,也应当死在杀敌的时候,与自己的剑死在一起。
她不该入宫,不该当掉自己的剑!
可司徒京却说:抬起头来。
他似是仔细端详了一番,点头道:你与你父亲有七八分像。
此话一出,银杏更是震惊。司徒京见过她的父亲?是了,算算年月,那时他应该也在宫中,见过父亲也不奇怪。那当年的事,司徒京也知道吗?
司徒京略一点头,缓缓开口:你父亲蒙受不白之冤,此事我也略有耳闻。可当年之事牵扯甚多,你想为父亲洗脱冤屈,怕是不能。
银杏默默听着,心里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她绝无可能撼动这颗大树,扳倒让父亲蒙冤之人。
可究竟是谁害父亲蒙冤,银杏直到现在仍然不知。
若你肯替我做事,我便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你不想知道是谁害你父亲蒙冤下狱,又是谁让你家破人亡,落到如今境地?司徒京眯起眼睛笑了,像是笃定银杏不会拒绝。
做……做什么?银杏不安地问。
司徒京笑容不变,吐出两个字:一切。
司徒京给她时间慢慢思考,银杏便权衡起来:若是给司徒京卖命,不知道要替他做多少肮脏事!可若是一直做小小女官,她何年何月才能复仇?带她出逃的嬷嬷从来只说父亲蒙冤,银杏再问详情,她却一概不知,想来对朝中之事知之甚少。司徒京却全都知道,只要她点头答应,就能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答案,这样的诱惑叫她怎么拒绝得了?
也许是思虑过重,一连想了数日,银杏生了场病。小葵姐来探望她,说最近天气转凉,宫里不少人都病倒了。她喂银杏喝药,又握着银杏的手让她安心,那副模样让银杏想起自己的妈妈。
妈妈,妈妈。银杏在心中呼唤,眼泪和着汤药一起咽进肚子。
银杏的病很快好了大半,小葵姐却病倒了。起先只是小病,咳了几天仍不见好,渐渐地身体也虚弱下去,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寻常的药不管用,银杏心中焦急,想去求位太医来诊治,可却碰了一鼻子灰。最近太医院正是忙碌的时候,哪有闲暇管一位小小宫女?
银杏急得落泪。她挨板子的时候都没掉一滴眼泪,此时的眼泪却掉个不停。小葵见她这样,伸手为她擦泪,声音却像是随时会断掉的蜘蛛丝一般,轻飘飘地挂在半空。
杏儿,杏儿,我对不住你。
有什么可对不住的?银杏只当她是病糊涂了。虽说这段日子掌设的活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可自己病着的时候,小葵姐不也一样?
小葵姐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下去,银杏已别无他法,只好跪在地上,求司徒京给小葵姐找位太医诊治。
司徒京饶有兴趣地看着银杏,良久他问:那你愿意用什么来换?
一切。银杏答道。
司徒京突然大笑起来:一切?你真要为了她押上自己的一切吗?
银杏再拜:小葵姐待我如姐如母,求大人救救她。
司徒京冷笑:那你可知,是谁将你的梦话告知于我,才让我戳破了你的身份?
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银杏想起那日小葵姐说,梦中的胡言是当不得真的。
银杏不可置信: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司徒京怜悯地看向银杏:无非是想谋个一官半职,换份更清闲的差事。如姐如母?这宫中无人不想向上爬,你的小葵姐也不例外。既知如此,你还想救她吗?
银杏吞了眼泪,咬紧牙关,再拜:要救的。
小葵姐死在初春,即便有了太医的诊治,她还是没能捱过去。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银杏已在二皇子府,只觉得春风也冰冷刺骨。她想起小葵姐的笑容和她粗糙的手,想起她说女人像水,无论什么样的沟沟坎坎都能趟过去。
可银杏成不了那样的水。她只是一片小小落叶,即便想要挣扎向上,却只能顺流而下,身不由己……
长叹一声,她将信纸与泪水一同扔进火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