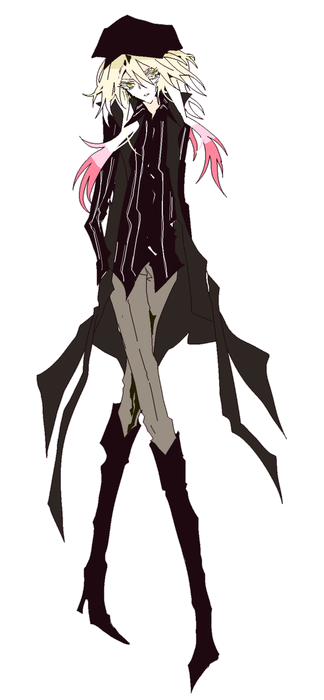“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实际的人生是从四岁开始的。”
于是医生饶有兴趣地示意他继续讲下去,G便说。
“那天晚上我的母亲送我上床,然后坐在床头,打开夜灯,给我读小孩子看的书,读着,肥皂,拿着肥皂的小女孩。然后,然后。
“然后我就有了一种恶心的感觉,世界崩溃天旋地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活在这里,活在这个女人的眼前,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此时此刻偏偏是我在这张床上,这样的痛苦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很恶心,很害怕。我就突然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她出去了,我一个人哭到发抖,哭到想立即消失。像水落在污泥地里消失掉。开什么玩笑。
“是啊,开什么玩笑。”他带着自嘲般的嫌恶说,“居然有人从四岁开始厌世。”
“恶心”。她的声音恰好在这时响了起来,虽然医生是听不到的。G感到一阵不快,肌肉和神经又紧绷起来,一层层贴在骨骼上。“恶心的”。
“这可能是敏感。”医生说,“冒昧问一句,你是你母亲亲生的吗?”
“是的。”
“何以证明?”
“不知道。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七的可能是,不是也没什么要紧的。”他说。“小时候我总是在哭,莫名其妙的哭,直到忘记几岁开始,我难过到哭不出来了。”
医生停顿了一会。
“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错误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
“不,从不。”
G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讨厌世界?”
“也不。一个心智刚刚起步的小孩子,谈不上什么喜欢讨厌。我只是对身边的一切感到怀疑和紧张,然后再到恶心。我唯一想到的只有这一切毫无意义。”
“嗯,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所有人的。我们所有人的,一系列抽象的偶然下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与分配好的人建立关系,阴影下无意义地生无意义地死。”他拧紧外套的袖子,抱着一只毛绒老鼠,缩在座椅的角落。
“像是一场惨痛的凶杀。”
“那好,请解释凶杀。”
两三次预约的诊疗之后,G才勉强习惯与医生的相处。他非常热衷于提问,可能提问本来就是咨询的基础手段。虽然他提出的问题绝大部分G会给出否定答案。
“我不知道。”G窘迫地诚实回答。
医生便交叉十指,摆出一个轻松的姿态靠在座椅一旁。虽然G完全享受不来和医生在一起交谈的时间,但是他止不住对医生的扮相感兴趣,盯着黑色格子的地毯的同时,他用余光偷偷注意着医生的头发,显眼的长发,会顺着一边窸窸窣窣地垂下来,颜色美丽但粗糙无光,像录影带里几十年前的华丽金属乐手的长发。
他不禁带着些戏谑地去想象这个热爱循规蹈矩着提问的家伙去弹bass会是什么模样。如果像那样扭起腰,那这头发大概会很有节奏感地两边甩动。
想象一下还是挺漂亮的。
“偶然的一个意象?那我不追究。”医生说,略微抬起头,G马上又警觉起来,“现在我要问的是,让你立刻回想起童年的一件事的话,你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件旧事。曾经在学校里,老师让我们所有人做一朵白花带来。”
“啊,你们那里是有这种活动的。然后?”
“然后他们用纸做了假花带来,蜡纸,复印纸,被铅笔印磨得黑黑的粗草纸。我不知道自己脑子为什么短路,我带了一朵真正的白花。一朵白山茶,和所有的白纸花一样圆又白而且花瓣重叠。然后它和纸花一起贴在了橱窗里,新鲜的,闪亮亮,格外漂亮又格外难看。
“做手工的时候我永远觉得我做的是最难看的那个。”
“你自卑吗?”
“不,客观表述。因为我总喜欢用心做的非常标准,和各种各样的粗劣次品比起来太显眼了。我受不了看上去显眼,这很让人恶心,与众不同就显得我是最丑的那个。我宁愿我也做出一团垃圾,在所有垃圾里特立独行,但不惹人注意。”
G说。
“然后我的花枯了,变成黑黄的一团,挤在假花里可怜巴巴,像假装自己曾经也是一片纸。”
“约拿困境。”医生说,“人害怕成功,害怕引人注目,下意识想去瞄准平均线,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害怕没有用,我并不喜欢隐藏才能,不是不能,但真的要我故意花大力气做出领一团垃圾只为了这样荒唐可笑的理由,我也不可能做。我不自卑,我自恋得一塌糊涂。
“这就很麻烦。”
这就很麻烦。G抬起头,用关节敲了敲鱼缸,三条金鱼猛然游动起来,四处打转,搅出细小的水泡声。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每次回过神时他就忍不住要去敲些什么,去吓唬什么人,鱼也可以。强烈的反胃与震眩感已经消退,他感觉自己终于又能动了。站起身时他感觉膝盖一酸,很不自然,好像上一次从这椅子上站起来已经是十几年前。
好了,还是能恢复正常的。
地上洒了几滴酒,他的便宜货白兰地。他弯下腰把滚进桌底的玻璃杯拾起来放在桌上,不打算去擦掉地上的酒,就把台灯干脆地熄灭了,反正床便在身后不远处。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是个不自知的癫痫患者,突然地跌倒在地,失心地抽搐,把周围搞成一团乱麻后再昏昏沉沉地醒来。不,要是在外面的话我还是能稍微控制一下的。他反驳了这个想法。
不过在外面他控制过什么呢?像那种起因于半截白纸的惆怅?控制自己不要畏缩,不要痛苦到反胃,不要倒在地上变成带刺的一团?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从来不用去想要控制什么。他记得自己什么都没试图去控制过。
那我怕不是快要死了。那就干脆快点死吧。
G昏沉地想着翻上了床。
“再冒昧问一句,你的童年有没有经历过什么重大的灾难?”
来了来了,弗洛伊德派的路子。
“没有。”G说,“我的童年是无害的。”
“灾难包括各种,环境变故,家庭暴力,欺凌以及其他。你没有经历过以上任何一项吗?”
“没有大到可以颠覆人生观的地步。比你想象的更加无害。”
“奇怪。”医生又翻了个白眼,像后来几次说他内心充满恐惧需要寻求保护时一样,“那你可不会像这样缺乏安全感。”
“我到底哪里缺乏安全感?”
被不算熟悉的人反复地如此评论,G还是有些不开心。虽然他对被如此评论的理由的好奇心还是远大于不适。
“你要是很具备安全感就不该总抱着这个玩具了。自从第一次见面起你总是带着这样的一只玩具,我不觉得对于你这个年龄的人而言这是正常的行为。”
医生说。小孩子们喜欢玩具熊。曾经熊的表演流行大街小巷,被绳子套着的,受伤的马戏熊,让孩子们联想到自己的伤痛和遭遇。所以把玩具熊抱在怀里就反映了一种潜在的自我保护意识。虽说后来玩具熊也是成人玩具的一种,它们隐喻了一种脆弱,感伤的内核……
G有些无奈地摊开手。
“这是老鼠。”
一只毛绒老鼠。和所有的毛绒玩具一样,柔软又沉默的毛绒老鼠。它尺寸不大,所以说是抱着也有些勉强,只能说G拧着外套袖子把自己塞在里面时,有一只手紧抓着一只毛绒。有些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只老鼠不是什么奢侈的玩具,灰白色,大眼睛,丝绒商标耷拉在一边,只是百货商城玩具栏里一系列小动物毛绒里其中一个。就算各地贩卖的种类各异,也算不上什么有收藏价值的稀有种类。
通常畅销的是狗与海豹,老鼠卖的不是那么好。
“你喜欢老鼠?”医生似笑非笑地咧开嘴。
“可能。”
“为什么?自己很像老鼠吗?”
“我不觉得。”
“那么老鼠让你想到什么?一个形容词。”
“可怜。”
“可怜。”医生又念了一遍,“所以为什么是老鼠?”
童年的受难对将来的影响会是致命的。弗洛伊德派很喜欢这个论调,心理咨询师也是。医生看来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是老鼠”,也不觉得自己能问到有意义的回答,于是抽身而退。
“问到童年是因为性格成因是多方面的。”他说,“负向的性格尤其。比如,举个例子,像我所知的一个年轻人,平时喜怒无常言语偏激,而且无法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的话,那么他有很大可能幼年时受到过创伤刺激,而且是长期的。”
“我没有这么严重,是吧。”G不以为意。
“是的,这只是个例子,按我的习惯我称他为W,少年W。”医生好像提出了熟悉有趣的话题,暗淡的双眼变得更有神起来,“他比你要糟糕,但你让我想到他。你有过难以控制的暴力倾向吗?”
“会故意砸坏自己的东西,算不算?”
“算。我认识的W,情绪激动时就变得精神失常一般暴力,我仔细想过,追根溯源是他直到八岁都生活在暴力的环境里,在各方面的暴力下,失常是一种后果但也是另一种自保机制。”
“比如哪种暴力?”
G偏过头。
“不,这属于隐私范畴。我提这个例子只是想说遇到你这样的性格往童年经历思考,除了理论基础外也是有经验主义的成分的。”医生的嘴角稍微翘了翘,有些似笑非笑的险恶感,“他甚至不是因为绝望而施暴,这更加麻烦了。”
“所以他现在治好没有?”
“没有。”
“直到现在都没有?”
“顽固的拉锯战很浪费时间,我也不想这样的。”医生耸肩,“看着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一个个过得如此痛苦,我很替你们悲哀。”
“替我什么?”
“悲哀。”
谁让你自作主张给我悲哀了?G马上感到一种被轻视的愤慨。为别人悲哀是优越者的特权,傻瓜,就好像唱颓丧的歌是失败者的特权一样。医生这悲悯里潜藏的优越让他不满起来。不过他能把这一层正常人的悲哀理解成一种褒奖,一点不满马上又消失了。
“好吧,还有一点。我经常会梦见自己。”G说,“小时候的自己。”
“有多小?”
“有时是四岁,有时是六岁或者八岁。可能六岁最多。”
“六岁。通常看见他——幼年的你——在哪里?”
“床上。”
G倒在床上,抱着毛绒老鼠,闭上眼,不去看没有拉窗帘的窗口透进来的一点点路灯光。这一点他记得还是清楚的,因为他现在也能看见。他倒在床上,会看见同样在床上的另一个自己。金鱼在游动。
是的在床上(重复道)。一直是这样。
你呢?
我在另一边,我在看他。我在床头,他看得到我。
然后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嗯……我给他唱歌。
什么歌呢?
经常不同(他揉捏着毛绒老鼠,回忆着)。不过我记得唱过那首,那首儿歌。这样唱,我想要一只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猫……
猫的儿歌(医生自言自语道,在键盘上敲击)。
我只是碰巧会唱这首而已。
你还能想到自己说的其他的话吗?
其他?我不清楚,可能还有“我现在要睡觉了,希望神能保管好我的灵魂”之类的句子。“如果就这样睡死了,不要让我被恶魔带走”,可能。
G有些认真地回忆着。在若干个梦里,他看见的一个小孩,坐在放着故事书的床上,穿着灰白色睡衣的小孩,圆形的大纽扣与猫的图案的睡衣里,睁着发红的双眼的小孩。他忍着无来由的眼泪,用尖刺般的目光紧盯着他。也没有错,流泪太久的眼睛会也会有尖刺一样的酸痛感,酸中带涩,锐利的绞紧的铁丝。G并不想说出什么深情的话,只是轻松地坐在他床头的椅子上,低下头来。
好了,小孩。他不怀好意地说。开心点,人死了并不是无处可去的,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死了,我就把你带到从来没见过的有趣地方,像梦里的恶魔,像一只邪恶的白猫。
是白猫。当无理由的祷告式的句子与儿歌混杂在一起时,黑猫就是灵魂的保管者,是神灵,而白猫是夺魂的恶魔,保护般的黑梦中忽隐忽现的白色鬼影。
——所以再问一遍,你信教吗?
医生又这样问了。
——不,不信,也不相信死后世界。这只是歌词。
他感觉自己回答问题用了实在太多否定的字眼,有种惹人失望的讨厌感觉。“我想做一个真正的毫不关心他人的任性的自我主义者,那样我才会幸福起来。”他说过这句话,但他一直做不到,这让人很沮丧。
伤害别人的感情从来不会给正常人带来幸福感,所以只有尽情伤害自己的感情时才是最肆无忌惮的。怪不得自己只会经常梦见自己,德性匹配下场。
“除此之外,”医生突然打断他飘忽回忆着的与自己的对峙,“你有经常梦见过其他人吗?”
“怎样的经常?”
G莫名的感到不悦。
“像你梦见你自己一样经常。”
“没有。”
“那好,你有过其他的重要人际关系吗?”
“比如?”
他有着隐约不祥的预感。
“比如恋情关系。”
医生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