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锐锋
Created by 栖于寒枝
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
不太真实。但是的确是一点点流失的感觉。
唔。体力,精力,思维,记忆,感情。
清凉的海浪抚垮了新筑的沙堡,死亡也逐渐流蚀了我的一切。
CV中村悠一

-

阳锐锋人设纸
-
“听我说,伙计们——”身材窈窕诱人、有一对丰满嘴唇的缇娜·伍德朝身后抛了个眼色,今年四月才登上啦啦队队长宝座的她显得干劲十足,“要不要为今晚的聚会找点乐子?”
安德烈·卡伊库尔深蓝色的小眼睛立即亮了起来,他本来长得并不好看,白皙的脸上布满浅褐的雀斑,鼻头又显得肉太多,要不是校队四分卫的头衔和那一身吓人的肌肉,大概他也不会成为全校气焰最嚣张的学生之一。
“说说看。”安德烈咧咧嘴。
“你们看见坐在最左边树下的书呆子了没,就是那个带着眼镜的亚洲人?”缇娜撇了撇唇角,“他可是个十足的怪胎——听人说那家伙在看关于死亡和黑魔法的书,他好像还会一点传说里的炼金术……”
不待她说完,站在一旁的安格斯·鲁已经噗嗤笑出声来,他有些歉意地冲脸色突变的女孩摇了摇头:“抱歉……继续说,宝贝儿,我只是突然想到他挥舞着魔杖的样子……哈!”
“所以我要去邀请他参加今晚的聚会。”缇娜翻了个白眼,很快又恢复了神采飞扬的样子,“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对吧?”
安德烈吃吃笑了起来,像是有一架故障的推土机碾压过了草地。
“没有缇娜约不到的男人啊。”安格斯微笑着说。
受到鼓励的缇娜朝伙伴们信心十足地眨眨眼,扭着腰身朝树下走去:她顺直光洁的金发在阳光下熠熠夺目,被紧身牛仔裙包裹得紧紧的翘臀搅动着七月的热浪。所经之处引发的频频侧目让她嘴角的弧度愈发上翘,她大步来到树下,黑色的投影毫不客气地覆盖在亚麻书面的文字上。
阳锐锋抬起头来,尖瘦的脸上戴着副又大又圆的黑框眼镜,如同一张透不过气的面罩般压在他苍白的皮肤上。他有些懵懂不安,甚至朝四周望了一圈,像是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人发现一样。
缇娜朝他勾了勾食指,阳锐锋愣了一两秒,然后顺从地站了起来,手里握着他的书《法医、警察、与罪案现场:稀奇古怪的216个问题》。
看到他站起身来,远方围观的人群低低发出一阵充满期待的欢呼。
缇娜瞟了一眼书名,拧起半边眉毛,在心里“哇哦”了一句——虽然她连整个书名都没有看全,更准确地说,只看见了“罪案”两个字。
在内心发出惊呼的不仅仅是缇娜·伍德。看见阳锐锋站起身后,安格斯·鲁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笑容慢慢地从他脸上褪去,神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那大概是两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安格斯从体育馆三楼的器材厅下行到二楼的走廊上,正在前往网球馆的途中,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一声不太明晰的声响。
他警惕地停下脚步,没等他思考出个结果,下一秒响彻天际的尖叫声便从游泳馆的方向传了出来。接着人群开始剧烈骚动,更多的惊叫此起彼伏,他像是瞬间卷入一股巨大的洪水之中,被不可抗拒的冲力推着连连后退。从嘈杂的人群中不断迸发出“有人开枪了”“有人死了”等令人惊恐不安的信息,安格斯不由得抓紧背包,也顺着人潮朝大门跑去。
这时,他看见一个穿衬衣和米色针织背心的家伙,正拼命地试图挤过失控的人群——不是顺着人潮,而是逆着人流。刹那间,安格斯真的以为自己看错了,那并不是什么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或是全副武装的特警——那只是个学生,再普通不过的男学生。
所以当这个无法用常理逻辑形容的家伙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安格斯伸手一把捞住了他,对方惊讶地回过头来,发出一声轻轻的“嗯?”的疑惑声。
安格斯这才看清楚这个男孩跟自己仿佛年纪(或者更小一些),有着苍白的皮肤外加一副沉重的黑框眼镜,凌乱的长发搭在前额上,遮去了眼中大部分的光亮。
“那边出事了,很危险!”安格斯冲着他大叫。
“我知道?”对方有些错愕地轻声回答。
尽管周围很吵,但是这句清晰无误的回答还是让安格斯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在这时那男生又讲了一句话,让他迅速从诧异中回过神来。
“那请您赶紧逃吧。”男孩说。
安格斯皱起了眉头,一把狠狠拽住男孩的胳膊:“说什么屁话,现在可不是看热闹的时候!”
“啊啊?我……我不是去看热闹的?”
“什么?!”
被安格斯强行拽着,男孩看上去有些无措,他翕动着嘴唇,进行着无助的解释:“很抱歉……可是请您快逃吧,不然会很危险……”
“——上帝啊,你以为我现在在做什么?!”安格斯将男孩按在自己身前,用一侧肩膀挡住汹涌的人潮,让这个看上去瘦弱不堪的家伙不至于被淹没。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体育馆的侧门前,被推揉着通过那扇巨大的、透明的玻璃大门的瞬间,安格斯突然放松了下来,他撑着发软的膝盖大口喘气,以至于那个黑发的古怪男孩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管他呢,”他汗流浃背地想着,“那可真是个脑子奇怪的家伙。”
而这名脑子奇怪的家伙,此时正面对缇娜的凝视,一脸茫然地盯着草地,似乎那上面藏着一个可以通往异世界的兔子洞。
“嘿,你好。”缇娜笑了笑。
“您好。”
“今晚有个聚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缇娜单刀直入地问道,“会有很多学校受欢迎的人在,而且今晚——”她挑逗地耸了耸肩膀,手指从小腹上滑过:“我会穿那件新买的比基尼哦。”
“呃。”阳锐锋盯着地面,十分小声回答,“不去。”
缇娜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什么?”她机械地问道。
“我说,我不去。”阳锐锋的头埋得更低了,感觉马上就会拔腿而逃。
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缇娜逼近一步,同时若无其事地解开了上衣第三颗纽扣,露出玫红色的内衣和半边诱人的胸部。“真的吗?”她甩了甩金色的头发,不死心地问道,“真的不去?”
“真的不去。”阳锐锋捏紧了书脊,飞快地往缇娜胸前瞟了一眼,“而且……你的内衣好像开线了。”
整个邀约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不超过三十秒,只见缇娜气哄哄地树下大踏步地走了回来,咬牙切齿地对大伙儿说道:“那臭家伙是个基佬!”
男生们哄笑了起来,他们安慰着(夹杂着些许嘲讽)自尊心受伤的女孩,反复许诺着一定会让那个不识相的亚洲佬好看。
安格斯跟在人群后面,回头望了一眼那棵绿荫茂密的树下,一个白色的身影正缓缓离开。
朝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
【Triangle】逆行者
-
当安格斯查收那封来自两周前的邮件时,离同学会还有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
他当下拨打了阳锐锋的视频电话,在提起今晚在某酒吧举行同学聚会的事情时,对方的反应听起来就像是早就知晓了一样波澜不惊。
“所以你会去吗?”安格斯问道。
“我不会。”阳锐锋平静地说,低头看向手中的试管。“他们并未发邮件给我。”
“呃……他们一定是——不小心漏掉了几个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失误。”措不及防的转折让安格斯有些尴尬地笑了几声,手指在桌面快速敲了敲。
“你知道我一向不受欢迎,鲁。”阳锐锋装作并未看见对方来不及掩饰的错愕之情,用嘴角回了一个微笑。“现在我们是SO,今晚你去了,就代表我也去了。”
安格斯看着屏幕上淡漠如水的身影,咽下了本将说出口的请求。“好吧,”他改口道,同时耸了耸肩膀,“亲爱的,记得吃午饭和晚饭,那不会占用你太多实验时间的。”
阳锐锋敷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半个微笑,通话便一下子挂断了。
安格斯靠进椅背里,叹了口长气。
那家坐落在繁华街头的酒吧倒是十分显眼,尤其对于一个本身就想灌下几杯下肚的人来说,找到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嘿,安格斯·鲁——”他还未走到吧台前,便有人高声喊道,“你迟到了!”
他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一眼就认出了挥手的人——汤姆·克林。学生时代一直跟在他和安德烈屁股后面混日子,有着一头栗色卷发和爱尔兰水猎犬般的棕色眼珠,常年挂在嘴角的笑容很是讨巧,是个不怎么起眼且不容易惹人讨厌的家伙。
安格斯看见汤姆后也举手示意,并随手在吧台点了两杯威士忌,端着杯子冲那个角落走去。
老实说,他当初并没有料到,在和安德烈·卡伊库尔发生那场等于公开决裂的斗殴之后,汤姆仍然和自己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也算是现今他还能随时叫出来喝酒或帮忙的几名同学中的一个了。
“今晚人到得挺齐的。”汤姆往舞池中努了努嘴,“安德烈和缇娜也来了。”
“那倒是少见。”安格斯啜了一口酒,视线在舞池中扫了一圈。“他们还是老样子?”
“不,当然不。”汤姆兴致勃勃地解说道:“安德烈在上季联赛中旧伤复发,已经公开宣布要退役了,下个月七号的比赛就是他职业赛中的最后一场了。”他摇了摇头。“可怜的家伙。”
“可不是吗。”安格斯轻声附和,他倒是突然怀念起以前的学生旧时光了,那些自以为是、年少轻狂的日子总是如同塞满特效的大片,在回忆里熠熠生辉,谁又会在乎实际上是怎样的?
“缇娜?”他将手中的酒喝完,又朝一旁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她还在之前的珠宝店当营业员,组过几次SO,都吹了。听说跟最后一组SO搞了个孩子,但孩子的抚养权不在她手上。她一向脾气不好——你知道的,后来还染上酗酒的毛病。以前在小型机器人售卖点工作过,因为跟上司有点不清不白,没多久就被辞退了。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了现在这个工作……不过最近我听人说她位于十六街的破公寓里总有陌生男子进出——”汤姆耸耸肩,摊开手做了个“谁知道呢”的表情。
安格斯扯出一个不置可否的笑容:“那是他们的生活。”
“我想他们今晚有点旧情复燃了。”汤姆凑到他耳边说,指了指舞池中相拥一团的黑影。“所以说——嘿老伙计,你怎么样?”
听到这一百八十度大拐弯的问话,安格斯挑起半边眉毛,斜瞟了汤姆一眼。
“你之前不是说自己跟一男一女组了SO吗,我还记得你给我看过那些给他们拍的照片。上帝啊,你小子真是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情人,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当年读书的时候你身边总是不缺姑娘了——话说你和格蕾丝还有联系吗,她今晚也来了呢,你不去请她喝一杯吗?说不定你们可以像安德烈和缇娜一样,有个不错的夜晚!”汤姆边说边举起双手,扭头不看安格斯送过来的白眼,投降般地辩解道:“好好好……我错了。我知道你在交往期间从不出轨,你就当今晚哥们多喝了几口胡说八道,千万别往心里去……”
“早散了。”安格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唉,我就知道这些SO都是鬼话,所以我才一直奉行独身主义。”汤姆无聊地说,满脸失望。“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格蕾丝?据我所知,她也还单着呢。”
说着,他扭头看去,旁边的金发男人就跟听到什么荒唐的笑话一样,微笑地摇着头。
“真可惜,你们当年挺般配的,俊男美女往哪儿一站,叫谁不羡慕。要不是你小子和安德烈决裂……诶,对了那个男生,就是你替他抱不平的那个亚洲佬,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汤姆用两只褐色的大眼睛望着灯光斑斓的天花板。“以前的同学会我还记得他来过一两次,稍微露了个脸,后来就再也没见着了——你们还有联系吗?”
安格斯点了一支烟,没有回答。
好在汤姆对此毫不介意,继续沉迷在自己的自言自语中。“如果那小子也来就好了,虽然他有些奇怪,看上去不太与人亲近,但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他抓了抓鼻头,像是对接下来的话感到不好意思似的。“你知道那时候,我是说我们如果不选择跟谁站在同一队,就会受到排挤和欺负。其实这点我还蛮佩服那个亚洲小子的,他似乎跟谁都不是一队,现在想想也蛮酷的。”
“是啊,他就是那样的人。”安格斯吐出烟雾,眯着眼睛露出一个会意的笑容。
“所以我也很佩服你,真的。那天你为他打架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这个朋友我汤姆·克林交定了——在关键时刻,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有勇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虽然那时候你看起来和安德烈一样混……”
说到这里,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像两个傻瓜一样,浑身颤抖着,酒液从杯子里撒了出来,压抑的低笑也逐渐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笑。有几个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又扭过头去——酒吧里的疯子可不足为奇。
“打搅了,这里没人吧。”
一个清淡的女声切断了他们疯狂的笑声,安格斯睁开眼睛,只见梅伦希尔·爱德华斯站在他们面前,黑发蓝眼,面色柔情,端着一杯鸡尾酒,看上去很是疲惫,却仍高雅如旧。
安格斯收敛了笑容。
那是个晴朗的日子,一个苍白的亚洲男孩曾站在图书馆阴暗角落里,眼神涣散、精神失控,只因为他喜欢的女孩子牵了别人的手。
梅伦希尔·爱德华——
“俊男美女往哪儿一站,谁不羡慕?”汤姆的话再度在耳边响起。
那个男孩心里在乎过的人,谁知道是不是过去式。
就像每个存心买醉的家伙一样,他内心里脆弱的那部分被自己亲手射出的子弹击中了。
那是三年前,冬季里平常的一天。
一栋看上去很普通的单身公寓房外面,隔着一条不算太宽的街道,一个有些落魄的金发男子独自守候在蒙蒙细雪之中。
男子的脸色明显透着一股憔悴,未经修剪的胡渣沾着晶莹的雪粒子,鼠灰色的连帽衫外罩着一件卡其色的长款风衣。他双手插着口袋,缩着肩膀在零下三度的风雪中不屈不挠地伫立着。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十分钟前他刚看了手表,现在他几乎无法感受到双脚的存在,深藏在口袋里手指则捏成拳头,像是拼命攥着一根无形的稻草。
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的细雪持续了整个下午,他就这样从天明一直站到了天暗,可仍然固执地不肯从公寓前离去。
“再过一分钟,他就会回来,开那扇公寓的门。”他反复这样对自己说,皮肤和衣物上都结了碎冰,寒冷一点一点地麻木了那充满整个心脏的焦虑和失望。
“他也许还在实验室里工作。不,也许他只是睡着了,一会儿就会亮灯的。”
漫无边际的等待中,他一次次紧紧闭上眼睛,又一次次地狠狠睁开。
“求求你……”他无助地在内心祈祷着。“……一次就好……开门啊,阳!”
可是除了风雪的声音,什么奇迹都没有发生。
他不想去看手环里这期间打来的电话记录和愤怒的信息,男子只是迟缓地转动身躯,往那个业已支离破碎的SO之家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自己回去之后又要面对怎样的争执和吵架,但至少他很清楚——
这个跟自己打的赌,他输得彻底。
酒吧里的喧哗声把安格斯猛地从回忆拉到了现实。他仍坐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前堆满了空酒杯,手指间夹着一根已经燃尽了的烟。
他将烟头按在石英烟灰缸里,拨打了那个熟记在心的电话号码——不出意外地,电话没人接听,而是转入了语音信箱。他略一犹豫,然后对着接收器说道:“是我。我好像喝多了……你能来接我吗,在第十大道的酒吧。”
“你在给谁打电话?”汤姆醉醺醺地靠了过来,“要是约姑娘的话,帮我叫一个呗。”
安格斯新点着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又长长地吐了出来。“只是打了个旧赌罢了。”他淡然答道。
汤姆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暂时睡过去了。安格斯收敛起轻浮的神情,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是一脸严肃地默默抽着烟,冲着每一个朝他走过来的女人摇头表示回绝。时间无声地流逝着,他的眼神也逐渐由明亮转到黯淡,这时身旁的人动了动,揉着眼睛醒过来了。
“我睡了多久?”
“两个多小时。”
“你一直呆在这儿?”汤姆看上去对安格斯竟然没有和某个女人去开房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安格斯之前说的话。“你是在和谁打赌?”
这时一个穿着兜帽的身影闯进了他们的视野——汤姆还没反应过来,他身旁这个一直闷头抽烟的男人突然站起身,正面迎了上去,不待穿兜帽的那家伙开口,他就捧住对方的脸猛地吻了下去。
汤姆愣住了,他隐约意识到周围有些认识他们的家伙也愣住了。
然后他看见安格斯搂着那人走了过来,在看清对方面貌的同时,他也听见安格斯一字一句地介绍说:“阳锐锋,我的SO——现在,人都到齐了。”
【Triangle】以吻封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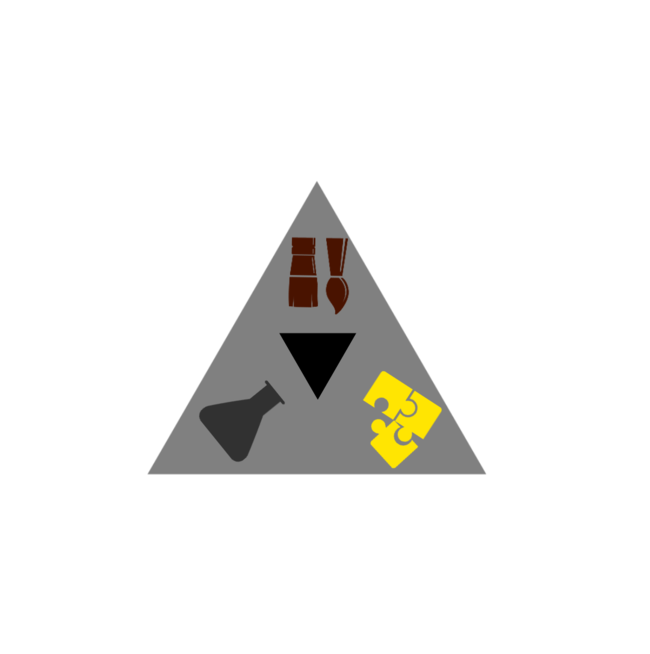
AAA组SOlogo
-
*记错打卡时间,以为是今天24:00,结果看到是9月1日……
*不是大结局,大概还有一篇
======================================
安格斯进门后立刻发现气氛不太对头。
他怀着一颗警惕且忐忑的心,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背上,一边摘领带一边往里屋走去,室内自动调温器还开着,阳的围巾和理查德的写生用品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对于眼前这片诡异的寂静,他不由得打算先从这两人吵架的可能性去猜度。
盥洗室的门咯吱一声开了,理查德有些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从里面走出来,无意对上安格斯的视线时,明显地愣了一愣。
“你怎么才回来?”抢在对方开口之前,理查德有些冲动地两步上前狠狠拽住他:“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你统统都没接!”
“上午开会,所以把通讯接收器关掉了,怎么了?”对于理查德突如其来的火气,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个来找你的人!”理查德气得有些语无伦次,“那个自以为是的红头发女人!见鬼,也不知道她究竟跟阳灌了什么迷魂汤。她离开之后阳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把自己关进房间就是不肯出来。”
“等等,什么?”安格斯试图搞清状况,“红头发的女人?找我?”
“是!找你,一个红发的女人,还他妈的叫我转达信息给你!”
“慢点,你别急,是什么信息?”
“她说,”理查德的胸脯剧烈地起伏了两下,狠狠吐出一口恶气,“告诉安格斯,乔治希望他快点回家。”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阳锐锋本来打算置之不理,可是整整五分钟过去了,本应在楼下画画的那个家伙依然没去开门,而来人似乎也不打算放弃,执拗地发出一连串令人烦闷的敲击声。
阳锐锋撇着嘴角摇了摇头,不耐烦地丢下手中进行到一半的化学实验,打开卧室的房门,探头往外望了望,敲门声仍在继续着,没有人回应。他烦躁地咂了下嘴,拖着便鞋跑下楼梯,只见理查德闷头挥舞着画笔,脑袋上戴着阳才买的簇新耳机,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
阳冲着那个专注的背影无奈地翻了翻眼睛,也不去打搅,自己来到玄关,拉开门一个陌生女子赫然出现在视野中。她盯着阳,不待询问便主动地说:“我是来找安格斯的,我知道他住在这里。”
“他不在,您换个时间再来吧。”阳下意识地避开视线,就要关门。
女子急忙伸手拦住:“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您可以打电话问他。”
女子咬了咬嘴唇,很有些踌躇的样子,但是并没有松开挡在门上的手。
“你是他现在的SO吧?”她头一偏,装作无所谓地耸耸肩,如果阳的视线没有落在门口那块灰色脚垫上的话,大概一眼就能看透她这蹩脚的自我安慰。“我听别人说你们还在实验期。”
阳的肩膀僵住了,然后第一次抬头看了女人一眼。“你是谁。”
“啊,我叫薇琪,是安格斯之前的SO。”女子条件反射般地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让人联想到她富有张力的名字,她朝阳伸出手:“嗨,你好。”
阳立刻往后缩了一下,愣愣望着那只手,宛如提防着一条毒蛇。
“你没事吧?”薇琪试探性地问。
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他可能勉强自己笑了一下,也可能只是一脸木然地往屋内走去。在退回来的过程中他撞到了那个放着花盆的铁台架,一些易碎的东西掉了下来,稀里哗啦地损了个干净。
我又做错事了。他盯着那堆绿色的残渣想,一些陶瓷碎片溅进他的鞋里,令他每走一步都像在被细小的蛇噬咬着,警报声骤然在脑海中大肆作响。这就是了,我他妈活该被惩罚,作为拿了属于他人东西的报应。阳锐锋挪到沙发前跌坐,失控地大笑起来。
也许是花盆粉身碎骨的功劳,也许是对阳本身情绪的波动比较敏感,这场变故终于惊动了窗台前专心画画的人,理查德摘下耳机,视线在客厅里的两个人之间来回扫动,一脸的莫名其妙。
“——嗨,我是薇琪。”
“呃,理查德。”理查德一边小心翼翼观察着阳脸色,一边慢慢靠近那名不速之客。“你是阳的……呃……”他飞快扫了一眼面前这位鲜艳的打扮和半露的刺青,立刻将“朋友”及“同事”的猜测统统咽了回去。他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这是怎么回事?”
“呃……实际上,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薇琪做了个“天知道”的动作,理查德的出现似乎让她松了口气,“我只是跟他随便聊了两句。”
“随便聊了两句?”理查德拧起眉毛。“他就变成这样,你是巫婆吗?”
薇琪咬了咬嘴唇,翻了个白眼。“好吧,听着,我只是来找安格斯,仅此而已。”
“安格斯?谁?我们这里有这个人吗?他是做什么的?”
薇琪看上去有一瞬间的迷惑,她张了张嘴。“我以为……”她的眼珠子快速左右转动,在理查德和阳身上分别作短暂停留。“我以为你们三个是SO。如果你不认识安格斯,那么你是谁?”
“嘿,小姐,我在问你问题。”理查德嚣张地歪了歪脖子。
“安格斯——”女人突然大喊,“你在吗?我来了——”
“嘿!别在我家里吵闹!”
薇琪望着理查德眨眨眼睛,仰头笑出了声。理查德迅速瞟了眼躺在沙发上的人,而阳只是以之前的姿势靠在那里,就像草丛中一个熄火了几世纪的机器人。
“哇哦,我只是——”她做了几个不明所以但可以理解为轻视的手势,戴的那些戒指几乎要闪花理查德的眼。“没有想到,他会跟你们组SO。”
“我也没有想到。”理查德笑了笑,眼神像是一触即发的枪弹。“他会认识,你。”
薇琪眯眼回敬了个微笑:“帮我个忙,给安格斯带个口信。”
“祝你回家途中一路平安么?”理查德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薇琪笑了。
“所以这个他妈的乔治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理查德气急败坏地质问:“是你之前的SO吗,竟然叫你回去?”
安格斯没有说话,沉默的眼神让理查德十分不安,他捉紧金发男人的衣襟,感受到一双有力的手握住了自己紧绷的胳膊——安格斯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令他生畏的镇静——是一种强压愤怒后展现出的冷漠。
安格斯的目光从理查德脸上转移到旁边的房门上,他凝视着这扇紧闭的门足有好几秒,松开理查德被卡得隐隐作痛的胳膊,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了房子。
“嗨,是我。”出租车中的薇琪望着窗外的街道,手环上显示出视频电话的画面。
“情况怎样。”淡漠的陈述语气,画面中并没有出现人物,展现出的是一个薇琪没有见过的办公桌。
“没见到人,但是我见到了另外两个。”
“你当然没有碰上,因为整个上午他都在公司开会。”还是那个过分自信而容易令人不快的声音,薇琪坐在车上,很明显地皱了皱眉。
“你在哪儿?”她问。
“放大画面。”那个声音命令着。“现在,看见了吗?”
薇琪睁大眼睛,望着画面中那个相框,微微张大了嘴。
“你在安格斯上班的地方?”她的音调提高了。“我刚才见过这个人,他叫理查德。”
“理查德。”那个声音复述道。
“还有一个亚洲人,他看上去似乎有点不正常,我记得理查德叫他‘yang’。”
“yang。”设计公司里靠窗的某个工作桌前,一名金褐色头发的英俊男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曾在安格斯的通话记录里见过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家伙无关紧要,安格斯甚至都没在桌上放他的照片。你觉得安格斯会来找我们吗,乔治?”
“我觉得……”乔治伸手拿起桌上另一个放着风景照的相框,把相框背面的锁扣打开,接着慢慢露出一个训练得体的完美笑容。
“嗯?”薇琪挑眉——这么久了,她还是搞不懂这个男人。
这是一张不错的人像照:照片中黑发的男人站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杯咖啡,专注地凝望着窗外,透出一股平静的温柔神色。
打量着这张被摄影师小心隐藏着的作品,乔治胸有成竹地笑了。
“我觉得——”他说:“很有必要先找这个‘阳’谈一谈。”
【Triangle】不速之客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