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限定的爱豆project,有兴趣的也可以来试试……?
以网络游戏《龙之谷》为背景设定的亲友小组。
是家里一群私设崽子的集合地。
因为人懒,您现在看到的所有立绘几乎都是阿穆的图(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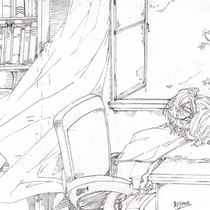
*艾尔第一人称视角,没什么意义的小故事
几百年前写的黑历史了(
魔法山脊的雪景很漂亮。
雪花轻盈的飘落,慢慢的就将裸露的土地全部覆盖在白色下,视野所及是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哪。
——虽然无论哪里的大雪都是这般模样,我是说,看见这样的景色,总让我想起当年……
“所以你只是触景生情而已,这鬼地方一点都不好……”坐在我对面的十字军正在借酒消愁,他直白的话语和牛饮的动作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差劲。
我冷下脸,手指不断的用力敲击木桌,发出咚咚的响声:“不好就滚。”
“呜呜……不要嘛……”他开始假哭起来,壁炉昏黄的火光映着他的脸,半眯着的紫色眼睛像是透明的一般,有着某种我不能够理解的美感,“我可好不容易找到你啊阿尔,你好无情你好无趣,你可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什么都是我教你的,你以前那么可爱呜呜呜呜……”
我垂下头:“时海,你好烦,不要拿以前说事。”
我真的很烦他提起“以前”,那个我还被关在该死的房间里的以前……连床都不能下,偶尔的活动时间范围也只是房间里,我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
如果时海还留恋那个时候的话,那还是赶紧滚的越远越好吧。
——面临死亡的时候无力逃跑的所谓以前,到底有什么好的。
“喔……”
他含糊的应了一声。
我看不见他的模样……大概是觉得很尴尬吧,他居然不再多嘴了。
一时陷入了沉默,房间里只有火舌舔舐木柴的噼啪声,和酒瓶酒杯撞在桌上的声音。
——与其说他喜欢以前,不如说他是喜欢以前的我,我晓得的,我也承认有某一段迷茫的时候我也喜欢过他。
那个房间实在太可怕了,基本隔绝了外界的所有东西——除了时海这个人。
我怎么能不喜欢他呢。
他从我能够记起来的时候就开始照顾我,送饭陪聊和哄我睡觉,我看着他从一开始的小豆丁长成个不错的青年——虽然长什么样我实在是不记得了——然后开始对我另有企图。
太好笑了……那么傻的对他那么依赖的孩子,当然轻易的被他哄到手了。
真的很好笑。
然后我们两个就死了,不如说整家人都死了,被放了一把火烧死的。
或许有些是被砍死的,谁知道呢,没兴趣。
葬身于火海之后……大概是第二年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醒过来了。我走近那所大房子,从手到身子到脚,整个人穿过了木门进去,又穿过了行走着的人的身体,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没有人能看见我。
喔,我死了,不是诈尸,只有灵魂。
——然后我就开始流浪了。
我走过了很多很多地方。
曾经有段时间特别累,就呆在一家人的壁炉旁边每天不是睡觉就是睡觉。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了恋爱了结婚了吵架了,最后背叛了对神的誓言离婚了,我心里有些许不是滋味。
然后我就换了个人跟着,他大概是个骑士吧,某一次与怪物厮杀的时候被另一头怪物偷袭而死——我记得我当时叫喊着躲开,他却一点没发觉。
毕竟我死了嘛。
……然后,大概又过了很久很久很久,换了很多很多的人跟着之后,我突然遇见了也在飘荡的时海。
他就像普通人一样呆在人群里随着他们移动,但我在半空能够清晰的看见路人穿过了他的身体,还有他茫然的表情。
太好笑了……那个样子,我躺在空中打滚,笑得肚子疼。
其实也没有肚子疼那么夸张,我是说,我已经不会肚子疼了,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真的笑得很夸张。
如果有实体的话大概能笑出眼泪……
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发现我了,还很激动的朝我飘来。我也很激动的看着他,然后拍开了他伸向我的手,跟他说“快滚吧”。
“我不喜欢你,所以快滚吧。”
那是我第一次说滚这个字,我也已经不记得是从哪学的了……总之自从那之后,我每次看见他,脑袋里就只剩这个字眼了。
那之后偶尔我也会感慨他的坚持,被我赶走之后又厚着脸皮回来找我……他到底是喜欢我什么啊。
我承认那段时间还真的有点感动并且愧疚。
但是这不证明我就会喜欢他了。
我很清醒的认识到了一开始我对他只是对同类的依赖,因为那个世界里只有我和他,所以他喜欢我的时候我也会喜欢他。
——只是不想失去我眼中唯一的活物。
但是当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一开始的迷茫抗拒到现在的乐在其中,就不再有那样的感情了。
毕竟变成这样的并不只有我们两个,我高兴的时候甚至会去找附近同样飘荡着的灵魂聊个小天……虽然我们彼此无法相触也没法触碰活着的人们所创造出的物件,但是也聊胜于无。
换而言之,已经不需要他了,他不再是特别的了,所以我不再去喜欢了。
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断定自己是个渣男,用完就扔。
——直到我看见了现在这具身体。
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沉眠在冰块中,一动不动。他的脸跟我很像,头发也是相似的颜色,只是他扎着马尾,我披着长发。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长得蛮好看的,怎么就这么死了呢。
活着说不定还能祸害个把人呢。
叹了口气,我决定在这儿长住了——于是我穿过地下室,开始在这栋和当年那栋规模相似的大房子里游荡。这里的人有个和那小孩长得特别像的牧师,似乎是他父亲,还有一个总是会哭的漂亮法师,冰系的,我看见她练习魔法——那似乎是他母亲。
果然脸好看是会遗传的。
我突然有点好奇我的生父生母的样子。
但是即使我现在回去,也只能看见灰烬了而已。
非常不幸的是,我在这儿还没住上几天,时海就跟着找了过来。
他看见地下室里被冰封的小孩的时候,眼睛里闪过的那种迷茫和惊喜,还有怀念……那神情让我觉得,背后一凉。
好阴森啊。
我不禁后退了一步。
“他真像以前的你,那么安静……”时海注意到我的动作,笑着对我说,“那么乖巧,比现在你这样可爱多了。”
……
所以你到底喜欢的是我的什么啊?!
“……Fuck。”沉默了一会儿,我爆了这几十年来的第一次粗口,“你给我离这个家远点。”
什么时候不喜欢我了再来见我,太可怕了,这个人是因为以前能控制我才喜欢我吧。
我一定一定不能让他碰这个小孩,一定。
但是那小孩的脸,我承认,真的太像我了……
所以某一天我没忍住,还是把手伸向了冰里。
我想看看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记得我的好像是紫色,他母亲的是蓝色,父亲的是紫色……
他会不会像他爸爸……或者说像我?
然后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只是恍惚了一下,就突然发现自己有重量了,想睁开眼睛却睁不开。眼前是一片黑,思维也是一片黑——我试图挣扎,但无法动弹,只能感觉冷气不住的往身体里钻,很痛苦。
我调动了一切我能掌控的力量去控制自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间或能听见时海的声音传来,但我也无法开口回应。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要疯了。
……大概是孤独逼疯我的。
有时候恍惚间我能听见水流动的声音,或许不是水,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力量在呼唤我。但是我不敢去想,直到我自暴自弃的想着要死了,用意识呼唤它触碰它,它就飞散开了。
那是什么呢……它穿过我的身体,甚至于充盈了我的身体,非常的疼痛,痛不欲生,我根本不能想象在死了快百年之后还能感受到痛。
所以那痛感实际上或许很轻微又或许很强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时候我只想就地死亡,并且非常后悔去碰那个小孩子,后悔到我都快要咒骂女神了。
——但是当我准备骂的时候,冷气消失了,我能动弹了。
哦,完全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该死的。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是在地下室里。
低下头看的时候,身边都是水,身上也是湿淋淋的……衣服也换了一套,款式和小孩的衣服一模一样。
……???
一模一样?!
“……我的女神喔。”我自言自语道,声音很是沙哑。
完蛋了,完蛋了,真的完蛋了,该死的。
我这次是真的诈尸了,还是诈别人的,完蛋了。
会不会被那个漂亮妈妈用魔法捅死……
……但是我的身体活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甚至能感受到心脏在重新跳动,虽然缓慢得像快死了一样。
我伸手按在自己的左胸上。
“你在想之前的事情吗?”
突然有声音打破了回忆。
我这才回过神来,发现手正按在左胸上。
——是的,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活了过来……虽然还是像具尸体。
酒杯碰撞的声音已经没有了,那个声音的主人一定是时海……
不用想我都知道坐在对面的那个该死的家伙刚刚趁我发呆的时候盯着我看,于是我非常自然的放下手,重新敲击起了木桌:“没你的事。”
“是的……是的。”他这么回答我,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抬头看向他,内心有些惊异还有些欣喜——他终于想通了?终于意识到我有多么烦他了?居然承认我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他的表情很复杂,复杂得我根本没兴趣看懂,特别是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下:“你真的有那么不喜欢我吗?”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你。”我忍不住嗤笑一声,“骗小孩很好玩吗。”
“……阿尔。”他凝视着我,低声道,“那你喜欢那个战士吗?”
……啥。
我挑了挑眉。
这是说莱奥还是林德还是小黑?我比较喜欢小黑,毕竟伊尔很喜欢小黑,莱奥也还行……
还行吧。
有点喜欢,但是也不是特别喜欢。
不不不好像这个不太能比……
不不不不对,不要叫我阿尔!
“艾尔,艾尔·洛佩斯。”我面无表情的纠正道。
对,这个才是那句话的重点,我喜欢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洛佩斯大少爷。”他沉默了一会儿,视线还是在我脸上流连,“我想我该去享受下女神给予的第二次生命了……总耗在你身上也不是个办法。”
他的声音有点哑,断断续续的。我知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大概是会难过,应该,至少他表现出来的很难过,这让我突然有些久违的愧疚。
我偏过头向窗外望去,还是一片白皑皑。
“我走了,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时海毫不介意我的走神,轻声道,“等不再留恋你了我再回来吧。”
我点头,想了想好像不太对,又摇了摇头,又点头。
“但是你以前真的很可爱。”他又补充道,“我喜欢的就是你那种依赖我的样子,真的,什么都要我一手帮你包办,而且你只会听我的话。”
……
我突然又火大了起来,把他推出门外:“现在你看不见了可以滚了吧。”
“你好凶哦。”他扁扁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换个人去满足你那疯狂的占有欲吧管家大人。”我倚在门框上忍不住嘲讽他,顺便理了理身上厚厚的睡袍,“我不是小孩子。”
“好吧,好吧。”他举手投降,“不给个离别礼吗,嗯?比如一个吻……”
“你是小孩子吗!”我终于忍不住了,扯着他的领子对着他的耳朵喊道。
“就这一次。”他很诚恳的看着我,“面对要离开了的老管家,大少爷好歹给点表示……”
我不耐烦的松开他,视线却撞进了他的眼睛里——浓厚又难以理解的哀伤,但是好歹再也没有出现让我熟悉到反感的情绪,仿佛就真的是讨要朋友间的离别礼。
我冷着脸,就像对每一个离开我的孩子做的那样,轻轻的用嘴唇碰了碰他的额头:“祝你好运。”
总归这人还是照顾了我二十年,虽然动机不纯,就当回礼了。
……感觉这样好像无缘无故他就比我小了一辈,我占便宜了啊。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十字军走远,有些感慨。
呆在一起八十年也没什么好下场……日久生情都是骗人的吧,该是朋友的一辈子都得是朋友。
或许两辈子三辈子都是。
“门口不冷吗?”
身后传来了谁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莱奥抱着手臂站在里面看着我,表情似乎有些不太爽。
“没感觉。”我摇摇头关上门,“想睡觉。”
——有点心虚,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心虚……但是我好像没做错事情啊。
——应该没吧。
我感觉自己很无辜。
“睡吧。”他叹了口气,牵着我带我走进了房间里。
——是嘛,没做错嘛,一定是因为他长的太凶了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感觉。
心里的小人了然的点了点头。
我面不改色的拆掉了扎着头发的发带,随手一扔就爬到床上把被子滚成一团搂着打算睡觉。
“你先松手。”
我感觉到怀里的被子被扯出来了,然后盖在了我身上。我烦躁的睁开眼,看见莱奥躺到了我身边。
“陪你睡一会儿。”他说。
“……我要睡一整天。”我抱住他,良久开口道。
“嗯。”
“午安。”我亲了下他的唇,闭上眼头一歪就睡了过去。
****
我要把那个叫时海的十字军拉进一看见就打出去的黑名单里。
听见情敌索吻全过程的莱奥咬牙切齿。


大概是两个在《绝对不能交往的男性TOP10》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警察恋(互)爱(怼)的故事。
国防部特工大战资本主义
公馆相关设定放置处
个人世界观OC放置处
用来分组归档自己的原创创作,大多未完。 都是古风,不需要了解作者也可以看懂的普通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