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无尽的黑暗大海中,漂浮着一座层层叠叠的岛屿。
在现代的人类社会中,传说中的生物自云端跌落,被黑暗所扭曲的现实 ,恐怖于和平,希望与绝望,牺牲与背叛,一幕幕的话剧描绘着着与现实不同的现实。
而这是讲述我在那个岛屿上看到的故事。
自娱自乐的故事
-------
没有分类的都是废弃的文案,但是设定不冲突
T-IW=Tera-Infinity World(垓-圈外世界)
+E站的文手们快来抱团取暖+
+小组主收文手,可自由发作品交流学习,熟悉后一起以T-IW为团队进行企划策划、组内世界观设定以及无限的创作合作吧——!+
+非常欢迎热爱日轻、国轻、奇幻、西幻、魔幻、科幻、超现代、异次元、意识流、设定及策划的文手们,但主古风民国玄幻的小伙伴抱歉啦+
+期待你的加入!+
[我在那里……
1%的墙壁背后,我一定会在那里……]
T-IW系列纯文字企划弟一弹——《Tera-Infinity World:1%》
>>企划宣传
第一阶段-[T]
《序章(α)-Tableau》
刚才那是……什么?
耳鸣、晕眩,好像又有点反胃。
想要移动,身体才像是刚刚解冻般,生硬地发生了位移。
骨骼发出了“咯咯”的声响,极速的心跳,在头颅间回荡。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我的家吗?
液晶显示屏,刚开封的盒装果冻,僵硬的手尚握着白色的塑料勺。
正午的艳阳印过格纹窗帘打在缩小的瞳孔上,蝉声喧嚣。
不自觉调起进度条,电脑荧屏上影视剧的画面已超出了自己的认识,但似乎,又只是错过了几句台词。
只过了一分钟?明明刚才我还……
赤、黑、银、蓝交融绵延。
哄笑、嘶吼、鼻息、轻语此起彼伏。
木香、铁锈、血腥、酒气涌入鼻腔。
现实中绝对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直感。
不小心睡着做梦了吗?
装备着精致甲胄的飞龙悬于利齿的腥臭唾液滴落在手背时粘稠的触感;
躯干附加起令人自豪的重量同时,身后银甲的圣官抱臂爆发出豪迈地笑声;
与同期加入圣骑士团的他们,在璀璨到犹如天明的星空下眺望红土尽头绵延的绿色植被。
不……这绝不是幻觉!!
“嗡嗡——”
调成静音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颤抖着的双手捧起矩形的电子产品。
非日常的新信息。
“欢迎回到基点。
在初次世界线叠合间隙,您前往的是偏差值=-1.26的N线。期间您的行为,造成了世界线变动率正向增加0.016。请登录网址(:blank)提交本次《改动者手记》。在网站内您能关注世界线变动的最新情况,也可加入聊天室和其他改动者进行交流。
期待您的下次表现。”
“发件人:神的使者”
[可公布客观背景设定]
由于[进入第二阶段后解锁]的原因,遭受强行干涉的客观世界定律增添了新的设定。
> 将当下所处的现实世界,公元2016年,定为基点,以原子结构式的K、M、N、O、P层为由内核向外扩展的五个放射性圆环世界线的模型,现实世界这一平面与有规律地做圆周运动的原子结构层按照一定周期相交,各层周期不同。
> 在叠加周期内,K、M、N、O、P五层世界线中的不定数层与现实世界逐渐重合,“世界线偏差值”或正或负地叠加在基点上,正向叠加象征着向未来迈进,负向则回溯。
> 改动者(即企划参与者)是来自现实世界基点的人,受到偏差值的无差别影响从而进入另一条世界线(企划参与者可自行选择是否受到影响)。届时其记忆、潜意识等都会将自己归为原本就存在于这个世界线的人(例如在P线里,潜意识会将自己定义为人造人,试验体,变种人,尖端科研人员等等;交错偏差到其他世界线,不可思议的穿越者、魔导公会会长、海贼商贩等等只要符合该层基本设定皆可)
>> 企划初期每个改动者在其他世界线的自定义身份不能变化。
> 偏差绝对值越小,真实的、现实世界的记忆便恢复的越多,完成该世界线内主线支线任务的几率也就越小,横向探索的时间同样会减少,因此对该世界线的变动率影响也会变的更小。
☆ 改动者在K-P世界线里直间接引发的事件(包括任务范畴)若对该世界线变动率影响的足够深远,那么改动者的行为甚至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同时也有可能被转移到另一条世界线。
随着世界线运动,偏差绝对值越来越小(即越来越接近现实,周身环境也越来越向现世环境靠拢),叠合周期结束后改动者全部回到基点,回到现实世界。
>> 在其他世界线与现实世界中时间的流逝速率不同。
> K-P五层,每一层都有截然不同的地形、生态系统和文化等基础背景,基本风格对应如下。
[所有Eg.只是举例并非世界观设定,例子偏向争端,参与者设定的世界线可以十分和平]
现实世界-并不科学的科学向(类似命运石之门等)
[每人都有可能受到偏差值的影响但若偏爱现实风作品也可作为研究人员/爱好者/???在现实中对世界线偏差进行研究或进行相关活动)
K线-魔幻向[关键词:魔法融入日常生活的幻想世界](类似妖精的尾巴/龙之谷等主流魔幻)
Eg.“魔导协会在极北大陆的分部将在圣冰素魔道学者的帮助下设……该死!那家伙又忘了给火元素施放定时休眠法术了!……会长送的高级食材啊……”
M线-童话向[关键词:犹如童话般充满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世界](类似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Eg.“你知道吗?在灰白之森南面的燃烧湖底沉睡着星辰的碎片,一定是闪亮亮的吧!如果交给金银山里的长着鹿角和鳞片的工匠说不定能铸成世间最美的誓约之结!”
N线-西幻向[关键词:古欧风铁与血的幻想世界](类似魔戒等)
Eg.“精灵猎队与矮人十字军大张挞伐的进程迫在眉睫!所有高贵的圣骑士们啊,举起圣剑,为了我们伟大的联盟,备龙、出征——!”
O线-奇幻向[关键词:蒸汽朋克+宗教 科技和神学交融纷争的世界](类似最终幻想等)
Eg.“A部队的十六艘蒸汽飞艇已于时间神教廷所在岛屿边境成功着陆,隶属于冒险者公会的冒险者们将凭借最新技术压缩蒸汽进行突入。是时候让那帮信仰着子虚乌有的蠢货们感受到技术的力量了。”
P线-科幻向[关键词:超现实未来幻想世界](各类科幻作品均可借鉴)
Eg.“抵达目标地点后迅速建立屏障,资源采集任务完成之前在驻扎区域建设临时通讯站,人造人部队,解散。”
并不知晓 神 的存在与目的的改动者们将在不同世界线受到神的使者的引导,最终将世界引向……?
参企细则(不完整版):
整个企划分为[T][E][R][A]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未定)个章节。新阶段开启时会公开新增情报,阶段结束时则会对所有参与者在本阶段中的表现作出总结。对世界线变动率改变最大的参与者将会接受特殊剧情任务和特殊剧情奖励,第二到四名则可获得对应奖励,届时会发布细则。阶段剧情等越延后越能体现出参与者对世界的改动,整个故事的结局自然由各位的表现决定。
***每位写手上传作品的标题必须按照格式
[世界线](类型)《文本标题》
例如:[N线-1.26](日常/主线剧情/横向探索]《???》
神的使者(企划主饰演)会根据K-P线周期定期在改动者交流网站(:blank)上发布即将重合/分离的世界线及其变动率信息,改动者可以选择性的进入所给出的数个世界线中的一个。若改动者在该世界线直接/间接触发的事件足够深远,则有几率获得支线地图开启条件等奖励,甚至可以实现“跳转世界线”,即被转移至另一时间点的某世界线。
***除基点以外的世界线内也存在着等同于改动者交流网站的板块。根据所处世界观不同,形式也不尽相同(比方说现代聊天室论坛体,西幻布告栏之类,甚至在同一世界线中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切记内容也会随着世界观类型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 关于任务模式
有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之分。
主线发展(即纵向发展)自然是首选,改动者整体的主线进展正是推进剧情的主要方式(也是产生分岔结局的主要因素)。
同时,改动者也可以就各个世界线中自己感兴趣的细节展开叙述(系统会进行辅助提示),也就是支线任务(即横向探索)。比如在O层A地区(x,y,z)坐标处有一栋疑似研究院/通讯中心的超现代建筑废墟,系统会给出特定的进入条件(例如研究所磁卡/钥匙/撬棒等,可以通过优秀的设定或者任务奖励获得)玩家便能进入该地点并且自由发挥。支线地图的探索文,作为该地区的设定补充,会提供专门板块以供上传。支线地图中,关于某一个地点的细节具体到一定程度,系统会提供下一相关地点进入方式的提示。
由于每条世界线都有鲜明的特色,所以专爱某种风格的写手可以多次选择特定世界线,完成主线任务后进行横向探索,且横向探索的进度亦会影响到纵向的主线发展。
>> 关于《改动者手记》
改动者在偏差周期结束,回到现实世界后会通过各种方式接受到神的使者的总结信息(如宣传文内所示),随后必须登录改动者交流网站(:blank),以改动者的第一人称自述在本次前往的世界线中发现和感受到的各种事物。(在后期如果和其他改动者组队行动的话,小队成员探索结果没有太大差异可以只提交一篇手记)
手记存在的目的便是方便之后的改动者了解你在某片区域设定的新细节。因此各位在手记里务必带上所有你觉得必不可少的重要设定。
先来后到,如想前往的区域已有其他改造者探索过,则以他人提交的手记内容作为探索的基础。
***> 手记内请尽量不要一次性添加太过具体/宽泛的设定
打个简单的比方:
“《YY的探险者手记:21》
我在P层世界A地区(x,y,z)坐标发现了一座疑似通讯中心的超现代建筑遗骸,和小伙伴xx凭借上张地图通关得到的钥匙进入了设施遗址内,刚进去就被1L干涸了的血墙及数万台杂色的全息荧屏吓了一跳!xx还在角落拾到了一张工作人员的身份识别卡,这个名为塞托罗夫的实验员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都出现了乱码…总之我们打算先在O层虚拟网络覆盖的地方征集队友过后再深入进去。总有种不详的预感啊…… ——YY”
此后如果有其他参与者想要进入该遗址就必须遵照YY所设定的“1L有血墙和数目惊人的杂色全息荧屏”、“研究所工作人员有身份识别卡”等预先设定。
参与者在初期请依旧以世界线设定为主要目的。
***务必注意:请不要为了设定而设定。行文人称不限,但请将你角色的第一视角作为探索和设定的主视角,角色在新世界线一个周期内的行动范围有限,不能为了让自己的设定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次性对整个世界线进行大规模设定。
简单的正面范例:“待一阵晕眩后回过神,我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片了无边界的废墟中。(此处省略环境描写),(省略心理描写)。茫然地沿着坍塌石像向前摸索,瓦砾堆中有个闪着光的物体,(各种省略),我轻吹去徽章表层的灰尘,只能隐约辨别出“Saint ??"的字样(省略细节描写)……”
简单的反面范例:“N线由XX大陆、XX之城与XXX构成,而我位于的XX大陆以漫无止尽的灌木丛著称,……(等各种客观视角设定)”
若出现反面范例中所示的设定文,系统会提出警告,全员可无视。
>> 关于文字
为了体现文字的趣味性,每次(主线)任务都会加上不同的限定。
例如:
任务附带着数个关键词,每篇任务文都必须提及关键词
支线地图的进入条件是一道谜题,要求你文章第4-8章节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谜题的答案。
组队限定任务中,队员A文章的第一句话与B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和C文章的第一句话合起来是一首诗歌的某段诗词。
等等……
=第一弹宣传的可公布情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继续关注T-IW纯文字企划!欢迎各位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各位有时间,麻烦回复下所有吸引你的和你不感冒的设定吧。=
T-IW系列纯文字企划弟一弹——《Tera-Infinity World:1%》
>>企划宣传
第一阶段-[T]
《序章(α)-Tableau》
刚才那是……什么?
耳鸣、晕眩,好像又有点反胃。
想要移动,身体才像是刚刚解冻般,生硬地发生了位移。
骨骼发出了“咯咯”的声响,极速的心跳,在头颅间回荡。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我的家吗?
液晶显示屏,刚开封的盒装果冻,僵硬的手尚握着白色的塑料勺。
正午的艳阳印过格纹窗帘打在缩小的瞳孔上,蝉声喧嚣。
不自觉调起进度条,电脑荧屏上影视剧的画面已超出了自己的认识,但似乎,又只是错过了几句台词。
只过了一分钟?明明刚才我还……
赤、黑、银、蓝交融绵延。
哄笑、嘶吼、鼻息、轻语此起彼伏。
木香、铁锈、血腥、酒气涌入鼻腔。
现实中绝对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直感。
不小心睡着做梦了吗?
装备着精致甲胄的飞龙悬于利齿的腥臭唾液滴落在手背时粘稠的触感;
躯干附加起令人自豪的重量同时,身后银甲的圣官抱臂爆发出豪迈地笑声;
与同期加入圣骑士团的他们,在璀璨到犹如天明的星空下眺望红土尽头绵延的绿色植被。
不……这绝不是幻觉!!
“嗡嗡——”
调成静音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颤抖着的双手捧起矩形的电子产品。
非日常的新信息。
“欢迎回到基点。
在初次世界线叠合间隙,您前往的是偏差值=-1.26的N线。期间您的行为,造成了世界线变动率正向增加0.016。请登录网址(:blank)提交本次《改动者手记》。在网站内您能关注世界线变动的最新情况,也可加入聊天室和其他改动者进行交流。
期待您的下次表现。”
“发件人:神的使者”
[可公布客观背景设定]
由于[进入第二阶段后解锁]的原因,遭受强行干涉的客观世界定律增添了新的设定。
> 将当下所处的现实世界,公元2016年,定为基点,以原子结构式的K、M、N、O、P层为由内核向外扩展的五个放射性圆环世界线的模型,现实世界这一平面与有规律地做圆周运动的原子结构层按照一定周期相交,各层周期不同。
> 在叠加周期内,K、M、N、O、P五层世界线中的不定数层与现实世界逐渐重合,“世界线偏差值”或正或负地叠加在基点上,正向叠加象征着向未来迈进,负向则回溯。
> 改动者(即企划参与者)是来自现实世界基点的人,受到偏差值的无差别影响从而进入另一条世界线(企划参与者可自行选择是否受到影响)。届时其记忆、潜意识等都会将自己归为原本就存在于这个世界线的人(例如在P线里,潜意识会将自己定义为人造人,试验体,变种人,尖端科研人员等等;交错偏差到其他世界线,不可思议的穿越者、魔导公会会长、海贼商贩等等只要符合该层基本设定皆可)
>> 企划初期每个改动者在其他世界线的自定义身份不能变化。
> 偏差绝对值越小,真实的、现实世界的记忆便恢复的越多,完成该世界线内主线支线任务的几率也就越小,横向探索的时间同样会减少,因此对该世界线的变动率影响也会变的更小。
☆ 改动者在K-P世界线里直间接引发的事件(包括任务范畴)若对该世界线变动率影响的足够深远,那么改动者的行为甚至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同时也有可能被转移到另一条世界线。
随着世界线运动,偏差绝对值越来越小(即越来越接近现实,周身环境也越来越向现世环境靠拢),叠合周期结束后改动者全部回到基点,回到现实世界。
>> 在其他世界线与现实世界中时间的流逝速率不同。
> K-P五层,每一层都有截然不同的地形、生态系统和文化等基础背景,基本风格对应如下。
[所有Eg.只是举例并非世界观设定,例子偏向争端,参与者设定的世界线可以十分和平]
现实世界-并不科学的科学向(类似命运石之门等)
[每人都有可能受到偏差值的影响但若偏爱现实风作品也可作为研究人员/爱好者/???在现实中对世界线偏差进行研究或进行相关活动)
K线-魔幻向[关键词:魔法融入日常生活的幻想世界](类似妖精的尾巴/龙之谷等主流魔幻)
Eg.“魔导协会在极北大陆的分部将在圣冰素魔道学者的帮助下设……该死!那家伙又忘了给火元素施放定时休眠法术了!……会长送的高级食材啊……”
M线-童话向[关键词:犹如童话般充满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世界](类似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Eg.“你知道吗?在灰白之森南面的燃烧湖底沉睡着星辰的碎片,一定是闪亮亮的吧!如果交给金银山里的长着鹿角和鳞片的工匠说不定能铸成世间最美的誓约之结!”
N线-西幻向[关键词:古欧风铁与血的幻想世界](类似魔戒等)
Eg.“精灵猎队与矮人十字军大张挞伐的进程迫在眉睫!所有高贵的圣骑士们啊,举起圣剑,为了我们伟大的联盟,备龙、出征——!”
O线-奇幻向[关键词:蒸汽朋克+宗教 科技和神学交融纷争的世界](类似最终幻想等)
Eg.“A部队的十六艘蒸汽飞艇已于时间神教廷所在岛屿边境成功着陆,隶属于冒险者公会的冒险者们将凭借最新技术压缩蒸汽进行突入。是时候让那帮信仰着子虚乌有的蠢货们感受到技术的力量了。”
P线-科幻向[关键词:超现实未来幻想世界](各类科幻作品均可借鉴)
Eg.“抵达目标地点后迅速建立屏障,资源采集任务完成之前在驻扎区域建设临时通讯站,人造人部队,解散。”
并不知晓 神 的存在与目的的改动者们将在不同世界线受到神的使者的引导,最终将世界引向……?
参企细则(不完整版):
整个企划分为[T][E][R][A]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未定)个章节。新阶段开启时会公开新增情报,阶段结束时则会对所有参与者在本阶段中的表现作出总结。对世界线变动率改变最大的参与者将会接受特殊剧情任务和特殊剧情奖励,第二到四名则可获得对应奖励,届时会发布细则。阶段剧情等越延后越能体现出参与者对世界的改动,整个故事的结局自然由各位的表现决定。
***每位写手上传作品的标题必须按照格式
[世界线](类型)《文本标题》
例如:[N线-1.26](日常/主线剧情/横向探索]《???》
神的使者(企划主饰演)会根据K-P线周期定期在改动者交流网站(:blank)上发布即将重合/分离的世界线及其变动率信息,改动者可以选择性的进入所给出的数个世界线中的一个。若改动者在该世界线直接/间接触发的事件足够深远,则有几率获得支线地图开启条件等奖励,甚至可以实现“跳转世界线”,即被转移至另一时间点的某世界线。
***除基点以外的世界线内也存在着等同于改动者交流网站的板块。根据所处世界观不同,形式也不尽相同(比方说现代聊天室论坛体,西幻布告栏之类,甚至在同一世界线中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切记内容也会随着世界观类型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 关于任务模式
有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之分。
主线发展(即纵向发展)自然是首选,改动者整体的主线进展正是推进剧情的主要方式(也是产生分岔结局的主要因素)。
同时,改动者也可以就各个世界线中自己感兴趣的细节展开叙述(系统会进行辅助提示),也就是支线任务(即横向探索)。比如在O层A地区(x,y,z)坐标处有一栋疑似研究院/通讯中心的超现代建筑废墟,系统会给出特定的进入条件(例如研究所磁卡/钥匙/撬棒等,可以通过优秀的设定或者任务奖励获得)玩家便能进入该地点并且自由发挥。支线地图的探索文,作为该地区的设定补充,会提供专门板块以供上传。支线地图中,关于某一个地点的细节具体到一定程度,系统会提供下一相关地点进入方式的提示。
由于每条世界线都有鲜明的特色,所以专爱某种风格的写手可以多次选择特定世界线,完成主线任务后进行横向探索,且横向探索的进度亦会影响到纵向的主线发展。
>> 关于《改动者手记》
改动者在偏差周期结束,回到现实世界后会通过各种方式接受到神的使者的总结信息(如宣传文内所示),随后必须登录改动者交流网站(:blank),以改动者的第一人称自述在本次前往的世界线中发现和感受到的各种事物。(在后期如果和其他改动者组队行动的话,小队成员探索结果没有太大差异可以只提交一篇手记)
手记存在的目的便是方便之后的改动者了解你在某片区域设定的新细节。因此各位在手记里务必带上所有你觉得必不可少的重要设定。
先来后到,如想前往的区域已有其他改造者探索过,则以他人提交的手记内容作为探索的基础。
***> 手记内请尽量不要一次性添加太过具体/宽泛的设定
打个简单的比方:
“《YY的探险者手记:21》
我在P层世界A地区(x,y,z)坐标发现了一座疑似通讯中心的超现代建筑遗骸,和小伙伴xx凭借上张地图通关得到的钥匙进入了设施遗址内,刚进去就被1L干涸了的血墙及数万台杂色的全息荧屏吓了一跳!xx还在角落拾到了一张工作人员的身份识别卡,这个名为塞托罗夫的实验员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都出现了乱码…总之我们打算先在O层虚拟网络覆盖的地方征集队友过后再深入进去。总有种不详的预感啊…… ——YY”
此后如果有其他参与者想要进入该遗址就必须遵照YY所设定的“1L有血墙和数目惊人的杂色全息荧屏”、“研究所工作人员有身份识别卡”等预先设定。
参与者在初期请依旧以世界线设定为主要目的。
***务必注意:请不要为了设定而设定。行文人称不限,但请将你角色的第一视角作为探索和设定的主视角,角色在新世界线一个周期内的行动范围有限,不能为了让自己的设定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次性对整个世界线进行大规模设定。
简单的正面范例:“待一阵晕眩后回过神,我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片了无边界的废墟中。(此处省略环境描写),(省略心理描写)。茫然地沿着坍塌石像向前摸索,瓦砾堆中有个闪着光的物体,(各种省略),我轻吹去徽章表层的灰尘,只能隐约辨别出“Saint ??"的字样(省略细节描写)……”
简单的反面范例:“N线由XX大陆、XX之城与XXX构成,而我位于的XX大陆以漫无止尽的灌木丛著称,……(等各种客观视角设定)”
若出现反面范例中所示的设定文,系统会提出警告,全员可无视。
>> 关于文字
为了体现文字的趣味性,每次(主线)任务都会加上不同的限定。
例如:
任务附带着数个关键词,每篇任务文都必须提及关键词
支线地图的进入条件是一道谜题,要求你文章第4-8章节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谜题的答案。
组队限定任务中,队员A文章的第一句话与B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和C文章的第一句话合起来是一首诗歌的某段诗词。
等等……
=第一弹宣传的可公布情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继续关注T-IW纯文字企划!欢迎各位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各位有时间,麻烦回复下所有吸引你的和你不感冒的设定吧。=
http://elfartworld.com/groups/932/
假如将每一个故事都比作一滴水,当它们汇聚在一起,就有了海洋。
所谓的历史,正是由无数的故事组成,即使并非神明,但只要我们的手中还有笔,就能够创造世界。
[T-IW系列文手企划]
+以虚构的世界观为背景进行的开放性创作+
+开放性世界观 相关创作中增补的设定会纳入大世界框架下+
+纯文手限定+
*性质上来讲近似于九州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如果人数够多的话也会增加一些新的互动方式(虽然并不觉得会有人来)

呵呵
系统提示有超过我10级的怪出现,这狼王至少也有20级了吧。
阿山转身想要逃走,我大声叫他快去捡回武器,自己勇敢地向狼王冲去,狼王算什么,想当年……咦?铁剑砍在狼王头上,不掉血!
我明白没有希望取胜了,只能帮阿山牵制它,只要阿山捡回武器,我损失经验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准时机,忽然从侧面跃到狼王背上,然后双手紧紧扣住狼王的脖子。
狼王烦躁地甩着身体,想把我甩下来,不过哪有那么容易,我可是身经百战的骨灰级玩家,随便它怎么剧烈的运动,我的心都不会惊慌,双手也不会有丝毫放松,不过,虽然暂时没被它甩下来,我的HP也随着剧震一次损失10点的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HP快没了。我一边用意识下着吃血药的指令,一边大声叫阿山快跑回村。
阿山目光中闪过一丝感动,不过他知道救不了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转身逃走了。我继续箍着狼王的脖子,拼光最后一瓶血药,最终被狼王挂掉。
掉到9级,我的10级任务便被系统取消了,练了两小时,升回10级,村长也不再给我任务了。
清除了村子里的几只野兽,“村卫”的工作完成,休息一下。
这时阿山向我走来,说了声“谢谢。”然后准备离开。
我可不能放过他,平时那么冷漠的人能说出谢谢,证明他对我的好感非常高了,怎么也要跟他要点好处吧。
于是我向阿山提出学习技能,阿山同意了,不过居然还要收费。
阿山会两种技能:“陷阱术”和“切割术”,虽然据他说只是“象征性”地收了100个铜币,但我的钱袋也马上见底了。
接下来,在我和阿山六个小时连续不断的努力下,村子周围的野兽减少了很多,很少有进入村子的了。
村民甲一家种田时不再受到野兽骚扰。于是,村子的属性上升,武力加2,治安加3,生产加1,环境加1。与村民甲一家人重新对话,以前经常提到的“迁居”字眼基本消失了,让升到13级的我有不小的成就感。
游戏中轻松了一些,我现在特别想了解现实生活的事,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变成什么样了。
可是系统提示,玩家50级以前不能使用游戏内置的论坛。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基本是不能离开游戏的。而且这个游戏没有管理员,一切由电脑控制,不能反映情况。现在的我,就跟玩一款单机游戏没什么两样嘛。
现在,我最渴望的就是开通村里的传送阵了,好想见到“活人”啊。不过魔法10的标准是不容易达到的,有村长这个魔法师,村子也只有一点魔法,就算我学会魔法,最多不过再加一点,等村子有10个魔法师,那不知要到哪年。
我向每一个人都反复询问“魔法”“传送阵”这些关键字。终于,见多识广的小贩告诉我,在往邻村去的方向,有个叫蓝玉山的地方,藏有一种魔晶石,据说可以增加村庄的魔法值。不过,那座山离我们村子有一天以上的路程,路上高级怪不少,暂时还不适合我去。
就在我全力冲级准备到蓝玉山找魔晶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我居然病了!
从前的游戏中,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玩家会有生病这样的状态。在游戏中生病一点都不好受。
村长告诉我,附近的半边崖有一种叫赤果的草药可以治我这种病。因为没人帮我,我只好咬牙拖着不到平时三分之一能力的身体上路了。
三个小时,我经历了这一生中最艰苦的三个小时,我终于找到了“赤果”。看着红红的小果,我几乎要流泪,就算是从前杀死一只终极BOSS,爆出神器,我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开心。《创神世界》,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游戏世界啊。
吃下“赤果”,能力值一点点回升,我又收集了一些备用。 回城的路上,虽然我的力量只恢复一半,不过杀怪的感觉已经是说不出的痛快。
我这时发现,自己的作战技巧,在逆境中磨练之后,竟然又上升了一大截。在兴奋之中,我升到了14级,我惊讶看着自己获得的奖励:力量5,体质5,敏捷5,精神力5,游戏中患病机率下降为万分之5。
惊喜,绝对的惊喜,一次20点的奖励点数,我知道,我与其他同等级玩家相比,由先天不足带来的差距已经被缩小了。以同级玩家来说,我现在应该算中等水平了吧。
这时系统正在报告,“恭喜玩家撒旦第一个升到30级,奖励声望1000。”
我有些惊讶,计算一下,从上次系统报告这个玩家20级到现在将近三十小时,升得也太快了,我现在14升15需要的经验来看,估计要三小时才能升一级,而越到后来,升级速度越慢啊,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卖掉路上切割的战利品,这次虽然能力升得多,不过血药损失惨重,我的财产亏了一半。重新买好药,趁着病还没好透,向18级猛虎的领地扑去。
三个小时后,终于升上15级,看看奖励,下降了一些,力量4,体质4,敏捷3,精神2,但总数达到13点,比普通玩家最高的12点还高,又缩短了与别人的差距,感觉真爽!
没有忘了找村长学魔法,村长只能教两个魔法:“治疗术”和“火球术”。
魔法技能比生活技能贵得多,或者说村长比阿山他们贪财得多?一个就要我1银币,三小时打到的虎皮虎骨算是白捡了,连虎肉都没剩几块了。
学到两个魔法,MP自动加了10点,现在我HP75,MP30,每放一次魔法需要10点MP,在小贩没有魔法药水卖之前,没办法大量使用,不过看着小火球每次打怪20血的威力和治疗术每次加血20的美妙,我的心情还是相当愉快的。
现在不用拿石头引怪了,放1个小火球,然后原地等着猛虎过来,拼死它之后,我还有30的血,加一个治疗术,血就有三分之二了,慢慢走一会儿,找到下一个目标,血涨满,蓝也回得差不多了,再发火球,如此循环,轻松之极。猛虎现在也成垃圾了,我完全不用费药。
不过我只是用这种方法放松自己紧绷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神经,为了得到更高的成长,我必须增加战斗难度,换个说法叫“自虐”?
拼杀了四个小时,终于升到16级,这一次除了力量3,体质2,敏捷2,精神3,HP+10之外,由于使用魔法,MP成长速度有了明显提升,也达到了5。
看着天空左上角显示的游戏时间,七个小时我升到10级。
回到村子,村长交给我10级的任务:“杀死20只老虎”,我苦笑一下,我是侦查过老虎等级的,18级,不用说,我又破不了防,现在杀不了。
我刚要出门,村长叫住了我:“年轻人,由于你为本村清除了大量的野兽,我想请你担任本村的‘村卫’,怎么样?”
我不由大喜,便问道:“村卫要做些什么?是不是只能为村子站岗,不能自由活动?”
“不是,除了尽量清除进入村落范围的野兽之外,你可以自由活动,你在村里杀死的怪物,依等级和数量给你发薪水并记录你对村子的贡献值。
“那我能得到什么装备吗?”“嗯,本村很穷,我这里只有一把铁剑可以给你,另外还有一个‘村卫’的徽章,一张本村的属性表。”
铁剑锈渍斑斑,查看属性,攻击+7,已经不错了,也许我能破16级怪的防了。
村子的属性表,是我以前玩的游戏里没有的,显示本村属性:失落之村,人口7,武力4,文化2,魔法1,经济1,治安1,生产1,环境1。村落综合实力排名10666666,看来游戏中有一千万个村落啊。
仔细琢磨刚才村长的言语,我认为他的智能相当高,而且对我的好感度似乎也提高了很多,决定再去打听一些消息。于是回去向他询问了技能与魔法等问题。
村长告诉我,由于村子的衰败,村民流失。现在剩下的人,村民甲和村妇甲加上小孩甲这一家人,职业是农民,只会“种植术”和“饲养术”;酷酷的那个NPC阿山,职业是猎人,应该有不少技能,他老婆阿水则会最初级的“缝补术”。
村长则是魔法师,不过他告诉我,等级15级才可以找他学魔法。
村长还告诉我,村落是可以发展的,村子属性上升了,会有一些流浪汉和更落后村落的人迁来。另外,如果村子的魔法上升到10,传送阵可以恢复,便能直接到附近最近的村子去了。
我走出村长小屋,决定再跟其他村民好好聊聊。
村民甲一家三口的智能显然很低,何况种植术和饲养术我也没兴趣,问了一会儿没有新发现,就放弃了。
阿山夫妇是有名字的NPC,智能就明显不同了,所以我把工夫全放在他们身上。
虽然阿山老兄还是比较冷漠,不怎么理我。不过由于我已经是“村卫”身份,帮村里杀怪也得到大家一些认同,因此还是从善良的阿水那里了解到阿山的情报。
阿山前些天打猎时,遇到一只狼王,他慌乱中把武器都丢在草原上了,阿山没了武器,不能打猎,只好等小贩下次从城里给他带武器回来。
我看阿水挺好说话的,就把最近得到的兽皮拿出来,问她能不能帮我制作一些东西,当然,我是付费的。
阿水帮我做成了一套防具:防2的牛皮衣裤,两个防1的牛皮护腕,防1的狐皮帽,敏1的狼皮靴。
我穿上这套装备,防虽然高了些,但因为笨重又不合身,反而降低了我的敏捷。
我试探着问能不能学习她的技能,想不到她真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学到了我的第一项技能:“缝补术”,不过不可以升级。
再与阿山对话,我反复提到“武器”“狼王”等关键词,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阿山被我搞定了,向我说出他“很想找回丢失的武器”这一暗示性的话语。我当即提出,只要他给我带路,我就帮他找回他的武器。阿山非常勉强的答应了。
花半小时时间,我给阿山制作了一把木弓,由于没有木匠技能,木弓仍然是攻击1点,至于箭支,阿山那里还有不少。我又把自己淘汰的铜剑借给阿山,然后一起上路。
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一片不大的草原。
阿山的记忆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很快就找到失落武器的地点,远远看去,武器都在,太好了!
就在我们为行动如此顺利而欢喜的时候,一阵腥风吹过,一只巨大的银狼出现了,狼王!
处身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这也算是一个村子吗?几间残破的民房,村外树木枯黄,野兽出没其间,一派荒凉的景象。但我根本没心思去细看周围的环境,现在我失去所有,但我还拥有游戏世界,无法回到现实,我就要在游戏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将纷乱的情绪强强压在心底,虽然心依然疼痛,但我的理智已经逐渐恢复,慢慢查看着游戏的帮助菜单。
我所在的这个村叫“失遗之村”,处在整个大陆西北角,是安排给最贫困玩家的村子之一。
看看自己一身垃圾属性,再看看包裹里只加攻击1点的木剑和加防1点的布衣,要指望用它们升级,恐怕有点困难,还是先问问NPC看有什么东西送我不。
按游戏惯例,先找村长了解情况。
白胡子村长告诉我,由于村子太穷,所以只有一个小贩兼任杂货商和药品商,另外还有两户人家共五口人。
问村长有新手任务没有,村长说需要我升3级才能接第一个任务。
再找到小贩,小贩那里只有最便宜的低级血药卖,每个加20点血,要10个铜币,可我只有5个铜币,穷人就是命苦啊。
再问其他NPC,他们都很冷漠,基本没什么语言,也许是因为我被系统判定为很普通的魅力值5,影响NPC好感度吧。
看着周围逼真的场景,每一块石头每一根草我都可以使用,不像从前游戏里那些背景只能看不能动,我决定利用这一点好好设计战斗方法。
从树上选了一根树枝,做成木棍,捡了块石头,将木头削尖,做成一支长矛。系统果然没让我失望,经过计算,发出提示:“由于玩家君临天下的创造力为10,因此制作成功一支铜器长矛,由于没有‘木工’技能和‘长武器制作方法’,长矛没有加成属性,攻击力1点。”
做完之后,我四下眺望,终于在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理想的练级对象:山羊。
山羊的敏捷比我高些,但目标比较大,我很快就拟定出了战法。足足耗了一分多钟,才杀死了一只山羊,还不错,属于越级杀怪,得到10点经验,不过升1级需要100经验值呢。
半个小时后,扣除死亡减去的经验,我终于升到了2级。
系统提示,“由于君临天下是‘特别成长型’玩家,每次升级获得的点数不固定,根据玩家本级表现。君临天下获得力量1点,敏捷1点,精神力1点,HP+2。”
我查帮助知道,这个游戏中普通玩家每升一级,力量、体质、敏捷、精神四项都有机会上升1—3点,偶尔还会有某项属性能达到4、5点的。
幸运的玩家每级能有12个点数甚至更高,最差也是4点,而我这个“特别成长型”,名字好听,却只获得3点属性,比常人还慢,有没搞错?
冷静地想想,系统说“根据玩家表现”,也许是自己付出的努力不够吧,毕竟杀山羊的难度比较低。
在打怪的同时,没忘了挣钱。我按照惯例,切割山羊的尸体,得到羊肉材料。小贩那里以1个铜币的价格收购,我总算挣到十几个铜币,买下两瓶血药。
有血药垫底,可以适当挑战“高难度”了。我双手分持木矛和木剑,先是用石块引来野狗,然后用木矛横扫或刺,野狗闪过木矛近身,我就用矛身格档,用木剑还击。
杀到第六只野狗时,我不得不喝了两瓶血药,野狗身上没有东西卖钱,只好再杀山羊,得了羊肉卖了,再买血药。
艰苦啊,太艰苦了!终于,随着我动作的熟练,野狗再难伤到我要害,我损血越来越少,当我升3级的时候,系统给我奖励点数为力量1,体质1,敏捷2,精神2,总共6点。
想起村长说3级有任务给我,赶紧去找他,没想到,任务居然是“杀10只野狼”。
晕倒,这可不是我这级别能做的,我13点的血量,只够野狼抓两下的。
但是我没有气馁,为了3级任务的奖励,也为了越级杀怪那丰厚的经验,我决定再想办法。
很快,我想起了以前游戏中猎人的技能“陷阱”,虽然我现在没有这个技能,但这游戏仿真度这么高,应该会允许玩家利用地形杀伤怪物的。
四下寻找工具,正好看到村民甲一家人在种地,连忙上去搭讪,最后商量好,给他们2个铜币,租来一把锄头。
花了两小时,挖了个1米多的深坑,下面插上我用木头削出的尖刺,在深坑上铺了从破屋中收集到的草席,用泥土掩盖一下。忽然传来系统提示:“你制作陷阱成功,由于没有陷阱技能的加成,陷阱本身伤害为1,困兽能力为1。”
想不到这个系统智能化程度这么高,这么原始的一个坑它都能认出是陷阱,于是我开始用石头引狼。
第一只野狼落下陷阱后,我马上搬来一块块大石往坑里扔,把它活活打死。
靠着我以前的经验与技巧,一小时后,又9只野狼先后被我引入陷阱砸死了,切割尸体得到十张狼皮。
回村交任务,村长给了我一把铜短剑,攻击加3,但我更欣喜的是终于有了一把利器,以后制作工具省力多了。
拿着铜短剑,卖掉九张狼皮买药,另留下一张钉在一块木板上,系统提示“你制作成功一面皮盾,由于没有‘皮匠’技能,皮盾没有加成属性,防御力1点。”
有了新武器,信心倍增,带着几个血药,开始正面搏杀野狼,直到用完血药,总算杀死三头野狼,升到4级,得到力量3,体质1,敏捷2,精神1,一共7点。
看到这样的战绩,我微微一笑,作为职业玩家的我,向来很在意自己在游戏中的地位。有了希望与目标,力量和信心好象也一下子增强了,我不再犹豫,开始疯狂地冲级。
黑暗,无尽的黑暗,没有思想,没有希望,我在这黑暗中一动不动,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让我知道,自己还是存在的。在这黑暗中,时间似乎也静止了,一切都是不变的、永恒的。
黑暗中出现了一点灰色的光,我看着那光,从光中感受到力量,渐渐的,我的意识可以移动了,我慢慢地向光飘去。
终于到达了光的源头,像是黑色的墙壁上的一个小孔。我动了一下意念,然后整个意识从小孔中飞了出去。
久违的光明与色彩啊,我现身在一个圣殿里,圣殿中央站着一个白衣天使。
天使向我微微一笑:“你好,亲爱的玩家,欢迎来到《创神世界》。”
花了至少一个钟头,我才开始平静下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是从无边的沉睡进入到了梦境吧?哎,自从我成为职业玩家,睡梦中出现太多次游戏画面了。算了,我不要做梦了,快醒来吧。于是,我向天使说道:“我想退出游戏。”
天使点点头,我重新回到黑暗,我呆住了,为什么,我退出游戏没有出现在自已的家,还是这黑暗的空间里呢?
我再次跟着那光回到刚才的圣殿,无奈,我向天使点点头:“我想进入游戏看看。”天使手一招,我面前出现了一张巨大的羊皮书:《游戏协议》。
签完协议,天使请我取名字。“君临天下!”“取名成功。下面进行玩家生理分析……”
终于,扫描结束,天使列出一张表格。我看了一眼,笑了,这真的是在做梦啊,看看这个扫描结果吧:
HP10——玩家血量。
MP1——玩家法力。
力量1——影响玩家物理攻击、物理防御等。
体质1——影响玩家物理防御、魔法防御、回血等。
敏捷1——影响玩家移动、命中、闪避等。
精神1——影响玩家魔法攻击、魔法防御、回蓝等。
其余属性隐藏。
天使想了想说道:“由于你属性总值太低,符合游戏的‘弱者照顾条例’,请问你是否接受游戏资助点数?”
我大笑:“我倒要试试看自己这个垃圾属性怎么玩,不用资助!”
天使愣了一下:“你确定?那么,根据条例另一方案,设定玩家君临天下为‘特别成长型’,是否接受?”
我这次选了接受。天使请我选择职业,可是,在她一挥手之后,我眼前没有任何战斗职业和生活职业的图示。
天使呆了足有5分钟,终于说:“由于你没有任何一样属性超过2,没有适合的职业,程序经过思考,临时增加隐藏职业‘学徒’,可以学习所有职业的技能,但技能只可升到见习十等。”
嘿,全职者,越来越好玩了,现在我开始希望不要那么快醒来了,忽然,大脑象是被一道闪电击中,眼前一道白光,我被传送到了游戏世界。
本企划以fate stay night为模型蓝本。企划主舞台为架空的魔法与科技世界,在此企划中教会不再作为监督者观察圣杯战争,而是作为谋划者促进圣杯战争的行进,而与教会对立的帝国,以及自由者们夺取了圣杯的名额,与相当于幕后黑手的教会,展开了时长达5个月的战争。
好吧其实是一群人打打闹闹的故事www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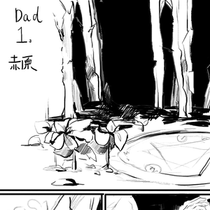
堆堆凯特的人设
【核心】坏心眼
【说明】所以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喜欢说笑话,然后等到别人开怀大笑的时候一脸冷漠而已。
【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存在的,因为太无聊开始创世玩,然后自己进入不同的世界寻找乐趣。所以是创始者。
【概括】
1.因为存在太久了,所以外表看起来是个人类,内心却已经和老人没什么两样了。
2.看起来很开心的时候可不能算开心,说不定他只是在“感觉”有趣而已。
3.有时为了让其他人开心,会干一些奇怪的事情。
4.喜欢耍帅。
5.面对不认识的人很彬彬有礼,如果熟了的话估计会变得很放荡不羁了吧。
【贯彻一生的目标】
1.“凯特,成为正义吧。如果是你……不死的你……就一定可以……”
【你的名字】
“喂你这家伙没名字啊??不是吧,你看起来都20岁了啊?哈哈哈哈。”
“哼,长得成熟怪我吗,你还是先去死吧。”
“等等等等!!!!会死人的!真会死人的!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吼……完全不感兴趣……”
“嗯…………………………………………叫凯特怎么样。”
“……我就知道不该期待的。”
——————————————
“转眼我也已经60岁了啊……虽然我早就发现了……你这家伙……从我们相遇那天开始就没老过啊。”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哈哈哈哈!咳咳……咳……你讲吧,凯特你的笑话我可不期待啊。”
【相遇】
一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回过身发现,原来不只是一个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同伴。但是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仅仅几秒的时间,世界就会天翻地覆。不……假如能创造出所有人都不会死亡的世界会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自己身旁了呢?抱着这个想法,凯特开始着手于那个世界的创作。
【戏剧性结尾】
在那个世界被破坏以后,凯特的身体便四分五裂了,恐怕他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迎来这样的死亡。
【我是伟大的创始者,制造者,主宰者,可是我却没办法救一个人类,这件事让你感到可笑吗?】
【不,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你就是创造出我的人。】
直到最后,赤原这么说道。


原创世界观“试验型理想时空”,简称桃源。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主要用于堆砌作为创世神的我对于理想世界的想法。
1.与身边多数人的认知相反,轰代防在学生时代学得最差的科目恰好是他最喜欢的政治。
2.轰代防对于法律条文,不,概念性强的文字叙述段落的死记硬背能力很差,为此曾经怀疑自己的智商。
3.是政治老师的鼓励和信任让小轰找回了学习的自信。
4.轰代防非常容易信任他人或使他人信任自己;但与此相反的是,唯一始终怀疑轰代防作为辩护律师的才能的人还是他自己。
5.轰代防从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律师,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合格的成人;他时常感叹自己“还没有长大就已经开始老了”。
6.轰代防至今对于父母纯粹为了缓解家族矛盾而实行的毫无感情基础的所谓“和亲”怨气滔天;能摆脱他们不休的纠缠就是轰最大的心愿之一。
7.为什么是“之一”?因为其他“最大的心愿”还有不少,包括但不仅限于“和王孙城小姐结婚”、“所长快点回来吧”、“成为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之类……
8.轰代防最大的恩人除了好心的政治老师就是他可亲可敬的所长大人。是所长好心收留了他这个四处奔波只为寻找一份“离家最远、假期最少的工作”的可怜的设计系毕业生。
9.然而一年前所长突如其来的离家出走导致整个事务所的天塌了半边儿;当时甚至差点有人这么唱,“蕤宾姑洗,蕤宾姑洗,镇立(律师)事务所倒闭啦!王……”
10.王泥喜法介是轰代防最敬佩(以及感激?)的异世界同行,不为什么。
11.上一条的理由其实是:轰代防其实做过自己去往《逆转裁判》世界观的梦,在事故中被炸伤双腿的他作为证人积极地帮助成步堂和王泥喜,从而和他们一起揭穿了事件的真相。而王泥喜是轰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他救助并且鼓励了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的轰。
12.除了上一条以外,轰代防这辈子基本上没做过什么美梦,真的。因为他睡着时一般并不会做梦,所以……
13.轰代防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做自我介绍,总是不忘自己的朝鲜人身份,哪怕这样说会引来一些人不怀好意的哂笑。
14.轰代防对社会主义(相关的事物)有着超乎想象的认可度。他真的很希望能去贝尔茨克市旅游,或者亲眼见一见金慧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化身),但只要所长还没有回来……
15.生活起居和办公一体化的事务所二楼事实上成为轰代防的私人住所以及唯一(认可)的家,白天一般都被楼梯上的栅栏门锁住。他在这里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曾经的室内设计系学生的特长。
16.轰代防的健康状况确实不是很乐观。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等原因,一直小毛病不断。他尤其容易肩酸背疼和头晕脑胀,甚至有些轻微的高血压。
17.轰代防认为自己“已经老了”的确凿证据就是他的少白头,还有那与多数年轻人格格不入的爱好以及相对来说较为保守的价值观。
18.无论遭遇怎样的痛苦,轰代防总是强迫自己不要哭泣;然而他一哭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对餐巾纸和卷筒纸们来说这是致命的噩梦。
19.人设里说过,轰代防一旦感到害羞就会整个人怔住。具体表现是,他整个人不仅神情呆滞恍惚,而且全身僵直,完全不能动弹。当他冷静下来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但具体需要多长时间呢……
20.从不少方面来讲,轰代防都可以算是个钢铁直男,然而他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即便如此他的异性缘还是出人意料地不错。
21.上一条的实例是,轰代防至今仍然为他的第一位委托人——小学音乐教师中村直子所思慕。
22.轰代防实在无法容忍东海林检察长的“女儿”真琴(Makoto)的怪脾气,直到他和葵青江无意中发现真琴其实是一个既聋且跛的残疾儿童,并且是名为“诚(Makoto)”的男孩子……
23.使王孙城满与轰代防(在私人关系上)达成共识的第一件事是:生、带孩子是比审查疑难大案还要困难一百万倍的艰巨任务,我们承受不起,所以……
24.轰代防与王孙城满正式确立关系必须过远山夕阳这一关,然而不幸的是轰与远山在某个方面一直在互相伤害……
25.像本作中绝大多数的朝鲜裔角色一样,轰代防很能吃辣并且讨厌油腻的食物;他唯一喜欢的西餐可能是奶酪培根披萨,因为那是所长请他吃的第一顿饭。
26.轰代防是非常知恩图报的人,但同时也相当记仇;只要“恩人”开始态度冷淡或者对他不好,他就会迅速忘记对方给自己的好处并且再也不会原谅对方。
27.轰代防不是很清楚某些对他来说不太常见的东西的吃法——他甚至曾经把山竹和百香果直接连壳一起吃下去。
28.轰代防无论对于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非常认(jiao)真,所以他绝对不能接受别人对他撒谎或者开玩笑戏弄他,哪怕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
29.轰代防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自己之所以朋友很少就是因为自己对于感情关系的要求太过苛刻。
30.轰代防头上的三个“鱼鳍”也是头发的一部分,可以根据自我意识左右上下活动;他从中学就已经想要开始留这个发型,付出的代价是被大人“混合双打”外加剃成寸头之后关了一天的禁闭。
31.如果可能的话,轰代防宁可时光永远在他最为自由的大学时代无限循环,永不前进。然而他不知道已经有一个小学生已经实现了他梦想中这样的生活……
32.作为音乐名城蕤宾市的居民,轰代防理所当然也有几样自己所擅长的乐器,那就是钢琴和电子琴,中村直子也曾教他如何演奏马林巴。但他无论如何就是拿吹奏乐器没辙,曾经差点把王孙城家的古埙给弄坏。
33.轰代防的名字就字面意义来讲是“代替(他人)防卫轰炸攻击”,而姓与名则分别是“轰响声”与“代理防卫”的意思。
34.如果把名字的含义作为设定初衷,轰代防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总是无端承受本不应得的攻击的背锅奇侠。
35.每当轰代防没有“今日事,今日毕”,他就会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除了那些由他接手的案件以外。
36.轰代防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填写各种社会问卷,但当他意识到这会泄露他自己的个人隐私并带来潜在的危险以后,他最终没有提交这些问卷真正的答案。
37.轰代防曾经写过一首名为《在违法的边缘引吭高歌》的曲子,结果差点被他的老朋友天海清正(刑警)和东海林慎司(总检察长)请去谈人生。
38.轰代防最喜欢的东方系列音乐是《天鸟船神社的结界》,然而他最常拿来练手的却还是《天使传说》和《御伽之国的鬼岛》。
39.听《天使传说》的时候,轰代防时常会有种自己在宇宙中飞行的感觉,这一点得到了四海大辅的认可。
40.轰代防和人间都市的大多数著名人物基本上都认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记得住他……除了发型以外的部分。
41.轰代防的手机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热门的社交软件,因为刷朋友圈对他来说是很烦很干扰工作的事情,而备忘录、信息和联系人就已经可以解决一切了。他甚至恨不得专门去换成功能简单的老人机,遗憾的是新潮的蕤宾市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42.姑洗镇立律师事务所就名字来看像是——对外宣传上也是——全蕤宾市唯一的公立律师事务所,但真相是——因为身为所长的赤城五岳长期失踪,在轰代防一个人撑不起全局的情况下被镇政府暂时托管。(桃源人间的法律允许政府高层这样做)
43.对轰代防来说,手机摄影永远比专门的摄像机方便得多。他经常联合山冈岚在现场附近出各种歪招花式偷拍取证,虽然这永远都会被天海清正或者叶听言发现……
44.轰代防特别讨厌倒计时,不论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那种煎熬的等待过程给他带来的压迫感不亚于自己对死亡的思考;而他每次作出这种思考,就会觉得自己离终结和死亡更进了一步,毕竟“你的人生已经走过了二十五个年头”……
45.作为一名人民律师,轰代防比起无罪判决更向往的是真相与正义。但不巧的是,除了直子老师以外他遇到的真正无辜的委托人可谓是少之又少;尽管如此,他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向着真正正确的道路前行”,哪怕一辈子背负“队友贩卖机”的败家恶名。
46.轰代防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为自己所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事业而感到后悔。
47.轰代防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收到了来自别的异世界的创世神们的同人的人们。
48.轰代防一直都在为成为真正自信、勇敢、能够独当一面的人而努力前行着。他深切盼望能够战胜被心病所束缚的“过去的自己”,并像信任其他人一样信任全新的自我。
49.轰代防无意中发现创世神大人往往只有在写这些扯淡性质的、看似不那么正儿八经的东西的时候文思如泉涌好似吃足了炫迈一样。
50.“我,律师轰代防,一定没问题的——!!(私、弁護士轟代防、問題ありません——!!)”
宇都宫真由美(Utsunomiya Mayumi,日:うつのみや まゆみ/ウツノミヤ マユミ)
性别:女
种族/民族:人类(大和民族)
身份:中学四年级生
出身地区:人间都市-南日里市
年龄:16岁
生日:10月10日(天秤座)
身高:160cm
体重:45kg
血型:O
亲属及相关人士:宇都宫守路(哥哥)/一之濑明日香,曾良野今荒(朋友,旅伴),兔黄冻(宠物)
外观:是看起来非常适合作为漫画女主角的“普通”美少女的样子,虽然一直尽量保持自己外观上的“非独特性”但不管怎样总能被认出来。棕色及腰长发,M形刘海,鬓发中长,典型的大众发型,(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偶尔会扎成马尾。眼睛是深浅适中的蓝色。身材其实很有料但本人对此缺乏自觉。服饰通常为上衣较短的蓝白水手服,领结红色,在领口与裙沿各有一条白边。低于膝盖的白色中短袜搭配棕色制服鞋。
简介:生活在桃源人间南方重镇——南日里市的“普通女子中学生”,(自认为)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很平凡无奇的存在,除了略长于一般人的名字以外。一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般的故乡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作息和南日里的任何一个中学生一样规律,只是偶尔会在周五放学的路上故意不直接回家而是走到学校后门面对的大路边,眺望缤纷的晚霞与远处南日里的海;她对外面的世界好奇而又向往,内心希望能够“出去看看”但一直没对其他人提起过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拥有着连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会体现在什么方面的强大潜能。如果说杉山智之助是(设定上的)路人男主,那么(还是设定上的)路人女主非宇都宫真由美莫属,虽然这两位仅仅在真由美的果之岛之行中有过一面之缘。
属于永远把未来往好的方面想的、典型的乐天派,具有不亚于塞翁的乐观精神,坚信“否极是泰来的前兆”,总是给人积极向上、活泼开朗印象的女孩子,心很宽,不是很容易生气或者难过,但在某些关键的方面也很有原则。非常诚实且说到做到,学不会说谎和立flag,因此很受朋友们信赖。说话做事略微有点冒失和直来直去,但因为不犯大错不作大死或者道歉及时,往往会被宽容并原谅。成绩一般,对背课文十分头疼。或许是受一贯规律的作息所影响,宁可找点什么事情做也不喜欢闲着,不管什么都能做一点但又不是很精通。喜欢三明治和汽水,不喜欢令人咀嚼困难的食物。
总想尽可能地做一个不被注意的、默默无闻普通人,无声无息地融入茫茫的人海,但同时也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与认同,却不是很清楚如何调整这样的矛盾。很容易就能适应新的环境与人群,人缘出乎自己意料地不错,在学校和邻里都有不少能说得上话的好朋友,但只有住在同一楼层的、低自己一年级的一之濑明日香算是真正知心的挚友。真由美和明日香在不用上学的日子里经常互相串门,就她们喜欢的东西以及南日里乃至整个人间都市最近发生的大事进行深入交流。在四年级结束后的第一个暑假之后与明日香一起去海边游玩并捕捉了一只兔黄冻作为宠物。在看到广袤无垠的大海以后,真由美果断接受了明日香关于环游世界的建议,从此开始与明日香还有隐藏身份的时间之神——曾良野今荒一同进行周游整个人间主大陆(包括为动物所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的活动,主要负责摄影与旅途记录。
一丰田实穗(Ichitoyota Miho,日:いちとよた みほ/イチトヨタ ミホ)
性别:女
种族/民族:神明(原生神)
身份:胜利、成功与丰收之神
出身地区:人间都市-永茂之田
年龄:大于5000岁,具体未知
生日:1月14日(摩羯座)
身高:170cm
体重:68kg
血型:(不适用)
亲属及相关人士:黄永爱(创世神,可能的上级?),菲特斯提妮(损友),曾良野今荒(好友),玉音晶纯(冤家对头),其余众神(同僚)
外观:就外观和打扮来说偏向旧世界欧洲民族风格的女性,中等身高,身材较为丰满但因保守的着装而不易体现。偏向亚麻色的浅黄长卷发通常束起盘入白色头巾内部,偶尔会梳成双麻花辫或者是公主辫;头巾有时也会换成花环或稻穗状饰物。无论如何不喜欢让头发完全披散下来,那会使她感到麻烦。铺得很密的碎刘海,鬓发呈螺旋卷状并在末端坠有红珠,该装饰似乎是受到魔王之一的彼得潘多拉的影响。偏好田园风格且装饰繁复的长裙,通常会有以植物或花卉为主题的花纹图案。总会携带一个内容物大部分情况下为食物的双盖提篮。
简介:桃源原生神明之一,象征胜利、成功与丰收的女神。名字的寓意是“一片结满充实的稻穗的丰收田野。”和秩序之神罪源清毒、时间之神曾良野今荒关系较好,和他们一样是驻守在人间、无形地潜藏在人类生活中的神明。与爱神玉音晶纯是冤家对头,二人经常因为在各种方面意见不合而争执,但往往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尽管如此却并非相互怨恨的关系,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而已。常与命运女神菲特斯提妮一道破坏人们生活上的一帆风顺;但与玩弄他人命运于股掌的菲特斯提妮不同,她是为了试炼“真正的强者”才故意“降大任于斯人”。
比起高不可攀的天界与充满诡异气息的魔界,更喜欢的是留在人间静静地观察世人的一举一动,并为她所中意并认可的人们暗中送去祝福和必定成功的保障。因为积极美好的象征意义而受到仅次于玉音晶纯的喜爱与崇拜;不会拒绝或反驳任何的赞颂,但对他人的溢美之词永远是以冷静客观到近乎冷酷无情的心态来看待,并以此自勉。能够真正得到她认可并通过考验的人永远是极少数,因为一丰田实穗对于成功者的要求十分严格近乎苛刻;她最讨厌“特例、走捷径与一步登天”,只有信念坚定,堂堂正正、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达成目标,并且不会为“神明的赞许”所冲昏头脑而功亏一篑的人才是她所欣赏的,本质上算是非常公正不阿的神明。向往真理但又固执己见,因为自身象征意义的原因而多少有些成王败寇的偏见,不是很瞧得起政治上的失意者还有能力不足却不努力改变现状的人们。虽然大部分时间住在永茂之田打理农务,但并不是个家里蹲,相反非常喜欢出去“走基层”,是为数不多亲自走遍整个人间的神明,在每个城市都停留过不短的时间,并且还会实时关注她评价最高的几个城市的新闻动态,认为实地考察才是能够深入且透彻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好方法。她也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去直接了解他人,但往往得不到十分准确的结果,因为“人也是会变化和伪装的”。
在永茂之田深处的农庄过着看似清闲的生活,实际上每天都有不少(自己布置给自己的)事情要做,也不喜欢轻易动用神力解决问题,只看外观和生活习惯几乎根本不能被认出是神明。意外地也有很宽容的一面,不会介意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们将她误认为普通的乡下女子,“我本来也可以算是农业的神明啊。”喜欢木制品,闲暇时也会做些布艺手工并暗中推销给其他女神。
轰代防(Todoroki Daibo/Goeng Dae Bang,日:とどろき だいぼ/トドロキ ダイボ,朝:굉대방)
性别:男
种族/民族:人类(朝鲜族)
身份:职业律师,姑洗镇律师事务所副所长
出身地区:人间都市-蕤宾市
年龄:25岁
生日:12月4日(射手座)
身高:170cm
体重:65kg
血型:AB
亲属及相关人士:事务所所长(身份成谜的上级),天海清正(工作联系),王孙城满(常年竞争对手,暗恋对象),远山夕阳(女神的危险手下),中村直子(委托人之一)
外观:中等身高的青年人,标志性特征是终年不变的、形似一条大鱼的发型,因此获得绰号“轰大鱼”。短刺状竖起的头发本来是纯黑,自从正式从事律师工作后开始发白故呈现均匀的深灰色;没有刘海,扎着形似鱼尾的辫子。头顶和耳后的紫色“鱼鳍”似乎其实不是装饰,而是真正的头发,失望或非常悲伤的时候会一起塌下来。红色眼睛。服饰是深绿色的西装,系紫色领带,似乎具有“四次元领口”的谜之能力,将作为防身武器的高周波刀藏匿其中。
简介:桃源人间都市音乐名城——蕤宾市的一名普通律师,目前正替因故“离家出走”的事务所所长代行其职责。是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孩子所以名字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虽然朝鲜语讲得并不好但从来没有放弃练习。个性认真,学习工作总是很有效率,但也因为凡事都太爱较真所以根本开不起玩笑。对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一定会不遗余力排除万难将其完成。为了缓解心理压力会时常听一些东方系列的纯音乐,最喜欢的还是《天鸟船神社的结界》。
从小生活在不和睦的家庭中,父母双方祖上有历史积怨,自代防记事起便日常闹离婚;但二人在为了儿子好这方面出奇地一致,心情好的时候超级无敌宠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恶劣的事情都对他做得出来。冷热交替的生活环境使轰代防产生了既自傲又自卑的分裂性格,对外则表现为傲沉。直觉发达,推理分析能力和口才其实都很不错,但一旦被不利因素直接干扰就很容易思维混乱而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所谓“不利因素”就是诸如说话突然被打断,对方故意表示他说得不清楚,在他自己明明将事情讲解得非常透彻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咬文嚼字,死缠烂打地往真正无关紧要的细节之处追问,还有一些明显戳到他痛处的挑衅话语,例如“大人根本不喜欢你”,“王孙城小姐很讨厌你”,被歧视其朝鲜人的身份之类;而令他头疼的是这些情况多数时候并非仅仅发生在庭审现场。
热爱自己的工作并经常强迫自己加班,宁可一直留在事务所整理案例也不愿意回家面对大人,总是拒绝应有的休假,从而导致自己精神上非常疲劳;连心理医生都不想去看,因为怕自己一不小心口出狂言伤到对方。珍惜证据和机遇,从不放弃一切可能翻盘逆转的机会,但比起收入和名利更在乎的是真相和正义,不会为了已被自己证实有罪的被告的无罪审判而违心地强词夺理,因此有“诅咒缠身的队友贩卖机”之称。难得遇到被告确实无罪的情况便会当着时常作为其对手的王孙城满的面态度狂妄地嘲讽检察院众人,等到所有人离开法庭的时候却一个人躲在桌子底下哭,担忧自己第二天被检察院联名批评。是嘴上说着“交给我吧!没有问题!”但心里总是觉得自己一定会把事情搞砸的极度不自信的人,越是给予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对自己的不信任感反而也会随之增强。不习惯应对来自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被表扬的话会害羞到发怔并且完全说不出话。并不知道王孙城暗恋自己并且希望成为自己基友的事情,还以为被嘲讽过多次的她很讨厌自己。害怕作为王孙城的护花使者的远山夕阳,曾将其误认为杀手。
“王孙城小姐会怨恨我的吧。我为什么又要讽刺检察院偶尔的疏漏之处呢?她的支持者肯定会通过什么渠道来喷我的吧。又是这样……我受够了。”
个人填坑用,阅读请先看下方指南
banner支援大欢迎(?
1
“不要勉强一个三流侦探。”
藤原方结用手指关节敲了敲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房间肃静下来。
“我还能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已经是极限了——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清洁工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当的,我从今天开始会消失一阵子……几天,几个月,几年,说不定。你联系不到我的。”
方结从兜里拿出钥匙,旋开锁着的抽屉,按下侧面的机关,夹层露了出来。
“如果你是个有独立能力的人就照顾好自己,至于我,丝毫不会想着你的。”
他从夹层里拿出一个纯黑的笔记本,纸张边缘已经泛黄,看来用了一阵子。
“我想我还不需要您的担心,如果您是那样看待我的话,那只能说明您的眼光可能不太准了。”
“别啰嗦。”
方结将笔记本塞给清志。打开它,在扉页上有着“diary”的字样,接下来的几十页被撕掉了,后面则是崭新的。虽然方结没有明确表示,但大概这算是清志的十四岁生日礼物。
“……莫非您属于,有秘密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类型?真是细心呢。”
“撕掉的几页是什么,你没必要知道——这玩意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你看得出来吧?”
“真是抱歉,我想名侦探先生还是高估我了,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日记本而已。”
“那就算了。它现在连着哪个平行世界我也不知道,但既然怕你在我离开之后会寂寞得死掉,姑且让你玩玩这个笔记本。”
清志发出了不屑的嗤笑,被方结丢过来的笔记本砸了个正着。
“费劲千辛万苦才搞到的——弄丢了的话就拿命来偿还吧,也许这玩意确实比你还有价值。”
“记住。”
“你的人生,没有任何人期待着。”
……
清志认为他不像是在开玩笑。
2
“你知不知道你中了诅咒?”
清志正对着漆黑一片的夜色张开双手,高呼着太阳,结果被摊在沙发上喝着冰果汁的方结泼了一顿冷水。
“我相信这里的隔音很好,就算扰民,也只是扰到了您一个而已吧。”
“没数落你,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件事……最近工作精神紧张嘛,结果就忘了告诉你了。”
“你活不过18岁的。从结论上来看是这样。”
清志用看傻子的眼神瞥了他一眼,转过身继续对着夜色发出热忱的呼喊。
“之后不用和我强调我知道的事情,和您不一样,我想我还没有健忘的毛病。”
当清志想起来要回话的时候,方结早已经睡着了。
3
“您考虑过您的死亡吗?”
“那还不是当下应该考虑的事情,一事无成就死去的话,只是白白浪费了宇宙的能量而已。”
最近这小子学得越来越有模有样了,指的是这种堵死人的说话语气。
“我当初就不应该教他。”清志挠了挠头,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
“你不教他也会。”方结凑过来,瞟了一眼日记的内容。
“……您这种不让我的话落地的行为,真是让我感激不尽。您还真是对那位小少爷期待不低啊。”
“人家至少比你有用,浪费宇宙能量装置。”
“那是因为您目光短浅到没有意识到死亡的精妙之处。”
清志拖长声说着,同时把这句话写了上去作为回应。
“说这种话,还不如努力活个19年试试看。”
“那是不可能的——”
清志转过身来,拉过方结正在擦着的枪杆,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烟花的绽放只有一瞬间,但却是极美的。”
4
“看见那团火烧云了吗?”
“您一直着眼于那种不切实际的东西,明明桥下这滔滔水浪才是唾手可得的,为什么……“
“你要是敢从这里跳下去,我就先一枪打死你。”
“……血肉横飞的样子太不美观了,还请您放过我这一次。”
方结用手指擦拭着枪杆,靠在墙上,惨白的余光从窗缝里挤了进来,渐渐暗淡下来。
“大雨天就别往桥上跑,尤其是别穿着那个质地优良的披风,你也心疼一下回去之后擦地的人。”
“我当然知道您的辛苦,如果您能允许我不回去的话……”
一颗子弹从清志身边擦了过去,透过桥栏杆的缝隙,冲入了桥下的河中,溅起一簇浪花。
“……非常抱歉,我并没有想到您的脾气相比之前会恶化,果然世间万物都是在永恒发展的啊。”
清志转过身来,背后靠在桥上,天色阴沉,染上了浓重的黑青色,已经开始下起了大暴雨,桥上没有任何人——他一个人可以独占这个地方。
“下雨天不应该有火烧云。”
“是啊。”
“您可真是个魔法师啊,操纵气象这种事情,也只有您这样伟大的人才想得出来吧?”
“只要你想,你能做到比这个更夸张的事。”
“呵。”
电话那头沉默了,方结以为他不会再继续说别的,于是把手机放下,开始整理东西准备离开。
“火焰真的很美,像是企图把天地灼烧到融化一般……这样轰轰烈烈的欲望,真的好美。”
“相比之下,沉没在冰冷的深水里,无人问津,倒像是十分无趣的谢幕了。”
“……能否用这样的谢幕赢得更多的掌声和喝彩呢?我很好奇啊。”
没有人听见这些话。
5
“你好啊。”
对面的人点了点头,有些腼腆,反而突显出了自己过于张扬了。方结放下翘着的二郎腿,换了个姿势,学着他一样端正地坐着。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世界是难得的宝物?”
“这一点我们都清楚。”
方结哈哈地笑了,虽然他并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你真拘谨。”
“是啊,倘若我也学着您的脾气,估计会得罪很多人吧?”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中,夹杂着子弹上膛的声音。
“不要学他的语气和我说话。”
方结一只脚踩在了桌子上,枪口已经对上了面前这个人的太阳穴。
“不要这么对待自己——不过就算你开枪了,也是无事发生,毕竟这里是梦境。”
“其他人可是会乖乖的执行'人被杀就会死'的真理哦?只有你不遵守规则。”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哦?”
“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尝试。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是否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欲望会产生很大影响。”
“你觉得你能打破诅咒?”
“你相信神的存在?”
“当然不。”
“那就是了——既然没有绝对意志控制着这个世界,那么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呵,那你就尽管挣扎吧,在这出不去的牢狱。”
“你要承认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个世界已经无法容下你我的欲望了,所以……”
“话真多——”
方结用扣下扳机的方式打断了这场谈话,瞬间他睁开了眼睛,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很好。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当陷入深度睡眠中,会在梦里见到其他的“自己”。方结感觉到自己最近睡眠质量很好,毕竟用恼人的演说辞吵醒自己的家伙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
“说什么,结果还不是那样……人被杀就会死啊。”
end
方结弯下腰,从海水里捞起来这个已经无法再使用的日记本。
“这还不是弄丢了吗,结果真的拿命来偿还了。”
他摸出打火机,干烧这个湿透了的日记本,数分钟之后,火焰终于慢慢燃起,忽地生发,包裹着,吞噬了整个遗物,大片的灰烬落入了海中。
“艺术家的人生,果然只有自己才期待了吧?”
Day0
“你,”
“醒一醒。”
Day1
“更多地关注你自己。”
响这么写着,笔尖停驻在了末位的句号上,钢笔的墨水从手里流淌出来,句号中空的圈被晕开了。张开手心,生命线在一片漆黑中清晰可见。
“活着是没有意思的,但如果现在就死去的话,平淡地死去的话,毫无梦想与欲望与追求就死去的话——”
“你在说谁啊?”
“稍微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再发话吧,既然已是牢狱中的囚徒,就活的像个犯人的样子。”
“一生,痛苦着,挣扎在人间地狱吧!”
响像是被这些看似什么都没说的恐吓惊到了一样,虽然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第一次开始在这个日记本上记事开始,就发生了这种事情——日记对自己记在上面的话会自发产生回应,像是,有人在应答着自己一样——而这应答,正是响自己的想法。
像是自己在应答着自己一样。
“真的羡慕你啊,能口无遮拦地说出这种引人不适的话——想必是不受欢迎者的自暴自弃吧,演说家先生。”
响轻描淡写地回应了,自己这样不饶人的语言风格,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大概是受到了日记那边的人的教导,但响认为这才是自己应有的语气——工作上表面惯用的套话提不起思考的欲望,就像是,少年外交家面对着于自己谈判的人一样,
“无趣,无聊,毫无生机,简直枉费了从小到大细胞分裂的力气,这种家伙,更不配拥有死亡的权利。”
演说家当初是这么说的,大概这也是响的想法。
Day2
日记本并不是每天都会被启用,更多的时间它被锁在了抽屉的夹层里。
并不是今川家的少爷有什么要瞒着家人的秘密,只是响无法想象那个日记中的“存在”被别人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一直以对待傻子的目光看别人的他可不希望被别人当做傻子,或是精神病什么的。
“会和日记对话的,你脑子也进水了吧?”
这是日记里传来的回应——相信着日记那边存在着一个人,这么妄想着的自己,肯定已经与疯狂不远了吧。
“我讨厌这个世界。”
这是响在十四岁生日拿到日记本时,记下来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
“我不喜欢我自己。”
“真是愚蠢,你想死吗?”
日记上会自己出现回应,常识人培养出的外交家完全被吓到了,却伴随着极大的兴趣。
“你是谁?”
“在问我之前先介绍你自己才对吧,这点基本的礼仪都没有吗?”
“今川响。”
停顿了一下,响甚至以为字迹不会再继续出现了,果然,刚刚的那些是幻觉吧。
“别和我提你的姓名了,令人作呕。”
日记本被摔了出去。
少年跑向自己的父亲,喊着日记本里发生的怪异,但这种荒唐的话并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响被迫结识了一位没什么用的心理医生。
“哭泣不能解决问题,在交涉手段中,最忌讳的就是真向敌人做出让步。”
“笑容不能带来思考,在演说技巧里,最可怕的就是让自己被听众带动。”
“你是谁。”
“在问我之前应该先问问自己才对吧,至今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看来你真的不清楚时间的意义。”
响合上了日记本,刚开始的对话,和七八年之后现在的对话,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自我意识”,仅此而已。
Day3
今日无事可做。
比起无事可做,不如说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工作日一如既往地没有去学校上课,对于网络上的社交更是没有丝毫兴趣,这个外交家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却像个社交废人一样——假如他还算得上有朋友圈子的话。
为了工作需要的表面兄弟倒是多,却完全不是适合深交的类型,所以响拿出了这个日记本,翻看着以前的“对话”,若是能从这位“朋友”身上找到一些刺激感就再好不过。
“你的才能是什么?别告诉我你就是个普通的凡人,那我真是看走眼了。”
外交家并没打算回应他,当天的对话在这里就戛然而止了。那个演说家经常在这个日记上打稿,响早就熟悉了这一点,所以对他的身份有了一些模糊的猜测。那个人的心里显然并不是光明的,语句中看到的是太阳,温暖与光芒,响却可以听到真相是嘲讽的讥诮。
“希望”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伴随着冷笑,隐藏着暗示,暗示着死亡。
“你其实是艺术家吧。”
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响翻到末尾,写了上去。
没有回应,也不知道演说家是否认同这个评价。
过了几天,再看到这一页的时候,在末尾,多了两个字。
“烟花。”
Day4
“被劝说去上课。”
“真好笑——当初明明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们认为学校里的教育对我没什么帮助的,现在却突然反其道而行了。”
“我想原因你都猜得到,人类,因为傲慢,真的太好懂了。”
今天日记里仍然没有回应——差不多已经有一周了,那个演说家可能厌烦了这样的对话,最近便不再理睬自己。响合上了本子,放回抽屉夹层,盖好夹板,推回去,用随身携带的小钥匙锁起来。
他当然听说了那些人请来了一个侦探,要解决他们的儿子——自己,被日记里“付丧神”作祟的事情。那个无能的侦探至今没有任何作为,每天只是逛逛附近,和邻居们聊聊天而已。他所要求的,所有与响的谈话都被响拒绝了。企业家的耐性更是已经随时间消磨地差不多了,想到这里,响冷冷地笑了一下。
他马上就会被赶走的,毕竟,终究只是凡人。
“我明天去学校。”
在晚餐上,他这么说。
“没什么原因,只是突然想去。”
姑且,给予那个侦探一点希望好了——然后让他一无所获,重新跌入绝望的地狱。
Day5
“你必须在没有我的时候也能活下去。”
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空白的页面,却只有这句话浮现在那里。墨水是血红色的,已经凝固成了黑,却仍然能看出本色,响看到这行字的时候,莫名地心头一凉。
“你在说什么?”
没有回应,一如既往的,应该已经适应了才是。
“回答我。”
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得不到回应的问题,看上去像是奇怪的自言自语。
“你还……”
笔尖断了,高档钢笔的笔尖,从中间劈开,滑落在日记本上,流下了蓝色的墨水痕。
心跳骤然加速,头痛欲裂的感觉莫名其妙生了出来,深呼吸一口气,想要出去走一走冷静下来,打开房间门,却发现那个深蓝色头发的青年站在门外,手指划着手机,像是在等人一样的姿势,那个侦探。响没有招呼他,深红色的眼睛被盖在厚头帘下,对付这种人还用不着,他想。
“打扰了…,我想和你聊一聊。看在我在这儿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还请给我个机会吧。”
冷笑了一声,响扭头就走。
“那么至少,请把您的日记本收回到夹层里,放在桌子上的话很容易被别人看见。”
响反应了一会,终于因感到震惊而回过头,却发现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Day6
“为什么人们都看不到自己以外的存在呢?”
笔尖停下,终于意识到了就算这样做也无法再得到任何回应,响就这样盯着这行字。四本用不同国家语言写的书籍就这样摊开在旁边,但他却没有一点想去阅读的激情。
时间是半夜,然而一点困意也没有,心底却隐隐的涌着没有由头的激动。
“死亡终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就算再悲伤,也要活下去……”
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但这几天以来一直萦绕在脑中的那种痛感,伴随着钢笔落下,突然间集中爆发了。房间里充斥着少年无法抑制的叫喊声,失去了方位感,双手抱头撞在了墙上,后背传来了仿佛被锐器刺穿的痛觉,喘息着,却突然发现气息跟不上来,是潮湿的窒息感——有什么东西被吞下去了。
意识再次恢复,响发现自己平躺在房间的床上,门关着,桌子上的东西也没有变化,但是桌边却坐着那个外来的侦探。
“我不想再见到您。”
“请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
“毕竟吃了镇静剂。”
响猛地站起,上前揪住了他的衣领,侦探的表情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仿佛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动作。他抓住了响的手腕,轻而易举地把他按回了床上坐下。
”如果刚刚我没能进来处理的话,也许你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了吧,你知道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吗?”
“请出去。”
“看来是猜到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可以……”
响重新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对着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从我这里,您什么都别想得到。”
Day7
“先看看你自己吧。”
响看着那个人伸向自己瞳孔的指尖,从对方镜片里映出的影子,他竟然听到了自己的情感——尖锐的,刺耳的,掺杂着杂音的,恐惧。响过于沉浸在这种激烈的情感当中,连头帘被萤火放了下来都没有立刻意识到。
不应该,不应该这样,明明到刚刚为止,这个“谈判”都是我占优的,他这么想到。
忽地注意起来这一直隐约就可听得见的,从那个侦探心里传来的笑声,这个熟悉的笑,肯定是在哪里听过的——是自己的声音啊,一模一样的,自己的声音,除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声音和自己一样的人。
“你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吗?”
响颤抖了一下,那个侦探,现在已经把视线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大概是觉得自己不足为惧了。明明没见过几次,对方却像是对自己了如指掌一般,真令人感到恶心。
“平行宇宙的事情——在这个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差不多一样的空间。当然,人也是。”
“……这个假说还没有得到证明吧,用这种道听途说的概念去认识世界,确实是独特的风格呢,侦探先生。”
响渗出了冷汗,对于自己这样的语气,对方一直表现出已经很习惯了的样子,响已经知道了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同时又意识到了自己不想听到他之后的发言。
“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存在,就像是你无法否认你左眼的视觉异于常人一样。”
“只是共感觉症状,故弄玄虚不应该是职业者的风格。”
“你相信这样的说法?”
回应萤火的是沉默,响盯着他,像是在思考怎么反驳一样,却没有结果。
“那么继续吧,至于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平行世界的假设是真实的——这样说吧,我与平行世界的'我'们共享着记忆。”
对方把响控制不住的吃惊表情当做了回应,轻描淡写地继续说着。
“既然是平行世界,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的存在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实际上——我自己,江户川萤火,与另一个世界里叫藤原方结的人是同一个存在。名字和身份都不一定相同,本质上却始终是同一个人,我这么说的话,你应该能懂了吧?关于日记里的意识的,真相。”
响没有回应,面无表情。
“他的名字是今川清志。”萤火叹了口气。
房间被寂静充斥着,数分钟过去,响突然拍案而起。
“我从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
响保持着撑着桌子的动作僵持了一会,最终坐下了,向后靠在椅背上。
“我不承认。”
萤火望向窗外,没有直视他。他看到夜空中一颗流星划落下来,孤独地,又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觉。萤火又看了看响的脸,忽然对这个男孩“既定”的命运产生了同情。
“……果然还是把这件事忘了吧,你还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
响站了起来,脸色阴沉。
“所以我至今所做的,只是与我自己进行对话吗。”
把日记本摔在桌子上,摊开的一页,金色的特质墨水呈现着“只有胆小者才不敢接收对自己无益的现实。”字样。
“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虽然是同一个人,但终究是有着不一样的思想……”
“不,我们的精神是相同的,我感受得到,我可以理解……”
响抱头跌坐在沙发里,披风掀起的微风让日记翻了几页,不明所以的内容呈现出来。
“您考虑过您的死亡吗?”
“那还不是当下应该考虑的事情,一事无成就死去的话,只是白白浪费了宇宙的能量而已。”
“那是因为您目光短浅到没有意识到死亡的精妙之处。”
萤火拿手盖住了这一页,平和地盯着响。事已至此,在场的两个人都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这个名为“今川响”的人的,生死观。
“你没有再给出下一步的回应,因为你明白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不正常的寻死冲动,但同时,你又知道生的可贵。”
“够了……”
“你是奇迹啊。”
“我不想知道……”
“你是,也许能打破诅咒的奇迹。”
Day8
“您觉得。”
“我,正常吗?”
响放下手中摆弄着的当期杂志,也并没有抬头,就这样唐突地发问了,那名同校的前辈看向他,愣了一下,怀疑着他是不是在和自己说话——毕竟两个人互相都不熟悉,仅仅是曾经在学校图书馆有过一面之缘而已。
“为什么问我?”
这个时间书店里还没有其他客人来,判断响不是自言自语,于是前辈回应了。
他发现响死死地盯着他,大概是因为没有给出正面回答。放下手里刚拿起来准备看一下简介的哲学著作,他扭头看向别的地方。
“……在我看来很不正常。”
响低下了头,没出声,低头继续翻着手里的杂志,三五秒一页,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在关注内容。忽然,他又抬起头,按住了那本哲学著作。
“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是平行宇宙论。”
“以华而不实的词藻粉饰根本无法成立的基本论点。”
“因为无法证明所以一直在关键问题之外周旋。”
“最终同无能的古人一样,求助于万能的神明,企图以上位意识的存在来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无能者自我安慰的最终手段。”
“……”
本来以为他已经说完了,结果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对这种劣质书籍感兴趣的话……我可能要重新斟酌您的品味了。”
“哈啊………”
前辈抬手稍稍用力地摁压着自己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试图以此压下自己不禁烦躁起来的心情,这个家伙不饶人的说话方式,还真希望他能改改才好。
“不好意思,虽然大概能理解您想表达些什么,但我目前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心情来照顾小孩子脾气的外交家大人。”
对着响,前辈露出自己最擅长的完美微笑。
“对那种杂志上心的您的品味也十分………算了,自视清高的小少爷对这种低俗刊物感兴趣反倒也不算什么奇怪事吧,从小被饲养在家中从不外出的猫咪也很难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呢。”
“我在追这个连载小说。”
出乎意料地,响竟然没有反驳,也许是因为过于沉浸于内容,根本没听见对方说了什么。
响指了一下自己手里的杂志,摊开的这一面,一眼扫去大概是什么不入流的悬疑小说,没过几秒,响已经翻到了下一页。
“不买回去看?”
“没必要,这种内容也不值得细读,这个作者的水准我不敢恭维,十秒就能看完了……垃圾小说,不堪入目。”
响翻完了连载的部分,把杂志放回了原位,双手插兜里,走了。
“那小哥每周都会来看一次……还什么都不买,这不就是明摆地来白看的吗……”
“这么点时间就看完了?不可能吧?”
响走了之后,两个店员议论着,因为书店里现在只剩下一个客人了,他们也就没太在意音量。
说着内容不堪入目,结果却每次都来关注,这样的人,也许确实很不正常吧。
前辈重新捧起这本被响讽刺的一无是处的哲学著作,封面上印着作者的亲笔签名,潦草的花体字并不太容易辨认,勉强能认出来是“Leonardo”的字样,是并不认识的外国人。
Day9
“梦是可以逃避一切的最高明手段。”
“所以你先沉睡了,而我却在这里,不得不保持清醒。”
“你可真是脆弱啊。”
已经从萤火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情的全貌,响写下来这些作为最后的道别,于是这本日记也就物归原主了。当然,因为萤火把委托人要求销毁的事情告诉了他,日记的内容已经被他重新誊写藏在了其他地方。
“如果有心情的话,多去去学校交几个朋友吧。”
交还之时,被那个一看就没有多少朋友的侦探这么说了,响感到十分不爽。
“份外之事也要强差一手的话,可能会比现在更不招人待见吧?”
“看到你这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那么,祝你活下去。”
“这应该还轮不到您来担心。”
Day ???
“烦躁?”
“想要逃避?”
“想死?”
“不会的,我不会允许你去死。”
“就算用尽一切手段。”
“因为,只有我是独一无二的啊。”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作为独立的个体。”
末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响和萤火都没有注意到。
周旋。
仍然是那种无聊的感觉,生活的漩涡裹挟着自己,却丝毫没有对它产生的向心力产生一点恐惧的感觉——明明是个活人,却有一种死人般的安稳。
“你胜利了,祝贺你。”
今川响冷漠的从父亲身边径直走过,没有抬头瞧他一样——就像是那位父亲的语言里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喜悦一样,平淡。这就是今川家的家庭概念,外交家的谈判一如既往地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上级领导只要理所当然地接受结果就好,偶尔给予可有可无的嘉奖。
时间还早,但响没有去学校的打算,那个用于培养才能的地方,他早就应该毕业了。响没有处获胜中获得常人会有的满足感——他清楚的知道,自己那是最低劣的,言语中伤的手段,毫不留情地掐碎对手心灵上弱点的,最不符合于“人类”身份的行为。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甚至他的对手也可能一辈子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心里会产生对那澄红色瞳孔的恐惧感。所有人,自己以外的所有凡人见到的都是最后的结果,在这为强者喝彩的世界里,唯心主义的奇迹大概是不可能发生了。
这样的人被称为有才能的外交家——这样的世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想着,响闭上了眼睛。
————
“下午好,我亲爱的,人类朋友们。”
“这么称呼也许会显得很奇怪,但希望我的听众们并不是头脑空空就来到这里,只要是稍微准备过一点的人,应该都能够理解这样说的意义。”
“今天的主题是,存在。”
响看到那红色的披风伴随着抬手的动作而扬起,边角上红褐色墨水打出的草稿,在那只眼睛精微地洞察下发出了声音。
“存在即毁灭。”这样的东西,不断的重复着。
响伸手按下左眼前过长的头帘,遮住眼睛,声音停止了。他忘记了去关注演说者所述的内容,再回过神,周围已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他跟着旁边的人一起站起,机械性的拍着手,尽着一名听众的基本礼仪。
“我与他人的区别在哪里?又如何判断我现在是作为自己而活着的,更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比如,那位白发的朋友,你如何判断,自己仍是那个名叫'响'的存在?”
响在惊愕中发现周围的听众早已全部坐下,黑压压的视线汇聚到了自己身上。紧接着是聚光灯刺眼的白色,演说家在一片金光中伸出手,请他回应。
————
响回到了会议室里。
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人影,大概是梦境里记忆被模糊了,无法辨认他的外表与身份——但是没关系,至今以来的对手,没有任何区别。他的话语在手上凝成了钢铁铸的匕首,他站起来,不留情面的插进了对方的身体里。
黑色的血液涌了出来。
————
“在生命仍未消逝之时挣扎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宣扬自己的存在——”
“却只是存在而已。”
会场的聚光灯回到了演说者的身上,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自顾自地说着。信徒鸦雀无声,更无从知道,他们究竟是折服于这个人的话语,还是无聊到睡着才是。
只是在演说家的眼里,他们听到的,永远只是自己心里的一面之词。至于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在意了。
这样才好。
————
“请问,您把您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呢?”
“这件事情,若只是从您的角度出发的话,似乎对您的利益没有任何增益吧?”
响轻柔地抚摸着那把刀所插入的地方,像是关心着被害者在死亡时会不会感到疼痛一样,死亡已经是定局,在临死之前展现出虚假的仁慈,也许连冥界的检察官也能骗过。
————
“但是,个性,独特性,差异,这些让我们欣喜若狂的满足的欢愉,却必须是要基于生命的存在的。”
演说家张开双臂,很好,无人回应,这才是真实,半晌后响起从众心理的掌声,甚是无趣。
————
“为何不直视自己的存在呢?”
“请,放弃吧,您眼前展现出的是光明,是无限的希望与未来——为何要被他人囚禁在这渺小的一方天地,您的才能,若非为了眼前的苟且,一定能更为世界所认同。”
响拔出了匕首,再一次,粘稠的血液喷溅出来,纯白的头发被染成了墨汁的颜色。已经宣判了敌人的死亡,执行官的死神就是他自己。
无需论是非。
————
“死者无法分享世界——人类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
————
“在被社会的力量压到之前,更加地为了自己活下去,这样如何?”
“希望您,慎重考虑,那么,到此结束吧。”
————
“所以,活下去吧,在不得不面对彼岸之前,坦然地活下去吧!”
————
响在又一次的雷鸣声中惊醒,夕阳从落地窗中射入,洒在他的后背上。他发现自己原来是趴在书桌上睡着了,双臂下垫着的是那个日记本。
“梦是可以逃避一切的最高明手段。”
“你可真是脆弱。”
日记在他清醒之时,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1
其实他也算不上什么作家,三流杂志上的小说作者罢了。
神鸣泉今天也无所事事。虽然并不认为自己写作的能力有多么强,但是不会为死线担心这一点倒是值得自豪——总是能冒出莫名其妙的灵感,逛街的时候就能把下次的剧情打好大纲……虽然他觉得这是因为三流杂志收稿标准太低的原因。
他想起来自己其实很少逛街,原因是没钱。他的生活很拮据,从另一个城市搬到这里已经用尽了他身上一半的钱——他甚至对房东,江户川先生不回来这件事情感到庆幸了。
总体上,他对这个住处很满意,除了一点——那个侦探的笔记本电脑每天会自己开机关机,不定时的。这件事情大概足以吓到普通人,但对于被称作灵异小说家的悬疑小说作者,也许还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吧?
“侦探不在吗?”
今天的电脑在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打开了,比往常多弹出了一个笔记本文件,上面打起字来。泉正倒在旁边的沙发上看报纸,他就这样侧着盯着电脑屏幕,看看它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反应。
“都多少天没上班了!谴责!”
报纸上的版头是关于最新AI技术的新闻,据说它们已经可以开始像人类一样的思考。想着莫非江户川先生的电脑里装了这样的玩意,泉过去在键盘上敲了几行字进去。
“你好。”
“!?”
“?????”
电脑里的“AI”像是很惊讶的样子。
“你找江户川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你谁啊?”
看着“AI”很不客气的回应,泉稍微思索了一下怎么继续谈话——他想,这个经历大概可以写到下个月的小说里。
“江户川先生还在外面工作,没有回来,如果有委托的话贴在事务所的告示板就好。”
“????”
“啊。你莫非是,那个,新人?”
“AI”连这个都知道吗?真厉害。泉这么想。
“三流侦探,竟然连电脑都忘了拿了,算了,我也懒得告诉他。”
太真实了,这种发牢骚的语气,泉对它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你是什么时候被安装的?”他敲进去。
“哈?”
“……你问这个程序吗,也就不到一年吧,在这之前我还不认识他。”
“你知道开发者是谁吗?我很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
“????”
“哥,这种商业机密肯定是不能外泄的吧?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玩意,这种技术怎么能说分享就分享呢?”
这次轮到泉不理解了。
“……我确认一下,你是谁。”
短暂的沉默。
然后是满屏幕的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不会一直以为我是什么聊天机器人这样的东西吧?那你也太天真了。”
“是真人哦,不想出门到事务所去的人。”
“喂?你还在吗?”
“……不在算了,等侦探回来之后转告他一下,上次那个活的工资还没给我。”
泉拖着下巴在电脑屏幕前陷入沉思,良久。
此时,远在其他城市的江户川萤火并不知道自己把电脑忘在了事务所。
2
这周的稿件被拒了。
泉认为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毕竟作为一个三流杂志,标准应该是很宽松的,然而自己引以为傲的稿子却被拒了。
编辑只有一句话:“灵异小说里出现AI好像不太好,神秘感没了呢。”
这句话很打击这位作家,这位以为自己写的是悬疑而不是灵异小说的作家。泉开始思考以后完结的时候,结尾应该怎么按照“灵异”标准来处理。
“毕竟真正的灵异事件是不存在的吧?最后肯定都有个科学的结局。”
泉喝了一口凉掉的茶,叹了口气,向后仰去靠在沙发上,拆开一包pocky叼在嘴里——不知道为什么,事务所里放了好多各种口味的pocky。他对面的男子高中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颓废的样子。
“不一定吧,所谓'科学',可能只是人们迫不得已作出的牵强解释?”
“莫非你认为妖魔鬼怪真的是存在的吗?年轻真好啊,当初我也有过想象力丰富的时候……“
“停一停。”
男子高中生拿手指关节敲了敲桌子。
“虽然有些失礼,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听您抱怨十分钟了。请问江户川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
泉大概懂他的意思了。半小时前这个少年来到事务所,泉告诉他侦探现在还没回来,于是少年就在这里坐了下来。虽然并不知道事务所平时接待的办法,但想着晾着客人不太好,泉泡了两杯茶,试图陪他聊一会——结果话题自然引向了稿子被拒的这件事情,没办法,这个作家没有多少交心的朋友。
“抱歉……侦探先生现在正在出差。”
“……”
空气尴尬起来,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泉方才明白自己一开始误会了少年的意思,他是想等江户川先生回来。
“……没事,是我没问清楚。”
男子高中生戴上黑色外套后面的帽子,边缘金色的扣子碰撞着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等江户川先生回来之后——麻烦帮我问问他,我委托调查的事情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少年把留言记录在便签上递了过来,泉注意到角落处的签名是佐佐木白夜。
“那么打扰了,工作辛苦了。”
把已经凉掉的茶水一饮而尽,白夜走出了事务所。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有一些事情无法单纯用'科学'来解释。”
他最后留下了没头没尾的这句话。
3
“你都在干什么啊!”
“你都在写些什么啊!!!”
那个声音又在脑中想起,靠在沙发上的泉忽地站了起来。自己否定着自己的呐喊,于恍惚的梦中再现。
梦魇。自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每当绞尽脑汁想写出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总会有这种声音在脑子里响起,那样的恶魔用着和自己一样的声音阻止着脑电波的扩散,泉的手指插入了头发,扎好的辫子被挠乱。
“你都在干什么啊!!!”
猛回头,这样的声音,从电脑旁边的音响里播出。像是12、3岁小孩的感觉,不耐烦,略带着点愤怒。
“可恶你不看屏幕的吗,那我不就只能远程语音了嘛!!”
“闹鬼了?”
泉敲了敲电脑音响,里面的声音又叫了起来。
“你个电脑白痴!!是语音通话啦!总之你快看屏幕——”
这样一行字样被泉注意到了:
“晌午时分,暑气氤氲,余饥渴交加不可求之以饲,望贵人相助,若有所损,直须取之于江户川者也。”
泉愣了一下,强行憋住了笑。
“也就是说,你不想出门买吃的,所以让我帮你觅食吗?”
“正是!”
对方好像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过分不自然的语言风格,反而说的很自信。
“你就不会自己叫个外卖吗?太小了?爸爸妈妈都在……”
“你才是小孩子啊!!余可是独当一面的成年男性!都怪那个逃债的家伙不给钱!余只能饿着——”
泉思考了一下成年和男性两个词的意义,决定不去深究。至于没钱吃饭的事情——他想到了前几天这个电脑里的孩子还在给他炫耀新买的最新款主机。
“嗯,所以地址和联系方式呢?没有这个的话外卖也是到不了的吧?”
对面沉默了一会,像是在思考能不能把自己的信息就这么轻易地给出来。过了数分钟,一条简单的地址,和联系电话被发送过来。
“伊佐凪”,那个孩子大概是这样的名字。
4
“泉哥,你不觉得头发挡眼睛很碍事吗?”
“嗯?不觉得啊?”
算是习惯了吧,泉这么想着,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为了节约剪发开支养成的不良习惯。白夜盯着他散乱的头帘,叹了一口气。
为了及时告诉他江户川先生的消息,泉和他交换了Line,来往了几天的信息之后,也就觉得稍微混熟了一点。网络上的白夜似乎做着游戏代打的工作,通过评论了解到,这家伙可能还是个专业级的游戏高手。
【江户川先生说今天回来】
两分钟前泉给他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两分钟后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了事务所里。
“你会瞬移的吗。”
“放学路上经过而已,为了不为耽误事,我是随时接收消息的。”
“是游戏代打?”
“是正经工作。”
“游戏而已。”
“性命攸关。”
“……现在的年轻人啊。”
“我认真的。”
泉还想说些什么,门口传来了开锁的声音,会用钥匙开门的,只有这个事务所的主人了——虽然泉很想向他喊一句自己根本没锁门。
白夜已经冲到了门口,一把拉开萤火正在试图开的门,帮着他把出差带的东西都搬了进来,看上去真的对自己的委托十分上心了。萤火也看出来了这一点,把东西都放进来之后,他并没有着手收拾,而先请白夜坐下说话。
“江户川先生,关于我的委托,想问一下现在进展如何,给您发line也没有收到回信,我想可能是您工作比较忙……”
“等一下……?”
萤火给他倒了一杯茶。
“有两个疑点,第一,我的line并没有收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
萤火仿佛意识到了事情不太对劲,表情凝重起来,半晌,他慢慢吐出剩下的话。
“第二,你并没有委托给我任何事情……”
白夜猛地站了起来,冲到门口的告示板——上面并没有自己的委托内容,或者说,“原本”属于自己的那条工作安排,现在变成了空白一片。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