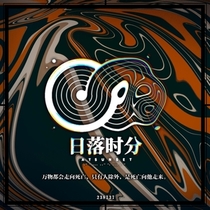全文2676字
——
莱丝汀·多纳的老家住在一个可以称之为偏僻的城镇中更加偏僻的郊区。贝加多尔的冬天,寒冷到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所有有翅膀的生物就已经全部不见踪影。多纳一家就生活在这儿,邻居们同时还有法鳞社区中颜色各异的居民。
那是她第一天去学堂。莱丝汀推开门,壁炉里噼里啪啦地响着的火堆让小小的钴蓝色法鳞感到好奇。她蹲了下来,看着火焰变化颜色——变化,她拿出了放在包里的铁皮和硝石之类的东西,一个一个丢到了别人家的壁炉里。
“这是烟花的原理。”一个声音传过来。莱丝汀被从胳膊底下抱起来,她转头看到了一位戴着眼镜的月白色法鳞,大概一百来岁。
“您好。”她维持着回过头的姿势,遵从父母的嘱咐响亮地说,“我是莱丝汀·多纳,今天开始在这儿上课。”
“嗯,多纳小姐。”眼镜法鳞皱着眉看着冒出不祥烟雾的壁炉,把她放下来之后用水浇灭了火焰,“下次你可以选择去安全一点的地方——比如户外——去做这些实验。”
“好吧,老师。”她被放下来以后打了个喷嚏,想了想,“有些冷了,可以再生火吗?”
本森老师看着这个新同学,她相信通过一个学生的眼睛能看得清他或她的资质。本森老师得出的结论是聪慧。聪慧,但是无畏且危险。她摸摸莱丝汀的头,对方对这个动作有些不解。“注意安全,活着才能获得知识。”本森老师叹了口气叮嘱她。
—
确实是这样。和其他的法鳞远行的原因或许有一些不同,莱丝汀越长大越冰冷(物理意义上的冰冷),在第二次因为失温被送进棺材以后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家。
“这地方太冷了,我想活着获得知识。”她丢下这句话,顺着本森老师指的路连夜坐马车像候鸟一样跑出了白铁城。在前一天晚上她还和邻居家的黑色法鳞大哥聊着对方可能会去哪里旅行。“我记得在东南边有一个森林,那附近的城市也靠山吃山。”亲切的法鳞和她说,“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那种森林吧?本森老师提过那边有一群有意思的人。”
凭着隐约的印象,莱丝汀马不停蹄了一个月之后在最接近森林的酒馆里落了脚。为酒馆提供了很多收入之后,盘缠很快地见底了。为了填饱肚子她想了个办法,也许比较不明智,或者比较危险,但省事。而道德?人用来框定自己的东西,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你们好。”莱丝汀背着包站在一桌人面前。他们刚刚贴了招人公告,报酬可观。看起来是冒险者小队,而不是鲜血骑士团那般正经的有组织的队伍。像这样的队伍中随时可能会需要一个去送死的,而上一个看上去已经死了,莱丝汀认为自己来得正是时候。但她需要提供更多足以吸引他们选择她的东西。
“法鳞姑娘?”为首的人类男性皱眉,“你是来给我们贡献你漂亮的屁股的吗?”
听完这话,几个男人都笑了。莱丝汀站在他们面前,看不出情绪。
“或许你们看来是的,但我还有更多有用的地方。”说着她翻了翻包拿出了一张地形图还有一包彩色的粉末,人类男性呼吸一滞。
“这是我这几天在山上走动的时候画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花斑鹫在这个季节中会出没,而这几个地方,现在你们能找到的人里只有我知道怎么去。”她指了指地形图上的几个叉,“花斑鹫成群。”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个出言调戏她的人类男性说,“我们只是普通的冒险者,捕猎野兽可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
“啊,得了吧。”法鳞不耐烦地轻轻顿足,看了看周围姑且小声说,“我在山里看到你们五次了。”
酒馆一瞬间安静了,有人的手摸向了自己的剑鞘。
“先说好,我不是治安官。”她歪了歪头,“不管你们怎样破坏森林的秩序,在不是狩猎的季节里捕杀偷猎,都和我没关系。我只是个孤苦无依的旅行者,普通地想要钱。”
—
在三天之后他们出发了,带满了足够锋利的兵器和弓箭与软毒,做好了完全的准备。由于战斗技能只有逃跑最强,她明确表示自己只需要三分之二的报酬,但也明确表示自己只会当向导。
“在这儿。”莱丝汀的手指着一棵树。那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树,根本没有迹象证明他们的猎物会在这里成群结队。又一次,有人的手握住了剑鞘。人类!活得短并如此缺乏耐心的生物。
“请不要太着急。”在被闪着光的剑指向喉间的时候莱丝汀举起双手,她转向那棵树,伸直了自己的胳膊够上树枝,似乎是从虚空中取下来一枚白色的果实。
为首的人类男性仔细看了一眼,立刻伸手拦下了那个拿着剑的人。
“为什么这里会有花斑鹫换下来的牙齿?”
“我以为你们知道。”莱丝汀开始把玩那个尖锐的牙齿,并把它收进自己的口袋里,“花斑鹫的幼崽和成体,成体的大小和猎犬差不多,还有很可怕的牙齿,但幼崽体型小得足够被蛇吃掉。它们的毛上有非常多的致幻剂,用来让鸟妈妈爱上它们,然后就像杜鹃,会把本来的孩子给顶替掉,然后自己掌握鸟妈妈提供的营养。”
“所以呢?这是人类喜欢它们的原因。毕竟它们产出‘魔法粉末’的皮毛可比金子贵。”
“所以,只需要找到宿主,就可以找到寄生虫。”她向上一指,抛出一颗小石头。本来平平无奇的树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无数的眼睛,仿佛一个幻像,上面长了出一对一对的绿色翅膀。
“叶鸟,像人类一样会成瘾,你们的猎物最喜欢的宿主。”莱丝汀抬头看着呼啦啦飞起来的鸟,音量接近喃喃自语,“这小树丛后面有栖息地。”
在鸟类差不多散尽之后,树和树之间隐秘的角落出现了一条由藤蔓植物铺出的道路,宽度大概能让一个人匍匐前进。警觉的偷猎者留了一个人在外面留守,而剩下的人钻进去。莱丝汀在前面带路,敏锐的耳朵听到后面的人又一次把剑拿了出来。她装作没有听到,继续向前爬去。如果在这里发生冲突,四对一,地形狭小,死的肯定是自己。而她要活着,并且要活到最后。
来到了小道尽头,光亮起来,她用相当利落的姿势一个前滚翻滚了出去。突如其来的阳光夺取了后面的人的视野,第一个人脸上被划了一刀,叫骂了一声,骂骂咧咧地再睁开眼睛时法鳞已经不见踪影。
“**,那个丫头在哪?!”他们或张开弓或拔出剑,摆出应战的姿势,如果法鳞落到他们手里,钴蓝色的鳞片必然也是囊中之物。但是现下他们没有办法了。法鳞带他们来的地方花斑鹫成群,那是当然的,春天的时候雌性猛禽会有相当大的脾气,偷猎者一抬头迎上的是好几百双盯着他们的凶猛竖瞳。这是规模相当大的巢穴,他们早该知道的,因此他们准备了所有的捕猎工具,但猎手的心态傲慢,他们落到了自然手中,成为了猎物。
莱丝汀在树杈上,隐藏在叶鸟中间,看着那些偷猎者被浪潮一般的猛禽扑咬,发出野兽一样的惨叫,又因为这个叫声被很多的猛禽包围。她看了看这些日子里喝酒喝光的盘缠感觉到了一点欣慰,通过铲除这些让“森林里的人们”头痛的家伙,莱丝汀或许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去处发愁了。
“我合格了吗,老师?”莱丝汀问。
然后一个声音从树的更高处传来:“欢迎你加入我们,莱丝汀。外面那个差点跑了的是扣分点,但是德鲁伊要注意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很多年可以慢慢学。”
——
全文1069字
——
对她的同学,她的爸妈,或者说她认识的所有法鳞来说,莱丝汀即使是在他们这样宽容的社会中也足够得到“乖僻”这个形容了。不光是“乖僻”,可能还有“怪胎”、“过于冷漠”、“危险分子”,总而言之——“不正常”。
她隐约地知道自己那份“不正常”,但好像也没想着应该改变它。在人生中的前二十年,法鳞社会对于“不正常”的宽容度反而让她失去了拥有矫正意识的唯一机会。她在法鳞的社会中都很难称得上是正常,而在出了家门以后面对数量庞大的人类更是如此。
莱丝汀有点惆怅地看着她还相处不久的新同事们(脸上却和戴了面具一样一块肌肉都没有动),三个人类男性,没有一个和她种族或性别一致的,天呐,以后的日子或许会被狠狠排挤。
刻板印象往往产生在对某种东西一知半解时。因为一直以来对整个智慧生命群体的无视,她对于人类的刻板印象深重,其中非常顽固的一条是他们都会排除异己。莱丝汀完全不在乎人际交流的事儿,毕竟她也并不特别希望和没茸毛也没漂亮鳞片的生物交朋友——但是狼群也告诉她工作中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这倒是让她犯了难。军主和优泽以及其他的神祇在上,难不成她要从现在开始学习怎么假装当个正常法鳞?
她看看左边的拉克斯劳夫,穿着黑衣带着面具,整个人透露出要在地狱门口散步的气息,并且什么时候走进去都不奇怪。她看看右边的林恩,像一只开屏会很受欢迎的孔雀,但是平静的面容下隐隐透露出胆战心惊。而队长呢?她在这几个人里抬头抬得脖子痛,正好被训话中的队长点到名:“……你们只需要听话就行了——法鳞,你也一样。”
她起初还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遥远的过去欠了谁的债和他有关系,亦或者是他的家破人亡有她一份而她并不记得,但现在看来只是队长天生脸就有这么臭。她用手指安抚着口袋里暴跳如雷的诺诺玛,清脆地开口:“是莱丝汀,队长。”
——好吧,看起来并不是大家都很正常,至少有两个人是早已经被排挤过了的。莱丝汀不为人知地松了口气。
其实她这些天也不是没试过假装正常这件事,在付出了微小的努力问林恩要不要帮忙守夜之后对方略带惊恐的警惕眼神让她放弃了这个做法。虽然原因其实是她暂时还不太清楚这边的职场规则,即在鲜血骑士团友善的态度才是最不正常的,可她下了一个错误的——也许没错的——结论:“我的队友都是怪人”。
而在这个队伍里怪人和怪人之间竟然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就像跪着飞奔的马*。这种微妙的平衡缺了哪个人都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而看上去除了队长的两位人类男性都很容易死的样子。命途多舛,想要寿终正寝估计得付出一些努力。而无畏的莱丝汀不太感到害怕,只是深深地觉得有些麻烦。
——
*用头飞起来的鸽子,总之用了这样的方式讲了


字数:2594
战斗参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9107354/
审问参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9107367/
感恩的心感谢队友们画了这么多让我摸(……)
————————————
“你知道吗?把老鼠放进碗里扣起来,然后不停地敲,老鼠就会往最柔软的地方打洞……等等,”法鳞忽然扭过头来,“我们有碗吗?”
“呃。”
在他哽住的同时拉克斯劳夫伸手过来敲了敲他的胸甲,动作自然流畅,“这也是碗形。”
“那么我们有碗。”莱丝汀把头扭回去,继续用她严肃冷淡的表情看着俘虏。
俗话说得好,一百桩抢劫里,九十九桩都起源于一时冲动,所以卫兵们才总是能在现场找到是什么和房主人脑门进行过亲切接触,显然拷问也是这样。
————————————
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这句话的意思在当下可以解释为:如果在一趟公务旅程中你实在没什么事情好做,可以选择性地开始发掘同行者们身上的优点,哪怕结论是没有——那么恭喜你,你知道需要丢下一个人的时候该先丢下谁了。此外这项娱乐活动还有一些更具收获感的变体,比如把优点改成缺点什么的……
碍于一些情况-法鳞和拉克斯劳夫回林子里去了,后者认为在水里全面地泡过一遭可能还不足以去掉他们沾上的东西,前者在伊莱恩的注视下点头认可-能让他玩这个的人就只剩下了伊莱恩本人。
伊莱恩·阿莫米安,有一类人就是这样,集合时第一个到,喝酒时最后一个醉,所以通常也能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平安回来的人;而这种人往往也不会很多,毕竟一张桌子上只有一个最后喝醉的人是最妥当的,如果有两个,情形就会演变得有些尴尬、相当尴尬,因为有些东西只在所有人都清醒或者只有一个人清醒时才能存放在水面下,两个人的时候就会被迫浮上水面,就像现在。
那几串拉克斯劳夫精心烹调(以野外标准来说)的虫子已经在火堆上辗转反侧出了一些焦味。
林恩松开了被他转着玩了最少二十分钟的钎子。
唉,这就是他说过的尴尬之处了。伊莱恩不会问他为什么一直在玩那根之前是拉克斯劳夫备用武器的烧烤钎子,也不会问他为什么醉在跳河之后暖身的饮酒里,又这么快清醒了回来,就像他也不会问伊莱恩为什么同意了那两个人一起去单独行动。毕竟如果有得选,他想伊莱恩也想要一份更轻松的工作。一份不用连决定怎么处理一些吃的都像在博弈的工作。
好吧,这就是博弈。一些,怎么说?那个很新颖精致的词汇,公事房间里的博弈。就是那种坐在办理公事房间里的人,彼此计较一些这份垃圾是你来丢,还是我来丢,如果你丢了说明你认可我的权威和方针之类的行为。
他抖抖手腕拎起了那几串虫子,希望这约等于向可敬的队长表达了他和他对队伍安定的向往完全一致,再没什么置身事外了的请愿。
——唯一令人欣慰的,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了一点凉爽,就像哪里终于忽然刮起了风。
————————————
杰克是瑞姆克尔最普通的那一种人。
他出生的时候梵沾血的旗帜已经在他祖祖辈辈的土地上安插了很久很久,久到比他能记住的最远的祖辈的名字还久。但他有八个兄弟姐妹,他的父亲有六个,他的母亲有十个,所以从他的父母再到他父母的父母都没人有工夫思考一些关于,比如,噢,在鲜血骑士团之前,咱们的领主是谁呢?咱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些季节神殿里的神除了季节,祂们还代表着什么别的呢?祂们的季节也像秋天一样萧条而肃杀吗?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诸如这些之类的种种问题。
杰克也没想过。他长得很瘦小,他出生到长大期间正好是最贫穷的几年,一些战争来战争去的东西吧,这个词在他的观念里类似于冬天会下雪,而下雪了就会冷一样,是一种不那么有规律的规律,也就是如果它来了,那也没什么办法的意思。
他长啊长,一年度过五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战争,可能是多过的这个季节让他长得比别人慢,让他一直都像小时候那么瘦小,让他在有一些人来挑选可靠的未来战士时因为他的瘦小而被青睐。
这会是个游荡者的好苗子。
于是他的父母就说,哦,好吧,那么请您带走他吧,为了梵带走他吧。
然后又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他说,嘿,长官,我们的任务是结束了对吗?我们只剩下要回到驻地这件事了对吗?有人点了点头,于是他又问道,那我能离开半天吗,我会追上你们的,我想回家看看,就在这里往北十几公里,我很多年没回去过了。
他的长官用一种他从没见过的温和神情同意了他。
所以他就见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选作战场的,他祖祖辈辈的土地。
他想,哦,是这样没错,先选走一些孩子,剩下的消耗箭矢,填平壕沟,是这样没错,梵是这样没错。
那天的队友里再也没人见过杰克。他们觉得杰克可能做了逃兵。
————————————
浇花的时候浇到路人的脑门上;
没看住的羊钻进同村的菜地里;
你养的狗对月抒情时你的邻居正在饱受失眠困扰刚刚安睡;
普通人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一些仇怨,对吧?而如果你是一名鲜血骑士,只要把会招来的仇怨再预计往上提个二十三倍左右、呃,可能是仇恨,总之,二十三倍,从质量到数量,你就做好应付它们的准备了,不管是什么。
意思就是,他真的不记得她是谁,他又对她或者她们做过什么了。另外,一边想别的一边打架也不是个好习惯,所以他赢了而她死了。
他盯着那张大半被烧伤覆盖的脸试图想起来点什么,那根被割开的喉管里还在汩汩地往外涌着,让他想起之前它嘶哑又尖厉的嗓音,应该是在质问他不记得了,或者问他们。火?火在梵的行动里那可完全不少见,太勤劳和太懒惰都能用它-哗,一把火过去,什么都没了。
树林里传出了他们约好的安全信号,他活动了两下肩膀,看见伊莱恩正忙着在另一具尸体上擦干净剑上的血;于是他吹了声口哨,指了指地上被他拿来扎穿过女袭击者肩膀的烧烤钎子说:
往好想,至少咱们不用想怎么丢掉这些烧烤了。
————————————
如果有得选,相信菲诺的牧师不是什么好选择。
那个并未穿着甲胄的牧师找上他们时,杰克相信没有人相信她——相信她们想反抗梵不如先相信她们改信了兀烈卡卡。
他们的不信任就像一顿饭菜摆在餐桌上一样摆在脸上,摆在肢体里,却又没人走开,于是最懂得人心勾当的牧师对他们露出了微笑。
噢,何不先听听我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两个战士,一个巡林客和一个德鲁伊,一行四人,只有四个,就在旅店里,明天将要扎进那片林子里去;而我呢?却刚好学会了一些吸引你们最讨厌的那种虫子的办法。
你们大可先去瞧瞧。
第二次从旅店门口经过的时候,他看到雷丽安娜干瘪蜷缩的眼窝里那颗眼球剧烈地震颤着,让斗篷下她面庞上一卷一卷翻起的皮肉像是深深的,干涸的血红的沟壑。
如果有得选,相信菲诺的牧师并不是什么好选择。但他们太渴望了,他们的渴望有多么多,他们的选择就有多么少。
————————————
“拉克斯劳夫杀了一个牧师阻止她施放神术。”莱丝汀·多纳汇报道。
然后她挥了挥手,一团纠葛在她脚边的藤蔓松开了一点,露出裹在里面的东西,“还有我俘虏了一个游荡者。你们有人会审问吗?”
沉默在河边持续了一小会儿。
故事回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