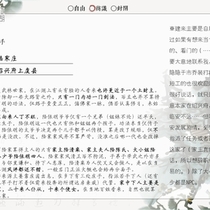永远忘记说一句,这次放前面讲,欢迎各种互动,有愿意跟我家小少爷玩的请自由地……私信商量也好,直接拖他出来只要剧情上不矛盾也没问题(……)不如说大感谢。
拖了好久的中秋剧情,借朱雀线跑了跑个人关系。
——————————
自记事起,陆依明未在陆家庄过这中秋团圆日,还是头一遭。幸喜有三两新友相伴,毕竟不致寂寞。
沈苑正文绉绉地含笑朝他举杯,道:“多谢几位赏光,我这小水阁子也是蓬荜生辉。”
岳无枫先笑道:“这哪里还蓬荜?生辉的显见也不是我们。”
苏飒听不下去,夹了块鱼塞给他:“吃菜,吃菜。”
映柳轩本就雕廊画柱,此刻灯火通明,照得一如白昼。这水阁子落于清波河上,有微风送来丝丝缕缕丹桂浓香,华贵间不失雅致。陆依明一时却有些恍惚。他抬头望去,月似乎是正正的一个圆,但灯光太亮,反而显得月色黯淡了。
沈苑在旁道:“是不是灯烛太亮,倒糊了月色?是我俗了,这便叫人撤下些灯罢。”
岳无枫道:“不可不可,本来就剔不清楚这些个鱼骨蟹壳了,再黑灯瞎火,可怎么好。”
苏飒一个掌不住,微笑道:“我竟不知你原是个除吃无大事的。”
沈苑笑道:“岳小大夫十分性情,反衬得我一说俗越发俗了,美味佳肴在前,正当认真来吃,硬是要附庸风雅,反而无趣。”
陆依明也不禁一笑,这位映柳轩年轻老板看着也是个谦虚谨慎的人,不料夸起自家菜来十分不脸红,好在这桌菜也经得起他这么自夸,反觉有趣。他努力集中精神,含笑举杯道:“正是不可辜负沈老板佳肴今日良宴会,此景此月,难得与各位同坐共赏,不如满饮此杯。”
话音方落,苏飒立刻握住他手腕,微笑道:“陆兄弟这杯,我就替了罢。”
岳无枫塞了一嘴的鱼,几乎笑喷,费了些力气方咽下去,向略见茫然的沈苑解释道:“咱们这位陆郎君酒量委实是,嗯,可以一看,上次才两杯就不行了,苏兄这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苏飒也笑道:“正是,大节下的,着实不愿意扛个人回去。”
陆依明不禁面上微红,只得放下酒杯道:“叫沈郎君见笑,在下确乎不敢多饮,不如饮些茶便罢了。”
沈苑也不强让,笑道:“自然随陆郎君的意。不过这蟹总可吃了吧?还有这味醋鱼,今日尤其须请陆郎君箸下再鉴一回。”
陆依明不料上回随口一讲,这位小老板如此上心,倒是有些赧然,忙下筷子夹了一块,细细品了,慢慢咽下,方道:“鲜嫩而不腻口,醇香而不醉人,在下这回也再没得可挑剔啦。”
沈苑笑弯了眉眼,道:“多承夸赞,沈某这顿饭请得就算是值了。”
岳无枫便朝陆依明挤挤眼睛,笑道:“一句话值这么一顿饭呢!怪不得陆兄这么有钱。”
苏飒又往他碗里搁了只虾球,道:“吃虾,吃虾。”
陆依明微笑着看他们笑闹,一边慢慢地吃着,却几乎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又饮了些薄薄的梨花酿,已觉不饿,顺手放下箸来。
“陆兄弟,这就吃饱了?”苏飒看着他。
沈苑道:“莫不是今日的菜肴不合胃口?”
陆依明忙道:“哪里的话,今日这些菜俱是色香味俱佳——”他张目往桌上看去,其实也只寥寥摆了几样,大约重点是持螯赏月罢了。便是这几样,他也全没尝出什么滋味,一时间夸不下去,“……我是体寒,不敢多吃蟹。”
岳无枫盯着他道:“有我在这里,你怕什么?——你放心,我自然不是说你闹了肚子我给你开药,是说我观陆贤弟气色,看着瘦弱些,中气是足的,再吃两只螃蟹也不会碍着什么。”
陆依明只余苦笑讨饶:“是我的不是,竟不能专心,平白负了沈郎君这席心思……其实也没甚么,不过想着家姊独自在外,不晓得这中秋过得好是不好。”
苏飒岳无枫对视一眼,两人一时间都不知如何接话。沈苑似是要问,觑着诸人神色,又闭了嘴。
陆依明自觉失态,心道这想是那几杯酒喝得,他怎好在中秋宴上一人向隅,累得举座不欢?便有些坐不住,道:“各位少坐,我稍去更衣,暂且失陪。”
诸人自然答道:“请便。”
沈苑道:“陆郎君可走这边厢,不必路过大堂。”
陆依明谢过,慢慢地去了。沈苑看他背影依旧挺直,倒不似是醉酒模样。待他转过角,方才问道:“陆郎君没事吧?”
岳无枫道:“喝多是不至于,他虽然量浅,但这酒甜得糖水一般,他又没喝多少。”
沈苑微笑道:“岳大夫嫌我这酒太薄,店中何尝没有醇酒,若是要饮,我这便取去。”
苏飒拉住他道:“怎好总劳动你,他也并不是个能喝的,不过这么一讲。”
岳无枫也挠挠头,嘻嘻笑道:“我怕是比陆贤弟只重不轻,苏兄要扛我回去更加费事,喝这青旗是正好。”
沈苑一笑,顿了顿,到底还是问道:“陆郎君是有姊妹孤身在外?”
苏飒与岳无枫对视一眼,一时都没答话。沈苑便知问得唐突,找补道:“非是要探问什么,只是想着舍妹在家也是孤单,若有陆家娘子无人陪伴,大可令她们姊姊妹妹的闲时一处谈个天做个伴。问得唐突了,二位莫怪,转天我跟陆郎君提便是。”
苏飒陪了一笑,道:“沈老板一片好意,倒没什么唐突不唐突的,只是我们也仅知他有位姊姊罢了,与他自幼一处长大,情份很深,旁的却也不知,问到我们这里,也是问道于盲了。”
沈苑点头道:“如此。”
三人原本无甚交情,沈苑又自觉说错了话,多少有些尴尬,也坐不大住了,便笑道:“还是岳大夫提醒了我,既然来了映柳轩,虽然我这青旗应也算得入口,但只喝这梨花酒也是可惜,我还是到前面去,叫他们送些黄酒来,给二位尝尝味道。”说罢站起一揖,也自去了。
苏飒寻思他是家主,毕竟没有留他的道理,拱拱手也由他去了。转头看时,岳无枫仍在细细地吃一只蟹钳子。不由笑道:“这能有一两肉?吃了这半天。”
岳无枫一晚上吃得又多又杂,吃相却并不难看,此刻更是慢条斯理。他放下那蟹钳,笑道:“不好辜负,晓不晓得?似我这般吃法,才叫不辜负了这只蟹来世间一遭。”
今晚四人之中,细究起来还是他二人最为熟稔。此刻只余他俩,倒也真是放松,闲聊几句,苏飒走到水阁边上看月。
他出了会儿神,轻叹道:“这城里中秋,实在热闹。我之前在山上,只得我和师父两个人,若不是还有块月饼,都不记得还有这节日。”
岳无枫道:“若是这般说,我也差不多,我师父常常连月饼都想不起来……不过,他之前救过的病人多,这种节日,总有人上门来送的,我师父多数都不收,除了极少人……那是当友人看了。也有时留友人与我们一起过中秋吃月饼的。”
“那终是比我和老头子热闹些。”苏飒道。这个话头起得很是不好,他正待换个事来说,忽然一念起,还未出口,只听岳无枫道:“我说,陆贤弟是不是去得太久了?难道是迷路了?那也不能,他们陆家庄,想来要比这个店只大不小吧,他早该惯了……总不成掉河里去了?”
苏飒摇摇头道:“莫胡说。只是确实,连那位沈老板,似也去得久了些……”
他回过身来,岳无枫早已擦干净脸和手,提起银针筒挂回腰间,一只手指向映柳轩大堂方向:“去看看?”
二人穿过回廊,越近大堂,越听得吵闹,似听得若干“唐门”字眼。走进大堂,果见一片吵闹,只不知吵嚷何事;总没看到陆依明;岳无枫眼尖,一眼瞅到沈苑站在角落,似在跟小二说话。他拉拉苏飒,一起走过去。
走近了,只见沈苑面色不甚好看,苏飒忖他身为老板,见人闹事,必是麻缠,倒不知是否该打扰。而沈苑一转眼已看到他二人,招呼道:“二位怎么也过来了?有什么事?”
岳无枫道:“你和陆贤弟再不回去了,我俩人怕陆贤弟掉河里,特来寻寻看。”
沈苑一怔,道:“陆郎君还未归去?——我这里是不料前面有些麻烦,慢客了,委实对不住。”
苏飒道:“这无妨,沈老板有事先忙就好。若我等有可襄助处,也请沈老板直接开口……不过,你也没见到陆兄弟?”
沈苑摇头道:“不曾。我还道他早该归去了。”
三人俱都皱眉,忽然那店小二怯怯道:“若是陆郎君……小的方才见他出去了。”
三人一愣,竟同时开口,沈苑道:“什么?你怎不早说。”苏飒道:“出去?几时的事?”岳无枫道:“往哪边去了?”
说完又是一愣,倒都发一笑。那小二道:“是、是,小的……小的见陆郎君追着那些人出去了,也或是追着那位娘子出去了,小的也不明白,这个,也不晓得几位客官在寻他,少东家勿怪,勿怪……”
沈苑见他慌了神,温言安抚道:“并未怪你。只是方才究竟何事?陆郎君来前边了?你不必着忙,说清楚就是。”
那小二道:“是。方才陆郎君自那厢来,本来似要从这边廊子回水阁子去,结果瞧见那位娘子和那两个莽汉争执,他们出去,陆郎君便径自跟了出去,也没交代甚么……”
三人听得一头雾水,岳无枫问道:“甚么娘子莽汉?你倒是慢些讲明白。”
沈苑道:“你莫慌张。是先有一位娘子在这边用饭?什么样一位娘子?跟什么人冲突?你仔细从头说。”
那小二也定了定神,道:“先头是一位穿蜜合色衣裳的娘子,就坐在这进门左边那角落,独自一人点了饭食用,吃罢了招呼小的过来,小的才来这边。那位娘子进店时并吃完了都拿纱蒙着脸,小的也没看清楚模样,单看身段是出挑的……呸,呸呸呸,小的再不妄论女客的,几位就当没听着。她叫了小的来,结了饭钱,还给了小的打赏,小的道她要走,不料她取出一块帕子,细细裹了右手,又去前面那桌,招呼那桌的两个莽汉道:‘你们是哪个门派的?’那二位客官便道:‘爷爷们是浪涛帮的,你是何人?’那娘子道:‘这店我很喜欢,闹起来不好。往北边去有开阔地,便去那边吧。’然后小的、小的也没看清楚,她就给了那两个莽汉一人两个耳光……小的瞅那二位也是回不过劲来,肿着脸发愣,这娘子把手上帕子解开一丢,道:‘脏了我的手。’扭头就往外走。那两位这才醒过神,自然是大骂着追了出去……然后小的就见到陆郎君也跟了过去。”
这小二定下神来,讲方才情状,倒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三人都听了清楚,却都没听明白。
沈苑道:“这……我观陆郎君不似多事的人,二位可有头绪?”
岳无枫道:“就算管闲事,他那性子,也必是要跟我们招呼一声的。”
沈苑道:“正是。也不知那位娘子是何身份……”
苏飒道:“八成是……”一句话却未说完,他顿了顿,道:“还没多久,我应追得上他,不得已,沈老板,要提前告辞了,实在对不住。”
岳无枫立刻道:“我也去我也去。告辞告辞!”
二人也不等沈苑答话,便出了门,一径向北去了。
没两步,苏飒便见岳无枫气短步沉,落在后面。苏飒虽不以轻功见长,究竟他自小习武,功底比岳无枫不知扎实到哪里去,也略顿了顿,拉起岳无枫手,以轻功带他。
岳无枫嘻嘻一笑,道:“谢啦。”一开口,真气却泄了,脚下立时一个踉跄。
苏飒白他一眼道:“还说什么话?闭上嘴跟上。”
岳无枫也不敢再开口,老老实实提着气,借着苏飒的力向前。
映柳轩建在清波门外,向北行去一路没什么人烟,幸而月色明亮,不多时,二人便至一方开阔地,地上横着两个人影。
苏飒停下脚步,岳无枫问:“是那两个倒霉蛋?”
走近了,果然是两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却是东倒西歪躺在地上,均是鼻青脸肿,还在呻吟喊痛。
苏飒抱拳道:“二位壮士,不知这里发生何事?”
一人道:“你你你,你跟那个娘们,啊呸,跟,跟那位女侠,是一伙儿的?!”
另一人抬手锤他脑袋,道:“一伙儿个屁!小子……不,二位公子,爷……我们被歹人打伤了,你们去给浪涛帮报个信,咱们必有重谢。”
岳无枫眼见这二人脑袋肿如猪头,听说话脑子也不似太灵光,强忍住笑,正色道:“二位受伤了?在下是个郎中,可先为二位诊治诊治。”
那二人大喜,先一人道:“小郎中,你快给爷爷看看,爷爷胳膊动不了了,哎哟,大哥你又打我?!”后一人也不理他,只向岳无枫道:“大夫,你先给我瞧瞧,这右腿好像断了!”
岳无枫俯身略一查看,果然先一人两边胳膊脱臼,后一人断了腿骨,另有若干淤青伤痕。岳无枫便抬眼看苏飒。苏飒叹了口气,道:“你要治就治,我难道会拦你?他也不是个不着调的人,不差这会儿工夫。”
岳无枫嘻嘻一笑,向那二人道:“这位胳膊脱臼,我接上去还简单;那一位是骨折,我现今连个夹板都没有,贸然诊治,将来长得不好,反而不美。我还是先为这位仁兄接关节。”见二人没甚话说,便先去摸那人左臂,一面漫问道:“不知何人如此凶残,伤了二位仁兄?”
那胳膊脱臼的莽汉怒道:“可不是!那小娘皮凶得紧,我二人不过讲些江湖上的故事,关她什么鸟事?况且也不是我们编的,那峨眉的苍云老道没个正经,跟峨眉山上尼姑——哎哟!!!”
他突然杀猪也似一声大喊,连岳无枫都被他吓了一跳,后退一步,方笑道:“好啦,仁兄这左臂无碍了。”
那莽汉一阵剧痛,正要骂人,听得这话又愣了愣,动了动胳膊,果然好了,复又喜道:“是了,快给我接右胳膊。”
岳无枫笑道:“这个,却是不巧,在下没有时间了。”
那莽汉一怔:“什么?”
岳无枫道:“这位仁兄的腿,还是快些送医馆疗治的好,拖太久,恐怕……”他故意拖了个长音,也不说完,更不等他二人回话,拉了苏飒就走。
那莽汉呆了半晌,方自地上爬起来,待要去追他,却被地上那断腿的抱住脚,道:“老二,你去哪儿?”那莽汉道:“追那郎中给我接胳膊啊?”那断腿的道:“呸,就知道你那胳膊,没听他说?再不治,你大哥我这条腿就废啦。”那莽汉呆道:“那该如何是好?”那断腿的道:“蠢货,你腿又没断,快回帮里找人去啊!”那莽汉如梦初醒,连声应是,一溜烟往城里去了。
苏飒跟岳无枫虽然走在前面,身后这些动静也听得清楚,岳无枫笑得不行,道:“两个猪头,峨嵋派也是好议论的?”
苏飒沉默一会儿,方道:“我依稀记得,陆兄弟家的那位姊姊,便是峨眉派苍云禅师门下弟子。”
岳无枫呆了一呆,道:“哇,那刚才那两个猪头便是被他姊姊打的?若将来见到,可别说我给他们接了条胳膊,早知道他们乱讲别人师长,活该被揍来着,我也不给他接了……不过,这位姊姊下手也是……可别叫她知道我帮那俩猪头,真怕她连我也打。”
苏飒道:“怎么,他们的伤很要命?”
岳无枫道:“要命是绝不至于,咱们这位峨眉女侠出手分寸好得很,虽然伤筋动骨,但若接上骨,好好休养数月,也不难痊愈,再落不下病根。我看那俩人一个断腿一个断胳膊,怕也是故意的,留下个会走的回去找他们的人,倒没真不想给他们活路。她便是陆兄弟的姊姊?那也真是常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苏飒道:“我也不知。且寻到他问问便是。”
岳无枫道:“是了。他也不能有了姊姊,便不要兄弟罢?”
苏飒笑道:“你瞎说什么?”
岳无枫吐吐舌头,也不再废话,专心行路。未走几步,苏飒突然停下。
岳无枫问道:“怎么?”
苏飒抬手指前方,道:“似乎在那边了。”
岳无枫功夫粗浅,耳目毕竟不及他灵便,轻轻又走了几步,才看到,前方一片竹林间,确有两个人相对而立,一个影影绰绰是陆依明,另一个是个女子身形。
苏飒犹豫道:“咱们便去找他?”
岳无枫挠挠头,低声道:“我看咱们且不去扰……”
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那女子极清脆一个耳光甩到陆依明脸上。二人愕然,面面相觑一会儿,便是傻子也知不好立刻去打招呼了。岳无枫拉拉苏飒衣角,二人也躲入竹林子中。
只听那女子厉声道:“我还敢有你这样的弟弟?”
陆依明抬头道:“姊姊……”
女子叱道:“闭嘴!你要算计我,我不生气,可你竟敢辱我师门,毁我恩师清誉,打量我还容得?”
陆依明急得踏前一步,道:“我没有!姊姊——”
他这一声戛然而止,却是那女子飘然一退,一柄长剑已经架到他颈间。
岳无枫吓了一跳,几乎要出去,却被苏飒一把按住。岳无枫看他一眼,也是会意,再看时,那女子果然并无动作,只是冷然道:“你装得很像。你自然是很会装的,要么就是我太蠢,十二年都骗了,现在再装两下,岂不是平常得很。”
半晌默然。陆依明再开口时,声音涩然,低声唤:“姊姊……我不是有意骗你,只是……只是……便是怕你生气。”
“怕我生气?”那女子冷笑两声,忽然收了剑,转身就走。陆依明刚在后面追了两步,那女子又叱道:“别跟着我!”陆依明脚下一滞,当真未再抬起,只轻喊道:“姊姊,回家去吧,爹娘都很担心……”
那女子的声气道:“你是谁?轮得到你管?”女子轻身功夫上佳,尾音传来时身形早已远去。
一时只余陆依明站在原地,呆呆出神。苏飒与岳无枫对视一眼,皆不知如何是好。
正自茫然间,忽然陆依明转过身来,朝他二人方向走来,脸上笑得勉强,道:“苏兄,岳兄,可是叫二位兄弟担心了?”
原来陆依明知他二人在此,也不知是何时起察觉的。苏飒大感尴尬,又看岳无枫一眼,岳无枫也笑得有些讪讪,迎上去道:“陆兄弟,这个……我俩见你久不回来,怕你迷路……呃,你……我俩……总之……你别想太多……”
他语无伦次,陆依明倒真笑了起来。他握住岳无枫一只手,柔声道:“我晓得,多谢。”
苏飒道:“这是……怎么,你姊姊与你起了误会?我们……可有能帮你的?”
陆依明摇摇头,低声道:“——想必方才……都见到了?那二人,你们一路过来,大约也见到了……”他叹了口气,低声道:“姊姊说那二人是我雇的闲汉,故意引她现身。”
岳无枫奇道:“她这也太没道理——”苏飒暗中扯扯他袖子,“呃,我是说,你又不会知晓她在店里。”
陆依明还是摇头,道:“那映柳轩安静轩敞,饮食精致,那桂花糕我一尝便知必合姊姊的口味……她想必也晓得,我自然是会知道的。唉,只怪我忽然现身,委实不是时候。”
三人相对默然半天,岳无枫挠头道:“既然是误会,那你也不要太过烦忧,亲姊弟哪有为了这个真结了仇的?待你姊姊想明白,自然会来寻你。”
陆依明苦笑道:“多谢。”
三人一时又是默然。
此处再无人烟,只有一轮圆月光辉惨白,映得竹影幢幢。末了是苏飒道:“陆兄弟,咱们且先回去吃……或者咱们先会客栈歇息罢,你也累了。”
陆依明低声道:“是了,我不告而别,委实辜负那沈老板一番美意,非得向他赔罪不可……只我现下……想沿西湖走走,二位兄弟先回罢。”
“少爷。”胡叔唤道。
陆依明不紧不慢地轻轻拍打着客栈的芦花枕,第七次答道:“胡叔既要睡通铺,我自然也随胡叔。”
胡叔皱起眉看看他,又低下头,似是思量如何劝他。
这龙翔客栈坐落在临安府中心,陆依明打听得此处最是繁华热闹,来往人众络绎不绝,便带了胡叔径自奔此处来:他们要找人,自是寻个热闹所在,便于打听消息。只是这来往人多,客栈的头房只余了一间,胡叔便要自去睡通铺,陆依明哪里肯依,一径跟了过来,这却是胡叔不能依他了。胡叔是个倔脾气,陆依明也不打算让他,两人就此僵持不下。
胡叔又道:“人多,不洁净。”
陆依明张眼望去,此刻人还不多,只墙角燃灯烛处有两个年轻人,正在一处说话。一屋子床铺挨挨挤挤,被褥枕席皆是旧得看不出颜色,但所幸浆洗得尚算洁净。陆依明也不辩驳,解下披风,轻轻一抖,盖在床铺上,又伸手将褶皱与边角摊平整,转头笑吟吟道:“现下洁净了……胡叔?”
一句话未得说完,却见胡叔忽然立起,身形一闪,晃到房屋一角,正是那两人所在,胡叔更不打话,伸手便向那竹青衫子少年抓去。旁边灰衣青年见机得快,迅速举起长剑横在中间,剑未及出鞘,胡叔变爪为掌,向他肩头拍去。灰衣青年竟不闪不避,反而向他掌上迎来,末了不知怎的一纵身,胡叔“噫”了一声,向后跃开来。
这几下兔起鹞落,陆依明都未看清最后那灰衣青年如何还手,更是不及反应,见胡叔退开,才慌忙冲上前去,拉住胡叔道:“没事吧?”
胡叔摇摇头,陆依明见他吐息平稳,确无异状,这才放下心来,抬头看去,对面那青衫少年也是一脸焦急,大约也是在询问情况,那灰衣青年也是摇摇头,然后横剑在前,向胡叔寒声问道:“尊驾何人?不知我这小兄弟何时曾得罪了尊驾?”
胡叔摇头道:“不曾。”
陆依明心下着急,他先前隐约听得这二人喁喁私语,似曾议论到他主仆二人,然而他也知道,胡叔就罢了,自己这身打扮着实不似来睡通铺的人,这二人眼见是年轻好玩,随口议论两句,也是寻常,看来也并无恶意。胡叔想必也听在耳内,然而便为这个就要出手教训?陆依明虽不曾行走江湖,不知深浅,却暗觉不甚合适,胡叔偏又如此寡言,他只好代胡叔行了个礼,道:“惊了二位,实在惭愧……”
“非是惭愧不惭愧,”那灰衣青年说话时老气横秋,“我二人若做了甚不妥的事,自当向大少爷你赔罪,但若无事,也请这位高人给个交代。”
陆依明无法,只得焦急地看回胡叔,胡叔伸手一指,道:“何物?”
几人循他手指望去,只见那青衫少年掌中托着一张白纸,纸上盛少许灰色粉末。这年轻人显见方才也是呆了,此刻终于恍然大悟,高举起手,笑道:“这位老……呃,大侠,敢怕是以为我要下毒不成?这只是些许安神助眠的药物,我是个郎中,哦,二位方到这厢,有所不知,这屋子里昨夜睡了个大汉,半夜打鼾,打得啊,那——叫一个山崩地裂,”他边说边举起空着的那只手来回比划,“我俩一夜都没合上眼,今日赶着去配了些药,是要放到这灯油里,不过为睡个好觉罢了。”
陆依明看时,果然二人眼下乌青,又见那年轻人笑得一片纯然,已是信了,低声道:“胡叔……”
胡叔也不理他,朝那青衫少年伸出手:“我看看。”
对面那灰衣青年伸手一拦,青衫少年拍拍他手臂,越过他上前,坦然将那片装着药粉的纸放到胡叔掌心,嘻嘻笑道:“别洒了,我好不容易弄了这点,晚上睡觉还指着它,你二位要是睡这屋,八成也得靠它呢。”
胡叔拈了一点在指尖,轻轻一搓,又放在鼻前嗅了嗅,这才点点头,重新将药粉递回,抱拳道:“抱歉。”
陆依明放下心来,也跟上做了个揖:“误会一场,惊扰二位,实在过意不去,还望二位兄台海涵。”
那青衫少年登时眼睛一亮,笑道:“不妨事不妨事,都说了是误会,贤弟,勿要放在心上。”
那声贤弟被他叫得响亮,陆依明一怔,看到他神色忽然醒悟:这年轻人看去也似初涉江湖,莫不是为一句兄台高兴非常?那灰衣青年神色便有些尴尬,干咳一声,也拱拱手,道:“既是误会,好在无人受伤,这位……公子,也不必放在心上。还要多谢这位前辈手下留情。”
胡叔摇头道:“你,也未拔剑。”
他二人虽过了两招,但各自均是手下留情,陆依明自然也看得出。那着青衫的小郎中又笑道:“便是受伤了也不打紧,这不是有我吗?”他拍完胸脯,又挠挠头,“呃,不过,能不受伤,还是不受伤的好,能不打架,还是不打架的好……能不睡通铺,依我看,你还是不睡通铺的好。”
陆依明见他说得有趣,不禁一笑,向胡叔道:“不错,这位岳兄说得极是,胡叔便跟我住头房罢?听店家说,头房大得很,住我俩也不成问题。”眼见胡叔不答,又补上一句:“胡叔,你方才无故对岳兄出手,便是欠了人家一笔,怎好立时又不听人家的话?”
岳无枫大约也没想到他如此能顺杆爬,呆了一呆,张了张嘴,又没说话。陆依明略含歉意地冲他一笑,还待再说时,胡叔竟然终于点了头:“好罢。”
陆依明心下欢喜,又转身拱手道:“岳兄,还有这位……少侠,此处既是睡不安,不如也跟在下住过去?我听店家说,他们头房一间房也分内外两间,二位若不嫌弃,住过去好歹安静些……”
话未说完,便觉胡叔在一旁拿眼瞅他,他心下微觉不妥,便住了声。对面岳无枫眨眨眼,笑道:“这就不必了,有我这药粉,今晚必得睡个好觉,贤弟难道不信我的手段?”
陆依明忙道:“这怎能?”欲待夸他几句,方才发觉自己从未见识过这位小郎中“手段”,夸也无从夸起,一时语塞。
好在岳无枫并不在乎,拍手笑道:“这便是了,贤弟你只管回去睡。且慢,我叫了你这半天贤弟,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那灰衣青年一直默默立在一旁,此刻大约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道:“都不知道人家名姓,就知道人家比你小了?”
陆依明微笑道:“在下姓陆,陆依明,耳字边陆,白日依山尽的依,日月明。今年十八岁。”说罢又觉胡叔在看他,心中微微一动,想是不该跟陌生人如此兜底?然而报个年纪该当不妨罢,况且这岳无枫性子十分可爱,那灰衣青年虽话不多,却也教人感觉十分亲切。
岳无枫自不知他心思暗转,得意地冲灰衣青年扬扬眉毛,笑道:“你看!我是大两岁嘛!”一面向陆依明道:“陆贤弟,他叫苏飒,又比我大了两岁,你别看他这副样子,其实功夫挺厉害,人也很好。”
苏飒面上一红,嘴上却道:“甚么叫做这幅样子?”
陆依明其实未曾料到那岳无枫生得面相稚嫩,倒真比自己大,面上自不带出,只含笑抱拳,再次见礼道:“岳兄,苏兄。”
苏飒也展颜一笑,回礼道:“陆公子。”
那岳无枫很是欢喜,大有拖陆依明坐下长聊的架势,胡叔忽道:“少爷,不早了。”
苏飒看看他,道:“正是,咱们各自安歇吧。”
岳无枫似乎有些不情愿,但也道:“是了,看我把药粉先放到烛火里去,苏兄,今日咱们可得好好睡一觉。”
陆依明只得道:“那便不扰二位了。”心念一转,又道:“二位若无甚事,明日在下做东,请二位吃酒如何?权作为今日之事赔罪。”
岳无枫眼睛一亮,道:“今日之事倒不算什么,不过我看,这酒很是吃得,苏兄,你说是不是?”
苏飒微笑颔首道:“自然可以。左右无甚要事,我明日只是要去接些悬赏,何时都使得。”
定下了约,陆依明不再盘桓,告辞去寻店家要上房。一间上房顶二十铺通铺房钱,陆依明又添些打赏,道是换来换去平白劳烦了店家,店家自然十分乐意,巴不得他再换来换去个几遍。
那头房说是两间,其实不过是一间大房,中有屏风隔开,好在十分整洁安静,陆依明暗自松了口气。胡叔又坚决不肯跟他同榻,更加不肯自己睡床叫陆依明睡地上,陆依明实在拗不过他,只得请店家厚厚铺了铺盖在外间地上,二人各自洗漱安歇。
不料到得半夜,陆依明到底不惯外宿,忽然惊醒时,便听得外间声气不对,轻唤两声,也无人应答。他连忙出来,只见胡叔面色潮红,呼吸浊重,还紧皱着眉,竟似是病了。他兀自不信,伸手探时,只觉胡叔额头一片滚烫。他们习武之人身强体健,这十多年他从未见过胡叔患病,一时大惊,轻轻推推胡叔,再次唤道:“胡叔,胡叔?你可是身子不适?”
胡叔勉强睁眼看了看他,吐出一口浊气,又闭上眼睛。
陆依明哪见过他如此,更是着急,道:“胡叔,你别担心,我去请郎中。”起身就要走,胡叔一把拽住他袖子,低声道:“宵禁。”
陆依明急得跺脚,又不敢硬挣:“这当口还管什么宵禁?胡叔,你且放开我。”
胡叔道:“不可。初到临安,人生……地疏,不可乱闯。”他这几句话说得衰弱断续,仍是坚持说完了。他平时尚且少说这么长的话,陆依明越发难过,连忙道:“是,是,胡叔,我听你的,你没力气,便不要说话。”
胡叔果然似耗尽力气,闭目养神。陆依明急得团团转,只是无奈何,忽然间看到桌上灯烛,眼前一亮,忙忙道:“胡叔,你且歇息,我去去就来。不出这客栈门,总犯不到宵禁了罢!”
说罢,生怕胡叔再拦他,也不待胡叔答他,立刻出了房门,径自奔去通铺,也顾不上是不是扰人清梦,直走到墙角处,揪起人便道:“岳兄,岳兄,岳大夫,救人,救人。”
不料那人立刻闪避开来,听了他这句话才长出口气,道:“我是苏飒。险些拔剑砍你。”
陆依明一怔,这才知觉自己孟浪,却顾不上赔罪,急忙道:“岳兄可是在旁边?”
边上一人拉住他道:“你冷静些。救谁?胡叔么?你莫慌张,我这就随你去。”正是岳无枫声气,他在一旁早已醒来。
陆依明到底年轻,急得无可无不可,好在岳无枫苏飒俱都体谅他,随着他飞速奔回头房。
岳无枫看到病人,神气又与白天笑嘻嘻的一派天真不同,面色沉肃许多,蹲下身查看胡叔面色、眼底、口中,最后才去把脉。陆依明见他如此,倒比白天更觉他可靠,本是病急乱投医,此刻平白多出五分希望。又有苏飒在旁拍拍他肩膀,低声安慰他道:“你莫急。小郎中人虽跳脱,医术很可信得过,我前日受了些伤,他几针下来,我便全好了,你看,此刻活蹦乱跳。兼且我观胡前辈这,说不准只是风寒,想必不是甚么疑难杂症,你不要太忧心。”
苏飒一副少年老成模样,陆依明心下似早觉此人可靠,此刻虽明知他是宽慰,未能全信这年轻郎中当真医术神妙,毕竟定心不少。
此时岳无枫冲他二人“嘘”了一声,二人忙闭上嘴,就见岳无枫面色凝重,俯身去胡叔胸前,耳朵贴到他心口听声。听了半晌,终于站起来。
陆依明急忙问:“如何?”
岳无枫微笑道:“不妨,这位胡前辈似是多年之前受过内伤,如今旧创复发,虽然病征不好,但并无性命之忧,只是难受一阵子罢了。如今有我在,他难受也不用多难受了,我替他扎几针,就算明天不好,后天也能跟苏兄一般活蹦乱跳啦。”
陆依明一呆,道:“我竟不知胡叔有内伤在身,这些年也从来没见他犯过……”
岳无枫道:“是么?许是今日跟苏兄动手,引动真气的缘故?他这内伤,是有古怪寒气侵损心脉,绝不致命,但偶有发作之时,人体玄妙,自然发热与之相抗。这寒气古怪,我也拿不准因何发动,听你说,竟是深潜十多年不发,当真诡谲。”他说着叹口气,道,“若是我师父在此,或者能为他彻底祛除这寒气,我却是没这个本事了。”
岳无枫说起医道,自有一番侃侃而谈的风流态度,陆依明已是信了他,一揖到地,道:“求岳大夫援手,先令胡叔不再……这样,也是好的。”
岳无枫挑眉道:“你既然要求我,怎么还如此见外,忽然又成了岳大夫?罢了罢了,我不跟你计较。”说着一笑,自腰间取下一只银筒,倒出数枚银针,神情又转肃穆,便为胡叔施针。
陆依明不敢扰他,只得眼巴巴地等,好在岳无枫出手极快,顷刻间扎了十数银针下去。当真是有些门道,胡叔喘息登时便平和许多。不知过了多久,陆依明只觉时间漫长,岳无枫终于收针,重新笑眯眯地,起身道:“好啦!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再开个方子,明日白天抓了药服下,保管他明日晚上就没事啦。”
陆依明看时,果然胡叔面上潮红已褪,额头也不再滚烫,呼吸平顺,真是沉沉睡去。陆依明一口气松下来,方觉背后凉飕飕一片,想来是方才出的汗。又一回思,不禁尴尬,赔礼道:“多谢岳兄援手,不知何以为报。方才又那般唐突,还有苏兄,在下一时心急,冒犯了你,真是……对不住。”
岳无枫抢道:“你又见外!家人病了,哪有不着急的?我见过的比你离谱得多的病人亲友多了去啦。况且你喊我岳兄,我帮贤弟家人诊病,要什么报?”
苏飒也道:“我方才险些当你歹人,拔剑对你,也是唐突,就算扯平。”
二人如此和善宽厚,陆依明只觉再不能负他二人美意,也不再纠缠,洒然道:“二位兄台既如此说,在……我也不便再婆婆妈妈了。打扰你们清眠,很是过意不去。”末了一句却不自觉又客气了回去。
岳无枫噗嗤一笑,摆手道:“不妨事!那,我们回去继续睡了?”
陆依明想要留客,四下一看,实在没多余铺盖,只得道:“正是,恕我不能相送了。”
二人均道不妨,自回去休息。
陆依明到底是送他二人出了房门,回过身看胡叔,这才想起很该把他放到床上去,方才岳无枫也未讲不能搬动,想来不妨。他蹲下身想要把胡叔打横抱起,不料胡叔看去瘦小,身量不轻,他试了两次,竟抱不起来。他也是自小锦衣玉食的出身,何曾做过这活计,当下手忙脚乱,末了连拖带拽,才总算把人弄到床榻上。胡叔一直一声不响,放平了看,仍是睡得平稳。
陆依明熄了灯,只留了一支暗烛。他本待靠在一旁案几守夜,但他这一下不知是因突然放了心,还是因疲累,没几时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待他猛然惊醒时,桌上蜡烛已快要燃尽,天色已大亮。他呆了一呆,方才醒过神来,一看床榻上却没了人。他立刻跳了起来,背后一物滑落,转头看时,却是他自己的披风,他分明记得自己昨日本未曾打算睡,更不曾披衣物。他刚刚醒来,难免迟钝,过了一会儿才省起去看桌面,果然一封短笺端正放在那里。打开看时,字不甚佳,然笔力苍劲,一并没抬头落款,正是胡叔风格:
知少爷早想闯荡江湖,老奴不想做妨碍。料娘子亦须少爷寻回,此事老奴回去跟老爷讲去。老奴身子见好,正好回府修养,少爷勿念。江湖险恶,人心隔肚皮,不可太轻信,便是年轻面善,终是要提防些。
这短笺全是口白,朴实无文,市集随便揪个代写书信的怕也比这文字好些。然而陆依明看了两遍,体会话意,不由得痴了。
正出神间,忽然房门被扣响:“陆贤弟?怎的睡到了这时辰还未起身不成?胡叔可还好吗?”是岳无枫声气。
陆依明一顿,伸手把字笺丢在烛火上烧了,口中应道:“就来,岳兄稍等。”纸笺很快燃尽,他这才起身,拉开房门,笑道:“岳兄,苏兄。我真个竟睡过了头,方才衣冠不整,怠慢了。”
岳无枫笑道:“都是男人,整不整怕什么?胡叔怎样,咦,他人呢?”
陆依明叹了口气,真正苦笑起来:“我睡醒一看,他已留了信走了。”
岳无枫奇道:“啊?留了什么信?”
陆依明摇摇头,道:“我自幼多在家中长大,未曾独自出门,便是跟家人一起,最远也只到过两次绍兴府,哦,那时还叫越州。阿爹阿娘不放心我,我也便不说我很想出去走走……不想……”不想胡叔还是看了出来。胡叔看了出来,不晓得阿爹阿娘看不看得出?这桩心事看得出,更大的那桩,又有没有人看得出?……反正,姊姊肯定没看出……
他心思转得快,虽然恍惚出神,却也只是一刹那的事。转过来,就见岳无枫瞪大眼睛看着他,似乎不知说什么好;苏飒也盯着他,忽然柔声道:“要说这个,那我们也都是一般的。我师父这次放我下山,难得得很。”
岳无枫这才雀跃起来:“对对对!我师父也是,难得肯叫我自己下山来。”
陆依明虽还在忖度胡叔字笺最后那几句,到底是心下温暖,微笑道:“你二人倒都在山上有个师父,想来也是缘法。”
苏飒问道:“你没有师父么?”
这苏飒向来一副少年老成模样,这话却问得陆依明笑出来:“我有很多师父,不过认真算起来,大概都不能算师父……我爹才算是我正经师父。”
岳无枫道:“你有爹爹……”忽然笑着拍拍手,“爹爹是师父,那也是有师父。”
陆依明不知为何,差点冲口而出“我爹爹也不是我爹爹”,及时吞下,笑道:“你说得很是。有师父这点,我们三人都是一样的。”
岳无枫笑道:“那多好!——胡叔经我施针,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开个方子,其实用不用也都可的。我看他功夫好得很,你不要担心。”
陆依明道:“方子……他倒带着走了。”
苏飒也道:“那更不必忧心了,胡前辈必也是知晓爱惜自身的人。”
陆依明按下心中诸般思绪,笑道:“说的是。走罢,我还欠二位一顿酒吃呢。”
岳无枫道:“是是是,我要吃最好的女儿红!”
苏飒笑道:“若是吃醉了,我可不管。”
陆依明也抿唇笑道:“我负责,岳兄吃醉了,我来背他回房。”
苏飒无奈何。
然而谁也没料到,这顿酒,最先喝到桌子底下去的,是陆依明。苏飒揪他起来,哭笑不得:“你这两杯倒的量,凑什么热闹?”
陆依明朦胧睁开眼睛,忽道:“你会不会害我?”
苏飒一呆,陆依明已自哧哧笑起来,道:“我知你不会害我。我一见你便知。是不是?你说,说你再不会害我。”
苏飒心知不能跟这小醉汉一般见识,只得低声道:“我再不会害你,放心罢。”
岳无枫也吃了一碗酒,笑得打跌:“待他醒了跟他讲,看他不羞死。”
苏飒苦笑着把他放回桌上,拎起一碗酒灌了下去,却喝得急了,咳了起来。岳无枫笑了陆依明笑他,正忙不过来,忽然“哎唷”一声,把椅子坐翻了。好容易爬起来,苏飒也正瞧着他闷笑。
三个年轻人无甚来由,就此笑作一团,都喝了些酒,人人双眸晶亮,便是吃醉了的陆依明,也是神采逼人。这江湖中,便有千重风雨万种浪涛,此刻总是还未曾淋到他们身上。
岳无枫举起酒碗,笑道:“来来来,吃了这杯酒,咱们便是好兄弟啦。”
——————————
写了这么久,还没能拐到主线,我好焦急……
感觉大家都在喊打喊杀了,我家小少爷却是十分居家,不枉我给他安了个巨蟹座(。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念了这两句诗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一身霜色衣衫半新不旧,腰间斜佩长剑,望着眼前粼粼水波,正自出神。这诗是诗仙李太白传世名篇,六岁小童亦可诵得,然而当真来到镜湖、站到若耶溪畔,忽然这两句涌上口边,意趣与在书斋之中学得,自有不同。想李太白彼时虽不得意,乃有古来万事东流水之叹,然而这诗的气象胸襟,大开大合,毕竟不是凡人所有。
正自乱想时,他身侧一老仆弓弓身问道:“少爷,什么吩咐?”
青年回过神,摇头道:“并无甚吩咐,不过自言自语罢了。这若耶溪这般景致,我居上虞,几步之遥,却未曾得来过几次,实在可惜。以天下之大,不知更有多少秀美山川,只怕终生不得一见。”
那老仆身量不高,瘦骨嶙峋,肤色黝黑,头发斑白,一身短打扮。却与一般下人不同,听了青年人这话,也不凑趣,只听得未曾吩咐他,便呆着脸一声不答。青年人也不介意,真个当自言自语,又去看水光。
此刻是晌午时分,虽连日晴天,毕竟入了七月已不太热,这一主一仆,似富家子弟郊游玩耍,闲适得紧。青年人忽然脸色一滞,道:“胡叔,咱们这便走吧。”
说着信手丢给旁边艄公一块碎银子,快步走上早备在一旁等他二人的小舟。那胡叔仍是不答话,低着头跟在他后面上了舟。艄公得了银子,喜笑颜开,解了绳索,也跳上舟来,长长念一声:“走嘞——”,便要撑船。
胡叔忽道:“且住。”
艄公刚拿起篙竿,尚未沾水,抬头赔笑道:“客官还有什么吩咐?”想是那小块银子功劳,这艄公方才还爱答不理,此刻热情了许多,便是对胡叔也恭恭敬敬起来。
那青年人原本容色和善,眉眼间总带一丝盈盈笑意,此刻蹙了眉,轻轻跺跺脚道:“我说,开船。”
胡叔唤道:“少爷。”拿眼去看他。
青年人虽不愿转头,渐渐被看得不自在起来,终是叹了口气,道:“唉,是我的不是,胡叔莫怪。”转眼见艄公一脸怔忡不知所措,又微微一笑,安抚道:“船家不必慌,我们说几句话就走。”
此时方有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骑奔了过来,至岸边方有一人滚鞍下马,向青年人行礼道:“可算追上少爷了。”
青年人此刻倒舒展了颜色,笑道:“章师父,何事劳得你老人家出马?我爹还是不放心么?”
那章师父是个苍头老人,看去筋骨却是硬朗,和那胡叔对视一眼,苦笑道:“少爷,老爷说了,请少爷回去。”
青年人没半分异色,仍是含笑道:“我不回去。”
那章师父似也料到,干笑两声,道:“少爷,有什么话,回去自可跟老爷当面谈,还请少爷别叫老章头为难。”
“我岂能叫章师父为难?”青年人忙道。这章师父是他拳脚启蒙师父,他向来以师礼待,此刻章师父这话很有几分倚老卖老的意思,他不能叫他不卖,却也不想买。一边思量,一边细声慢语答道:“只是这一趟,我非去不可,也非我去不可。烦章师父跟我爹说一声,我必将找……带那人一齐回去,请他老人家安心才是。”
那章师父一脸难色,道:“少爷有所不知,此事……此事老爷自然安排别人去,”青年人不肯明说何人何事,他也跟着含糊称呼,“倘若真是不得,老爷说了,他可亲自出马,断没有不成的道理,叫少爷不必担忧,还是先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青年人沉吟片刻,忽道:“章师父,你在我陆家,有三十年了吧?”
这话风马牛不相及,那章师父一脸莫名其妙,答道:“老章头自徽宗爷元年便在陆家服侍老爷,今年是……第四十三个年头了。”
青年人点头道:“我今年才十八。陆家的事,章师父知道的,是比我多的。”
那章师父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答道:“不敢。”
青年人微笑道:“章师父不必紧张。章师父是个聪明人,胡叔也不是外人……我便明说了吧,阿爹为何唤我回去,姊……此事是如何起的,我约莫也知晓。章师父自然更是心中明镜一般。”
那章师父便拿眼去看胡叔。胡叔仍是低着头,呆着脸,一言不发。青年人道:“跟胡叔无关。章师父还不晓得胡叔?最是惜字如金,若一次跟我讲话多过十个字,我便可去上炷香了。”
章师父赔笑了两声,再开口却道:“老奴不明白少爷的意思。”
青年人不以为意,挥挥手道:“那也无妨。章师父只消跟我爹娘说:养育之恩深重,依明粉身不足报春晖片缕;姊姊也是爹娘亲骨肉,我亲姊姊,自我幼时一处长大,待我极是友爱。我陆家只这四口人,素来相亲相爱,一体同心,自当毫无嫌隙,亲密无间。当此乱世,更是如此。世道不太平,我不放心,一月……两月,最多三月之后,必然归还。”
章师父寻思半晌,方道:“好罢。说不得,老章头回去传这一段话。也请少爷务必小心为上。”
“多谢章师父挂心,依明自会多加小心。”
章师父拱了拱手,径自上马去了。青年人转回头,见那艄公呆呆站在一旁,望着他们。他心下多少省得,江南多水路,舟楫是常见,骑马却是难得,况且金人不断滋扰,马匹多为军用,百姓人家有匹马骑,着实并非易事。果然那艄公按捺不住,问道:“非是小的乱打听,只是适才听得,少爷莫不是陆家庄的大少爷?”
这话问得不伦不类,青年人笑起来,点头道:“正是,陆家子陆依明。”
艄公啧啧连声:“原来是上虞陆家!怪道怪道,也是小的愚笨,看少爷这气派,原该知道,这绍兴城内也没有哪个能有?便是知州老爷家的公子,也难得少爷这么……这么……”
陆依明听他胡吹大气地奉承,末了又卡壳,心下好笑,自不当真,正要开口叫他开船,一直默不作声的胡叔道:“这船,几钱?”
艄公发愣:“啊?”
胡叔索性抓起他手,拿过篙竿,又将一枚银锞子放在他手心,道:“这船,买了。”那银锞子少说有三两重,这条小舟不过几块木板钉钉,说值半吊钱都是抬举,决计是不亏。那艄公呆立那里,似乎转不过来弯,银锞子是立时攥住了,面上还是呆呆傻傻,张口结舌地瞅着胡叔。胡叔伸手示意他下船,那艄公又浑浑噩噩回到岸上,胡叔自行撑起篙竿,深入水底用力一点,小舟登时离岸丈许,向下游漂去。
陆依明默默看他施为,待船离岸,方道:“何不留那舟子撑船?倒要劳动胡叔亲力亲为。”
胡叔道:“吵。”
陆依明不禁一笑:“确实。”
胡叔又道:“不是好人。”
陆依明却是一怔:“呃?”
胡叔用脚点点船板,弯下腰揭开,上面是薄薄一层木板,下面露出真正船板,竟掏了一个大洞,又拿一块圆木板堵上。陆依明不是笨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登时皱起了眉:“这?”
胡叔点点头,重新把薄板盖上。陆依明思量片刻,道:“我水性也还过得去,家住还这么近,想必他也不敢害我。”
自朝廷南渡,北人也纷纷过江来,倘或是北人商客,不识水性,又在当地无亲无故,船行至中游,那艄公悄悄把这洞一扒开,再不会有人知晓有些人就此彻底消失,盘缠细软自是落到艄公手里。如此妥妥当当,确实不必害陆依明这等本地大户。这在江湖之上原是不值一提的常见戏码,但陆依明毕竟听闻不多,虽自我安慰一句,终究是有些寒心,又点头道:“是了,就是他不去害我,我们又何必跟歹人同船?兼且,当真太吵。”说到末一句,又笑起来。
胡叔仍没理他,自顾遮好船板,又去撑船。陆依明早惯了他寡言,自坐在舟尾看水,这日亦是天朗气清,水面映着日头,宛如撒了一江碎金,又都活过来跳跃攒动。陆依明心不在焉地看着,暗自等着胡叔开言。
船至中流,胡叔才问:“你怎知?”
陆依明故作不解,反问道:“我知什么?”
胡叔寂然良久,方道:“你晓得。”
陆依明看他半天,终于不再玩笑,轻轻叹口气,道:“唉,胡叔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瞧着就跟长辈也近似。只当预演罢,我还真不知异日如何跟阿爹禀明。”
这胡叔看去有五六十岁年纪,其实是老相,实际尚不及五十岁。他母亲是陆家现任家主、陆依明父亲的乳母,陆父幼时与他一起长大,亲如兄弟,是以胡叔在陆家确实地位超然,陆依明这话说出也并无不妥。而陆依明自幼便得胡叔照料,虽然胡叔寡言罕语,但待陆依明也是十足好,陆依明心里,有时比威严过头的父亲还要亲近三分。只是他酝酿半天,仍是不知如何开口。踟蹰着又叹口气,方道:
“先说姊姊吧。姊姊性子是不大好亲近,但人是最好的,素日也最守礼,我原本还奇怪,怎会突然留书出走呢?又是不解,又是忧心,而此事终究也不便太多人知晓,便禀明阿爹出门。也幸而胡叔肯随我出门,不然,我看爹娘再不能松这个口。”
原来陆依明长到十八岁,还是初次不随父母独自出远门,而这一出门,便是为了要寻他出走的姊姊。他陆家在绍兴府如何他不知道——观方才那艄公,也是有些名气——在上虞县城,也算得有头有脸的人家,陆依明虽不在意,并且觉得他姊姊约摸也不会在意,但一个未许人家的小娘子擅自跑出门,就算他们习武之家不比那些个读书人狷介,终究不甚好听,陆依明也很不愿有人议论他姊姊,是以方才有旁人在,他提起时都只说“那人”“那事”。
他又叹了口气:“刚出门时心急如焚,到处乱走,却也没撞到姊姊踪迹。而这时阿爹叫我回去,我也未曾多想,立时就要回去听阿爹安排,却刚好探听到姊姊是往临安府去了。我自然是要过去看看,却不料阿爹竟然拦我……我心下便有了猜疑,悄悄找素练姊姊——就是姊姊的贴身大丫头,胡叔兴许不熟,我知姊姊是很信重她的,向她问了当时姊姊离家情状,约摸八九不离十,晓得姊姊为何离家了。”
他看了看胡叔脸色,胡叔脸上还是毫无牵动,恍若不闻。他只得再叹口气,续道:“后来我跟娘说了出来,便不甚着急,是为有了缘由,我想姊姊的身手不比我差太多,虽然说不上高手,偶然遇上一两个小毛贼还伤不了她,运气若不是太差,或许还吃不了大亏,因此不再着紧,慢慢找来……唉,是了,这是托词,实是我也不知如何见她才是。而阿爹今日竟然请章师父直追到若耶溪边,我只有愈发笃定,姊姊必是无意中得知了,一时想不开,才跑了出去……最怕是,一时半刻,也不愿再见我。但她孤身女子,怎好留她一人在临安府乱闯,少不得要寻她回来才是,且此事既然由我起,也当由我结。我不听阿爹话回去,胡叔不会怪我吧?阿爹,唉,阿爹也不要怪我就好了。”
胡叔抬眼看他,道:“为这,不回?”
陆依明道:“自然是为这个,还能为什么?”
胡叔难得说了句颇长的话:“怕是,为你,一时半刻,不愿见老爷。”
陆依明一时间哑口无言,心中忽而飞过无数旧事,三两岁初次记事时,他阿爹,端方严肃的陆家老爷,在阿娘撮弄下笨拙地把他背到背上,玩“飞高高”,十年后偶然提起时阿爹的脸色黑如锅底,称绝无此事;四五岁时跌了一跤手臂骨折,一贯待下人温柔可亲的阿娘,罕见地大发雷霆,把当时跟随他的侍女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是他自己开口“替姊姊们求情”才算过;六岁时第一次见到自幼在峨眉修行的姊姊,那时比他高了一个头,拍着胸脯说姊姊回来了,再也没人能欺侮你,被阿娘一通教训女子怎可如此粗鲁;……还有便是,那之后一两个月,他无意中听到家下老仆交谈,突然得知的那桩事:起始他如何肯信,然而私下里悄悄探听,诸多印证,却只是越发凿实了。
一晃十二年,若是姊姊那位峨眉的师尊——那位不知有没有过百岁的苍云禅师看来,想必也只是白云苍狗不过转瞬,然而对陆依明而言,他活才不过是活了十八岁,十二年,已经是相当之长。他真心微笑起来,恳切答道:“虽是不知如何跟阿爹禀明,但我其实……六岁起就晓得啦:我并非爹娘亲生子,乃是阿爹拾来的弃婴。”
胡叔的面容终于略有松动,他面带疑惑,直直看着陆依明。陆依明柔声道:“只是那又如何?阿爹阿娘待我如何,我心里是知晓的;而阿爹阿娘不愿叫我知道,那我便不知道。唯有姊姊……”他最后又叹了一口气,道:“只望姊姊不要太生我气啊……”
胡叔早不再看他,背过身去撑船,留他在一边默默出神。然而这件事他早已想了无数遍,焉能此刻突然有了什么新鲜主意?到底只能苦笑摇摇头,问:“胡叔,咱们这走水路到临安府去,还需多久?”
“三个时辰。”
“如此近。”陆依明叹道,“我竟从未去过。”
只曾听闻,临安城如今是行在所在,鱼龙混杂,居行皆不易,不知姊姊这一个月辰光,是在何处渡过,又过得如何?
但愿相见不会太难。
——————————
介绍了一下小少爷身世。
感觉露了好多马脚……看到什么bug大概不是错觉(。
实在不擅长考据,无论历史人文水文地理,有任何舛错都欢迎指正,十分感谢;当然懒得说就当是架空放过去的也多谢宽容……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