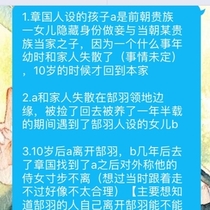它一定会变长的,我要施个相信自己的魔法,呼啦啦啦(。
-
序
哦,拜托,那个带着小圆镜片的图书管理员已经盯着我看很久了,好吧,我只不过是翻书的姿势粗暴了一点,拿起一本丢下一本,请别对我过于苛责,我保证他们基本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你说放的不对?好吧,那大概是我搞错了。
虽然我讨厌这个地方,但基本的规则我还是懂的,不要喧哗?向上帝发誓我绝没多话,我不过是在楼梯口忍不住挽了一下一位差掉摔倒的妙龄女郎的腰,又趁机不住向她美言几句,对着美人献殷怎么能算是过错,可我着实讨到了“变态”这种不雅的名号,这真是让人不快,所以我多抱怨了几句也应该被理解吧?
实话说,我讨厌这里。
闻闻这是什么味道:发臭的樟木头以及陈腐的灰尘沫,对此过敏的人进到这里绝对会一命呜呼。再看看这些方块形的小东西,“巴黎圣母院”、“茶花女”,饶了我吧,净是些法国佬,让我来看看别的地方,“雾都孤儿”我还有印象,“远大前程”这可是我的噩梦,还好它没耽误我的毕业。
我叫菲尼·瑞恩,从前我的家人们喜欢叫我小菲尼,而我的狐朋狗友们喜欢叫我瑞恩,实话说他们应该对我尊敬点,叫我瑞恩大爷,麻烦事我可为他们解决了不少,可那帮家伙从来不知感恩。
私家侦探瑞恩第一讨厌的是黄豆(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豆制品),第二讨厌的就是书。要是你非要探讨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并不是没有缘由,但这当口我实在是没有心情谈论这件事,我的脑袋被这些眼花缭乱的书页搞得神志不清,渴望畅快地呕吐一番然后向肚子里填些清爽而朴素的沙拉拌生菜,可出于某些原因,我不得不呆在这里,发挥我一年半职业生涯的经验寻找叔叔给我留下的线索。
我拿起一本非常薄也非常旧的书打量着,书页边卷起泛着深黄色的污渍,标题字数太多以至于字母像是庞大的家庭合照般挤在一起,封面看起来也毫无美感,那种特殊的潮湿的味道扑面而来,让我有一瞬感谢自己不是过敏体质,呼吸系统也足够健康。
我掂着手中的小册子,看到作者一栏写着:“埃德加 ·爱伦 ·坡”,不认识,然而当我翻开第一页看到“塔尔博士与费瑟尔教授的疗法”这一行字的时候,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我就知道,每次遇见懒蛋托尼和他那只灰黑色毛的癞皮狗时我都会倒霉,也许我该接受凯瑟特夫人的邀请,而不是抄近道去吃那夹着烂菜叶的过期汉堡,就算被那分不清“a”和“o”的小坏蛋弄得一胸口鼻涕也比被狗吠厄运缠身强。
我在此刻郑重宣布,我,菲尼·瑞恩,是坚定不移的猫派。
-
第一章
显然我到的比在场所有的人都早,而且这个事实出乎预料,也许它原本就不应发生。当我试图将手伸向放在壁炉旁的花瓶时有人出声制止了我。
“先生!”他叫道,“是谁允许您进入这里的?”
那是个身材魁梧、有模有样的老派绅士,两撇小胡子翘得有模有样,他的模样看上去蛮威严,可面容以及神态透露出一种微妙的不协调。
“真是一团令人愉悦的火。”我说道。
话音刚落,连我也察觉到了怪异,因为在此之前我既没感到火堆的热气,也绝不会发出这种老旧得像个老头子似的发言,与其说是我脱口而出不如说是这个句子在脑海里骤然显现。我低头向身旁的壁炉看去,那里确确实实燃烧着一堆火,并且势态正旺,绝不会是刚刚才点着的,正当我疑惑之时,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方才被灰布蒙着的钢琴突然被响了起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姿态优雅地弹着曲子。
“是的,真是一团令人愉悦的火。”
老先生愉快地拍了拍手掌微笑着对我说,演奏的女人停了下来向门口望去,紧接着一个看起来愣头愣脑的小子随着那位先生走了进来。待他温文尔雅地向所有人包括我打完招呼之后,我发现第四个人出现了,这次是一个褐发的小姑娘。
她坐在一把小巧的扶手椅上,肥大的裙摆覆住了大半个椅面,那姑娘似乎无意与其他人交谈,只坚定地看着那年轻人。我听到了她与他的对话,从中捕捉到了一些诸如“精神病患者”“安抚疗法”的字眼,这更坚定了我内心认为这地方不同寻常的猜测。我想自己应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说不定能发现些被隐藏的奇妙的边界。正巧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那女孩的身姿也消失了,我于是向门口走去,而剩下的三人对我的举动毫无反应。
于是我畅通无阻地走出了这座小房子。
tbc.
-
非常惭愧,土下座orz

它本是一株紫竹。
受着充沛的日光,又喝饱了甘露。
西南多雨,风里带着湿润和温暖,它轻轻地往下一拂,万千生物就都熙熙攘攘地长了起来。
雨季未逝,已是绿匝匝盈满人间。
这儿山连着山,没有路,只有骡子队踩出来的小道,裸了的地里透着红,腰带般环着山,弯弯曲曲,远望去又如同没有头的蛇。
寨子就扎在这些山里,一幢接一幢的吊脚楼,用竹子搭了,和林子半化在一起。
一片寨子便是一个部落,由土司管着,凭着每年向上的进贡,便能得大明的皇恩庇护。土司之间偶尔也有不合,但只要是不犯上,朝廷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也少不了一些不服管的寨子,隔几年便不安分地跳出来闹一闹,又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打压。这些暂且不详谈,总之大多数时间,寨子中的日子是平静的。
白天里男人们外出耕嫁,女人们就在家里织作。孩子打落地后就不管了,放去山里自个玩耍。炊烟袅袅,从寨里徐徐上升,携着欢歌笑语飘入碧空。
夜里,红日落了下去,月亮升到半空,明晃晃地洒在山里,照得树影斑驳。
天暗了下来,山却燥了起来。风漫过竹林,敲打着枝叶哗啦作响,如同千万铜锣在碰撞,这响声还未停,一声嘹亮的吆喝忽得划开了月夜。
那是个让竹也不禁陶醉的好嗓子,气沉丹田,粗旷中又带着点温柔的缠绵,在半空吊了三圈,一停,再一滑,便一路向下,绕着山缭绕不绝,震得竹林微颤。
他唱:“小小荷包双是双线飘/妹呀嘛挂在郎腰/妹嘛挂在郎腰/小是小荷包/小是小吊刀/荷包吊刀嘛挂在郎腰/小是小情哥(哎)/等是等等着/不呀等小妹嘛要等哪一个”
尾音刚落下来,就被一个女声接了起来:
“荷包绣给小哥带/捎呀信小哥嘛买线来/捎信小哥嘛买线来/红绿丝线多多买/郎要的荷包嘛绣起来/哥戴荷包街前走/小呀妹随后嘛紧紧跟/小妹随后嘛紧紧跟*”
一唱一和,整片山都被歌声罩着。
后来越来越多的歌声加入,此起彼伏,不知唱出了多少对佳人,又勾出了多少爱慕。
竹细细听着,不禁醉在歌中。
日头正高的时候竹听见了人声,它知道那是名为“人类”的生物。它听到她们的笑声,看到一双双纤纤手臂捧起溪水,把那水扬到润湿的衣物上,流水潺潺,棒槌敲打在卵石上邦邦作响。
不多时,女孩们便陆陆续续起身开始往回走,只有一个姑娘,恋恋地在水边,不愿起身。
女伴们叫她,她才慌张地起身应和,紫竹辨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是那夜夜合歌中最好听的女声。
女孩起了身,但仍是一步一回头,如此几番,终究是走远了。
女孩子们渐渐走远了,林又寂静了下来,过了一会,从林子深处显出一个青年的脸来。
青年急急地往溪边走,竹叶刮了脸都没能让他停下脚步,他步到溪边,蹲下细细摸索,突然叫了一声,捧着个东西猛地站了起来。
那什物在林子里闪着光,亮得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星。
紫竹不明白那是什么,不明白青年为何将那小小玩意儿紧紧捧在胸口,它所知道的是,自那之后青年时常来到这里,偶尔抚着自己暗自低语。
紫竹偏爱他温暖的手掌,那是生命的温度,只是它并不明白,那语言究竟有何含义。
夜里的歌声依旧回荡不绝,但却少了她最熟悉的那对歌声。
它只是看着,听着。
尚未开化的心智尚且懵懂,但却已萌发出了好奇,想把这世间一切都放眼心中。
风摇叶落的萧萧索索,雨打溪面荡漾出的一圈圈水光,它望着与自己相似的一株又一株紫竹,身体里的某处在悄然无声地叫喊。
紫竹只能记起那个夜晚,月光很凉,而他的手也是同样的冰凉。他踏着月色无声地来,用斧子在月色裹挟下带走了它。
紫竹被分截为了许多部分,青年挑挑拣拣最终取了其中一段,他用那双有力的手反复掂着它,用雪亮的刀子将它一点点打磨。
它感到了疼,但却觉得开心。
它知道自己即将在青年手中得到升华。
青年一刀又一刀,谨慎又笃定,每一下刀,似乎都带着某种祈祷。
削割、烘烤、定调、钻孔、打磨。
他的手始终是那样温暖,他的目光是那样的热烈而虔诚。
紫竹已逝,现在它成为了一支巴乌。
青年的目光经常望向某处,巴乌明白,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姑娘。
青年随时随地都将它带在自己的身边,不时便捧着它细细打磨它,巴乌不知道,那双深邃而专注的眼睛中有什么,但它却觉得这样的目光让自己也变得沉甸甸。
雨季正在慢慢逝去,但那雨丝所浸湿的漫漫情愫却越加浓厚和深长。
一个夜晚,月亮刚爬上枝梢,青年便踏着月光走出家门,爬上了高地。他用那双满是茧子的手抚着巴乌,然后捧起它,吹响了它。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身体内被气流充满,激荡、旋转,然后终于找到出口冲出,本来只是普通的气流,再入世间时便化得柔美悠长,脉脉含情。
青年捧着它吹了一夜,直到天边启明。
巴乌感觉身上被一种腥咸的液体浸湿,隐隐约约中,它仿佛看到了青年嘴角的一抹暗红。
之后它便被包裹在了黑暗中,隔着布条,巴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它再也感受不到青年粗糙的手掌的温度。
再度见到光亮时,巴乌感觉自己被一双更加纤细和柔软的手捧着,它看清了捧着自己的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姑娘。
姑娘的长发黑亮而柔软,脸蛋小巧,身子纤细修长,还有一双黑而明亮温婉的眼睛。巴乌觉得这个姑娘似曾相识。
姑娘抚着巴乌,将它贴在自己的脸庞,巴乌感到她在颤抖,温热的液体流过自己的身上。
巴乌不知那是什么,只觉得那东西骚得自己发痒。
那姑娘经常抚着巴乌,对它絮絮念念,偶时她会将它吹响,悠悠乐声便在颠簸的黑暗中回荡,久久不息。
忽有一日,巴乌感到了姑娘的不对劲,未等它察觉出什么,便被缠进了更加紧实的黑暗中。
从此巴乌再未能歌唱,它被束缚着,自此与人间隔离。不知天高、不觉月明。
它不知,这仅仅是个颠沛流离的开始。
日日夜夜,巴乌被裹挟在狭小的黑暗中,渐渐地,它陷入了沉睡。
梦中有青年粗糙的手掌,一刀又一刀将它雕琢;梦中有姑娘温婉的指尖,奏着它唱响月夜与芳华。
沉睡中的巴乌,等待再次被吹响。
然而包裹它的容器换了一个又一个,在它身上停留的手掌换了一双又一双,却再也没有等来那只捧起它将它奏响的手。
金飞玉走,暮去朝来。
时光悠悠流转,人间花木几经开败。
巴乌的世界里却只有寂夜恒长。
一日,沉睡的巴乌忽然听到了声响,那声音断断续续,似是孩童的欢笑声。
接着突然天旋地转,它感到自己沉重地摔倒并滚了出去。巴乌终于感到了亮光,却是以这种莫名又激烈的方式。
“呀!它掉出来了!”巴乌听到有个稚嫩的声音气急败坏地叫,“盒子坏了!”
“不惧它!这里放着的都是些陈物,扔了也不足惜!”
那声音中带着不以为然,又似乎含了从骨子中便生出的骄纵气。
巴乌感觉自己被抬举到空中,被粗暴地翻动。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笛子么?老头子就喜欢乱收罗,这么多东西他也管不过来,直接扔了就是。”
“等等,这个给我吧。”一双手将巴乌从那骄纵儿手中夺了过来,“我识得的,这叫‘巴乌’,不是笛。”
“你可会吹?”
“不会。”
“那要这玩意有什么用?”
“留给你也是要扔了吧,不如给我耍耍。”
“这倒是,反正得处理了,不然万一哪天老头兴致来了看看,发现这残次品少不了拿我是问。”
“你把它丢了你爹就发现不了了吗?”一个陌生的声音又加了进来。
“这个……”
“你爹若要是问你就说是我向你讨走了,剩下的我想法子应对。”拿着巴乌的人这么说道。
“好主意,你爹喜云儿,一定不追究!”
“好!就这样定了!”骄纵儿喜笑颜开,搂住了那个被唤作云儿的男孩的肩,“走走走,继续玩儿去!”
陈放数载之后,巴乌又有了新主人。
新主人和之前那些主人们不同,他似乎懂得巴乌的心意,再未将它囚禁在黑暗中。
他时常惦着巴乌打量,孩子的手又软又热,捂得巴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暖意。
白日里他读书,巴乌被摆在桌旁架子上,便也跟着听;晚上时他挑上了灯,橙黄晕染了房间,如同暗夜中的月亮。
巴乌看着这眼前的一切,仿佛新生。
这间屋子宽敞又明亮,面向南边有扇窗,打开后便能看到一园子的花色。无论是明黄的迎春还是雪白的杏花,不必费力便能入眼。
新主人闲了的时候便捧起巴乌摸索,只是他吹起来毫无章法,乱七八糟,如同是敲打破了的罐子。
尽管如此,巴乌却感到开心,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再将自己吹响。
窗外的景色变了又变,迎春落了后是粉如霞的桃花,有时随风飘进屋子,带进一阵清香与甘甜。再远一些的是大如盘的洁白的琼花,底下绕着一丛丛不知名但繁盛的小花。
夏日院子中葱郁一片,绿叶笼罩了半边天,树影斑驳地挂在墙上。使那热风也瞬间凉了许多。
秋来时伴随着桂花的香,这香溢四处飘荡,园子里盛不下,便溢了出去,直至整个城仿佛都浸在香里。
冬时的园子比其他三季寂寞了许多,不过还好有那梅花,料峭寒中独立着,顶着一身白色的雪。
伴着园色的流转,云的吹奏技术也在渐渐精进。
当那乐声终于再次飘扬起来时,巴乌有一瞬觉得自己回到了故乡,那远的不知在何处的故乡。
屋子中不时有人来来去去,但最常来的还是那个将它带到这里来的人,巴乌只知道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字:云。
它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字。
旁言碎语时常穿进它的身子,它渐渐从中得知了云的身世。
他本是个小妾生的孩子,生下来不久便经历了一番波折,流落异地他乡,自个的命虽然保了下来,却小小年纪便失去了娘亲。
也许是心生怜惜,自从将云接回府上后,老爷便处处都放任着他,任他和自己那狐朋狗友们到处寻欢作乐,也未曾约束与他。
巴乌安静地听着,感觉那些闲言碎语中所描述的云仿佛是另外一个人。
在巴乌看来,与自己独处时的云,是个深沉而又温柔的人。
从他所奏出的悠长的旋律中,巴乌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是那般含蓄又幽怨,缠绵中带着思念与坚毅。
巴乌不解,它不懂为何一个人能如此千变万化,虽然被种种不同的模样裹着,却仍是一个个体。
它只是一支巴乌,岁月与天地赋予了它以灵,却终究不懂人心。
于是巴乌只能选择陪伴在他的身旁,默默地祈祷着请岁月以悠长。
只可惜世事万变,这种祈愿从不会实现,命运总是与心愿相背而行。
巴乌又一次失去了它的主人。
那一日他抚摸着它,与它道别。
它从未见过他哭,那一天也未见到。
“我潜心等了如此久,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如今的我已无法回头。”
青年只是说着,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述与巴乌。
“只有你的存在,让我得以忆起娘亲,找到些许寄慰,”说罢他苦笑了一下,嘴角抖了几抖,“我倒是痛快了,只是苦了你,又得颠沛流离!”
巴乌本看惯了离别,只是这一次,却与从前都不同。它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上某个地方,正在无声地裂开。
那夜,明火将夜照的如同白昼。
她知道他已睡去,永远。
她想起,自己本是一株紫竹。
生于西南,成于刀斧。
所有的生死离别恍如一场大梦,不曾想,梦醒,竟已过去了悠悠百年。
——————
*出自《绣荷包》(云南民歌)
有些地方没能找到考证,于是暂且这么半架空了(。)如有明显错误请大力指正我会赶紧修改的(土下座)
一个简单的前置故事,借着一支巴乌总算是讲了一回爱情故事(。)接下来就是属于巴乌自己的故事了,安心躺尸等主线剧情……
正如您所见,这是一支完全没有用处、还不能出声的普通乐器hhh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来和她玩(没底气)
互动都会回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