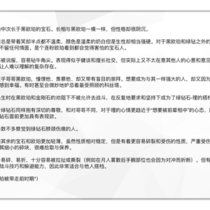推开房门的时候,布蕾柯看见了在沃特尔受伤后大家罕见地聚集在一起。
声音很杂乱,屋内丝毫不安静。似乎是有些习惯了那曾经一度沉默到尴尬的气氛,他不太适应地缩着颈子。
——有多久了呢,自那孩子受伤之后。
最年长的欧泊轻轻地扯松了胸前漆黑的领带,那东西总是如同法尔的双眼一般束得过于紧凑,仿佛是要扼断脖颈的小手一样隔着那薄薄的衣裳缠绕起身体,就连喘出一口气的余裕都不肯留给他。布蕾柯缓慢地呼吸着,抬起眼瞧过去。
果不其然,科丝塔站在中间。
那作为全家最后光辉而存在的年轻的孩子(他们总是这么开玩笑),小弟弟科丝塔一如往常般地闪烁着不太耀目的光。他周身尽是些闪烁的东西,耀目的法尔和沃特尔、与满面冷静的缪珥柯往他身侧一站,发出的光就几乎已经破开了其周身的雪白粉饰,让这本来就小小的孩子更加散发出一种近乎要消去了的透明感。
他没看见自己。布蕾柯在心里想。
欧泊一族素来就只出产些硬度又低脆性又高的孩子,他与三个弟弟,无论哪个单拿出来都实在不能被说是绝对的强大;哪怕是拿去与硬度更低的宝石相比,他们也会是单薄易碎的那个。于是只得时刻注意着一切风吹草动,努力令仿佛藏着刀子的风无法再从他们身上夺去什么;而最晚诞生的科丝塔,除去这一切脆弱的本质以外,他还有更让人头疼和怜惜的内在——个性。
这个小小的弟弟,他易碎、温柔,又总会被不知名的东西给吓到。
不过那也并非就是一切了。年长的哥哥望着灯光下的弟弟,无声地对自己说。
科丝塔与他们似乎全都不同,自出生起就能透过更多的光,这让他变得十分危险——欧泊总是含有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幸免——可也偏偏使他变得特殊。
这小小的孩子早在刚刚出生时就有着一双不可小瞧的眼,无数的光从那透亮的眼眸里穿过,带来的当然不只是平平无奇的变彩,除去这一切悲哀和遗憾,这个还勉强运作的世界最终还是赐给那可怜的孩子一双能把一切都收入心中的眼。布蕾克靠着一边的墙,从浅浅的光里看过去,突然就回忆起不知多久前他还小时,远远地从几里之外就大喊着哥哥哥哥狂奔过来的傻样子。
不过下一刻,这突然泛起了慈爱之心的大哥,就给发现了。
小弟弟闪着光的圆眼睛不一会就扫过来了,接着他开始喊叫起来,朝着他的哥哥走过去——是了,这是布蕾柯熟悉的那一套了——即使面对他人时总是显得手忙脚乱、乖巧胆怯,但真正对上宠爱自己的兄长,就算是乖巧如科丝塔也很难免俗地露出些寻常孩子的模样来。
小朋友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下来,但似乎是又想到什么,就缩了缩头。而一连串的动作与声音下来就连法尔和沃特尔也再不可能看不见这黑欧泊了,一红一蓝两对眼睛眨了眨,几乎同时开口问了好。
于是刹那间平淡的声线与温和的混杂在一起,难以言喻的和谐感被触发。那仿佛一切争执、一切意外、一切悲伤都不曾发生,温暖又安稳的气氛,让平静可靠的兄长也忍不住一下子晃了神。
不过这并未持续太久,熟悉感还没让兄长来得及品味,两人就再次统一地又换上了尴尬的神色——沃特尔的眉毛撇下来,嘴唇紧紧抿着,水一样的眼垂得很低,他精致温柔的脸上全是畏惧与苦涩,但却又有着被剖开喉咙也不可能发出的犹豫。而法尔似乎也并不就乐于看见自己双生的哥哥成了这副模样,有着日落般长发的宝石突然用上一副很是烦躁的表情,眉毛紧紧蹙起,布蕾柯这不太会表达的兄弟轻轻从嘴唇间发出不悦的咂舌声,而随着这一声,那温柔的兄弟则禁不住地抖了抖肩膀。
他们的哥哥自然将这一切收在眼底。
好在布蕾柯没能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这双生子的一举一动,他眼前突然出现的、粉红的、蠕动的、被弟弟举起来的软体小怪物,一时间打断了他本来还算缜密的思维。
绕是见多识广如大哥,这时候也忍不住在弟弟们面前显露出从未有过的不耻下问。
“这是什么?”他说,声音古怪得简直不像从喉咙里发出。
于是小朋友很是兴奋地站起身,他手里那承装有水和这小小怪物的木质容器也跟着一颠一颠的,一旁似乎是还闭着眼休息的缪珥柯就像不用看似的,他纤细洁白的手只是轻轻一托,就恰到好处地扶住了这歪歪扭扭的小家伙,结果这才没最终闹得人仰盆翻。
等到科丝塔解释了许久,说了长长一番话,口气都从精力十足变得有些畏缩时,布蕾柯才终于明白过来他那个刚刚看见自己时缩头的小动作从何而来。
“你居然又跑出去了。”从不好好听重点的大哥十分严肃地说。
年轻的晶质欧泊轻轻地挤了挤眼,抱紧了怀里的水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讨厌过布蕾柯这不会抓重点的性格。
不过这煎熬也并非是全无意义的,在一场事无巨细的讨(说)论(教)后,他亲爱的哥哥终于还是想起了这盆里那个已经快要被念到枯萎的柔软生物,粉红色小东西半透明的躯干萎缩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无力地发出着啾啾的叫声,那一整个软软的躯干都紧紧贴住了木盆加工平整的边缘,似乎是立刻就将要消失了一样。
来自于大海、睡醒就看见了、木棍可以戳下去……一连串完全不知所谓、能够令人陷入茫然的描述让欧泊们的长兄身心俱疲。
但科丝塔非常兴奋,不停强调着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么软的东西。
而原本打算立刻就拎着盆去老师那里的布蕾柯,也因为这句话忍不住地顿住了。
“该怎么样,才是保护呢。”
他突然想起几日前来自于那长发师长的发问,现在的他与当时一样全无回答的能力。
作为哥哥,他比谁都都明白科丝塔其实并非是个有许多要求的孩子,他大多数时候其实正如同他所表现出的那样,安静、乖巧、毫无争抢的欲望,那双眼睛里的神色和视线,就算是与温柔的法尔相比都显得更加弱小。
这个孩子清楚自己的无能,也知道努力守护自己的人的辛苦,因此即使是同时心怀自卑和期待,他也并不曾真正做过什么令人头痛的坏事。
于是布蕾柯停下了动作,忍不住地问自己,留下这奇怪的生物或许也并不是坏事?
扪心自问,他十分明白自己不可能随时随地地陪伴于这个孩子左右。他有自己必须要尽的责任,也有不得不完成的工作,即使再担忧科丝塔随心所欲的闲逛与好奇也无能为力——他不可能将每一个人都保护到严丝合缝,月人每日都在进攻,他能做的也只是拼上最后一块碎片去战斗。
而比起他们的安全,比起那种毫无生气的安全……布蕾柯想着。
他或许,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的笑容,并非是单纯让他们存在着,而是保护住这幸福的存在。
欧泊的大哥微微咬住嘴唇,他看见了缪珥柯正睁开一只眼瞥向自己——他也必须下个决定才行。
于是基于这个决定,这成了此后不短时间里,科丝塔所炫耀的事。
毕竟自那以后,宠物的事,最后似乎也就那么定下了。
------------------
你们知道吗,最悲伤的事是主角(蛞蝓)响应不到。
我与沃特尔,是一同被“产下”的。
由海中、山地而来的宝石,被名为金刚老师的人所拾取,拼凑,最后雕刻出面容,赋予人格、记忆、意识,最后成为一种类似于“人”的存在。
他们说,这就是“出生”的过程。
所有人在睁开双眼的一瞬间都有不同的际遇,不论是得到的名字还是初次所见的事物,它们总是不同的,伴随所有人,直至被夺走、被粉碎的那一刻。拥有喜怒、感到情绪、行动、看书、战斗、爱着他人、恨着他人……或者忘记他人。
那不一定就能算作是此后一切的一部分,只能说万物皆苦,此乃源头。
但他们仍然热衷于谈论自己出生的那一刻——月光石的第一眼是面色严肃的长发男人,是这里所有“人”付出尊敬与喜爱的对象,于是被叫做老师、布蕾柯的第一眼是其他五光十色的宝石,不过他似乎没能看懂他们都是什么、海德薇说他睁开眼就看见了天花板、苔丝看见的是盖在身前的布……他们有段时间几乎狂热地讨论着这个话题,就好像真的有多么重要似的。
而我的第一眼,是水。
澄澈透亮,平稳安静,却又散发着要让我那具刚刚刻好的硬壳身体从内崩塌的明亮光泽。
对面这张开了双眼的家伙,无声无息地笑着,安静又寡语。似乎也看见了我,也似乎仅仅只是笑着;那双透明的眼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却又装下了一切。一切都在他身侧变得绵软而悱恻,像真的就是一团被凝聚起来的水似的——并非是得以塑形的冰,他毫不冰冷,没有一星半点的坚硬。于是当那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便柔软得似乎没有棱角。
那就是沃特尔,我双生子的哥哥。
那就是,水。
巨大的殿堂般的房间有着很高的穹顶,窸窣而过的风带动着轻薄的窗帘与厚实的门扉,外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流光溢彩的颜色,四处都是交谈的声响与走动的声音。
而我与那个和我一同诞生的人躺得极近,眼睛里星星点点地全都是彼此。
科丝塔有段时间非常地沉迷于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说,他有天很是高兴地对我说,书里把充满了戏剧性的、可笑的初遇画面称之为邂逅,是浪漫的奇迹。
可是两个人,打从“出生”就邂逅,以后一直也不肯分开,那到底算是幸运还是惨剧。
我问不出来,心里明白科丝塔也答不出来,这个最小的弟弟其实并不真的在意我对这个词会有什么想法、也不期待我也会抱有什么念头,我知道他——他就是想要告诉我自己看到了点儿什么而已。
这个话题我也同样没敢对布蕾柯说——尽管他或许能知道什么——他说话的方式太过于莫名其妙,明明飘得望不见尽头,却又似乎真的能合洽上这本就无头无尾的话题;如果问了,我就要生怕他真的看出来些什么,又反而希望他明白什么,然后被他把话题带着走,那才是真正的不能忍受。
我烦恼的空当里沃特尔走到我的身边,天上下起了零零碎碎的雨滴,一副要死不死的阴霾。他从外面跑回来,头发上落了稀稀疏疏的水珠,衣服也多少打湿了些;沃特尔一身的白粉被水冲去了不少,于是他就这么斑斑点点地出现在我眼前。
——缪珥柯对我说过,我双生子的哥哥是水色的。
我漫无边际地想着,没有回应沃特尔的询问和担忧,他声音从出生起就没太变过了,就像硬度一样算不得太强势,却又有点清脆的意味。
——沃特尔,是水色的。
透明的水珠从他的头顶滚落,悄无声息地被甩进空气之中,沃特尔的马尾辫跑得有点松散了,睁着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告诉我他回来了。那眼里满是柔软,浸泡着放松后的安稳,闪烁时就像将这原本就昏暗的天光全都吸进了自己的双眼一样。
澄澈透亮、平稳安静。他总是他自己,他每一刻都能与那个出生时就露出了笑容的家伙重合。
我在收拾着他人的碎片时,曾经想或许有一天我也将忘掉自己。缪珥柯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和布蕾柯就算是忘了自己也不会忘记彼此。
然后我想了很久,在这一刻、逐渐倾盆而落的大雨里,终于有了些明白的势头。
打从出生就邂逅了彼此,而后也放不开双手,像是水与火一样彼此相映、顽固而执着、令我们都痛苦又喜悦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幸福。
我忽然想到,诞生于世的第一幕或许不太足够成为此后一生的一部分,但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却早已经是紧紧握住不愿放松的一切。如果说有一片东西是得以被埋藏于最深处的、至死也不会放开双手的,那么它一定会是我睁开双眼第一次所见到的东西。
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