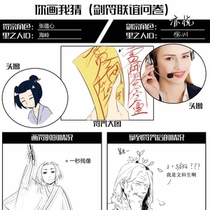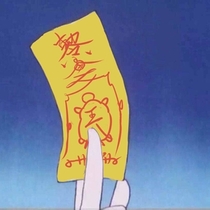○概要:亲爱的,离别时请为我唱支歌。
是很容易猜到的事件真相
——
“也许你想不到……”女鬼喃喃。
男子最终停下了脚步,垂下头去。
“他/她应该已经不再爱我。”两人同时停下动作,眼神复杂,说出同样的话。
一人一鬼,看着地铁车顶,落入名为过往的漩涡。命运将两人带上同一辆列车,忘记了也是它叫两人生死相隔。
真的是这样吗?在人与鬼的无尽落寞中,你似乎听到命运在低语:
他们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焦仲卿与刘兰芝。
命运的声音细碎难便又夹杂着轻微的嘲讽:我什么也没有做。
“起初我们也是很浪漫的。”女鬼说着露出怀念的表情。
“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男子笑得像是个孩子。
“他/她那时候非常耀眼。”
他们接下来所说的话却与这一句自相矛盾。
“他那时候只会穿格子衬衫头发长了老长才知道去剪,嘴上念叨小姐姐小姐姐但一到社团聚会就缩成一团。”
“她那时候从来不会打扮说话大声举止只能说man,社团破冰的时候扳手腕比赛能把三个大老爷们扳弯。 ”
“我当时怎么就看上这样一个人呢……”两人骂着骂着突然笑自己。
“也有过诺言。”
“他说过等他当上代行就一起去挑戒指。”
“结果那天她加班……”
“她说过等她跑完业务就请年假我们一起去海南堆沙雕。”
“结果假请好了他却生了病住了很久医院……”
“相互理解……”两人喃喃,“我当然理解。可是如果总是这样……人都是会厌烦的吧?”
“她做的菜真的不是给人吃的。”
“他进屋总是忘记换鞋。”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东西全都藏起来,我修个灯泡她还说我把地弄脏了?有没有搞错?”
“他难道没有基本常识吗?为什么用厨房的拖把拖卧室的地!?故意给我找事做吗?”
“我明天还要工作啊!”两人这一喊把旁边的小鬼吓了一跳。
“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特地给他买了蛋糕。但他回来晚了,脸色也很不好。”
“那天我手底下的小子出了些差错,我替他背了锅……回去路上那个毛小子请我喝了几杯。”
“他平常不喝酒的……”
“那小子告诉说我既然已经买好戒指了不管怎么样她都会喜欢的,让我快点给她……结果……”
“我没有真的认为他对我不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竟然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她可能真的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也许是因为虽然住在一个家里却根本见不到对方几面,待在一起的时候又都已疲惫不堪……”
“也许是因为明明努力工作但一交房贷就不剩多少,省吃俭用到头没了时间。”
“也许仅仅是因为那天下了场暴雨吧……”男子说着抹了抹眼睛。
“她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
“他说如果后悔了就滚……”
“我看着她哭着跑出去。”
“后来他追出来了……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他就不会滑倒吧……”
“如果我没有滑倒……”男子咬牙。
“不过,还好他滑倒了。”女鬼露出窃喜。“不然——”
“那辆车就一下把我们两人都撞了。”男子与女鬼听到了对方在说同样的话。但两方言下之意却截然不同。
两方为了见到彼此都豁出了性命,但如今碰头却一语不言。或许是因为愧疚,或许是因为恐惧,男子颤抖起身子。女鬼想要安抚他,但想起自己的模样,缩回了手。
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男子也看得出来她剩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这个。”男子从兜里拿出一个丝绒礼盒,他想要帅气的打开,但用错了门道。经过一系列毫无美感,甚至称得上暴力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黑色绢绸上躺着一枚很小的钻戒。“你喜欢吗?”
“……”
“……”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地挑中我最讨厌的这款啊!”
“你不是盯着这个看了好久吗?!”
“因为我在想——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戴这么丑的戒指啊!”
“……”男子本能反驳,但死这个字眼叫他立马住嘴。他拿出戒指想交给女鬼,但女鬼无法触碰到它,也无法拿起它。他只得捏住戒指,让女鬼将手指伸进去试试大小。
在穿越指环的一瞬间,有什么跨过人与鬼,生与死,唯心与唯物连接起这两个个体。它并非如你所想,是热烈温暖的东西,相反它冷冰冰又湿漉漉。诚然,双方对于彼此的热情早被琐碎而平凡的摩擦淹没。名为甜蜜的火热在生活中风干磨碎随风飘尽。
他们不再热爱彼此。也因此不再小心翼翼,不再以他/她为先。所有潮水都会退去,并非因为命运做过什么,而是因为自然就是如此。
而他们失去彼此的那一瞬间,命运的确做了件过分的事。他将他们生命中的一块砭石硬生生扯走。
他们并非失去了恋人,他们失去了家人。
指环内女鬼的手指一点点消失。
“去找个喜欢它的女孩儿吧。”她终于笑了起来。
“还有,生日快乐。”
从远心端到开始,女鬼本就不稳定的躯体一点点化作无形。男子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女鬼唱起生日快乐歌,那是她生前没能道出的贺言。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她想忘也忘不掉的日子。
她走了。男子愣在原地半晌,终于动了起来。他朝着帮助过他的孩子们深鞠一躬,在下一个站台下车。
门灯闪烁时,他仍有些呆愣。地铁缓缓启动,他的眼眶似乎红了。
“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站台上,有什么东西轻拍他的肩膀。回头,那是之前闹事的鬼魂方负责人。
O抱歉过了这么久才写了这么一点儿可以发的东西。
O被剧情憋成一只咸鱼,不会说话没有逻辑只会啊啊啊和吐泡泡(躺)。
O擅自互动。如有不妥,一定修改。
O概要:这个处处散发着“另请高明”气味的老师,看上去很像一个骗子。
——
曾几何时张觉得学好这些本事,讨得师傅欢心,每天的日子就会像太阳一样东升西落,永远这么过下去。每天都是好时候。从没想过这一身本事到底有何意义,这书上的道理到底有何深意。以他的见解:每日待在山上钻研,好过山下万千红尘。要做到常清常净,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人。
他没有什么济世救人,开天辟地的心志。那些匡扶大义,指点江山的术士高人他也不曾仰慕憧憬。道,与他而言就是有一日算一日,做好每一日于他而言就是活着最好的方式。尽管这看上去优秀得浑浑噩噩。但也平凡到一帆风顺。
这原是张蕴心的道。
在那段单纯无邪的日子里,他在书房里磨墨熨纸,在田野里浇水扑蝶,在广场上扫叶舞剑,在早课上打坐温书。他跟着他的师兄弟一齐在道馆里翻书,附和着师傅的声音一起念搭配: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由于某一位老师有罚人抄书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抄写书目。最上面一本就是《师说》。张蕴心再看到这本书时,心中不免泛起涟漪。
阴错阳差,最为浑浑噩噩的他到如今成了现代人口中的一座灯塔,一根蜡烛,一个灵魂工程师。设身处地,才知道要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哪里有那么容易?传道受业解惑,下笔仅仅六字,真要做到周全妥当受之无愧,非神即仙。
原以为上蜀山是桩闲差,没料想实是苦活。张蕴心自认没有当好一个老师的功力。
“老张,你怎么也看起《师说》了?你们哪个娃娃不听话?也要抄这个?”
扈安走进办公室时,手上还拎着一副烤箱用手套。多年老同事叫老张知道,这位电子设备白痴许是需要人帮他摆弄一下新世纪高科技灶炉——也叫烤箱。张蕴心将插头插上,点亮黑色立方体前面的触控面板:“没有没有,我随便翻翻。对了,你今儿要做什么?”
“布丁。”
“那我预定一个试吃位,这玩意儿要烤几分钟?”
“要先把烤箱预热10分钟的……”
老扈这股不耐烦完全是因为他已经说了不下五遍烤箱要预热的事,但老张每次听完就像第一次听见似的:“还有这种讲究?”
一边的老扈放着自动打蛋器不用,一手抱着打发碗另一只手拿着打蛋器高速运转,整个人都想通电了一样干劲满满势不服输:
“老张你可长点心吧。”
不止同事这么说过,他的学生也这么觉得。这位符宗老师上课迟到已是常态。其中原因说出来丢人,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跟这群娃娃打交道,而是因为他在蜀山呆了几个春秋依然没记住哪个教室在哪里。有时侥幸被他蒙对了地点,他也会因为没带教案在走廊上草丛间翻东翻西,把自己变成一个真园丁。如果有人统计班上谁没带课本的次数最多,结果一定是张蕴心(老师)。
他不是不想做好,他也想脚步生风昂首挺胸手上端茶徐徐盈盈,身后桃李满天下。但是人这个字只有一瞥和一捺,万事总有做不到,要求不能太高。硬要做成一个王,只会从人变成八。他只能做到把要用的试卷放到正门口,好让自己一出门就能记起它。他只能把银行卡密码贴在银行卡背面,好叫自己不会因为试太多次被吞卡。
用他的话说,活了一百多年了,脑子不好使也是很正常的事。
就这样的人,要做老师这样一个精细活,不是强人所难嘛?况且,学生自有老师传道受业,那老师又由谁来解惑呢?曾经的老张以为自己活得明白,不过是因为日子过得简单。现在的老张生得糊涂,是因为他自己个儿也找不到答案。难到生存还是毁灭,简单到有学生陷入困苦时,你帮还是不帮?
老张从没觉得自己选对过。
如果帮,那么——
“你这个老师真他妈烦!”段语在三年级的时候对着老张这样说。
这是个清澈的孩子,上课十分认真,作业也按时完成。如果没有那句发聋振聩的直白话,老张几乎就要确认他是自己上辈子修来的好福分,难得碰上的好学生。
这个孩子最讨人喜欢的一点,是记性好。
就是几天前讲得知识点,他都能倒着背给你听。哪怕是你无心的一句玩笑话,他也能记在心上。老张有一次听见他劝其他同学不要把雷符往手机上贴,原因是“你他妈是傻逼吧?要给手机充电也要在符上写上变压公式啊!直接贴雷符不炸就有鬼了。”除去话语中浅显的道理,内核显露出来:要给手机充电需要在雷符上写上变压公式——这是老张随口胡吹的一句昏话,符上哪里可以写什么变压公式?但这孩子相信了,不但相信了还记在了心里。
老张曾盘算过把这孩子骗进符宗,但最终没有这么做。一是这孩子确实有更适合去的宗门,二是他有身而为人跨越不过的限制——他的手使不上力气。
明明是一位丽人,手上却总缠着绷带。明明抱着十二万分的努力,可画起符来还是有些吃劲。老张注意过这个埋头描贴的孩子,看他一横一竖尚且笔直工整,一点一瞥就已经缺了力道。符小些倒也不打紧,但是符大了,这少点劲道,那却点势头,先辈前人道尊神佛误认他这好小孩心不诚,不顺他的意随他的心。神仙一任性,符没了效用是小事。损了他的自信才是真事。
为此老张专门跑去医宗问了问,问他这手到底是怎么伤才能变成这副模样,也问了有没有什么法子治。结果辛夷没把答案给他。(反倒把好苗子给拐跑了。当然这是后话。)
“他这是筋骨折损之症,只能以草药外敷调养。无药可医。”
老张没了声音。
一来是心疼他小小年纪就经此大劫,二来是心疼他经此大劫却依旧是赤子一个。而他最喜欢这孩子的原因,变成了他最心疼这孩子的原因。换作别人倒还好说,但老张心里清楚,记着以前的事情是什么滋味。那些搅扰心绪的东西天天扎在脑袋里头叫嚣着迟早要完。叫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要是能忘掉反倒是一件幸事。
在某节课上,因为有同学提问符宗到底能干啥?感觉既不能打也不能扛。
“上天入地段段不行,打架杀人也是够呛。”老张没有生气,倒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随便画了三两笔。第一笔止住了第一排同学不停歇的咳嗽,第二笔修好了教室里那个已经不转的风扇,第三笔画成,只见四个大字:骗钱诓人。
他以为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段语这小子真的把老张随手画上黑板的鬼东西拓了下来。那治病的符箓这本不是三年级该学的东西,对他这双手来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东西。
可这傻小子就是犟,下课了还是在画。老张一直没走,最后实在看不下去,把他叫到了教室外的走廊里。
“段同学……有时候,其实你没必要把有些事记牢。”
“我记我的,关你什么事?”
“记住了却什么也改变不了,还不如忘掉。”
“你这个老师真他妈烦!”段语没听进去不说,还恼了。“神特么就算你是老师也别把自己的观点套在我身上啊,你跟我又不是同个人!。”
老张眨巴眼睛,十分想回答:被和自己有三位数年龄差的人训斥自己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自己记着,我自己开心。我至少这样活过!”
“您别瞎操那闲心了行不?”他扭头就进了教室阻止别人把那张符擦掉,继续他的描写工作。留老张一个人回味那句我这样活过。
他的努力和认真都是因为要以更好的姿态活着。他将好记性认作是他引以为豪的特色,他用这天赐的能力拾起岁月中的贝壳。小心珍藏,好好保养。才不管贝壳本身是黑是白,有好有坏。
毕竟,说到底,贝壳就是贝壳。
那一百多来岁,原来都是虚长的。老张思索半晌,只觉得自己白白老了,不如年轻时敞亮通透。可想到头去,还是想不明白。即使能掐会算,到头来还是活成了这副模样。若是不掐不算,倒地是过得更糟还是反倒活出本样。
罢了罢了,只希望段语其人,不忘始终。老张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
如果不帮,那么——
自段语那件事后,老张不再多管学生的闲事。直到他犯了一个大错误。
老张是眼看着如圭脚下一滑,整个人落到沟里去的。摔倒后小姑娘甚至没有发出叫喊。
你可能遇上过很多帮你看相的瞎子,似乎瞎了双眼睛就代表他们泄露天机受了天谴,是看卦准度的凭据。但事实上,这些瞎子都不是真瞎,他们骗完你的钱就会睁开他的眼睛。而真要是窥探天机,要赔上的东西绝不止一双眼睛。这件事老张也领教过故而对谁盲谁瞎看得很淡。全校可能就他一个老师记不住相宗的凤如圭是双目全盲。也可能就他一个老师会看到这孩子在路边晃悠时,还神经大条地以为她只是像普通女孩那样在伤春怀秋。
把那孩子拉上来之后,老张看到了她的眼睛才发觉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放任学生去做危险的事情不说,还不出手帮忙。自己这副模样还算什么老师?而这女娃娃,她正慌忙整理自己的衣衫。她明明把自己打理好了依然还在摸自己的头饰,疑虑它是不是歪了。确认一切规整完毕后,她郑重向老张道谢。
小女孩朝着刚才见死不救的老东西深鞠一躬。但是很明显朝向了反方向。这不怪小姑娘,毕竟是老张羞得想悄悄溜走故意没发出声响。
“谢谢你拉我上来。额……请问你的名字是?”这句把老张嘲地脸都红了。他只好轻手轻脚挪回去,接下小姑娘的谢意,然后装出自己是普通学生,故意捏尖嗓音:“啊?我,我是隔壁符宗的,我一会儿还有课,同学,你自己小心些。”
姑娘连连点头,继续握紧她的盲杖,敲打前行。
“……”老张看着姑娘越走越往左边偏,下一步又要滑到沟里去。还是忍不住开了口:“那个……同学。”
“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如圭看不见世界,但却知道如何对人展现一个笑容。
“我要去西边的教学楼可我不知道怎么走,你能带我去么?”老张面对如圭的善意,一时间满心酸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不能说出来。
她明明是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姑娘,但却乐于给予别人她力所能及的帮助。反观刚才不管闲事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才是老师?
老张的确又忘了自己接下来要去哪一间教室上课,但这是他所有话里唯一是真事的东西。他不会向如圭问路,因为如圭自己也需要帮助。他只是单方面觉得,让这个迷茫的姑娘知道有一个同样迷茫的同伴陪伴着她,能让她觉着好受一些。自己也可以用同伴这个身份帮她一程,而不至于损害到她的自尊。
如果如圭看得见的话,她会发现张骗子说这话时满眼都是对于她的歉疚。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老张合上《师说》,那烤箱正好发出“叮——”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