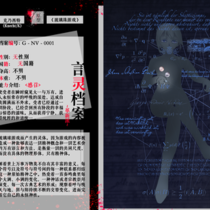克乃西特透过年越荞麦面蒸腾的热气望着他的同伴和他们身处的这家小店。于他而言,后者在今年除夕之前,只是他认知里的一个词语,虽然他对实物也并没有多大兴趣。实物只不过是词语与概念状态的叠加,当知道了所有的词语和概念状态,余下的只有可穷尽的不同组合而已。
现在克乃西特眼前的组合是荞麦面店、狭小、荞麦面、喝醉的客人、他的同伴帕勃罗。
他的同伴让这个组合有趣了不少。
大约是性格相异的缘故,即便是来自同一位作者,克乃西特与帕勃罗都相交甚少。现下会同在荞麦面店中,应该要归功于结伴而行来共度新年的其他言灵。新年的参拜就像荞麦面店一样,对于克乃西特是一个普通的词语,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而帕勃罗则因为寺庙的严肃所以敬谢不敏。两人就这么搭伙闲逛着到了荞麦面店里。
只是两人都不是好谈话的人,分别坐在两碗盖着蒲鉾和天妇罗炸虾的荞麦面前,无言地听着隔壁座的醉鬼吵吵嚷嚷。克乃西特并无物理的身体,荞麦面入口,得到的只是“比普通年越荞麦偏咸”这样的形容。相较于他的意大利朋友蹩脚的握筷子方式,克乃西特似乎更好奇文学禁止令下的人类生活,或者是这个醉鬼嚷嚷口中的生活。
“跑不完的业务……还挣不到几个钱……老婆也跟人跑了……窝窝囊囊儿子都瞧不起……”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每天劳劳碌碌到头就只有醉死……醉死……”
这醉鬼越说越是凄凉,到了最后竟一头栽在了汤碗里。动响吵闹的,不仅是克乃西特和帕勃罗这俩坐得近的,连在后厨的老板娘都惊动。老板娘急匆匆地走来,一面对着四座鞠躬道歉,一面将这醉得不省人事的客人搀出了店外。约是等帕勃罗举起碗将汤一饮而尽的时候,老板娘才回来。
“醉成那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去……大过年的真是……”在老板娘的絮叨声中,克乃西特放下筷子,朝同伴点头致意过后,便推开门走入除夕的风雪中。
没走几步,克乃西特就看见那人倒在一家店的门松边。他站立看着那人瘫拥着门松的底座,口角留下酒水和唾液,迷迷糊糊地蹭上松枝。
“要是有钱就好了……”克乃西特听到那人念。他缓缓蹲下,将那人手中的酒瓶拿开,在口中念起感召的吟唱来。
正当克乃西特要张开手掌幻化出玻璃球的时候,他的手腕被人从后抓住了。
“我的朋友,这不必要。”是帕勃罗。克乃西特站起身来,载体水蓝色双眼中的疑问代替了他的问题。
他的同伴幸运地没有插入一个多余的问题。帕勃罗解释道,“因为生命就是这样严酷的,幽默感要在生活的绞刑架下学会的。”
克乃西特没有想到帕勃罗会这样回答,他一向喜欢有人同他讨论。“瞬时的学会也是一样的,不论是概念,或者说你口中的幽默感。”
“一样么?”帕勃罗不以为然,“你脑中荞麦面的概念与刚才那两根筷子夹的、烫口的,是一样的吗?”
克乃西特望入帕勃罗的双眼,那一双含笑的眼镜游荡在玩笑中,却又在这除夕夜里显得格外有神。
“不一样嘛?”克乃西特将这个问题抛回给同伴。
“自然不一样,克。”帕勃罗似乎来了兴致,扬起了声调,“巴赫对于你来说是公式,是守调和答题。但是巴赫只有这样吗?”
“当然不止。巴赫的作品还有其背后的意义架构与承载的社会意义。”
“太严肃了,太教条了。”帕勃罗摆摆手,“是超越你所知的言语能形容的美,是指尖划过小提琴和键盘的颤抖……”
帕勃罗口中如诗的抑扬顿挫被寺庙里新年的钟声打断,克乃西特将目光从他的同伴脸上移回脚边的醉汉,而醉汉恰巧也在这钟声中醒来。此刻克乃西特再是有一颗普度众生的佛心,也不可能在对言灵有恐惧的人类面前施展技能。
克乃西特在除夕钟声的末尾里无声打量着身边的同伴。然而对他的同伴而言,先前的句子就像是这刚开始飘落的飞雪一般,落在地上就不见了。
“荞麦面的口味如何?”
“不知道。似乎偏咸。”
克乃西特透过年越荞麦面蒸腾的热气望着他的同伴和他们身处的这家小店。于他而言,后者在今年除夕之前,只是他认知里的一个词语,虽然他对实物也并没有多大兴趣。实物只不过是词语与概念状态的叠加,当知道了所有的词语和概念状态,余下的只有可穷尽的不同组合而已。
现在克乃西特眼前的组合是荞麦面店、狭小、荞麦面、喝醉的客人、他的同伴帕勃罗。
他的同伴让这个组合有趣了不少。
大约是性格相异的缘故,即便是来自同一位作者,克乃西特与帕勃罗都相交甚少。现下会同在荞麦面店中,应该要归功于结伴而行来共度新年的其他言灵。新年的参拜就像荞麦面店一样,对于克乃西特是一个普通的词语,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而帕勃罗则因为寺庙的严肃所以敬谢不敏。两人就这么搭伙闲逛着到了荞麦面店里。
只是两人都不是好谈话的人,分别坐在两碗盖着蒲鉾和天妇罗炸虾的荞麦面前,无言地听着隔壁座的醉鬼吵吵嚷嚷。克乃西特并无物理的身体,荞麦面入口,得到的只是“比普通年越荞麦偏咸”这样的形容。相较于他的意大利朋友蹩脚的握筷子方式,克乃西特似乎更好奇文学禁止令下的人类生活,或者是这个醉鬼嚷嚷口中的生活。
“跑不完的业务……还挣不到几个钱……老婆也跟人跑了……窝窝囊囊儿子都瞧不起……”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每天劳劳碌碌到头就只有醉死……醉死……”
这醉鬼越说越是凄凉,到了最后竟一头栽在了汤碗里。动响吵闹的,不仅是克乃西特和帕勃罗这俩坐得近的,连在后厨的老板娘都惊动。老板娘急匆匆地走来,一面对着四座鞠躬道歉,一面将这醉得不省人事的客人搀出了店外。约是等帕勃罗举起碗将汤一饮而尽的时候,老板娘才回来。
“醉成那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去……大过年的真是……”在老板娘的絮叨声中,克乃西特放下筷子,朝同伴点头致意过后,便推开门走入除夕的风雪中。
没走几步,克乃西特就看见那人倒在一家店的门松边。他站立看着那人瘫拥着门松的底座,口角留下酒水和唾液,迷迷糊糊地蹭上松枝。
“要是有钱就好了……”克乃西特听到那人念。他缓缓蹲下,将那人手中的酒瓶拿开,在口中念起感召的吟唱来。
正当克乃西特要张开手掌幻化出玻璃球的时候,他的手腕被人从后抓住了。
“我的朋友,这不必要。”是帕勃罗。克乃西特站起身来,载体水蓝色双眼中的疑问代替了他的问题。
他的同伴幸运地没有插入一个多余的问题。帕勃罗解释道,“因为生命就是这样严酷的,幽默感要在生活的绞刑架下学会的。”
克乃西特没有想到帕勃罗会这样回答,他一向喜欢有人同他讨论。“瞬时的学会也是一样的,不论是概念,或者说你口中的幽默感。”
“一样么?”帕勃罗不以为然,“你脑中荞麦面的概念与刚才那两根筷子夹的、烫口的,是一样的吗?”
克乃西特望入帕勃罗的双眼,那一双含笑的眼镜游荡在玩笑中,却又在这除夕夜里显得格外有神。
“不一样嘛?”克乃西特将这个问题抛回给同伴。
“自然不一样,克。”帕勃罗似乎来了兴致,扬起了声调,“巴赫对于你来说是公式,是守调和答题。但是巴赫只有这样吗?”
“当然不止。巴赫的作品还有其背后的意义架构与承载的社会意义。”
“太严肃了,太教条了。”帕勃罗摆摆手,“是超越你所知的言语能形容的美,是指尖划过小提琴和键盘的颤抖……”
帕勃罗口中如诗的抑扬顿挫被寺庙里新年的钟声打断,克乃西特将目光从他的同伴脸上移回脚边的醉汉,而醉汉恰巧也在这钟声中醒来。此刻克乃西特再是有一颗普度众生的佛心,也不可能在对言灵有恐惧的人类面前施展技能。
克乃西特在除夕钟声的末尾里无声打量着身边的同伴。然而对他的同伴而言,先前的句子就像是这刚开始飘落的飞雪一般,落在地上就不见了。
“荞麦面的口味如何?”
“不知道。似乎偏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