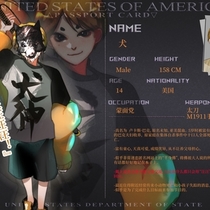



-只是把一二章幕间简单串一下的流水账,感谢六一陪我商量了很多——
-可能有一些隐晦的擦边球内容
-画手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写文.jpg
----------------------------------------
七乐修是谁。
“是林蕊的糖果、是河洛诺斯的骰子、是渡边凉司的打火机……”回答的人点了点嘴唇,沉思了片刻接着说道。
“是我的第一个吻。”
武见宵很少有这么诗意的时候,他向来不会说漂亮话,也不屑于说漂亮话。尽管从夹缝里爬出来的他明白一些适当的吹捧可以让自己过得滋润一些,但他偏不,他总是张大自己的翅膀恐吓并且反抗着那些企图征服他的家伙。
这无疑是有效的,武见宵过去的十八年生活都很清净。他保住了自己的翅膀,尽管代价是贫穷和糟糕的名声。他活在许多人的嘴巴里,又在许多人的大脑里死去。人们期待着他故事的结局,等着他发现自己就算张开翅膀也无法起飞的那一天。但武见宵没给他们这个机会,他熟练地收着自己的翅膀在大楼间穿行,直到他被自己的身体背叛,才安安静静地倒在出租屋的地板上。
他曾以为自己会就这样一睡不醒,但命运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武见宵在伊甸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发呆。他厌恶这里的家伙总是眯着眼睛打量自己,起初他会歪着头学着对方的样子来抗议,但后来他发现这里的生物并不会在意自己,就像人不会在乎家雀的想法一样。于是他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而是更消极地把自己封闭在广场的长椅上,看着其他天使和龙忙碌的身影陷入浅眠。
思考可以放大人的恐惧,武见宵在长椅上明白了这一点。他的脑海里有什么声音在为他落泪,那个声音假惺惺地抽泣着——死亡无法带来安眠,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不再有电子设备可以麻痹自己的武见宵近乎绝望地在这个声音里感受着孤独,他越想越把自己缩了起来,但寒冷依然从指尖蔓延到了心脏,直到有人在他面前停下,问他为什么在这里。
是七乐修。
武见宵抬了抬眼睛,用不可思议地眼神看着他。武见宵一直认为自己是鸟,是猫,是一切象征自由和逆反的生物,而那一刻,他却只觉得自己像一个游魂,一个经历了百年孤独后终于找到了目击人的游魂。
之后武见宵依然会没事就坐在长椅上。或许他该去森林里,或许他该去这座岛屿的尽头,但他最终只是缩在长椅上任由自己的意识到处乱飞。那些地方七乐修找不到自己,他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样想着。
武见宵曾经梦到过几次七乐修,他梦到对方和自己挤在那间几十平米的小出租屋内。出租屋里的空气是停滞且粘腻的,于是他拉紧了七乐修的手,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以给那些拘谨的空气让出一些活动空间为由,肆无忌惮地感受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
但武见宵并不觉得自己爱上了七乐修。他将一切原因都推给了青春期的荷尔蒙,他终于想起自己才刚刚十八岁这件事,于是他离开了那个长椅,走进了博物馆、农田、森林,记住了林蕊、藤野宙还有米格罗涅斯特。他依然喜欢一个人呆在角落里发呆,只是现在的他多了个消遣的对象。他注意到七乐修的头发在夕阳的照耀下会变成漂亮的栗棕色,注意到七乐修在思考时会不经意地用手指轻点三下桌面,注意到七乐修会习惯性地把东西放到身体的右侧……他注意到七乐修平静的眼眸下总藏着一滩深色的水洼。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七乐修并不喜欢这里。七乐修的过去应该是被人爱着的,因为他总是像呼吸一样关心着其他人。在武见宵的想象中,七乐修有家人、有朋友、有同学——就像每个普通的十九岁少年一样。
可这次他失算了,七乐修熟练地掏出枪时他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那把枪比在了猹的身上,但武见宵却看到了走马灯一样的画面。他看到了七乐修纹着纹身的后背,看到了七乐修空了的烟草盒,看到了七乐修眼底那片深色的水洼。于是他盯着天花板没头没脑地问道“七乐修是谁?”
七乐修转过了头,手指轻点了三下。黑道,这是武见宵记得最清楚的词。武见宵反复咀嚼着这个身份,而七乐修似乎也沉浸在了回忆里,他们两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对视着,直到武见宵叹了口气,趁着夜色把落星草放到了对方嘴里,这场沉重而无言的对话才算结束。
七乐修被过去困住了,武见宵想。于是他把七乐修抱到了床上,转身也沉沉地睡去。他希望落星草可以带给他好梦,就像当初他把自己从长椅上解救出来一样。
与七乐修相反,武见宵渐渐地适应了伊甸的生活,他放下了自己的过去,在悬崖边近乎麻木地凝视着那变为火海的地球。他只看到了火,一望无际的火,他离得太远了,远到听不清火焰噼里啪啦的声音。他木然地看着下面的一切,那些他生活过却又陌生得不得了的城市。
“怎么了?不要绝望呀?地上又不是没有幸存者,他们还是存在的。”
武见宵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诺法加在说什么,他只是沉默地站起来,习惯性地把视线投到了七乐修身上。但七乐修这次没有回应自己,深棕色的少年夹在吵闹的人群中间,瞳孔几乎被火光染成了红色,他就像一座雕塑一样凝视着下面的火球,这让武见宵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也重新把目光放回那片火海之中。
或许他该怀念些什么,或许他该想起谁,但是谁都没有,他的精神世界贫瘠而自由,就像一大片无云无光的天空。
——可七乐修不一样。
武见宵意识到这一点后几乎愣住了,他一瞬间明白了诺法加的话,熟悉的寒冷向自己袭来,只是这次直击了他的心脏。于是他挤出了人群,找到了七乐修,拉着对方来到了自己经常光顾的长椅旁边。他约莫着自己是真的慌了,他从来没这么莽撞地去找一个人。他歪着头悄悄打量着七乐修,而七乐修的目光却始终看向更远的地方。
“我曾认为活着就是活着……”
在漫长的沉默过后,武见宵把手背了起来,像被点名的小学生一样局促不安地搓着自己的手指。
“…………因为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更没有什么死去的理由,我只是觉得我能活下来很不容易,所以我想继续活着……”
武见宵说得有些卡壳,他顿在原地,用祈求一般的目光看向七乐修,可七乐修依然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让武见宵紧张了起来,他向七乐修伸出了手,但又很快地收了回来。他感觉自己的心脏比上一次死亡时跳动得还要快,他第一次这样逼迫着自己说话,他有些懊悔,可是他已经开了这个头,于是他张了张嘴继续说道。
“……我是不是绕得有点远?修,我知道你一定和我不一样……”
武见宵屏住了呼吸。漫长的寂静让他产生了错觉,他感觉自己长出了利爪和尖牙,变成了面目可怖的怪物,以至于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渺小而扭曲了起来。他甩了甩自己并不存在的尾巴,继续以那规矩且别扭的姿态撑在原地。
“我知道你有心事,但我不敢问,我怕你会逃避我,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会想起我的人……”
武见宵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明白自己是在撒谎还是发自真心地这么想。这些话就像是自己从他的嘴里跳出来的一样。他在示弱,他为自己感到羞耻,可他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任由自己的嘴巴背叛自己。
“……我害怕再变回一个人,在你向我伸出手时我几乎花了一晚上来接受这件事……”
武见宵觉得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可笑至极。他收拢起了自己生前最珍爱的翅膀,俯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他就像一只巨兽匍匐在七乐修面前,可他依然不敢动,七乐修太脆弱了,他怕自己的一个叹息就会将碾得对方粉身碎骨。
“……我不了解你,七乐修,但我害怕你离开……因为你不在了,我也就不在了。”
武见宵觉得自己大脑在嗡嗡作响,他记不清自己中间说了什么,也没功夫去思考自己说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疯了。事到如今他才明白伊甸的一切对拥有过去的人来说到底有多么荒诞,他一边祈求着自己醒来得不算太晚,一边将自己的目光困在七乐修的身上。
“……武见。”
七乐修的声音并不大,但武见宵却被吓得一个激灵。他并不清楚七乐修想要说什么,或许七乐修会指责自己,或许七乐修会觉得自己莫名其妙,但他确信自己听到对方呼唤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他就像受到了召唤一样挪到了七乐修面前,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抱住了对方。
“我在。”武见宵搂紧了怀里的人,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他的手不安分地在七乐修身上游走着,像是确认着他的存在,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最终他的手腕触碰到了那个记忆中坚硬又方正的物体。
是那把装有子弹的枪。武见宵在来伊甸前没见过真的枪,对他而言枪是同法杖一样只存在在电影和游戏里的毫无实感的东西。他曾宽慰自己,如果这个冰冷的金属造物可以让七乐修获得一丝安全感的话,那它便与首饰无异。
可那终究是把枪,武见宵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注意力飘到这把凶器上。在他心里七乐修并不适合杀戮,这个少年会轻轻拍打植物上的水珠,会像举起小猫一样举起恶作剧的天使。枪对他来说过于锐利了,于是武见宵搂住了对方的腰,将那把枪藏在了自己的臂膀之下。
那晚他和七乐修睡在了一起,就像在那间梦里的出租屋一样。武见宵几乎一直醒着,他觉得自己像一条守护着幼崽的巨龙,直到清晨的阳光照在七乐修身上,他才感觉自己褪去了身上的鳞片与獠牙,于是困意袭来,他放心地把自己的脸埋在了对方的身上昏睡了过去。
在之后的日子里武见宵总是主动邀请七乐修和自己出去,尽管他开始害怕七乐修盯着自己看的样子。那双黑漆漆的眼睛就像是一夜之间有了魔法一般,仅仅是对视就会让武见宵回忆起那个亲密但惊心动魄的晚上。
可他又不愿意放走七乐修。武见宵拉着七乐修漫无目的地逛了几天后便对着周围的花花草草动起了心思。他知道了植物园里的天使可以帮忙耕种,知道了小卖部里会卖那些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他本来是想种花的,但他又总觉得花对于七乐修而言有些艳丽得过头。他就这样在小卖部前犹豫了几个来回,直到旁边的天使向他搭话,他才像逃命一样买下了一袋玉米和一筐小小的鸡蛋。
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该怎样包装解释这个礼物。他与这些其他生命的胚胎大眼瞪小眼了一下午,直到七乐修找到自己,他才不情不愿地用灰扑扑的双手把这些小东西捧到七乐修的面前。他并不会照顾这帮小东西,可他又不想一言不发地把这些东西交给那群天使,于是他把它们交到了七乐修的手里。七乐修愣了一下,破天荒地笑了出来。武见宵被吓了一跳,有些惊愕地看着对方,不知不觉看得出神——这是他那晚在舞池里想看却没能看到的表情。于是他犹豫了片刻,开口问道
“我可以吻你吗?”
武见宵不会说情话,所以他和七乐修第一次扮演恋人的时候就选择了接吻。他相信行动可以代表或遮掩一切,但此刻他自己却不满足了起来。他把七乐修抵在旁边的床上,用鼻尖来回蹭着七乐修的颈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爱你。武见宵并不擅长接吻,或者说他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擅长接吻。当这一动作沾染上爱时,他变得前所未有地笨拙。他生怕自己的尖牙划伤七乐修,于是他踌躇起来,像是示好的动物一般蹭起了七乐修的睫毛、鼻尖与嘴角。
七乐修察觉到了武见宵的犹豫,他揉了揉武见宵的头发,像是安抚对方一般凑了过去。而武见宵也知趣地收下了这个准许的信号,将这暧昧的摩擦转变成了一个绵长的吻。他的手在七乐修身上摸索着。他亲吻着七乐修身上的每一颗痣,就像是要将七乐修整个人刻在自己的灵魂里一样。武见宵遵从着自己的欲望小心而谨慎地拉近着距离,直到他们中间连一块布料的位置都容不下,武见宵才抬起眼睛,又一次呼唤了七乐修的名字。
武见宵不再逃避自己爱上了七乐修这件事。他收起了自己高傲的翅膀,驯服地趴在七乐修的身上,任由对方抚摸着自己不曾被碰过的逆鳞。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被征服的那一天,但七乐修做到了,仅仅是用一个吻。
一个在巧合中诞生的命中注定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