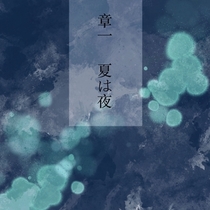雪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夜过后,前日的一切踪迹了然无痕,打开窗户放眼望去,皆是一片白茫茫。阿雪知道这就是自己名作雪的缘由。言后即弃,过耳即忘,风流之间的街井传闻要被埋在下头,缝起嘴巴,行事小心,莫不可被人追溯到留宿旅人的身上。
小豆子失踪一事已过去百日有余,老板娘早把那孩子抛之脑后,反倒还是常来下榻的旅人问起得更多一些。每每遭人打探,她总会嬉皮笑脸地说,啊呀,小豆子被人赎走啦,你们来得太迟,前些天里有个素未谋面的浪人对她一见倾心,掏空身上所有仍不得已,最后拔刀威胁所有人才把她抢走的呢。懂事的人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小豆子真是有福气,不懂事的人便问,那浪人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阿雪便竖起手指,在脖子上划一道直线,答道:不可说,不可说。
于是三个月过去,连总是下榻的旅人也不再问起了。期间,阿雪趁夜拜访了一次水天宫。从魑魅魍魉手中拯救平民百姓的神职竟因血脉传承,而在区区一介饭盛女身上觉醒,可真是莫大的讽刺。阿雪第一次去水天宫时,小豆子熬了一晚替她在松屋守夜,生怕有人发现她不知所踪——但一切都惊人得顺利。当阿雪见到那只从自己身体里钻出的猛禽时,她只是歪了歪头,听见巫女们管它叫玉响。玉石间的回响,她想,这从万叶集的一词中振翅而出的,分明只是一头半透明的白尾海雕,而玉响仅仅只是一刻,在碰撞,或是被砸碎时才能涌出的水声,蜉蝣之命般短暂,无法停驻。这海雕因成为自己的某种武器而无法真正飞往远方,故而,巫女只不过是万千困住飞禽的容器而已。
她们目如浅溪言之灼灼,说所有的人都是千鹤的后裔,从各式各样的地方继承了传说中那位巫女的血脉,于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便是要从鬼女手中保护她留下的圣器,以防那些吞食人类的鬼魅们重出人世。阿雪恭敬地低下头接过那套洁净明亮的巫女服,上好的棉布在指间是有厚度的,抵得上她们平日里叠上两层的质地,在夜晚和她的玉响一样散发出月亮般的光芒,但是,她抱着白衣绯袴和从来没见过的那么崭新的肌襦袢时,环顾四周,忍不住想:千鹤怎么能有如此之多男男女女的后裔?难不成,那唯一的神圣巫女生前也是个和自己一样的婊子?
于是她抱走漂亮的衣服,决定不要成为水天宫的一份子,因为什么样的人就该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古老的鸟居是千年牢门,她拒绝迈入其中。神官有马愁次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他只是垂着眼,和许多次阿雪瞥见他时一样,站在垂枝樱旁,因超乎常人的身高而总是拱着背,使得他很多时候像是从树根中生出的另半分树干,疲惫地向她摆枝点头。他和阿雪还有小豆子明明都差不多大,却总有种老态龙钟的神态,好像上千岁的不仅是棵樱树还有少年人本身,使得阿雪会幻想自己换上巫女服,又如待客时那样动用些技巧在他面前半褪衣衫能不能撼动一些那老树皮般的神情,但她终归还是没有这么做。她对自己接客的过程中有多少程度利用了这天生觉醒的催眠异能心知肚明,没有自信在神宫面前造次,更重要的是,无论最终有没有扒下这层树皮,有马愁次郎也都不可能付钱,而没有一个松屋出来的女人会做没好处的事情。
街头巷尾再度流言四起,有人说,吃人的鬼女又来啦,夜里可千万要小心,但是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水天宫世世代代守护着我们,她们可比夜密迴那些粗鲁的走狗更可靠。她回去并不出于责任,也毫无荣誉可言,只有一个问题:水天宫有听到过小豆子的消息吗?没有,有马愁次郎摇头,没有,蹦蹦跳跳的朱鹭捧着蜡烛跃进水天宫时关切地顿了顿,没有,手持神乐铃的雪踪巫女满脸忧虑,我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吗?什么小豆子,根本就没听说过!乡田真忠皱着眉头喊道,外边帮不上忙的人就别在这个时候来烦我们啦。阿雪一无所有地去了,又一无所获地离开,于是她仍然遵循着这一准则,不会得到什么的话就不要付出什么,而选择隐瞒了一个信息:
鬼女泷之宫亚已落塌松屋数月有余。
在遇见泷之宫前,魑魅魍魉不过传说,或栖山泽,或隐水域,阿雪只在流言与水天宫的情报中探得一二。泷之宫是她狭路相逢的第一个鬼女,从天而降的旅人,在小豆子失踪后出现在吉原外的街道上,她说不清究竟是谁先反应过来,到底是斗笠下陡然亮了亮的眼神,还是从自己身体里弥漫出的震动,巫女的使节在她做出反应之前率先窜出她的身体,半透明的海雕在月色下确实泛出浅青的光晕,她望着它也望着以非人速度扭身飞奔的鬼女,本能地跟着海雕屈身追上。
你见过小豆子吗?她追着鬼女问,想起男人的枕边语,他们得了瘤子病,靠近它的人都会得那病,然后他们被吃掉,他们就消失。你见过小豆子吗?鬼女一味逃窜却不语,阿雪只觉无名之火从身体里熊熊燃起,它明明在她的身体内侧,却灼痛她的脸,令她的旧伤在月下火烧火燎地疼。
找到小豆子有好处吗?她扪心自问,有的吧,一定是有的,比如两个人的日子一定比一个人的好过,比如小豆子要是还能继续赚钱,那么自己也能继续偷钱买糖,用别人的钱买糖和用自己的钱买糖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好处的事情……
tbc
*来不及写了真的来不及写了我先滑铲卡上!! 瞎响应了一下大家ry
吉原外围的跑腿,松屋的小豆子,在一场打焉了紫阳花球的暴雨里,从病榻上一跃而起,宛若女童般喊着狐狸卖糖啦,狐狸卖糖啦,留下敞开的门洞,光着脚,踏上这辈子从未离开过的路,一去不复返。
被闹到的人只有阿雪。太鼓未起,钟塔尚在睡,不足卯时,大抵仍是三更,暴雨罕见地下了整整一日,故耳里灌满雨线。小豆子的叫嚷在拢紧的破棉被间只渗进了几个音节,喊道,狐狸,狐狸。阿雪半梦半醒,恼火不已,想那开满梅花的小妮子就算在梦里也要找她麻烦,真是一天比一天更疯,看样子不能再留情面,必须得好好教训她一通。清晨,町奉行所的巡逻太鼓一如既往敲醒了小松屋里的人们,阿雪睡眼惺忪,一时吃不准夜里的动静究竟是不是一场梦。她起身,扭头看向一旁,在无风的雨声中,布帘静静晃动着,另一头的草席平坦得像被摁瘪的稗子饭。
更衣后,阿雪走到敞开的门边,听见老板娘抱着双臂骂道,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睛的叫门敞了一夜,若是隆冬腊月的,可不就是想冻死全屋人。门槛被雨水冲刷得亮晶晶的,前夜洒了大半碗酱汤的污渍不见踪影,阿雪偷偷抬脚,在门槛上磨蹭了两下,发现也不黏了。心想,好嘞,偷懒一下也不坏,这下老天倒是替她收拾了。那今天就饶了小豆子也可以吧,就当作是还一个恩情给老天。她回头喊小豆子,没有回音。
明和八年,阿雪十七,小豆子不过十六,正是绽放的年纪,小豆子明明更小,却事事走在阿雪前头。不光月水,还有早早舒张花瓣的满身赤梅。倒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这地方人人都懂,开得早谢得便也早,某种程度上,阿雪应当感谢那几乎斜斜蒙过她半张脸的伤疤,如野兽皮毛的纹路,在小豆子曾经姣好稚嫩的面容旁黯然无光。她又喊了一声小豆子,仍然没有应答。
不是好梦就喂给貘。她念着口诀,回想夜里小豆子的声音,喊她狐狸,狐狸。上次她偷了四文钱去买糖吃,小豆子有没有发现呢?管它呢,一日没被发现,她就一日不必操心该怎么还上,再说了,只要咬死不承认,小豆子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可小豆子究竟上哪儿去了?她该不会是想偷偷躲起来,好让自己不得不干完两个人的活儿?还是说,她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阿雪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狠狠地哆嗦了一下。小豆子总是这样。看起来天真无邪,其实精明得很。倒不如说这松屋的门面下,天真总归只能成为一种衣装。两人都是住在旅笼的饭盛女,名义上是替留宿的旅人盛饭端汤的下女,实则把能干的都干了。好人家的孩子谁会来这地方,何况是没有天资的卵虫,连吉原的门槛都摸不进。
老板娘的嗅觉毒辣,此刻已从门边收了回来,朝她身上瞥。阿雪佯装镇定地回过身。阿妈呀。她说,知道此刻一动不动或是一言不发只会引发更大的怀疑,于是笑嘻嘻地撩了撩那头火红的长发,这种事,可只有那疯疯癫癫的小豆子干得出来了。说罢,便晃着步子,回到隔壁空荡荡的铺间去了,留下老板娘的声音在身后不断徘徊,小豆子!小豆子!
趁着老板娘尚未生疑,阿雪溜回接客的房里,掀开破木箱的盖子,拿开装着些铜钱的包袱布,打开底下一层木板,露出仅三指厚的薄隔层,下面躺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巫女服。干净,柔软,散发着不属于这笼子里洁净的气味。她刚要松一口气,发现角落里多了一团棉腰带,压在一侧,揉得看不清模样。她才没有那么俗气的腰带——一定是小豆子发现了这个秘密,故意塞进来的。想到这脏兮兮的腰带搁在她最漂亮的衣服上好几天,她就恼火得要命。
小豆子呀,那只不过是买糖的四文钱,就这样拐弯抹角地发出警告,也未免太小气了。阿雪咬咬牙,若是弄脏了这套她好不容易装模作样才从水天宫里骗来的衣裙,她这次定要饿上那家伙几天。阿雪抓起那团腰带,在察觉到它底下几串铜钱,以及它出奇的沉重之前,她已经甩开手臂,将它丢向空无一人的草席。长长的布条在中途散了开来,露出洗得干干净净,星星点点褪去半分的玫色,像撒出了一大把花瓣似的,十几枚四文铜钱在空中骤然坠下,滴溜溜砸了一地。每一枚都已冷去一夜,每一枚,阿雪都能记得小豆子藏起时的侧脸。
暴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下,屋外,噼里啪啦地落起冰雹。老板娘合上破拉门,在留宿房客的连天哈欠与催促中回到屋内,重新喊道,阿雪!阿雪!
阿雪飞快地俯身捡起一枚枚硬币,重新包回腰带里,塞回夹层,合上木箱,伸手去取一旁脱了一地干活的衣裳,裹上头巾,扎在脑后,露出长发下,那道叫人第一眼瞥去时都难免一惊一乍的伤痕。她不需要看见自己的脸也能日日见到那疤痕,记得它的凹凸斑驳,深浅不一的玫红。她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能确保她从中看见自己。她应声回到前厅,老板娘扭身过来,她伛偻着背,手里攥着竹竿,一脸狐疑又恼怒。
“可是,那没用处的小豆子究竟上哪儿去了?”
阿雪摇摇头。正值六月尾声,距离小豆子最喜欢的两国桥花火大会只余下两日,而她对小豆子的去向毫无头绪。
“小豆子,谁管她啊。”
老板娘气冲冲地抬手甩了她一记耳光,脆亮地响,手背打得,不疼也不会红,阿雪捂着脸作势皱眉,“留在小松屋里,多少还能帮帮手呢。”
“多一张没用的嘴!要我瞧,就是那忘恩负义的小鬼逃跑了,就成那样了,大概脑子也不清不楚了,没想过就那样一个身子,有谁会要,又怎么活得下去吧?”老板娘哼了一声,“我倒该瞧瞧那个小东西有没有顺手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会的。阿雪想,她不可能偷走任何小松屋里的东西,因为她连属于她的东西都没有带走。一枚接着一枚的四文钱啊,攒起的数千宽永通宝,连这些都没有拿的小豆子,必是身无分文地失踪了。她不是逃走,她只是在没有月亮的夜里走丢了。
“她可走不远呢,阿妈要是愿意,我今日便能将她找回来——”
“找找找,你能找什么,别再想着偷懒了!”
阿雪灵巧地歪过身,躲过老板娘抄起的竹竿,窜向桌边,“知道啦!该做的可不会停下——瞧瞧,客人就要来啦。”
啊呀,回头客了,您还记得小豆子吗?对,就是那细身柳腰,笑起来嘴巴有点歪,总爱眯着眼的姑娘,人人都夸她的浅渍萝卜做得好呢。不记得了,无妨,您贵人多忘事,往后再来小松屋啊。哟,您今日从哪儿来呀,经过了溜池?还有日本桥,⼗轩店的人偶真漂亮,是不是?您有没有见过一个比我高一些的孩子,她脸上肯定脏兮兮的,啊呀,就好像染色的人偶。对,她一个人,但她没有旅人的衣裳,您说笑呢,就是打听打听罢了,您今夜留宿?只是留宿吗?不去吉原……我就偷偷告诉您呀,吉原的那些个红人,有时候也来小松屋吃口浅渍萝卜呢,尝尝鲜,散散心,您要是留在这儿,或许还能远远瞧上一眼……
“她呀,我根本不记得那张脸。”
有资格迈入吉原门槛的女人倒也并不一定个个艳压四方,才华横溢,有丑女人,也有蠢女人,又丑又蠢的女人更多,眼前就有一个。女人趾高气扬迈进小松屋的那一刻阿雪就该偷走伙计的羽织披上就走,结果大概是走投无路,鬼迷心窍般开口问她,吉原里有没有小豆子的传闻。回答自然叫人失望。
“什么小豆子小梅花的,你们这旅笼里的丑八怪,谁记得清楚这些呀。”
“有理。”
阿雪说着,转头去后厨端来一份腌萝卜和炸豆腐,放在女人面前。黑发女人一身毫无掩饰的华服与梳得繁复的发髻引来众多宿客不加掩饰的贪恋,可那双吊着眼梢的赤瞳却炯炯有神地盯着阿雪,不放过她的一举一动。她这会儿倒是来了劲,朝阿雪挥挥手,瞧她回到跟前了,手一推,便把小皿打翻在地上。
“就这破萝卜,你倒去喂鲭鱼还差不多。”
阿雪在衣摆上搓搓手,歪头笑道,“真是的,鲭鱼又不靠萝卜喂,再说了,我们这不过是供人下榻歇脚之处,倒也只能端出这些粗茶淡饭,远比不上您的住所。您要是瞧不上,直说便是,莫用顾虑我的心情,还说什么喂鲭鱼去吧。红叶姐姐真是体恤人心,不愧是偌大吉原里也要数一数二的红人啊。”
伙计在阿雪身后赶紧上前两步,抢在红叶发火前头就蹲下身子去收拾狼藉,但仍是没忍住在阿雪腿边噗嗤地笑出了声。后者瞧见红叶脸上一阵发青,又说,“啊呀,怪阿雪太粗心,没注意到红叶姐姐已经用过晚膳了 。”
“谁跟你说我吃过了——”
“晚膳里该有赤豆吧?喏,那么一大颗,还沾在嘴边呢,啊呀,真是的……”
她瞧着红叶强掩慌乱,精心涂抹上染料的指甲在白皙的脸庞上游移,而一旁屋中几个零星的旅人已低笑出声,眼见红叶瞪大眼睛,阿雪倾身向前,抓住红叶的右手,拇指抵住她的食指关节,便朝她的嘴角一侧探去,“喏,便是在这儿——”
阿雪眯起眼睛,未经梳理的长发从耳畔垂下,令她侧脸酒窝的凹陷和伤疤渐深。她没有看到红叶气得发抖的嘴唇,也没有看见捧着碟子碎片和腌萝卜的伙计,只是有意地,缓慢地,抬起眼,停留在那个小口小口抿着味增汤的旅人身上。他压着斗笠,遮住了大半面孔,但没有掩去投向这边的视线与唇角的笑意。
“啊呀——”她轻启朱唇,贴在红叶耳后,“恕我眼拙,原来这是姐姐的美人痣呀。”
如月般浅金的双眼没有躲闪,直视着那旅人。若是她的眼神没错,那么大概能隐约瞧见桌下平织半袴的纹样,说不定还是个今夜去不起吉原,想来这儿寻求慰藉的武家人。不过,只要付得上钱,武士也好,卖油郎也好,饭盛女总归是来者不拒的。阿雪朝男人眨了眨眼。后者抬起头,在斗笠下回以无声的邀请。
“……没有听说过。”
男人喃喃道,“小豆子?这叫什么呀……还是阿雪好……”
在破旧的屋檐下,阿雪赤身裸体,从后方拥着男人,伸出手臂。掌中握着一支精致得好似不在此处的发簪,如饵悬在他的眼前。垂下的樱花坠子在无风的夜里静静摇晃着,近乎洁白的粉晶体之中,玉絮涌动如云流。男人盘腿坐在草席上,和阿雪一起望向窗外。
阿雪跪坐在散开的襦袢与绯袴之间,低声说,“你没有见过吗?比我还要高一些的孩子……脖子和手腕上都有梅花的斑痕……疯疯癫癫的……”
虽说阿雪年长几个月,自幼却是由早熟的小豆子领着长大的,打打闹闹,形同手足。听闻,自己尚在襁褓之中时便被人丢在了松屋门前,险些冻死在新年的第七日,因此,阿雪对于老板娘捡了自己一条命回去毫无怨言。但小豆子不一样。四岁时,她的生父牵着她的手,将她送入了这扇拉门中,听闻卖了个不错的价钱。她们谁都没提过自己究竟是怎么到松屋来的,但就像生来便接受了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对彼此的来历一清二楚。每当望见有人携着重金替花魁赎身,吉原花楼摆起连夜的欢送宴时,小豆子总要问阿雪,会有一日,路过的旅人对我一见钟情,倾囊相助,替我赎身吗?这是只有小豆子才会问出来的问题,因为任何见过阿雪的人,都不会冒出分毫这样的念头。阿雪因此暗暗记仇,也往往诚恳作答:别做梦了,小豆子。
“流娼脏兮兮的……”男人的呓语绵绵不断,视线却没有从前方的坠子上挪开,“小豆子是什么名字?红豆啊……梅花,怕是花柳病吧,就该躲在后头,别出来了……害人,害人不浅啊……红叶很漂亮,听说她自称是鬼女……谁知道她也这么疯疯癫癫的啊,太傲了……阿雪,再抱抱我吧……”
他们彼此贴近的一小块皮肤渗出汗水,阿雪没有动,也没有松开他,任由男人打开话匣子,如落樱接连掉下。“你真漂亮啊……挡住脸的话,很多人会喜欢你的吧,成为花魁也有可能呢……啊,那个干巴巴的怪人…… 盂兰盆节前,他们请了驱魔的纸人,要消灾除厄呢,为了啊,为了驱逐瘤子病……”
“瘤子病?”
阿雪攥紧簪子的手心冒汗,屏息追问,同时感到男人的视线与指尖的连接变得更加粘稠,坚韧。 她无法描述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并非花魁的三味线或是将棋,依靠长年累月的修习,积累经验,便能讨人欢心。催眠是一种扎根在血里的东西。阿雪想,就和月水一样,某一天醒来时,便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携有这东西的人,有些人会有,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而她正是前者的一部分。催眠又何尝不是一种魅惑:她因脸上狰狞的烫伤而失去进入吉原的可能性,却又生来具有她们百般雕琢才能习得的技艺,阿雪想,大概她的天职便是如此吧。
“瘤子……或是花柳,梅花……鬼女不会死,鬼女也不吃人……怎么会有不吃人的鬼女呢……但是人会被吃掉,啃掉……”男人说,“他们得了瘤子病,靠近它的人都会得那病……然后他们就被吃掉了,他们就消失了……”
“消失?”
“被花,或是瘤子,吞掉了……”男人念道,眼皮犯沉,和手一起垂下,擦过阿雪的肩膀,手臂,和腰腹,“而那东西一直在流浪……哪怕被夜密迴的武士讨伐了,它还在继续……听说前些日子还在日本桥附近出没,人们说它叫,叫阿……”
它叫什么?他说,啊。好像感叹也好像是一个名字。啊。一个音节,缠在阿雪的心头。它织入夜晚小豆子喊出一声接一声的狐狸里,锻入铜钱串的划痕,绽放在两国桥的夜空中,和花火大会后三日,被人在夜巷里发现的小豆子身上的斑痕融为一体。
同日,泷之宫亚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迈入了小松屋的门槛,在老板娘的惊呼中,陌生脸孔的旅人松开手中的脆木枝,面朝下方,扑通地倒了下去。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