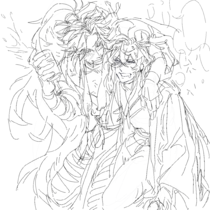剑破竹风。
一剑霜寒十四洲,小米粥腊八粥…
苔痕上阶绿,两道身影自后山窄渠鱼贯而出。
暮春既望,余行至云梦之陲,李不悔深吸一口山外清气,草木晨露之味透腑,暗扶葛布捆绑长物。
“这鼠蹊亏你还记得。”
陈忱拧去袖口泥水,湿发贴额,长睫凝露,朽木短笔已拾回袖中。
“总强过撞石头。”侧耳听风送远处铁靴踏石声渐杳,“你就说是不是溜出来了。”
对视间,眼底皆掠过一丝鲜亮。练剑年年,觉风都带着野草气,鼓荡薄衫,亦撩动心弦。
未走坦途,专拣樵猎荒径。李不悔步阔而沉,背负之物随行止自有沉钝韵律。陈忱稍后,身形轻灵,目掠道旁虬枝岩纹,似有蹊跷。
俯身观摩,只见那枝叶攀升竟化作一狗,向着陈忱扑来,舌头直愣的舐舔。
“!”
“快晌午该吃饭了,”李不悔支楞的看着天上提议,久久得不到回应,暮然回首却瞧见陈忱与狗共舞。
“你啥时候背着我养的新宠物?”
“看甚!”陈忱推搡着狗杞唐突的热情,“没见到我被狗咬了吗!二狗你再不来救我咱俩就完蛋了!”
“你要染上狗细菌了!”
“少废话!我要打你一顿。”
不由得继续闹哄,李不悔赶忙着扯那枝叶,狗杞黏着认定了陈忱一样难办,前者思来想去遂撮拳蓄力,铆足了劲向妖物打去,那妖却将身一扭,滞留作浊气消逝不见了。
“嗷!”
。
“饭可晚吃,”陈忱淡道,却虎视眈眈的盯着李不悔似要透穿他,后者羞赧挪开视线。
话虽如此,脚下未停。方向似早已默定,不真争执。只这山径沉默走得久,李不悔身后的视线似化真针戳刺着,便随山风步履,渐活渐躁。
至溪谷开阔处,水缓滩平,卵石累累,清可见底,银鱼倏忽。日升高,岚尽散,天光清透,四野唯闻鸟啾虫吟,幽静更深。
风声掠颈,寒毛乍立,凝气擦过三寸。
侧目而视即是陈忱偷袭。
李不悔腕抖,葛布散落,露出黝黑宽阔剑身。无鞘无锋,只刃口一线幽光,泛沉凝乌泽。
起式未平,剑已动。非直刺,乃横拍。剑身厚重,破风低沉,卷起枯叶细沙罩向陈忱面门。未运灵力,纯是筋骨气力与兵势,简极。
陈忱错愕见李不悔兴燃之情,足尖卵石轻点,身如风中絮后飘,实却迅捷。啄点食中二指并拢虚点,引符凝指风破空,正正点在袭来的宽厚剑脊侧。
“嗤——”声如裂帛。剑势带偏三分,擦陈忱衣角掠过,劲风鼓袖。李不悔腰胯猛拧,臂回带,重剑竟似无物般灵动翻转,变扫为撩,自下而上划向陈忱下颌。变招快而突兀,衔接无痕。
陈忱并指如戟,身前凌空划半弧。又一缕更凝指风迎上,如柔丝缠铁,抵在剑锋将起未起之节。
重剑撩势果为一缓,但绵绵抵不过真势。恰陈忱已趁此微隙,身如游鱼侧滑数尺,拉开距。双手指诀变幻,或点或划或拂,凝练指风不直攻,只以巧劲扰动气流,将李不悔那势若千钧的重剑招,化于将发未发、方发即偏之微境。
两人便于卵石溪滩交手。李不悔剑势大开大合,劈扫崩砸,招招着实,虽未运灵,却将重剑重、惯性用得淋漓,每击皆带沛然力感,剑风激荡,野草尽伏。
陈忱始终外围飘忽游走,步法轻灵奇诡,时如蜻蜓点水,时如风送流云,合以神出鬼没凝练指风,每每于间不容发之际,以巧拨千斤,引偏滞阻沉猛攻势,身形摇而不与重剑硬撼。
谷中闻剑破空闷啸,风林竹影抖,日光穿疏林,光隙间腾挪身影,溪水映交错人影剑光,被剑风拂皱,碎作万千粼粼金片。
“躲啥呢!瞧这!”久攻不下,李不悔胸中气血涌,躁动化战意。低喝一声,剑招转疾,不再求一击建功,化连绵攻势。
重剑抡圆,横扫未尽,已踏步前冲,剑身借势回环,化崩山式,剑尖抖出三点虚影,分取陈忱上三路,如惊涛拍岸,浪高过一浪,将陈忱身形彻底笼罩,直逼溪边苔痕青石。
陈忱身形已被剑风压得凝滞,背脊堪堪触及冰凉湿滑岩面,退无可退。
蓦然眼中光芒倏凝,非但不闪,反迎剑影重重,并指成剑,顺符疾点而出!此次,指尖微芒凝至极,虽仍不显光华,却隐隐牵动周遭气流,发细微蜂鸣,正正点向重剑力道流转、虚实转换最核心的枢纽关窍。
出乎意料符纸并未得力,霎那面面相觑,沛然前冲刚猛力道,剑势为之一窒,现刹那凝滞。电光石火间,陈忱揉身直进,如游龙欺近,掌在李不悔持剑腕脉处轻拂按下,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砰!”
闷响,气浪荡漾,地上细砂草屑激扬。二人各退三步方稳。重剑哐啷落卵石,砸出浅坑。陈忱胸口微伏,气息显促,符纸随着效力消逝。
谷中骤静,唯余潺潺溪声。日暖尘浮。几只惊飞山雀试探落回枝头,啼鸣清脆。
李不悔甩甩微麻臂,俯身拾剑,指腹拂过微凉剑身,咧嘴露齿:“中了不?!再不中你要炸死我俩同归于尽啊!”
陈忱缓缓平复呼吸,狼狈在青石上喘息,抬手拨去水草:“去你的。”见符箓湿透浸开,“要不是没摁对我就赢了。”
休沐片刻视一地狼籍。
“不过倒也是,你若辅以运气…不对啊,欺负师兄算什么本事?!”
“哦哦…!”李不悔将剑仔细裹好负背,动作熟稔,“那多没劲!凭手脚功夫分高下,这才痛快。”
抬头看天,日近中,林梢影长。“这一下筋骨活泛,肚也空了。走,寻处有烟火地。”
“……嗯。” 陈忱轻颔,目亦投谷外。
言闭掸去身上草屑尘土,辨向续行。步履间,多几分从容。
山路渐下,林色斑斓。枫赤似火,银杏黄如金,间杂松柏苍翠。林梢越鸟,留细鸣。
日偏西,终循渐晰烟火人声,觅得一处依傍官道小镇。镇不大,粉墙黛瓦,青石板路贯穿。镇口立饱经风霜石碑,笔力遒劲,字迹漫漶。
推门扉,堂内已燃盏油灯,光昏黄温暖,驱秋日暮寒。栈内各围坐,就简酒菜低语,碗碟碰撞、偶响爽朗笑,嘈杂富生机市井交响。
见两年轻人掀帘入,虽衣着普,甚至因赶路切磋略显风尘,但那挺拔姿、清朗眉目,气度不同。
“先打尖。” 李不悔拣窗边桌坐,重物靠墙。
“劳烦掌柜,拣几样拿手热菜,快些。再打两角好酒,务必烫热。”
掌柜忙不迭点头,“好嘞!客官稍坐,热茶马上,酒菜立便!” 高声朝后厨吆喝几声菜名,又提来壶滚烫粗茶,为两人斟上。
温热茶入喉,带粗粝茶香,确驱几分秋夜凉意。不多时,家常菜蔬并两壶温酒上,无珍馐,却热气腾腾,香气实在。
李不悔拍开泥封,各斟满面前粗陶碗。酒液在碗中微荡,映跳动灯火。
“来!”端酒碗,眼中带轻松笑意。
陈忱亦举碗,与他轻轻一碰,碗沿触,发清脆轻响。遂浅啜,辛辣酒液滚喉,带一阵灼热,随即绵长回甘。
酒乃镇酿土烧,入口辛辣,后劲绵长。数杯下肚,连日情欲皆化温酒饭菜热气中。话渐多,低语枫林镇烈酒、残碑林古意,眉眼间尽少年偷闲鲜活。
正当酒意微醺,身心俱松时——
窗外,西北方向,巍峨连绵的群山深处,原本已被夜幕完全吞噬的天际,袅袅升起一缕红烟,猛然炸开!
那光芒并非一闪即逝的流星或寻常烟火,而是以一种极其不祥的方式持续存在,每一次闪烁,都仿佛带着无声的尖啸。
是(啥来着那个信号枪)!
宗门法典载(哦哦这个信号枪的介绍忘了)。
陈忱手中粗陶酒碗落桌,酒液泼洒,速浸湿一片。面上笑意瞬间冻结,血色褪尽。
李不悔捏着竹筷的手指停在半空,灯火亮印在瞳孔间,瞧着陈忱。
堂内客亦察异样,挤窗边,指血天,惊恐低语。
栈外远方飘来传言:妖物入侵了!
二者猛起身,木椅腿刮地刺耳锐响。李不悔一把抄起靠墙重剑,裹缠葛布三两下扯落,重剑于灯昏黄光下,泛冷硬如铁石光。
陈忱摸到口袋抚下符箓,另手起死攥住笔。遂看向李不悔,喉结滚动,无声。
无需言。
方才酒肉微末暖意,被血光映照得荡然无存,只余冰冷刺骨寒意,自脚底直冲天灵。
偷得浮生半日闲?少年意气踏秋游?
皆成泡影。
甚不及交换一眼。
李不悔已然转身,不及反应揽腰带走陈忱,紧压肺腑后者敲打无果。重剑一提,向客栈大门,跃向那血光冲天西北群山。步伐沉重迅疾,踏地有声。
二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寒意料峭的秋夜之中,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将暂得如同一场错觉的安宁与闲适,决绝地、彻底地抛在了身后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冰冷夜色里。
风,在耳边呼啸,带着远方隐约可闻的、不详的震颤。山路崎岖,夜色如墨,星辰皆隐,唯有西北天际那缕缕升烟,成为天地间唯一的方向与坐标,冰冷地指引着归途,亦昭示着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何等命运。
随便水了一些。。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