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沃德
Created by seeotter
“我知道黑桃犹如战士的利刃。我明白梅花仿佛战场轰鸣的枪炮。我认为方块就像到手的财宝。但那都不是我心(红桃)的形状。……如果我说我爱你,你大概会认为我说的话有点问题。但事实上我并非多面善变之人,我的面具始终如一。”

-

理查德·沃德人设纸
-
安格斯注视着倚在墙角里的那只深褐色皮箱。
自从他与理查德认识以来,在他的记忆里,这玩意儿就似乎永远和理查德·沃德这个名字紧密缠绕在一块儿,哪怕把它说成是理查德身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器官也毫不过分。不管亲爱的理奇处于如何糟糕的境地,这个箱子都从未离开过他半分——哪怕有段时间理查德曾不告而别地消失在自己的生活里,中断了与自己的一切联系,然而等他再次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这只褐色的皮箱就默默靠在他的脚边。
街头初次相遇,理查德的身旁立着这只箱子,他抬起灰色的眸子,冲着自己露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明亮笑容。当他们在理查德的“八号安全屋”中忘情激吻时,还差点双双被黑暗中的箱子绊倒在地。理查德提出和自己组成SO邀请的那天,酒吧里昏暗的灯光投照在脚边的箱子上,每隔两秒便将其染成另一种颜色,虚幻又妙不可言。现如今他们组成了SO,过上了每天大可堂堂正正亲昵示爱的日子,却仍然摆脱不掉这只碍眼的旧皮箱——这玩意儿一直未曾脱离出他的视野,理所当然地占据着理查德生活的一隅,宛如情人般如影随形。
安格斯之前也曾十分好奇地询问过:这只从未当着他的面被打开过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贝——全身赤裸着躺在旁边的理查德眼神里顿时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警戒色,眯缝着的灰色瞳孔像只狡黠又慵懒的暹罗猫,然后他支起身体,毛毯从肩头滑到腰际。安格斯看到理查德背部瘦削的骨骼突了出来,他任由那双棕色的手臂缠上自己的脖子——他们的面庞挨得很近,眼神接触,均试图从彼此脸上读出对方潜藏的心绪。
“里面全是我债主的艳门照,你不会想看到的。”理查德满脸都是明朗过头的笑容,然后献上了一个甜美的亲吻。
安格斯努力将自己沉浸在这个吻中,不去回味这些玩笑话背后的意思——不要问,亲爱的,因为那不是你可以触及的底线。
那个东西,仿佛充满着生命,有着自己的意志。就好像它其实是一个活物,随时都可以从那个该死的角落离开——只是计划着想要不起眼地呆在那儿,嘲笑着他藏于心底的耿耿于怀,润物细无声地继续阻隔在他和理查德之间。
安格斯有时会从半夜惊醒。
从很久以前他就是这样了,大概是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身边若没有人的体温便很难睡得踏实。
身体往往比意识更早做出反应,尚未睁开眼睛他已伸手去摸身侧,并未触摸到期待中的温热,于是在刹那间完全清醒。
“理奇?”
他轻声唤道,无人回应。
冷汗瞬间爬满脊背,心跳落在太阳穴上,他掀开被子从床上跳下,赤着脚冲到隔壁房间——
那箱子还在。
提起的心落回了原处,但紧张的神经仍在皮下隐隐作痛,脚步声经过房间门口,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安格斯?”
他回首看见理查德,腰间松松扎着自己的衬衣,像只是去厨房取了一杯水喝的模样。黑暗中虽看不清对方的脸,但仍然能感受到那落在自己身上的诧异目光。
“……你吓我一跳,大半夜的傻站在我房间做什么?”理查德问道。
安格斯听见了问话,却无心解答对方内心的疑惑。一种奇异的安心感伴随着缺氧造成的晕眩让大脑里空空荡荡的,他呆呆愣了几秒,然后缓缓朝门口挪去,在一片漆黑的沉默中他猛地将站在走廊里的人扯进怀里,用不可理喻的力量把对方牢牢环扣在双臂之间。
理查德像是被安格斯这股突如其来的热情给着实给惊到了,但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你真笨。”他轻声埋怨道,声音却透着温柔的笑意。“难道你以为我如今还会不告而别吗?”
安格斯依旧没有回答,但是那徒然收紧的手臂无疑证明了他的猜测。
“别傻了,你要是每晚都这么一惊一乍地我可受不了。”理查德亲密地凑近至安格斯的耳边,低声在他耳边痒痒地说道:“嘿,虽然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过——但是我无意中在上衣内袋里发现你的公寓钥匙时,心里他妈的有多么惊喜吗?见鬼,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去’,于是我对客户撒谎说自己肚子疼得要死,推掉了所有的邀约工作,拎着行李跳上了最早那班飞机,用那把钥匙大半夜地打开了你公寓的房门——”
“然后你看见我光着脚跑出来的狼狈模样。”安格斯轻轻说道。
“是啊哈哈。”理查德笑了起来,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热,有什么在体内不安地躁动着。“屋子没有换锁,床上也没有野女人或者野男人,我甚至闻不到空气里存在过香水的味道。”他贴紧安格斯结实的身体,呼吸微微急促起来,“我说这位帅哥,你是一直在等我回来吗?”
“一直。”
他们在黑暗里亲吻。没人想起那只皮箱,就静静呆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角落里。
【Triangle】潘多拉之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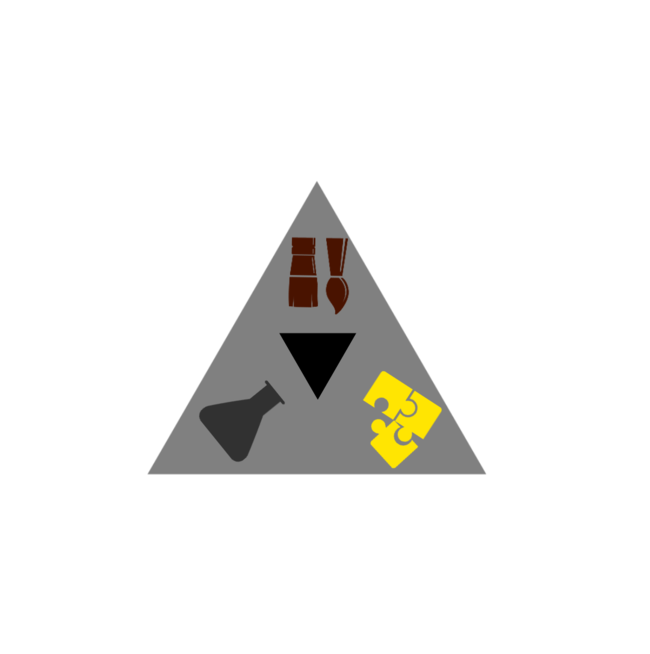
AAA组SOlogo
-
*很抱歉这篇拖了这么久,再次对互动的向日葵小姐表示深深的歉意,也很愧对同组的另两位成员,鄙人三次元的变动还在继续中,不能按时打卡真的很抱歉!
*再次道歉【鞠躬
如果没有这场台风的话,他们现在大概还在公寓里就着炸鸡和啤酒重温那部看了不下五十遍的老电影《黑色大丽花》。米娅·科什娜饰演的伊丽莎白有一双会说谎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透出风尘又纯情的光采。黑白屏幕里的少女倚着栏杆坐在地上,带笑的嘴角被泪水打湿。她摇晃着膝头,孩子般天真地用手指抠着丝袜被勾破的地方。
“看着那双眼睛,无论她说什么你都会相信的,不是吗?”理查德歪躺在沙发上,后脑勺枕着安格斯的腿,五根手指还插在爆米花堆中,嘴里嚼着一块炸鸡,灰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泛光的电视画面。
安格斯用视线勾勒着理查德脸部的轮廓,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当然了。”
理查德往嘴里塞了一把爆米花,没有发觉安格斯的视线。
“……我曾有个未婚夫。过去他常给我写漂亮、华丽、浪漫的情书……”电影里,黑色大丽花咬着嘴唇,笑容灿烂,晶莹的眼泪却扑棱棱直掉。“……后来,他死了。”
传来理查德吸鼻子的细微声音,安格斯下意识地用指尖轻轻敲了敲沙发的皮面。尽管这些电影他已经陪着理查德看了很多遍,但是每到一些关键情节,他这位深色皮肤的恋人还是会陷入片中角色的忧伤之中。“多愁善感是艺术家应有的特质。”理查德曾经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画画而你不会!”
我爱他。安格斯想。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陪他看电影一百遍也不觉厌烦的原因。
“阳什么时候回来?”理查德突然问道。“刚才我还瞅见你摁手环来着,是在给他发短信吗?”
“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也没有回我的消息。这种天气希望他不要一个人傻乎乎地步行回来……”金发男子显出一副很头疼的模样。“路上太危险了。”
“你是要他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吗?那也太寂寞啦!”理查德丢下炸鸡和爆米花,将两只油腻腻的手伸到安格斯面前,连连催促。“走吧,我们开车去接他。快点。”
还是老样子。安格斯握住理查德的手腕,替他吮去指尖上的油渍。这家伙有时候就像一只被宠坏的猫,金发男人将混着啤酒爆米花尼古丁和调和油的味道咽下——没办法,理查德就是知道他愿意惯着他。
“下次别选这款辣酱。”他咂了咂嘴。
* * *
“抱歉,我是不是打搅到你了。”视线对上的一瞬间,他从栏杆旁起身朝她走去,态度自然得像是在跟老熟人打招呼。“今天真是个适合写生的好日子。”
“是啊,天气不错。”她带着些许善意的疑惑笑着回答。
“让我看看——”他望向画纸,那上面色彩斑斓,每种东西都以令人困惑不解的形状和颜色分布在画面的各个部位,于是他笑了,那是一种很亲切的神情。“真是一副好作品。”
他诚挚地说。
* * *
“真是棒透了!”
理查德踩着不断上升的积水,飞快地爬上离他最近的那辆车,一屁股坐在引擎盖上,脱掉湿透的鞋子随手放在车顶,却不小心在缩回手时将其中一只碰落水流中。
“小心点,辛德瑞拉。”
安格斯正好从车道另一边走过来,弯腰从水里捡起被冲走的那只鞋,甩了甩水重新放回车顶上。
“怎么样?每个出口都被锁上了吗?”理查德问。
“我们真是幸运,这里的车库全是最新式的安保措施。”安格斯自嘲地笑了下,“台风一断电,车库自动全封闭。”
“信号也不通。”理查德烦躁地挥了挥手腕。
“我没带烟出来。”安格斯对理查德的烦恼置若罔闻,翻了一通口袋,抓抓头顶深叹口气:“打火机刚才掉水里了。”
“要是能出去,我马上去买彩票。”理查德嘴里嘟嘟囔囔着,突然“哈啾”一声吸了吸鼻子。
“我去给你找条毯子。”安格斯四下张望——应急灯昏暗的白光在黑暗的车库中像是一个个朦胧的幽灵,寒意从水流里顺着他的小腿肚虫子一样往上窸窸窣窣地爬。
“我们要在这里被困多久呢?”理查德缩了缩脖子,他不喜欢陷入冰冷的黑暗,也不喜欢安格斯离他超出一个手臂的距离。
“我不知道。”安格斯顺着车道涉水而行,他从那些仿佛陷入死亡沉默中的轿车旁走过,透过黑漆漆的车窗向车内吃力地探视着。
“阳要是回来了怎么办。”
“我希望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安格斯一边回答,一边抡起手里的铁棍——那是他之前寻找出口时在角落里发现的,碎裂的玻璃纷纷掉落,激起一连串令人寒悚的水花声。
* * *
“你喜欢吗?”
“当然,”他颇有兴致地笑道,“有什么不对吗?”
“不,”她也笑了起来,有阳光、泥土和花草的气息。他想,和那个人的气味有点像,又不尽相同。
“很多人说我的画很奇怪,让人难以理解。”她凝视自己的化作,无奈地耸耸肩,金色的长发从衣领旁滑落,如午后清风翻过干爽的书页。“有人能喜欢我的作品,我感觉很……开心。”
“别误会,我不是来泡妞的。”他直视她的眼睛。“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他操作手环,打开立体投影,翻找着一张张图片,“可以证明我并没有故意说谎来哄你开心。”
他将那张图片转向她,而她也在看见画的瞬间,会心一笑。
* * *
安格斯从破碎的车窗里拖出毛毯,回到理查德所待的那台车前,将毛毯递给正用双手揉着鼻子的SO。
“披上,保持体温。”安格斯搓着双手,站在冷水里让他开始感觉到有些鼻塞。理查德一手展开毯子,一手拍了拍车顶:“别傻站着,快上来。”
他们坐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顶,披着从另一个陌生人车里偷出来的毛毯依偎取暖。
“……我好像在什么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景。”
他们在沉默中静坐了很久,理查德突然喃喃自语。
“泰坦尼克?”安格斯对那部电影有很深的印象——因为理查德看电影的时候哭得像个三百斤的孩子,不仅当着他的面用完了一整盒抽纸,还将剩余的眼泪鼻涕全部抹在他最喜欢的那件衬衫上。
别告诉阳。理查德顶着通红的眼睛压着嗓音说。
好好好。他连连答应躲在自己身后回房间的理查德。我会把晚饭端你房间里来,并且保守一切秘密。话说伙计……现在可以松开我的衣服了吗——不然我怎么去给你拿毛巾和冰块?
“……斯,安格斯?嘿!”
耳边突然放大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嗯,什么?”安格斯回过神来。
“我说,不会有人出事吧,我是指……我们。”
“如果能够早点恢复电力,而且下水道的积水不倒灌的话……”这话刚说出口安格斯就后悔了,因为理查德望向他的眼神像是丛草半掩的洞穴,隐藏着躲躲闪闪的恐惧之色。这家伙吓着了。安格斯想。可是他也无法保证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获救,眼下涨水的势头很猛,已经快淹到后备箱了。
* * *
“这是你。”她露出颇为惊讶的神情,连连点着头。“一朵玫瑰——”
“初次见面时他送给我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饭。”
“噢,一定是次不错的约会,以至于让您忍不住向一位陌生人炫耀。”
安格斯被她的打趣给逗乐了,干脆在画板旁边选了一块地方席地坐了下来。
“近些年我也看了不少画作,你的画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望向波光粼粼的平静河面,岸边生长着大丛大丛的蒲公英和蝴蝶兰。“我在理奇的画中也感受到类似的东西。”她的视线在自己的画作上稍作停留,又慢慢落在他的身上。“虽然理奇没有跟我提起太多他的过去,但是我知道以前日子对他来说,是段坎坷难熬的经历……在遇见他之前,我是个痛失一切的混账小子——虽然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安格斯抿着嘴做了个手势,而她像是理解般地颔首微笑。“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废弃多年剧院里仍旧点亮的一束灯光,是遭遇洪水冲刷后的一块陆地,是攀爬在斑驳墙角的一株植物……默默无闻而又如此生机勃勃。他很有才华,我相信他的潜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坚信这一点。但是他没有遇见理解他画作的人——我看见你的画,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会喜欢他。”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像是在等待一个确定的答案。
“是的。”她字字清晰。“我很喜欢他的画。”
* * *
“……你后悔吗?”
“理奇?”安格斯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侧过头去。“你说什么,亲爱的?”
“我是说,”从背后传来带着点含糊的低沉声音以及令人心安的体温。“如果不是我提出要开车出去……”
“闭嘴!你是脑子进水了吗,说这种话做什么?”安格斯迅速打断了理查德话头,然后马上放缓了语气:“我也会做跟你一样的事情,如果是我先提出来的,你现在会后悔跟我出来吗?”
“如果阳回来了,却看不见我们——”
“他会来找我们的,就像我们会去找他一样。没有人会出事,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的——我保证!”他朝天花板狠狠地吐出一口气,疲惫地合上眼睛。“所以你那爱瞎想的小脑袋瓜不如思索一下,回去之后要看的电影清单。”
“……嗯。”
“理奇。”
“嗯?”
“我后悔没能早点拿到体检报告。”
安格斯淡淡地说:“我后悔没能在阳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留在他身边。”
“我后悔自己上一次草率和别人组SO的决定。”
安静的空气中,只有他的自言自语。
“我后悔没有追问你关于那只皮箱的事——”
“嘿!”理查德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你一直在意这个?”
安格斯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是啊。”
“那里面只是一些过去的画而已!”理查德冲着身后大嚷,无奈地挥了下手臂,“一些有关尤的,他是我过去的老师及监护人。”
“之前我问你的时候怎么不说?”
“因为我觉得你会瞎想,你是个对什么都想知道的控制狂。”理查德咬牙切齿地摇着头。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会让我瞎想的角色?”安格斯扬起一边眉毛,带着几分自嘲的口气。
“我年少时候有段日子的确有些……迷恋他。”理查德竖起一根手指,像是强调般地放大嗓音:“停下——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鬼表情,别以为我看不见你的脸就不了解你。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我也没有沉溺在过去里。不像你,哈!每次我们去酒吧和舞厅,那些吊在你身上的姑娘是怎么回事,你他妈是棵圣诞树吗?别试图打断我的话,还有上次在大街上亲吻你的有着漂亮绿眼睛的西班牙小哥,别他妈跟我说你们不认识。还有你组过SO的事情,你也从没详细跟我说过。我敢打赌,你最近三天肯定又和哪位帅哥美女搭讪过——”
理查德停顿了两秒,听见背后传来“啊,是呢”的回答后,顾自摊开双手翻了个白眼。“我就知道。”
“她还给了我电话——真巧,就放在这件上衣口袋里。”安格斯用手肘碰了碰理查德,理查德扭头看去,是一张名片。
“拿开,我不想看。”
“向井向日葵,自由画家,风格另类,不被理解。”
理查德拧起眉毛。
“什么?”
“我搭讪的女孩子,很漂亮。然而她是一位画家。我觉得你们有些相似,说不定可以聊聊,一起开个画展什么的。顺便一提,我给她看了你的一些画,她很喜欢。”
话音未落,安格斯感到食指与中指缝隙间一松,名片被抽走了。
“我会调查的。”理查德像花栗鼠一样撅着嘴。“我想好回去你陪我看的电影名单了。”
“你想好了。”
“嗯,首先就把《泰塔尼克》看一遍。”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意外?”
“你该好好学学怎么说话,在最危难时候,人家说的是‘赢得这张船票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而不是像你这样追问什么见鬼的皮箱!”
噗呲一声,安格斯笑出了声。
“好吧,平安夜那天被叫回去加班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闭嘴!你是脑子进水了吗,”理查德有些受不了地呲牙咧嘴,脸蛋在黑暗中红了一半,学着安格斯之前训斥他的样子。“说这种话做什么?”
骤然亮起的灯光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刺目的白光让他们不得不暂时用手臂遮住眼睛。几秒钟后,安格斯用力眨了眨眼,跳入没腰的水中。
“等等,我跟你一起!”理查德叫道,扶着安格斯伸过来的手臂,跟着跳了下来,冰冷的积水顿时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上帝!我们还真是倒霉得很哪,是吧?”
“又冷又落魄,就像是我们遇见的那天。”安格斯喃喃着。理查德还没反应过来,嘴唇就被一个炙热的吻住了,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异常温柔地说:
“那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相遇之一。”
=================================
(一段学生时代的小事)
“嘿!等等……我说你呢……等等!”
足足花费了半分钟,安格斯才意识到这个声音是在叫自己,刚从枪击现场逃离出来的他,还没有完全从那场混乱中缓过神来。他困惑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比自己矮了一大截的瘦小男生站在自己面前。
“你撞到我。”男孩生气地撅着嘴,身上那件沾满了颜料的白衬衣显得他深色的皮肤更黑了。“我的画笔掉了,在人群中踢来踢去,还被踩断了。”
安格斯不耐烦地掏出一张纸币:“拿着它,别来烦我。”
可是这个举动似乎惹怒了对方。“我知道你们这些贵族学校的家伙格外傲慢,自以为了不起,总是看不起人是吗?”
“嘿,离他远一点——”
一个红头发的女生突然冲过来将黑皮肤的男生一把推开。以至于男生打了个踉跄,这才没有失去平衡跌倒。
“滚开,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警告你,乡巴佬!!”女生地朝他竖起一个中指。
安格斯正了正领口,对眼前这场纠纷一句话没多说,转身就走。
黑皮肤的男孩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往地上啐了一口。
“见鬼的交换生!”他低声骂道。“别再让我遇见这个混蛋。”
【Triangle】戏剧性
-
*记错打卡时间,以为是今天24:00,结果看到是9月1日……
*不是大结局,大概还有一篇
======================================
安格斯进门后立刻发现气氛不太对头。
他怀着一颗警惕且忐忑的心,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背上,一边摘领带一边往里屋走去,室内自动调温器还开着,阳的围巾和理查德的写生用品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对于眼前这片诡异的寂静,他不由得打算先从这两人吵架的可能性去猜度。
盥洗室的门咯吱一声开了,理查德有些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从里面走出来,无意对上安格斯的视线时,明显地愣了一愣。
“你怎么才回来?”抢在对方开口之前,理查德有些冲动地两步上前狠狠拽住他:“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你统统都没接!”
“上午开会,所以把通讯接收器关掉了,怎么了?”对于理查德突如其来的火气,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个来找你的人!”理查德气得有些语无伦次,“那个自以为是的红头发女人!见鬼,也不知道她究竟跟阳灌了什么迷魂汤。她离开之后阳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把自己关进房间就是不肯出来。”
“等等,什么?”安格斯试图搞清状况,“红头发的女人?找我?”
“是!找你,一个红发的女人,还他妈的叫我转达信息给你!”
“慢点,你别急,是什么信息?”
“她说,”理查德的胸脯剧烈地起伏了两下,狠狠吐出一口恶气,“告诉安格斯,乔治希望他快点回家。”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阳锐锋本来打算置之不理,可是整整五分钟过去了,本应在楼下画画的那个家伙依然没去开门,而来人似乎也不打算放弃,执拗地发出一连串令人烦闷的敲击声。
阳锐锋撇着嘴角摇了摇头,不耐烦地丢下手中进行到一半的化学实验,打开卧室的房门,探头往外望了望,敲门声仍在继续着,没有人回应。他烦躁地咂了下嘴,拖着便鞋跑下楼梯,只见理查德闷头挥舞着画笔,脑袋上戴着阳才买的簇新耳机,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
阳冲着那个专注的背影无奈地翻了翻眼睛,也不去打搅,自己来到玄关,拉开门一个陌生女子赫然出现在视野中。她盯着阳,不待询问便主动地说:“我是来找安格斯的,我知道他住在这里。”
“他不在,您换个时间再来吧。”阳下意识地避开视线,就要关门。
女子急忙伸手拦住:“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您可以打电话问他。”
女子咬了咬嘴唇,很有些踌躇的样子,但是并没有松开挡在门上的手。
“你是他现在的SO吧?”她头一偏,装作无所谓地耸耸肩,如果阳的视线没有落在门口那块灰色脚垫上的话,大概一眼就能看透她这蹩脚的自我安慰。“我听别人说你们还在实验期。”
阳的肩膀僵住了,然后第一次抬头看了女人一眼。“你是谁。”
“啊,我叫薇琪,是安格斯之前的SO。”女子条件反射般地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让人联想到她富有张力的名字,她朝阳伸出手:“嗨,你好。”
阳立刻往后缩了一下,愣愣望着那只手,宛如提防着一条毒蛇。
“你没事吧?”薇琪试探性地问。
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他可能勉强自己笑了一下,也可能只是一脸木然地往屋内走去。在退回来的过程中他撞到了那个放着花盆的铁台架,一些易碎的东西掉了下来,稀里哗啦地损了个干净。
我又做错事了。他盯着那堆绿色的残渣想,一些陶瓷碎片溅进他的鞋里,令他每走一步都像在被细小的蛇噬咬着,警报声骤然在脑海中大肆作响。这就是了,我他妈活该被惩罚,作为拿了属于他人东西的报应。阳锐锋挪到沙发前跌坐,失控地大笑起来。
也许是花盆粉身碎骨的功劳,也许是对阳本身情绪的波动比较敏感,这场变故终于惊动了窗台前专心画画的人,理查德摘下耳机,视线在客厅里的两个人之间来回扫动,一脸的莫名其妙。
“——嗨,我是薇琪。”
“呃,理查德。”理查德一边小心翼翼观察着阳脸色,一边慢慢靠近那名不速之客。“你是阳的……呃……”他飞快扫了一眼面前这位鲜艳的打扮和半露的刺青,立刻将“朋友”及“同事”的猜测统统咽了回去。他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这是怎么回事?”
“呃……实际上,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薇琪做了个“天知道”的动作,理查德的出现似乎让她松了口气,“我只是跟他随便聊了两句。”
“随便聊了两句?”理查德拧起眉毛。“他就变成这样,你是巫婆吗?”
薇琪咬了咬嘴唇,翻了个白眼。“好吧,听着,我只是来找安格斯,仅此而已。”
“安格斯?谁?我们这里有这个人吗?他是做什么的?”
薇琪看上去有一瞬间的迷惑,她张了张嘴。“我以为……”她的眼珠子快速左右转动,在理查德和阳身上分别作短暂停留。“我以为你们三个是SO。如果你不认识安格斯,那么你是谁?”
“嘿,小姐,我在问你问题。”理查德嚣张地歪了歪脖子。
“安格斯——”女人突然大喊,“你在吗?我来了——”
“嘿!别在我家里吵闹!”
薇琪望着理查德眨眨眼睛,仰头笑出了声。理查德迅速瞟了眼躺在沙发上的人,而阳只是以之前的姿势靠在那里,就像草丛中一个熄火了几世纪的机器人。
“哇哦,我只是——”她做了几个不明所以但可以理解为轻视的手势,戴的那些戒指几乎要闪花理查德的眼。“没有想到,他会跟你们组SO。”
“我也没有想到。”理查德笑了笑,眼神像是一触即发的枪弹。“他会认识,你。”
薇琪眯眼回敬了个微笑:“帮我个忙,给安格斯带个口信。”
“祝你回家途中一路平安么?”理查德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薇琪笑了。
“所以这个他妈的乔治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理查德气急败坏地质问:“是你之前的SO吗,竟然叫你回去?”
安格斯没有说话,沉默的眼神让理查德十分不安,他捉紧金发男人的衣襟,感受到一双有力的手握住了自己紧绷的胳膊——安格斯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令他生畏的镇静——是一种强压愤怒后展现出的冷漠。
安格斯的目光从理查德脸上转移到旁边的房门上,他凝视着这扇紧闭的门足有好几秒,松开理查德被卡得隐隐作痛的胳膊,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了房子。
“嗨,是我。”出租车中的薇琪望着窗外的街道,手环上显示出视频电话的画面。
“情况怎样。”淡漠的陈述语气,画面中并没有出现人物,展现出的是一个薇琪没有见过的办公桌。
“没见到人,但是我见到了另外两个。”
“你当然没有碰上,因为整个上午他都在公司开会。”还是那个过分自信而容易令人不快的声音,薇琪坐在车上,很明显地皱了皱眉。
“你在哪儿?”她问。
“放大画面。”那个声音命令着。“现在,看见了吗?”
薇琪睁大眼睛,望着画面中那个相框,微微张大了嘴。
“你在安格斯上班的地方?”她的音调提高了。“我刚才见过这个人,他叫理查德。”
“理查德。”那个声音复述道。
“还有一个亚洲人,他看上去似乎有点不正常,我记得理查德叫他‘yang’。”
“yang。”设计公司里靠窗的某个工作桌前,一名金褐色头发的英俊男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曾在安格斯的通话记录里见过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家伙无关紧要,安格斯甚至都没在桌上放他的照片。你觉得安格斯会来找我们吗,乔治?”
“我觉得……”乔治伸手拿起桌上另一个放着风景照的相框,把相框背面的锁扣打开,接着慢慢露出一个训练得体的完美笑容。
“嗯?”薇琪挑眉——这么久了,她还是搞不懂这个男人。
这是一张不错的人像照:照片中黑发的男人站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杯咖啡,专注地凝望着窗外,透出一股平静的温柔神色。
打量着这张被摄影师小心隐藏着的作品,乔治胸有成竹地笑了。
“我觉得——”他说:“很有必要先找这个‘阳’谈一谈。”
【Triangle】不速之客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