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稿流出之三。前面线稿后面少量只有分镜。
#少女##恋爱#
*不好看!(不然我也不会发到e站
其实不是短篇但是我觉得这个e组快变成私组了(…)还可以把坂本和东扔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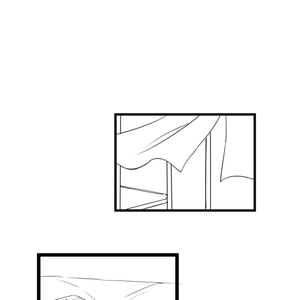
废稿流出之二。只有线稿。
#少女##恋爱#
*不好看!(不然我也不会发到e站
其实不是短篇但是我觉得这个e组快变成私组了(…)还可以把坂本和东扔过来(……)

废稿流出。
#少女##恋爱#
*不好看!(不然我也不会发到e站
其实不是短篇但是我觉得这个e组快变成私组了(…)还可以把坂本和东扔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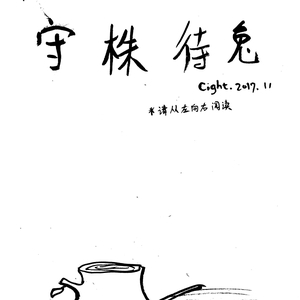
存个档然后删除源文件(……
给我一朵红玫瑰,我会为你唱最动听的歌。”
——《夜莺与玫瑰》
莎莉死了。她那心碎的母亲抱着她再不会睁开双眼的头颅,用毫无知觉的双脚走在龟裂的大地上,连续失去爱人与女儿的伤痛令她哭干了所有的眼泪,直到一头倒在坟地里再没能爬起来。
人们说,那位吉普赛母亲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她终究没被莎莉独自残留在人间,又能跟挚爱的家人在地下团聚了。
洁白的雪花盖住了莎莉一路滴落的血迹,它们像顽皮的孩子,嬉戏打闹着从大地上奔走而过,丝毫不在乎脚下所埋藏的事物。
我见过那个快乐的吉普赛孩子,莎莉——她被带来教会的时候我与她擦肩而过,女孩纯白无垢的眼睛眨了眨,盯着我手中厚厚的书,乌黑的眼睛像夜里的明星。半晌,她又抬起头,问:“您就是这里的神父先生吗?”
她像一只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夜莺鸟,蹦蹦跳跳地就想跑来我的跟前,不顾身后带她来的人紧紧扣住她的手不让女孩前行。我一时间有些意外地看着将小少女扭送来的魁梧大汉们,向他们投去不解的眼神。只有污蔑主的犯人才需要被这样粗暴对待,那位可爱的少女究竟犯了什么过错呢?
“她在水井里施了巫毒,神父先生。”
少女猛然变了脸色,她撇过头,稚嫩的声音里充满着愤怒:“我没有!我没有!我只是坐在井边,想要给自己梳头,那里的水很清澈,像镜子一样……我没有往里面施巫毒——”
“那我们先走了,神父先生。审判长还在等着我们将这罪恶的异教徒带过去,听说她跟某位异端有很深的血缘关系,所以还有话要问她呢。”
“所以,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根本没给莎莉辩解的余地,娇小的少女就被反剪了胳膊粗暴地拖走了,她的呼救声如针扎一般刺入我的脚心,而我却只是干站在原地,目送着她被拖进黑暗之中。
我无能为力,她是主所认定的罪人,身为神的奴仆,我没法向被判定为罪恶的她伸出援手,神的圣典不容许沾染一丝灰尘,他教导我们罪恶会像刚发的新芽一样飞速成长,直到将我们自身也染上为止,所以我不能去拯救她——主会给予她应得的惩罚。
哪怕她只是一个孩子。
我不会去想象她将遇到什么,异端审问的刑官们可不会管她的年龄,任何残酷的刑罚都有可能降临在她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都在飘着雪花,它们悄无声息地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我坐在忏悔室里,炉火将空旷的大厅烤得暖烘烘的,想聆听神的话语的人们都乐得前来取暖,唱诗班的孩子们赞美着主的功德,而我将主的福音传达给受难的人们,为他们打开光明的前路。时间总是要向前行走,过去的只能被掩埋在烟尘之中。
突如其来的,这份短暂的祥和被一阵骚动打断,仿佛有人在门口大声嚷嚷着什么,只听见响亮的鞭打声,便没有了踪迹。我连忙举起手示意民众不要慌乱,打算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右手紧紧将圣经按在心口,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教堂的门。
“诺曼神父,您在这儿。”正在和什么人说着话的主教看见了我,冲我招了招手。我便不明所以地跟了过去,只看见一个被拷打得不成模样的男人跪在殿前,过于严重的伤和脱水令他连膝盖都要无法支撑,我所不熟悉的味道——铁锈一般的血腥味弥漫着我的鼻腔,而高大的行刑人们仍在用恐吓一般的话语逼迫着他。
“主教,这是……?”
“行刑的时间快到了,诺曼神父。这个男人是死囚,被举证他施展异教的黑魔法,似乎还跟一个异教女人生下了一个小女巫。”主教点点头,转身向火刑场走去,“走吧,我知道你对这种场合还不大适应,但那是我们的职责。主最终会定夺他的罪孽。”
我不由得再转头看了眼那位异教徒,他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眼睛里充满着惊恐和疑惧,在目光触及刚刚赶到的我时,他猛然伸出手,拽住了我的袍子下摆,这个突然的举动令我一时间来不及躲开,本能驱使我拼命抓着布料向上提,想要将袍子从他的手中拔出来。事情发生得太快,连刑官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我只是挣扎着,而他费力地张开口,用几乎破碎得无法听清的沙哑声音喊道:“神父……神父……救救我的女儿莎莉……放了她,她是无辜的……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
莎莉,莎莉,这个熟悉的音节仿佛在我的脑内炸开来,小女孩的笑颜从我的眼前一晃而过。是她吗?那个吉普赛女孩,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
我正要开口说什么,刑官可不给他多余口舌的时间。男人的手被用力踩在了地上,伴随着他痛苦的低吟。我的袍子从他的束缚里解脱了出来,主教连忙示意我跟他离开。
“真是疯狂的异教徒。”他说,鞋子急促地踏在砖地上发出清亮的响声,“安德烈・提恰卡,在房间里有大量黑魔法研究痕迹,他的女儿也是个小杂种——一家子都是撒旦的奴仆,明明是他亲生的孩子,却死活一口咬定不认识这个人也没见过他,用什么刑都没用,甚至那个让很多异教徒都痛苦求饶的针刑也没有什么用……”
“是在说那个叫莎莉的小女孩吗?”我问道。
主教摆了摆手,不耐烦道:“随便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怎样用刑都一口否认自己不是女巫,也不认识安德烈。总之,异端是一定要被处死的。”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宗教的死刑,我看见那个男人在火焰灼热的温度里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身体不自主地扭曲着,火焰舔舐着皮肤发出毕毕剥剥的爆裂声,焦臭的糊味和柴草的熏味夹杂在一起,流入围观死刑的欢乐人群里。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撇开了眼睛,不忍心再看下去,而疯狂地叫喊着“再来一个”的人民令我感到了茫然。
这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神吗?是正确的吗?我在心中暗暗问着自己。明明是再熟悉不过的教堂,我却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而现在,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却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那对苦命母女不起眼的坟头前。他们是异教徒,更是罪人,所以没人为他们立碑。我想要在胸前画上十字,却又感到了无比的讽刺。
这位远道而来、对自己丈夫和女儿的下落毫不知情的夫人也曾来找过我,她来到我的忏悔室,跟我讲述着她与家人的幸福的故事,甜蜜与家人失踪的焦急在她脸上交替浮现。她是一个漂亮的吉普赛女人,却能像任何一位忠诚的教徒那样熟练地背诵圣经的段落,可面对她期待的脸庞,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残酷的真相。
直到现在,我听到她的噩耗,一切已经晚了。
白雪一如既往地翩翩而至,将母女的尸体掩盖在大学之下。也许很快,没有人会记得这场悲剧曾经发生过。
教堂的钟声回荡在城镇上空。我无言地看着脚下的路,却不知它究竟通往何方。

作品不够作业来凑………………我专业不是漫画,这个作业的课题是品牌推广,所以它其实是个广告………………(笑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