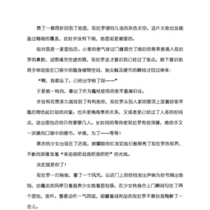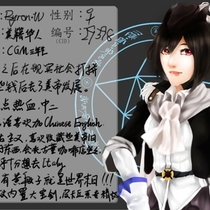企划内时间均可报名
===============
大家经过了四年的学习终于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魔法师
磕磕绊绊中魔法界的建设也终于有了起色
但这看似平静的日常下却酝酿着狂澜
——
谨遵着传承千年的教诲教育拥有神力之人
然而拥有神力之人突然减少
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恶魔的诱惑
——
企划群:245552006
官PO茨格姆魔法学校http://weibo.com/u/5271268752
佛罗里达州冬日的街道上,一个身穿纯白长羽绒服的男人站在路边搓着手,不时地对手上哈一口气,并且左右张望着,似乎是在等人。
来来往往的行人偶尔会多看上他几眼,不仅因为他长得确实挺好看的,还因为他的头顶有一双狐狸耳朵。
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女大大咧咧地跑去打招呼:“嘿!我是见到了传说中的兽人吗?”
男人笑起来,他伸出手指戳了戳自己头顶上的狐耳——狐耳纹丝不动。
“只是一点小小的癖好,小姐。”他眨了眨眼睛,比了一个嘘声的手势。
少女露出“我懂”的眼神。
在少女离开之后,男人走回了街边店铺的阴影里,轻轻地抖了抖他的狐耳。
“呼……外面的冬天真冷。”
一阵很轻的脚步声从背后传来,一顶厚厚的绒线帽被扣到了他的头上,他瞬间哭丧下脸来:“我讨厌帽子……”如果不是因为怕冷,又需要合适的长衣服挡住尾巴,他连羽绒服都不想穿。
身后的人没有理会他的抗议,帽子被往下拉了拉,套住了他的整个后脑勺。
海因切转过身,向着后面一言不发的好看黑发男人张开双手:“猫,你看!狐狸穿着鸭子的羽毛!”
被称为“猫”的裹在黑色羽绒服里的男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一点没搞懂这个冷笑话的笑点在哪,倒是海因切自己突然捧腹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勾着猫的脖子说着:“你真可爱~”
猫扭过头去,从海因切的角度正好能看到他侧脸微微地发红。于是海因切坏心眼地把自己的脸贴了过去。
他们之所以会在学校外,是因为要调查三天前佛罗里达海岸出现的一次小型海啸。
虽然那场海啸只造成了大量人受到惊吓和小部分人受伤,不过据那位外表看起来只有十几岁、实际年龄却是俩魔法生物加起来还要翻好几倍的茨格姆校长瑞尔斯所说,这场海啸很可能是非自然因素引起的,考虑到最近普通世界魔力变强,他认为还是找人去调查一下比较好。
从教会逃脱出来之后无所事事的某狐狸和某猫就接下了这个委托,并被告诫了在普通世界期间要好好隐藏自己以免被普通人或教会注意到。
说起来,这场教会和魔法界之间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年,如果把教会抓捕魔法界人士的时间都算上的话时间更久。如今想到教会他们俩都有点不爽——谁也不会喜欢一个自己莫名其妙被强制关押过的地方是吧。
刚才海因切和猫刷脸向当地居民们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奇闻异事之后,又分头勘察了一下这个滨海小镇,但是都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只好直接前往发生海啸的那片海滩。
猫回想起刚才突然贴过来的脸颊,有些赌气似的故意不去看开心地拉着他走在沙滩上的狐狸。
他才没有在害羞呢。
以前也不是……没有亲过,贴个脸蹭两下什么的,才没什么好害羞的!
他努力把注意力放向四周而不是海因切牵着他的手。前几日的海啸看起来给镇上的居民和旅客带来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往日摩肩接踵的热门景区今天只有寥寥几人,不过这显然方便了他们的调查。
这片沙滩若要说有什么奇怪之处,那就是它从被一条从后方陆地一直延伸到海里的凸起的长条形岩丘一截为二。这条岩丘越是远离陆地的部分越高,就好像一条通体漆黑的龙从陆地深处向着海面探出头,直到尽头处突兀地扎向海里。
狐狸松开了他的手,蹲下仔细地摸了摸露在沙子外面的岩石:“正如刚才看的那本旅游杂志上所说,这条岩石带保持这个状态应该已经很久了,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那么,和这次的事情难道没有关系?
猫膝盖微弯,把整个身体向前弓了起来,腿部猛地发力跃上了岩丘,然后转身看向狐狸。
“也是,都走到这里了,不如再往前去看看。”海因切说完,站在原地笑着向猫伸出双手,“我的弹跳力可不如你啊。”
猫额头上蹦出一个十字,僵持了几秒,还是伸手把这家伙拉了上来。
他们沿着长长的岩丘走向大海,黄色的细沙逐渐从视野中退去,蓝色的碧波从天空向着岸边轻轻地回荡,仿佛将天海连成一片。猫吸了吸鼻子,他们的周围已经满溢着海的味道。
“从岸边看和从海底看真是完全不一样啊。”走到岩石带的尽头,海因切眺望着海平面感慨道,“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咦。”
猫站在岩丘的边缘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看岩丘的侧面,海因切走过去小心地半蹲下向下望去——刚才爬上来的时候让猫拉他一把其实只是因为想偷懒来着,不过平衡感方面他确实比不上能在树枝上穿行的猫,要小心一点才行。
这一部分岩石塌陷了不少地方,乍看上去十分紊乱,不过把脑袋再探出去一点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在残缺的岩盖之后显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洞口大小目测正好能让他们俩蜷着身子钻进去。
“岩丘里面居然是空的。”狐狸惊讶地挑了挑眉毛,“如何?看得清里面吗?”
猫皱眉,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那个岩洞。
“嗯嗯,那就一起进去看看吧。”
洞口看起来离岩丘的顶部不远,但是因为比岩丘的最外侧往里缩了一点,实际要爬下去也费了一番力气——这是海因切的情况,猫则是单手勾着岩壁一跃而下就钻进去了。
一进洞口,海因切明显感觉到周围的魔力浓度变强了。他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前几日的海啸打湿了洞口,不过大多数的地方都已经快干了,看来即使是涨潮的时候水也不会漫到这里,但是,有一小块地方却留下了密密麻麻深色的丝状水迹,从被海水拍打着的岩丘底端一直延伸到洞口里面。
先进洞的猫凭借着夜视能力稍微往里走了一点,又折返回来。
海因切问他:“里面有积水吗?”
猫摇头,并投以了询问的目光,海因切把洞口的水迹指给他看。
“那可能是有什么海里的东西被吸引到洞里来了。”
他们俩都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水迹,也想不出到底会是什么东西留下的。
海因切握着猫的手,跟着他放轻脚步慢慢地往岩穴深处走去。因为眼前一片漆黑,听觉和触觉变得更加敏锐,越是往里走,周围的地形就越开阔,至少他们现在能直起身体行走了。耳边一开始只有洞穴外海浪击打在岩壁上的声音,慢慢地,能听到从黑暗的前方传来了戚戚促促的声音。
猫突然停下脚步,握了握他的手,他猜想可能前方会有什么,于是回握了一下表示没问题。
他们转过一个拐角。
几乎是一瞬间,戚戚促促的声音骤然变响,伴随着阵风扑面而来,海因切反应迅速转身抬腿,感觉脚踢开了什么轻飘飘的东西,然而有更多的响声围绕了过来。
之前保持安静和黑暗是生怕打草惊蛇,如今既然已经被发现,海因切也就索性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擦亮了一两根,往周围一探,然后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和猫身处在一个上下前后都是石壁的通道内——本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周围的石壁上布满了一种黑色丝带状的游动生物,满得连石壁都看不见了。火焰很快熄灭,他又点燃两根,试探着去烧那些生物。那些丝带全然不躲避,有几根被烧断了就轻飘飘地落到地上,感觉像是死了。
猫蹲下身看了看,却突然发现靠近墙的地上有一块凹陷。那块地方刚才被黑色丝带所覆盖着,现在它们在空气里游动了起来,这个凹陷才得以被发现。海因切看到猫突然呲着牙警觉起来,全身绷紧似乎随时准备做出攻击,出于好奇又点燃一根火柴并举高了一点,也凑过来想看看地上有什么。
那是一个爪印,一个长宽皆有半米左右的爪印。
往前一段距离的另一处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爪印,形状和刚才那个成轴对称,看起来是左爪和右爪的关系。
海因切严肃起来,伸手比划了一下两个脚印间的距离。
……之前曾经在这里待过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啊……
考虑到爪印的主人如果此刻回来他们并没有能全身而退的把握,他们决定先回去把这个发现告诉瑞尔斯,临走前猫用指甲勾走了一条游动的黑丝带,并为了防止有人类误入而用石头堵上了洞口。
瑞尔斯坐在办公桌后,双手叠成塔状深沉地看着那条黑丝带。几乎是在海因切和猫走进校长室的同时,那丝带瞬间把自己抖擞精神了从猫的手指尖飘下来,向着瑞尔斯飘去。
海因切开心地接管了猫空闲下来的手。
“从你们的调查判断……那条岩丘下原本沉睡着体型庞大的魔法生物,由于最近外界魔力浓度上升而苏醒过来,潜入海中引起了海啸。大致应该就是如此吧……”他把黑丝带打了个蝴蝶结,打结之后这个小东西似乎失去了判断方向的能力,开始在房间里乱飘,“这个黑丝带是一种靠吸食魔力生存的魔法生物,没有眼睛,能凭借触觉判断出魔力的强弱,喜欢往魔力强的地方飘,因为需要的魔力量非常少,两三条基本没什么危害,就是烦人了点,打个结就好使了。我记得它们不是群居动物来着,会大量聚集在那个山洞里的原因应该就是之前住在那里的大型魔法生物了。”
“那家伙竟然没被这群东西吸干吗?”回想起洞中那多到恐怖的数量,海因切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大家伙醒来根本不是由于什么魔力浓度上升,而是因为不堪“蚊子”之扰。
“它们会判断宿主的情况,如果感觉到宿主不是绝佳状态了就会停止吸魔,甚至原先的宿主身体情况变糟的话,它还可能主动离开去寻找新宿主,所以也会有人用它来判断别人的身体情况哦!”
也就是说……被那么多黑丝带同时吸魔还处于“绝佳状态”的某不知名也没有脸的巨大魔法生物,从里到外都非常厉害啊。
也许是传说级别的魔法生物也说不定?
=====
字数3478。
时间是校长被主教解开魔力封印之前,如果有BUG的话求指出/_\
7000字
http://music.163.com/#/song?id=25918422
推荐,推荐!有条件务必听着食用啊!
最后蹭上了建立防御魔法阵的活动……校长!校长你看看我!对不起我午睡过头了【痛哭流涕】,熬夜到现在赶完能不能算上啊!!!!!!!
<凶者当屠 – 渔家傲>
飞机到达时刚过凌晨一点,如果不是这些年张青的样子没发生什么变化,单凭气质和背影,拙仓几乎要认不出她来。
他偷偷瞒过家人,向学校递假,通过法阵来到中国的据点,借了辆车,驱车赶往机场,在接机口不停张望着,直到张青走来拍上他的肩,才发现对方。
她变得沉郁且漠然,少时眉目间的肆意和张扬都不见了,笑容几乎没有,声音干涩,双眼直直望着前方或地面,如果没有什么事阻拦她,仿佛就要这么一直走下去。从正面看去她依然挺拔,顽强的像杆枪,宁折不屈,再难也要硬撑着。背影里却满是疲惫,恍恍惚惚的,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一般。
拙仓驱车赶向她说的地址,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简陋,向着远离城市的村落驶去。张青一路都很安静,拙仓通过后视镜看去,发现她侧卧在车后座上睡着了,面朝前面,双臂抱在一起,微微倾身趴着,像是不敢压到脊背,小心翼翼又沉沉的睡去,睡着睡着,眼角无声的落下泪来。拙仓看着,心里像是窝了块棉花,苦闷的直想大叫。
“北国夜无雪,隐隐惧相逢。”张青睁开眼睛。
“这里是南国。”
“我又梦见阿爷了。”
“小时候听你说过几次。”
“那时候还好,和你们吵吵闹闹,很多不想回忆的事就想不起来了。”张青说,一旦有了交流对象,她的语言功能好像恢复了很多,又或许这些话她一个人反复思索了许多遍,早就烂熟于心,“这些年一个人在异乡生活,心里空荡荡的,格外多梦。”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好的坏的,开心的悲伤的,压在心底却未曾忘记的,统统化作求不得放不下,在夜里汹涌入梦。雨水和蚊香燃烧的味道一直不曾散去,催着她惊醒,又催着她沉入更深的梦境。
“天要亮了。”她看着窗外的天空,东面隐隐泛白。楼房已经全然看不到了,轿车驶过一个石桥,远处山峦间云雾朦朦,缓缓变化移动着,像有巨兽沉眠于此,缓缓呼吸,又像龙翻飞着拢在山川上,周遭是它的蜃气。
山脚下是一片大湖,泱泱无壅,直到石桥底下。有渔家早起,几个墨点似的船缀在上面,浅滩处种着小片水稻,人寂寂水汤汤,似一幅画。
唯一破坏气氛的就是他们座下铁车,跟它载的人一样,往哪站都突兀,和周遭格格不入。
张青又睡了过去,拙仓看着不痛快的天色: “是个阴天啊。”
车轮碾过积水,停在村落前,白墙灰瓦,窄巷青阶,偶尔有低洼处的积水深到脚腕,居民懒得修补,就用石块和砖头临时搭出一条路。围墙低矮又简陋,比起防卫,更多是用来标明领地。
拙仓喊醒张青,她把枪提在手上,领着他穿过村落,向更深处走去,民居开始稀疏,绿色渐多,竹林间的土路宽阔平坦,比两侧微微高出一块,路尽头是座大院,张青停下脚步,遥遥看着它。
“几点了?”她问。
“五点了。”拙仓说。
“过了多久?”
“……大概四个小时?”
“十四年啊……”拙仓发现张青在喃喃自语,“十四年。”
她伸出手去敲门,木门却被敲开了一丝缝隙。她愣愣的看着,收回手来,又伸出去,手掌贴着门板,不敢用力,从未害怕过什么的女性此刻惴惴不安的咬着嘴唇。
“近乡情怯?”拙仓问。
张青没有回答,用力一推,木门拉长调子“吱——呀——”作响着打开了,她走进去,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打量。院落里干干净净的,正中间摆着个一人高的香炉,有几片被夜风吹落的树叶落在地上,她抖开裹枪的粗布,枪尖撵着树叶一挑,托在空中,舒展身体送出枪去,正中树叶中心,啪的把它打成两折。
张青笑了笑,眼神里染上欢愉,那股像毒龙般暴烈的力量被收起,她无声的舞起枪来,血液和身体渐渐变热,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腾出一丝不同于水汽的雾。
锋走白虹,杆出惊鸿。
“出枪甚长,且有虚实,有奇正……”
气烈如鸣,似风从虎。
“其进锐,其退速,其势险,其节短……”
雾随枪走,如云从龙。
“不动如山,动如雷震……”
张青收枪而立,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好枪法,我要是能有先生一半资质,就……”男人忽然不说话了,他死死盯着张青。张青回望过去,看着他那头和张炎一样火红的头发,无声的笑了。
“阿顷,谁啊?”两鬓斑白的老人披着外套从正卧出来,天刚亮,露水对年纪大的人来说还是重了点。
张顷结结巴巴说不全话。
“你……你……你……”老人的眼睛渐渐瞪圆,抬起手来指着张青,你你你了半天,转身冲回了屋里,一阵翻箱倒柜和妻子抱怨的声音,然后拎着鸡毛掸子又冲出来,眼眶发红,快步向她走来,举手就抽。
“你这个……!!!”
鸡毛掸子伴着怒吼落在张青背上,她眨了下眼,噗通一下跪在地上,把张老爹吓得倒退一步。
“你……干什……怎么了?”张义不是一点半点发懵,这个幺女小时候“不跪天不跪地不跪父母,我谁都不跪!”的狂言他还记得一清二楚,虽然现在自己老了,但也不至于糊涂到以为张青会痛改前非。
张青没有回话,脸朝地面,脱力般直直向前倒去,一滩血迹在背上缓缓洇开。
张青记得,自己父亲以前很上心查夜这件事,每晚睡前都会亲自把各个院落检查一遍,门是不是落了锁,锁是不是锁好了,起夜时再顺路检查一遍。
那个时候她以为,这多半是防着怕挨打而逃出家门的自己,直到今天她推开那扇未落锁的门才明白,父亲只是借着落锁偷偷观察自己回来没有,如果有,他是绝不吝开门,然后给自己留下个硬梆梆的背影的。
可是没有,一次又一次,张青从没有回来过,她和父亲共有的倔犟、别扭,像是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拙仓说近乡情怯,其实并不是,这个感情早在漫长的空中旅行里磨灭了 ,剩下的只有急切归家的心。
只是发现门没落锁,让张青很惶恐。
这座大院是不是换人了?是不是空了?如果不是,为什么没有锁门?落锁的那个人……死了吗?
万幸的是没有。
是真的没有锁上吗?是为我留的门吗 ?
是不是锁链太长,再推一下就会绊住了?
万幸的是不是。
她少见的沉沉睡去,无梦侵袭。
张顷招呼拙仓一起吃早饭,炸酱面、豆腐卤和馒头,拙仓实在不知道面条和馒头要怎么搭配,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豆腐卤和面条简直齁死个人,馒头软的一捏就扁,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还挺好吃的。
比、比赤拟做的好吃……
“阿青多受你照顾了。”张顷真心实意的感谢,“她行事鲁莽,要是说话冲撞了也别往心里去,替她赔罪。”
“诶没事,都习惯了。”拙仓心想言语冲撞算什么,当初她直接拿着枪来扎我我都没说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照顾的,很多年不联系了,前几天才又联系上。”
“那你知道她背上那伤怎么来的吗……?”张顷把原本她这些年都在干什么憋了回去。
“不知道,她没说。”八成是教会打的。
张顷叹息,对不能教训欺负自己妹妹的人感到扼腕。
“伯父不吃早饭吗?”拙仓把话题移开。
“他拿了两个馒头去阿青门口守着了。”张顷有点好笑,“自从阿青走得久了,爸晚上都不敢锁门,怕她回来进不了家。每天盼着她回来,真盼回来了也不知道好好说话,竟然一鸡毛掸子抽过去,还当她是小时候的屁孩儿呢!”
“……父女俩一样的。”拙仓也笑起来。
陌生的天……地板。
张青睁开眼,自己正趴在床上,鼻子发酸,额头也疼,估计是晕倒时脸着地了,背上凉嗖嗖的敷了药。她扭了扭脖子,看到守在床边的女人。
“阿妈。”张青轻轻唤了声。
“嗯?嗯……!”迷迷糊糊打着瞌睡要从椅子上跌落的女性猛睁开眼,惊喜的摸摸阿青的脸,“你醒啦,饿不饿?喝水不?”
“嗯。”她吭了声,女人匆匆推开门,一声“ni——”憋在嗓子里,张青看过去,一截深棕色的拐棍悄悄缩到门后。
不方便吃面,她就啃了两个馒头,并对牛奶表示了厌恶。
“刚下的奶。”阿妈端过来,张青往后缩了缩,干脆扭头用后脑勺朝着女人。
“喝了要吐。”她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
“这娃……一点没变。”女人嗔怪的给她换来温水。
“诺言呢?”张青问 。
“在城里呢,你哥给他打过电话了。”
“老头子呢?”
“咳。”张义应景的推门进来。
“门后躲着呢。”女人挤眉弄眼的压低声音,指了老头一下,末了笑笑,“你爸老了,身子不如以前硬朗,你可别再气他。”
“我知道。”
女人退了出去,阿青想老爹真是老了,人老了就容易心软,放到以前,他是断不会来看自己的。 两人聊了一会,她坐起来,缓了缓,穿上外衣站起。
“你去哪?”老头有点紧张。
“去看看爷爷。”张青说。
老头沉默了会,背着手走出房间。
拙仓兜兜转转,终于在竹林深处找到了张青,她坐在长椅上,亭子中间放着个火锅,用木炭烤着 ,菜和肉在一边放着。
“你弄得?”
“张顷。”
“给我准备的?”
“别人,你想吃也行。”
“不了,刚吃过。”拙仓说,“我这就打算回学校了,有些话……想和你说。”
张青没有说话,看着亭外。
“赤拟的侄女入学了,今年刚13岁,看到她们就好像看到当初的自己。”拙仓自顾自说着,他们很久没有见面,见面后也没有一句寒暄,阿青沉默又冷淡,既不问他过得怎么样,也绝口不提自己现状,但拙仓知道她肯定不好过。
“真诚也一岁半了。”他说,“魔法界扩大了不少,人手紧缺,教会蠢蠢欲动……有空可以回去看看。”
“嗯。”张青木然的应了声,没有更多回答。她坐在亭子边缘的长椅上凝望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拙仓忍不住顺着她的视线去看,入目一片青翠,除了竹林还是竹林,越往深处越是苍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却依旧分不出张青到底在看什么,他想说阿青你很少笑了,从我们见面开始都是一副郁郁的表情,是只有这段时间这样,还是自分别后都这样了?
“……张青。”他忍不住开口。
“嗯。”
“我走了。”
“嗯。”
拙仓起身往前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有消息说余弦还在魔法界,不过不一定准。”拙仓看着她的背影,“这些年我都有帮你打听她的下落,我想你早晚会回来的,不是觉得自己多了解你,而是因为相信天意。”
人生在世,多艰多舛。乱世难为,天意……如刀。
阿青石像一样沉默着。
他叹了口气,撑开伞离去。
“枪靶。”忽然有人从背后叫他,拙仓回过头去,看到阿青向他缓缓露出个笑容,没了少时的嚣张桀骜,这笑容看起来安静又疲惫。
“我很好,你放心。”她说,“过段时间我就回学校看看。”
“走吧,我送你出去。”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两人走在碎石板铺成的小路上,身边绿色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白墙青瓦,和夹杂其中的狭窄巷道。
“你我有没有推心置腹谈过话?”
“没有。”
“哦。”张青哼了声,“回学校后请你喝酒。”
“喝多了赤拟要骂我的。”
“你不喝我要打你的。”
“你现在打不过我了。”
“你确定?你半生安安稳稳呆在学校。”张青停下脚步,似笑非笑的凝视着他,“可知我半生颠沛流离,经历些什么?”
完了。拙仓心想。戳她痛脚了。
他仔细打量着张青,半晌还是摇摇头。
“你不用骗我 。”张青一甩衣袍,踏步向前走去,披在肩上的单衣随风鼓动一下,“我记得我离校前拉着你喝醉过,想必酒后失持,同你说了什么,不然你也不会十几年如一日,为了一个不知道回不回来的人打听一个失踪的人。”
你怎么不担心酒后失持和我做了什么。拙仓在心里深深的吐槽。
“我还有事托你。”
“说。”
“如果哪天阿炎发疯,你要拦住她。”
“她是教会的人。”
“她会听你的。”张青说,“不听就想办法让她听,什么办法都行。”
“弄死ye……”
“你敢。”张青眼角忽然一翘,冷如刀锋般。
“我开个玩笑。”
“别看她好像很好相与,发起疯来比我也有过之无不及。”
“张家人都这样。”拙仓回答,“学校见。”
“学校见。”
她回到亭子时,长发的男人正坐在火锅边涮肉,刘海上粉红色的挑染异常显眼,头发在颈后扎出个细细长长的小辫子。
“说了是给你吃的吗?”张青在诺言对面坐下。
“那还能给谁?”男人说,“不是我帮你看着锅,汤早沸了。”
“多谢你喽?”
“不客气。”诺言自然的接受道谢,“你找我什么事?”
“原本有些话想说的。”张青看向外面,“现在忽然不想说了。”
诺言无所谓的摊下手,毫无表示的埋头苦吃。
阿爷就葬在竹林里,她等诺言吃完,一起过去,在坟前洒上一杯酒,点上香,无言的看着石碑。
“我记得你小时候很活泼。”诺言说,“现在话这么少了。”
“人总是会变得,我年岁已经不小了,活泼不能再用来形容我。”
“外貌几乎没变。”诺言打量她,“性子倒越来越像老头子期待的那种人了。”
“你不期待吗。”
“不,很无趣。”
“你觉得什么有趣?”
“你就很有趣。”
“……”
“如果想再有趣一点……”诺言眯起眼来,“我该让你背道而驰,绝不让你成为老头期待的那种人。”
“我是沙包,任你们揉圆搓扁 ?”
“不,只是什么都在一个死人的掌控中发展,这种感觉很糟糕。他说你是奇迹,可我觉得你该是腐朽的奇迹。”
“神经病……那又是什么东西。”张青忍不住骂。
“腐朽的奇迹,”诺言眼皮跳了下,“不就是人类吗。”
张青转身往家走去,小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
“那个男人,”诺言问,“是你男朋友?”
“……不是,是我同事。”张青脱力,“拙仓都结婚生孩子了。”
一直漂泊的旅人仿佛就这么在家乡安居下来,一住半年,年关将至时张炎也赶回家里,身边跟着稗田墨。
“你女朋友?”张青认出了这个女孩。
“小跟班。”张炎耸耸肩,“非要跟着监视我。”
稗田一瞪她,她就嘻嘻哈哈的岔开话题,把一本诗经拍在张青怀里,“来,稗田给你的见面礼。”
“我的诗经……上次是落在你哪了!”稗田跳起来去抢,被张炎拦在怀里拖进屋。
“哎呀……我再给你买一本嘛……实在不……我给你手抄一本?”
声音渐渐小时了,张青摊开书,很快找到了折角的那一页,红色的水笔特地标记出来一行。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新年那天罕见的下了点小雪,张炎记得上次这块地界落雪,还是14年的事。
十五一过,张青收拾好自己行李,再去看了看阿爷,敲开老爹的门。
“可以不走吗。”她在门口就听见老人的声音,低低的,带点恳求,让人心里发颤。
她不敢答应,又不敢不答应如此低声下气的父亲。
原来我也在老去啊。她想。心越来越软。
“你不说 ……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老头激动的用拐棍戳了下地面,“无非就是些和诺言差不多的事!”
张义摇摇头,又摇摇头,有些不知所措,“你从小就亲近你爷爷。”他声音发苦,“我看着他把你往不归路上领,心里急的要命。你阿爷要一个完美的作品,你就把自己天生的狂妄和资质当筹码给他,交换来力量,我看你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异常……剑利易折,枪硬易断,他把那些力量交给你,就是在给你魔鬼。
“有谁会期待自己孩子变得像把武器一样?你要那么强做什么?我不能保护你吗?我是你父亲啊!”
“可你不会永远是一个能保护女儿的父亲。”诺言握住张青抓着门把的手,把她拉过来,自己上前,直视自己名义上的哥哥,“有一天你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垂垂老矣瘦弱无力的人,她只是更早的预见了这一天。”
老头闭上眼,有些绝望,“那这次走……还回来吗?”
“……不知道。”张青小声说,比起半年前刚回家的时候,她更像一个人了。
“如果再回来。”老头说,“……就别搀和那些伤身的事了。”
张青心里发慌,拽着诺言掉头就跑,像小时候那样躲开老人的视线,来不及给一句回答。
“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阿爷并不爱我。”张青在村口停下,拙仓的车停在附近,她踩了踩积雪,低声说,“尤其是这些年,手上没有事干的时候就止不住的琢磨很多事,常常觉得阿爷对我像是一个工匠对最完美作品的喜爱和慰藉。可是又想起他握着我和大家的手,说血浓于水,你们有骨肉相连。”
“你觉得阿爷是坏人吗?”她问。
“……无所谓。”诺言替她撩了撩鬓边落下头发。
“事实到底怎样,谁都不知道。”男人说,“他已经离开了,有再多故事,再多心思,再多遗憾,都无济于事,连世界都不会在意,我们又何必计较?你就权当他是对你好了。”
张青盯着他的眼睛,两人无声的对视着。
拙仓摁了两下喇叭,诺言摆摆手转身。
“诺言。”她喊了声,男人转过身。
“你一直都觉得自己聪明,”她说,“猜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啊?”
“?”男人鄙视,“没头没脑这谁能猜到。”
张青突然扶着他肩膀亲上去,像豁出去一样,一直注视着这边的拙仓受到了成吨惊吓,一巴掌拍在喇叭上,笛声长鸣,或远或近的狗此起彼伏狂叫起来,诺言紧紧抓住阿青,在混乱至极的气氛中加深了这个吻。
他本以为这是对方心血来潮的恶劣玩笑,此番举动定会让脸皮薄的张青激烈反抗。
然而没有,他顿了下,后撤一步,拉开距离。
“啧……没意思。”诺言皱了皱眉。
“欠你的。”张青好像很嫌弃的擦了擦嘴,弯腰握了个雪球,啪的丢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吵死啦!!!!”
“走咯。”她小跑过去,突然又握了个雪球,朝着诺言丢过去,准准丢在衣领和脖子间。
诺言俯身让雪块滑落,匆匆清理干净衣领,抬头看到她冲自己笑了笑,钻进了车里。
回到魔法界后张青更加清闲下来,不需要上课也不需要授课,她用自己漫长的闲暇时间在林子边缘建了座木屋,和护林员比邻而居。然后找了个图书馆保安的工作,成日泡在图书馆里发呆,看书。
她开始学画画,最开始线条乱七八糟涂满一纸,后来渐渐能看出人形,最后不仔细讲究也算说得过去。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就趴桌子睡觉,带着折叠床来在角落躺着睡觉晒太阳,别人不找她,她也不找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倒是让耐心好了不少。
最近一次被人喊出去,是去建立岛上的防御法阵,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她远远看着奥斯德念了很久咒语,又听说koi酷炫狂霸拽的特殊画阵方法。回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坐在西侧的悬崖往下看。
一片落差巨大的断壁,脚下是狭长的沙滩。
她这样发呆,直到太阳西沉,拙仓来催促进度,她把对方轰走,很快又两手空空出现在拙仓面前。
“这么快?”
“呸,我花了一下午时间冥想呢?”
你只是在发呆吧?!拙仓腹诽。
“枪呢?刚才还看你拿在手里。”
“作为阵眼插在那了。”
拙仓望去,乌金色的长枪生生埋进石头里,周遭没有一丝裂缝,像是从里面长出来一般,“法阵呢?”
“在枪身上。”张•耐心只有三秒•青不耐烦的往回走,“武器可是武士的灵魂,我把自己三分之一的灵魂都放在那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她说,“如果壁垒有用的话,武士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