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书拟人的企划。
来自不同时代、承载着不同思想的书化为人形。
“我想……看到世间所有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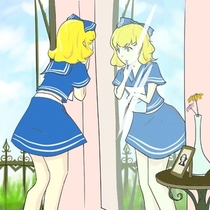
(突然に興奮する作者:这篇写得超爽的——!!!玩梗玩儿得飞起XDDD欢迎来找!两个人物的设定都好喜!!!如果读出了一些太宰老师的味道的话窝就再高兴不过啦!!!——字数3138)
◆津岛洋三篇◆
一直以来,我过着华族少爷的生活。
华族,或者说是虚张声势的华族,更为确切。那就如同与人比试剑术的时候,一招一式都大声地呼喊出来,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样恐惧。并不是害怕被人刺中,事实上,我情愿穿着二重回打扮得惹眼在街上乱步,我想用尖锐的语调在礼堂与人辩论,我站在空旷的公园中央等待着被人射杀——那样总比被别人的短刀刺进了胸膛,那人却惊异地“啊”地叫了一声,这感觉怎么竟像刺进了枯木,不,是刺中了女儿节的雏坛上的偶人吧,所谓的华族,原来就是这样外强中干的东西呀,然后露出了受骗一般的失望的神情,要来得愉快得多。有一种说法,叫“诞生的烦恼”,世人总以为生在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是没有烦恼的,其实恰恰相反,仅仅是有这样想的世人的存在,就叫我寝食难安。
世人的可怕,在于对他人的痛苦完全的无理解。(虽然,我以为自己也得算在此范围内。只看到我的外表,就想将我全部了解是不可能的吧。与此同时,我也对他人一无所知。)曾经,我还是个任性的小少爷,不知不觉地,便成了这个世界的弃子。我独自住在广场东北侧的公寓六楼房间,称为“仙游馆”之处。和式房间,桌子对着窗口,可以眺望“玻璃之眼”公园的小树林。门旁边的墙上,有一幅不知是谁写的字。内容有些熟悉,仿佛在哪里听说过似的:
悠々なる哉天襄、
遼々なる哉古今、
五尺の小躯を以て比大をはからむとす、
ホレーショの哲学竟に何等のオーソリチィーを値するものぞ、
万有の真相は唯一言にしてつくす、
曰く「不可解」
后面似乎还有内容,然而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坐在桌子前,用手支着脸颊,想了好久,也想不起下一句应该是什么。想不起来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的过去和将来,倒也不急于一时。那么,不如去外面转转,看看有什么收获。打定主意,我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咔噗。
一声轻轻的锁响。我竟正巧和住在对面的人同一时间走出了房间。那人是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绅士”,这个词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果然,他很友好地帮我按下了电梯,然后回过头向我示意。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的门牌。
「津岛 隼。」
这个姓氏令我在一瞬间感到,仿佛看见镜子里一丝不挂的自己一般羞耻。为什么……他会和我同姓?他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走马灯的画面从我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却看得非常清楚,像是一下就做完了几十场噩梦。
“你好,我是住在你对面的津岛隼,从今以后请多关照了。”隼的脸上带着笑容。起初,我为那友善的笑容感动得几乎流泪,后来,我才发现,他对所有人都是那样的笑容,宛如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这就是所谓的作为商人的“职业的微笑”吧。不知为何,我竟对那种打折促销的贱卖的微笑,产生了生理的排斥。
然而那个时候,我却是老老实实地脱下帽子,态度恭谨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津岛洋三,然后和他一起走进电梯。狭窄的电梯里只有两个人,我,和他。
沉默了几秒,我便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沉默了。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比起忍受一秒的沉默,我宁愿接受十年的徒刑。于是,我讨好似的对他说:“隼君,怎么样,有空的话去喝一杯吧?”
隼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虽然只有一秒钟,可我的脑海里的打算却已经如同放起了四国的烟花,如果被拒绝,又该怎么办,怎么填补这急剧地空白的空气,我的喉咙里像要伸出手臂,从这盒子里扒出一个窗口,哪怕外面就是大海,我也可以闭着眼跳下去。
“……好。”他的喉咙里似乎是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一个非常短促的音节,听起来奇妙而又不真实。可那对我来说,是久旱逢雨的救赎。我竟一不小心就眼眶湿润了,为了不被发觉,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偏过脸去。
◇津岛隼篇◇
我会写下去。我会写下去。把我的一切皆交予主。我的主唷。当我跪在您的面前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拿出这篇手记,毫不羞愧地说,我已经把所有真实的想法都写在了里面,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任由您的裁决。
是的,我很冷静,也很清醒地在写这篇手记。我有偶尔小酌一杯的习惯,然而喝了酒之后,我是不写的。喝了酒,我就改不掉这个夸夸其谈的毛病,要是写下了什么自己也以为是真实的谎言就不得了啦。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的谎言,我是不认同的,那样的谎言太过低劣了。可是,把自己给骗了,却骗不了您的谎言,那可是死一般程度的羞耻。要是出现了那样的纰漏的话,您还是直接让我去地狱吧!正因为我比任何的基督徒都要敬爱您,才不能够忍受这种情况的发生。
请允许我,从头开始说明吧。我叫津岛隼,是一名商人。商人是非常不受人欢迎的职业。您一定知道犹大•伊斯卡利特吧?对不起,我又开始胡说了,您是无所不知的。让您回忆起不好的事情来了,真是万分抱歉。这或许就是商人天生背负着比普通人更深的原罪的原因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商人”,和“虚伪”、“贪财”、“庸俗”等等词语是很亲近的,几乎是肌肤之亲的程度。而且更为可笑的是,人们喜欢钱,却也喜欢把钱说得一文不值。请看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劫富济贫的故事吧,难道身为有钱人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吗?穷人总认为自己很苦,而我以为商人才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当我读到《新约•马太福音》的那一节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在颤抖,一种莫名其妙的悔意令我泪流不止。我真是丑恶啊,丑恶到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丑恶的程度。像我这样的人,就算是缢死在耶路撒冷的城郊,也死不足惜。
好的,好的,我不再哭了,一个哭得不像话的中年男人的样子实在是目不忍睹。对了,我正要写的是我在广场东北侧的公寓六楼的住处对面的邻居的事情。他叫做津岛洋三,这是我早就从他的门牌上得知的,作为商人,需要懂得观察。可我那时候还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可能是他生活的节奏跟我不太一致的缘故。
巧合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了他,在我的房间外,在我正准备下楼的时候。他穿着二重回,系着浅蓝色的围巾,戴着一顶圆礼帽,举手投足间,透着一丝忧郁的气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一定是个相当有情趣的人。虽然身为商人,我却自以为自己非常能理解“精神家”,总是乐于和那些人为友。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很美,和我这种俗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眼眸还未遭污染,像孩子一般无欲无求。倘若他们可以允许我呆在旁边,在必要的时候伸出一点援手,我也觉得像是得到了神子的眷顾,灵魂或许还有救也未可知。
我主动地和他打了招呼。后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态度太过于谄媚,以至于令人感到虚伪。啊,我一定是刚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我被他讨厌了,那个人从来就没有对我有过任何的好感,只有我像个傻子似的毫无怨言地照顾、体恤着他。
他在我的面前脱下帽子,弯下了头颅,用非常郑重地语气说道:“初次见面。我是津岛洋三,今后烦您多多指教了。”
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加上毫无必要的郑重语,还有,带着含羞的微笑。可能他自己都未曾察觉,那种含羞的态度,就是他放出来消除别人的警惕心、吸引女性的烟雾弹,他是个欺骗别人任劳任怨为他献出一切的高手!我天生有着敏锐的嗅觉。虽然我也觉得那是因为我的灵魂低俗的缘故,并不喜欢这样,但我确实具有一眼看穿他人弱点的洞察力。
即使如此,我却觉得他很可怜,很值得同情,这也许并非出自他的本心。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拯救他。我和他登上了同一架电梯,我想,要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了。
就着这个时候,他突然对我说:“隼君,怎么样,有空的话去喝一杯吧?”
虽然有些别扭,可是,他竟将我称为“隼君”,我感到心脏如遭浪潮冲撞一般,忽地眯起了眼睛。我被忽然到来的幸福弄昏了头,差一点不知所措。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我才勉强稳住心神,点点头答应了他。
他却沉默着偏过了脸,好像很嫌弃似的。我的主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太过分了,总是故意把我当傻子玩得团团转,他根本不配做人!没错,我很清醒,想得很清楚了,我全部向您坦白,从第一次见到那个人开始,我就讨厌他。
正文1039字
情节废不断回忆杀注水中Orz
最后水果静物是玩原著的梗ww
===================================
在学会画画之前,我执不算真正的活着。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比起五六岁就开始拿笔在纯白的纸面上涂涂画画的小孩子,他接触到这些的时间格外地晚。或者说他从未想过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件事,因为这与他的生活毫无交集,他又因为日复一日的忙碌与幸福而变得麻木——直到某个黄昏。
他没有在街头看见艺术家们挥毫作画,也没有在什么画展上受到百年前大师的震撼,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我执就和平日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他忽然就不想回去了。
于是他就穿着那天上班时穿着的西装,带着口袋里的一点零钱,走向了与家完全相反的方向。
宽大保暖的斗篷是他某天倒在街头时,有个陌生的好心人给他盖上的。使用了上好木料的拐杖是在独居的老人家过夜后的顺手牵羊。而他当时所带出来的那一点点零钱,全部换成了画具。
没有老师,也没有任何可以予以指导的书籍,我执在前人走过的路上一次次地走着弯路,不断地碰壁又不断地遇见欣赏他才华的人,然而他依旧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可能人生全部的意义所在都是一片混沌,只有握笔创作的时候,神识能获得半刻的清明。
我执依旧处在这样的迷茫里。
他从来不是那种可以一个人照顾好自己的人。
永远灰扑扑的旧西装和旧皮鞋,有了破洞的斗篷,一看就很多时日没有再保养过的拐杖。他也几乎攒不下钱,用着最好的画具吃着廉价的面包,迷惘又坚定地就这样走下去。
经常来玻璃之眼公园的人,大概都已经对我执印象深刻了。哪怕是烈日当头或者暴雨倾盆,我执都会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这里,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比如今天,他会带上一张大大的透明塑料布,把自己整个裹在里面,依旧坐在温泉边上进行每日的写生。
下着雨的公园除了我执以外空无一人,矮矮的篱笆墙后,花草也没有晴天时那样明艳灿烂,他忽然有些想念那个有些聒噪的金发邻居,但他只会在能看到夕阳的日子里出现。
自己是不是也害怕孤独呢?虽然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只要能够画画就可以很好地活下去,但是现状真的是如此吗?
然而这只是一个瞬间的闪念而已。
我执终究是个无情无义的偏执狂,为了自己的目的,他可以坦然地伤害无辜者,甚至坦然地伤害帮助过自己的人。
可是这某几个瞬间的闪念,这某几个瞬间的愧疚和痛苦,只会让他更加想逃避。
最后他还是看向了眼前的画纸,画下了雨中的一朵玫瑰。
那是我执的救赎所在。
回去的路上,天放晴了,我执不由自主地微笑着,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他哼着歌回到了家里,忽然打定了主意,明天要到商业街去买点水果,因为“想画水果静物”这个想法,正在他脑海中不断翻涌。
(正文1552字)
(不会编剧情的中之人今天也在逃避。少女心理活动凑字中……)
---正文---
上午,太阳还远没有走到天空的中点,宴冒着冷冽而清新的空气来到公园一角,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到手里的书上。初冬的阳光被云层一滤,光线更加柔和,甚至没能在书页上留下斑驳枝影。眼前这幅景象寂静而和平,其中却隐约透着一股不安,宴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住在欧洲的时候经历过相当漫长的冬天,这样灰白的天空她见惯了。与一些其他人一样,她常常愿意在外面坐一整天,等着阳光横扫大地的奇迹般的时刻出现。到那时,那种突然卷遍全身的温暖会盖掉所有不安。不过人们不一定能等到这样的时刻。
在这里,即使是冬天也没有那样严寒,但足以让宴回忆起那些漫长的等待,希望与雀跃,和希望与雀跃之前的压倒性的沉闷。所幸阳光并不是那么稀少的资源,图书馆的午后尤为如此。中午时分云应当会散去了,在那之前就这样读书也不坏。
今天带着的是一本描述欧洲的书。宴对欧洲的了解除了亲身经历之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些书中既有她熟悉的事物,又有连她的想象都难以企及的内容,两相交织,几乎扰动了部分记忆,使她偶尔感到自己度过的岁月不止区区十三年。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面前的书本好久都没有翻过一页。在旁人看来,宴大概一直是一副专心读书的样子吧。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回过神来,视线在纸张上逡巡一会,还是回到页首重新往下读。书里正是一段诙谐的世态描写,本来是相当吸引人的。
不过这一次,连贯流畅的阅读同样没能持续多久。
一个清亮的声音在一段距离外响起:“早上好,宴!”
抬起头一看,有位少女正在向这边挥手。是对门的邻居泪茯,一个兼具活泼与优雅,十分可爱的女孩。宴也同样回应:“早上好,泪茯。”
大概是很开心能在这里遇上,对方一路小跑了过来,带起一阵小小的风。宴刚刚合上书站起来,却见活力十足的少女被石头一绊,“啪”地摔到了地上。
连摔倒的动作都带着不寻常的风。
宴有点被这冲击性的一摔吓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而泪茯自己却好像不以为意,念叨着“哎呀哎呀”三两下就爬了起来,宴去扶她的动作也落了个空。
“啊……没事没事……”泪茯拍打着衣服,一边说着,“比这重得多的跤我都摔过呢,有一次在草地上摔进兔子洞里……”
虽然不大明白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摔进兔子洞,宴还是认真地听着。
“……那只兔子尽说些听不懂的话,后来遇到的猫也是,真希望我能明白它们在讲什么……”
忍不住好奇地插一句嘴:“完全听不懂的话,是吱吱吱、喵喵喵之类的吗?那为什么会知道它们是在说话呢?”
“不是吱吱喵喵,真的在说话,只是听不懂……不对,那应该是能听懂……可是还是不明白……”
宴大概理解了,这就像自己现在听她说话的感受一样。但是她谨慎地没有说出来。
“……不过那次真的摔得很奇怪呢,从那么高的洞里掉下去竟然没有受伤……”
虽然还是不大明白一个兔子洞究竟有多高,宴觉得现在不是问这种问题的时候。
“说起受伤——泪茯你的膝盖是不是擦破了?”
“?!……咦,好像是有点疼……”
“快来,坐这儿。”
两人并排坐下,宴开始从披肩内侧的暗袋里往外掏东西。
碘酒、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安全剪刀……
“小宴……”
“什么?”
“你、你竟然随身带着急救包?!”
消完毒贴上创可贴,泪茯的兔子洞故事也将近讲到了尾声。
“……就是这样,这一跤摔得,不得了啊。是我前几天做的一个梦哦!”
看着邻居一脸得意的样子,宴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想象力真是不一般。虽然不合逻辑,她的故事却有莫名的魔力,仿佛深处藏了秘密。
“泪茯还有其他有趣的梦可以讲给我听吗?”
“当然有啦!话说有一天我正在照镜子,突然……”
坐在那里述说奇妙故事的泪茯,收敛起一开始咋咋呼呼的劲头,看起来是位完美的小淑女。
不知不觉间太阳升高了,空气里依旧泛着冷冷的色调,但阳光的直射让周围略微温暖起来。泪茯讲完了她的第二个梦境,转而问起了宴做的梦。
宴回想一下,又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回答。
“不,我都不记得了。”
---正文完---
*关于披肩里的急救包:原作结束的时点正值二战,所以宴是拥有强烈危机感的孩子。披肩的样式有点参考一战战地护士制服,就顺手这么设定了。(当然并不是说战地护士也会把医疗用具塞在披肩里。大概不会的……)
*一切你看出来或者没看出来的吐槽属于上帝视角。宴不是个吐槽型的角色(……)。
“美丽的小姐,请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突然被这样问,即使是蕾舍尔·25岁大龄·恨嫁剩女·吃货·凯萨尔也会感到一丝意外吧,她无奈地站起身,对着面前看起来中二感十足的少年柔声用着妈妈的语气回答到:“小弟弟乖,大中午的不要随便乱跑,家长会担心的。”
费尔南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居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有些慌乱地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定了定神才再度问到:“……呃这位小姐,我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参加晚宴嘛?专属于我们二人的。”
听到晚宴二字蕾舍尔双眼放光但是为了彰显自己是个沉稳的成年人,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接过请帖。
“这里蕾舍尔·凯萨尔,请多多指教。”
“费尔南·兰波,蕾舍尔小姐可一定要准时赴宴呢。”
“这是当然。”
其实蕾舍尔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下来,大概又是自己用来吃的那个脑子发话了吧。听说那个孩子是法国人,也好,跟着他学学什么法国礼仪也是不错的吧……当然重点是晚宴了,不知道带点什么去比较好。
酒吗?要说酒的话自己的酒柜里还是有不少好酒的,平时也没有机会喝,一个人喝闷酒听起来也太可怜了,所以她宁愿去酒吧点其他的酒喝。说起来带什么酒比较好呢?是这种皇后城堡红酒,还是那瓶伏特加?或者说是十年藏白葡萄酒?
蕾舍尔站在酒柜面前犹豫着,完全忘了最重要的应该是自己穿什么服饰而不是带什么酒。等她选好的时候,太阳已经半沉入地平线,用最后一片光线染红了一片云彩。
“呃……如果是正式的晚宴的话果然还是礼服比较好吧。”拎起了一件衣服在身上比划比划,顺带瞄了一眼时钟,发现时间逼近之后当作没看见偏过头继续选衣服,“或者说穿上次的那件小裙子?”
女孩子的更衣时间是不可计算的,再加上化妆时间那简直比在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以及蕾舍尔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时间观念的人,一套准备下来早已日落西山甚至月亮都要爬到头顶了。
“抱歉我迟到了!”蕾舍尔踏着8cm的黑色鱼嘴高跟鞋匆匆赶来,身着深褐色的抹胸晚礼服,裙边缀着银线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些晃眼。脖子上带着黑色的颈链,一块黑曜石缀在锁骨之间散发出神秘的气息。
费尔南站起来,作为一个绅士替蕾舍尔拉开了座椅:“没关系,女士都有迟到的权利,尤其是……”他说话顿了顿,一手捋过蕾舍尔散下来的金发轻声说到:“那么美丽的女士。”
蕾舍尔满心都是关于晚宴也就没有去在意费尔南说的话,“费尔南你也坐下吧,呃我带了一瓶红酒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瓶很合我胃口你试试看?”说着就拿起开瓶器将自己带的红酒打开了,站起身来往费尔南杯子中倒了进去。
“红酒和美人,都是我所喜欢的。”费尔南说的话大概是在道谢吧……蕾舍尔这样想着。
菜品一道道端了上来,夜空点缀着繁星点点,映衬这两人的身影,两人的吃得尽兴[事实上只有蕾舍尔吃得很开心],聊得也很开心[大概也只有费尔南聊得很开心]。
“蕾舍尔小姐去过法国吗?”费尔南拿起红酒杯抿了一口缓缓问到,“若没去过我可以带你去领略一下法国的美景。”
蕾舍尔此时正在和牛排搏斗,嘴上随意地回答道:“去过啊,法国。我14岁的时候就在普罗旺斯住着了。要说法国最喜欢的果然还是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吗,的确不管是薰衣草还是红酒和蕾舍尔小姐很适合呢。”费尔南还是太天真了。
“呃……硬要说的话最喜欢的大概是那边的菜肴。”
“……”感到了挫败的费尔南无言。
“嘛,总之今天晚上我很开心!”当然是指吃得很开心,蕾舍尔忍住了不说出来,绽开了平时看不到的灿烂的笑脸道谢到,“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一起……”想下次继续蹭饭的心情在,但是却表达不出来。
与费尔南告别后一个人踩着愉快地步伐回到了房间,把喝了一半的红酒放回了酒柜开始进行了卸妆大业。
蕾舍尔·25岁大龄·恨嫁剩女·吃货·凯萨尔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