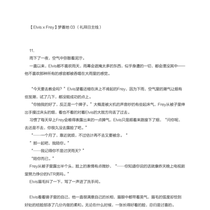那位神父——扎哈尔和他在岛上的相见次数仅有来岛上第一个月的几次会面,他只知道对方是黑发绿瞳,白种人,左眼角下方生了一颗泪痣,连名字都忘了问。
就像擦肩而过的两名路人,扎哈尔第一第二天还在想那位神父鼓励自己的话语,并且把对方引自圣经的那句话在经典中圈了出来,然而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好好大哭一场宣泄了不少压力,并且一直忙于接受新环境和新知识的扎哈尔•小没良心•伊萨阿科维奇先生就把这个神父彻底抛在了脑后。
直到——他在15岁生日之后的第三个礼拜日,倒霉催的被同学恶作剧,和班级里最矮的朗曼先生一起关在学校壁橱里,和那些结着蜘蛛网蒙了一层灰的破烂扫帚得到了一样的“礼遇”。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出在是和克里斯托弗•朗曼关在一起,其本人的存在像是把一整个巴别塔拴在班级成绩后面那样,害得平均水平一坠到底永世不得翻身,倒不是说对方的智商最低值突破了扎哈尔的忍耐力,让他连和对方共处一室都会觉得反感。
虽然过了一年多说起里洛尼亚语来,舌头依然由于北国家乡的口语习惯而永远捋不直,但是伊萨阿科维奇怎么会是那样心眼好像针尖绿豆的人呢?!他绝不会因为第一次站在班级讲台上自我介绍时被对方嘲笑了几句“嘿!新来的小子!你舌头上有八个结!”而记恨的人!绝不是!
不幸的根源是——这个克里斯托弗也自认是扎哈尔的冤家对头。
严格说来,扎哈尔认为自己在克里斯托弗先生眼里是那种恨不得半夜按着对方的脑袋把他溺死在便器里的死敌。
而这种莫名其妙的仇视,在扎哈尔看来毫无根据,他不记得自己这个可怜的外乡人在哪儿招惹了对方以至于让对方冠以如此深仇大恨,除了成绩好点儿以外?而作为自卫,当然,扎哈尔自然对克里斯托弗没有好脸色。
绝对不是因为克里斯托弗嘲笑他那来自亲爱家乡的口音。
扎哈尔愤怒地踹了一脚橱柜的大门,木门卡啷卡啷响了几声后,纹丝不动。
旁边传来小个子的嗤笑,声音挺大的,故意让扎哈尔听见似得,然后那个头发微鬈,鼻子两旁有些小雀斑,皮肤黝黑,呈现出一种健康而自然的阳光颜色的混蛋矮子克里斯咂咂舌,大摇大摆抱着臂欣赏扎哈尔困扰的样子。
“喂,伊萨阿科维奇。”在扎哈尔面无表情地瞪过去的同时,那个矮子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的额头狠狠撞到了橱柜门,眼镜一下子给磕掉了,黑乎乎的橱柜里本来能见度就很低,所以当高度近视的扎哈尔捂着撞痛了的额头,努力睁大自己那双形同虚设的眼睛之后,他发现看不见的程度变本加厉了。
“哦抱歉,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扎哈尔听见对方毫无诚意地道了歉,然后一股力量就伴随着咔擦一声,疑似眼镜被踩断了框或是弄坏了玻璃的声音,揪住了扎哈尔的领子,并由于主人身高的原因强行把他向下拽了拽,“怎么样,哭了吗?”
额头很疼,满肚子窝火的扎哈尔恶声恶气,一边挑起眉毛用比对方更加混蛋的表情笑起来一边奇准无比地用语言化作利刃,一刀戳中对方心口:“真是对不起,我还不至于像个您所期待的娘炮那样哭哭啼啼,克里斯托弗•矮子(朗曼意为高个子的人)先生。”
然后他带着笃定的胜利者微笑,接着在对方疮口上倒了一罐子盐上去:“感谢您好意‘搀扶’了一把被小矮妖推了的可怜人,伊萨阿科维奇我本人对此‘感激不尽’。”
朗曼先生的脸从脖子根开始倏地一下红了个透,他看起来简直怒发冲冠了:“不许说我矮!你再说我就——”
“怎么?你要用我的脑袋把门砸开吗?”
“克里斯大爷我不打牧羊犬。”
“哦,那看起来刚刚真的是小矮妖推了我一把。”
对方一时半会儿被堵的说不出话来,扎哈尔难免有点小小的得意,唯一让他沮丧的是,他没法亲眼看看对方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倒霉相。
隐约有教堂的钟声从外面,顺着狭窄到连根小指头都伸不出的壁橱缝,悠扬而平静地回响,在霉菌和灰尘的味道里,扎哈尔额头上的痛感已经消失,火气也渐渐消散,他在视觉并没有什么用的情况下,百无聊赖地用手指摸索着扫帚上的稻草杆,偶尔会触及到细小的蜘蛛,然而刚一碰到,对方就顺着轻细到要融化在空气中的丝线小径逃跑了。
“……喂。”他伸脚踹了踹对方的小腿,在对方发火之前抢先问道:“克里斯,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说说吧,这儿没有别人。”或许是扎哈尔的声音出奇的平和,其中夹杂着一些超出他这个年龄的疲乏感,让克里斯托弗觉得有些不大舒服,而且这里确实没有些人——一个壁橱,绝佳的密探会面地点,最适合用来交换彼此的秘密。
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别别扭扭地开口接下话题:“什么?大舌头,你是不是傻,你是全班最高的,而我最矮!”
哦,我不该对朗曼的智商抱有任何希望的。
扎哈尔有一瞬间真的感到了绝望。
“而且你居然不记得我了!”对方带着积压了很久的愤怒,几乎是咆哮着吼道;“你说我是你安抚过的第一个羊!用你那口糟糕的里洛尼亚语!而你只过了几天,开学的时候居然不记得我了!”他过于激动,拽着扎哈尔的衣领,又把他向自己的方向拎了拎,那身力气大得不同寻常,终于使扎哈尔记起对方黑羊的身份,然后隐约和刚上岛的那个月,他颤抖着手,在那位不知名的神父帮助下,安抚的那只狂躁的小家伙对上了号,仅限身高方面——克里斯实在太矮了,以至于他以为对方是年纪更小的羔羊。
“我还亲切地和你打招呼!”朗曼先生气得哼哼唧唧;“而你,伊萨阿科维奇,瞪了我一眼,然后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开了,整整三天没和我说话。”
“你管那叫亲切?嘲笑我的发音?!而我管那叫嘲讽!”
“你的发音确实挺好笑的。”克里斯严肃地表示自己情真意切。
“胡说!卷舌音多可爱!”扎哈尔用愤怒地一把甩开了对方的手然后反过来揪住对方的领子来回应对方的情真意切。
“但是你忘了我,别狡辩!”克里斯咬牙切齿,耀武扬威恶狠狠的威胁高个子的少年,像只不断发出低沉喉音的狼崽子,“我发誓会一直欺负你到你哭着忏悔为止!”
“……那天是不是还有个神父在场?黑头发,绿眼睛,眼睛下面有颗痣的那个……?”
“那是贝戈尼亚神父。”克里斯严肃地打断扎哈尔,严防他花言巧语地狡辩。
而扎哈尔只想要捂住脸,然后惨兮兮地呻吟:“……哦主啊,我高度近视,朗曼先生,那天我没戴眼镜,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我还以为自己帮助的是一个小小的羔羊。”
“而你又没有留下名字!我怎么知道那是你!”
在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扎哈尔听见了克里斯托弗压抑不住有点儿欣喜的声音:“……所以你记得我是吗?”接着是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一个断了腿,而且碎了半片玻璃的眼镜架回了自己的鼻梁上,然后他感到克里斯吹了吹眼镜上的灰,经过几秒钟适应之后,模糊不清还带着裂痕,但是起码可见的视野又回来了。扎哈尔眨了眨眼睛,看见克里斯的眼睛在黑乎乎的壁橱里发着亮,从狼崽子变成了摇着尾巴的狗,这个前后反差让他一时间有点儿难以适应。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扎哈尔取下眼镜,一边呵气,一边擦拭。
“哦,是的,朗曼先生,我当然记得,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决定要去研究院工作的。”扎哈尔微妙地有点儿磕巴,觉得脸上稍微有些发烧,“……为了帮助更多的羊。”
“哦,这个我猜到了,贝戈尼亚神父早就说了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以后我就叫你扎哈尔啦!……你不愿意?每次都念伊萨阿科维奇太麻烦了,那大舌头行不行?”
扎哈尔踹了对方一脚。
“哦!……呃……卷舌音确实挺可爱的。”
克里斯托弗这么说着,轻而易举地一把打开了柜门,光线猛地射进来,刺地扎哈尔眯起了眼睛。
钟响了五声,是下课的时间了。
研究员扎哈尔•伊萨阿科维奇从回忆中被钟声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对着那盆秋海棠发呆了太长时间,这可不符合一个优秀的研究员的行事作风,他用食指指背揉了揉眼睛,然后重新对着文件俯下身去。
——————————————————————end——————————————————————
啊那个,贝戈尼亚神父和克里斯托弗·朗曼都是原创npc。【捂脸】可能再也不会出场的那种。
海岛上空气潮湿,早上醒来寒冷就着湿气往每一寸肌肤中渗透。“真冷。”撒尔瓦托这样想着,却依旧只穿着薄薄的睡袍,光脚站在阳台的地上,那上面的地砖经过一夜的冷却,像冰一样——这是撒尔瓦托来到岛上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半,寂静的东方没有一丝光亮。
大概站了二十多分钟,撒尔瓦托的脚和嘴唇变得微微发紫,终于走进了房间。前一天中午入住这里之后他把地擦了整整六遍,浴缸十遍,撒尔瓦托有洁癖,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房间里铺着很高级的地毯,装潢也颇为考究,家具的摆放也完全模仿着以前撒尔瓦托房间里的布置,甚至连厨具都是和以前一模一样。现在撒尔瓦托将略微冻僵的脚趾在柔软的地毯上稍稍擦动,看着眼下周围,十分满意。可懂些心理学还是其他什么玄乎理论的人能看出来,这房间的主人不安的像躲在角落不肯出来的猫崽,太明显了,他几乎就要把恐惧和不安写在墙上,这房间里满满的全都是对以往的怀念,甚至妄想催眠自己从未离开过以往,可当你看向房间主人的脸时,那只会有温和的微笑。像撒尔瓦托这种人——如果撒尔瓦托有同类的话——他们往往会把情绪表达得非常明显,当然不是在脸上,反倒是除了脸之外的任何地方。
撒尔瓦托给自己煮了一杯奶茶,坐在皮质转椅上看着东方如何一点点透出铁锈色的黎明。他习惯早起,他每天早上都会慢跑一小时。但今天不会。今天是礼拜日,也是他到这个岛上经历的第一个早晨。“Domenica。”他缓慢念出这个单词。撒尔瓦托的家族是虔诚的国教徒,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参加礼拜。但是撒尔瓦托不喜欢这些繁琐的事,以至于他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记住礼拜的所有流程。他想起在他变声以前,常去的那个教堂的主教曾拉着他的手夸赞他声音好听“圣洁得像天使一样”并大赞他的虔诚,而他微笑着听着,认为那主教是个变态的恋童癖,撒尔瓦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不是很愿意去做礼拜,因为他最喜欢的那套正装在前一天被洗了没有干,而他在坚持要穿那湿衣服三遍未果后,抢过洗衣佣的熨斗烫了她的脸。不知道那滑稽的红色伤疤现在下去了没有,撒尔瓦托噗嗤的笑了一下,那玩意儿的形状就像是没啃干净的猪脚。
奶茶喝完,撒尔瓦托又坐了半个小时。已经六点了,不去晨跑的早上显得格外漫长,他站起身开始换衣服,不多时,就站到了房间门口。在锁门离开前,撒尔瓦托又带上了立在门口的黑色雨伞,昨夜起过风,今天的太阳肯定会格外刺眼。
教堂不难找,在这个宗教性质的岛上,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是极为显眼的建筑,教堂前是气派的圆形大广场,高大的柱廊环绕两侧,廊顶有精美的雕像。广场中心有座漂亮的雕塑喷泉,撒尔瓦托走过去,摘下手套摸了摸冰凉的石头喷池,很舒服。他的面前就是灰黄色的教堂主体,教堂周围保留着历史建筑和立面仿古的新建筑,分外神圣辉煌。撒尔瓦托静静地看了一些时候,天也开始亮起来,喷泉流水的哗哗声伴着鸟雀清晨的啼叫声使得这神圣的广场有了些许生气。他看得厌倦了,便离开了广场,在周围转了一会儿,等到教堂一开门就急匆匆的走了进去。
撒尔瓦托坐在靠后的位置,即使他差不多是第一个入座的教徒。他一直都很想坐在后排试试,这在以前的家里是不允许的,他们家作为贵族和虔诚信徒,一直都是占据最前几排。他一般被安排坐在母亲的右边,这个习惯延续到母亲去世后的今天,他会故意空出左边的座位,有时还会在坐下前先往左边座位上铺一块手帕,父亲再婚后,坐在撒尔瓦托左边的换成了那位眉峰奇高、浑身肉滚雪白的新继母,但他依旧会空出一个座位,这让那位新继母非常不满,甚至有几次差点在教堂发作,撒尔瓦托并没有在意过那位继母的态度,在他眼里那继母只不过是一个坐错位置却又没被责罚的拙劣的管家。他偏过头看了看左面的那些空位置,心想即使等到礼拜结束,那儿也再不会有傲慢无礼、浑身散发俗气香味的下贱女人了。他又开始低低的笑起来。
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涌入教堂,礼拜很快就开始。撒尔瓦托在教堂的角落位置向前望去,几乎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后脑勺——全是男性。虽然在来到岛上之前已经听说了有关“庭院”的事情,关于里洛尼亚的超能力者“羊”和“犬”,但听说和实际见到是两回事,撒尔瓦托稍微皱了一下眉头,“Fastidioso。”他低沉的念叨,都是男性,他讨厌男性,实际上他也讨厌女性,如果他不够自信他连自己也会讨厌。空气中混合着几千人呼吸出的二氧化碳,撒尔瓦托感觉自己好像被无数个烂糟糟的肺给埋了起来,仔细一些的话,甚至可以嗅到昨晚或者更早遗留下来的肾上腺素和某种体液的味道,他蹭了一下鼻子,糟透了,简直要吐了。主祭念完了长长的经文,唱诗班的少年在台上唱诗,这使他又想起那个主教,撒尔瓦托心里快速的闪过一句脏话,然后又快速的忘掉,比起坐在温暖教堂里的四个小时,他更喜欢清晨寒冷空气里只有自己和鸽子。
最后一次祈祷了,撒尔瓦托喝下分发下来的水,然后把剩下的一小块面包装在口袋里。他没有吃早餐,但他也不愿意碰那块面包。祈祷结束,唱过圣歌,撒尔瓦托几乎是逃出了这偌大的教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里面还未全部散去的人群,那里面,有结队的人在交谈,有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询问,饥饿的猎人在寻找猎物。撒尔瓦托摸了摸鼻子,转身离开了教堂,走到广场中心喷泉旁边时候,他把口袋里的面包揉碎扔向面前的鸽群。
撒尔瓦托掏出一张纸擦了擦喷池的边缘然后坐下,登录庭院局域网的休闲论坛。在这个岛上,有个搭档最好,听说得到政府信任的话,还能稍微离开这里几天呢。他所关注的那个网页上有很多的征友信息,撒尔瓦托按了几下屏幕,输入了自己的信息,还拜托一位路人帮他拍了一张照片附了进去。其实并不是多么急切地想交朋友,撒尔瓦托又看了一会儿鸽子。帖子有了回复。
屏幕上那人混着金色刘海的半长头发看上去并不让人讨厌,嗯……影子、成年、最重要的是看上去很沉默。撒尔瓦托笑了笑,回复道:“Grazie,兰道先生,希望我们以后的合作会很愉快。”
【*PS:文中对教堂的描写参考圣彼得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