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章】进行中 时间:5月16日-6月15日*
通过审核的玩家可以加入交流群374787588,验证填写自己的【角色名字】。
距离【百年法案】之后的三十余年之后,发生了【天狐暗杀事件】,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暴露出了一个军方研究“人造半妖”的组织。在最近几年中由于人类世界的战争愈演愈烈,军方曾多次向天狐提出援助(主要是请求妖异参与人类战争)都被拒绝。这次事件的原因可以推测为“以人类手段进行某种示威”
重伤清醒过来的天狐,认为“人造的半妖”只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战争兵器,是一种悲哀的存在,以“给予他们慈悲”为名对人造半妖进行抹杀行动。
目录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12552/
BGM推奖:訣別 - nihilism http://music.163.com/#/m/song?id=33211958
我想这个故事写到这里,或许已经临近终章了。
从我起笔至今,前后约莫不过一年光景,而书里也不过二度春秋,我却把它用来描述一个人的一生。这很鲁莽,并且草率,但我认为我必须留下些什么。我像个真正的人类一般,反复着斟酌落下笔的每个用词,使它尽可能地贴近我的记忆中的真实,这在我以往写作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这并非创作,只是单纯地复述,而我此刻才发觉这竟是如此困难的一件事。我开始浅眠,梦里时常惊醒,有时与人交谈时听到别人口中一个绝妙的词汇,忍不住工工整整地记录在随身的手札里,思忖着在哪一行字中可以化用进去。
(……纸张上有少许的皱褶和茶渍,字迹有些模糊)
但我终究完成了。这不是一本小说,只是一段漫长的复述,只关乎一个灵魂。我将它用文字的方式从专属于我的回忆里誊写下来,立于世间。我不奢望有任何除我以外的人能阅读它,但我依旧希望如果有人能看到这本手稿,在翻至最后一页时,可以接纳这个孤独的灵魂,对他张开双臂,平凡地给予他一个拥抱。
——这便是我写下每个字的意义了。
弥生
大正八十一年春。
高河千代,十二岁,家中经营一家和果子铺。帝都这场巨大的变动对她而言的记忆并不深刻,唯一令她疑惑的是她最喜欢的长兄刻人自几年前参加军队后就很少归家。而在两年前他们全家因为战争迁到了郊外之后,她便再没见过她的长兄。她们去年从郊外搬了回来,重新开张了和果子铺,然而一直挂在店门口的全家合照却再没挂上去,如今被一张剧院的宣传海报所取代。她不止一次问过她的刻人哥哥去了何处,而每每她问起,母亲微笑的神色总会黯淡下去,只说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服役,很久都不会回家了。
元旦也不会回来吗。
不会,但哥哥是个很负责的军人,他会在远方保护我们的。
……但是千代想哥哥。千代也低下头,撇了撇嘴,像要哭出来一样。哥哥很久很久之前就答应过我,要带我去剧院看春季话剧的。
妈妈也能带你去看啊,等到下次休日,我们就去看你喜欢的“少爷与猫”可好?
十二岁的千代很快就开心了起来,大声说,那等他回来,我再和哥哥去看一次!
千代甚至已经盘算起了,等到哥哥回家,要让哥哥带她去吃剧院旁的西点铺子里的抹着白色奶油的水果蛋糕,听他给她用温柔语调讲他的朋友,他的生活,他在途中见到的人与事。她还想给哥哥看她在郊外的海边捡到的漂亮贝壳,正反的色彩都一样精致好看,千代想把贝壳从中间分开,送给她的哥哥一半,自己留住另外一半。千代掏出绣着哥哥名字的小巾着里的贝壳,对着光认真地比对了很久,开始思考起了他会更喜欢哪半的颜色。
风铃声代表有客人进来,母亲在后间忙作时,千代也会帮忙收钱。进来的是位戴着帽子和眼镜的客人,看起来年纪并不大,应当和自己的哥哥差不多。而他笑起来时也会眯起眼睛,友好地对自己摆了摆手,他问,你年纪这么小,怎么一个人站在柜台这里啊。他的声音不大,很温和,像春天和煦的风,让人心生亲近。
妈妈在忙,爸爸去进材料了,千代一个人也可以帮忙的!
原来如此,真可靠呢。
他要了两个红豆馅的鲷鱼烧,说他有些走累了,想坐一会,如果可以的话,让千代再给他倒一杯热茶。茶水都是现成的,千代用棕黄色的油纸包好点心后和茶水一起端给了他。他一脸满足地捧过茶杯,抿了一口后出了一口长长的气。
……活过来了,他说。好久没这样逛街,走了这许久功夫,我的脚都有些痛了。
他环视四周,看着千代把托盘抱在胸前,栗色的眼睛望着他,眨动间闪烁着好奇,他也便饶有兴致地回望过去,随后就像千代招了招手,示意让千代走过来,也坐在他的身边。没事的,我现下只是有些无聊。他又抿了一口茶,声音顿了一下,之后眼睛又眯了起来,向千代展露了温和笑意。千代觉得眼前的这个客人很特别,也很神奇,她愿意多亲近一点,也喜欢同他多讲一点话,甚至当对方的手温柔地抚摸上自己的头发时都不会觉得讨厌。
千代觉得,他有些像自己的哥哥。
“您……您会讲故事吗?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在说出口之后,千代才发觉自己的失礼,连忙侧过头捂住嘴巴,匆匆地给对方行礼道歉,“抱歉!我太久没见到自己的兄长了,您感觉上有点像他,才会突然提出这样失礼的要求……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对方睁开眼睛看着她,这时千代才发现对方的瞳孔是很温暖的金色,像是他身上温度的来源,柔和地和窗中透下的春际阳光融合至一起。
“当然可以,敝姓有栖川,是个不入流的写书人。”
那是千代从未听过的,一个漫长到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
但仔细算下来时间,也并非有那么长,前后不过二年时间,而在故事里也便是几段话的功夫。三言两句,只言片语,语调和缓地描述着惊心动魄。有些地方太过细腻和晦涩,千代并没有完全理解,但却不想打断;而对方比起叙述,更像是在一边述说,一边回忆。他金色的眼睛没有看向千代,而望着的似乎是更加遥远的,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途中千代的母亲从后间忙完后来试图拉回千代,笑着跟他抱歉说小孩子打扰了他,他却只说无妨,友善地留下千代,说让她再陪伴自己喝尽这一杯茶。
那后来呢?
……他认为他不能逃避他应有的命运,他选择了自己接受上级对「他们」的裁决,再离开那里一年后,主动地接受了对他们「公开处刑」的命运。
好可怜。千代感觉自己快要哭出来了。明明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那么他死了吗?
他……。
有栖川一直持续和缓的语调首次出现了止顿,他的目光从远方收敛了回来,紧随其后的便是沉默,但这份沉默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门口突如其来的风铃声和千代母亲的欢迎光临所打断。
“就猜到你会在这种地方,又在给小孩子说故事听吗?”
踏着声音步入门内的是位青年,他体形修长,步伐也很大,从门口到千代他们所在的位置有些距离,他却几步就走到了。待离近后,千代才注意到青年的右脸颊上有黑色的,类似火焰一样的黑色痕迹,从脖颈处一直爬上来,蔓延至了右眼眼角。明明是有些可怖的疤痕,但眼前的青年却好像并不在意,没有刻意掩盖,也没有带上任何饰品试图分散视线。千代的视线一时没能离开那一片黑色的痕迹,青年看起来与之前的先生年纪相仿,但在黑色的痕迹末处却能看到鬓角处的少许白发,白与黑的对比一时竟有些刺眼。
“哎呀,你回来了吗,等你等的有些无趣,我便找了家店坐坐,这里的鲷鱼烧味道很好哦,你要不要也尝尝……喔,不经意间竟然被我吃的第二个也只剩半个了,但好在剩下的是馅料多的部分,试试看?”
千代本以为青年会拒绝,因为青年并不像之前的有栖川先生一般,给人以亲近随和的感觉,相反,从千代看到他进入店后,除去对母亲的招呼微微点头回礼以外,她甚至没看到青年的有过变化。尽管千代从未和他交谈过一言片语,青年身上自带的疏离气息还是让她不自主地向后倒退了一步,脚步落在榻榻米的地上,发出了蔺草被挤压的细微声响。而对千代来说本不应会被人注意到的动静却被青年捕捉到了,才刚刚接过有栖川手中用油纸包裹的半个鲷鱼烧,他的视线却突然回转,落在了千代的身上。
“抱歉,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啊,不!并、并没有!只是我觉得我站在这里,似乎打扰了你们的谈话而已。”
“没有的事哦,和千代能这样谈话,我很开心,不过我等的人来了,我也要走了。”说罢,他伸手从桌上拿起帽子戴上,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的下摆,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青年的身边,牵过了他的手。而对方也似乎习以为常般,任凭他牵着,配合着他的步幅大小慢慢向外走去。
“等一下,有栖川先生!您……您还没说完那个故事的结局,我有些在意!”
他停下脚步,眯起眼睛回头对她笑了,模样一瞬间让千代想起了猫。
“没有什么结局,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这是关于一个人的一生的故事,然而这个人还没能走完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也对结局一无所知。或许未来会有,或许我会将他写下来,即便如此,我写下的依旧只会是只有一个结局的故事。”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人的命运,不会只有一个结局的。”
——大正七十六年,零式前中尉 三千院司,被公开处刑。
最后一页上,只有这样的一行字。
千代再向后翻,竟然已经是空白。
这和她曾经听过的故事一模一样,就连在开场序章中的第一句,也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她在书中看到了戛然而止后的结局,她听过的故事却没有终结。她无从得知曾经的那位有栖川先生和这本书的联系,她重新翻过书的扉页,虽然标注了作者,却没有任何作者的照片和简介,只有名字和一行字,那行字的意思有点古怪,比起是写给读者,更像是写给特定的某个人。
昭和二年
三千院 景纪 作
此生得逢,是我之幸。
-----------------------------------------
后记。
大正九十二年,已是大正的最后一年,在度过这个漫长冬天后,便是昭和元年。
而昭和元年的春天似乎来得很早,踩着三月的尾巴,帝都的樱花就开了漫山遍野。
千代总会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去看望她的兄长——高河刻人,前零式上尉,于大正七十六年被公开处刑。在那个时代,零式被处刑的军人不被允许留在帝都的土地上,连尸骨都不允准,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墓地。而在大正八十二年时,由松竹梅财团出资,留下了一块纪念石碑,上面没有名字,也没有刻下任何的内容,仅仅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巨大并且沉重的石头,矗立在了一片空旷的土地上。
他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只说这是用来纪念在那场战争中逝去的人们。
这不是为任何一人,只是为了所有人,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
千代每年总会在她哥哥曾经喜欢的季节里去放下一束木棉。那块石碑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花包围着,一年四季,从未间断,等不到看见有花朵干枯,就能看到有新的花捧放置上来。但今年千代在石碑前却看见了之前从未见过的物品。那不是花,而是一个纸袋,稍微离近些,还能多少感觉到温度,仿佛放下他的人还没走远。
——是鲷鱼烧红豆沙的软糯香味。
千代突然听到了铃铛的声音。
不同于店中客人到访时的风铃的轻盈响动,风中夹杂的是更加沉重并且缓慢的铃声,逐渐远去。
阳光爬上空无一字的石碑,渐渐填满了每个角落。
千代放下花,安静地凝视了石碑片刻,说了两遍再见。
————————————————————————————————
高河刻人是我故事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NPC,有关他的篇章可以看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4962/ 五里雾中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6560/ 溺れる物は藁を掴む
主线就差不多这样算完结了 真的很感慨……第一次正经跑完一个企,一直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篇
总之我也是填了坑可以拉目录的人了
谢谢看过这个故事和评论过的每一个人。
事后会有两篇番外,作为中间发生的事的全部第一人称顺序叙述。
整合目录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12552/
我从未见过海。
事实上,我也曾经在脑海里试图勾勒过海的模样。在我年少时,曾有人对我描述过海的样子,说那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到足以接纳任何异于自己的物种的所在,任何高级的或者低级的生命在海水的广袤面前会失去意义。他指着书上的那一片像是闪耀着神秘色彩的蓝色,笑着打趣说道可惜他也只是远观过濑户内海,并没有那个好命可以乘船破风起行。我问他原因,他却只是避而不答,只是说了句我不明就里的话,当时的我没能理解,甚至没放在心上,只当是一个有点怪的写书人念的一句我不懂的诗,或者哪本书里的句子。
而当我无数次地在夜里惊醒的时候,那句话反倒一遍一遍地在我心头浮现,如同被拂去灰尘的刻印,每回忆一次,就更加鲜明一分。
他说,一旦适应海水,就无法再回到岸上了。
在那之后我们又谈了许多,谈了海生的妖怪,还谈了人鱼姬的故事,不过那些对现在的我来说只留有个模糊的印象,确切的内容我的确是记不清了。
不过我想如果现在让我看见大海,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跃入其中,并非是想要求死,只是单纯地渴求着在阳光下被温暖的海水包裹的感觉。除了呼吸以外的事情都无需加以思考,更不需要考虑该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在海水里所有的景物看起来都没有区别。
我在对他说出这番话时,他眯起眼睛,躲在被炉里的身体又向内缩了些,手里捧着装着散发热气的棕色茶杯,刚吃过鲷鱼烧的嘴边还有没抿干净的红豆沙,舔舔嘴唇的样子活像只餍足的发懒的猫——然后这只猫一本正经地看着我的眼睛,问我说,你是想变成鱼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
他对着我笑了起来,说鱼类通常忘性很大,他认识的某条人鱼,几乎每次见到时都要对他说爽朗地说初次见面,可他们明明见过很多次了呀。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那条有点脾气古怪的人鱼,对我说他们每次聊到最后,他都会很疑惑对方是不是真的记起了自己。说着说着,他的目光突然回到了我的身上。对方的眼睛的颜色很特别,是金色的,但平日里总带着的圆形的平光镜片,会将人的注意力的分散开,让人不大能注意到他的瞳孔。不过,我对那双眼睛记的很清楚,因为在很多夜晚里,我都是被那抹奇异又温暖的颜色注视着,安抚着,才能勉强入睡。
小司要是变成鱼,会不会记得我啊。
我思考了一下,点点头,说,我想会的。
对方眨了眨眼,露出了满意的神情,看着他的样子,我的心情也跟着一同放松了些,几乎要忘记了还有半句话含在嘴边没能出口。
……可我还是想忘了所有的,就当做从没存在过。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说。
残生
帝都四条河源町二街三号。
这个地方离市中心不算远,当然因为房租便宜,也算不上多近,不过考虑一下性价比,该算得上是十分划算了。房东森先生住在主屋,有栖川租下的只是别所,但好在有小门直通街道,所以平日里也很方便。只是森先生最近发现自己偶然从后街路过的时候,经常看不到自家房屋的小后门,甚至邮递员还反映过说森先生的门牌是不是该换换了,明明几次都是经过门前,却都注意不到,有几次还延误了信件的投递。森先生也和有栖川吃饭时谈论过——当然是以他喜欢的「灵异事件」的名义,本以为对方会感兴趣,没想到有栖川只是草草应了几声,后又说可能是因为房屋有些旧了,混在一条街上大同小异的屋子中,才没那么显眼。看着有栖川兴趣缺缺的样子,森先生不免有些失望,吃过饭后也没像以往一般留他在屋内喝茶,两个人便回了各自的屋中。
“真是吓我一跳,晚饭时他突然跟我谈起别人注意不到他房屋的事情,虽然这样瞒他我用了术式我有点歉疚,不过像这种事,也没办法说出口啊……小司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你给的那本书很有趣。”
三千院比起他们初次见面时瘦了很多,一半是因为伤病的缘故,但更多地是因为心情。不过和之前在SPST研究所的时候相比,还是相对好了些。虽然依旧少眠寡语,但在靠着他的时候,至少能安静地闭上眼睛,浅浅的入睡片刻。他还是多梦,即便在为数不多的睡眠时间里,也总会因为梦境挣扎着醒来,而每每有栖川问起梦境内容时,他便又沉默了下去。这种时候有栖川通常不会追问,会选择谈一些虚无缥缈的话题,像是他曾经的一个妖怪老友之类的,无从考证,但往往被他讲的妙趣横生,在滑稽之处让人莞尔,在紧张之处又忍不住屏气凝神。当一个故事结束,三千院总会觉得放松些,脑子里浮现的不再是那些幽深昏暗的如同甩不脱的淤泥一般的场景,而是一个个会说会笑,让人倍感温暖的妖怪。
三千院睡不着时,偶尔会与他谈起以前的事,但谈论的部分只有两段,只关乎两个人,其余的部分都只是提过便算,甚至从不提起,好像小孩子阅读画书一般,只执拗地反复阅读自己觉得有趣的情节,而自己不喜的章节,就草草略过。更多的时候还是有栖川在说,他会说很多人,很多事,有些与他自己有关,有些没有。但有时也会什么都不说,趴在床上打着瞌睡,这种时候有栖川总是离他很近,身体几乎要蜷缩在他的胸前。而对方身上的暖意仿佛有生命一般会慢慢从他的胸口扩散开,即使在冬天,身上也似乎没有那么冷了。
三千院想,带着暖意的海水,或许也不过如此了。
四月是个温暖的季节,而帝都的四月是盛开着樱花的。往年这个时候,街上最是热闹不过,神社的赏樱祭上总是充满了人,枝垂樱会连成成片的粉,雾一样的缠在枝头。
但今年略有不同。
街巷中的气氛有些紧张,街头依旧拥挤,只是全然没了赏樱时本该有的那份闲适与安宁。人们步伐匆匆,小声议论着,而有的院子家门紧闭,院内居住的人几乎足不出户。这种情况并非一天两天,而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时常能看见有葬礼,樱花落在黑色的棺木上,有些刺眼。有栖川没有仔细地阅读过报纸,但仅凭所见和与邻居和街巷中人的交谈,大概也能猜到遥远战局的状况。
——大正七十六年四月,帝国军对外战线全面退败,全军退守帝都。
街道上一时间多了很多军人,有些人有栖川甚至还留有印象,他们身上多少都带有战场归来后留下的痕迹,有普通的人类军士,也有人造半妖,而民众看见他们再没了之前带着崇敬与自豪的眼神,大多只是低头匆匆走开。一时间城内的物价也飞涨,街头上有了更多的募兵宣传,有些年轻人选择加入,有些人选择迁移到更加偏远远离战火的村庄去。都内的店铺和生意场所经营都趋于惨淡,唯有剧院和居酒屋的生意愈发红火。路上时常有醉汉在高谈阔论,但很快就被人拉到一旁捂住了嘴。街上的游警也多了起来,不过这对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依旧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有栖川原来还会劝说三千院随自己一同在街上走走,身上太过明显的妖异纹路他会用幻术帮他掩盖住。三千院通常并不情愿,但有时也会答应,他会穿起厚厚的外套和斗篷,带上手套,像个小孩子一样牵住有栖川的手,陪他走过几条街,买几件不起眼的小玩意,大多时候是纸笔和各色的和果子。有栖川也曾带他去过一家古董店里,却只是站在一旁和店长交谈几句,他们谈的很普通,连古董都未曾谈及。也曾路过被他弄坏过雨伞的伞店,他站在一旁,远远地道了歉,而店家似乎并不记得他是谁,只是对着他普通的笑了笑。然而隔过几个月后,再路过相同的地方时,却是已经关闭了。不过三千院现下已经很少出门,即便已经不像之前那般抗拒出行,满街的旧日同僚还是让他有些不自在。
三千院曾经问过有栖川,说,我是不是只是在逃避自己本该和他们一般的命运。
你认为你的命运是什么?他反问道。
三千院沉默了。
你并不是孤身一人。有栖川拉住他的手,温度顺着指尖逐渐传递过来。
……我并非没有想到过死亡这个字眼,也并不缺乏实施它的意志。我没有自救的能力,但我依然渴望能触碰到某些温暖的,让人安心的物体。一只会在我脚边打转的猫,一个愿意将糖果分给我的孩子,一个会笑着对我说欢迎回家的室友,一个许久不见会与我一同饮酒的同僚。我愿意和他们一起看明日的太阳,拾起我所剩不多的勇气与他们一起往前缓慢地迈出一步。
但我不确定他是否是那个人。
他拥有漫长的寿命,我想即便是我生命中出现过的所有人的年岁交叠起来,他的年龄也依旧不遑多让。他从未在某处过久的停留过,他看过我从未见过的山与川,见过远超出我理解范畴的人和事。他是个旅人,从神秘的异界而来,在无干他的生命里穿梭着,见证然后记录。
我反视自身,我是否有值得他所书的地方?我是否有值得他停留的意义?
我们生命的交集又会有多久?
他说与我曾有过“约定”,但我此刻却不记得与他约定过的详细内容。我无数次地试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得到却只是不成句的零散片段。
那是否意味着,约定完成后,他就会起身离开?
我惧怕得到问题的答案,比死亡更甚。
今夜的我依旧在深夜醒来,胸前充斥着暖意,他的头发软软地伏在我的胸前,我没有动作,害怕吵醒了他。
但我知道,梦总是会醒的。体型巨大的鲸鱼尚会搁浅,不属于水中世界的人类,总会被冲回岸边,等到潮水褪去,就只有被水浸透了的,冰凉的沙地。
从春到夏并没有经过太久,而冬天来得依旧很早,天气很快转凉了。
大正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国首相黑泽总一郎因病逝世,随后不久,帝国签订战败条约。
我想,是时候醒来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去看看外面的雪景,我说。好啊!他回我道,他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准备好了外套,说要陪着我去,还说新年才没过多久,想和我一起去神社参拜,顺便带我去见他一位老友。我答应了,他随我一同出了门。他在这条街上人缘很好,即便现下时局里人心不免惶惶,邻居对他依旧热情,他转过身和人聊天,放开了我的手,伸出双手接过对方递上的还散发着热气的点心。
我对他说想到附近转转,一个人走过了街巷转角,心里默默说了再见。
大正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失踪的零式前中尉,三千院 司,自首于四条河源町临时军务所,主动要求公开处刑。
——————————————————
咸了这么久,来补补结局。
还没结束,我不会这么轻易地结束……!(
*月岛与雨宫的忙碌之旅。
*可能没什么意义的提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木村=秋叶苍海,第二段初春时候的事情就发生在秋叶潜伏于SPST期间,来源见此: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9270/
*月岛知道白川是半妖只是因为对半妖的气息很熟悉,加上白川的瞳色本身也比较特殊。
*文笔很一般,伏笔啊剧情啊这些,希望容易理解就好。
*修改可能,如有OOC也可敲我,感谢借用角色给我的大家。
【大正七十六年 夏末 Gleiphir侦探事务所】
明明是热闹的季节,商店街上却有点冷清。仍然在忙碌的人们情绪不像过去那样高昂,只有偶尔从不知哪家铺子里传出的孩子们的说话声,给这条街道带来一点生气。跟着名片上的门牌号,穿过一楼的商铺,经过一段老旧的走廊,月岛梓和雨宫礼治站在一扇非常普通的木门前。听到敲门声后来应门的,是一名瞳色浅蓝的年长者。
“您好,请问这里是Gleiphir侦探事务所吗?”
“啊,没错,你们是?”
“敝姓月岛,这位是雨宫先生。我们是通过木村先生的介绍找来这里的。”
“木村?”年长者沉思了一下,回过头朝门里大声询问了起来:“让治,你知道木村嘛?”
几秒钟后,黑发黑眼的男性来邀请他们进入了房间。
“我是私人侦探,铃原让治,这位是我的助手白川。”铃原笑着介绍了起来。与此同时白川端着泡好的茶走了过来。这两人年纪相近,看起来共同相处了很久,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股默契。
月岛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摊在桌上的,有最新的报纸和杂志,还有一些笔记,房间里目光所及,尽是些书,杂志,本子之类。空气中漂浮着木质与书页的香气。随着白川的走动,微小的尘埃在光线里搅动着。看起来是一个相当令人舒适和安心的场所。
父亲听说她要去这家侦探社,一大早塞给了她一个食盒。“铃原侦探啊,他喜欢吃和菓子,当年在我们家光占地方不消费,虽然平时吵吵闹闹的,但还算是个好人,你就尽情拜托他吧。 ”月岛将食盒放在了桌上,向铃原讲述了自己的来意。
【大正七十六年 初春 SPST研究院主楼二楼走廊】
木村写完最后几笔,合上了笔记本。笔记中密密麻麻记录着早上与泉清里教授讨论的内容。这之后是一些设备的确认工作。
他向二楼尽头的设备间走去。研究员们这个时候都还在各自忙碌着。他发誓不是故意去听什么,但是这争执的声音在空旷的长走廊里回荡,哪怕不想听也直直地灌进了耳朵里。木村放缓了脚步,靠近声音的来源——其实只是顺路而已——他听到有个女声在强调几个关键字“妖力影响”,“抑制剂”,还有一些长句子因为语速很快而难以听清。而另一方是一个低沉的男声,只是淡然地说着“实验室最近没有那么空”,“物资申请和批准需要更多时间”等等令人无从着力反击的回应。最后,以女声的“我会去想办法的,到时候请不要加以妨碍。”结束了对话,房门忽的打开,又被甩上。一个怒气冲冲的身影快速经过了木村的身边。
“那个。”木村在一眨眼之间就决定了要叫住这位女性。
“怎么?”女性在回头时依然带着低气压,在看到木村后才整理了一下情绪,努力平复下来。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听,但是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地方,还请不吝开口。”木村尽量温和地笑了,看起来是一名非常值得信赖的后勤工作人员。
“不,我才应该说抱歉……”女性仔细看了看木村的脸,“我想起来了,你是最近在泉老师那边帮忙的……木村先生?”
“承蒙您还记得,月岛小姐。”
“您的记性也不错。”
两人客套了一番,将谈话的场所移到了月岛的办公室。
“这么说,有一些特殊的材料需要准备……”木村皱了皱眉。
“是的,无法轻易在外面找到,我会尽量从其他的渠道寻找的。多谢木村先生的好意了。”
“原本我是没有资格多问的,不过,这是用于制造非常重要的药剂吗?啊,不方便的话拒绝回答也没有问题的。”
“至少我认为是的。只是作用的话说说也无妨,这种药剂可以使实验体状况维持稳定,抑制很多种副作用,但它也有可能削弱和限制某种情况下的作战能力,所以上头一直都不怎么支持。”
“的确对于战争来说可能不太被考虑呢……”木村耸耸肩,“但是这样的研究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不管怎样我都会尽力去做的。”
“虽然我无法帮上什么,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从随身的小包中翻出一张名片:“可以找这位侦探先生,是一位乍看之下不起眼,但其实相当靠谱的人,也认识很多能人异士,相信他对于你的想法会很有兴趣的。”
这样的事情也可以确认吗?侦探和研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带着疑惑,月岛梓收下了名为“铃原让治”的名片,之后两人便道别后各自继续忙碌了。
【大正七十六年 夏末秋初 Gleiphir侦探事务所】
距离上次从侦探事务所出来后不久,月岛梓便收到了铃原让治的联络。
此时她与约见之人正在事务所三楼的房间内。
“又见面了,月岛小姐。”青年一如之前在研究所时的模样,温和地笑着。
月岛梓看着眼前之人,单刀直入地问道:“木村先生,龙姬还好吗?”
“她很好,不用担心。”提到龙姬,木村的表情有些冷了下来。
月岛梓花了一整个下午解释了包括秘术泄露、妖力暴走和抑制剂的事情,木村的表情始终凝重而认真。楼下的房间里铃原让治和白川透安然地看书聊天,时不时和陪同月岛一起来的雨宫礼治聊上几句。傍晚时刻,铃原下厨做了一整桌饭菜,这才上楼喊两人。
“龙姬会需要这些的。有一些研究我也需要她的协助,这个忙你会乐意帮的,是吗?”铃原下楼后,月岛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觉得有些疲惫,便决定暂时停止这场科普会议先下楼蹭个饭。
“我会好好考虑的。”说罢,木村也安然地走下楼。
饭桌上的气氛还算不错,吃到热烈的时候,白川突然抖出了毛绒绒的耳朵,只是一下便收了回去。铃原轻轻拍了他一下。在这个特别时刻,半妖们都应该非常小心翼翼。
月岛梓看了一眼同样毫无反应的木村后,对着白川说道:“那个,白川先生,您可以放松……我知道您是半妖。我不会做对您不利的事情。”
“真的吗,哎呀,其实没什么的,本来就应该……沉稳一点。”白川看了一眼铃原,老实地收着耳朵,埋头吃饭。
“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铃原先生帮忙。”
铃原收回了看着白川的眼神,问道:“你尽管说。”
“您一定知道无铭会吧。”
铃原让治和木村同时作出了反应。
“可能只是我比较乐观,但现在有让半妖停止半妖化,甚至恢复到人类的方法。我需要无铭会的帮忙将之扩展开来,才能帮到更多的人。”
“人造半妖呢?”
“可以抑制妖力影响,控制残留的药物副作用。”
“这可真是……”铃原思索了一下,又看了看木村的反应,便应承了下来,“我想应该没问题。我会找到联络人的。”
临走前,月岛梓递给铃原让治一份名单,说道:“这是我的私人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帮我搜索一下这上面的人的消息,不论……是怎样的消息。报酬由你决定就行。”
铃原接过了名单道:“我会尽力的。”
雨宫瞥了一眼,那纸上写着熟悉的名字,泉清里,鹫塚鸠羽,后面的因为铃原将纸折叠了起来而没能看到。
【大正七十六年 夏末秋初 Gleiphir侦探事务所楼下】
走出侦探事务所,月岛深呼吸了一下,表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看起来还挺顺利的,雨宫前辈,谢谢你陪我。”
“我说,”雨宫突然停了下来。
月岛也接着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什么?”
“差不多该把敬语去掉了吧。SPST都已经不存在了。”
“但前辈还是比我年长啊。”月岛思考了一下,“唔……雨宫先……先生?”
“嗯……就先从这个称呼开始吧。”雨宫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月岛。”
“……嗯。”
两人并肩走在深夜的小路上,小声讨论着抑制剂后续制作的细节,见到无铭会的接头人之后要如何进行他们发放抑制剂的计划,还有建议当初受到秘术扩散影响的半妖暂时远离帝都的提议等等后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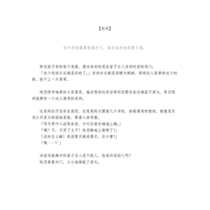





【填一勺土,和【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4761/】有點關係……】
“阿菊,阿菊姊姊!那位先生來了!”
女子雪白色的臉龐映在明晃晃的鏡面上,抹了胭脂的食指正點向櫻桃小口,話音未落卻凝在半空中,一雙烏黑的眼睛循聲望了過去,看向急急忙忙趕過來的禿。黑得發亮的云髻下裸露出的琥珀色頸子乾乾淨淨,遠比臉上厚重濃膩的粉脂來得可愛,生出一種潔淨的情色。
“叫他在外面等著吧。”阿菊細細用食指將那片艷紅塗抹乾淨。傳話的小童得到答復,便又踩著不停發出吧嗒聲響的拖鞋跑了出去。阿菊即放下那慢條斯理的做派,匆匆將妝畫完,之後,卻又反復審視起鏡中的面容,拖著時間。到鏡前的蠟燭成了一串凝固在淺碟上的越橘時,阿菊才慢悠悠地拉開紙門。方才一直在房間內為阿菊梳妝、跟在她身後的禿提起和服過長的下擺,幾步並做一步跟著高出自己幾頭的藝妓。
阿菊原本是以潑辣文明四里的藝妓,有著酒豪美人的說法——起先這名聲還為人所不齒,可卻慢慢傳開,甚至有了不少為了喝倒阿菊而不惜砸下重金的客人前來,不知什麼時候起這讓藝妓少了嫵媚的缺點也就成了招攬客人的優點。
除卻酒豪,這位年輕藝妓是位母老虎的說法要傳得更遠。
明治以前,吉原不可帶刀的規則便已默認,雖說如此,卻總有客人犯下此事,更有被丈夫拋棄的怨婦會來找人尋仇;前些日子,便有位女子持刀害人,結果卻被阿菊以空手奪下刀刃。從此,母老虎的名聲越傳越遠,甚至蓋過了原本的酒豪稱號。
就是這樣一位女性,最近卻不知怎麼軟化了下來。
旁人不知緣故,一直處在阿菊身旁、年幼的禿卻看得清楚。這位素日豪邁的姊姊之所以會變成這樣,都是在見過那位落語先生之後。
那落語先生的名字,年幼的女童已經記不清楚,只記得一張圓闊寬大的臉,好像客人帶來的玩偶一樣滑稽;那人生得臂膀粗壯,身材高大,輕易就能將自己高高舉起來;談吐間則帶著股市儈氣,來青樓的男人,有大半是想從游女那兒奪回僅存的自豪與榮譽感,這落語先生也不例外,與藝妓阿菊相談時,總是帶著半炫耀的口吻,提起“女人家不懂”的大事。可令女童不解的是,阿菊姊姊面對那男人,卻總是一臉微笑地聽著。莫非那人是什麼厲害人物嗎。女童想著,盯著手中紋路華麗的和服愣神。現在要是不問,接下來整夜都要好奇了。這麼一想,禿就又鼓起勇氣,輕聲問道:
“阿菊姊姊……”
“怎麼?”藝妓隨口答著,並不回頭,腳步也不曾慢下。
禿急切切地跟著,將和服兜在懷裡:“那位先生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能讓您這麼傷心呢?”她等著阿菊的反應,對方似是驚訝了一番,可頭上的簪子卻連擺動都沒有一下。
“你這孩子,人小鬼大的……真機靈。”阿菊側過身子,摸了把女童的臉,後者驚得瞇起眼,得到溫柔的撫摸後,也就不再害怕,“男女情愛麼,總是這樣,男人一個個都是傻瓜,不出些手段留住是沒辦法的……”
“那落語先生,也是傻瓜咯?”禿問道。
“可不是,傻瓜中的傻瓜,每次來都是厚禮相贈……要是遇到別的藝妓,才不會那麼簡單放跑他呢,肯定是好好敲一筆。”阿菊道。
“我還以為阿菊姊姊怠慢那落語先生,是因為……”
“若是他來了,我就急衝衝地過去,也未免太掉價了。你雖年幼但也記好,不能人家說什麼便應。這樣,才能使自己在男人心裡留下地位。”阿菊又說,腳步仍是慢吞吞地。禿聽後,連忙點頭,已經懂了一半,隨後又像往常般說了些招人喜歡的話,逗得年長藝妓的臉上浮現出微笑,兩人才停在客人等候的房間。那落語先生在房間裡,桌上的茶杯空了一半,想來也等了段時間。
“阿菊小姐,你來啦。請坐請坐。”男人拍了拍大腿,講得好像自己才是此地的主人一般。阿菊也並不見外地坐了下去,禿卻分明從這位潑辣姊姊的眼裡看到熱戀中女子才有的嬌媚。
罷啦,罷啦,就讓他們兩位大人迷惑去吧。禿想著,悄無聲息地退了出去。
吉原春夜,三味線弦不絕於耳。
【哎,我很喜歡有些男女關係中,雙方都覺得對方是傻,但還是挺喜歡彼此的那種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