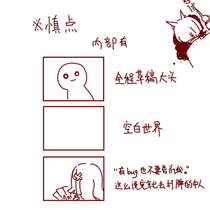*【终章】进行中 时间:5月16日-6月15日*
通过审核的玩家可以加入交流群374787588,验证填写自己的【角色名字】。
距离【百年法案】之后的三十余年之后,发生了【天狐暗杀事件】,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暴露出了一个军方研究“人造半妖”的组织。在最近几年中由于人类世界的战争愈演愈烈,军方曾多次向天狐提出援助(主要是请求妖异参与人类战争)都被拒绝。这次事件的原因可以推测为“以人类手段进行某种示威”
重伤清醒过来的天狐,认为“人造的半妖”只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战争兵器,是一种悲哀的存在,以“给予他们慈悲”为名对人造半妖进行抹杀行动。
写完了之后发现还是适合投第二章……真是进度缓慢。
因为涉及教官部分的内幕所以不要脸地圈一下教官>w<
还有几张插图没放,之后有机会排版重发吧Q-Q
--------------------------------正文-------------------------
- 蝉时雨 -
“♪鐘がぁ~ ゴンとなりゃぁ
上げ潮ぉ、 南さ
カラスがパッと出りゃ コラサノサ
骨がある、サーイサイ
そら、スチャラカチャンたらスチャラカチャン”
混着沙沙的电波杂音,古典落语连珠炮般快速的对话声中突然响起一阵荒腔走板的民间小调。年轻的噺家迷亭信乐用他略带粗哑的嗓音,生动地诠释着农夫八五郎妄想着钓上美人骨头时色迷心窍的可笑模样。虽没有寄席中表演这一段时观众例行的应合声,多少失了些乐趣,但这段小调还是被他唱得有滋有味,连音量都不由得大了几分。
但正是这声量些微的提高,让本已有些睡意朦胧的心又忽然睁开了眼睛。压下惊醒时心脏那阵不自然地悸动,她深呼吸了几次,在床边摸索了一下,翻出半压在枕头下边的便携式的收音机。
“……以上,是由迷亭信乐为您带来的骨つり,下面是由真打春风亭八云先生的死神……”没等主持人讲完,心就按掉了收音机的电源,坐起身将它放到一旁的矮桌上。
身旁龙姬的床铺上被铺整齐地透不出一丝曾有人居住的痕迹。四月对民间部分开放了消息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龙姬都会去安昙野家小住几日。开始心还会跟着一起,渐渐地她便不再陪同。俊臣先生目不能视,她又口不能言,龙姬又是个看不懂人情世故的,在一起时总不免交流困难,种种尴尬。现在的龙姬早就不再是那个处处需要自己跟随的不安定因子。说来可笑,龙姬不在的时候,石野心骤然发现自己竟是有些依赖上了龙姬的陪伴。就比如入夏以来,没有她在身边的晚上,不知怎的就是无法入睡。
即使隔着玻璃窗,外面的蝉声依然透过缝隙挤进耳畔,彻夜不宁。夏天闷热的空气混着暧昧不明的蝉声,在莫名空荡的房间中酝酿成了沉甸甸的烦躁感。屋内的老式台钟咔哒咔哒的跳动声都显得吵耳起来。
心放弃般地长呼了一口气,起身打开了窗。蝉鸣的浪潮同泥土味的晚风一起涌进屋内,总算是稍稍打破了些闷热。看着窗外不远处那个小公园,突然想起前几日听到的琴声和那位话语间都是荒诞胡言的高个子落语家。
信乐先生转交的“仙人花束”还放在写字台上,虽然他还特地平分了两半送给她们,却不知最终还是打乱了插在了一个花瓶里面。过去常常去后山的花海看花,但是鲜少有将其带回装饰在房间中的时候。她总觉得离开了土壤和枝干的时刻,就是花朵死亡的时刻。就算将其矫饰成诱人的模样放置于精美瓶中,也无法掩盖它们已经失去生命的事实。不过别人赠予的花束总不好轻易丢弃,那日将花束带回后特地找月岛借来花瓶,将看起来已经有些萎靡干瘪的花束摆了进去。谁知第二天再看的时候,几个已经垂下去了的花茎竟然挺直了腰杆,还未盛开的花苞竟也有了些绽放的趋势。
*
—— 哪怕是如此弱小的生命,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有着莫名地倔强。
她走到桌前又端详了一下那朵已经完全绽放开的波斯菊。拿起笔,接着昨天写下的句子继续写着。
—— 闲话少叙,这次来信除了归还之前的发饰还有一事想拜托秋叶先生。
前几日店门前挂着的那串火箸风铃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日没有与您详说,其实我与那样的风铃也有几分缘分。
记得初进道场寄宿时年纪尚幼,夜不成眠。老师便从自己的书房摘了别人赠与的铁箸风铃悬于我卧房窗前。听着它的清响,不知不觉就能入梦。哪怕是没有风的夜晚,等候着它响起的时刻也会让人心情平静。直到现在,想起那个声音似乎闭上眼还能看到那开着大片蓟草的道场后院。手心中仿佛还握着那柄因汗水湿滑需要紧紧握住才不会脱手的沉重竹刀。都有些怀念起练习过后冰水镇过的撒着盐的红色瓜壤的清香来了。———
不知不觉间,纸张上的字迹已经排列到了边缘。心简单收了下尾,表达了下想要邮购那组风铃的意愿。又草草读过一遍之后,她将信纸折叠了起来放进装了一枚樱花发饰而显得有些鼓囊囊的信封中。
万川阁 秋叶苍海 敬启。
这是大正七十五年这一年,二人频繁的信件往来中的第一封,也是无关龙姬的唯一一封。
那个时候石野心和秋叶苍海还都不知道龙姬对于对方来说是怎样的存在。但心隐约有种预感,这个男人的再次出现意味着终将到来的改变。对于龙姬来说,这改变或许会是机会,但也或许,会是灾难。
- 墓菊 -
怀中那捧白菊正散发着微苦的香,混合着冬日清晨刺凉的雾气冲进山犬半妖过度敏感的鼻腔。她皱了皱鼻子,将捧着花束的手放低了一些。花期将过,这家花店的秋菊却盛开得格外灿烂。它们肆无忌惮地朝四面八方伸展着细弱的花瓣。明明是献给逝者的花,却活的如此顽强。
“为什么扫墓时候要用菊花呢?”
年幼的心曾这样问起。正在往墓碑上洒水的东山老师放下水舀,拿起一支盛放的白菊递给心。
“这是因为菊花不会凋零,它象征着亲人对逝者长久的思念。”
那年秋天,十一岁的石野心偷偷地把那支白菊养在了自己的小房间里,想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不会凋零。白菊一日日地失去了水分,变得干枯消瘦。曾经白嫩的花瓣蜷缩成枯黄的一团乱絮,似乎稍稍碰触就会碎裂一地。虽然确实没有像樱花或者海棠那样散落一地花瓣。
但无疑也是谢了。
所以,我们对逝者的思念也是如此吧。不会消失,不会凋落,只会不断地缩小,干涩,最后变成心里一团模糊的惆怅吧。
*
杂草在墓碑间肆意生长,七年的时间褪去了碑文的颜色,藤田家利人和井源家有介的两个窄小墓碑并立在一起,石台的中间还摆着去年的几朵残菊。
心还记得利人喜欢抽洋烟,却没有钱买,总是去找人打赌,把津贴输得精光之后还四处借钱。也记得和他一个寮出身的井源总是一脸嫌弃地拒绝他层出不穷的借钱理由。可不抽烟的他身上却经常装着一包香烟。在利人又在他耳边聒噪起来的时候,偷偷摸出一根塞到他那张跑起火车来无边无际的嘴里。
记得他们两个进值班室时带起的那股焦糊的烟草味,还有利人嘴里似乎总不会重样的荤腔笑话。但那两张脸已经模糊,她甚至想不起记忆里模糊的那副圆形的铜框眼镜到底戴在他们中哪一个的脸上,是他们,还是那个笨嘴拙舌的好人田中呢?
清水洒在整理一新的墓碑上,字迹从尘沙中再次浮现出来。脑海中模糊了昔人容貌的灰幕却没有被洗去半分,只有那几个横躺在血泊中的背影格外清晰。手腕的伤将将愈合,还使不上力气。她有些吃力地双手拎起木桶,向墓地更深处走去。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了故人。
只比他大上几天,却一直坚持要她喊师兄的比良野健次。竹刀被他打落时笑眯眯地说再来一次的样子,离开道场去军校报道的那天,偷偷抹泪的样子。还有七年前的那天,双臂颤抖着也要冲到老师前面,却被锋利前肢贯穿的样子。这段回忆几乎每次来这里时都会重复一遍,只是随着立场的变化,那一日心中对spst和龙姬愤怒已经和其他的那些面孔们一同褪去了颜色,只剩下一种无所适从,无法言喻的悲哀。
然而这次却不尽相同,脑中比良野和常世妖狐幻境中被刺穿的龙姬重叠到了一起。
心楞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那时看到这般幻觉或许不仅仅是出于恐惧,她心底的某个角落,似乎期待着这样的情景发生。心脏猛地一颤,手上不由地多用了几分力气。腕上一阵突如其来的痛楚,臂间夹着的几支白菊顿时散落一地,回过神蹲下身捡拾的时候她才发现手心已然一片通红。
正当她伸手探向最后一支花时,一双锃亮的军靴在此时不期然地进入了她的视野。
*
“原来之前花是你放的。”留着胡子的男性军人皱了下眉头,捡起地上那支白菊后随手扔到一旁。他转身整理健次墓前新换上的一捧明黄色的花束。
“还以为你脑子里只有那无情无义的实验品,早就不记得他们这些没有价值的牺牲者了。”
心咬了下嘴唇,垂着眼帘慢慢摇了摇头,不知是在否定哪一部分,无情无义,不记得,还是没有价值。
比良野健太没有回头,他擦拭完墓碑上的字迹,将脏污的抹布随手扔进一只水桶里,又舀出另一桶清水淋在上面。都做完之后他也没有回身,而是席地而坐,对着墓地中沉睡着的弟弟回忆起了当年在道场时的日子,权当身边的石野心不存在一般。但她清楚这些昔日旧事,多少也是说给她听的。
比良野兄弟是心在东山的道场时最亲近的人。兄弟两人父母是道场师范东山年轻时的战友。夫妇二人牺牲的早,留下年幼的兄弟俩无人照顾便由东山接回了道场,视如己出。健太比心大七岁,健次和她的年龄差不多。刚来道场时,几乎只有他们两个小孩子。心的父母那时还在世,不过也已经被派去了海外战场做后方的铁道营建工作,家书都随着战况断断续续地,经常三五个月也没有一封。每逢年节的时候,道场里的弟子们纷纷回家与家人相聚,总是只留下他们四个。中秋的一起看着月亮吃月见团子,大晦日东山老师亲自下厨做的手打荞麦面,还有正月的年糕和端午的柏饼,年年岁岁皆是如此。
直到健太上了前线,心和健次一起进了士官学校。
当他升为中佐,从前线调回帝都的陆军参谋部调查厅时。这间曾被称为家的东山道场中,只剩下从研究所告老退役的东山老师一人带着几个捡来的孤儿。健次死了,凶手不但没有得到惩罚反成了新设部队的王牌,一路春风得意。而一直被他当作妹妹看待的心竟然选择站在凶手的一边,成为了‘它们’中的一个。
他始终不能理解心的选择,也从未打算原谅她的背叛。可是,一想到再过不久,她也将被派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冲杀,多半葬身他乡,终不能再相见,比良野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忍。
“东山老师近些日子身体不大好,说要把手打荞麦面的秘诀传给我,以后就由我来做给大家吃。他也真是老糊涂了,道场里那些年轻人多半都上了战场,战事还在扩大,现在才十四岁的凉太和小光马上也要去服兵役。到了明年,哪里还会有什么大家……”说到这里,比良野沉默了半晌,重新戴上了捏在手中的军帽,站起身来。
“今年过年也回来吧,趁还见得到。”
说罢径直离开了墓园,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 大晦日 -
时近半夜,年近六十的东山老师进来染了些寒症,身体不适需要先一步回房休息,久违的家宴结束地比往年都要仓促。两个小孩发出了抗议,似乎是先生说好了新年钟声响起时陪二人一起放烟火。心听着远处房间中传过来老师一阵阵地咳嗽声,还没等她做点什么劝阻孩子们,比良野已经一手拎着一个的衣领直接扔进了二人的房间。
心也笑笑,跟着回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
屋里充满着令人怀念的熟悉味道。看到铺好的床铺,忙碌了一天久违的家事,却比训练了一天还要疲累。心连腰带都懒得除下,孩子气地一下扑倒在被褥上。榻榻米的竹香混着沁入了中那股木造屋特有的陈年松木香包裹着心,久违地将所有的不安和警惕都抛诸脑后,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十几岁时一般,带着幸福的满腹感,闭上眼睛脑子里面竟然空空荡荡,下一秒就已经睡着。
过了不知道多久,朦胧间被隔壁的少年们透过薄薄的樟子门传出的细细碎碎的嬉笑声弄醒。看来是还没有压下玩心,决定一会儿等大人们都睡了,去仓库偷了烟火带出去玩,两人聊得开心,音量不觉稍稍大了些。果不其然,一声男性威严的轻咳直接在二人门口响起。
一时间,整个宅子都安静了,只能听到后院盈满的响竹的敲击声。
似乎有些太安静了,她睁开眼睛,盯着天井。片刻后,她听到门外细不可闻的脚步声,此人走得极为小心,仔细分辨似乎是军队中常见的潜行步法。心顿时脑内警铃大作,第一反应是有人暗中潜入宅邸。她迅速取下腿上绑着的军用短刀,小心地蹲伏在门口观察着走廊中的异动。
脚步声经过她门前时,一阵轻微的香气被她异常灵敏的嗅觉捕捉到,竟是荞麦面的味道。
比良野?
走廊另一端只有东山老师的卧房。若是找先生有事何必半夜三更如此鬼鬼祟祟。心皱起眉头决定跟上去看看。
“……她们出发了?”东山的声音有些轻微的沙哑,但比起晚餐时明显多了几分底气,丝毫不见方才苍老衰弱的迹象。
“刚接到密报,‘龙’带着一个实验品小队已经出发前往三条巷。‘那边’已经准备好收网,她这回一定逃不掉。”男人压低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很久没有听到龙姬被如此称呼,比良野的语气阴冷,‘那边’指的会是什么她已经猜到。眼前似乎闪过高大犬妖扬起的利爪,被士兵搀扶着的三千元司中尉血迹斑斑的上衣,狐妖劈斩下的妖刀和龙姬被刺穿的惨状。
*
“死伤不论,回收实验体‘龙’。”五年前的冬天,东山老师转达任务时的表情冷峻,似乎笃定龙姬不会活着回来。之后二人重伤归队,老师竟一次都未来探视,痊愈之后心才得到东山告病辞职回家养老的消息。现在想来,恐怕那次围捕命令从一开始就不是下给龙姬一个人的。东山老师擅自更改了任务细节,他希望龙姬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一个人去送死。失败后称病辞职,龙姬神智不若常人,便一直没有人质疑任务下达时的细节。
三千院被疑叛军押往调查厅进行审问前恰巧有妖异将其劫走,以心对三千院中尉的了解,他不像是会出卖军队情报的人。那时得知三千院押送时间的除零式赤见中佐,高河少佐之外便只有调查厅的相关人士。如果信息泄露方需要一个替罪羊,那么将三千院的信息透露给祸津鬼无疑是最便捷的方式。若比良野归来后就和东山老师联手想要向龙姬和spst复仇,那么研究员和改造实验的消息,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内部泄露。调查组没有着手过这个方向,很容易怀疑到他人身上。那之后比良野只需要顺水推舟。
这次新年若不是比良野邀请回道场一起过节,按章程本该轮到心和龙姬一起驻守部队。五年前的误传任务,让心迟些出发多半也是为了保她安全。比良野虽怪罪她过度袒护龙姬,老师也无法理解她自愿改造的决定,却从未有过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牵连心的想法。
但那又如何呢,为了报复spst,为了向杀死健次的凶手复仇,竟不惜将整个部队置于危险的境地。报社事件之后,很多士兵接连遇袭,鸠身负重伤至今不能行动,久远和茉莉也生死不明。他们进入零式不过一年,和七年前的事件没有半点关系。这样的复仇,即使达成目的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结局,难道健次就会心安吗。
手中军刀,本为护国卫道的利器。东山老师交给她的那天,质疑无法担此重任的人是自己。而今,却是将刀交给她的恩师成了悖道叛军之人。
老师和健太的做法心无法认同,却也没有立场去阻止。龙姬面临危险,可如今负伤无法持枪的自己连助她战斗的能力都所剩无几。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劝龙姬迅速脱离战斗,逃过这次合围再做打算。心捏紧了手中的字条和短刀,手腕处未愈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寒风卷着零星的雪花,灌进她单薄的衣衫。为久违的节庆特地选择的白底红梅绘羽沾染着奔跑间飞溅起的泥雪,整洁清隽的纹色荡然无存。相似的风雪,相似的无力感,心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的那天。
东山道场和三条巷之间不足千米的距离。
却漫长得比这冰雪还令人心寒。
-END-
————————————————————
相关剧情:
-蝉时雨-
交流会后清晨偶遇迷亭: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5746/
还给秋叶的发饰的故事: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4973/
与秋叶老板的后期通信: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8117/ target='blank'>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8117/
-墓菊-
七年前龙姬暴走,警卫队全灭: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0829/
扫墓前几日营救三千院,手腕受伤,看到龙姬死亡的幻觉。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6589/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6593/
-大晦日-
五年前龙姬单挑仓松重伤: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0170/
三千院被怀疑和调查: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4962/
后续剧情顺序:
除夕当晚(龙姬视角)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7353/
除夕当晚(秋叶视角)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7355/
除夕当晚(查视角)
待更
除夕当晚及后续(心及当间视角)
第三章 赤い鬼 待更
数日后(秋叶视角):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8117/ target='blank'>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8117/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4962/
接受他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是一个非常玄妙的过程。
“三千院教官啊,虽然长得很凶,事实上也很凶……但是买过糖心蛋给我所以其实还挺温柔的吧?”
“很冷淡啊,明明才是二十多岁的人,但是从来不会跟我们一起喝酒呢。”
“不太好亲近呢……不过我有见过他在操场角落喂野猫哎。”
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形象塑造总是出于一件单一并且片面的印象,而这印象则会成为唯一的标签贯穿相识始终。即便有再多的“然后”发生,在提及这个人时,所复述的也大多是第一次的相遇。而在那之后,即便是再惊心动魄,也不过是对第一印象的二度辅证。
“我叫高河,算是你的同期,你做出这样的事,不但上面吃了一惊,也蛮出乎我的意料的。不过无论你有什么解释,都等见到中佐再说明吧。请跟我走,三千院中尉。”
三千院只觉得外面的阳光十分刺眼,同时在意着,自己右眼角处的黑色纹路究竟蔓延至了何处。太过在意,以至于高河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目的也好,理由也罢,统统都没放在心上。
像他人会如何看待自己这种问题,对于连自我认知都困惑不清的三千院来说,早没有任何意义。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
高河自己也是人造半妖,和身旁的三千院一样。也正是由于此,考虑到三千院在被逮捕时可能会有的反抗行为,才会派他这个中佐的直系下属来逮捕。
人在发生突如其来的状况时,多少都会做出一点反抗的。即便是无辜的人在街上突然被抓住,自我防卫本能机制就会发动,像是逃跑,大声呼救,或者针对抓捕行为的暴力行为,之类的。而人造半妖的特异性无疑强化了这份本能的强度,比如像三千院——在完成试验时的强度测试中,厚达十五公分的高强度混凝土墙壁在他的挥击之下和一块普通的塑料板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不是由于半妖化后的身体各项机能会大幅衰落,应该也早就跟自己一样,能升到上尉的官职了吧,高河想。但他带走三千院的时候,对方却出离地冷静,换个方式形容,该说是漠不关心。机械性地听从了他的话,身体跟随着指示行动,而到现在为止,除了在一开始对高河的言语发表了一下疑问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发出任何声音。
如果不是呼吸声,车里沉寂的气氛几乎让高河以为他带来的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幻象。
这太异常了。
高河印象中的三千院,虽然不是个话多的人,但至少也不该是面前这幅连视线都不知落在何处的样子。车子的方向也越来越靠近位于城郊的调查厅,恰逢途中路过荫蔽的一片树林。十二月即便有阳光也是冷的,被掉光树叶的枝杈这么一遮,车里车外,空气都近于冰点。
“我说……三千院君,你真的,做了那样的事吗?”
回复高河的,不是沉默,也不是三千院,而是锐物撞击车体的巨大声响,而在下一秒,视野所及的事物就上下倒转了过来,车体在空中翻落的失重感让高河也有些目眩,头脑来不及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好在身体足够机敏,鳞片迅速地爬上了脸颊,他拉住三千院,白骨的羽翼直直向后张开,撞开了车顶。
“这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墨色羽翼的巨大阴影遮蔽住视线,连天空都一同消失不见。
——下午六时——
三千院和高河本应在今天下午一同到达这里。
考虑到三千院的反抗和对其行为的压制,时间拖的久一点也不意外,但距离高河离开已经足足有五个小时,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未免太久了。能想到的原因或许是三千院在途中逃脱,但是赤见的桌上也并没收到类似的紧急通报。自己的下属和三千院,就如同一齐凭空消失了一般。
赤见叫来下属,让他带一小队人,顺着路找找看,能不能打听到发生了什么。
一个是自己心腹的下属,一个是自己曾经珍重的学生。即便三千院有嫌疑,这嫌疑也要问清楚再算,无论如何,现在都不该是出现意外的时机。
只希望不要事与愿违。
——下午八时——
三千院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在被气浪掀开的车子摔落在地之前,似乎有人把他一同从车内拽了出来。但紧接着就被更大的冲力打落在了地面。凭借着多年军人的生涯,落地时的卸力翻滚是刻在骨子里事项,这才免于受伤。只是还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尝试将实现聚焦于眼前的事物上,后脑传来的重击使意识再度趋于涣散。
在那一刻,三千院居然觉得这样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眼中残留的事物是可怖地缠绕住天空的枝杈,黑色的,灰色的,支离破碎,不规则地拼接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撕咬。明明只是最简明不过的两个颜色,依旧交融成一团,难以名状。
如果能令这样污浊的存在消失就好了——
包括自己。
——???——
三千院曾经是个很骄傲的人。
骄傲这个用词或许会不太恰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十七岁的三千院,带着从收养家中独立而出的喜悦,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带着责任感与梦想,加入了帝国军。
“如果能踏遍所有想去的地方,那么即使战死在何处也不会后悔。”不止一次,他是这样和他的朋友讲的。被分派去各地通常不是项讨喜的工作,因为各地辗转则意味着分离,与家人,与亲人,与当地建立的短暂联系,都会渐渐淡化下去,终至消失不见。但三千院却对此兴致勃勃,对他而言,只是踏在从未接触过的土地上,感受着相异的风,就足以令他开心起来。而他也一直足够优秀,优秀到无论身处何处,都是被人依靠着的。
一个可靠并且有趣的人,这是大多数过去的人对三千院的评价。
然而二十三岁时的一场战争却将一切都转变了。
他不再是人类。
从任何一方的定义来看,他都无法将自己归属到人的范畴里去。右眼无法辨识色彩,无法控制的力道,自手腕处开始逐渐蔓延攀爬而上的黑色虎纹,逐步失去体温调节机能的皮肤,哪怕仅凭一项,就都是足以被人称之为怪物的程度。
他想,起码我还活着,只要我自己保有自己人的本心就好。
但腐朽是从内里开始的,等他注意到的时候,早就被蛀得一干二净,徒余一具空壳而已。
——身体的痛感将他唤醒了。
右颊处血流下的触感温热,而冰凉的尖状物划过眼角,直至下颌。简单的划伤带来的疼痛却比想象中更令人难以忍受,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播种在伤口里,吸食着他的生命力,奋力向皮肤的深处生长。他难耐地皱了皱眉,换得的却是不知源于何处的低低笑声。
“军队的小哥,不要怕,在下只是想问一点情报。关于你,以及你是从何而来的,之类的。”
三千院没能理解当下的状况,但四肢被大片黏稠的网状物粘连住,连想要抬下手腕都无法做到,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抓入了女郎蜘蛛的巢穴一般。
“快点说出来比较轻松,虽然抓你来的不是在下,不过在下,耐性也很有限。”
——是过了多长的时间呢。
钝痛折磨着他的神经,三千院的双眼无法视物,只能感受的到身体各处传来的被啃食一般的痛感。女郎蜘蛛的毒素蔓延的很快,虽然并不致命,但他的意识已然有点恍惚,让他无暇分析身周的状况。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或者没有。被改造过的部分似乎与侵入体内的毒素起了对抗心,喧闹着要与之一绝胜负。右半身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麻木的就连右耳都丧失了分辨声音的能力。
接收到的声响来源是更远的地方。
无法接触到地面,无法视物,声感逐步被剥夺,三千院觉得连自己的存在都要消失于此。不知怎的,他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住过的孤儿院,中午偷偷跑出去被发现就会被关进间连窗子都没有的储藏室罚站,一站就是一下午,直到老师过来叫他放他出去之前,什么都不能做,连坐下都不被允许。
黑色是缺乏生气的颜色。
但最可怕的,是连自己的身体,都被卷入黑暗之中,然后消失不见。
——杀了我吧。
像是在回应他的呼唤一般,腹部的一阵剧痛让他多少清醒了过来,然后就是带着怨怪地制止,和不以为意地说着一个人造半妖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死的言语声。巨大的痛觉攫取了他全部仅存的思索空间,连回忆都被迫中断。身体的右半部分再度鼓噪了起来,但却无法和意识连通,如同夜下的猛兽,自顾自地对着黑暗嘶吼不休。
——如果是人的话,大概早就该死了吧。
——因为我不是人,所以才还能活着,连死都不被允许的活着。
三千院突然有点想笑。尽管不合时宜,他依然想大笑出声。愚蠢地认为自己只要抱着一颗胸腔里和血管连通维持生命的器官就依旧是人类,天真地以为有人能允许这样的不符合世理的异类存在,对军队而言他们不过是弃子,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只是战争工具,而对妖异来说他们则是污秽,世间难容。只有他们自己还做着自以为是的梦相信他们还能被人所爱,被人接受,被人毫无芥蒂地拥抱入怀。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怎么笑了?”
太可笑了。自己听过的关于妖异的故事不过是说书人肆意改编的谎言,四处各地除了战争逝去的亡魂和杀戮以外什么都没有,都是谎言,就连自己现下的存在也是他自己为了能让他的自我认知接受才强迫相信的谎言。他不是人,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个异类,一个从出生起就被丢弃的不应存在之人,一个被禁术强行带回世间的违逆世理之人。
“杀了我……求你。”
回应这细不可闻祈求的是一声嗤笑。
“你不会死的,一个异类死在这里,血都未免脏了这里的土地。”
没有声音。
三千院的心,消失了。
——————————————————
因为牵扯人物太多而且需要太多性格于是全篇NPC
二章两方都太忙于是我写了发一下接剧情
如果未来我们有闲情逸致再来搞插图版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