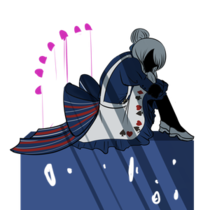拥有才能意味着什么?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以做到很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
和其他人不同意味着什么?
“你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去帮助他人。”
试着询问别人,得到的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答案。
帮助他人。
有才能者可以帮助他人。
有才能者被建议去帮助他人。
不,不是“建议”吧?
这么多人都这样“建议”,这么多人都这样“劝告”。
那应该说有才能者是被“要求”去帮助他人才对吧?
有才能者几乎可以获得一切的社会,也是有才能者必须贡献自己的社会。
“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他甘愿付出的报酬而已。
“这么想还真是不公平呢……”
中学时的我还会像这样坐在教室里自言自语着。
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教室,眼看着窗外逐渐落山的夕阳。
“——不公平呐!!!”
不知朝着什么东西大声呐喊,这样的肆无忌惮。
“……”
然而,某一天。
尽情呐喊之后的我,听到了门外脚步声停下的声音。
没考虑到外面可能有人会经过是我的疏失,但这个时间还留在学校里的人未免也太奇怪了一点吧。
……好吧,这个时间还留在学校里的怪人,我也算一个。
“什么不公平?”
门外的怪人并未现身,进入教室的只有他的声音。
是因为不好意思吗?毕竟是偶然听到了别人的自言自语,会这么觉得也无可厚非。
然而他甚至没有连为此道歉,只是唐突地丢出这样的疑问。
真是有意思的家伙。
“要求有才能者付出的社会,相当不公平。”
我没有离开座位,坐在那里回答他。
“确实,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他的语气平静得不像是人类所有,
“但是,这个‘不公平’,正是源于更为本源的那个‘不平等’。”
孕育出“不公平”的“不平等”。
“‘才能的有无’……吗?”
想想也只有这个了。
“正是。”
他或许有点点头吧,不过从说话语气来看他应该不是会用这种小动作表达情感的人。
“天平向着有才能者倾斜,于是无才能者就拿出了自己的砝码。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
就只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已。
“……就只是这样而已啊……”
简单到让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疑惑实在是有够蠢的地步。
“这么说来,你是——”
不等我继续提问,门外的脚步声已经自顾自远去。
//
裁判场,处刑场。
原形毕露的凶手在我眼前被处决。
“或许自己真的阻止不了什么吧……”
观察、聆听、交谈,根据每个人的痕迹演绎出他们各自的人生,进而推算出他们可能被利用和煽动的弱点。
掌握了漏洞便可以对症下药,制定出阻止自相残杀发生的方法。
这是我原本的计划,也是已经失败的企图。
或许我一开始就不该期待它能顺利进行。
侦探是解决事件,而非阻止事件的存在,甚至有人会认为是侦探本身的存在引发了事件。
拥有才能的同时,也被限制了能够做到的事。
“我就不该来这儿吗……”
我摇了摇头,将负面的想法驱出大脑。
就算把责任都扣到自己头上也于事无补。
更何况,最应该负责的那个人,一手造成了这一切的元凶,在场另一个有才能者,就站在那边。
“你觉得这样的世界很有趣吗,平等院玄真?”
不是嫌恶的绰号,不是亲切的昵称。
不仅呼其名以拉近关系,更不尊称其姓以表达重视。
只是将代表他这个人的名号陈述。
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刻意忽略。
他没有做出任何回答,自顾自地消失了身影。
“欸……”
扶额,然后叹气。
“算了……”
受限于这个世界的我奈何不了世界的掌管者。
“我们回去吧,保安。”
我转身对一旁的永生まもる说道,
“今天应该还有些时间,我们——”
“真田君。”
佐崎良见出声叫住了我。
“有什么事吗,佐崎同学?”
只见他摸着下巴低头思忖。
酝酿了许久之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死的感觉……如何?”
教人有些大跌眼镜的询问。
不过倒也不能算是意料之外。
“不算很好呢。”
我瞥了一眼永生手上拿着的卡片。
那是游乐送给我的、现在成为了我的附着物的卡片。
如果可以选的话,就算要作为幽灵复活我也不会选择这张卡。
因为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失败,想起自己没能预料到游乐会被诱导犯下罪行的过失。
我是因为这个失败才死的,要说感觉有多好,那绝对是在骗人。
“怎样的死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呢?”
刚刚的他还在为该不该忽然提出奇怪的问题犹豫,在得到我的回答后似乎稍稍放下了心进一步追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当然只有一个:
“完成使命,寿终正寝。”
作为有才能者,为无才能者贡献自己的才能。
“虽说……一般而言很难做到啦。”
既然阻止不了,就尽其所能地解决吧。
毕竟,这就是侦探的责任嘛。
一键衣橱
消耗:2mp 推荐场景:日常
平等院建言:需要更多的衣服样式,这是合理的要求。
详解:仅能对个人房间的衣橱使用,在脑海中构思服装样式后可以发动,发动后可以自由在衣橱内生成任意样式服装,每次使用可以自由生成任意件数服装,当衣橱无法容纳更多服装时使用失败。
思念写真
消耗:1mp 推荐场景:任何
平等院建言:事实证明,直接将想象力转换成图片是无法做到的。
详解:可以以纸片为对象使用,使用时需在脑海中构思场景,或者直接以视觉目击场景,10秒后纸片上将浮现出对应的场景。但非实际目击场景时,念写结果将必定会模糊不清。
虚空图钉
消耗:1mp 推荐场景:任何
平等院建言:用于展示物品十分方便。
详解:将一件重量低于5kg的事物固定在空中任意位置,持续时间5小时,该事物被施加超过5kg的力时魔法立刻解除。无法重复将事物固定在相同的位置,因此使用时能够看见周围曾经被使用过虚空图钉的痕迹。


身体不行了……先打卡。
感谢南锅代打【?】
----------
这是乌云笼罩着的密闭空间。四下无人的凌晨三点,只有一人在青苔气味的冷风中穿行。如果雨下大点、再下大点的话,陈年的烟味和人类的血液一定就会这样被洗刷而去。
不撑伞的黑影度过狭长的街巷,敲了敲无数相似的铁皮门的其中一扇。
马上就要入冬了吧。
祂这样想着,直到门打开为止,水珠也不断从濡湿了的发丝中滴落。
黑色的高楼、黑色的栏杆,没有他人,路灯也坏了。
什么都看不见。
除了眼前这个淡漠的、沾着血的人。
“让我进来吧。”
不要拒绝我。
“血要滴进眼睛里了。”
如果是这样的初遇的话,这一定会是最糟糕的恋爱故事。
可这并不是一个恋爱故事。
作为故事的读者,要给一个怎样的评价才好呢?
【现在想起来,我一定是比那之前更早地对尼古丁上了瘾。
比吗啡更廉价,比大麻更简单。
比任何一场梦,任何一次濒死,都要如临天堂。】
-
手上是与血肉亲密接触的触感,司在熟悉不过了。
粘稠的血液伴随着铁锈的气息,所有的感觉似乎都在试图让祂回忆起那些渗入骨髓的本能。
刀闪着冰冷的光泽,手娴熟地划破皮肤,破开肌肉,瞄准了筋腱的地方,下刀,挑起。
最后是动脉——司的眼神定在这个地方,冰冷而尖锐。
祂感受着,数具躯体在祂的视线下从火热变为冰冷。
“……”
抬起手悬在半空,司睁着眼,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摆放着双稳且有力的手,五指半抓着空气,最终握住了另一条手臂,用要杀死谁的力度攥紧。
嘶——哈——
就如同这样,确认自己还活着。
过了会,司的呼吸稳定下来,眼神也逐渐恢复为正常温度。
下意识掏出点燃香烟,薄荷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驱散着梦中那股浓郁的血腥味。
-
司觉得自己像是个才上学的小孩子一样,不容易专心也不知道该专心什么。
————
“……——”
……有谁在说什么。
“——那么,开放魔法自习课程!”
又是那只莫名其妙的猫……司晕晕乎乎的,晃了晃头保持清醒。魔法不必听就会被灌进脑子里很难受,但长时间的去听不想看见的人说不想听见的事,那就是痛苦了。司作为一名遗传差生感觉这种痛苦化作细针真正刺激他的大脑,刺激得祂越发烦躁。
“即使是凡人的诸君,若能以自身的努力跨越困难,就能朝各位的愿望确实迈出一大步了VON!”
呵。司冷笑一声,裁判场的曾经浮现在眼前,什么邀请函,什么承诺。
都是什么玩意。
-
奇形怪状的幻想生物停滞在空气里,黄铜色的灯光被鳞片折射泼洒在墙上,一切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如此这般罕见的标本被展示在这宽敞的空间,还附赠了别有用心的造景,却还是让人觉得有一种铺张浪费的感觉。
“虽然是这样罕见奇怪的生物,死后却和普通的动物一样做成了标本呢。”
“嗯?嘛是吧。”
司习惯性的张望了一下,然后保持着走神的状态。
“啊,比起那个,要去吃饭了吗。”
“……我没关系。”
“那我也没关系。”
海沼敏锐的察觉到话中蕴藏的故意给人寻尴尬的态度,尽管可能祂并不总是愿意这样,“……那,吃什么……你也应该无所谓吧,我来决定?”
“好啊。”
两人来到食堂,司一眼就找好了位置坐下,目送海沼一人去点餐。
面前的食物层层叠叠不知夹了多少种类的食材和酱汁,热气腾腾的放在碟子上。
“哇哦,这是什么。”
“……大阪烧。你没吃过吗。”
“没有诶,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司用餐刀尖比划着,最后利落的一刀切了下去,手感比想象中还要脆弱。
这场用餐在一场略带尴尬的气息中过了半场,祭御狩的出现才略有缓和。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司没有抬头,继续进食,为了不让好不容易打断的尴尬不再重演,海沼看一眼司应了下来。
之后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些,但仍然看不出来司在想些什么,第一个吃完第一个走,表情无不在诉说:我在走神。
保持着这个状态,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换上了一条舞裙——那是祂以前经常穿的,记录着某些故事的舞裙。
司看着这条漂亮的舞裙,手指比划着什么,想:这就是所谓的魔法,祂讨厌的东西。
从镜子里司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有些差,差到了别人能明显能看出祂的心情糟糕的境界了。
-
——つかさ。
法华津纱夜知道这个称呼。
姓氏、职业、户籍、年龄、性别,仅她所知就有无数个不同的版本。只有这个称呼不会改变。
到现在,比起那些只是一纸档案的假信息,她更加无法看透这个人了。
-
“……?”
哐哐。
有谁在敲门。
司站在门前,祂身着优雅的黑裙面带微笑,如同贵族中的交际花一般,一只脚向后划,简单地行了一个礼。
“晚上好,法华津小姐madam。”
纱夜有些愣神。同一个人,仅仅是换了一身衣服,面前的已然不是她熟知的杀手,而是午夜时分邀人共舞的风流女性。
高跟的舞鞋敲击着地面,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连双足着地的步伐也撩人似的流连不滞。司已经进入了房间,纱夜下意识关上,门的声音响起,她在那时候终于明白了,自己已经被那笑容所迷惑,而放入一个致命的猎手与自己独处一室,而自己不幸就是那个被困住的猎物。
足尖以精致的角度回旋,随着布料的摩擦声,裙摆被解开而几近垂地,黑色之间露出了显得新鲜的肌肤。祂抬起手似乎隔着无形的东西怜爱地抚摸着情人的面颊,手指在空中暧昧地起舞勾动着,最终落在法华律的肩头。
“你总是这样发呆吗?这可不是好习惯。”话毕,祂托起纱夜垂着的另一只手,哼着调子先一步动了起来。
等纱夜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随着司起舞了。司跳的是女步,却主导着她的步伐引领着她舞蹈,祂哼着歌,声音不大旋律却一节不落入了纱夜的耳,是La Cumparsita。
司的音准节奏都在,不过纱夜无心欣赏。太近了!纱夜想,但她无法挣脱,手心冒出的汗也无法让她的手顺利脱出,舞步随着节奏在继续,她得分出一小部分的心思去跟上以免踩脚,大部分的则在想面前这人的动机。
现在是滑步,想要挣脱司的纱夜弄巧成拙反而将拖鞋踢到了角落。
司并没有为纱夜的不解风情影响半分心情,微笑的弧度上扬了几分。纱夜出声制止,但司跟预想的一样没有为之所动,继续着自己的舞步,在下一个节拍点迅速换了姿势下腰,等纱夜反应过来时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她几乎是喊出来:“停下来!”
纱夜用力一推,终于是挣脱了司的手,跌在床上。她的脑子现在一片混乱,跟司相处过一段时间后她愈发觉得这人不能信任。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明明知道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纱夜不敢直视司的眼睛,她怕认清自己猎物的处境。
“我不知道啊。”司的声音犹如平静的冰水,刺激着纱夜。
祂放轻脚步捡回拖鞋,“你在害怕什么。”
纱夜沉默着,她说不出口。如果司是一位冷静的猎手,那么祂现在正端详着祂的猎物,也就是她。作为猎物的她面对这样的猎手这样的处境除去诸多疑问,剩下的只有死亡的预感。
“你有着跳探戈的天赋喔。你现在就像探戈一样,怪异又多疑,充满了攻击性。”司的语气不变,纱夜却察觉出这一滩冰水中似乎藏着一丝杀意,“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一定学得很快吧,说不定马上就会比我还出色……”
“……我没法相信你。”纱夜说。
“你觉得我会因为想出去而杀人,么。”
纱夜看起来有些艰难地抬头:“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事到如今还能那幅享受的样子。”
司站在祂原本的位置,只是看着纱夜:“那你可以慢慢琢磨怎么完美杀人,你或许还可以下个订单去买平等院的人头。”说到平等院这三个字,司几乎咬牙切齿,掩藏在冰层下的杀意喷涌而出,“你很想出去么。”
她终于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我还有我的工作,我的责任……”话音未落,司突然冲上去,纱夜下意识往后拉开距离,直到司将将纱夜逼到了墙边。
司低着头,祂的长发垂了下来,遮住了表情。“那种东西,就像拖鞋一样踢到世界的角落吧。”
纱夜攒紧的手心充满了汗水,她咬着自己的下唇。她确信如果司真的动手,在刚才这位优秀的猎手就能满载而归,而她就是猎手的战利品。
司观察着她的表情,缓缓开了口:
“我说啊,纱夜,你也知道吧,你所坚持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你。这里的所有人都只是垃圾堆里的废纸而已,那种三流地下小说根本没人会看。”
司终于抬起了头,纱夜看到的不是什么奇怪的表情,只是微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微笑。
“我不会背叛你的,如果你要我杀人,我会做。相对的——你要养你捡来的东西。纱夜(master)。”




接上【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6886/】聯動【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7328/】
【不好意思和我互動的各位,之前因為比較忙所以填得慢,這篇三千出頭,剩下五千繼續補】
結束了。
走上劊子手的高臺是如此輕而易舉的事情。二十七雙眼睛看向刑場的中央,呼吸也在此刻停止了。
一切的始作俑者面無表情地坐在那裡,就像在俯瞰一場悲情的猴戲。名為黑間久郎的假面被撕下去了,從裡面露出來的是冷淡的革命者的臉龐。
如果是為了宏大的理想,一切就可以被原諒嗎?
答案是否定的。
於是,川端由紀子按下了按鈕。
***
心情不快的時候就會想吃拉麵。
由紀子的視線掃過食堂的食譜,最後定在了其中一行字上。魔法廚具則在料理台後懶洋洋地在飄著,好像已經對自己的職責感到懈怠。不知是否因為剛剛辦完學級裁判的關係,食堂裡人多到離譜。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大部分人並沒有吃早飯。
“醬油拉麵加叉燒和竹筍,糖心蛋請給我實心的。”由紀子合上食譜。廚刀就好像被哪位老練的大廚握在手裡一樣,嫻熟地在木板上削下一片叉燒。過了一會兒,鍋子烹煮著醬油麵湯的香氣傳過來了。
由紀子端著那碗看起來頗為專業的拉麵,像往常一樣搜尋著窗邊的座位。不過,自己平時常坐的那張桌子旁已經坐了一個人。
“叨擾了,我可以坐在你對面嗎?”由紀子向那個獨身一人坐在窗邊的男生問道,“你不介意的話。”儘管如此,對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並沒有做出回答,因此由紀子決定將那個當做是默許,坐了下來。或許是因為之前發生的事件的原因,即便是此前沒怎麼說過話的人,現在的關係卻也被拉近了。
不得不說,拉麵的味道意外的好吃。雖然不知道味道算正宗不正宗,但頗具風味這點卻是肯定的。麵湯意外的爽口,筍乾的淡淡的煙熏味也起到了點綴的作用。
剛剛死過人,就這麼在午飯大啖美食好像不太好,但是死人不能吃飯,活人才需要。退一步講,食物也能讓人忘記難過的事。由紀子捧起湯碗,將鮮咸的湯底大口喝了下去。
活過來了。由紀子從麵碗上抬起頭來,看向坐在她對面的少年。
“八木澤耶和華同學……是嗎?”她輕聲問道。對面似乎沒有料到自己吃到一半突然搭話,眼神不易察覺地飄向了窗邊。
“……是的。”
“嗯……”由紀子用筷子攪拌著那碗湯麵,“八木澤同學覺得人會隱藏自己的真心嗎?”
並不是什麼愉快的午飯間會談的話題,但是,由紀子卻覺得如果不問問對方的話,自己的立場就會開始產生動搖。
要說起來,其實是相當突兀的一句話,八木澤似乎也是這麼覺得。不如說,對方似乎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由紀子在詢問他,而是遲疑了片刻之後,用溫吞的視線掃視了一次由紀子的嘴唇,才緩慢地回了一聲:“……唉,啊……”
或許是因為自己的問題太突然,對方沒反應過來自己在說什麼吧。由紀子歎了口氣,向八木澤道歉道:“對不起,突然問這種事。給你造成困擾了。突然提起來很抱歉。”
“是,怎麼了嗎……”八木澤小聲地追問,目光意外地回到了對話中來,“……”
“……唔。”由紀子看著色澤清澄的醬油湯,繼續說了下去,“想知道你是怎麼看平等院的……或者說人類戴上假面這回事。”
果然還是太突兀了嗎?而且用這件事問超凡人級的贗作師似乎很失礼。由紀子暗自揣摩著,小聲地為自己下了個台階:“突然在說什麼呢……真抱歉。”她撈起一口麵條,好應對沒有人回復的尷尬感。
“唉……唉……?我沒太懂,那個,假面和平等院先生有什麼關係嗎……?”意外的,八木澤放下食具,用困惑的雙眼柔軟地叩擊這個描述,表情卻在暗示她繼續說下去。
“人裝作是其他人活下去這件事,可能嗎?”
在沉默中八木澤再度拿起了餐具。
“啊……”八木澤慢悠悠地旋轉著那柄叉子,最後將視線投到了自己的盤子裡,“……我不知道,您覺得呢?”
“我原本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由紀子的胸腔因為自己的思考而再度灼痛了起來,適才通過食物撫平的心緒再度回到了原點。比起來怨恨平等院,倒不如說……
在知道黑間久郎就是平等院的那一刻,由紀子的內心反而理解了對方一半。
那並不是原諒之類的情緒。計劃好殺人,并將那樣的事情推在別人頭上,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人原諒,更何況,由紀子並沒有那樣的權力。
“但是……”八木澤在食桌對面重複著,他的視線並沒有從盤子上移開,因此由紀子並不能猜測出對方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催促著她說出來的。反倒是意外的,不知是以什麼為起因,想起來了那個金髪少年所說的話。
大家在這種地方應該都抱著不同的想法。有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種答案。而且,只要想法足夠堅定,就誰都說服不了誰。
“就算是出於心裡嚮往著某種東西,強迫自己變得更好,得來的應該也只是一個人的一面吧?也就是只有憧憬的那一面,被模仿者其他的部分,對模仿者來說並沒有任何仿摹的價值。”由紀子慢悠悠地將思考了已經有一陣子的疑惑一股腦地吐訴而出,隨後,她在等待對方回答的漫長時間裡試圖看穿對方的雙眼下湧動的情感。
可是沒有,對方的雙眼裡所蘊含的東西由紀子無法理解,也不可能理解。八木澤的雙眼在迴避著這個疑問,比剛才還要更甚:“您……為什麼會,思考這個呢……”他以耳語般的音量小聲說著,但並沒有要停止這對話的意思。
“我想知道大家都是怎麼想的。”
“嗯……那個,真的對不起……我沒想過,但是,嗯……”八木澤摘下來耳機,有別于由紀子對其平時的印象,他的語調突然變得尖銳急促了起來,“您討厭平等院先生嗎?”
“我不清楚……如果說是黑間久郎做了這一切我會討厭他。”
由紀子討厭他背叛了所有人,也背叛了他自己。
“但是平等院的話……我……”
如果這件事是平等院所做的,雖然並不能原諒他,但是……
如果是平等院做的話……
那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因為,作為始作俑者的平等院的人格,在場並沒有人知悉。
對於黑幕的靈魂,且不說由紀子,其他人也沒有什麼期待。
是不是就可以說,如果幕後黑手是平等院玄真而不是黑間久郎的話,雖然不能原諒,卻是可以理解的?
“您覺得,他對平等的理解,有錯誤嘛?”八木澤一反常態地抬起頭來。這次,由紀子終於看到了他的神情。
“怎麼說呢,我在學級裁判時非常的生氣,——我因為黑間久郎說的話而感到生氣,因為黑間久郎不會做這樣的事,所以才不可原諒……但是平等院,我並不認識、也並沒有對他的人格有什麼期待啊,只是,他在對平等的理解上陷入了常見的邏輯錯誤。
八木澤並沒有接話,只是眨眨眼,他將耳機捏在手裡,等待著下一句話。
……這麼說下去真的好嗎。由紀子想著,不過還是繼續說了下去。
“身為超高校級的他,首先否定了才能的存在、將才能視為絕望,然後希望我們能夠變成超高校級,也就是獲得才能。說到這裡,話的矛盾開始變得奇怪了起來,那就是人類要全部獲得才能是不可能的,那麼到了這個地步,平等院究竟是站在哪個方向的呢。在一度否定過後他進入了否定了自己的否定的情況——雖然很正常,但是,如果是要說服我們的話就說不通了。另外一點是,他本身對平等的定義非常含糊。不知道是有意為之,還是如何,但是現在看來他自己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的理論。這就是所謂唯物辯證的否定態,也可說是……我不知道這套理論他是通過套用哪種思考模式得來的,……你在聽嗎?”
八木澤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把耳機戴回去了,並且早早就閉上眼睛了,直到由紀子在話題上急剎車,他才從那種狀態中回過神來。
“啊,麵條坨掉了。”
由紀子用筷子戳著泡得發漲的麵條,為對方居然反客為主、並沒有透露由紀子想知道的心緒,反而詢問起由紀子的思考而感到生氣了起來。不過,這與其說是在對八木澤生氣,不如說是她對自己不多加思考就輕易放出的言行感到生氣罷了。
而且,也沒有得到想要的解答。
“抱歉……我沒太聽懂,對不起,打擾您了……要不要重新點一碗?”八木澤匆匆地從餐具後投來歉意的視線,隨後又回歸了那個和開始時一樣的、旁若無人的狀態。
“沒有啦沒有啦,本來就是我想問問題,結果莫名其妙地變成我說了一大堆。學校的擔擔麵不錯哦,我也很推薦。”由紀子捧起湯碗,慢悠悠地喝了起來。
兩人在無聲中結束了對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