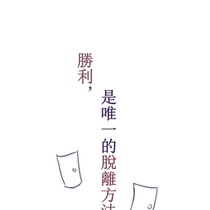企划已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
企划是一个BG限定的组队形式企划,是含有战斗要素的恋企,背景魔改自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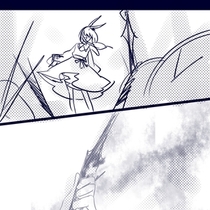


字数6472
.
.
.
.
走离仙境的人们
小镇的狂欢还没有结束,看不清面容的镇民依旧手舞足蹈地聚集着,欢呼着。他们打扮得体面又稳重:绅士们戴着高礼帽,小姐们的宽幅裙撑支起点缀了丝带和蕾丝的裙摆,就连最朴素的农妇村夫也把自己拾缀得干净精神--不过在他们毫无节制的疯狂中,他们的精巧包装已经随着理智一起被撕破了。
琳希乖巧地缩在沃尔德西怀里,环住他的脖子。“他们总是这样。”沃尔德西说着,灵巧地穿梭在小巷中,娴熟地避开僵尸一样的镇民,像在林中滑翔的雨燕。女孩还来不及一一辨认伸向她的手,沃尔德西已经侧身闪过他们,或是恰到好处地一拨,让他们互相撞上。
他们很像是琳希其他梦境里让她害怕的黑影,总是伸长尖锐的黑爪尝试捉住她。梦里她努力奔跑,躲进荆棘丛里捂住耳朵,闭上眼睛,等待清早的闹钟。
不过现在她并不感到害怕。琳希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再温柔不过的梦--她头一次希望自己不要醒来。
她又紧了紧自己抱住沃尔德西的手,靠到他的肩膀点点头当做给他的回答。又顺着沃尔德西毛绒绒的头发捋了捋,权当是自己没问题的证明,并不考虑对方能不能理解。
他们在镇外的树林里停下,潜伏在有翠绿叶子的柔软树丛中,学习转动耳朵隐藏身影的兔狲,侦查潜藏的风吹草动。在琳希的注意力被跳上叶片梳理触须的蚱蜢吸引走一段时间后,沃尔德西松了一口气地站起来伸展身体。蚱蜢被吓到,后腿蓄力,跳到琳希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他们大概是……太过热情了?”沃尔德西弹走琳希头上的树叶,希望她没有被吓到。虽然他能多少猜到到女孩的心情,现在也很难说琳希呆呆的样子是被吓到了,或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甚至是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没事,兔子-先生在的。”她颤颤巍巍踮起脚尖,努力地伸长了手拍拍沃尔德西的头,又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小野餐篮,分给沃尔德西一块小奶油泡芙。“好吃的。”她笃定地说。总是散漫混沌的蓝色眼睛认真地看着沃尔德西。
她在笑。
沃尔德西看着他面无表情的“爱丽丝”,非常肯定。
“好吃?”琳希一直看着沃尔德西,确认他好好吃掉了泡芙,目光又散漫开,不知道聚焦在哪里。
“嗯。谢谢。”
小泡芙有些太甜了,但是今天是个吃甜食的好日子。
琳希和她的兔子慢慢地走在小树林里。她并没有告诉沃尔德西准确的目的地,于是沃尔德西像是遛猫一样,任琳希自己走走停停地在林子里晃悠。沃尔德西隐约知道自己需要把她带到仙境,之后也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并不很确定那是什么。反正到时候就会知道了,就跟确认琳希是他的爱丽丝一样。在那之前,他们有打把的时间慢慢消磨。
有什么理由不安心呆在这里呢?这是沃尔德西的家乡,琳希的病情看起来也很稳定。下午三点悠远绮丽的天空飘浮着金橘色的,棉花糖一般的云;到凌晨三点,不规则排列的星星会点亮每一个深夜还未沉睡的梦,像是流水的井或是摇动的铃。金色的天空下是苍翠的草地和永不停歇的茶会,一切少女能梦想到的甜蜜都溺爱地,无止境地只为满足她而存在。河流是漂浮的彩带,鲜花是闪光的宝石,脚下小路的终点是另一个柔软的梦。
该如何用除了仙境之外的词句去描述仙境呢?语言是苍白且无力的。每个人的想象无法被区区几个句子表述。就让我们说这是仙境吧,也就让我们如此去理解它吧。是梦的话就让它再晚一点醒来,就让它变为现实。
现在,琳希和她的兔子,沃尔德西和他的爱丽丝,走进了被精心打理的花园。
“这又是谁来了?”红色的大丽菊探过头来,有些刻薄地发问。
“又一个爱丽丝,总是爱丽丝,每次都是爱丽丝。”小一些的三色堇不满地抖抖花瓣。
“总是要好些的。比莫妮卡要好,也比伊丽莎白让人舒服。”纯白的马蹄莲端着架子,叶子却忍不住地往这边偏。
“她要去哪里?噢!还有白兔!我可不喜欢白兔,这个爱丽丝看起来也很蠢!噢!”大惊小怪的百合喷洒着花粉,让琳希打了个喷嚏。“天呐!真没礼貌!你这个土拨鼠一样的爱丽丝!真没礼貌!”她一边抱怨,一边喷出更多花粉。
沃尔德西给琳希递了手帕,打着哈哈:“她们总是这样,也许我们该换个地方。”
他隐约觉得哪里有些奇怪,但是没有多想,这些花实在太吵了。
越来越多的花围过来对着他们大呼小叫。
“你们该到红心城堡去!”她们说,七嘴八舌地叫嚷让人听不懂的话。
“那里的头颅已经发芽了,明年夏天会开花的。”
“被丢到河里的手指和头发,他们缠绕在一起,每晚地跳着舞,让国王睡不了觉。”
“加波沃奇要起来了!是白皇后的错,她吃了青虫冬天的蘑菇。”
“跑起来吧爱丽丝,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要死啦!”
“藏好你的骨头,乌鸦会拿它去筑巢的。”
“两千个日与夜,你的兔子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琳希捂住耳朵。花的影子重重叠叠,长出利爪和荆棘。根茎缠住她的脚,守林人藏在窸窸窣窣的叶子见,他拖在身后的斧子划过地面,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金属的尖叫。藏了很久的阴影从她头发下探出触角:“着火了!!!”它们对着琳希的耳朵大叫:“都烧起来了!!你烧起来了!!那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那些焦炭!!你睁开眼睛看吧!他们还盯着你呢!!”
于是巨大的,滴着黄色浓水的眼球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咧嘴笑起来。
琳希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边那一小块儿草地,小声地念起童谣,悄悄用脚跟打着拍子。她努力想象自己在箱子里,旁边有沃尔德西给过她的玩偶兔子。她开始想着那只玩偶兔子足够大,能抱住自己。
「虾蟆虾蟆要去哪里吖?」
「要到狐狸的房子做客吗?」
沃尔德西看不到琳希眼中的幻象,也听不到阴影的声音。他只知道周围多嘴的花让琳希很难受。
「狐狸先生娶了妻子啊。」
「有火红的尾巴和脖子。」
让她们闭嘴会好些。沃尔德西本能地这么觉得,于是他伸手折断了百合的茎,扯下大丽菊的花瓣。
「狐狸先生请了伴郎啊。」
「有雪白的耳朵和爪子。」
他很轻松地踩扁三色堇,撕开马蹄莲的花瓣,玫瑰的刺也没法保护她自己,水仙来不及闭上叶子就被摘下,睡莲也没及时躲回水里。
「虾蟆虾蟆要去哪里吖?」
「让我坐到兔子的尾巴尖,」
「跟你一起去吧。」
沃尔德西拍干净身上的花粉,重新帮琳希系好头绳。抱起念着童谣的女孩,头也不回地离开花园。
“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百合厉声尖叫。
沃尔德西没有理会她,把花朵的诅咒和呻吟留在身后。花茎流出的透明的血打湿了他的耳朵,他要去河边洗洗,然后晒太阳。
琳希意识清醒过来时怀里抱着大大的兔子布偶,沃尔德西躺在一旁的草地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星星跑来跑去,告诉她现在是晚上三点。
她安静地看着沃尔德西,她曾和不存在的怪物单枪匹马地战斗,现在她赢了。
我回来了。
她在心里这么跟自己的兔子说。
沃尔德西一定也经过了自己的战斗,多半是为了保护她。她还记得恍惚间沃尔德西的温度和气味。
可她还没办法为他做什么。这让琳希有点沮丧。她可以给沃尔德西编辫子,但是沃尔德西已经救了她两次,这并不是对等的事情。
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没办法跳得那么高,或是跑得那么快,也没办法驱赶沃尔德西的烦恼和痛苦。她看着沃尔德西,努力地想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然后,像是从土里钻出来,或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只拿着指挥棒的,有尖锐牙齿的小兔子噶呜噶呜地叫着,在琳希面前跑过来跑过去。
琳希盯着小兔子,停止思考。
沃尔德西是被一边拆房子一边重建一样的声音吵醒的。他在享受暖洋洋的午后的阳光时不小心打了个盹,抱着醒来后能见到活蹦乱跳(或多或少)的琳希的愿望,做了个有甜奶油泡芙气味的梦。梦才到一半就被吵醒了,还是以这种非常粗暴的方式。
他摸不着头脑地坐起来,不记得自己睡在工厂。
周围是拿着各种乐器发出噪音,本身也在胡乱叫喊着跑来跑去的小兔子。他们数量很多,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琳希正坐在兔子堆中间,目光空洞。头上还有一只,一边挥舞着指挥棒,一边嗷呜嗷呜地啃着她的脑袋。
沃尔德西拨开两只组合起来,用小提琴发出锯木头噪音的兔子,小心地避开它们的尖牙,把琳希从撒泼打滚的兔子堆里拔出来,弹走啃着她脑壳的那只。
“真壮观。这是什么?”他把琳希举高,笑眯眯地问。
琳希的脸皱成一团:“呜……兔子……”她嘟囔着比划,手舞足蹈地学着它们嗷呜噶咕噜啪呱地叫了几句。
沃尔德西被逗乐了。他把琳希放到安全的树枝上,让那些兔子够不着她:“是你叫出来的兔子吗?”虽然这些小团的兔子真的很吵,但是并没有真的伤害他们意思,至多也就是给琳希咬了个印子。
“大概……”琳希倒是气鼓鼓的,像个河豚:“四-舍五入……”她又比划了比划:“很---吵!”
沃尔德西躲开空中挥舞过的钢琴,颇有些开心地笑出声来。
拿着指挥棒的兔子爬上他的裤腿,又蹬着他的脑袋往琳希身上撞。女孩伸长了手拎着它,小心不让指挥棒敲到自己或是沃尔德西,然后像修理坏掉的收音机一样用力上下摇晃兔子。
“咕嚓咔嚓噗噜噜噜噜…??”兔子发出意义不明地叫声,不过好歹老实了一点。
琳希得意地点点头,坐在树枝上用指挥家努力组织比起乐团更像建筑队的兔子。
沃尔德西则一边憋笑,一边像幼儿园老师一样把站错位置,或是跑太远的兔子揪回来,放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
直到下午三点,乐团才好歹不会因为钢琴兔子绊了一跤砸到其他兔子,或是鼓手的鼓棒脱手砸到沃尔德西,再或者号手一头载进自己的圆号里之类林林总总的事故。
于是琳希带着指挥家,身后跟着兔子的乐团,演奏着不成调的曲子,配合着乐手们自己咕啦嘎咔地叫声,行进在草地上。
琳希绞尽脑汁地回忆自己为数不多的音乐知识,尝试让兔子们演奏除了噪音之外的东西。她并不认识谱子,只能凭记忆地摸索着正确的声音,还要时不时摇一摇指挥的兔子,确保它还能正常工作。
乐团排练的时间她被兔子们演奏的噪音吵得头疼,休息时被兔子们自己发出的噪音吵得头疼,还要提防这些尖牙利齿的兔子啃树桩或是路过的什么小动物。简直又吵又凶,还蹦得很高。
最后琳希好容易让它们能拖拖拉拉参差不齐地合奏音阶,她觉得自己简直感动得快哭出来了。
“您好?我听到了奇异的音乐,过来看看。”
陌生优雅的声音传来,伴随着盔甲移动的碰撞声。
琳希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沃尔德西迅速挡在她面前,从他脚下为原点,草地被翻涌着扩散开的木制地板代替,弧状的穹顶替代了天空,把双方扣在没有墙壁的圆顶音乐厅中。印刻在血管中的排斥反应让他本能地进入战斗模式。
几乎是同时间,对方小个子的骑士也站了出来,左脚微微向前,肌肉紧绷,做好了随时向前冲锋的准备。钢铁制的盔甲严丝合缝地护住少年的咽喉,胸腔,和双臂。他手中像是指针形状的片刃的大剑蓄势待发,比少年自己都高出不少的剑冷冷地反射出尖锐的光。比剑锋更锐利的是他的眼神,红色的瞳孔凝聚着西伯利亚的雪和贝加尔湖的风。
“爱丽丝殿下,请后退。”少年转动手腕,钢铁划破空气撕开尖锐的呼啸,他双手持剑,剑尖对准了眼前的沃尔德西。沃尔德西稍微眯起眼睛,一步不让,双腿暗自发力。虽然做出了反应,也本能地张开了空间,沃尔德西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战斗意向。如果可以,他还是想尽可能避免战斗的。琳希的精神也并不那么稳定。
“唔……!”打破沉默的却是少女的低吼。
稀稀拉拉的兔子交响乐团像是僵尸一样摇晃着聚集过来,发出比之前吵闹数倍的声音,尖锐的牙令人不安地上下咬合。兔子们挥舞着手中的乐器,组成防御壁隔在沃尔德西和穿着铠甲的白兔之间。
在沃尔德西身后,琳希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出现的另一只白兔,眉头紧紧地锁着,握紧了拳头。拿着乐器的兔子们似乎是随着她的心情变得越发狂暴,发出的叫声也变成像是齿轮摩擦,或是履带拉扯的刺耳噪音。
“不会让-你欺-负兔子先生!”
对琳希来说,沃尔德西就是她最甜的梦。整个仙境是因为她的兔子而存在的。这一切安心的根基,翱翔的飞鸟,发芽的种子,都是因为沃尔德西才值得让人注意,让人喜爱。他是琳希绝对不让的固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那么快的反应想很多的少女挥舞起自己唯一的爪牙。
她的乐团现在看起来更像被扼住绳索,只等一声令下就冲出去的狂犬们。它们咧开的嘴和牙更像是食腐豺狗,让人不禁怀疑兔子是否也曾是肉食动物。金属摩擦的声音从它们破碎的喉咙里被扯出,一直断断续续,吵吵囔囔的敲击或是弹奏的声音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整齐而单一,不断重复的音节肃穆而空洞地整荡在音乐厅,一次,一次,又一次。
见琳希出手,对方的骑士也不再保留什么,他的剑自下而上破开地面,整个音乐厅都随着他的举动震颤。穹顶发出痛苦的扭曲声,沃尔德西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过去以维护这个小空间的存在。他能感觉到对方有比自己强的压迫力,这本应该是自己这方客场作战,但是应该是出于某种原因,对方选择放弃张开小空间。他也能感受到对方强烈的意志和自信,于是沃尔德西谨慎地选择观望,确定自己能挡住任何威胁到琳希的危险。
比较靠前的兔子被骑士的剑风绞碎,但是更多的兔子从莫名其妙的地方冒出来,骑士不为所动地打算重整架势,这样乌泱泱的兔子对他的伤害微乎其微,只是非常吵。
“稍微等等,我的骑士!”
从矮小的骑士身后,他的爱丽丝走了出来打着黑色阳伞的她比兔子还要稍微高出一点:“对面的爱丽丝,您也可以先停手吗?”
纤细的她踏着稳健优雅的步伐,和她的骑士一样刚毅。
“我们并无冒犯之意,与其开始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不如我们先冷静下来谈一谈,”白发的少女尽可能友善地看着琳希和沃尔德西:“至少我们先知道一下对方的姓名?”
琳希依旧气呼呼地看着拿剑的白兔,毫无退让的意思。
“好啦好啦……”沃尔德西打圆场地拍拍琳希的脑袋,架住她的双臂把她举起来:“先冷静下来吧,你饿了吗?”
对方的爱丽丝见状也示意自己的骑士收起长剑。他微微鞠了一躬,顺从地照做,只是依旧踏出半步,护在自己的年轻的女士身前。
被举高的琳希还不服输的样子,不过最后还是被空空的肚子泄下气来,发出猫咪一样的呼噜。周围的兔子们也渐渐变回原本浑圆的样子,开始唔噜呱啦地乱走。
沃尔德西顺势让琳希坐在自己肩膀:“能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他微笑着向对面抛出橄榄枝。
白发的爱丽丝云雀般轻巧地行了个礼:“我叫薇拉,他是斯塔尼斯。请问你们也是白兔和爱丽丝吗?”
沃尔德斯点了点头,没官还在对着斯塔尼斯吐舌头略略略的琳希,自顾自地回答了薇拉的问题。
“原来如此……”少女颔首思索着,像是想到什么一样提出邀请:“不如我们先去喝午茶?交流情报时能有小块的点心就再好不过了。”
下午三点的茶会由两个爱丽丝主持。
在薇拉优雅地品茶时,琳希也愉快地吃着苹果派。
解开了误会的少女们很快因为发现了同伴而感到愉快,虽然琳希看起来依旧或多或少地防备着斯塔尼斯。
“所以那些花说的是对的……”薇拉想了想。
琳希点点头:“至-少有一些是对-的。”
薇拉沉默了,估计她也隐约感觉到在这里呆下去的代价就是是爱丽丝间的决斗。她和她的骑士都需要做更对准备。
不过眼下,还是等少女们用餐结束吧。
琳希不怎么说话,大多是安静地听着薇拉的见闻和经历,然后安静地吃泡芙和苹果派。
对乐团兴趣浓厚的斯塔尼斯则跟小兔子们建立了奇妙的友情。总是没法好好指挥的琳希惊讶地看着斯塔尼斯和兔子们大成一团,连沃尔德斯也不禁侧目。
骑士交了兔子们几首俄罗斯风格的歌后,又饶有兴致地组织兔子们排列游行的纵队。不战斗是文雅的少年和兔子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可以交流的语言,乐队的组建比琳希自己来顺利得多。
“你要回去吗?”薇拉问道。
琳希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自己的兔子先生,并没有做出回答。
“我想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人。”薇拉倒是非常笃定。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所以她才能用毫无阴霾的眼睛审视周围吧。琳希稍微有些羡慕眼前的女孩。
薇拉递给琳希一块小红香肠。琳希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决定战斗让她有些吃惊,她不觉得这个呆呆的女孩是好斗的一类。在从她连比带划的描述中知道了沃尔德西对她的重要后,一直都想要保护家人的薇拉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只需要再多一点的勇气和果敢。
描摹着对方优点的爱丽丝们也许也在这个冷酷的仙境中收获了一点点的友情。
“那么,洗碗的工作就拜托你们了。”薇拉笑着说。虽然此后就要和琳希分道扬镳,认识她也是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琳希迷惑地看着她。
“?”
“既然爱丽丝殿下招待了你们,那就应该由您这一边承担洗碗的工作。”骑士义正言辞地维护着薇拉。
沃尔德西则轻轻摇了摇头,代替琳希发布自己这方的宣言:“你们是下午茶的主人,不应该是由你们负责吗?”
刚刚成为朋友的爱丽丝们互相僵持了一下。
沃尔德西重新张开了剧院的结界,斯塔尼斯也扛起了大剑。
吵吵嚷嚷又圆滚滚的兔子们折磨着乐器,噶呜噶呜地奔涌出来。

刺耳的警示音響起。
列車高速駛過月台,揚起風沙,及少女被吹起的裙襬。
某天睜開眼睛,她的世界就變成這個樣子。
朵洛莉斯曾經和所有其他人一樣,認為天空就是藍的、雲朵就是白的;彩虹之上有小馬、盡頭處有妖精的寶藏。現如今,她卻再也找不到理所當然的一切。天空是什麼顏色都無所謂,彩虹有什麼顏色都沒關係,每天的生活就只是生活,因為生物本能地不想死去而進食睡眠。
叩叩叩,一天又再度到來。少女睜開眼,門板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朵莉?你起床了嗎?」
「起床了,媽媽早安。」
她看著門邊曾經溫暖的母親,身影隨著她內心的破滅逐漸化為陌生,風化而去。
窗外陽光燦爛,從那天起,她的內心再也無法感受陽光的溫暖。
高聳的建築、湧動的人群,站在繁華的街口,朵洛莉斯找不到現實存在的理由。她突然遺忘了做為人類生存的價值與意義,看著眼前的日常風景,陌生的人群行過街道像會移動的剪影畫,磕磕絆絆擦過她嬌小的肩頭。茫然失措。
世界太大,包覆了太多的靈魂。16歲的少女看著眼前景色;分明五彩斑斕,映在眼底卻成了廢墟一片。風沙一揚起遮蔽雙眼,什麼也看不清。她太弱小也太無力,無法將眼前毫無意義的世界破壞殆盡;明明身在其中,卻如旁觀者一般看著他人碌碌生活的模樣。
和他人的交流都是群體生物社交性的假面,由生物不願死去的本能驅使活動;除此之外她找不到任何應當這麼做的原因。夢想、理想、對未來的嚮往通通無法被碰觸,面對這樣的生活原本只是做為行屍走肉生活的少女,心底逐漸生出了一絲異樣的躁動。
沒有意義的東西就消失吧。
帶著清純無害的神色,少女蜷縮在早晨溫暖的被褥中靜靜的這麼想著。
無意義的藍天、無意義的白雲、無意義的世界。
她想,在街道上行走為了生活而生活的人們,追求遙遠的夢想、遠大的未來的人們,築起的高樓、奔波的世界通通湮滅吧。
--朵洛莉斯的心在崩壞。
「要出門上學了嗎?」人偶A說。
「路上小心唷。」人偶B說。
崩壞的究竟是心靈或其他的什麼已不可考,路上人行像是精緻的木偶,天色藍的不真實;校園人群的聲響彷彿從收音機的另一端傳來,橫亙看不見的空間,無法與她碰觸。恍惚中,她看見無意義的人影裡有綵帶飛舞,像是幻影一般,一雙長長、缺了半截的耳朵晃過她眼前,又隨即如夢境一般消弭而去。
「兔子……?」她睜大眼停下腳步,那飄渺短促的瞬間,她彷彿還和一雙紅色的眼對上。如石榴般閃爍著剔透的光,在嘈雜人群中命運般只映入了她的倒影。命運般的。直到刺耳的剎車聲與轟鳴的喇叭將她拉回虛無的現實,她站在道路的正中央,女孩湛藍眼底映入的是一輛鮮紅色的聯結車,在距離不到三尺的地方咆嘯,餘波撩起她一頭栗棕色長髮。
朵洛莉絲沒有印象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站在十字路口,和生死交界接近的瞬間,她的內心卻依舊不起波瀾。
這種事情怎麼樣都好。
駕駛的怒吼對她毫無影響,少女緩緩踱步至路口的另一端。
只有她的世界毫無意義。在他人眼中,世界和生活都有不同的意義;或疲憊或許痛苦,但他們眼中有著憧憬追求慾望與夢想。直到某天朵洛莉斯突然明瞭,讓這個世界失去溫度、失去意義的人,正是她自己。
她丟失了存在的意義,因此她的世界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她遺忘了自我的價值,於是她的世界也遺忘了自我的價值。
世界太大,弱小無力的她始終無法摧毀逃離;但她明白了,世界本身就只是世界,就像生活本身就只是生活。讓他們失去色彩失去生命的,一直都是以這樣的雙眼看出去的自己。
少女眨眨純淨湛藍的眼,她明瞭真正該被抹滅的,是丟失了意義與價值的自我。
她不斷看見幻覺裡的兔子少年。
在人群裡、在黑暗中,偶爾在旯旮角落裡會看見一雙殘缺的兔耳掠過;在充滿人偶、劇場似的日常裡,突兀出現的一抹艷紅總能準確的捕捉她的目光。
在枯燥乏味的讓人焦躁的生活裡,自病態的精神之中開花結果的幻覺成了朵洛莉絲唯一的期待。她開始尋找兔耳少年的身影,偶爾與之對視,在土灰色調的城市裡如夢一般的相逢;奔走在命運的巨輪下,那似乎成為少女在索然乏味的世界裡唯一的希冀。
地鐵行人間,朵洛莉斯抬起雙手遮蔽眼前的景象。
抹去高樓的影子,又抹去了繁忙的街道。分明是與自己毫無關係,卻像是地上突兀的垃圾一般,在她心底落下無法抹去的躁煩、漸次積累。
如果一切都消失,她是否就能重回平靜了。
如果她消失......
「不是這樣。」一雙蒼白的手溫柔的將少女雙手包覆,突然出現的兔耳少年衣著特異,周圍人群卻視若無睹一般從兩人身旁川流而過:「妳的存在意義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分明是強烈的違和感,卻是這些日子以來最真實的感受。朵洛莉斯專注地盯著那雙紅色眼睛,問道:「你知道我存在的意義?」
少年搖搖頭,僅存半截的兔耳隨之晃動;他放開手,轉眼身影就讓地鐵人群隱沒。「等等!」朵洛莉斯撥開人群,手背被包裹的溫度殘存,就算兔耳少年是她終於崩潰的幻覺--但對她而言卻是唯一的真實:「等等!」
她看見少年站在月台邊,列車入站的警示音大作,但她充耳不聞。隨著人群的驚呼聲,朵洛莉斯的眼中只有少年和他殘缺的兔耳,在看見她追來的同時轉臉露出病態的微笑。
「來吧,愛麗絲。」
疾駛而過的列車覆蓋了少女一躍而下的身影。
*
在黑暗中漫長的墜落削弱了時間感。
轟隆作響的機械運行聲在她落下的同時消失無蹤,寂靜拖出尖銳的耳鳴,刺痛少女的鼓膜。
空間在崩落,巨大的層架與書本、桌椅與花朵自朵洛莉絲身旁飄浮而過;在不思議的空間中她的心底卻感到久違的踏實--少女以某種玄妙而自然的方式理解這個空間的存在。這些物品:被翻閱一半的書本、以無重力姿態濺溢而不灑落的茶,全都是為了迎接她而存在。
愛麗絲、愛麗絲……
耳鳴化為最溫柔的耳語,朵洛莉絲伸出微微飄散毫光的手,捉住了飄落眼前的一朵玫瑰。玫瑰的刺被盡數去除,令人憐愛而無害的柔弱;深紅瓣色底下透出和黑暗瞬成反比的潔白,在少女看清的同時逐漸化作灰飛,彷彿在剎那受盡業火焚燒。
若不是灰燼不合常理的飛起,她幾乎就要遺忘自己正在下墜。聽不見列車穿越的聲響彷彿已經是許久前的事,朵洛莉絲伸手接住半空中一只瓷杯,在指掌碰觸杯耳的瞬間她能感受到沙土落下。
瓷杯同樣緩慢的化作粉末、風化而去;華美的雕花木桌、精緻細膩的實木棋盤、昂貴古舊的厚重書本,少女在掉落的同時碰觸的一切通通化作塵埃消逝。她的命運、她的時間,在墜落的過程扭曲變形,產生了全新的自我。
時光進行的速度似乎與她的墜落相對,朵洛莉絲手中握著蒐集而來、正逐漸消滅的一束玫瑰,或紅或白、或未完全上色,在混亂的時空及狂亂飛舞的殘瓣裡安穩的合上眼睛。
這時候已經看不見她落下的光點了。
黑暗像是夢境一樣,或許這就是夢境本身也說不定。
朵洛莉絲以為在漫長的夢境裡,她會看見的是更多在她手中灰飛煙滅的世界,然而並不然。
「愛麗絲。」
夢裡的世界一片漆黑,連她正在下墜的洞穴本身也不復存在。少女飄浮在某種黑暗的液體中,身遭散發柔和的光芒,照亮卻無法穿透深深濃濃的黑暗。靜寂的飄浮中,她注意到那個有著兔子耳朵的少年正在不遠處,用那雙石榴般的雙眼盯著她不放。
「是你……」
「愛麗絲。」
在失去實感的世界裡,只有少年的存在是如此真實而強烈。朵洛莉絲伸長雙手,扭動身軀想朝少年的方向移動;但每當她前進分毫,少年便如真正兔子般輕巧一躍,讓兩人之間退回原來的距離。
他們開始在黑暗的泥淖緩慢追逐,少女不懂自身的執著為何而來;她甚至沒察覺到自己對於少年異樣的執著。這個世界毫無意義、缺乏價值,但她莫名有種強烈的直覺在不斷低語:那個白兔般的少年就是一切的解,是她飄飄然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礎石。
--她要抓住他。
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少女身上發散的淡淡毫光不知何時悄然隱去。在彷彿唾手可及的距離,朵洛莉絲奮力伸手,在黏膩的黑暗之中用盡全身力氣吶喊:「求求你等等--」
未竟的話語悉數轉為少女的尖叫,自由落體不受控制的加速度突然清晰明瞭了起來。朵洛莉絲感覺到自己落在某種厚實的墊子上,重重的下沉,接著緩緩的、溫柔的支撐起少女的重量。
自月台邊的墜落好像很漫長,仔細想來卻又像是轉瞬間的事。少女穩定了身軀,扶著身旁帶著潮氣的枝幹爬起身。她正巧摔落到一層厚厚的枯葉上,枯葉沾滿潮氣帶著腐敗的氣息,和一旁的枝幹一道,隨著少女的碰觸崩落成沙土。
「兔子先生?」朵洛莉絲也不管自己是否真的瘋了。她知道追逐兔子的少女的故事,在夢境中左右張望的少女,看見兔子消失在遠方。
才不是這樣。
朵洛莉絲轉過頭,正好看見兔子僅剩的耳朵尖尖消失在不遠處。她離開枯葉化為的沙土,踩踏上柔軟雪白的地面;地面觸感特殊而富有彈性,但不足以讓她多做停留。地面的盡頭有斷差,有著兔耳的少年似乎是從這裡跳下。朵洛莉絲沒有猶豫太久,便撩起不知何時變換的裙擺一躍而下。
「痛……!」落下的距離不特別高,卻還是足夠摔疼屁股;泥土的氣息撲面而來,朵洛莉絲抬起頭,這才發現自己剛才落在一朵巨大的蘑菇上。
難怪沒有什麼疼痛的感覺。朵洛莉絲收回原本想碰觸蘑菇的手,這蘑菇接住了她,她至少能做到不讓蘑菇在她手中消失。朵洛莉絲看向兔耳少年離開的方向,茂密的樹林裡有條狹窄的獸徑;樹叢後,一抹紅色的纖細身影一閃而過。
少女已經連等等都說不出口。她伸手撥開擋道長草,細嫩草莖在她指掌間逐漸湮滅;鮮花野草在她身後不復存在,然而朵洛莉絲並不在意。她一心一意奔跑著想追上少年的身影--這可能是從她眼中的世界失去意義後,唯一一件能讓少女真正在意的事。小徑延伸漫長無盡,她的雙手毀去一切,腳下卻讓道中交錯的樹根狠狠絆了一跤。
再爬起來時,朵洛莉絲已經完全看不見兔耳少年纖細緋紅的身影了。
直到這個時候,她才開始意識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
原本穿在身上的學生制服不知何時變成了帶圍裙的洋裝,合身合適,在森林裡雖然沾上塵土卻不至骯髒。還有她的手,朵洛莉絲蹲下身,掌心貼上絆倒她的樹根;幾乎沒有甚麼預警或變化,樹根就像崩毀的沙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化為粉塵,延伸向上。少女低頭望著自己攤開的指掌,若有所思。
「又有愛麗絲來了呀!」一個細微的聲音在說話,截斷了她胡亂的思緒。
「最近能見到那麼多愛麗絲,真是太好了呢!」
朵洛莉絲四處張望話語來源,細言碎語不斷,她撥開草叢,視野赫然開闊。映入眼簾的是個巨大而美麗的花園,被妥善照顧,整潔而多彩;一眼望去全是各式綻放的花種,沒有人影卻滿是說話的聲音。「請問……」
「呀!是愛麗絲!愛麗絲來和我們說話了!」朵洛莉絲循聲看去,那聲音是從她身旁的一叢三色堇發出。明明無風,花朵卻彷彿有意識般自顧微微晃動,而後從紫色花瓣中顯露一張人類的面孔。
「愛麗絲本來就會和我們說話。」另一朵同樣有著人類面孔的紅色花朵說。
「我不是愛麗絲,我是朵洛莉絲。請問--」
「不,你就是愛麗絲。你想問什麼?」花朵們你一言我一語爭相開口,她大概能知道花園裡的說話聲是怎麼一回事。朵洛莉絲彎下腰,湊近花朵們開口問道:
「妳們有沒有看到一個男的,有兔耳,穿一身紅色?」
「那就是白兔嘛。」
「是白兔。」
「白兔呢。」花朵們婀娜多姿的擺動柔軟的莖與枝葉,掩嘴笑道:
「哎呀說起那白兔啊……」
「你們知道他往哪個方向走了嗎?」朵洛莉絲打斷花朵們的八卦,她有種必須要這麼做否則花朵們會繼續滔滔不絕的預感:「這裡除了我還有其他人嗎?」
「這裡還有很多人唷!」紫色三色堇笑著說。
「像我們,但不是花。」黃色三色堇天真無邪的說。
「白兔不見了。」一旁的紅玫瑰們斜睨她。
「原來是迷路的愛麗絲!」白玫瑰的聲音既尖且響亮,吸引了花園裡其他花朵的目光。花心裡的面孔一一轉向她,有喜有怒有悲有懼,在諾大的花園裡花朵們發出癲狂的笑聲。
「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
「是跟丟兔子的愛麗絲!」不知道是誰這麼尖利一喊,花朵們的笑聲更加高亢而張狂。狂亂的聲響裡朵洛莉絲發現自己被花朵們包圍,她大步跑開,讓飛揚的裙擺落在後頭。花兒嘲弄的笑聲如影隨形,少女停下腳步,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原點。寸步未移。
她只是渴望心靈平靜與踏實。
她只是想找到那隻兔子。
少女的面容清純彷彿未解世事,泫然欲泣的悲傷神情轉瞬即逝。
「這裡還有很多愛麗絲!」
她蹲下握住大把尖聲喧鬧的花朵。
*
朵洛莉絲離開的時候,花園已然歸於寂靜。大堆沙土鋪散在濕潤烏黑的泥土地上,隨著風吹過的死寂消散。
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岔子,還是這就是她在這個世界裡的定位。明明被稱作追逐兔子的愛麗絲,卻有著讓一切灰飛破滅的能力。
「兔子先生,你在哪裡……」
--剛剛花朵們說了,還有很多的愛麗絲。
像她這種連兔子都能追丟的殘次品愛麗絲,就算少一個也無所謂吧。這一切可能都是場夢,醒來她或許會在自己家裡的床上,也可能就躺在醫院裡。
朵洛莉絲看著自己的潔白如初的雙手,抓握生命的觸感像是在海灘抓了把白沙;白沙從指縫間傾瀉而下,最終什麼也留不住。
剩下的就如這片花園般,只有空寂。
少女在空虛的花園盡頭盯著自己的雙手,半晌,她突然將手掌往自己臉上貼去。
「妳在做什麼?」
掌心貼上的是意料之外的溫熱觸感。少年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朵洛莉絲抬起頭,正對上那雙遮蓋陽光的石榴紅雙眼。她愣怔片刻,才愕然放開雙手:「你、你……」
「我是德斯佩。」彷彿之前的躲避與追逐都不存在,有著蒼白面容的少年抖抖殘缺的耳朵,從懷裡掏出一副白色手套,對著面前嬌小的少女揚出白兔皮毛般柔軟乾淨的笑容:「親愛的愛麗絲,這是給你的禮物。」
白兔德斯佩牽起愛麗絲朵洛莉絲的手,他沒有化為灰飛、也沒有逐漸崩解。穿著露骨的白兔只是帶著疲倦而滿足的神情,專注的替少女一指一指拉勻手套。
「好了,這樣就不用擔心你的能力會傷害自己。」
「這是--」
「來了這麼久,妳一定餓了吧?」兔子自顧自的打斷朵洛莉絲的疑問,他一把牽起少女的手將她往前帶:「我們去給妳找點東西吃。」
少女的步伐跨度跟白兔比起來小了許多,但此刻跟在對方身邊卻沒有剛才那番追逐的侷促:她的白兔先生走在前面,只留給朵洛莉絲一個清削的側顏,修長的腿為了配合她縮短了每個跨步的距離。
「德佩斯佩……先生?」沉默維持不了片刻,朵洛莉絲便率先開口:「這裡到底是哪裡?」
「……這裡是仙境。」德佩斯佩正眼不看她,一邊走著一邊回話;握著少女的手倒也沒有要放開的意思。「朵莉,你不必稱我先生……」
「那、那德佩斯佩,你又是誰?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我啊……」德佩斯佩抖抖僅剩的耳朵尖尖,突然放柔了語調:「我是你的白兔,愛麗絲。」
「但我不是愛麗絲。」
「你是朵洛莉絲,我的愛麗絲。」
朵洛莉絲突然回過神:「所以,剛才花朵們說還有其他愛麗絲的意思是--」
「就是這個意思。」話說著,德斯佩一個回身將朵洛莉絲護在身後。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握著尖銳指針的兔子……
--及另一個愛麗絲。
戰鬥的號角響起的突然而迅速。
空間被封閉,展開了滿是鐘錶的背景。滴答滴答的齒輪聲遮蔽空間,對方愛麗絲握了握白兔的手,兩人隨即消失在視界內。
「不見了……?」朵洛莉絲喃喃道。
「那是對方的能力,」德斯佩解釋道,轉頭看了眼朵洛莉絲:「準備好了嗎?」
「嗯。」
「妳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我知道。」朵洛莉絲從德斯佩身後走出,從空間展開的一刻起,許多資訊湧入她的腦海中。她必須戰鬥,必須獲勝。即便她還不了解原因,但她明白,這是她在此應當做的事情。
德斯佩站在她身後,少女至今仍不明白白兔的能力,他在目前為止唯一顯露的不凡處只有碰觸她的雙手不會毀滅。朵洛莉絲站在擺盪的指針中,時間流逝間她依舊沒看見其他兔子與愛麗絲的身影。
「小心!」德斯佩的聲音自後方傳來,朵洛莉絲才轉過頭,一支形制華美的指針便穿透了她的肩背。並不疼痛,但骨肉被刺穿的感覺十分詭異,她的身體像橡膠材質構成,微妙的肌理處有被穿透碰觸的觸感。傷處連一滴血也沒有滲出,朵洛莉絲脫下手套,反手握住指針;指針緩緩從她觸碰的地方湮滅。
她看見握著指針的兔子在不遠處著地,隨手又從四周漂浮的鐘面取下指針。紮著馬尾的愛麗絲不知何時出現在他身邊,認真的開口:「投降就饒你一命。」
「朵莉,別聽她的!」德斯佩的聲音帶上嘶啞,他的肩上穿了個洞,汩汩湧出的鮮血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收止。朵洛莉絲遲疑的開口:「你……」
「別管我,看前面!」在朵洛莉絲再度感受到令人不適的穿透感的同時,德斯佩纖細的軀體在相同的部位綻開血花。白兔少年發出嗚咽,似乎卻已經相當習慣這樣的痛苦,僅如一塊骯髒的破布躺倒在原地。
「啊……真弱。」她聽見對方白兔細微的囁嚅。朵洛莉絲反手朝白兔臉上抓去,卻讓對方輕飄飄的避開來。空間內的指針瘋狂旋轉,陌生的白兔與愛麗絲再度消失,僅剩不規則的各種滴答聲填滿空間。
「唔!」指針開始從四面八方襲來,隨著陣陣破空聲插入少女體內,穿透而過。
「那就是我的愛麗絲……!」她像個垂敗的娃娃,沒有痛楚也不曾流血,後方白兔倒臥在血泊中。他明白,他們始終沒有脫戰所代表的意義。分明正忍受極大的痛楚,德斯佩卻在朵洛莉絲看不見的地方露出欣喜的笑容,任由鮮血從齒間唇縫內滲出。
朵洛莉絲被動的承受攻擊,她不明白也不在乎為何自己不會疼痛不會流血甚至不會死亡,在一次次被衝擊、穿透後,她突然伸手碰觸了空間裡的鐘面。
「既然沒有意義,就全部消失吧。」少女虔誠的輕聲說道。
她碰觸過的鐘開始緩緩消逝,時間的殘骸在空間內飛舞,她站在殘骸的漩渦間看著時間凋敗,瘦小的軀體上插滿巨大的指針,形容畸形而怪異。少女乾淨的湛藍目光穿透虛空,看向癱倒在血水中的少年。
她靜靜的等待著,突然間像是得到了什麼信號、又像是什麼也沒想般,徒手朝鐘錶的漩渦裡一抓。
那是一支短短的時針,尖銳的劃開少女的手。時針的另一邊是另一位少女,讓斗篷罩住的身形終於暴露在飛灰構成的漩渦中。朵洛莉絲平靜的看著少女驚詫的神情,毫無猶豫的伸出柔白掌心朝「愛麗絲」臉上撫去。空間內殘餘的鐘面指針全數停止,煙硝不再迴盪,飛灰碎片漂浮不止。這一刻彷彿被無限延長,只有誰驚恐的吶喊聲拖長了顫音在崩壞的空間內拉長再拉長: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