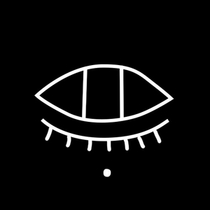
是3557哒。一半内容防爆爆(?
-离散
莉莉·索利达斯很想抽烟,虽然她既没有烟,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很显然自己身无长物,只余下身上所系的细皮带与固定在上的那一对短刃,在大步向前的时候拍打着绒羽的根部和腰背的皮肤。如果放在平时,她会更喜欢咀嚼树脂凝结的香料,但现在她只是有点想像认识的某人一样,将烟斗在手背上磕上一下、两下、三下。
女孩儿的唇间还残留着草药清苦的味道。她一下子分辨不清这到底是药物的作用还是真的沉入了梦中。巡林客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光芒:牛脂蜡烛、海蛇油的灯笼所产生的光芒远没有那样稳定,如此明亮的火焰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气味和烟雾。这里的空气虽然比不上德莫拉海边风暴后那般清丽,但也比窝藏在地下、点满了蜡烛以至于闷热昏沉的小酒馆好上太多。
直到第一名路人经过,冷漠而无言地拨开她半张开的翼翅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在路中央站得太久了。习惯了德莫拉港口的烦扰,站上半刻就会被兜售货物的小贩、兜售诗歌的三流诗人包围的热闹,此处虽然嘈杂却透着股疏离感的忙碌让她不由自主地退到街道侧方,好冷眼观察。城市的天际被精美的弧顶和始终带着湿漉漉光泽的建筑切得支离破碎,锋利的光到处都是,就连莉莉·索利达斯那只玻璃的眼睛都觉得有些不适。
“嗨。”停顿了一小下,巡林客接着说:“我在做梦吗。”
“……是。”另一位翼族收住了脚步,谨慎地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她,“是罢。”
“做梦也逃不过吗。”
尼格勒没有接这句话。他慢慢走向巡林客,羽翼收缩的程度同他的脚步一样小心。而他的问话更加谨慎,根本就没有从口中吐出的意思。过去的同伴、突然离开而没有留下任何音讯的——总之,不辞而别的同行者在梦中再次相遇,现在除了缄默似乎什么都做不到。施法者心中有一百个问题,但看着莉莉·索利达斯满不在乎、只是注視著前方的假眼球和紧紧追随者他的绿色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堆积在喉咙处,无法成型。
女孩儿突然笑了,也许是因为看出了尼格勒的窘迫。她习惯性地试图抛接一枚不存在的硬币,手抬到了一半便停住了:“要不然,我们还是聊聊现在的状况罢,叙旧不适合我们。”
现在就算是对方突然邀请尼格勒一起去喝一杯绿沼蜥的口水,他大概也会立即答应。施法者鬆了口氣,与女孩儿并肩靠在巷角的两侧,说出来的话里都夹杂着背巷里流浪汉的呼吸和咕哝:“似乎是做了个没办法醒来的梦。虽然说某些地标似曾相识,但景色完全不同。说到底,到底是我梦见了你,还是——”
“说到做梦,要不要试试看找个高处跳下来看看?有两种感觉很容易从梦中将人唤醒喔,下坠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种是死亡吧。”尼格勒叹了口气,重新找回了以前一同冒险时候的感受。巡林客干巴巴地鼓了鼓掌,算是某种程度上的鼓励。
“猜对了,没有奖励。”女孩儿用指尖敲了敲自己脸颊。
----
“那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巡林客依然有些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普通的漫不经心,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四处转染的空洞和冷漠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她。更何况神棍般的人她见得太多了,可以说在德莫拉她总和一屋子神棍朝夕相处,实在是打不起精神。
相较而言,这次的闲逛收集来的临时同伴似乎更有趣些。同样携带双刃,似乎眼睛也同样有些毛病的加莉娜在四个人形成的、围绕着占卜师的半包围圈中比其他人要更疏远些,似乎并不适应这样的交谈,随时随地都似乎要隐没进冷漠的人群;算不上熟悉也谈不上陌生的尼格勒相较而言离自己更近些,两人半张着的翼翅没有交叠,只是最长的飞羽不近不远地相指着。女孩儿不易察觉地翻了个白眼,不是因为出于不屑,而是要保持着脸的朝向大致不动,乜斜着眼睛想要好好打量卡尔·加埃塔诺·马里诺是一件与记住他名字差不多费劲的事情,她的眼睛都瞪酸了。幸亏占卜师小姐的脸庞半掩在兜帽下,一方面保护她的面容不被众人窥探的同时,大概也保证了她看不见莉莉相当失礼的白眼。
“代价吗。用你们的故事来换如何?”女性的笑声有些发空沙哑,像极了大部分占卜师仿佛洞悉了一切奥秘,光用声音就能搅拌坩埚里的蟾蜍汤的笑声,“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好故事可比金钱重要。”
“那么占卜所能揭示的、你所会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尼格勒的声音短促,没有女孩儿不知从何处学来的虚与委蛇。
“不先来试试吗?神谕。既然不需要钱,不想试试看吗?”
一阵尴尬的沉默。莉莉正在脑海中理顺下一句要说的话,想尽办法试图不着痕迹地从对方口中掏出更多的话来,又不会让自己太难受。想必自己脸上的表情既生气又出神,以至于尼格勒用翼尖碰了碰她长羽的尖端,大概是以为自己突然发起了呆。女孩儿瞥了他一眼,算是作为回应,刚想开口——
“那就试试。”另一位巡林客干干脆脆地吐出四个字,砰地一声砸在地上,把尴尬的空气砸了个对穿。莉莉·索利达斯从未如此希望自己也是个能言善辩的吟游诗人,不必在帽子上装饰花里胡哨的羽毛,至少能轻松快速地用真话说谎言,不必思考那么多。
占卜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只是发出那种轻柔沙哑但并不难听的笑声:“行罢。你们抽到的那张,就是你们的现在。”
加娜莉抽出那张代表现在的牌之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牌面相对而言还算朴素,只是简单地绘着巨龙喷吐着火焰的场景。
“你们现在正面临着一股无法对抗的力量,正是那股力量将你们留在了这里——”占卜师碰了下卡片的右上角,薄薄的材质在她的指尖下弹响,“仅凭通常的手段,你们无法与它对抗。”
莉莉的注意力全被她颈上悬挂的、蝉的吊坠吸引了,而尼格勒既不满也不甘的挣扎发问也被占卜师忽略了过去。她就像开始了一场表演的魔术师,走进了自己的节奏之后,不打算为任何话题停下脚步:“下一张牌就是你们的未来。”
如果放在以前,莉莉·索利达斯在抽这种所谓的未来的时候,立马会把它攥成一团然后吃下去。她完全不相信占卜,说是不想,其实更是不愿。女孩儿飞快地伸手将那张牌抽出抓紧,似乎慢上半秒未来就会不受掌握地从指缝间溜走。
“真老套。”她咕哝了一声,将绘着瑞图宁女神手执带着新芽枯枝的卡片稍稍倾斜,算是照顾一下踮起脚尖的小个子卡尔。
“这张卡代表,你们一定能够转为为安……无论你们遇到了什么,呵。”
“真是不知道该说是定心还是担心。”尼格勒也轻轻咕哝了声,无论从响度还是声调上都有些类似信鸽。占卜师抖了抖手腕,不知是把厚厚的一叠卡片收回到哪里,取而代之的是分置在她双掌中的宝石和水晶球。
“梦的旅人,你们想要选择那条道路?”
----
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了。即便是拿到了地址,问路也耗费了很多心思:大部分人只是敷衍地随意一指,连一个多余的字都不愿意说。四人只能顺着大概方位逐渐摸索,这里初看奇诡特别的建筑也逐渐腻味了起来,再怎么说也比不上真正人工构筑的城市看得顺心。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莉莉调整了一下皮带,“说真的,在路上突然拦着你非要给你占卜,可能就差在自己脸上写上‘有阴谋‘几个大字了罢。”
“至少比漫无目的的游荡要好。无论是好是坏,是阴谋还是偶然,只有不断推进事件的发生,才能获取更多的动机目的。”尼格勒颇为在意地放慢一下脚步,加娜莉之前果断地出言将“现在”捏在了手里,但随后又恢复了与其他人若即若离的状态。而与之相反,莉莉·索利达斯大跨步地走着,以至于卡尔不得不走上两步紧接着跑上几步,才能勉强跟上行进的节奏。简而言之,也许除了尼格勒,其他的人并不怎么在乎临时队伍的团结性——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卡尔应该排除在外,他全幅心思都放在跟上其他人的步伐上了。
越靠近酒吧的大致位置,行色匆匆的人就越多。比起在其他地方随意、漠然的态度,這裡的行人们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丝迫切。明明是下午,天空却有种说不清楚的昏暗,但不佳的光线倒也不影响众人远远地便看到了那块画满了眼球的酒馆招牌。
“品味好差。“女孩儿脱口而出,随即不得不停下咳嗽了好几声。酒馆在这条支路上有着相当夸张的存在感,除去招牌上遍布的眼球之外,连外墙上也散落着好几处眼球花纹的装饰。“一般来说,被这样盯着一定会心生厌恶或者恐惧吧。大概、生意不会很好……?”
她从没听过这样安静的酒馆,就像那不是饮酒作乐的地方,而是墓地或是其他了无生气的的场所。莉莉·索利达斯所熟悉的酒馆应该充满了交谈、划拳、大吼和醉话的动静,也许还会有下流的小调和酒瓶碎裂的声响。但这里太安静了,以至于尼格勒敲门的声音都带着小小的回声,没有招呼也没有吆喝,只是似乎有几百年没有上油的铰链发出吱嘎的声响,从门缝里透出昏暗闪动的光芒,完全不足以照明。
没有劣酒兑水刺鼻的气味,也没有油脂、木柴和人的味道。酒馆中央的光线还算充足,但也被许多破碎的形状遮挡。暗光在相对而言低矮的数排桌子边勾出相当多人形的轮廓,人们紧密地坐在原处,超过了一般来说安全舒适的心理距离。但显然他们不在乎,只是低着头、专注地——
冒险者们无从得知这些人们在专注于什么,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从酒馆上方昏暗而支离的阴影中垂下的金属,像是手掌或者藤蔓般沿着脊背,生长进那些人的身体之中。
他们闭着眼睛,似乎全部都在做梦。

加莉娜清楚自己是在做梦:这地方有什么都不奇怪,长满发光眼睛的钢铁城墙、投下虚幻帷幕的彩色弧顶、油垢腻着烟气熏着的怪异小巷……
可这实在又太奇怪了。在加莉娜尚且年幼又活泼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对她讲过,梦是人的寄予,梦是记忆的整理,梦是心灵的旅行——梦是现实的投射。一个遗都人想不出维斯的刚朵拉,长寿如精灵也不会明白短生种是怎样尽力奔跑、追着永不回头的河流。那么,她是怎样想出眼前这些东西的?这些僵硬冰冷的死东西、钢铁炼熔的寒冷森林?树木笔直向上,将天空啃咬出不连贯的缺口,残存的天空边缘线条曲折,还常撕出一道道细窄缝隙,迷幻的光和规律闪烁的星子就从那裂口往地面窥视。
雪精灵固执地走着,她面朝那个奇形怪状的神殿尖顶,使出她盯着猎物的毅力和忍耐,一刻不停地走。这是什么梦?她问,朝某个不知是否存在的对象:什么样的人会在梦里这样为难自己?追求一个永远到不了的道标?我可不干,不干了!
于是她突兀地停下来,望着远方那许多东西,披着钢铁的壳子,里面不知什么样,还有个顶上全盖着玻璃的东西,肚子里透出黄色的光。加莉娜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又带着点谨慎看看四周,倒还真有个发现:
两个翼族,一个侏儒。
他们穿着同样不合时宜的衣服,身上带着武器,跟她一样往前——也同样停在原地。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这三个赶路人也只能停下脚步,商量接下来的办法,其中,那个侏儒摸摸耳朵,又抬起手扶了下帽檐,接着他无意一瞟,目光恰好和加莉娜对上。
这就是几位梦中旅人相识的过程。
“这里大概是菲薇艾诺。”卡尔说。
他是一个工匠学徒,做首饰的,同时也是信奉珂宁的牧师。卡尔指着天上的弧顶,为身边的队友解释:“东西向的那条是‘拉文·艾佐’,西南向的是‘尤文·坎’,东南向的是‘菲宁·希尔’,也就是黎明、正午、午夜。
“……我们刚刚经过的应该是尤文·艾佐·希尔,也就是商区,我记得这里有家甜点特别好吃……嗯……对,‘门’应该也在附近。”
冒险者们在这莫名的地方走了段时间,没有十分有价值的收获。听着卡尔软绵绵的介绍,加莉娜仰着脖子看天,一点也不在乎这样行走会撞到其他行人,反正他们就算低着头也总能游鱼一样避开自己。这冷硬的城市依然会迎来黄昏,亮白色的光球一齐绽放在路旁竖着的铁杆子上,稳定地将光明洒在近旁;远处闪烁起令人惊叹的光,像彩虹女神手中落下的泉水,也像极北抚过夜空的柔软纱帘。
那是什么?
雪精灵皱着眉头,尽力将今天看见的一切想个明白,她在努力,试图从记忆里扒拉出点能派上用场的灰烬。这几年她一直将精力放在复仇上,对其他事物不大上心,可毕竟,她生在深林城,那是北方精灵联盟的首府,同精灵王城比也不会相差过多,可这里……
“几位旅人,要不要来试试占卜?”
他们循着声音看去,那是个坐在街边的占卜师,宽大的兜帽遮掩她的面容,从声音判断,那应当是位年轻女郎。雪精灵对这类虚无缥缈的活动一向没什么好感,难道她的命运就寄托在那几张薄薄的纸片上?这些人强硬地将不可捉摸的线条收束于点:概括性的几个词。再由点生发出——或者说建构起——对应的画面,内容取材于诸神,连捏造的功夫都略去。过去、现在、未来……口唇里落下的字句轻而滑,话头留在那里,剩下的交由询问命运的人自己补全,这实在是不错的生意。
而我的命运、我的命运……
“那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说话的是莉莉·索利达斯,她同尼格勒都是翼族,两人之间也更为亲近,像是之前就认识。很明显的,巡林客是两人中更能有技巧地使用语言的那个,在其他人尚且犹豫时,她回答了。
“代价啊……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如何?”占卜师稍稍抬起头,雪精灵能感受到她视线的停留,接着,她发出轻笑,像想到什么趣事一样,“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好故事可比金钱重要。”
加莉娜站在队伍末尾,最外围,她的脾性教她难以融入团体,或是与其他个体发展出稳定友好的关系。此刻,雪精灵睁着眼,面前的对话流水一样过去,没让她留下一点印象。直到不久前,她还一厢情愿地认定眼前的一切都是她那破损的脑子作怪,凭不知哪里听过的只言片语造起梦中的虚构楼阁。现在她倒是明白过来了,可那又怎么?她就得作出应和吗?
……
“至少我本人并不相信占卜的真实性,权当以故事换故事吗,或许不坏。”语言就那样从年轻翼族的口唇中流出,自然又快速,目标明确,“不过,好故事比钱重要,这样的说法倒是……很特别。”
她停顿片刻,说出那句话:“在交换故事之前,不如解释解释所谓神谕,权当展示一下你的诚意如何。”
“行啊。”占卜师说,并没有特别在意之前所说的“酬劳”,满不在乎地答应了。她从面前的桌子左侧扒拉来一个盒子,手指拨开锁扣,从里边拿出一叠牌。占卜师切牌的姿势很漂亮,动作流畅,这副姿态能为她挣来不少东西,至少在顾客看着她,焦急地等着命运的审判、等着天上落下的定数时,这好看的姿势能让占卜师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加分不少。
“抽吧,你们抽到的那张就是你们的现在。”她将牌顺着抹在桌面上,摆出一个好看的弧。
就在加莉娜神游的当儿,对话已经进展到她所能想象的前方。尼格勒和莉莉对视一眼,法师伸出手,干脆地抽走其中一张:
卡片上,一只巨龙正向山下吐着烈焰。
“嗯……”占卜师接过那张卡,随着她的动作,挂在她脖子上的吊坠落在领口外,那是个蝉的样子。
“你们现在正面临着一股无法对抗的力量,正是那股力量将你们留在了这里——仅凭通常的手段,你们无法与它对抗。”
翼族法师听到这话微微皱眉,似乎对占卜师话语中的某些词持不赞同态度,他问:“那么, 不通常手段呢?”
占卜师停顿片刻,通过她的动作,可以推测出她将视线放在尼格勒身上,又在片刻注视后将话题挪开:
“下一张牌是你们的未来。”
莉莉·索利达斯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抽取那张预示未来的卡牌。在这张卡牌上,春之女神瑞图宁手握一根枯枝,枯枝顶端长出了新芽。
即使在不明白神谕卡规则的雪精灵来看,图片的寓意也已十分明显,事情正如她所猜测,那占卜师再次笑起来,解释道:
“这张卡代表,你们一定能够转危为安……无论你们遇到了什么,呵。”
雪精灵还未来得及因占卜师的故弄玄虚发怒,就被对方取出的两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她将一块红宝石呵一个水晶球摆在桌面上,接着做出一个展示的手势:“梦的旅人,你们想要选择哪条道路?”
漫游的神思被某个字点醒,加莉娜问:“你知道这是梦?”
雪精灵的语气因她的急切和弥漫的些许怒气而显得有些咄咄逼人,好似她握着一把利剑,让剑尖悬在对方眼前。占卜师没有因雪精灵的突然发难而瑟缩后退,她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神色不变,兜帽遮住她的脸,让人没法从她表情的变化中窥视她的内心,但她放松的姿势足以说明她的毫不在意。
“梦和不是梦,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也许占卜师是以一个极为轻松的态度问出这句话的,这是面对雪精灵的一个简单回应,不必花费太多心思的说明,没什么意义的一个反问,试图将问题推还。从加莉娜的反应来看,她成功了。雪精灵此刻被身体深处骤然升起的喧嚣控制,那团嘶吼着袭来的风暴是如此激烈,加莉娜甚至没法在短时间内辨清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情绪。她不由自主地顺着占卜师的话语往下想象,是的,她向自己承认,梦与非梦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痛苦始终如乌云一般遮住她的头脸,伸出柔软的须枝扒着她,附在她身上,让一切明媚沾上黑灰。
“我讨厌这里。”加莉娜·伊万·涅夫回答,她说完这句,便不再开口。
尼格勒见她不再有继续对话的意向,问:“那这两条路,会引领我们去到哪里?”
“回家的路。”占卜师简略回答。
“至少我做梦还能梦到些美景……这两条道路有什么差别?”莉莉站在尼格勒旁边,打量着摆在桌上的两样物体。
“一条探寻你们自身,一条探寻这个世界。”
终于,一直站在桌边的卡尔提出疑问,他眨着眼看向占卜师,木桌遮挡他的视线,侏儒只能费些劲抬起头:“这个世界?这不只是一场梦吗?”
占卜师没有回答,只是伸出食指敲了敲木桌的桌面,催促这些梦中旅人快些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一阵商量后,这些外乡人的手指向水晶球,得到一个地址:眼珠酒吧。
“这个名字很有遗都风采啊……”尼格勒低声说,他想起将自己领回去的那个半精灵,不知他现在如何。
“所以,占卜师小姐要一起去喝一杯吗?”莉莉还记着之前的那个条件,“你要求的代价到了那里一并付清,如何?”
“这就不必了,小姐。”占卜师回答,“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旅程。”
顺着对方的指引。他们逐渐偏离宽敞的大路转向延伸向四方的岔路,又在经过几个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路口后拐进一条并不算大的街道。他们并没有花费很大力气就找到了水晶球预示的眼珠酒吧,它的招牌有些倾斜,在周遭不知用途的成束黑色粗线的遮挡下,经由的路人仍能一眼发现它——招牌上画着的许多眼球正从不同方向望着你。
这时候还是下午,在加莉娜的经验中,这是许多人一天中精力和热情稍稍减退的时刻,清晨的清醒随着时间磨损,午后强烈的阳光又常照得人生出困意……可这时候人们又得忙着将手头上的工作与任务解决,以求早些回到温暖舒适的家。在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地方说温暖舒适的家有些叫人疑惑,但道理总归是差不多的,只有闲汉无赖才会整天将自己浸泡在酒吧中,反正也没救了,不如来点甜头找点慰藉,寻求此时的快乐。因此,加莉娜认为酒吧中的寂静是符合常理的,可她又感到不快活,一片安静,某种氛围让她警觉,看不见的、被压缩成固体或液体的东西在酒吧门口踱步,审视这些外来者,间或伸出细长灵活的舌头舔舔尖利的白牙。
雪精灵不顾还在观察的队友,走上前推开活动的木门进入酒吧。一种叫人不愉快的湿冷扑上来,翘着尾巴钩住来客的脚踝,酒吧内部相当阴暗,没有“赫鲁晓夫”燃烧整个冬季的火炉,只有一些冷色的光在闪烁。大体上,这里的布置与加莉娜印象中的酒馆很是相似,尽管她只去过那一个酒馆,但这类地方看起来总是差不多的:桌子、椅子、人。
酒吧的客人们都坐在桌边,一根根东西从笼罩顶部的黑暗中垂下,那些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光彩的树枝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冷硬,它们甚至可以称得上柔软。这些树枝并不像道路上排列整齐的铁杆子一样笔直地刺出地面,带着一种力道与狠劲,而是以一种生物会有的韵律轻曼地摆下,像舞者做出手势那样,你会觉得那部位是活的,单独活着的。又是这些东西,以与外表不相称的锋利刺入人的脊背,植物的根系从死体上吸取养分或许也是这副样子,显露在外的部分看起来柔软又无辜,底下的却紧抓着培植自己的基体不放,细弱的分支蓬松地充盈,只有将它们拔起来才能看到那副惹人厌恶的贪婪模样。
雪精灵瞪着这副景象,她恍然自己的脑袋被放在黑暗的土壤里,隔着一层松软的沙土,再往下数一层带着点湿气的土层,接着才是她眼前看到的——这些人干嘛让植物的根茎扎在自己脖子后边?顺着这些根系往上,离开这黑暗的空间,这些金属植物会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
她想看看。
巡林客将心中的好奇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她没有忘记自己所处的状况。于是她让视线飞快往四周一扫,在确认没有可能存在的危险后,才走向那些金属植物。而在她背后,她的队友们前往房间一角:那里有这里唯一一个活动的人,他正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
他们都活着。
这是加莉娜确认的第一件事。她将手从温热的脖颈间收回,雪精灵可以感受到手指下跳动的脉搏,它很稳定,象征眼前的生命健康且平静,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加莉娜又顺着从颈椎摸到脊椎,那些管子正是在这条曲线上扎根,埋入人体。为着自己的方便,雪精灵提起眼前目标的背部衣料,凑上前透过制造出的空隙往里看,她不去在乎礼节与其他东西,只顾满足自己的好奇。加莉娜眯起眼,配合手的动作一点点确认,她发现在第三节颈椎所对应的部位有个小铁片,正正方方的,还有钉子的头部露在空气中,上面垂下的树枝就从这里进入他们的身体。来自深林的雪精灵用手指推了推这闪着银色光辉的小铁片,推不动,用指甲抠,也不动弹,她较上劲了,狠命去掐,倒是撕出一个口子,让铁片周围的皮肤与这薄而平的小玩意儿分隔开。红色的液体流出来,加莉娜皱着眉头拿开手,将之前拎起的衣料放下,按下,血液被不知什么材质的衣物吸收,洇出一片暗红。
不动声色地处理完这些事,雪精灵后退一步,终于忍不住去看这些人的脸……他们难道不会痛吗?
那是非常快乐、美好的表情。
曾经加莉娜也有这样的表情。当她听到母亲的呼唤,提着裙摆穿过树林,轻巧地跃起跳过粗壮的树根;当圆月洒下糖霜般的银粉,鸟儿衔起来吃下,于是唱出甜美婉转的歌;当柴火噼啪作响,母亲陪在身旁,父亲伸出手臂搂住她们,不善言辞的男人看着妻女火光映照下橙色的脸,体内的幸福要堆积不下,只得轻轻叹口气。
——就是这样的表情。
嫉妒的火焰燃烧起来,加莉娜双手抱臂深呼吸几下,她抓着自己的手臂,指甲掐进肉里。做梦多快乐啊,是吧?雪精灵恶毒地诅咒,别起来了,睡下去,看看那些假东西,然后现实里所拥有的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溜走,如同水流漏出指缝。
发泄一番后,雪精灵的心情很快好起来,她想起自己的队友,就往之前的角落走。翼族正在和那人交涉,他们身边还围着几个散发柔和光芒的光球,这些圆圆的东西按照各自的速度行进,在空气中划出自己的轨道,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所有光球都绕着一个中心旋转,它们各自倾斜着经过的路线正巧能练成一个个圆。等加莉娜回过神,吧台里的人已经拿着酒瓶喝起来,那酒似乎是翼族法师从上着锁的柜台里拿出来的。放出光球的法师仰头灌下几口酒,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他的动作很急,像饿了许久的人看到温热饭菜。
“告诉你们一些事吧。”他晃着酒瓶,最初的几口很好地缓解掉他对酒精的渴求,现在他算有闲情逸致去说些别的。
“可不要学他们那样,”他伸出手用大拇指点向其他人,“被那种东西接入,能够去另一个世界——不过,你的脑袋,可是会就此坏掉的。”
“你去过吗?另一个世界。”尼格勒问。
他耸耸肩。
“那些树枝是什么?”不顾队友的提问,雪精灵说,“我在苏利文从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那可不是树,那是 的一部分。”
加莉娜没有去探究对方话语中的缺失,那被不知名力量凿掉的浮雕,象征名字与荣誉。雪精灵只以为这是另一次的幻听,她常常这样,在无人处听见呼喊,看见早已消亡的身影。她的注意力很快分散,滑向其他地方,漫无边际地飘荡,那人的声音将她唤回。
“……你们觉得这酒吧里的眼睛,是谁的眼睛呢?”他问,“嘿嘿,说是画在墙上的,搞不好是长在那里的……你们怎么想?”
他动动手指,规律运动的光球四散而去,隐蔽住酒吧的灰暗在光芒下溶解,露出一直存在的真实样貌:眼球,数不尽的眼球,它们覆盖在墙上、柜台上、桌子上,铺天盖地,如同堆积在河底的石子,这些饱满的果实有的半睁,有的阖起,有的滴溜溜在眼眶里打转,成束的茎干埋在掩体下方,四面八方的通路都向上奔,也正是金属树枝垂下的地方。就加莉娜看来,这实在有些像长满树瘤的古木,树皮的纹路将这些突起串连在一起,作为树木的丑陋装饰,那瘤子里面指不定包着什么恶心东西,要是拿锐器戳破,说不定还会滴下浓稠的灰绿色脓液;也可能是被邪恶力量污染的畸形巨蛛产下的卵,有坚韧湿润的膜保护内里,可那东西总能被挤裂,于是未成形的怪物变为死胎落下,柔软的肢体粘在一起,被母体吃掉作为营养的补充。
加莉娜在直视这些东西的时候感到某种莫名的恐惧,这和她跪在焦土上哭泣时不同,这情绪不是由未来的失却带来,而是某种更深刻、更宏伟的……她感到一阵恶心,忍不住后退一步,挪开视线,低下头去盯自己的脚尖。。
“他们是在做梦……呵哈哈,在梦中做梦。”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她听到尼格勒冷静地提问。
“是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碰面有什么意义呢?哈哈哈,塞西尔把麻烦的事推了过来。”
在自顾自笑过一阵后,他说:“你们要找到书,能够打开梦神神殿的书。”
接下来的对话不再能吸引加莉娜的注意,她迈开脚步回到木桌旁,伸出手触碰。树枝是冰凉的,和真正的枝桠不同,这些树枝很齐整,有着相同的宽度,可以想象,如果横着切开它们,所有的断面都会是同样的圆。加莉娜试着去捏手上那根,它稍稍扁一点,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柔软,巡林客拔出腰后带有肠钩的短刀试图割裂树枝,一股阻力阻止她的动作,她能凭经验判断伤害的造成,但想要割断它们似乎要花更多的力气,如果她强硬地砍上去,金属树枝与她的短刀会两败俱伤。
“……加莉娜?加莉娜!”卡尔从吧台小跑到雪精灵身边,他叫她的名字,没反应,于是侏儒只能抓住雪精灵的衣摆摇晃几下。
“怎么?”加莉娜带着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该走啦!”卡尔没有去在意雪精灵不十分友善的语气,他照旧带着那有点软绵绵的笑容。
“去哪儿?”
“找一本书,嗯……”侏儒好脾气地回答,他好脾气地解释雪精灵因神游而错过的那段信息,“是这个城市里剩下的唯一一本书,好像怎么也毁不掉,要是把它给丢下,说不定还会‘呼啦——’一下飞回来。”
“等找到那本书,进入梦神神殿,我们就能回家啦!”
听到队友的解释,加莉娜总算有些动力,她跟在其他人后头,往酒吧的出入口走。
“去城中央……呼啊……”
被尼格勒搬到椅子上的法师抬起一只手伸出食指胡乱摇晃,他说梦话似地挤出这样几个字,接着又睡过去。
冒险者们在眼珠酒吧里耗去一部分时间,等他们再次走在街道上,天色渐渐暗淡,已接近黄昏。就在钢铁森林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就快和行人投射在地面游来窜去的影子融为一体时,荧蓝色的光从天上的三道弧顶向四周展开,在几个呼吸之间铺满城市的天空。加莉娜之前没见过这样在浑浊的同时还刺眼的颜色,她抬头看着望不到边际的天幕,想起书中提过的一种水生植物,南方的夏日尤为适合它的生长,据记载,河网联盟的部分河道会因为该植物的繁盛挤满绿叶,船只难以行走。现在本该洁净的天空也被莫名其妙的光芒污染,星辰也无法落脚——谁乐意到这样肮脏的池水中嬉戏?
光幕中由远及近走来一个女孩,她看起来像是精灵,可与真正的精灵相比,她的眼睛过大,几乎占去脸部的四分之一,像有人抠下两颗过大的玻璃珠子摁进眼眶。还没等加莉娜从突如其来的厌恶中回过神,那女孩动起来,她轻盈地转了个圈,蓬蓬裙表面的纱也扬起来,本该十分有活力的动作搭配上女孩过长过细的四肢,落在雪精灵眼里就像切掉线的人偶自己摇摆起来,僵硬死板。
“大家晚上好——我是大家的播报员夏绿书❤梦里的各位和清醒的各位,接下来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加莉娜将视线从不知怎么跑到天上的女孩脸上挪开,继续向前走,就在她低头的时候,那女孩偏偏头,视线交错……
就像她正在注视着他们一样。
tbc.
————————————————————————————————————
全文7312
由于角色(脑子不太好)的原因,可能一直都是po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