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只是因为吃了一口喜欢的食物,便莫名穿越到了这片味觉的大陆。
含糊其辞的神明的话语,来历不明的怪物,从未经历过的战争景象。
究竟为何而战?我们能活着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前方荆棘满布,充满迷雾。
那么,我在此真诚的期待各位冒险者的到来。
本企本质为有口味元素的架空幻想大陆企,为剧情向企划。
企划终章已开始,终章时间:2020.06.09-07.10,此后企划页面将会关闭,即为仅可浏览企划页面,不再接收相关产出的投稿。届时将通过企划E-Group供各位玩家进行后续的剧情补全及日常互动。企划小组内的投稿不再计分。
角色属于亲妈,OOC属于我
纯属丢人之作
字数:3443
灰黑色的天空沉得如同铅块,仰头去看它更是一片即将倾倒的沥青,潮湿的空气将所有的东西都黏在了皮肤上,四周围没有半点声响,不管是虫鸣还是鸟叫,这里像是一片被抛弃的陆地,只有泥土和建筑,弗莱茵侧了侧脑袋,余光看见了自己脚趾间沾着的泥,辨认了一下方向继续向前走。
“你不进去吗?”有人在耳边问,不破之吸了吸鼻子像是嫌弃这片土地的样子,腥臭、潮湿,还弥漫着奇怪的氛围,面前的建筑破破烂烂的,玻璃早就已经碎得精光,风蚀地貌或许都比这里要有观赏性,“女士优先。”
“是你不想进去不是吗?”弗莱茵抬起脚掌,用手拍了拍黏在皮肤上的泥。
整片城市如同被死寂包围,奇怪的植物盘旋而上,沿着建筑物一路延伸,朝着没有光线的天空延展,如同殉教者那般向着他们的神明伸出手而后溺亡。
面前的建筑物上刻着奇怪的文字,他们两人——或许更多,被抛弃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被引导向了这个建筑,不破抬头看见了在二楼窗口看着他们的男人,军装一丝不苟,他发誓,绝对在哪个新闻或者任务中见过他。
弗莱茵也看见了,但是她似乎跟专注于研究墙上被植物和空气侵蚀的雕刻,那些纹样有些像水浪。
指尖触碰到的地方几乎全是水汽,黏腻而腥臭的感觉挥之不去,然而碾了碾指尖,那里并没有任何东西。
这片土地甚至不能用已知的知识来判断地处何处,她到现在才有了来到异世界的实感。所有的东西都有着类似的既视感,然而并不能找到合适的出处。
说着女士优先的青年还真的就站在阶梯下,一动不动地看着弗莱茵偶尔才看一眼二楼的影子,过了好一会不破抬了抬手,面带微笑——那绝不是好意,他示意面前的女孩先进门。
“我相信你的反应力比我快。”不破之睁眼说瞎话,他向上拉了拉那件鲜红的毛衣,假装没有看见面前陌生人奇异的表情。
因为那实在不能被形容为‘笑’。
二楼的人也看见了,那张脸似乎有一瞬间的停顿,很快又隐进了死角之中。
皮肤贴着石砖蜿蜒而上的声音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
贝塔像是被这种轻而特殊的声音吵醒了,她从位置上爬了起来,碰落了自己的糖果,那些色彩奇异的圆球一个个落下来,砸在地板上。
似乎有谁笑了一声,走路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谁拉响扳机的动静。
“我睡了多久?”
她抬手的下一瞬间才想起来自己早就已经不在原先的世界了,圆形的石桌边已经坐下了好几个人,空气中的泥土味和潮湿感依旧让人喘不过气。
“是尸体的味道。”麻花辫的女孩一口咬下手里的章鱼烧,颇有些含糊不清,她看了看门口,却没能如愿看见来人。
“还要等多久?”贝塔打了个哈欠,缓缓地靠在了不舒适的椅背上。
房间的整体风格透着奇怪的氛围,看不出原型的石雕落在房间四周,散落成碎片的窗框和早已生锈的金属装饰被蜿蜒生长的粗壮植物包裹住。或许房间里还有过漂亮的画作,已然破了个洞的墙壁也不会提供任何线索,只有断成两半的画框还有一些遗留感。
“谁知道呢。”后藤奈奈子吸了吸鼻子用手指点着在场人员,“椅子一共有十五个,我们至少还要等十个人吧?”
坐在窗边的男子松了松自己的领带,毫不在意地靠在椅背中,他看见了那两个从门口走进来的人,虽说眼熟但也还不到能够精准叫出名字的地步,青年似乎在进门前和金发的女性交谈了什么,两个人都多多少少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夏佐眯起眼睛,轻轻敲了敲自己的扶手,那两个人都不是善茬,即便上楼的时候脚步声响的傻子都能听见,换做专业人士估摸着连其中一个人的气息都感觉不到。
他将视线放在了那个拆棒棒糖的少女身上,对方迅速将视线挪到了他脸上。
在场注意到这一点的不止他一个。
不如说——
“分我一个?”他开口,微微抬着嘴角,不带名不带姓,口吻熟稔。
对方随手捻起一个棒棒糖,那个东西打着旋从桌子的这一角滑到了另一边。
与此同时的,在走廊里回荡的脚步声终于有了结果。
“是个女孩子呢。”奈奈子挥了挥手,指了指最近的椅子,“可是人好像还没到齐。”
走进门的少女拖着快到小腿的金色长发,也不拒绝,直接往陌生人的身边坐,跟在后面的青年则是单手拿着狙击枪落座于少女的对面。
“我还以为你们是熟人。”夏佐没有拆那粒糖果,而是拿着塑料棒敲击了一下桌面。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没有朝我们扔刀子那真的有点可惜。”弗莱茵做了个毙命的手势,“说起来,你们在等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太过于直接,谁都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有坐在角落里的男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个女孩,而后又垂下头去保持沉默,嘴唇无声地开阖了一会,有点像是在祷告。
弗莱茵曲起双腿,整个缩在椅子里,看上去像是个无知少女,奈奈子看了看对方,判断出脖子上的淤青似乎与刚刚进来的男性手掌大小有所区别,思维发散了一瞬间,毫不顾忌地开口提问。
“你是清道夫吗?”
似乎有什么东西挠着地板,盘旋着发出细密的声响。
“为什么这么问?”
夏佐的视线终于从棒棒糖上挪开,看向了两个女孩。
“因为姐姐身上有死人的味道呀。”奈奈子指了指桌子下面,“那是姐姐的宠物吗?”
贝塔抿了抿嘴角似乎不愿意去细想盘旋在阴暗角落里的东西是什么,她看了看那个和金发女性一起走进来的青年,对方露出一个无害的笑而后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不要多问才是最保险的方式,不破活动了一下食指,那是下意识扣动扳机的动作。
他看见了那个大学生往桌子底下粘东西的手势,大有不行就连带着所有人一起炸飞的意思。
他敢保证不久前看见的那个炸弹犯就是这副嘴脸。
弗莱茵歪了歪脑袋,视线根本没有落在面前的小姑娘身上,她毫不顾忌地动了动手腕,从阴影里钻出一条黑长的东西,叼着那个章鱼烧爬到了门外。
梳着麻花辫的姑娘既不恼也不羞,反而是吐了吐舌尖将一整盒章鱼烧都给了面前的陌生人。
“这里似乎没有我们以外的别人。”奈奈子说,她看了一眼那个坐在不远处的白色女人,背后冒出了一点冷汗,那并非是恐惧,而是一种类似对于同类人的抗拒,“但是有人叫我们在这里汇合?”
“你确定吗?”贝塔似乎又困了,张开嘴打了个哈欠。
“我是跟着那个疯女人走过来的。”不破扬了扬下巴,出卖了弗莱茵,“还被她打了。”
“唔……先不管是不是叫我们汇合。”弗莱茵没有接不破的话,塞了一个章鱼丸子进嘴,毫不担心那里面到底是什么馅料,“他说我可以尽情——”女孩做了个手势,所有人的眼球盯着她的手指晃了晃。
杀气四溢。
“为所欲为这个成语或许不贴切。”在角落中一直沉默着的男子开了口,他长得高大精壮如同一柄长枪,完美体现了坐如钟的说法。
坐在角落的女人接上了他的话茬,“但是既然这里只有我们,或许可以默认,目标就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
坐得最近的不破从指尖撵出一粒咖啡豆,默不作声。
奈奈子似乎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她张了张嘴,却被弗莱茵捏住了手指,金发的女孩开了口:“我不介意哦——毕竟少一个人是一个,少一双,也落得清净。”
那名白发的女子不再说话。她用余光看了看正对面的男子,眉峰挑了挑。
“那个声音说的大陆不会是这里。”夏佐开了口,他始终没有拆那粒糖果,只是盯着刚才扔章鱼丸子的黑色角落,“这里看上去就已经被毁光了,在这种废墟里打架是不是有点——”
或许是英国人的习惯,贝塔看见他手腕活动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那怎么出去?”
不破用指甲打开了那颗咖啡豆,焦香四溢。
“还有钱。”木吉补充了一句。
“打家劫舍也没地方呀。”弗莱茵接上了话,“先找出路?”
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
“那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后藤奈奈子眨了眨眼睛,透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这里似乎也没有我的研究对象。”
贝塔困极了,又趴了回去,“似乎确实没有意义。”
木吉和那个女人先后站了起来,高大的男子绕开了那些黑色的角落,又摘走了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衣角上的章鱼烧。
“你的眼睛很漂亮。”娑诃从弗莱茵背后用双手不抬起了她的下巴,使得女孩不得不仰头看着她。
两个人的体温都有些低,一时间冲到天灵盖的血腥味包裹了她们,奈奈子不动声色,又极为嫌弃地捏住了鼻尖。
“你很喜欢吗?”女孩笑了起来,“Con nulla non si fa nulla. ”(不付出就得不到)
“गहरे पानी में एक मगरमच्छ की शक्ति होती है।。”(鳄鱼在深水里才有力量,离开了水,只能任人摆布)
娑诃又扭头朝着满脸疑惑的奈奈子笑了一下,说了一句什么下了楼。
“你们刚刚再说什么?”
“嗯——希望再见之类的。”弗莱茵睁眼说瞎话。
明显感觉对话氛围不是那么友好的不破在听见那两个人前后离开的声音后起身。
“我说,你来之前干了什么你老大要把你灭口。”
夏佐没有抬头,只是竖起了耳朵听。
“我也不知道呀。”
面对弗莱茵的间歇性发疯,不破只是挠了挠脸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夏佐大约是觉得没有好玩的了,也离了座位走之前把糖果塞给了奈奈子,“早点离开。”他说。
奈奈子吸了吸鼻子,起身就走,连再见都没说。
木吉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里什么都没有,即将倾泻而下的颜色铺满了整个天空,好像有谁躲在云层后面。
笑了一声。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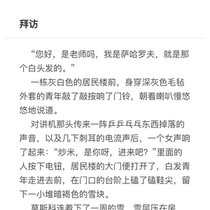
字数:3307
暗暗人见面就打架
可他们是两个远程啊!!
“早上好我的小姑娘。”
弗莱茵睁开眼睛看了看自己身边的男人,他穿着那件初见时的酒红色西装套,一双皮鞋上落了点鲜红色的东西,她已经分不清那到底是刚开的红酒还是杀人沾上的血。
周围的消毒水味太浓了,她几乎要以为自己的鼻子废了。
“早上好呀BOSS。”被叫到的女孩抬起脑袋,像是一个木偶那样,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着,直到一个她不能继续动的角度,“我有点冷。”
“真可惜。”男人脚跟碾了碾地上的东西,弗莱茵听到了响动,立刻看了过去,那是一把烫红的烙铁,上头沾着皮肉,正在散发着隔夜烤肉的香味,“我得送你去医院了我的夜莺小姐。”
男人伸手掐住了弗莱茵的脖子,那里的皮肤白得像被双氧水浸泡过,下颌线被男人的拇指轻轻摩挲着,透出了一些色情的意味。
“可是我没病呀BOSS。”弗莱茵动了动手腕,她才注意到,自己似乎已经被吊在这里超过了十二个小时,“我还有任务没做完呢。”
女孩的手臂纤细,从手肘到小臂掠过手腕,再到漂亮的手掌,五指秀气,指尖带着淡粉色,一周没修剪的指甲里卡着暗红色的块状物。手铐当啷作响,男人的笑声和女性的气音混杂在一起。
“你病了,病在这里。”男人没有拨开那只已经从手铐中挣脱出来的手掌,反而是用空余的那只手指了指女孩的脑袋,“你不是我的狗了,毕竟没有哪条猎犬会用爪子指着自己的主人。”
弗莱茵没有反抗,她的视线有些模糊,那应该是缺氧导致的,或许脖子上已经有了淤痕,可是那个女孩还是笑着,用为数不多的氧气发笑。她的嘴角几乎抬到了极限,而后被一把甩到了地上。
那里还躺着三天前被她肢解的叛徒,浑浊的蓝眼睛被抠出来泡进了福尔马林,正在两米外的架子上盯着倒在地上的自己和它的主人。
被捡来的女孩浑身雪白,沾染着血腥气和泥土味,平躺在地上,既不挣扎也不发抖,像是一个刚刚被制造出来的陶瓷娃娃,懵懂无知且带着最原始的罪恶。
——和十几年前一样,那个躺在雪地里,生吞下蜈蚣的少女现在成了生吃灵魂的魔女。
男人想着,那具躯体很好看,一头淡金色的长发耷拉在肩头,绕过腰线,一直垂到膝弯,蓝眼睛笑眯眯地,如同燃烧的钾,亮得灼人。
弗莱茵上车的时候只批了一块裹尸布,早就等在门口的警察似乎有些厌恶,他们拿出手铐用力地砸在了女孩的手腕上,脱臼的右手猛地一颤,等在后面的特警就拔出了枪。
“诶诶,为什么这么紧张?”弗莱茵用左手抓住了手腕,往上一推,接上了骨头,“我答应BOSS去看医生了呀。”她顿了顿,用手指点住了自己的嘴角,轻轻地朝上推了一下,“只有我一个人去。”
手枪上膛,打开保险栓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所有的警员都掏出了配枪,对准了这个长相普通的女孩。
‘永远不要相信别人,我可爱的夜莺。因为那不是你。’
“说实在的我不觉得我病了。”弗莱茵将那些卡在指甲里的血块一点点抠出来,“可BOSS他要我去医院呀,很过分不是吗。”
“.…..”
“还好你来得及时,我不想被扔进福尔马林里头。”
影在黑暗里的人似乎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被扔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抽水马桶里的那张纸巾。”弗莱茵甩了甩被弄干净的手指,“本来在后车座上好好的,周围的警察也挺帅气的。虽然他们都带了口罩,哎呀,我都同意去医院了,真的不会对他们冻手呀。”
少女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前座司机的女儿是淹死的,副驾驶的警长妻子自己出轨被对象捅死了,左边那位是个孤儿,右边那位的母亲自己不小心从高楼摔下来,后面那个用步枪顶着我脑袋的姑娘只不过是被卖了两个不成器的弟弟。”她的语气微微下沉,听上去有些无辜,“你看,我和他们也没有深仇大恨啊。”
“——”那个声音像是没了电波的收音机,断断续续地响着。
“诶诶你说什么?”金发的女孩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缠住了她的脚,还没迈开就摔倒在地。多足昆虫从她手边爬过,带着漆黑的影子,绕着光裸的手臂向上攀去,缠住了脖子。
那个声音颤了颤,像是在笑,它缓缓开了口,附在少女耳边,吹出一阵阴冷的风。
“破坏,那是你的专长不是吗。”
“不是哦。”少女也笑起来,被黑色的影子掐得发不出声,如同一个即将被吹破的风箱,“我只是喜欢看她们哭喊的表情。”
“那时一样的。”它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交易。我给你想要的,你给我那个完美的结局。”
“你和BOSS一样呢。”弗莱茵拨弄了一下那条影子,它慢慢地松开了身子,细长的足尖滑过皮肤,“你会送我去医院吗?”
“神不会苛责他的信徒。”那个声音说,在大脑中荡漾,在耳蜗中冲撞,从针刺的痛感中满溢出甘甜的香,“成为这个世界的深渊,发泄你的怒火,直到你尽兴。”
少女从那片黑沉的地方走出,扔掉了那块裹尸布一样的东西,露出里面的衣裙,裸足踏在泥土上,软绵绵的带着独特的腥味。
“呀。”有谁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对她打着招呼,“你果然在这里。”
不破之挥了挥手,臂弯间夹着一把漂亮的狙击枪,鲜红色的毛衣外披着一件长款的皮夹克。
“小道消息说秘密押送的小狗离奇消失的时候我就猜是不是你。”不破上下打量着那个向他走来的未来同伴,“好久不见啊,该死的清道夫。”
弗莱茵捂了捂嘴角,凑上去贴着男人的脸颊闻了闻,“不是你的味道呀?”
不破立在那没有多大的反应,过了好一会才缓缓抬起手捏住了自己的鼻子。
“你好臭。”
“大概是尸臭吧。”弗莱茵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抬起手腕闻了闻,“我已经闻不到了。”
“那块布是你用过的?”
“嗯——它的主人应该不是我。”少女嫌弃地往那块布上踢了点泥土。
“说起来你这种人怎么会被——”不破比划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说我不听话了,说我这里病了。”女孩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你上次食物中毒去的医院还记得吗,他想把我送去那里。”
不破没有答话,他下意识地想要反驳,总觉得那位黑手党教父的原意不是那样,武装押运的事情几乎在道上传遍了,谁都不会真的觉得那人是要把自己趁手的刀送去保养,而是应该送去火葬场。
“你这里大概真的有问题。”他说。
“那就有吧。”弗莱茵跺了跺脚,大约是觉得冷,她又把视线放在了那块被嫌弃过的裹尸布上。
“你应该先去找个浴室洗洗。”青年退后了两步,表达出了十足的厌恶,“你这样虫子都不会粘你。”
“那就糟了。我的储备粮只剩下虫了。”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把虫子当储备粮。”
“蛋白质是——”
“牛肉的五倍。”不破迅速地打断了少女的话,他忽地甩了一下那把狙击枪,“你我这么熟吗?”
“你哪里看出来我们熟悉了?”
过白的肤色,暗淡的光线,不破的半张脸也隐在那片沉重的黑里,他们被整齐地分成两半,从里头流出漆黑的芯子,咖啡的香和那股腥臭混在一块,从每一个毛孔中透出恶寒。
两人迅速拉开距离,不破早就看见了那条坠在少女身后的东西,细长且泛着光泽,趴在干涸的泥地上发出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迅速躲进阴影中的狙击手架起了自己的武器,银色的狙击枪被树荫全部遮住,看不见半点反光,一米七的男子就在几秒内消失在了这片林子中。
瞄准镜中的金发少女不紧不慢地走着,她没有躲进死角,也没有站在难以看见的地方,白色的裙摆摇摇晃晃地拂过地面,后面的生物用尾巴缠住了她的手腕。
难以被成为美女与野兽的场面让不破咂舌,扣下扳机的瞬间他看见那个女人迅速挥动手腕,泛着油光的甲壳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弗莱茵看见了被自己弹开的东西——那是一粒咖啡豆。
不破听见自己脑内吹了一声口哨。
他分不清那是自己的声音,还是那个奇奇怪怪的家伙在脑子里吹的口哨。
狙击手没有换位置,他只是迅速地填充着弹药,随时准备射出下一颗子弹。
弗莱茵的动作很快,就在换弹的瞬间,那个人已经拖着金色的长发消失在了视野中。
那个女人没有穿鞋子,泥地会吸收声响。
不破卸了狙击镜,两三下爬下树。
他是这么预想的。
跳下那颗树的瞬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缠上了自己的脖子,像是一条蛇,又像是一根白绫。
“嘻嘻——”
那个笑声太过熟悉,在几年前,他也曾经在爆炸中听见过这个笑。近在咫尺。
男人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割断那根东西,虽然它长着脚,不用想都知道有多恶心,狙击手举起了那把银色的枪械,朝着声音的来源扣下了扳机。
重物落地的声音和枪声混在一起。
林子里没有鸟,只剩下了那些回声。
少女露出笑来,抹开了脸颊上的血。
男人一把扯开将他脖子勒出青紫印记的蜈蚣,向着陌生人吐出了舌头。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哇。”女孩将那根黑亮的蜈蚣卷起来,像是一个过大的皮球抛接着玩弄,“名字很重要吗?”
“似乎并不。”男人将枪口对准了她,再一次扣下扳机。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