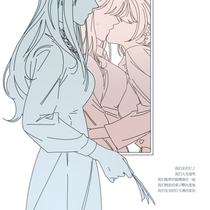

小常毕业以后去了老家随便一个单位当翻译。这年头生意不景气,老板发不出工资,公司看上去岌岌可危,同事们纷纷寻找下家,小常也不例外。她回到自己那所单身公寓,简历上让她写自我介绍。她迷茫地写下第一行,扎实的黑色笔迹突然扭动起来,像蚁群,吓得她连忙闭上眼,笔一扔,身体直接撞到椅背上。
小常才毕业一年半,大学宿舍群已经被拼多多和外卖红包刷屏,小常对他们的印象也开始变淡,她随手翻了翻群聊,翻不到尽头的分享里没有睡在对面床位的小寻,小常叹口气。她又在楼下的信箱里拿到了一个大大的黄色信封,沉甸甸的,上头贴了很多花花绿绿的邮票。邮政送信十分随缘,有时候能收到,有时候不能,有时候等个把月,有时只要两星期。小常撕开信封时没能注意,里面一张纪念款门票飘到了地上。她捡起来看,天河城自贩机又开了live,这次还开到了家附近,只可惜门票已经过期三天。
小常吹了吹上面沾上的灰,手指朝着门票上镭射印刷的乐队名弹了两下,收进信封。
南方的天气让信纸受了潮,原本硬挺的纸软软地耷在手上。寄信人的字清秀端正,信的内容上到哪里遇到了什么人,下到几点吃了什么饭,话题天南地北,仿佛这不是信,是从日记上撕下来的几页。小常读着那些字,突然痴痴的笑,笑完后,也不觉自己动情得肉麻。
小常做学生的时候,出行总要逮一个人作伴,这个伴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大学是她变成小常的一个开关,就像充气过头的气球在“砰”的一声后变成碎片,小常在远离义乌小城后立马变成了小常,此前她是学校3D打印出来的一个人形模板,此后她方便地和各路人说爱。
她刚认识小寻的时候,小寻正推着可能比自己还沉的行李箱搬进来。小常一觉睡到中午,被万向轮滚过地面的声音吵醒,小寻就穿着新绿色连衣裙出现在她眼前。
小常蓬头垢面,睡得衣衫不整,倒也不觉得尴尬。她起身看了看对面的空床位,挠了挠头,拉起床帘又打算躺下,手机亮起来,是时葳问她午饭要吃什么。小常爬起来问新来的室友要不要一起来一份,小寻正在把行李箱里的衣服挂进衣柜,她听到小常的问题,抬起头眨眨眼,说,已经吃过了。
中午,小常一手捧着杂粮煎饼另一手在手机上飞速扣字,男团选秀节目在笔记本电脑上寂寞地放送。她前几天刚甩掉一个男人,对方还不死心,换着号来骚扰。时葳拎着耗子尾巴在喂蛇,梁舒瑶吃完饭内衣一脱倒头就睡。新来的室友去教学楼新生报到,床还没铺完,床帘也只挂到了一半。新生入学总有些鸡飞狗跳。宠物蛇扭了两扭,咬住了耗子的头。
到了晚上,几个大二学姐带着新室友去学校附近家常饭馆里吃肉末茄子,小常边吃边像查户口一般向小寻问东问西,梁舒瑶和时葳头快埋进碗里了,小寻捧着碗傻乐。中途,时葳看了眼手机,嘴角立刻垮下去。小常不用猜就知道是她女朋友,室友点点头,说麻烦,本来周末出去游乐园,结果她老师调论文死线。小常笑道物理系嘛,正常得很。一旁小寻停下了筷子,像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种性向一般红了脸,结巴地问:“两个女孩子怎么谈恋爱?”
小常一听就乐了,这年头像她一样敢在公共场合开黄腔的女人不多,像小寻一样什么都不懂的更少见。小寻和她去过的宾馆里的床单一样白而整洁,看着舒服,就想躺上去弄乱。
小寻接着问:就是那个,同性恋吗?
时葳扒拉筷子:嗯。
小寻又问:那,和女孩子谈恋爱什么感觉啊?
时葳听罢,挑着眉毛:王小波说了,同性恋,不男不女。
小常知道王小波原话肯定不是这样,但让她去想什么女人可爱男人讨厌的话题她也烦闷,谈起恋爱来男人女人都一样庸俗可憎,泡在男人堆里和泡在女人堆里只有晚上和人上床时摸什么器官的区别。
小常自觉没那么爱女人。倒有那么一天,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在整理自己带到学校里来的玩具——什么玩具大家都明白——突然小寻就进了门。彼时她抱着毛概课本,一副规规矩矩高中生模样,在原地愣了半天,问:
“那些是什么东西?”
小常就使坏,问她要不要试试,说完就把她拉上自己的床铺,关上那不透光的帘。
学期还没过半的时候梁舒瑶整了个乐队,还缺个主唱。小常会唱歌,但她只会唱洋文,于是小寻就被软磨硬泡拐进了乐队。乐队里的人小常到毕业还没认全,光记得有个戴着九筒面具的常常上学校匿名墙。但小常经常去捧场,小寻站在台上唱,又唱又跳,唱他们三天内就写完的歌词,还挺顺溜,挺好听,挺美。现场宅男居多,围在前排举着双手。小常站在第二层贵宾席,居高临下地看。
那天晚上之后,小寻偶尔会钻进小常的床。小常不置可否,白天她和不同的男人拥抱接吻,晚上她抱着小寻温暖柔软的身体睡觉。总的来说小常不是一个会在意道德的人,爱是她的道德。而小寻无知而懵懂,眼里全是爱,小寻就是她的道德。她怀抱着道德睡觉做梦,没人能指责她沦丧堕落。
小常偶尔还去另一个乐队现场捧场,住在隔壁宿舍的司马相如顶着在场所有人都欠她五百万的眼神弹贝斯,蒋酉裕戴着浅蓝色美瞳,炸现场的样子特像哈士奇,高胜寒直接不穿上衣,打鼓的时候像和世界有千年大恨。两个乐队风格相去甚远。小常说不上喜欢哪个,帅哥美女她都爱看。放假在回浙江的动车上,她坐在蒋酉裕和云年的中间,她问蒋酉裕为什么乐队名字叫RCW。蒋酉裕翻了个白眼,掰着指头说:rain,cold,wind,忧郁,高冷,疯批。
小常笑得花枝乱颤,直接把一旁昏昏欲睡的云年吓醒。
她想起小寻在现场,唱的唯一一首不是乐队原创的歌。那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是日语,她不是日语专业,却也听得懂那些动人心弦。
上个月她又有了个新男友,两个人在酒吧认识。男人有家庭,妻子在老家考药师资格证。他见到她,就追求她,渴望她,说他和妻子没有孩子,可以随时离婚。小常笑道:离婚冷静期又不是摆设。说完便慈悲地和他上床,再后来一下班就去找他,仿佛无事可做。
小常不能称之为爱,爱不是上床这么简单,上床不能像爱一般开花结果,爱是可以不被满足的。男人将头埋在她两腿之间时,她又怀念她的道德。
在毕业后的三个月,小常收到了第一封信。小常偏爱这种古老而缓慢的通讯方式,见字如见人,小寻的字和本人一样美好。她翻动着那些信纸,不慌不忙地,静悄悄地,像抚过恋人颈项一般抚过那些字,然后把信稳妥地放在书柜最下层的纸箱,便披上大衣出了门。




鬼知道他这两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出门练习,出门练习,几乎天天都要出门练习,他觉得自己嘴皮都吹褪了三四层。更别提每天都要看到两张臭脸,或者听两个人讲着自己听不懂的时尚话题。
太糟糕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吧。梁子立每次抱着这样的心态准备提交退队申请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无法如愿。
比如有一次两个人都有事没来,梁子立就只能在练习室里自己吹想吹的曲子,想着退队还是要当面说比较好,磨磨蹭蹭到了练习结束的时候。
或者那天萧守顾说架子鼓不够国潮,直接拉了一台杨琴,让梁舒瑶换成杨琴的时候,梁子立觉得自己应该借着这压抑的氛围嘲笑然后退队,却被梁舒瑶凶狠打击杨琴的眼神给吓得不敢说话。
结果梁舒瑶真的认真练习着杨琴,而萧守顾自己拉起了二胡。
很多时候,因为和声没有达到预期,三个人互相嘲讽或者咒骂,当然梁子立更多的时候是在心里嘲讽。明明乐队的解散就在一线之间,却总是晃着晃着就是不断。
正躺在床上的梁子立看到乐队微信群里弹出了信息:
练习室开门了。
到了。
梁子立按掉了屏幕,用枕头盖住脑袋,但很快又站了起来。他如果不去的话,结果大概率是被萧守顾踹来宿舍门拉去练习室吧。
他只能磨磨蹭蹭地穿鞋,随便套上一件衣服,慢悠悠地去自己去刑场。
今天的练习室没有乱七八糟的音乐声,却听到两个人在互相吼着。乓的一声,梁子立看见梁舒瑶用力拍开门,迎面走了出来,和他的目光正好撞上,他看见梁舒瑶眼眶有些红,但是还没有泪痕。
他知道现在应该安慰一句什么,但是,有必要吗,自己本身也不想呆在这个乐队,又用什么立场来安慰她呢。
在他心理活动的时候,梁舒瑶明显地不耐烦了起来,低下头转身往练习室背后走去。梁子立没有决定好说什么,脱口而出:“今天还用不用练习。”
梁舒瑶停下,高举一个中指:“小喇叭!自己问队长!”
于是梁子立乖乖地走进了练习室。
练习室里,萧守顾低头调整椅子的高低,注意到他进来,萧守顾便说:“坐吧,今天练一下第二页。”
“你们怎么了。”梁子立问完这个问题,希望自己听到的回答是乐队要解散的消息。
“她说,想报名几个比赛,让我们有压力和动力。比如学校的歌手大赛之类的。”萧守顾像是在讲跟自己无关的事一样。
“我们参加比赛,第一轮就会被刷下来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萧守顾也坐下,准备拉二胡。
两个人的和声还不错,其实两个月打磨下来,乐队的演奏到了差不多能听的程度。只是他们还没有一首自己的歌,现在大多时间还是用已经有的曲目做练习。
一曲过后,萧守顾放下了二胡,突然问:“刚刚梁舒瑶冲出去,你看见她没。”
“嗯,看见了。”
萧守顾望着天花板,用右手挠了挠左脸:“她哭了?”
“没有,就是眼眶红的。”你刚刚到底说了什么。梁子立在心里吐槽了一句,但是没敢问。
“这样吧,你帮我去看看她还回不回来练习。”
怎么是我去,我也不会安慰人啊,我可不去。梁子立这样想着,一动也不动。
但是练习室里的沉默让他感到了压力,他叹了口气还是站起来,揣上手机出了门。
梁子立还在想要去哪儿找她才好,却发现梁舒瑶根本没有走远,就靠在旁边的栏杆上抽烟,地下好几个烟头,都被人用脚碾得稀碎。
她眼眶还是很红,但是脸上很干净,没有眼泪。
没等梁子立开口,梁舒瑶就开口问:“你觉得我们乐队水平怎么样。”
“说实话吗。”还是我应该安慰你说些不切实际的赞美。
“说实话。”
“挺差的,不知所云。翻唱也还算能听吧,原创简直像是猴子在哭。”原创简直像是猴子在哭。
突然,梁子立意识到自己把心里嘲讽的话说了出来,连忙抬头偷看梁舒瑶的表情。
他看见梁舒瑶眼泪流了下来,然后她仰起头,像是拙劣的演员一样大声念:“呜!呜!呜!”
路边的同学被吓到,都张望着想看声音的来源,而梁子立感觉很多视线是在责备自己。
“呜呜呜!”梁舒瑶又喊了一声。
可不是我把她弄哭的,或者说只有一点是我,可恶我不应该负全责。梁子立汗毛倒立,他只想拉住梁舒瑶然后把她嘴捂上。
然后马上,梁舒瑶抹了一把脸,想通了似的笑了:“梁子立,就算是哭,我也想别人听到。”
想被人听到。
梁子立突然懂了,为什么这两个人辛辛苦苦大费周章地撑着这个乐队。
因为想被人听到。
也不用梁子立安慰,梁舒瑶自己就安静下来,转身准备回练习室,却发现萧守顾就站在练习室门口。
萧守顾若无其事地说:“太大声了,我被喊出来了。”
“小喇叭。”梁舒瑶比了个中指。
“骂完了?骂完了跟你们讲件事。”萧守顾掏出手机,“我们是时候写点原创曲了,寒假我打算去北京采风。”
那关我什么事,梁子立还没来得及说。
“乐队肯定得一起采风,再买两张票。”梁舒瑶马上就说。
“等……”梁子立还没说话。
“好吧,买了。”萧守顾低下头操作手机。
梁舒瑶把手肘搭在梁子立肩上向他说:“就算你拒绝,大概也会被萧守顾绑过去的吧,所以最好不要拒绝。”
很合理,但是是犯罪。梁子立很想挺直腰杆对他们说不,但是却说不出话。
我的哭泣声,是不是也想让人听见呢。
他突然琢磨道。
带着眼镜的男生左顾右盼,十分不安的样子。无论是蓬松的发型,还是不修边幅的穿衣方式,他看起来跟乐队一点都搭不上边,倒是比较像是喜欢呆在家里面壁的人。
眼镜男左边是矮墙,右边坐着的是萧守顾,完全阻止了他偷溜。
跨过一张餐桌正对面坐着的是梁舒瑶,她正在低头咀嚼一块锅包肉。
眼镜男认真地看着左边的矮墙,在思考必要时刻能不能翻过去,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素质又果断放弃了。
这是江滨大学附近一家东北菜馆,不大的空间里满满当当坐了好几桌人,热气腾腾人声嘈杂。
“怎么样,你考虑好了么。”萧守顾单手转了一圈茶杯,漫不经心地说。
“不用考虑了,靓仔,虽然你……但是……也不是长得不能看,主要是我们挺缺人手的。”梁舒瑶不知道是在说服对方,还是在说服自己,又夹了一块土豆,哄骗的语气说,“乐队很好玩的,又可以交朋友。”
“哈?朋友?”眼镜男突然很大反应,“你们这种……居然说朋友。”
萧守顾听见后笑了出声,用粤语跟梁舒瑶说:“你睇,我话咗佢好搞笑啩(你看,我说他很搞笑吧)。”
梁舒瑶不明所以,喝了口茶压惊,也用粤语回应:“唔系……你同佢商量好未噶(不是……你和他商量好没的啊)……”
眼镜男如坐针毡:“你们叽里咕噜说什么,啊,在嘲笑我吗。”
“不是不是!”梁舒瑶露出微妙的表情摆了摆手。
“对,我们在嘲笑你衣服上有粒扣子没扣,这么久都没注意到。”
萧守顾说完,眼镜男马上低下头检查自己的衣服,才想起来今天自己穿的衣服上根本没扣子,面色又灰白了几分。
在眼镜男快紧张得窒息之前,萧守顾又认真地说:“没有,我们没有嘲笑你,梁子立,我们只是想知道,你要不要跟我们组乐队。”
眼镜男——梁子立,把头埋低,扒了两口饭,发现两个人都认真地等着他的回答,只好抬头:“你们找错人了,你们这种青春剧本里不应该找一个路人甲出演……而且,我会的可是唢呐。”
啪地一声,萧守顾突然一合掌,道:“太好了,就是要吹唢呐的。”
“你们脑子有泡?”
“你不懂,我们要搞的是国潮,新式摇滚。”萧守顾回答。
“这样啊。”梁子立低头腹诽起这两人拿国潮当炒作十足装逼,口头上却不说出来。
听见梁子立的敷衍,萧守顾开始小声哼起了一个调子,本来认真吃饭的梁舒瑶被吸引了注意力,抬头问:“这是什么曲子。”
“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挺有节奏的吧。”萧守顾用手指敲着桌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梁舒瑶听着节奏,拿起一根筷子,敲起半满的水杯,叮。她完全没注意到梁子立表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叮。
咚咚咚咚,叮,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叮。
……
一小段后,梁子立突然出声:“不对不对,这里是咚咚咚叮咚咚。”
梁舒瑶和萧守顾同时抬头看向他,他自觉失言,唰地站了起来,在两人的注视下翻过椅背,从后面一个卡座里跑了出去。
萧守顾对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记得下周一下午来练习室!”
“佢会来咩,咁怕丑(他会来吗,这么害羞)。”
“佢会来(他会来)。”
萧守顾的手机屏幕上闪过一条微信弹窗,然后又是一条:
不要把我吹那种歌的视频发出去。
不是我个人爱好,只是这种曲子在b站上很火。
你还没告诉我练习室在哪儿。
萧守顾划开手机发了两个字:成交。
“那个tie三分吧,不过对鞋不衬个发型,发型不衬条皮带,全身平均1分。”梁舒瑶背靠着绿色栏杆,深吸一口烟。
“我话2分咯,个副眼镜仲系有点意思噶(我说是2分吧,那副眼镜还是有点意思的)。”萧守顾抬了抬眼,扫了一下就兴致缺缺,看着自己手上的烟头明灭。
梁舒瑶不说话,弹了弹烟灰。
这是2020年初冬,寒假大概还有一两个月才会来临。
萧守顾大二,梁舒瑶大一,分别是校园摇滚乐队——天河城自贩机的吉他和鼓手,现在这个乐队只有三个成员,另一位则是大三的前辈兼队长,负责主唱。
三人认识是在广东同乡会,去的人不多,主持人正是这位队长——黄志强,他破冰的时候,清唱了一首曲调平平的原创粤语歌,很初级,但是总觉得歌声有种亮光,不是明亮的太阳,而是从夜空中随手摘了一颗星,任由其在指尖慢慢暗淡。
一曲唱罢,黄志强还说自己有乐队,吹得天花乱坠。梁舒瑶去询问乐队的事,才知道所谓的乐队,目前只有黄志强和萧守顾两人罢了。
为什么没有扭头离开呢?梁舒瑶思考过,但是没得出逻辑学的结论。也许她被暗星的亮光蛊惑,便也想摘一颗吧。
天色开始暗淡,校园里的同学不是往食堂赶,就是往宿舍去。向着活动室的步道上人烟稀少,稀稀拉拉的路人比被风吹起的落叶还少。
本应该在乐队练习室里的两个人却被锁在了门外,只能靠评判路人的衣品打发时间。
“那条友嘅衫点啊(那个人的衣服怎么样)。”萧指了指远处的一个人。
“周身黄黚黚,不是几好睇喔。好似要look chok,又用力过咗头(全身黄,不是很好看,好像想扮酷,又用力过头)。”梁有点近视,但是从来不带眼镜,完全认不出远处的人是谁,只能眯起眼睛。
萧嘲弄似地轻笑一声:“那个好似系我哋嘅队长喔(那个好像是我们的队长喔)。”
怎想梁舒瑶也笑一声:“佢嘅look一直都不算几好啦(他的衣品一直都不算多好啦)。”
萧守顾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也没有看梁舒瑶,就往黄志强队长那边走去。
梁注视一秒,百无聊赖地跟上。
穿着黄色系衣服的队长,就像落叶一般在风里抖动。看见两人都往这边走了过来,才加快脚步小跑起来。
还不等两个人说话,队长就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今日有点事想同你哋讲(我今天有点事想跟你们说)。”
梁舒瑶听罢抱起手臂,一副你说吧的样子。萧守顾微微认真起来,看着队长的眼睛。
“我,黄志强,终于下定决心。”队长深呼吸,又继续说,“我要退学,去北京开始做歌手。”
梁瞠目结舌,一时不知道怎么回话。
萧反而没有惊讶,似乎已经很习惯队长的突然袭击,只是淡淡问:“乐队解散吗?”
“不,不解散。”黄志强摇了摇头,掏出了活动室的钥匙,“给你,从宜家开始,你就系天河城自贩机嘅队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天河城自贩机的队长)。”
黄志强说完,不等两人回应,头也不回地走了。
萧守顾不以为意,拿着钥匙准备开门。
“咪住(等下)。”梁舒瑶非常困惑,“佢讲真噶(他说真的)?”
“系啩(是吧)?”
“你点解咁淡定(你怎么这么淡定)。”
萧守顾停下,很认真地问:“佢走咗了。你仲玩不玩乐队嘞(他走了,你还玩不玩乐队呢)。”
梁舒瑶没有思考,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咁咪得咯(那不就是)。”
“等等……”梁舒瑶总觉得还有别的事情没有解决,“我哋两个人,点玩乐队啊(我们两个人,怎么玩乐队啊)。”
萧守顾不紧不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取了一根点燃,然后用广普故作深沉地说:“现在,摇滚已经死了。”
“咩意思啊。”
“我近排识得一个人,可以叫佢过来试下(我最近认识一个人,可以叫他过来试下)。”萧守顾想了想那个人,真心地笑了起来,“佢几有gag噶(他挺有梗的)。”
“咩料啊(什么人啊)。”
“一个朋友,物理专业嘅。不过……”
“佢识咩乐器啊(他会啥乐器啊)。”
“嗯……就系……”萧守顾声音越来越小。
“哈?”
“suona。”
“你大声点。”
“唢呐。”
“锁……?!”
“不破,不立。”萧守顾叼着烟,含含糊糊地说,“玩国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