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诸多神秘千古流传,
神明与怪物皆非儿戏,
人与其历史编织万年。
亚当的子孙与莉莉丝的孩子,
孰是孰非早已无法分辨,
有多少人能放下过往的偏见与仇恨?
但也唯有放下过往,缔结约定。
千百年的怨恨痴缠,
在一夕一夜间断结。
人们从此不再知晓那异常,
但神秘依在,并将永远在。
那亚当的聪慧子孙们,
与众多的怪异结为同盟,
一同化作人类的坚盾,
——名为“埃癸斯”。
正因如此,世界的齿轮今日也正常转动。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世界的半架空企划,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并无法完美还原欧洲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万里无云的晴天是很少见的。散漫的阳光虽然驱散了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阴云,却没能拯救菲琳娜不太明媚的心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要去罗马尼亚啊——”她用力蹬掉拖鞋,抓过最爱的海绵宝宝玩偶,狠狠把自己摔进懒人沙发里然后打了个滚。
正式入职埃癸斯以后,菲琳娜就从家里搬了出来。她在一个距本部大楼的通勤时间约为四十五分钟的街区租了一间单身公寓,没什么活儿要干的时候,正好方便她跑到隔壁街区的街心公园放飞自我与天性。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愿意在白天跑出来溜达的一般居民也越来越少,菲琳娜甚至不用变回原形也敢在草皮上滚来滚去。
直到偶遇了一只像云朵和棉花糖一样洁白又可爱的博美犬,菲琳娜终于萌发了猫生仅有的害羞和矜持。在满公园撒欢乱跑乱跳之外,她终于有了另一个解压良方——云吸狗。当然,受限于她贫瘠的养宠经验,她至今还没能很好地和小狗套上近乎,也就没能成功撸到狗。
一个多月前的另一个晴朗的日子,刚结束外勤的菲琳娜拐到Farina Pizzeria买走了最后一块带肉的披萨。虽然同行的莱尼锡先生看到香肠卷边披萨上头的那几块澄黄的菠萝片后,委婉地表示了对披萨店长精神状态的担忧,但在无肉不欢的豹猫小姐眼里,这已经是她这会儿能拿出的、给小狗的、最像样的见面礼了。
博美犬却不领情。
像棉花糖和云朵一样可爱又洁白的博美犬一脸嫌弃地看着纸盒里菠萝香肠卷边披萨,用前爪轻轻地往前推了推,小嘴一张,说的竟然是地道的伦敦腔英语:我们狗不吃这玩意儿。随后,她优雅地冲菲琳娜点了点头,转身迈着小碎步往她来的方向走去。
菲琳娜在原地愣了好久才从“梦中情狗竟然也是奇美拉”的失落中找回自己的四肢,隔天又在埃癸斯大楼里看到了熟悉的蝴蝶结,这才幡然醒悟“梦中情狗”其实是自己的同事……啊——我这是做了多么失礼的事情啊!!!菲琳娜尴尬得快把自己挠出斑秃来了。
尽管帕瑞妮安(就是那只博美犬)看起来并不是很在意这件事,菲琳娜也还是想以奇美拉的方式向她赔礼道歉。只是,还没等她做好登门拜访的准备,埃癸斯努力维持下来的平静生活就被突如其来的魔女谋杀事件搅成了一潭浑水,而本已销声匿迹的邪教组织们,也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据锡吉什瓦拉当地线报所说,信仰邪教的吸血鬼家族中流传着吸干人血并挖出心脏吃掉的力量增强秘方,信者不是少数,事态已经严重危害到当地村落居民的生命安危了。埃癸斯紧急抽调了一支小队前往罗马尼亚,其中就有菲琳娜。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已经连轴转了两个星期没休息过的菲琳娜在嚎了一声后彻底被懒人沙发捕获,她不由自主地变回原形,陷入玩偶和坐垫间的缝隙瘫成一团,逐渐神志模糊了起来。
“睡个好觉吧。”
隐隐约约,一道未曾听过的声音在菲琳娜耳畔响起,但她已经彻底沉入梦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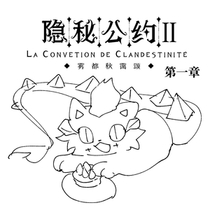








“你又旷工了?”
“哪儿能啊,我这是早早干完提前下班。”
八月的爱丁堡夏花极为灿烂地开放着,争奇斗艳般,将四处都装点地五彩斑斓。阳光和丽,正是出门的好天气,街上熙熙攘攘,走在路上,很容易就能听到几句随风飘来的笑语。温格转身避开两个迎面闯来的嬉戏打闹的小孩,弯弯眼睛回电话那头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为自己辩驳。
对面笑了笑,气音从听筒里漏出来,让他嘴角也情不自禁跟着扬了扬。
“那好好享受你的下班时间吧,”对面就差把你看我信吗写到他脸上了,还不忘提醒他,“小心被抓到了。”
“怎么会呢——”温格拖长了音调冲着对面摇头晃脑,“他们哪一次抓到我过——唉不对,”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挺直了背,沿着石头路向前的脚步也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秋果你这是在套路我?”语气颇有点委屈的意思。
“嗯哼,那就要我们伟大的执行司成员猜喽。”唐秋果的声音清爽干净,跟春风掠过窗铎一般毫无杂质,笑起来眉眼弯弯,脸上还有个小酒窝,可甜可甜。温格没打视频看不着她,却能很轻易地想到秋果此时的模样。这个时间的秋果往往不是在舞蹈室就是在回宿舍的路上,她安静地收拾好练习用的道具,关上舞蹈室的灯,然后看着沉寂的夜幕就着偌大的落地窗倾泻在教学楼顶层的舞蹈室里。温格年假的时候曾经去过几次秋果的学校,见过那个她几乎每天都与之为伴的舞蹈室,知道那里占了几乎一整面墙的镜子、光滑的木质把杆、堆满储物间的道具、笨重的蓝牙音箱,以及夕阳下旖丽的黄昏和夜色中漫天的星河。秋果有时候锁了门就走,有时候回头看看,也不开灯,就站在那里看漆黑一片的空教室,看从窗户中透进来的湛蓝色的天光。
唐秋果学的是古典舞,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一直到大学读了这个专业。温格五岁学的钢琴,两人又年纪相仿,因而这样说来,秋果学舞的时间比温格学琴还要长那么一些。温格很喜欢看秋果跳舞,第一次跟她见面就是在舞台上,说她的摄人心魂也许夸张了点,但一句令人神往却非言过其实。后来和秋果熟了之后,温格就更常见她跳舞。那会儿他俩上高中,一个音乐生一个舞蹈生,都是文艺汇演的常客,课余时间排节目更是少不了的。学校音乐教室本来就少,又要分配给学生上课,又要匀出给特长生排练的空间,一来二去两人就挤到了一个教室。温格用教室前面的钢琴,秋果用教室后面的舞蹈镜,端得是明明白白。温格慵懒,有时候练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坐在琴凳上,安静地看秋果跳,看她缓缓地下腰,又行云流水、状无声息地翻了个身。她细长好看的手随着音乐的鼓点律动,而这鼓点也一下一下地敲进了温格的心里。
都说日久天长就会成为习惯,而温格看着看着也变成了嗜好。他从琴凳上挪下来,调音箱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这些习惯养成了以后就没再变过,纵是后来忙碌,称得上一句聚少离多,一旦他们在一起,就还是那个十六七岁的样子。秋果站在舞蹈室的中间,对着镜子,而温格坐在舞蹈室靠墙的椅子边,守着那个笨重的音箱,一声清脆的响指,音箱顶上的唱片就呼呼转,摇出一首穿林打叶,晃上半道圆月疏桐。
想到这些,温格就忍不住弯着眼睛笑,周遭万花灿烂,可到底也比不上对面的人。他被秋果一句话哄住,把被套路的事也抛到一边儿,照旧笑着问她:你还没回去?
准备回了。秋果回答他,又问:那么温格先生这是准备去哪儿?
“爱丁堡艺穗节,大小姐要不要看看?”温格把视频打开了,秋果带着笑靥的脸很快出现在镜头前,他把摄像头转了转,让镜头朝着周围,欧式城堡、长廊、绚烂的花卉以及偌大的露天舞台很快挤满了屏幕。他就这样连着耳机,絮絮叨叨地讲:“一年一度的艺穗节,音乐戏剧舞蹈马戏什么都有……十岁前几乎每年都会被带着来,可惜离开苏格兰后就没了这回事。狐狸哥,啊,就是卢卡,你还没见过他吧,贝克街侦探联盟的家伙——他前些日子刚来过,说看了一场有趣的表演,体验感还不错,我就来故地重游一回了。”
他有点遗憾:“可惜你今年回校太早了,要是留到八月,就有机会碰上了。”他从小贩那里买了一串果串,在镜头前晃晃,向她眨了眨眼,“我觉得你会喜欢这里的。”
“那就希望明年的温格不要这么忙咯?”秋果笑起来,“后面是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吗,我听到那句台词了。”
“啊莎翁,”温格看了眼舞台上穿着精灵服的一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经典老番了。”
“你约了下一场?”
“还是秋果了解我。”温格咬下串串上的草莓,嘟囔了句好甜,得到了秋果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冲她眨眨眼,看她很自如地穿过教学楼的连廊,走到了校道上。“是《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他说,“还记得吗,叶先生曾经向我们盛赞过的那部歌剧。”
“当然。”说话间秋果已经穿过了林荫道,她头上的发带随着她的动作一扬一扬地,看得温格有些心痒,恨不得伸出手去碰一碰,“所以是蓄谋已久?”秋果一语中的,笑弯了眼睛。
“是呀,我的大小姐。”温格利落地认,开心的神色里又露出点得意的神情。这下秋果怎么着都能想象温格使了些什么法子才在埃癸斯得到了近半天的假期了。
“维吉尔和斐瑞应该没空陪你一起去吧?”她问。
“是啊,他俩忙着呢。”温格一想到他的两个发小就直叹气,一个月前,因为要处理几个家族的内部大事,维吉尔和斐瑞就跟他们的父辈一起飞到了德国,至今未归,在联络中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总而言之,他们错过了这场爱丁堡的盛会。“不过他俩指不定也不想我呢,尤其是维吉尔那小子,”他不走心地翻个白眼,“他可对和斐斐独处的时间珍惜得紧。”
“不过我也是请了朋友一起来的。”末了温格又说。他放心地看着秋果走进宿舍楼,最终停在了房间前,抬手敲了敲门。
秋果早猜到了,这小子看演出都不肯一个人去看的,铁定会拉个家伙和他一起去,他的两个发小都是惯常的冤种,进了埃癸斯,跟他相熟的自然也少不了,对此全是见怪不怪。她不问,因为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他们都不是急于一时的人,姑且惯着来日方长。中国到英国,四千八百三十四英里,八个小时的时差,那头还烈日当空,这头已经是满天星子了。于是她打个哈欠,朦胧双眼睛,跟他说了晚安。
温格的嘴角扬着,跟秋果通话让他心情不能更好。他收起手机,望了望人群的尽头,恰好看到了一撮熟悉的白毛穿过人群,向着他站着的雕塑来。于是他难得提起精神,向他招了招手,成功收获了一个有些震惊的表情。
狐狸哥:事出反常必有妖,无事殷情非奸即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