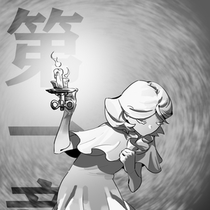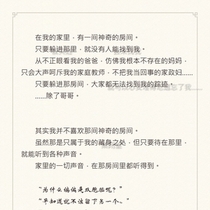不管是被欺负的孩子,还是孤单的孩子,你们都有一个藏身之处,这里黑暗、无光,仿佛连外界的声音都无法透进来。
纸箱、床底、柜子、楼梯间;无论对于你而言这是什么地方,你总会躲在这里。
直到下一次睁眼后,你的眼前出现一簇蜡烛的火苗。
限定为6-14岁的儿童企划,场内投递人物卡请携带链接至企划组私信。
场外仅需符合企划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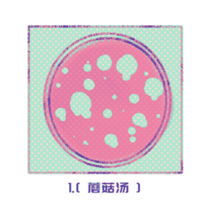
黑暗中只有烛火摇曳,栖也就就着这微弱的光前进着,她没有信心能通过那些管道,毕竟手上还拿着蜡烛,于是她转而向另一个方向走去,随后不知何时开始,她听见了滴水声。
有声音,至少不是寂静到可怕了。她只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继续向着声音那端前进。她不知道这是谁的恶作剧,这个地方实在很黑,像是什么大房子,蜡烛、小刀,一切看起来都不符合常理。会是把她关进去的那些孩子又趁她睡着时将她运到这里来的吗,可她并不是会睡得那样沉的类型……
栖有些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着,而那滴水声不断变大、变多,直到她看见了一片水池。那片水池的颜色比周围的黑深上许多,借着蜡烛的光也能看见些微反光。这里难道是死路吗?栖有些犹疑,下意识地向后迈出一只脚,却又在此时,像是要挽留她一样,从水中亮起了光。
不,不是从水中。
那是水上的光,一片一片的,像灯一样。
这还是栖第一次从蜡烛以外的地方看见光,于是她毫不犹豫,向着平台跳了过去。只是等她落地,下意识用一只手撑了一下地面之后,她才开始注意到,这并不是灯那种东西。
软塌塌的,却又冰冰的,它们自己发着光,又随着她的动作向不同方向摇摆着——是蘑菇。蘑菇怎么会自己发光呢?栖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于是她带着些许好奇,小心地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其中一个蘑菇。
刹那间,突然爆发出的笑声像是化成了音波一样,激得栖猛地收回了手,又向后退了几步,险险地停在了平台边缘。可那声音并未停歇,反而像是在嘲笑她一般,愈演愈烈。
栖下意识抬起手,可她要用一只手拿蜡烛,而只用一只手捂住耳朵,又怎么可能阻挡住那些声音呢?
而那声音自顾自地继续着,笑声渐渐小了下去,另一个声音再度响起,紧接着是另一个……渐渐的,栖也注意到了一件事——她听过这些声音。这是她听过无数次的,来自她同学的,来自她们周围的那些人的,这是他们的嘲笑与闲言碎语,她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不会再在意的。小孩们笑着,大人们也笑着,就连老师们也只是笑着,告诉她、告诉她的母亲:“都是小孩子,也不懂事,闹着玩的,忍忍就好了。”
她记得,她一直在这么做,可为什么再听见这些呢,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声音呢——
「我恨他们。」
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恨他们。」
那个声音在重复着,无数个蘑菇重复着,在笑声与指责之上响着,在整个空间中响着。
“不对……”栖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急于反驳,却又不知为何没法发出足够大的声音,只能用这样仿佛没有底气一般的音量说着,“他们只是什么都不懂,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是没办法的……等到、等到……”
「为什么是我面对这一切呢?他们为什么就没有错?如果他们都没有错的话,错的是谁呢?」
“谁也、谁也没有错……”
栖依旧维持着有些徒劳的、只用一只手捂着耳朵的姿势,慢慢蹲了下来。她的嘴唇都被连带着有些颤抖了,却还是倔强地继续着反驳着那非人的声音。她表现得很是着急,就好像如果不真正否定掉这些声音,她就会不再是她了一样。
「我也有时候会恨母亲,明明知道会导致这种事情,为什么还要生下我呢?为什么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只会哭?为什么根本改变不了现状,却又告诉我一切都会变好?」
“不,我最喜欢母亲了……她很辛苦,她真的很累了,我知道的,我知道她是因为太爱我了,她明明在我受伤的时候,看起来比我还要痛苦……我怎么可能会恨她呢,我怎么可能……”
栖的眼前变得模糊,来自“她”的声音在那些笑声之上重复着、重复着,夹带着恨意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回响,而她也一遍遍地重复着否定,直到——
她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伴随而来的是一句关心,“您还好吗?”。在最初的一些呆愣和小小的惊吓之后,栖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是有人站在了她的旁边。她有些慌忙地起身,看向对方。那是她从没见过的人,看起来十分的美丽而又优雅,此时拿着带着华美烛台的蜡烛,站在她的身边。
“冒昧打扰,小姐……我的名字是玛格丽特·纳维亚,您看上去脸色不太好的样子,请问是一个人吗?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邀请您与我同行吗?”面前的人如是说。
这还是栖第一次听见有人邀约,也是第一次在这黑暗的地方看见其他的人。一时间,尽管那些声音还在持续着,她也不由得觉得有些安心了下来。于是她回答:“谢谢,我已经好一些了,如果你也不介意的话,当然可以……对了,我叫栖。”
这是来之不易的同行人,至少栖是这样想的。但那些声音还在持续,或许对话可以稍微将它们压下去?可是她还是第一次与其他人有所交流,这种情况下该说什么好?她依旧想要反驳那些话语,却又顾虑着身旁的人,若是她听不见的话,自己会被当成奇怪的人,然后被丢下吗?
栖不确定,也不敢赌,于是她为了缓解一些自己的情绪,只好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抓住了对方的衣袖,好在玛格丽特看起来并不介意这样的接触,栖也放下了心。
不过,很快,玛格丽特再次开口,询问栖有没有听见那些蘑菇的声音。原来其他人也能听到吗?栖有些慌张,左右看了看,犹豫了好一会:要是她听见了那些声音怎么办?如果她也知道了自己的事,随后决定不再理自己了,将自己丢在这里又该怎么办?可她到底是听见了的,所以最终,她还是点头,承认了下来。
然而,已经做好了如何应对嘲笑的心理准备的栖,却没有迎来她所想象的后续。新结识的同行者带着与栖此前所见过的那些笑容不同的微笑微微侧头看着她,说话的声音正好盖过那些不断回响在耳边的笑声,也连带着栖自己也加入了这用声音盖过那些蘑菇的行列中。
“如果栖小姐觉得害怕的话,可以试试唱歌哦,我的管家说一个人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唱歌,爱你的人就会听到来找你的~”在交谈中,玛格丽特对着依旧紧抓着她衣袖的栖如是建议道。
栖从没试过唱歌,但她的确很中意这个提议。玛格丽特也说了,她并不介意聆听,这之前她也的确没有笑过,所以,栖想,这或许是第一次,她能够不被别人打断地、好好地唱一首歌了。可她从没有系统地学过一首歌,也很少去听。如今她唯一记得歌词和语调的,也就只有母亲曾经在她害怕独自入睡时,唱的那一首童谣。
母亲……栖深吸一口气,努力地回忆着当时母亲的腔调,和记忆中那首歌的歌词,有些紧张地开口唱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唱歌,紧张使得她总是时不时停下去回忆接下来的歌词。但好在时间充足,她的听众也没有对此表达什么不满,这倒是让栖渐渐地鼓足了勇气。
舒缓的调子就这样被哼唱出来,尚且幼小的声音在这样空旷的场所响起,倒是显得极其空灵。那一瞬间,栖的确基本忘记了那些此前就像是一直在顺着她的身体攀附向上的、来自蘑菇的声音,她的耳中被她自己的歌声填了大半,就连踩踏在这样有些潮湿又充满了蘑菇的地面上的脚步声,也不知何时与歌曲的小节拍相互吻合,而那之后不多久,空灵而又轻柔的声音多了一份,玛格丽特也加入了进来。
于是,在她们的耳畔回响的,终于不再是那样令人不适的声音,而是来自她们彼此的、空灵而又轻柔的歌声。
栖唱着歌,依旧牵着玛格丽特的衣袖,却不再像此前那么用力,她只是轻轻地捏着,就像是交织的歌声充当了连结两人的桥梁一般——这自然是因为她不再害怕,不管是那些蘑菇的声音,还是会和好不容易遇见的人分开的这种可能性,她如今已经都不怕了。
而她也终于能够回以玛格丽特一个笑容。

墙壁的缝隙里,一张纸条掉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格外明显。白色的,四四方方的,轻飘飘地如羽毛般落下,橘咏未把它捡起来,辨认出上面模糊的字迹:仿佛从不同的地方拾取了不同的字迹,再将它们按照一定规律拼贴在一切,最后凑成一句完整但没头没尾的问句——“你想要温暖的家人吗”,那些歪斜的字迹似乎有让人头晕目眩的能力,又或者说是因为处在这样漆黑狭窄的走廊之中,呼吸声都会让人变得草木皆兵,来不及思考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是某人的恶作剧,未曾停下的步伐带来了更多的问句。
「你喜欢永远回应你的声音?」
「你对你的家人满意吗?」
橘咏未停下脚步,回忆起那个改变一切的下雨天。冰冷的雨撞着玻璃,门外是掩盖不住的父母的交谈声,他们谈起他、他的未来、他的一切,但独独不询问他本身。起初他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往窗外看去,远处的山峦云雾缭绕,层层叠叠,他看得那么认真,装作深深沉入那些被雨模糊的风景中,响亮或沉默都不重要,他唯一需要的是远离门外如同诅咒般萦绕耳边的声音。随后他睡了过去,就连他自己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在那样的心境下入睡的,或许是不同于平日的昏暗光线,又或许是一颗疲惫的心,总之他倒在床上,只觉得这个白天黑得如同关了灯的夜晚,所有的发光体都被遮蔽,再次睁开眼,却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一路往前坐去,小心翼翼,生怕一点动静惊醒到沉睡的凶兽或是垂泪的女神,手中攥紧的白色纸条似乎成为了缓解一切情绪的工具,停下来的瞬间,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最初改变,那张纸条开始变化,黑色的字体被赋予生命般震动着、扭曲着,心跳声从四周隐蔽的地方袭来,他几乎要因为这些刺耳的声音晕过去的时候,它们又重新归于有序的平静,纸条上的字合为一体,最后齐齐变成了一句话——“你会喜欢这里的。”
仿佛过去很久,他也因此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出现了很多人,从学校的同学老师,到来家里做客的血亲和朋友,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而他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越变越薄,一旦有风吹来,温度迅速裹住他的身体,他从未如此轻易地感受到这些,所有的部分——他的脑袋、四肢、甚至是五脏六腑,随着逐渐透明的身体,一点点离他而去。他感觉自己正在失去一切。一开始是声音,随后是触感、再然后是嗅觉,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自己,意识到被所有认识的人忽略,一种即将要消失的感觉慢慢吞噬着他,他的存在逐渐融入空气和呼吸之中。他在这时候看见家对面的窗户后出现了一道身影。
他很熟悉这个人,这是居住在他隔壁的同龄人,佐藤一夜。
分明隔着一定距离,按照正常人的视力来看根本看不清,可橘咏未却意识到自己清楚地看见了她的模样。留着一头白色长发的少女站在床边,平静的红色瞳孔注视着他,看见的一瞬间,佐藤一夜笑起来,嘴唇翕动着,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你也在这里啊”。
再睁眼,他再次从梦里清醒过来,前方是黑暗的环境里唯一的光源——火焰的光在幽静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的冷。没有风,因此烛火如同被固定住一般原地不动,随后他又在蜡烛的脚边找到了一把泛着冷光的小刀,足够锋利,映出他的半张脸。橘咏未走过去,拿起烛台,又试探性地拿起那把小刀,在碰到刀柄的瞬间,一只白到堪称苍白的手出现在一旁。
橘咏未下意识后退一步,也因此看见了那只手的主人。身侧的女孩子穿着白到刺眼的裙子,即使处在黑暗中也有着让人不容忽视的漂亮的白色长发,她轻轻笑了一声,抬起手臂,手中拿着款式明显不同的烛台,随着晃动的风,摇曳的烛火映着她脸,精致、白皙,容不下任何瑕疵。是佐藤一夜。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几年前,隔壁搬来新的邻居,却一直没能有机会正式见面,某一天他回家,路过走廊时看见没能关掉的房门,本着好心提醒的想法敲了敲门,偏偏却遇见一阵堪称剧烈的风,他的手堪堪碰了上去,话都没能说出口,就被撞开。于是他看见房间里的样子:没能开灯的昏暗房间里,风从大开的窗户里吹进来,卷起窗帘和随意摆放在茶几上的几页白纸,在空中如羽毛般飘动着,又迅速落下来,而在窗台的边缘,坐着一个穿着白发女孩,她背对着他,长发散漫地扬起,洁白的裙摆像绽开的花朵。
“真是有意思。”她微笑着,他被她的声音从回忆里拉出来,烛火再度晃动,这次指向了不同的地方——就在不远处,狭长的走廊通向未知的黑暗,仅靠蜡烛的光无法辨认前方究竟会是何种存在。她看着面前的路:“一起走吧。”
佐藤一夜用的是肯定句,她如此笃定自己开口之后橘咏未一定会答应,而事实证明,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橘咏未拿起蜡烛和小刀,快步走到她身前,回头看着她:“我走前面吧,你小心点。”
最后他们停在了一间房间里,与其说是停下,不如说因为突然出现的斜坡而坠落,最后落在了房间门口。柔和的音乐在下落时响起,细小却清晰,让人昏昏欲睡,橘咏未猝不及防,如同被海浪吞没般,一头栽进了玩具堆里,他从中挣扎出来,去寻找原本在身后的佐藤一夜。
“佐——”
“我在这里。”佐藤一夜的声音传来,他回头,白发女孩正弯着腰,在一群玩偶里寻找着什么,最后停了下来,“快过来。”
橘咏未走过去,音乐的声音越来越明显,在破旧的玩偶堆里,他看见了一只熟悉的玩偶。小小的,白色的,针脚蹩脚的小熊,他和佐藤一夜都无比熟悉的小熊——那是他在学校的手工课里亲手做出来、送给身边女孩的礼物。
“真眼熟啊,你觉得呢?”佐藤一夜转头看着他,“像不像你送我的那只?不如说……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们朝着玩偶伸出手,在碰到它的瞬间,那段陌生却温柔的歌声消失了,四周变得无比寂静,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见。橘咏未于是重新打量起那只小熊,在成群结队的玩偶小动物里,它并不显眼,可是因为和记忆里的那个存在如此相似,他们几乎是一眼就锁定了它。
一眼、两眼,从小细节到整体轮廓,橘咏未终于确定,这就是那只他亲手缝制的小熊:“这就是——”
“是啊。”佐藤一夜早就认出,她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务必了解,她回应他的话,“这就是你送我的那只。”
白色的小熊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应,沉默地等待他们做出下一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