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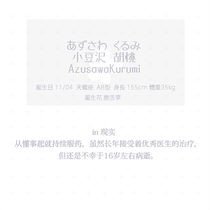



城市被罩在了黑夜的笼中。
温和的明月高悬在空中。若有若无的月色轻柔地钻过虚掩着的透明纱帘,不动声色地洒在瓷地板上,成为了这黑暗的空间里唯一的光源。就在窗边不远处,灰色长发的男子背对着窗坐着,他那细微的呼吸和微微颤动的睫毛证明了他并不是一尊雕像。
周昊然睡着了。他的大腿上放着那本速写本。速写本被摊开了,那页上是一片空白。
|
向前数两千九百二十余个日夜。
明亮的月光缓缓淌进了房间,书桌上亮着一盏小台灯,在桌前,周昊然正对着一个摊开的作文本发呆。这天语文老师为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一篇作文,题目是《童年趣事》。
周昊然感觉自己似乎就从来都不会写作文,尤其是这次的题目,他的脑海中好像独独缺失了对这类事的记忆能力,就算搜肠刮肚地找素材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童年……童年趣事……周昊然努力地试图回忆起和父母在一起时的有趣的往事,但那些事不是消失在了年幼的自己的记忆深处,就是……就是压根就没发生过。盯着一片空白的作文本发了十几分钟呆后,周昊然索性放弃了思考,“扑通”一声趴在了桌子上,决定小憩一阵。此时,来自紧锁的房门外的一阵阵噪音在屋内人放松了精神的同时如潮水般涌进,很快填满了整个房间。周昊然发现他没法打盹了。
在门的另一边,那个男人在喊叫着什么。听不清。
“我挣的钱……都得拿来养你这种没用的女人!你还想不想……”
有女人的回嘴声。门外的噪音更加肆虐了。听不清。
“你还好意思……!……身上的毛病哪个不是随你!”
我听不清,我听不清……。
“就连头发也和你一样!……,看着就喘不过来气!”
声音越来越大。出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和女人小声的啜泣。我要是个聋子就好了,周昊然突然这么想。
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炸雷一般地响起,周昊然浑身一颤,触电般地从座位上弹起,写满了恐惧的金瞳望见了屋角里的衣柜。“你个死小子怎么又锁门!!”男人的怒吼仿佛近在耳边,几乎是出于本能,周昊然连鞋都没来得及脱就逃也似地钻进了那个衣柜,把门外的喊声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外界的声音减弱了,他蜷缩在这狭小黑暗的空间中寻找着依托,孩子的躯体在柔软的衣物中微微打着颤。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周昊然紧紧抓着身边的衣物,捂着双耳,一遍又一遍地低声重复着。似乎过了很久,门外的声音渐渐低了,仔细听似乎还有别人劝架的声音。他总算松了一口气,是楼上的徐家人。徐家也有一个与昊然年纪相仿的男孩,叫徐谙,他们两人打小就认识,没事就喜欢聚在一起,两家邻居也因此走得很近。上次他们来劝架时,小昊然偷偷把自己拿着的家门钥匙和自己房间的钥匙塞给了他们。现在他们来了。
门外的声音断断续续,周昊然还不敢从衣柜中出去。突然,外面似乎响起了有人试图开门的声音,然后是锁被拧开,门被打开后猛地关上,紧接着是给门上锁的声音。周昊然不由得又向衣柜深处缩了缩。衣柜的门突然被拉开,周昊然吓了一跳,但他的视线随即对上了开门者那闪着担忧的湖蓝双眸。
“……徐谙!”周昊然惊喜地叫出了声,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声音中混进了哭腔。
“你没事就好……啊,你怎么又哭了啊?别、别哭啊……”徐谙的话中透出了欣慰,在发现周昊然脸上的泪痕后却变成了惊讶与担忧,同时有点手忙脚乱地安慰着对方,抬手想去帮他擦泪,却把鼻涕眼泪稀里糊涂地抹了他一脸。
周昊然也说不清为什么见到徐谙之后他就突然开始像个小妹妹一样抽抽嗒嗒哭个不停,直到看见徐谙把他的鼻涕眼泪糊了他一脸后那拼命憋笑的表情,他才忍不住破涕为笑。好不容易看见昊然终于笑了,徐谙也松了一口气,开始跟他找话题聊。
徐谙一转头,看见了书桌上那一片空白的作文本。“今天的作文你还没写啊?”徐谙随口问。周昊然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看着面前的好友,周昊然突然感觉作文能写了,来不及管糊了自己一脸的眼泪鼻涕,他赶忙跑到桌前,趁着灵感还没有跑走,开始在作文本上奋笔疾书。
“我知道写什么了!就写今年春天我们去春游的事!”迅速抛开了先前的恐惧与不安,周昊然兴奋地回答了徐谙。
没过多久,徐家人离开了周家,屋外恢复了先前的宁静。周昊然找到了那些快乐的回忆。
在那些回忆里,没有父母,但是有徐谙。
|
时间快进。
操场边,两个男生正并肩坐着,正对着天边那一轮红日。仲春的夕阳将它的余晖温柔地洒向大地,带着暖意的微风轻抚过他们疲惫的脸庞。
“离满分线……还差、还差五秒……”灰发少年大口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他的长发被汗水粘在了通红的脸颊上。
“辛苦了——你才刚跑完,别坐啊,站会儿先。”在他身边,一个金色短发的男生对他说,同时侧过身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塑料水杯,“给。”灰发少年对他点点头,伸手接过了他递来的水杯,仰起头猛灌了几口。
“嗨呀,为什么中考要考体育还得跑一千米……累死了……”周昊然上气不接下气地抱怨道。距离学校的放学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小时,这天周昊然和徐谙约好了一起去操场,为一个月后的中考体育测试进行加班训练。但他们这次一起出来的目的不仅仅是练体育,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他们无言地坐着,看着夕阳一点点没入地平线下,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询问对方。
两人间的沉默被徐谙打破了。“上周末市实验的特招,你也参加了吧?”金发少年试探着问。周昊然轻轻点了点头。“那天你去考艺体了,对吗?……我报了自主招生。”他谨慎地接过了话题。又一次沉默。他们总是要面对那个学生们最不愿提起的话题。
“……成绩怎样?”徐谙轻声问。周昊然愣了两秒,随后无奈地笑了笑,轻叹一声。“怎样?……没考上呗。”他看似随意地回了一句,接着整个人向后一倒,仰面朝天躺在了绿茵场上。“成绩?数学78,理化92,就这两科还能看。”
徐谙愣了半晌,才迟疑地问:“这两科……满分100?”然后他看到昊然点了点头。昊然微微偏头,看见身旁的徐谙正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看。“我好歹也是做过以前的自招试卷的……那些我看都看不懂的题,你个怪物能考九十多?!那你……怎么能考不上的啊?!”
周昊然早就料到对方会这么问。他望着蓝紫色的傍晚天空,缓缓开口:“别忘了还有两百分的阅读与写作。我语文和英语烂得要死……”他自嘲地笑了笑,“一塌糊涂。200分的题我能当100分做。……我考了98。”
徐谙沉默了。照这样说,周昊然自招总分268,而这次的分数线是285。他更加犹豫要不要告诉他自己的艺考成绩了。他索性自己也“扑通”一声,和周昊然并肩躺在了草坪上。
“……那你的艺考成绩呢?”不知过了多久,夕阳似乎已经沉进了地平线,周昊然才开口问他。
“呃……”徐谙慌了,有些不知如何开口,“你,你确定要听?”
“怎么了?”周昊然偏过头,“你画得这么好,肯定不至于考不上吧。”
“倒不是这个……”算了,反正就算我不说他也早晚会知道,这么想着,徐谙放弃了挣扎,无奈地叹了口气,“那我说了?”他看到周昊然点了点头。
“我是说在所有考实高的考生里面啊,也不是全市啦,而且是据我的老师查到的,据说,我的成绩……”徐谙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完一串后,深吸一口气,缓了几秒。
“……是总分第一。”
…………
周昊然只是叹了口气。“该说不愧是你吗……恭喜你啊。”他扯了扯嘴角,勉强的笑了笑。
徐谙看得出周昊然有心思,不只是没考上自招那么简单。他这几天也从父母那里听到了些许消息。“那……”徐谙有些犹豫要不要开口,他略显紧张地吞了口唾沫,“那个,你……你爸妈的事,怎样了?”
“果然还是被你看出来了……”此时周昊然脸上残存的最后一丝笑意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弥漫在他眉宇间的哀伤,“他们前两天刚办完离婚手续,等我中考完,我和妈妈就要搬回老城区的旧房子那边了。这边的房子不知道还会不会留……”周昊然顿了顿,侧过身看着身边的挚友,继续说,“妈妈说这种事要早点办完,她说怕影响我中考……只要再熬过这两个月就行了……但是,等我们上了高中,你就没有办法来我家了吧……”周昊然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被低声的啜泣取代。
徐谙只是默默地听着。从未经历过这些痛楚的他也想开口安慰些什么,但那些想要说出口的话在友人经历的痛苦面前几乎无一不显得苍白无力。
周昊然感到一阵温暖的触感覆上了他的脸颊。他睁开眼,看见徐谙正小心翼翼的为他擦着泪。“没关系,还有我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面前的少年轻声对他说。
我是个内向的人,我从来都不会交朋友,也从来不会有人想要主动接近我,周昊然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徐谙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只有这一个朋友。
“天要黑了,我们先走吧。”是徐谙的声音。周昊然点了点头,牵住了友人伸来的手。两个少年肩并肩,背对着夕阳的余晖,离开了操场。
所以我绝对不要再离开他了。
这是周昊然在离开之前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
记忆变得清晰起来了。是与三年前相似的场景,夕阳的光辉斜斜地照进了那段仿佛被压缩的岁月。
那是某个傍晚,在仅有半个小时的晚饭时段,周昊然和徐谙来到了学校中心的喷泉广场。他们坐在树荫下,背对着巨大的音乐喷泉,看着远处只有寥寥几个学生在散步的小广场。
“距离高考……”“还有21天。”徐谙无比自然的接道。他在年初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央美院的艺考,俨然成了全校艺体生中的佼佼者,而周昊然却因严重偏科失去了进入我理科尖子班的机会,被同学们看作成孤高的“异类”,每天都在巨大的压力下挣扎着度日。徐谙知道周昊然只有在自己要撑不住了的时候才会像现在这样单独叫他出来诉说自己的苦衷,只是稍稍说几句,最多掉几滴泪,只要得到了他的安慰,立刻忍住痛苦露出微笑,说着“那就好”像是害怕添麻烦一般不再向他倾诉,继续默默承受着那些悲伤。
……真是的,温柔得过分了啊,这家伙。
徐谙正自己胡思乱想着,坐在他身边的周昊然却突然开口:“……是,我的母亲。”他小声地说出了第一句话,略微颤抖的嗓音中透着悲伤与疲惫,“她每天为我操劳,很辛苦,身体不舒服了也不去检查……最近实在撑不住了才去了医院。”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中已混进了哭腔,“……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医生说就算全力治疗,也,撑不了……”周昊然说不下去了,他捂着脸,压抑着自己的哭声,泪水顺着指缝滴到了水泥地上。
夕阳的光辉仿佛比来时更加灿烂了。他们的身后一声巨响,巨大的喷泉开始喷出华丽的水花。扑啦啦地,不远处的树林中有群鸟被惊飞,徐谙默默地伸出手臂,揽住了身旁泣不成声的周昊然。
不知过了多久,循声来看喷泉的学生渐渐变多,周昊然的情绪稍稍稳定了下来,接着说:“我妈的收入不高,拿钱治病的话,就怕大学哭的学费会不够……所以,她不想…继续治疗了。……我……又要变成一个人了……”说着,周昊然突然抓住了徐谙的另一只手,泪眼朦胧地与他对视着,用近乎乞求一般的语气说:“徐谙,我只剩下你一个了,千万不要离开我……拜托了,请陪着我吧……不要再离开了,好吗……”
徐谙的心一颤。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挚友用这样的语气请求他陪着自己。虽然“不要离开”的请求,他已经从对方那里听到了很多次,但他感觉这次的请求,比以往哪一次都要真切。
“……别这样,我会为你心痛的。”徐谙轻声回答,像往常一样温柔地笑着注视着对方,“我已经答应过你那么多次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次也不会例外啊。要是你真的想让我再回答你一次的话,我就再说一遍好了。”
徐谙抬起被周昊然握住的那只手,缓缓放到了自己的胸口处。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
“你说过,绝对不会离开我的。”
意识陷入一片混沌之中。仿佛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不知何处的本能阻止了自己回想起来。
“你从来不会对我撒谎的。”
是手机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一定是我的错,对吧。”
杂乱的人群声音。炙热而坚硬的柏油路硌得膝盖生疼。远处似乎有救护车的鸣笛声。
“是我给我身边的人带来的噩运吧。”
“是你害死了他。”“是你害死了他。”“是你害死了他。”
“是你害死的是你害死的是你害死的”
“是你你你你你——”
胸口传来撕裂般的痛楚。面前似乎有谁倒在了柏油地上,是谁——
“大家都是骗子。”
周昊然睁开了眼。胸口的疼痛仍未消失,他呆呆地垂着头,盯着放在自己大腿上的速写本。屋内昏暗无光,只有速写本封面上的那一抹血迹刺痛着他的双眼。他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像梦游一般,他略显吃力地呼吸着,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将速写本放回了桌子上。桌面上残留着不知何时弄上的漆黑的痕迹,由于长时间没有清理而变得脏兮兮的。周昊然站在桌前,一手撑着桌面,一手拿起了一个在桌子上放着,半截刀刃还露在外面的美工刀。美工刀的刀刃依旧锋利,只是已经变得黑乎乎的了。
周昊然感到自己的心跳似乎停了半拍。本来就不甚清醒的意识突然被不明来历的痛苦撕扯起来,他紧紧攥着那把美工刀,艰难地大口喘息着,但吸入的空气每增加一口,胸口的疼痛就更剧烈一分。在他那一片混沌的意识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赎罪”。
“你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那个声音似乎在这么质问他。他不知道。
“你活着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噩运。”无休止的痛苦就好像要把他的心脏撕裂一般。
“你现在精神崩溃,疾病缠身,身边无依无靠。”周昊然不知道这个声音是谁,但他已经没有力气反驳了。
“你在痛苦吧?——来吧,把你手上的东西朝着你的痛苦狠狠刺下去吧,这样一切就都能结束了。”……啊啊,说的没错啊。反正就算我死掉了,也不会有人在意我的吧。
“你就算死掉了,也不用担心到了天堂后见到了重要的人会感到悔恨啊。”
周昊然举起了那把美工刀。他拿刀的手在止不住地颤抖着。
“因为你这样的人只能下地狱。”
周昊然将手上的刀猛地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
周昊然惊醒了。冷汗顺着他的额角淌下,滴在了速写本一片空白的内页上。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脏还在止不住地狂跳,伴随着胸腔内一阵阵的刺痛。依旧皎洁的月光照进屋内,映出了他因恐惧而苍白的脸。
“……刚刚的,是梦?”周昊然惊魂未定地看向一旁的书桌。书桌虽然略显陈旧,但是被打理得很干净。他扶着身旁的桌面站起来,从桌上的笔筒中抽出了那把美工刀。折断过几次的美工刀,刀刃上早已布满了锈斑。
“我为什么……会梦见自己,在自杀?”
周昊然出神地盯着那一片片不规则的锈班,意识仿佛被抽离了躯体一般变得恍惚,梦里的那个声音是谁,他不知道,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某一部分意识掩盖了自己本应理解的事实。梦里的自己似乎已经厌倦了活着,但周昊然感觉自己对“死亡”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现在的他仿佛被挤入了生与死的夹缝之间,徘徊着不知究竟该选择哪一边。
“如果要习惯这种痛楚的话……”
周昊然像是再次坠入了梦境一般地,缓缓举起了那把美工刀。但是这次,美工刀的刀刃落在了他撑在桌面上的左手上。
是皮肉被割裂的刺痛。刀刃所过之处,有殷红的血缓缓流出。
好痛。右手的美工刀滑落在桌面上,周昊然无力地跪倒在地。
“我不要,我不想去习惯这种痛苦的事……”
泪水顺着他毫无血色的脸颊缓缓淌下,滴在冰冷的地板上。自己的脆弱与无能再一次深深刺痛了周昊然的心。
没多久,钝痛混合着温暖的奇异感觉覆盖了手上已经停止流血的伤口。周昊然呆呆地看着自己被鲜血浸透的左手。“未被清理的血,会变黑。……沾了血的刀,时间久了会生锈。”
周昊然感觉自己的心里不知何处,在陈旧的血迹覆盖下长出了锈斑。
桌面上残留的血迹干涸了,原本是鲜红的地方变成难以清除的一片漆黑。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