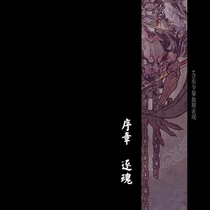“你还在下那盘棋吗?”
白子似是听到梦中有人这么说了,他感觉自己像是在梦里,有点温柔的气息包裹着周身,面前放着他执念的那局棋。
有个模糊的人影在和他对弈,每一子都落在他空荡荡的心里,泛出一丝的涟漪,挠的痒痒的。他对那影子有没由来的好感,好像从很久以前他就在仰慕着影子了。
“你还在下那盘棋吗?”
那声音又问了一次,白子想答:“是啊,此刻我正下着呢。”
但是他不能,困顿的情绪像是温水一样,柔软的煮着。他开不了口,只觉得困。
于是他在梦一样的地方入了梦,倒下之前那影子好像清晰了不少,隐约能见着轮廓了。
但影子却不是什么一直仰慕的人,那是白子自己,在看着自己笑。
我是谁?
离上一次见到已经有些时日了,相泽泪心早就静了不少,但每每想到如梦似幻般有些诡谲的灯会,还有在那之后那像个雾一样的邀请,还是在心间会敛起波澜。只不过悬在思维之上的那束冰锥早就化了,化作了一潭死水,想起的时候面色只有薄凉。
她是不想这样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心是自由的,如今却是被谜团束缚着。她想要恣意的追寻真相,但话到嘴边的时候总会咽下去,然后更深更深的谜团就浮现了出来,扎根在心里。可那个与棋为伴的白先生总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人开不了口的魔力。
那可真的是个神秘的男人。
相泽泪是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会变成这样心事重重的样子,毕竟如天赐福音,生得聪慧的好孩子总是一帆风顺的,就也不会有多余的想法了。如今这却像是多年的风调雨顺后,洪灾到来的那些个日子,她处在漩涡的中心,再也没能平安的出来。
她想叹气,但脸上却是和那个人如出一辙的似笑非笑,等意识到的时候,这笑容本身又让她想叹气了。她真如名字那样开始有了难,可她不想哭,她只是无法解释也觉得有点不自由罢了。
那可真的是个讨厌的男人。
待到寒气稍稍褪去的时候,相泽泪披着白先生留下的那披风来到了那园子里。这宅子本就是随着小姐一起长大的,虽然若是这样说会有点怪异的感觉,但要是这宅子,这卜伴园是个人的话,也是个能了解小姐心性的人了。说来也是神奇,这园林每每来的时候看起来都有些许的不同,而季节变换的时候更是如此。如今已是大寒了,先前的花早已谢了,却不合时宜凌乱的洒落在地上,盛放的寒梅疯了似的恣意生长着,毫无章法。只在相泽泪经过的时候像是人的手一样挑起那披风,撕扯一样的想要将它拽下来。
但相泽泪只是牢牢地抓着披风不想松手,她本不想披着的,这让她老是忘不掉的去想一个人。可是她想,她想一直想着直到想出个什么名堂来。少女的眉眼在雪的白和梅的红之中怅然又茫茫的楚楚可怜着,她开始有点不了解自己了,或者说第一次开始正视成长了,她甚至开始有些迷恋那被思考所围困的痛楚。
她走着,手无意识的抚过那些花瓣。还有些说不出名头的,看起来本不该是开在这个季节的花,那些花有着血似的红艳,带着令人眷恋的温度,疯长一样的蹭在了相泽泪的脸上,衬着那失了血色的脸有几分冷峻的活气,又像是恋人的手一样轻柔。那若是真的是个人,一定很爱小姐吧。
相泽泪不是没想过,她儿时来这儿的时候隐约的觉得能瞧见什么人,但再去细看的时候却又消失不见了。再等时日久了,也只觉得这园林能读的懂人心,再也没了别的想法。
她也是想过的呀,这园林若是另一位小姐,能陪着她该有多好。
解刻也是在这时候踏入院子里的,他没由来的感觉到心悸。刚踏进去的时候那些寒梅似是在阻挠着他一样,又放弃似的垂了下去,解刻甚至都能感觉到有什么视线在不满的盯着他,却又不屑于出现在他面前。他只是走着,看到相泽泪在中间无言的站着,木色的花枝和红色的花烙印在白色的披风和白皙的皮肤上,美得令人惊心动魄,却又带着点求而不得的悲伤。
“……你又在这呆着了,小姐。”解刻手搭在石墙上,面色冷的像把刀——他也确实是把刀,只不过是生来如此,没什么好说的。
相泽泪听见了也并没有回头,解刻也不语,一幅丝毫不准备过问的架势。两人就这么在似有若无的风里站着,然后风大了起来,吹散了娇嫩的花枝,那画一样的残忍开始逐渐的消亡,感觉却更冷了。
太冷了,若是再不能从海里逃出来的话,心是会结成冰的。
“我从前从未想过,但现在时而会想。”相泽泪紧了紧身上的披风,站在一地残花之中“你想要的真相,你追寻的。那是你想要的吗?”
“……何出此言。”
“你也看见了,我这些日子里来这幅不成器的样子,但我是愿意的,我心甘情愿。”少女的语气带着点自嘲的味道,但丝毫掩盖不了骨子里那股少年心气的骄傲“那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是为了得到一个我不想要的答案才去想的。但是你呢,你真的想等到那个人吗?哪怕我把你带了回来,我——”
“……我不知道。”解刻语气稳稳地,神色也未曾变过“我等了这么久,我也不介意再等久一点了。”
“你可真是个怪人。”相泽泪完全恢复了千金该有的姿态,那令人舒适的傲慢像一层柔软的轻纱重新的披在了少女的身上。这些精神上的装饰闪烁着微光,将少女重新包裹成了那个不知疾苦的大小姐。
“……我没有别的了。”解刻语气淡淡的,在相泽泪听来却有了如出一辙的薄凉“我没有别的了,这是我唯一能追寻的东西了。”
“…………你可真是个怪人。”
然后在院子里的两人都听到了脚步声,不知何时那些稍显多余的花枝都慢慢的褪去了,也许是因为那风的原因,整个院子都没有之前那般拒人千里的感觉了,或者说甚至连曾经有的灵气都消失不见了。等声音停下的时候,那故意造作出缓慢脚步声的主人才从一旁现身,饶是相泽泪觉得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了,却还是稍稍提高了声音有些惊诧的叫道:“……白先生?”
来者正是困扰了诸人多日的那位书院先生,相泽泪是早已放弃去问人怎么来的了,解刻倒还有点疑惑的巡视了一下周围不知自己到底是哪里疏忽了,只是这一看就和白先生对上了视线。
一瞬间解刻感受到了冷,不是那种寒风中实质性的寒冷,也不是被毒舌吐着信子盯上后的阴冷,那是一种空无一物的寒冷,就像是自己每一次忘得干干净净之后那种过于空白的寒冷,他习惯了,却依旧讨厌这个。
解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白先生已经开始盯着解刻摆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相泽泪可能是冷着脸,或者说有些许的愣住了,看起来并不能说点什么。沉默却还是由肇事者自己打破的。
“这位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呢。”
白先生话刚说完,解刻就露出了有点迷惑的眼神,随后转为了释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但他是实打实的不记得,这记忆丢失的极为平等,说不记得,就是真的不记得。
他也不是什么死要面子的家伙,也就如实答了,尽管他觉得不对劲,尽管他觉得总有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开始缠绕上自己的脖颈。
“抱歉,我不认识你。”
……但你身上有血的味道。
然后白先生小声的笑了笑,说了句毫不相关的话,解刻似是听懂了,又是没听懂的样子。解刻心想小姐说的这位先生确实是个让人不解的家伙,算不上讨厌却让人不舒服的很。
但他真的没有多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多想。只是脑子里有根琴弦绷得太紧了,紧的他头痛到没办法忽视这讨厌的第六感。
“…………可我想,我大概是要赢你一局了。”
我想赢你,我想带走你,我想看看你的心。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心。
徒然堂是个神奇的地方。
她被白先生诱着独自进了雾中的街道,辗转迂回到了处新鲜地,经一个自称常山的年轻男子介绍引路,相泽泪半信半疑到了处打着“贩卖缘分”的古董店。这里倒是好玩,一个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好奇地看向她,脸上充满期待,几句话介绍了情况后,店长兴致缺缺退下,只留她一个在店里随意闲逛。
“你好,你是灵器吗?”她觉得有趣,胡乱凑到一个装扮异于寻常人的孩子身边打招呼。三言两语确认身份后,相泽泪问灵器愿不愿意被自己带走。那孩子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她先是惊喜、意外,随后黯淡下来,露出犹豫困惑之色,最后,小小的人形器魂抬起头来,标标准准地冲她摇头。
“为什么?”她觉得意外,轻挑眉梢“你不喜欢我吗?”见灵器又是一阵摇头,她进一步追问:“我看你明明渴望被人带走,为什么我来邀请你,你却又拒绝了呢?”
“如果小姐您不是与我命中注定的有缘人的话,被你带走也没意义了……”
缘分。
又见缘分。白先生曾经淡淡给她留下一句“有缘再见”,那时她就不服这说法。只要人还活着,总有法子相见,总有办法再续前缘。她不爱这把人世际遇交给玄乎乎的时机这种态度(可能尤其是针对白先生本人?),若是无缘,只要有心,总能再见,不是吗?
她又在徒然堂里徘徊了一阵,和许许多多灵器交谈。也许是器物的本性作祟,他们都喜欢跟作为人拥有肉身凡胎的她说话,听她讲只有人类才晓得事,只有人类才明晰的情。可兜兜转转好几圈,她邀请了好几个孩子跟她走,无一例外,灵器们都断然拒绝了。她虽然不信这命运缘分命理之说,倒也多少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既然人家不肯,她也懒得违背别人的本心,扭转灵器们的心意。不愿意走,那就不走罢!
就在相泽泪对眼前的花花绿绿有些厌时,她瞧见一个浅蓝色的影子茕茕立在一株松树下。她好奇靠近了看,是个面无表情的男人,不知道出神得盯着树干想些什么,那松树枝干都快被他盯穿了。


“先生还当真是个体面人。”
白先生一从小巷子里出来,迎面就看到相泽泪从边儿上出现,眼瞅着直直的就要快步着撞了过来,却硬生生的在人面前停下了。只见往日里眉间带笑眼角上翘泛着水光的姑娘,如今却是一副生硬的面孔,抬着头望着白先生。
“也是。不管怎么想那张灯结彩和人花前月下的灯会,先生这般人物都该和其他人家知书达理的大小姐过着,而不是和我这个小丫头。”相泽泪语气薄的像是初春雪未融的时候湖面那层冰,只稍稍憋不住,满腔的带着活气的怨就要破开冰面浮出来了。但少女的声音动听得很,怕是那薄冰碎裂成的破片,尝起来都能有丝丝的甜味。少女的眼睛也是如此,纵然话中带着愤愤和不解,被那一双微微挑起的眼睛一瞧见,语气里都多了几分娇嗔的味道。
“但先生您未免太不厚道了,不知用的什么法子叫我去了那灯会,您没能来就不必说了,到了地方见到的却还是其他人——您这真是太不厚道了。”
“相小姐说的是,这是白某疏忽了。”白先生听罢露出了如往常那样的笑,其中有几分真假不得而知,但白先生自是不会在意这些的人,怕是他能这么样的低了头,都能算是福气了。
“所以——”
“但相小姐还请别太生气……那天你见到的——姑且算是白某家里人罢。”白先生像是知道少女要问什么一样,先开口打断了问话,也没在意相泽泪破功后那微微有些不满的脸“他是个好孩子,还请相小姐别太责怪了。”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神叨叨的——”
“这次是白某愧对了小姐,作为道歉,还请小姐收下这个。”
相泽泪微微低下了头,能看见白先生从袖子里伸出来的腕子一如袖子那般白的发光,而同样白的像是要化为虚无的手上则安安静静的有着一个白色的香囊。
相泽泪紧紧盯着看了许久,随后竟是笑了,语气中还有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讥讽“白先生是当真不懂女人心,我虽自是知道自己在你眼里不算成熟,但好歹你也从没见过女子用这么素净的香囊吧。”
“白某未曾自负到这个地步……相小姐不喜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即便如此还是希望小姐您收下。”白先生语气未变,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动过一丝一毫,只是用那双黑的不可思议的眼睛盯着相泽泪“我只是觉得,白色很适合您。”
这会儿说是要生气,也气不起来了。相泽泪近乎是刻意的强迫自己状似随意的接过那香囊,香囊上虽说是一片纯白,但细细看去有极其精美的暗纹绣在其上,藤蔓与花卉交错在一起,还有些说不上名头的纹样,连气味都不是寻常少女喜爱的带着暖意的味道,隐约的香气之中有点淡雅的意思。
这东西更像是白先生的。相泽泪只这样一想,就回忆起自己原来那个香囊里面还有一枚棋子“……你把这东西给我,那我是不是还得把你留在我这的还给你?说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放进去的?”
“相小姐自是不必担心,那枚棋子的话,早就已经回到这了。”白先生刻意忽视了后一个问题,单单是笑着,那递出香囊的手翻转了一番之后,一枚黑色的棋子赫然出现在手心。
那棋子还带着丝隐约的香味,分明是留在相泽泪那的那一枚。
“你——”
“白某送的香囊里也有一枚棋子。”白先生收回手,眼眸低垂着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摩挲着自己的扇子“棋自是从白某爱用的那副棋里取出来的,算作是一点心意吧。”
“……”
白先生还真是从不回答那些尖锐的问题啊。相泽泪这样想着,脸上不由自主的露出了有些微落寞的表情,但随着相泽泪愈是想,愈忍不住生气起来,那脸上落寞的表情也带着一丝少女的娇俏,变为了明显的不服气。
“白先生还真是自信,将自己整副棋里的棋送给了我。”相泽泪说出来的话似是夸赞,但语气里带着讥讽“若是白先生总归需要那一枚棋,却独独缺了那一枚,那该如何是好。”
“白某未曾想过——”
“别再那样酸唧唧的称呼自己了,没意思。”相泽泪哼了一声,将给外人看的小姐姿态卸的一干二净,此时只留了个眉目婉转的少女躯壳在这“先生你若是真的缺了这一枚,该怎么办?”
“白某——”白先生话未说完却又一顿,随后笑了笑,再度开口“说实话,若不是相小姐提起,我还没想过这件事。倒不如说……我认为自己并不会用到这一枚棋。”
“哦?先生还真是有自信啊……”
“那是当然。”白先生轻声答道,随后又用不知在想什么的眼神盯着相泽泪上下打量着,视线最后停留在少女的裙子上。
相泽泪确实是为了少女那爱美的心思,为了好看并没有选那厚重又累赘的服式,所以对于现在的气候而言,相泽泪穿的略显单薄。于是白先生解下了自己和衣服同色的白披风盖在了相泽泪的身上“……相小姐不是说了我棋艺应当不错吗,那既然是相小姐说的,自然得有点自信了。”将披风好好给相泽泪穿上后,白先生自然而然的替少女拂去了些微的褶皱,和善的开了口“相小姐还是好好穿着,别冷到了。”
也不知是真的因少女的羞涩,还是说纯粹是看到那个白先生做出这样的动作感到不适而已,相泽泪沉默着什么也没说,眼神只是在看着别处,手好像还在捏着那个香囊。
“若是相小姐还生气的话,不如我陪小姐您在这苏州逛一逛吧,难得来到了这儿。”白先生先开了口打破了沉默,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白先生的话里居然隐约带了点恳求的意味。
相泽泪也是难得来到苏州这地,而游玩途中居然在暂且歇息的住处收到了白先生的信,那信一如之前那样简洁的毫不讲道理。相泽泪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愿意赴约,明明因为之前灯会的事情自己生气的不行,但这次——说实话,相泽泪自然是不想来的,但想到白先生那个性子,总觉得不来,亏的反而是自己。
相泽泪甚至懒得去想白先生为什么会在苏州这件事,反正问了白先生也不会答罢。
“这儿可是苏州,白先生。您又有想法了?”
“说来也是巧合……我之前也陪另一位姑娘来过这儿。”白先生瞅见相泽泪脸上又露出那种混杂了不满和嗤笑的表情,不赶不急的解释道“并不是相小姐您想的那样,只是寻常事物罢了。”
“你以为我想的是什么样呀。”相泽泪扭过脸不再看着白先生,但手却悄悄攥紧了白先生披上的披风,然而终究是耐不住好奇,眼神悄悄的转了回来。半晌后见白先生只是笑着并没有答话,又叹了口气把脸扭了回来“可你连和我再下盘棋都不愿意了。”
“……白某有些自身的原因——”
“你又这样称呼自己了。”相泽泪将那复杂的表情洗了去,脸上带着温和纯然的宁静“那我先把你这道歉收着,逛逛的事儿也暂且放着吧。”
白先生点了点头,看着相泽泪叹了口气,只是与那之前稍显无奈的叹气不同,这次是带着轻松的情绪,那双眼睛里闪着水灵的光“但……我要是想起来要去逛着,你可不能推脱!”
有笑声。
相泽泪自见到白先生开始,第一次听见他笑出了声来,那平时似笑非笑的表情居然变得真挚了,但很快那声音就停了下来,似只有短短一瞬——那确实只有一瞬。
“那我可等着相小姐了。”
天好像更冷了,初雪梦一样的飘了下来。相泽泪抬起头,雪映入了少女的眼睛里,闪着白色的光。而此时白先生好像说了些什么,那话还有些耳熟,像是在哪里听过。
“——白色的……”
“你说什么?”
相泽泪抬起头看向白先生,白先生好像没注意到视线,只是望着天空出了神。半晌后才像是自嘲一样的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
“……”
相泽泪心想自己或许是累了,连看这神秘的家伙都显得有些多愁善感了起来,怕不是错觉,也或许是因为拿了人家的东西总有点心思在吧。这些日子遇到的事情都太过诡谲,可能真的是累了。
“相小姐。”
相泽泪循声看去,白先生视线并不在少女的身上,却是望着远远的地方。是该冷起来的天气了,但天明明带着些晴朗的感觉,唯独白先生看着的那街道浓雾散不开,相泽泪只好不解的继续看着白先生,等着一个解释。
“……那雾里似乎有个有趣的店呢。”
相泽泪依旧是云里雾里,只是眼神不由自主的跟着白先生的视线,牢牢地盯着那片雾。雪依旧在下着,但不知为何站在白先生的身边,纵然是披着衣裳,却依旧能感受到不同往日的刺骨到令人心颤的寒冷。但就算是如此视线依旧无法逃离开,只能牢牢的盯着,白先生的声音像是蛊惑人心的毒物一样,深深的烙印在了脑海。
他开口了,声音却不在身边,好像隔着很远很远,远到逐渐淡了气息,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白先生如同来的时候那样,只稍一会便无声息的不见了,但那声音还留着,让相泽泪不由得紧握了白色的香囊,直到握的痛了,直到能感觉到那香囊里形似棋子的东西。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