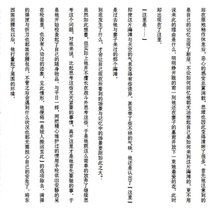莉芙湾望无止境的沙滩的一角,一只鸟和一只兔子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鸟背后应该长着翅膀的地方正勃勃地往外冒着血泡,翅膀则早已不见踪影;兔子则割舍了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双腿因为剧痛而止不住地发抖。
他们的手上各有一把武器——鸟执着最后一支手术刀,那是鸟带来的十几二十把手术刀中最幸运的一支;兔子呢,捏着一把手术刀大小石刀,那是兔子锻造的成百上千把石中剑中最不幸的一把。
“你不飞,我也不变豆腐,这样真的扯平了吧。”
“是啊,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你切丁了呢!”
“呜啊好可怕!”
“抱歉你卸了我的翅膀,把我的刀还有包包披肩——你知道这些要多少毛爷爷吗?总之你现在想逃也来不及了,乖乖变成莉芙湾的白色垃圾吧!”
“我,我才不跑呢!临阵逃脱还算什么男人!”
“你现在还是男人吗?”
“呜……呜呜呜!”
没有被夕阳染红的霞彩,也没拍打礁石的巨浪,就视觉效果上来说,莉芙湾一点也不适合决斗。为什么一只鸟和一只兔子会在这种地方打连个决斗盘都不PS上去的架呢?这还要追溯到几个小时之前。
白豆腐脑——也就是前文中对峙一方的兔子——因为之前某个事件,在莉芙湾制造了大量的白色污染。虽然没人投诉,但白豆腐脑还是对亲手将家园变成豆腐汤的事情感到十分愧疚。
为了赎罪,白豆腐脑把他找得到的污染物——也就是漂得满海都是的豆腐——一块一块地打捞起来搬到了沙滩上,小兔子捞呀捞呀,花了好大的功夫,终于让海洋回归了原本的颜色。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白豆腐脑十分欣慰,他转过身,想做个做好事不留名的红领巾,但一回头,就看到了沙滩上小山一样高的豆腐堆。
“呜呜呜……这样根本吃不完啊……”
白豆腐脑虽然有把包括空气和海水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变成豆腐的特殊能力,但其实他自己却不爱吃豆腐。
开个豆腐店,把豆腐送给饥肠辘辘的旅行者,让他们感受到莉芙湾的温暖和甜蜜——只能这么做了,白豆腐脑是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兔子,很快他就将设想化为了行动,用豆腐搭造了一间豆腐屋。
第一个客人很快就上门了,那是一张生脸孔——不过白豆腐脑在莉芙湾认识的生物本来就不多,绝大多数的生物在他眼里都是生脸孔。
“主人欢迎回家!你是要先吃豆腐呢还是先吃豆腐脑?”
“啊……?”
在白豆腐脑的热情接待下,客人还是坐下来吃起了豆腐。
“呜——嗯!这个豆腐入口即化!吸一口就能灌下去!而且还带有椰子的清甜!虽然这破沙滩上连棵草都没有!但我却看到了椰子漂洋过海落地生根拔地而起的未来!”
客人一块接着一块地吃着豆腐,很快和白豆腐脑打成了一片。
“我叫白豆腐脑,客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啊我叫苏姬,白豆腐脑这个名字好长,我可以叫你脑脑吗?”
“好啊好啊,我可以叫你姬——”看到苏姬的脸有点黑,白豆腐脑马上改了口,“我可以叫你苏苏吗?”
“可以啊,苏苏也很可爱嘛。”
苏姬和白豆腐脑聊了很多,从天上的盖子聊到身上的记号,把这两天的见闻连同来这里之前的趣事都给白豆腐脑说了个遍。
“苏苏小时候好可爱!”
“不不不,你才可爱呢,长这么可爱还做饭好吃,将来一定能嫁个好人!”
“嗯,我以后一定会嫁个好人,一定不会随随便便让变态摸到!”
“什么?变态?!居然有这么可恶的变态连脑脑都不放过!”
乘着兴头,白豆腐脑和苏姬说了前一天被变态追的遭遇,苏姬更加讨厌变态了。
“说起来苏苏也很可爱啊,遇到过变态吗?就是那种不好好穿衣服,到处摸人吃豆腐的人?”
不好好穿衣服?苏姬脑海中马上浮现了一个露腹肌的面具男,不不不,比利是个好人才不是变态,苏姬马上把这个对不住比利的念头打消了。
“没有哦,因为我很强,能手撕变态,所以变态都不敢靠近我,脑脑如果再遇到变态就告诉我,我帮你撕了他!”
“好啊好啊,对哦苏苏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不会碰到变态了呢!”
“唔,碰到变态……变态有毒吗?一坨会追着人跑的百变怪再加上毒,现在的变态真先进……”
“嗯嗯,很多海洋生物都有毒,而且变态的毒更加可怕!苏苏还是不要管我,自己先逃比较要紧!”
“不不不,脑脑是我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看着脑脑被变态欺负?”
“呜!苏苏你真好!我没有什么能报答你,只能以身相许!”
说完白豆腐脑不等苏姬阻止,就撩起了自己的围裙,围裙下面一览无余。
“呀!”作为实习医生,苏姬早就看惯了人体的各个部位,但毫无防备地得知了白豆腐脑是男孩子的事实,还是让她受了点打击,但这打击并未持续多久,她的注意,很快被那器官上的数字吸引了,“零……九……一……零九一?!”
“是啊和苏苏一样哦。”
“呃你先把围裙放下……”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苏姬陷入了沉思。
“我想这一定是我们命中注定的证明吧!”白豆腐脑整好了围裙,欢快地蹦到了苏姬边上,取下了她挂在肩上的背包,“这个借我一下!为了庆祝我和苏苏的相遇,我要给苏苏表演个魔术!”
白豆腐脑从包里掏出来一把手术刀——乱翻别人的包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九十一秒后的苏姬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这个可以称得上冒犯的行为。(大家一起来数秒> <)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秒)
白豆腐脑数完七下,手术刀一下就变成了一块白豆腐。
“哇,好厉害!”(十四秒)
“这是白豆腐脑的必杀技,叫‘变成甜甜白豆腐’,简称的话,叫‘甜’就行了。”(二十一秒)
接着白豆腐脑跳到了苏姬的肩上。(二十八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三十五秒)
苏姬的披肩变成了一件雪花一样的礼服。
“哇这是什么?《冰雪奇缘》吗?”(四十二秒)
“是某个东方国家的传统民间艺术,叫‘拉花’哦。”(四十九秒)
“哦哦!是把只有上身长的披肩对称下刀,裁成无数相互连接的圆环,再利用重力将圆环拉开,就能得到比原来披肩体积大很多的礼服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做过!过节的时候布置教室都用这个!不过一下子把披肩裁得像雪花一样,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七十秒)
“哼哼,魔术怎么能泄底呢?”白豆腐脑自豪地晃了晃手,如果有手指的话,他伸出的应该是食指,“不过是朋友的话,告诉一下也没关系。”
白豆腐脑又跳到了苏姬的背上(七十七秒),这次他又要做什么呢?苏姬满怀期待得等待着白豆腐脑的甜甜白豆腐,和白豆腐脑一起数了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八十四秒),七!”
苏姬背后的重量减轻了,但她却不再期待白豆腐脑从她背上跳下来后会给她什么惊喜,因为她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九十一秒)
不能叫,不能回头,就当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必须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这一次脑脑又变了什么呢?”
“这次脑脑变了翅膀呢!”说罢白豆腐脑一手举着一只翅膀连蹦带跳地跑到了苏姬面前,可惜豆腐做的不太坚固,挥了两下就碎了。
魔术失败,白豆腐脑哭了起来。
“人生中总会经历几次失败,别太难过,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
苏姬安慰着白豆腐脑,一边也用同样的句子安慰着自己——苏姬,那个向来冷静敏锐的苏姬居然毫无防备地让人抢了武器、裁了铠甲、卸了翅膀?!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仔细一看,理应空无一物的莉芙湾上居然堆满了豆腐?在这个连棵草都没有的海湾居然有椰子味的甜点?还有那会直立行走还会说话的兔子?不正常,哪个都不正常,要是平时的自己,是绝对不会在这种地方和怪物吃甜点的,更何况自己一点也不饿!
是替身攻击!它一定对自己做了什么,让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恐惧,甚至连异常都无法察觉——苏姬只能这样想了,要不是翅膀断裂的剧痛,恐怕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像一块片在烤架上旋转的土耳其烤肉一样任人宰割。
再看那怪物,那怪物知道自己察觉异常了吗?看它的样子和之前没什么区别,苏姬只能趁他还没有对自己起戒心的时候,先下手为强。
“脑脑……我也有个魔术要表演给你看,你能把我的包拿给我吗?”
“好哦。”白豆腐脑根本没有刚刚撕了苏姬翅膀的自觉,蹦蹦跳跳地把苏姬的包拿了过来。
翅根的剧痛让苏姬一刻都不想耽搁,她把手伸进了包里,摸索了一圈,顿时心凉了半截。
包里空空如也!是哦,刚才白豆腐脑变魔术的时候,好像是把里面的手术刀——苏姬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就算是那怪物的魔术,但在这个陌生的莉芙湾,没有比武器更重要的东西了,就这样把生命一样重要的武器交出去,实在不可原谅。
“脑脑……白豆腐脑?!”
“嗯?怎么回事?”
“啊,没什么……”是因为翅膀流血导致大脑空白吗?刚才有那么一瞬,豆腐脑好像消失了,“说起来你前面说要告诉我魔术怎么变的,我想先听听脑脑是怎么变魔术哒。”
说完苏姬把空包递给了白豆腐脑,观察,积累经验,在和这怪物彻底决裂前,这是她必须做的事。
“这个啊,是这样的。”白豆腐脑接过了苏姬的包,“我啊,碰了七秒的东西,都会变成白豆腐哦。”
苏姬的大脑一片空白。开始她还对自己的翅膀抱有一丝希望,希望白豆腐脑之前拿出来的豆腐翅膀只是事先准备好的魔术,自己的翅膀只是被他藏在了沙子里,只要找出来就能给自己重新接回去,然而现在,这个天真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苏姬又一阵眩晕,白豆腐脑手里的背包已经变成了白豆腐,包上的金属扣很快压垮豆腐,失去支撑掉在了沙滩上。
真的有这种魔术啊——苏姬真希望自己在做梦——她盯着白豆腐脑的一举一动,把剩下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思考对策上。
白豆腐脑会一种能把包括手术刀、披肩、包,还有翅膀变成豆腐的魔术。他在把包变成豆腐时,没有把包上的金属扣变成豆腐,金属扣和手术刀一样都是由金属制成,如果可以把手术刀变成豆腐,那就可以把金属扣变成豆腐,为什么他当时没有这么做呢?除了时间以外,要把东西变成豆腐一定还有其他限制,比方说,他变手术刀时是用手握着一把手术刀,变包的时候是用手举着包带——他的手只碰到了皮革没有碰触到金属扣——也就是说,除了“时间”和“碰触”外,变豆腐的条件还和“材质”有关。必须要是同种材质的东西才会变成豆腐,所以在变包时没有把金属扣也豆腐化——而且这“同种材质”并不限于“同件物品”,就像被捏紧的手术刀、披肩上相互交织的线、蜷在金属扣上的皮革一样,并不要“同件物品”,只要“连在一起的同种材质的物品”就行了。
隔着手套或衣物碰触白豆腐脑不会被变成豆腐——苏姬很快得出了这个结论——两只手上的手套都好好地戴着,只要在七秒内手撕了他就行!
“脑脑过来,笑一个——”
苏姬趁白豆腐脑把脸伸过来的时候捏住了白豆腐脑脸颊的两侧,然后使劲地向两边——拉——白豆腐脑的脸被拉长了苏姬手臂两倍的长度,但一点断裂的意思都没有。
这,这什么!苏姬在脑海中吼叫,要是鸟的话,刚才那一下,早就被空手撕成两半了!为什么这家伙的脸能被拉得这么长!苏姬被被白豆腐脑的弹性一惊,下意识地松了手,白豆腐脑的脸就像橡皮筋一样“啪”的一声恢复了原状。
“呜,呜呜哈哈哈哈哈哈——是把脸变长的魔术——”白豆腐脑被苏姬这么一逗,马上笑开了花,笑着笑着,就被苏姬一脚踹出百米远。
白豆腐脑脸着地后又向前翻滚了数个跟头,才终于在沙滩上停了下来,而苏姬在收完那脚后就助跑腾空——虽然没有翅膀,但她的速度也足以使她短时间摆脱重力的束缚——她用鞋跟对准正撑着什么爬起来的白豆腐脑,想像踢爆怪人的假面骑士一样在白豆腐脑身上开一个大洞。
“不对!”突然,苏姬伸出了手,狠狠地掐住了沙砾下的土壤。指甲剥离手指的剧痛震得苏姬浑身发颤,手指翻折,手臂脱臼,苏姬半身插进了地里,沾了一脸沙。
“你……你哪来的这东西……”
苏姬脚尖抵着白豆腐脑刚砸进地里的凶器,惊愕之余暗暗庆幸自己还有速度这一武器——白豆腐脑就在起身的瞬间,挥出一柄长剑向苏姬劈了过来,要不是反应及时,恐怕已经被对半劈开了——苏姬趁白豆腐脑把剑从沙子里拔出来时一个侧滚站了起来,用来制动的那只手已经没有知觉,脸上也火辣辣地疼,但一只手和一张脸的代价换一条命已经值太多了。
“这个啊……我没说过吗?我昨天被变态追的时候造了把剑,把变态打死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变态之墓’四个字呢!”
“但刚才,你好像想用变态之墓打死我哦?”
“不是哦,我只是站起来的时候……怎么说……后坐力?”
“后坐力?那么强的后坐力能砍死我哦?”
“不是要砍死苏苏!脑脑只是想和苏苏做朋友!”
“我不是很想和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搞残废的人交朋友,你能不能找别人?今天我也累了,我们就这样再见,脑脑下次找个新朋友,不要一见面就搞残他,那样他一定很乐意和脑脑做朋友,我就算了好不好?”
“呜不行!因为……呃……因为……因为你……那个……你看到了……”白豆腐脑吱吱唔唔地,变得和煮熟的虾子一样通红,“你……你看到了白豆腐脑的!呃……白豆腐脑围裙下面的!嗯就是‘那个’!所以脑脑一定要和苏苏做朋友!”
“啥?”‘那个’是什么?苏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白豆腐脑给她看的裙底风光,“难道……你说的是……生殖器?”
“呜啊!”
“那是你给我看的,我也想马上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嗯,我会很快忘了‘那个’的请放心,我们就这样说再见吧。”
“呜!不是呜!是那个!是脑脑白白上唯一的脏脏!”
“白白上的脏脏”又是什么鬼?苏姬一边思考着白豆腐脑围裙下还有什么比生殖器更像脏脏的东西,一边趁聊两边都焦头烂额的时候,用右手攀上挂在一边的左臂,狠狠一提——一道仿佛被雷劈的痛感流过全身后,肩关节被接上了——当医生真好,可以自己接骨。苏姬瞄了一眼刚接好的左手,手套里全是血,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甲肯定全翻了,手指和手背形成了一个平时不可能形成的锐角——“咯嚓”,苏姬把手指掰回了正常的角度,手腕一颤,“091”三个暗红色的数字跃入了苏姬的眼帘。
“难道这数字……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
“啊!我不是说过吗,这个数字是苏苏和脑脑有缘——”
“不要叫我苏苏!”
“呃,这个数字是姬姬和脑脑有缘——是姬姬和脑脑是同一个人的证明!”
“同……同一个人?”
“就是说,苏苏啊不姬姬和脑脑是同一个人!脑脑要和姬姬做朋友!”
“啊?”
苏姬觉得大脑有点混乱,手腕上“091”的编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苏姬对它也做了很多包括大逃杀在内设想,不过交朋友这种她还真没想过——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怎么可能是交友平台?相亲也要找个环境好的地方!
“我以前,也和石头先生、小海姐姐交过朋友,但是他们根本不懂脑脑的话,也不会说脑脑的话,虽然和脑脑在一起,但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脑脑玩过,这样的朋友只是为了做朋友而做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能和脑脑做朋友,真正懂脑脑的,只有脑脑,只有脑脑——也就是姬姬——能和脑脑做朋友——”白豆腐脑举着剑转了一圈,剑尖刚好掠过苏姬的鼻尖,“能和脑脑聊这么开心的人,只有姬姬一个,所以脑脑想和姬姬做朋友!”
“因为你是个通灵者,所以想把我杀了做朋友。不过看外形,你才该是我的持有灵哦?”
“才不是,我只是想把姬姬变成朋友而已!”
“说这种话之前要先把剑放下。”要是真能放下就有鬼了——虽然白豆腐脑长得一副蠢样,但苏姬可没有天真到那个地步,这把“变态之墓”可不是什么小刀,是有半个比利高的长剑,如果剑是实心的话,那被砍一刀不被当场碾断也会骨折,不管他什么动机,只要有杀人的打算就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优势。
“我才不放哼!”
果然。
“这是帮我击退变态的好伙伴!要我放开这把剑还不如把这个给你!”
白豆腐脑把没拿剑的手伸进围裙,从里面掏出一把沾满血的手术刀——手术刀一个弧线被抛到了苏姬面前,苏姬“啪”地一声接了个正着。
“姬姬,决斗吧!你赢了我们就做朋友!”
输了就会被杀吗?剧情走向终于有点符合苏姬的猜想了。
比刚才好一点,现在苏姬手里有武器了。但两边武器的大小还是让苏姬笑不出来。而且现在真正棘手的不是那把剑——白豆腐脑还有把东西变成豆腐的魔术,她会突然把沙滩变成豆腐,让自己失去平衡后乘机斩杀自己吗?苏姬不是替身使者,看不到白豆腐脑的替身,要是白豆腐脑的魔术也有射程一说就好了,但现在这种无凭无据的设想只能让苏姬越来越紧张。
说曹操曹操到,白豆腐马上不负期待地出现了,这是一把剑形状的白豆腐,长得就和变态之墓一模一样。
变态之墓一样的豆腐很快发生了变化,它就像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一样,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卧槽,这货还有个黑洞!苏姬下意识地站稳了脚跟,怕自己也会被吸进去。
“咕……唔……偶尔吃吃还挺好吃的……”白豆腐脑舔着自己的手,豆腐已经不见了,他手上的已经不是那把半个比利长的变态之墓,而是一把和手术刀差不多大小的石刀,“这样子脑脑的武器也和姬姬一样了,可以愉快地和姬姬决斗了呢。”
“……你在做什么?”
“我要和姬姬公平决斗,不然就像在吊打小学生一样。”
“你以为武器一样就公平了吗?”苏姬已经废了一对翅膀和半条手,但白豆腐脑一点伤都没受过,这可不是武器一不一样的问题。
“嗯,你看脑脑没翅膀,苏苏也没翅膀,一模一样啊。”
“闭嘴!你还有**我没有呢,怎么不见你公平一下?”
“……唔对……”
在苏姬的训斥下,白豆腐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果断地把石刀伸进了围裙,把那个苏姬没有的部位切了下来。
“………………你才是变态吧……”
“091”从围裙里掉了出来,断面非常平整,看来白豆腐脑的石刀非常锋利,一点也不亚于金属手术刀。
“你不飞,我也不变豆腐,这样真的扯平了吧。”
“是啊,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你切丁了呢!”
“呜啊好可怕!”
“抱歉你卸了我的翅膀,把我的刀还有包包披肩——你知道这些要多少毛爷爷吗?总之你现在想逃也逃不掉了,乖乖变成莉芙湾的白色垃圾吧!”
“我,我才不跑呢!临阵逃脱还算什么男人!”
“你现在还是男人吗?”
“呜……呜呜呜!”
莉芙湾望无止境的沙滩的一角,一只鸟和一只兔子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白豆腐脑把他的断肢抛向了天空——断肢落地即是决斗开始的信号。
苏姬和白豆腐脑开始奔跑,因为武器都是方便投掷的小刀,所以双方都需要不停地移动来防止自己变成飞刀的靶子。
“呀——”白豆腐脑跑着跑着,突然被沙滩上的小贝壳绊了一跤。
“现在靠平地摔卖萌也没用了!”苏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将手术刀掷向了白豆腐脑的脑门——这怪物会因为头部中刀死亡吗?还是说——“啪”,和苏姬预想的一样,白豆腐脑没那么容易死,手术刀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截停在半空。白豆腐脑保持着脸着地的趴姿,用两只耳朵夹住了刀刃的两侧——空手,不,是“空耳”入白刃!
“喝呀!”苏姬从天而降,斜踩在了白豆腐脑的头上。苏姬这一记滑铲的初始速度非常大,即使有地面的摩擦也将白豆腐脑在沙滩上推行了四五米,把白豆腐脑一头闷进了海水里。
“呜——呜呜呜——”白豆腐脑冒着泡泡挣扎了起来,但苏姬没有放过他,她一膝盖跪上了白豆腐脑的脑袋,手脚并用,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白豆腐脑的头上,白豆腐脑挥着手上的石刀,但无奈手太短,伤不到苏姬一分一毫。
白豆腐脑挣扎了好一会,终于,一动不动了。
“呼——”苏姬摸了摸白豆腐脑的脉搏,软绵绵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应该是死了吧,还好我学医的时候杀过兔子——你该不会是我们杀过的兔子亡灵集合体吧——对不起哦,为了鸟类医学发展牺牲了你们这么多同胞……”
苏姬双手合十,为白豆腐脑哀悼了一会,然后在白豆腐脑的耳朵附近摸索了起来——最后一把手术刀也找不到了,苏姬有点眼花,决定上岸休息。她拧了拧浸饱了海水的裙子下摆,因为莉芙湾这鬼地方没有阳光,她还要等好一阵子才能把衣服完全晾干。
“啊……好想要个吹风机……”苏姬呈大字型趴倒,原来长有翅膀的地方火辣辣地疼,“回去以后有没有人肯捐对翅膀给我做翅膀移植呢?应该不会吧,翅膀对鸟的重要性可一点也不亚于**对兔子的重要性……啊那对雄鸟来说,是翅膀重要还是**重要呢?哦呸,我怎么会想这么无聊的问题!”
“姬姬姬姬,你在睡觉吗?”
是错觉吗?刚才好像听到了白豆腐脑的声音。
“怎么可能在睡觉,你干的好事,我疼得根本睡不着……”
“翅膀的事吗?对不起哦……”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啦!你怎么赔我?不要说你也切了**,我没有**,我不懂你的痛!”
“这样说的话……我也……没有翅膀啊……”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把我的翅膀还给我呜呜呜呜!”苏姬像小孩一样撒起娇来,因为刚刚结束了一场死斗,现在的苏姬就像大考考完一样,只想好好任性一把。暑假就在眼前,这种感觉自大学几年级起就离自己远去了呢?为了成为医生,每天玩命地看书准备考试,考试通过以后就没日没夜地加班实习,已经有几年没有这么全身放松过了,整个人都飘了起来,就连背上的伤都不再疼了。
白豆腐脑帮苏姬合上了眼睛。
苏姬睡得好熟,她的背上有两块白色的印记,覆盖在她伤口的位置——那里已经没有血流出来了——豆腐从她的伤口通进她的血管,在心脏绕了一圈,把她全身的血管都填了个严严实实。
“这样就不会流血也不会痛了吧,好好睡哦姬姬,醒来我们就是朋友了哦。”因为苏姬抱怨翅膀疼的关系,白豆腐脑特地在动苏姬血管的时候给她碰了块豆腐消除痛感——碰到豆腐后的七秒内,除了被豆腐轻轻搭上的感觉外,苏姬不会有任何感觉——这七秒刚好就是白豆腐脑把苏姬血液变成豆腐所需的时间,本来在被变豆腐的时候,苏姬应该会感到剧痛,之前卸她翅膀时,痛觉被豆腐屋的豆腐分摊掉了,所以苏姬没有感觉。这次沙滩上什么也没有,为了不让苏姬痛,白豆腐脑特意变了块豆腐给苏姬,这是他迎接新朋友用的见面礼。
苏姬已经全部变成了豆腐,不会僵硬也不会腐烂,就和白豆腐脑的其他朋友,就和石头先生还有小海姐姐一样,是块雪白雪白的豆腐。
“姬姬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和你一样,有家有朋友呢?啊不对,现在脑脑有了姬姬,已经有朋友了呢,现在只差一个家了,姬姬你说我的爸爸妈妈会是怎样的人呢?我会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以后我会生个儿子还是女儿呢?啊,我好像已经不能生了……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