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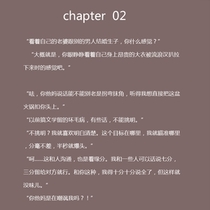





人类衰退后的第四百个冬天
“你是谁?”柏莎警戒地注视着面前这位突然出现的中年男人,手悄悄伸进野猪皮做的斗篷里,握着绑在腰间的石刀。对方穿着很怪异,柏莎从未见这种衣着。头上带着高高的帽子,看起来并不能保暖,衣服也穿得很薄,可中年男人却面色红润,似乎并不冷。
中年男人神经兮兮地环顾四周,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一步。柏莎跟着往后退,拿不准主意是不是要现在就用石刀戳瞎那个男人的眼睛。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就在柏莎犹豫的时候,那个男人发话了,“你如果知道了我的名字,你会被追杀的。”
柏莎皱眉,迟疑了一会儿:“什么是追杀?”
男人像是个受惊了的山鸡,急忙竖起一根手指:“嘘、嘘!小声点!”
一根食指抵在唇前,柏莎从未见过这种手势,不由得也将食指放到唇边,不解其意。
男人躬下身子,尽量与矮小的柏莎平视:“追杀……追杀就是……诶诶,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比你打猎还要危险。”
“不可能!”柏莎想也不想就否决,“还有什么比打猎还危险。”
男人努力眨眼,眼白发红而眼袋发黑,他揉了揉,伸出手指想比划比划,可又将手收了回去说道:“比打猎还危险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核爆炸,比如毒气实验,比如……比如……比如参加演唱会。”
“……听不懂。”
因为这一系列陌生的名词,原本应该保持的戒备在柏莎心底被慢慢腾升的好奇心取代了。
“总之你就装作没有见过我就好了!”男人有些烦躁,挥了挥手让柏莎离开,转身继续在地上挖坑。
在柏莎遇见这个男人之前他就在挖坑了,这个男人穿的奇怪,手上也没有任何工具,单纯只是用手挖土,也不知道是挖了多久,手上布满伤痕渗出鲜血。
——应该赶快回家。
虽然有个声音一直这样提醒自己,可柏莎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男人身边,慢慢蹲下来。而这个男人仿佛浑然不觉,只是继续用手挖坑,看也没看柏莎一眼。
“你为什么要挖坑?要布置陷阱吗?”柏莎终于按耐不住了。
男人仿佛突然惊醒,恐惧般地扭头死死盯着柏莎:“你是谁?你要来杀我?!”
对方的眼神是那样的陌生,仿佛全然忘了之前的对话。柏莎从没见过这样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她眨眨眼:“我是柏莎。”
“柏莎……哦,柏莎……我好像听过这名字,又好像没听过,记不清了。”男人停下手上的工作,稍稍抬头看着天际白云似乎在努力回想什么。
“……”
男人不说话了,维持盯着天空的姿势不动。柏莎在地上蹲了许久,可男人就像是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她考虑了许久,最后鼓起勇气轻轻碰了碰男人的手臂。
“噢噢!你是谁?!你要来杀我?!”男人仿佛重新恢复了意识,受到惊吓跌坐在地上。柏莎想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又要问一遍,可她还是回答了:“我是柏莎。”
“柏莎……哦,柏莎……对对,我记得柏莎,她是那么漂亮,眼睛就像是夜空一样美……对了,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柏莎不再回答,而是从地上捡起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块递到男人面前:“用这个挖吧。”
男人没说话,接过石块充当工具继续开始挖掘深坑。柏莎害怕男人又忘记了,趁着男人还记得自己,她赶紧询问:“你为什么要挖坑?”
男人挖坑的动作听了听,又环顾四周,然后凑近柏莎小声说道:“我在挖‘金字塔’!”
“金字塔?那是什么?”
男人突然兴奋了起来,手舞足蹈比划,然后又用石块在土地上划出一个三角形的形状:“金字塔是天地的尽头,肖邦在里面画画,梵高在里面弹琴,尼采在里面发疯,曹雪芹在里面跳舞,还有一个叫荷马的瞎子在里面呼呼大睡呢!”
肖邦、梵高、尼采还有荷马,柏莎认真地把这些名字在脑子里过滤了一边,但部落里确实没有任何人叫这个名字。
不要再继续问什么是什么了,那样到天黑也问不完。柏莎很聪明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顺着男人的话问下去:“那你挖‘金字塔’,是要和他们一起玩儿么?”
“一起玩儿?不、不、不,我要到达金字塔,然后把他们喊出来,我要救他们,金字塔要塌啦,他们不能在那里呆了。”男人神色焦急起来,继续加快挖土。
柏莎歪着脑袋:“谁告诉你金字塔要塌了?”
“苏格拉底。”
“他是巫师可以预言?”
“不、不,他不是巫师……他是……他是……哎呀我记不清了,可能是个诗人,可能是个跳舞的,可能他和梵高一起弹钢琴。”
“那你怎么知道金字塔在这里?”
“那天晚上,对,就是那天晚上,月亮像这朵花儿一样白,一个叫庄子的人告诉我的。”男人很高兴自己还能回忆起来。
“庄子?他总是巫师了吧?”
“不,不,他弹钢琴,知道肖邦的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么?就是庄子的作品!”
“可是你不是说这是肖邦的么?而且,你不是说肖邦画画吗?”柏莎很快地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男人皱眉想了一下:“我这么说过么?哎呀,我记不清了,或许是又或许不是,上帝不会介意的……你知道上帝么?”
这次不等柏莎提问,男人直接反问了一句。柏莎自然是摇头,男人突然变得愤怒起来,他脸涨得通红:“上帝就是个屠夫,他和宙斯是一伙儿的!你以后看到他们就要丢砖头,不要相信他们任何一句话!”
可是男人又突然平息了下来,脸上露出怀念的神色:“上帝什么都不做,这一点很讨厌,可又是他的优点,哎,你说,我要不要原谅他?可是如果原谅他了,那么谁来原谅我们自己?”
柏莎很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良久后她回答:“我来原谅你。”
男人的眼睛亮了亮,开心地瞪着柏莎,又好像没有看她:“太好了太棒了!这是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可说着说着,男人突然不笑了,。他的嘴角慢慢撇下来,将脸庞埋进满是泥巴和鲜血的手指里。过了好久好久,柏莎听见细细的啜泣声从男人的指缝里传了出来:“我好高兴,可是太晚了,太晚了……月亮还在,可太阳再也不会出现了。”
“太阳就在我们头顶上。”柏莎说道。
“不在了,不在了,黑夜永远不会离开了。”男人一边呜咽,一边喃喃自语。
兀地,男人又止住哭泣,抬头看着柏莎:“你是谁?你是来杀我的么?”
柏莎摇头:“我是柏莎。”
“哦……哦,柏莎,你好,你好。我很想告诉你我的名字,可是我忘记了,你可以叫我‘黑夜’。”
***
夜晚降临,树林里生起一堆温暖的火焰。
黑夜已经没有挖坑了,他全然忘记了金字塔,忘记了要救金字塔里的肖邦,荷马,尼采,曹雪芹和梵高。他目光呆滞地盯着火苗,又扭头看看正在吃野果的柏莎:“柏莎柏莎,你住在哪里?我要谢谢你给我温暖和食物,等我回家了,我要买最好吃的披萨送去你家,你喜欢洋娃娃吗,我也可以给你买个洋娃娃。”
柏莎咬破紫红色的野果,吞咽汁水,短时间的相处已经让她学会了如何与黑夜对话——只要选择能够回答和询问的东西就好,多余的问了也是白问。
“我不能回部落。”
“部落?那是在哪个街区?为什么不回去?”
“如果我被父亲和哥哥抓住,他们会砍下我的脑袋。”
“为什么?”
一时间角色调换,黑夜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停询问,而原本就是小孩子的柏莎却像个大人一样耐心解释:“我是部落里第十二个女孩儿,按规矩长到十二岁就要砍头,不然部落会触怒神明。”
“为什么?”黑夜重复询问。
柏莎摇头:“不知道,这规矩历来就有,现在父亲和哥哥可能正在到处抓我吧。”
黑夜又开始发呆了,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和柏莎对话:“十二个,十二个……为什么你是第十二个呢?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是叛徒,所以第十二个要砍头么?耶稣,是耶稣要追杀你!”
黑夜突然大叫了起来,一把将柏莎抱在怀里!
柏莎从来没有被年长的男性抱过,即使父亲也不曾如此。柏莎此刻大脑一片空白,她完全不知道该作何行动。而黑棋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柏莎的僵硬,紧紧将柏莎抱住,还用柏莎的野猪皮斗篷捂好她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要小心,你的敌人是耶稣,耶稣的耳目遍布世界,连这火焰也听他的!赫菲斯托斯听命于耶稣!”
“这……这就是追杀么?”柏莎嘴巴捂在斗篷里,闷闷地问道。
“对、对、追杀,追杀,追杀,追杀!”黑夜重复了好几次,每重复一次声音就更加大声,似乎在不停地确认什么。
有点明白了追杀的含义,柏莎抬头看着黑夜狼狈瘦削的脸,昏暗的火光中看不清楚:“那么,谁要追杀你?”
“波塞冬!波塞冬!波塞冬!”黑夜又叫喊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回答柏莎的疑问还是看见了波塞冬,更加紧张地搂紧柏莎:“不要害怕,我保护你!”
柏莎从来没有被人拥抱过,可她不适之后,又觉得有些舒服,如果是父亲抱着自己……柏莎很希望是那样,可她又突然明白,自己在父亲怀里的话,只可能是在没有脑袋的情况下。
“多可怜的孩子,还没学会怨恨,就要被恐惧追杀……不不、这是好事儿,是好事儿……”黑夜又开始疯言疯语,一边说一边哭。
柏莎从来没见过哪个男人这么能哭,以前父亲和哥哥打猎受了再大的伤也不会哭,最多送去给巫师医治的时候叫了几下。
父亲一直认为,巫师敷草药的时候如果哭了,就是不信任神明,那么就会被神明抛弃,死得很惨。
柏莎之前还有一个哥哥,可一次哥哥腿被划了个大口子,其实不算很深,但巫师医治的时候哥哥没忍住哭了。于是第二天浑身发烫,接着没多久就死了。
——如果哭泣会被神明抛弃的话,黑夜还能活多久?
柏莎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在一惊一乍的黑夜怀里睡去。然而,这样沉稳的睡眠并没有持续太久。
“柏莎,柏莎,醒醒,快醒醒!”
天微亮,柏莎朦胧中感觉有人在轻轻拍自己的脸。
“快醒醒,柏莎,不然来不及了!”
“快醒醒,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黑夜终于还是把柏莎弄醒了,柏莎迷迷糊糊地揉眼:“什么来不及了?”
“我要带你去我家!”
“去你家干什么?”柏莎没想明白。
黑夜很难得地笑了:“在那里没有人追杀我们,我会给你买新衣服,带你认识新朋友。然后你慢慢长大,我慢慢老去,等你恋爱了,有喜欢的男孩儿,到时候我就推着轮椅去参加你们的婚礼。老了之后我就找个地方睡一觉,不要难过,我只是睡一觉,我不会死的,不会死。”
柏莎想了想,反正也没有取出,去哪儿不一样?她点点头:“等天亮我和你走。”
“天亮就来不及啦,一定要在晚上。晚上的时候,回家的门才会打开!”黑夜很认真地解释道。
***
夜晚,黑夜与柏莎举着火把穿行在树林里,柏莎想过,要是有野兽冲过来,她就第一个先跑,不管黑夜了。可那一晚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是真的有什么力量在保护他们的安全,一直野兽也瞧不见。明明耳边还有虫鸣风声,可整个世界安静极了,安静得让柏莎想哭。
黑夜的记忆反反复复,可这个晚上却异常坚定,他很清楚“家”在哪里,并且一刻也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黑夜与柏莎开始登山,一边登,黑夜一边念叨着:“以前夏威夷不在这儿,可是莎士比亚把夏威夷推过来了,波塞冬把莫纳克亚巨人的脑袋按下来,要他跪着亲吻脚尖。”
柏莎不说话,这一片没有人敢来,部落里一直传说这里有怪兽,没谁愿意拿生命开玩笑。柏莎警戒四周,脑子里想象着一会儿会不会真扑出一个八个脑袋的野兽。
但是野兽没有出来,黑夜一路絮叨带着柏莎走走停停,突然,他停下了脚步,直视前方。柏莎意识到是到“家”了,她高兴得想看看新家长什么样,但夜还深,只能看到一团团黑影。天幕上的星光并不能起到什么照明作用,头顶上茂密的枝叶让一切都晦暗不清。
黑夜吞了吞口水,手牵着柏莎,渗出汗水:“到了,到了,就快到了。拿破仑和希特勒来过这里,好多人都来过,我还看到了伏尔泰的足迹,可是最后只剩我一个了,只有我一个了……快来,快来,柏莎,快来看看,我一定要让你看看!”
往前走去,柏莎发现那一团团黑影是巨大的树木藤蔓,而在这些茂密的植物从中,有一个怪异的东西,非常,非常奇怪。
“这是什么?”
“不要怕,跟我进来,这是回家的路。”
黑夜的回答根本就不算是回答,他拉着柏莎进入了这个“奇怪的东西”的内部。柏莎发现奇怪东西的内部地面很干净,但是布满灰尘,偶尔一些缝隙中长着杂草。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晚回响,像是两个偷偷摸摸偷吃食物的小孩。
“柏莎,这里是伊甸,我回来了,伊甸冷清了好久,它会一直寂寞下去,但是你来了,虽然不能改变,可是我很高兴,伊甸也高兴。”黑夜胡言乱语像是唱歌,柏莎一边听着,一边恼火为什么现在是深夜,什么都看不清,她真想弄清楚这里究竟是哪里。
最后,黑夜将柏莎领到了一个地方,面前有个更加奇怪的东西,黑乎乎瞧不真切。黑夜让柏莎呆在原地,自己上前鼓捣些东西。
安静的空气里,柏莎就听见乒乒乓乓和来回走动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黑夜温柔地说话了:“柏莎,快来看看,最漂亮的东西,父亲送给你的礼物。”
柏莎听话走上前去,即使她根本不知道礼物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她按照黑夜的指示,将眼睛凑近一个奇怪的东西,然后,她看见了美丽。
那是,无法言语的美丽。
漆黑的地方,可是黑得温柔,看不到边际,好大好大……大到柏莎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究竟有多大。许多许多的光芒散落在黑色里,调皮而柔和,瑰丽无比,那是一种秩序的美,一种最原始,最本质的美。那一刻,柏莎几乎忘记了呼吸。在她视野正中是一个圆圆的东西,红褐色,安静而精致。
“这是火星。”黑夜轻声说道,“来,看看银河,星云。”
许多许多,好大好大。柏莎只会这样的词语,而她非要多重复很多次才能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这些是什么?柏莎不知道,她只是觉得很漂亮,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为什么会觉得漂亮?没有理由,就像人生而畏惧强大的野兽,柏莎此刻接受这样的美丽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似乎从她生下来开始,血液里就知道这么个地方。美丽得让人不知所措,忘了呼吸,而后渐渐微笑。
有那么一瞬,柏莎觉得自己回家了。
“这是什么?”
“宇宙,最美的地方。我们的‘金字塔’。”黑夜笑了,摸了摸柏莎的头,“柏莎,不要忘记这些,不然柏拉图和歌德会寂寞的。”
“你说了那么多人名,这些人到底是谁?”柏莎头一次这么想知道,这么冲动地想知道。她害怕下一秒黑夜又把一切都忘了。
黑夜眨了眨眼,又笑了,这一次笑容里却带着狡黠:“他们是星辰,就是你眼里发光的那些东西。”
柏莎还想再说些什么,可远处突然传来了骚动和火光!
“柏莎,柏莎,快点滚出来!”
“柏莎,快点出来!!神明会原谅你的!”
“是父亲和哥哥!糟糕,我们不该点火把的!”柏莎慌张起来。
很奇特,在此之前,她觉得就算被抓了也没什么,死了就死了吧。可是现在,她见到了“金字塔”,突然不想死了,非常非常不想。
“柏莎,走那边。”黑夜推了柏莎一把。
柏莎:“那你呢?”
“我不会死在他们手里,他们的武器不堪一击。”
“父亲……父亲!”柏莎扑过去抱住黑夜,“你不和我一起‘回家’吗?”
“……原来我和你们一样,我真是又开心又难过。”黑夜又叫了起来,倏尔镇定,“你找到了我,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你不要伤心。记住今晚最美丽的金字塔。”
***
翌日,柏莎的父亲和哥哥拖着黑夜的尸体回到部落。有人认出了黑夜的脸,这个人是临近部落的居民,可早就失踪了好久好久。
没人知道他这身怪异的衣服是哪里来的,没人知道那晚男人的疯言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只有躲在墙后那个眼睛里留着星辰的女孩儿知道。

阿轩生在白帝城,长在白帝城,她也为自己打算过,等死后,就火化了埋在白帝城海边。早些年,父母都还在世时,就一直为她留意夫君人选,可挑了一个又一个,总是不满意。
事实上,阿轩也没什么意中人,她在白帝城不算最漂亮的,不算最知书达理的。可如果好好打扮一番,也算有点漂亮。
原本,一门亲事是定下来了,男方是城里一个船商的大儿子,阿轩也觉得挺好,对方也是个诚恳的人,这便足够了。
阿轩曾想过,如果当年那船没有在海上遇难,也许,今天自己已经有儿女了,也许,她也已经体味到了家庭带给她的,一个女人最喜爱的幸福。
可那天的船始终没有开回来,她穿着大红色的嫁衣,站在码头等了一天又一天,却等来了爹娘与未来夫婿一家葬身大海的噩耗。
原本已经说定,等他们从江都置办了货物回来,就成亲,好好热闹一番,但如今却只剩她一个人,如何热闹得起来?
爹娘过世了,除了伤心,日子还是要过。阿轩如今只剩下弟弟阿昂一个亲人,长姐如母,弟弟还小,她自是要为阿昂扛起这重担。
阿轩勤快,在白帝城开了家火锅摊子,原本火锅味道就不错,加之阿轩家的酒也很好喝,生意总是做起来了。
一天夜里,阿轩收拾了摊子,夜里静得很。她借着烛光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倒没觉得伤心。毕竟家里不愁吃穿,弟弟阿昂在书院读书虽成绩不是最好的,可也有模有样,一双没用的细皮嫩肉的手换来如今的生活,其实挺划算的。
可那天夜里的阿轩却怔怔地望着已经粗糙了的双手,总觉得自己丢了什么东西。
也就是那天夜里,一个披头散发,下巴长着胡子茬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火锅摊子,这一进来,就再没从阿轩的心里出去过。
“美人儿,可有酒喝?大半夜酒瘾犯了,寻不到还在做生意地酒家,老远看到你这儿亮着烛光,想是还没收摊吧?”
这是尹千觞见到阿轩说的第一句话,张口就讨酒喝。也是尹千觞每次见到阿轩时必定要提到的话题。
尹千觞是个四处云游的人,喜爱逍遥自在,并不会在白帝城久留,只是时不时回来溜达几天。而每次回来,必定要去阿轩的火锅摊子,一来二去,与阿轩相熟,尹千觞脸皮也越来越厚,赊的酒钱也越来越多,每每讨到了酒喝,就涎皮涎脸夸阿轩人好心善长得漂亮。
不务正业,每日嬉皮笑脸,兴致来了就躺在地上喝酒看那云卷云舒,招呼都不打一声欠下一屁股债就走,这样一个男人,却讨不少姑娘的喜欢,阿轩也不例外,她最开始是厌烦,却不知怎么得,心里渐渐盼着那个男人来白帝城赊久喝。
这个愿望不强烈,却总是有那么一个念想在那里,时不时念头冒出来了,望望白帝城的蓝天,想想那个人在干什么呢?
阿轩发现她想不出来,她没走过远路,想象不出尹千觞会遇到些什么人,见到什么奇景,如此,便也不想了。
有一日,很突然的,阿轩正在沽酒,她突然明白自己丢的是什么了。
她突然放下摊子,跑到码头望着大海,她突然发现当年那个穿着鲜红嫁衣的姑娘就一直站在码头上等着大船,等着自己的夫婿爹娘回来。
那个穿着嫁衣的姑娘一直都在码头上,再也没有回来。
“哟~阿轩,怎么这么巧,莫非是知道我要来?”
就在那一日,阿轩只是站在码头上,心里难受有点想哭的时候,尹千觞乘着大船回到了白帝城。
看着尹千觞一身邋遢,衣服起码有大半月没洗,腰间挂着酒壶,阿轩有一瞬间的恍惚,觉得自己的一个心结被这个嬉皮笑脸的男人误打误撞解开了。
她有点想哭,可又不想了,觉得那个待嫁的姑娘似乎回来了,阿轩对这尹千觞笑了:“怕是你闻着酒香顺路在白帝城下船吧。”
“嘿嘿,也可以这么说,我走了那么多地方,还是阿轩家的酒好喝,嘿嘿……”
自那以后,阿轩便爱穿着红色的衣裳,她总觉得,守着一个火锅摊子,看着弟弟长大成人,自己也慢慢老去,其实,一个女人所要肩负的责任,所要享受的家庭,她都有了,只是另一种方式而已。
既然如此,只需要要趁着年轻穿几件红色的喜庆衣服,忙里忙外的时候,也觉得精神些,觉得自己还是当年那个明日就会出嫁的姑娘。
“阿轩你穿这红色的衣服真好看,嘿嘿,美人美酒美景,妙哉,妙哉…..”尹千觞永远是那么油嘴滑舌。
阿轩轻笑:“这下一句,就是要赊了这顿酒钱吧?”
尹千觞笑了,完全没有那种不好意思的神情:“还是阿轩懂我,还是阿轩懂我,哈哈哈……”
阿轩懂尹千觞么?
该是不懂的吧,他的过去,现在,阿轩一概不知。
只是知道他爱喝酒,重情义,爱赌钱。
可有时阿轩也在想,尹千觞有酒,有钱,就够了,这就是尹千觞。
一年又一年,有一天,弟弟阿昂突然在饭桌上很认真地对阿轩开口:“姐,你为了我操劳了这么久,可以歇息了。”
“…….瞎说什么,你不还要娶媳妇儿呢,没聘礼哪家姑娘愿意嫁你?”阿轩往弟弟碗里夹了些菜,“而且,你姐我也忙习惯了,不累,有什么好歇息的。”
阿昂看着阿轩的笑容,替自己姐姐理了理鬓角:“自从爹娘过世以后,你就再没提过嫁人的事,就是你不愿歇息,也该找个人依靠吧?我时不时要走动外地,要是有人能帮你就好了。”
阿轩有点愣神,她突然意识到阿昂真的已经长大了,嗔道:“这些事,你少管。”
“依我看,我觉得那个时常来赊酒的尹大哥虽然看着不靠谱,但实际上还是个很不错的人,姐,你……就没想过?”阿昂突然打趣起自己的姐姐来。
阿轩有些尴尬,脸色绯红:“住口,胡说什么,这么多年不打你,欠管教了是吧!!!”
“哎哟,姐姐饶命,姐姐饶命!”
“你给我站住!”
那日的话,阿轩后来好好想过了,她想,自己是喜欢尹千觞的,如今弟弟也大了,如果……如果真的可以,她也愿意,同尹千觞游历山川。
下次,等他下次来白帝城,就……就……就说说?
做了这个决定的阿轩有些激动,有些害羞。
因为不知道尹千觞什么时候会来白帝城,她总是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记得尹千觞说过她穿红衣裳好看,她每日都穿着大红的衣裳,就像当年的嫁衣一般。
生意做累了,阿轩就让伙计照顾着摊子,自己没事就去城门那边走走,去码头那边看看,想着尹千觞回来的那一天。
他一回来,就将自己的心意说与他。
阿轩那时这样打算的,心里带着满满的期待,她也不敢想太多,怕对方不答应。其实不答应也没啥,只要能看到尹千觞再次嬉皮笑脸跑来赊酒喝,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尹千觞在外四处游历,见过的美女多了去了,对他倾心的也不少,阿轩没觉得自己比得过别人什么,只是,想将自己的心意说与他,也好了了自己一个念想,没准,没准……
可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尹千觞再也没有回过白帝城,一年,两年,三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去哪儿了?
阿轩不敢问,也寻不到人问。只有那一次,她强烈地希望尹千觞回到白帝城,可只有那一次,偏偏那个流氓一样的醉道士再也没出现过。渐渐的,当初那个冲动的念头也淡了。
一年年老去,阿轩也再没起过嫁人的念头,成了老姑娘,然后成了老太太。
有时候,望着白帝城的大海,抬头又看看天空,阿轩在想。
那个人去哪儿了?
那个人在干嘛?
如果尹千觞还活着,可还老爱赊酒喝,可还总是醉醺醺走一路?
如果尹千觞在过去某个她不知道的日子里死了,死前可还喝着酒?可还会念叨一句:还是阿轩家的酒好喝?
阿轩心里明白,那个穿着红嫁衣的姑娘,又走丢了,再也回不来了,也许,是跟着某个酒鬼一起去游历山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