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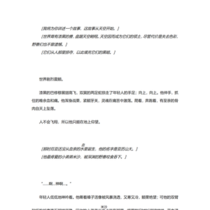






后来天亮了,这是亚伦的故事的结尾。他略去了很多内容,比如他在塌方的矿井里因为一瓶血族的血液长出獠牙、他渴求鲜血、那瓶血的主人,一个教会猎人来到矿井、他被带去圣伯拉教堂、他也成为了教会猎人,他作为矿工的普通庸碌生活了就那样被一次矿难切断了,血还是血的颜色,其他却都变成灰败的尘土色。纳塔城里这种叫做“湖骸”的怪物让他的头脑变得不太正常,但他讲的故事总算没有出现纰漏,至少听故事的人没有指出什么问题,也没有突然改变对他的态度。“天亮了,”他说,“最后天亮了,我获救了,于是我离开那里,当上了猎人,直到现在。”
“很好,很好,现在已经好多了。”听故事的老猎人在拆掉了刀柄的匕首尾端固定好了绳索,重新做成了一把绳镖,接着说道,“我们那时候的猎人有很多也是农民,武器是用梿枷和柴刀改成的,收完了秋粮,就那样去狩猎了。就像雷涅那时候那样。现在好多了,有人能教你们些保命的法子。”
他又点燃了一卷烟卷,也扔给亚伦一卷,说:“抽过吗?镇痛效果一般,但多少可以应付一阵。走吧,这片地方不能久留。”亚伦不需要这个,他的伤口实际已经差不多愈合了,但他还要假装自己是个真的人类猎人,于是也学着抽了一口。没有什么味道,只是嘴里微微发涩。
这是亚伦到纳塔城后的第五个小时,他的背包里还装着一封信要送给住在纳塔城东区玛格街二十八号的诺利亚先生,信是由亚伦代写的,他作为教会猎人所驻守的小教堂位于一个相当偏远的小镇,邮差一年也不去那里几次,所以常常由亚伦顺路充当信使。通常不识字的镇民会托亚伦给城里的亲友带口信,省掉他代写信这个冗余的步骤,但一个人要当父亲的消息还是由他自己拆开信看到比较好。亚伦·桑切斯的大部分生命(如果长出獠牙之后仍然能算活着的话)都在很偏远的地方度过,从前他在北边的矿区出生,长大后就在那里当矿工;后来他当了教会猎人,又被扔去了西南边很偏远的海森镇小教堂当常驻教会猎人;他从尸体上捡到一枚工会猎人徽章,决定开始扮演一个工会猎人之后,很少会来纳塔城和猎人的工会总部,即使他可以在日光下活动,和真正的猎人们长时间相处总会在什么地方暴露的,他不想冒那种风险。他当矿工的时候就是很谨慎的,所以才会被安排当负责配火药的小工,还有了学习读写的特权,以及最后能在那个坍塌的矿道里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很少来纳塔城,到达这里的时候,本来要问路人玛格街怎么去,却发现这里所有房子都门窗紧闭,越往东去空置的房屋就越多,街道上飘着浓烈的腐臭味。他闻到血的味道,很多人的血,他满心疑惑,但是仍然向东城区赶去——如果诺利亚先生已经遭遇不幸,他至少能带个消息回去,这时候已经过了午时,但天色还算明亮,何况这里是猎人工会总部所在的城市,他自觉不会遇到无法逃脱的险情——然后他就真的遇到了那样的险情。
老猎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老猎人常常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有时是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增加气氛的背景。猎人能活到被称作“老”,就会变成这样相对特殊的一类人。亚伦·桑切斯生命发生转折的那个故事里也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老猎人,他在矿坑血案发生之后来到达纳矿上,同时负责了法官和刽子手两个角色:他轻松抓住了逃进林区的亚伦,并准备根据他的调查和收集的口供来判决这个新生的吸血鬼的生或死。亚伦·桑切斯最后成功从老猎人的手中逃脱了,但并非依靠供词,而是依靠一位感受到了自己的血液被使用了、并造出了一个新生后代的教会猎人G夫人*。G夫人在几十年前丢失了这瓶血液,盗窃者是她作为人类时生下的亲生儿子,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故事,G夫人一直在等待这瓶血液被她的儿子使用,让她好去找到这个不成器、盲目追求永生的儿子,好好教育他——用血族的方式,但很显然G夫人在成为血族后对时间的感知有了点偏差,当她跟着自己的感知来到亚伦和老猎人面前时,才意识到那漫长的等待长达数十年。略去其中所有复杂晦暗的细节,不考虑她对这个“新生子嗣”后来的“教育”和作为,G夫人还是出面为这个陌生的新子嗣做了担保,凭借教会猎人的信誉将亚伦·桑切斯从老猎人犹豫不决的审判中挽救了出来。
相较之下,此时此刻在亚伦面前的老猎人在故事中的角色通常要和善得多,或者更常作为那个增加气氛的背景出现,有一个非常温柔的代号叫做“夜莺”,但他差不多已经是那种场景的标识了:血腥和尸体的腐臭味,幽蓝的提灯灯光和葬礼,亲人的哭泣和朋友的哀悼。如果人活得太久,久到年轻时候的朋友大多都死掉了,就会逐渐失去角色,变成更年轻人故事里的背景,一个人总有些部分是要靠那些朋友的记忆存在的。老猎人艾德蒙·斯宾塞就是这样一个失去了大部分他人记忆的家伙,很多人见过他,也许一起喝过酒,却和他并不熟悉,也相当鄙夷这种从死人身上敛财的生存方式,看到他和他的提灯、他的熏香炉时,想到的只有死亡和葬礼而没有艾德蒙·斯宾塞这个名字,也很难记起那个不再去狩猎、只围着死尸打转的老鬣狗曾经也是真正的猎手。
而在这一天萧条冷清的纳塔城东城区,出现在亚伦故事中的老猎人倒不是个背景了。
起初亚伦几乎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他的耳膜像被扎穿了一样疼,左眼也一起疼痛起来。他想起那尖锐啸叫本来好像是一阵美妙的歌声,他看到一堆会动的黑色东西,近了才看到那黑色黏液下面是许多不应该出现在一起的人或动物肢体挤成一团蠕动着。他想他知道这东西一定不正常,可他想举起锤子时却古怪地犹豫起来,错失了将它击开的机会。他想,糟糕了,这东西影响了他的头脑。很难形容,像喝醉了,像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漆黑矿道里,感受到的温暖的死亡正拥抱他。他在昏沉中感到疼痛,疼痛让他获得片刻清醒,踹开了正在啃咬他手臂的怪物,往来的方向逃回去。老猎人艾德蒙是在这时候出从高处跳下来,将那怪物斩断了的。
“小子,”他戴着三角狩猎帽,脸藏在面罩后边,只露出一双眼睛,他走近了,从耳朵里摘出耳塞,问道,“你怎么在这种时候进城?”
“我从西边回来工会,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亚伦迟疑着回答他。
“西边没有这种东西吗?那就说得通了。”老猎人点点头,从背后抽出一把用来剁肉的屠刀,走过去把仍在蠕动挣扎的怪物切成了小块碎肉。这也许是它最原始的样子,一堆不应该聚合在一起的死尸的肢体。“‘湖骸’,我听别人说叫这个,从东边铃兰内湖那边沿水道来的。”他随手指了指那些紧闭门窗的房子,“东区和南区闹得最凶,这些房子大多数都空了。”
“那您还留在这里?”
老猎人转头看了看他,整张脸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一双老练猎手的眼睛,刚刚猎杀怪物,不,更可能是已经连续几天猎杀这样怪物的血光还没有从里面褪去,看上去狠辣而危险,反倒比亚伦看上去更像个渴血的鬼怪了。明明看不见脸,但亚伦却感觉他笑了起来。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我想起你来了,你是雷涅的那个……朋友?搭档?我在帕斯玛那里看到过你们一块儿行动。”
“噢,雷涅,”亚伦说,“我觉得可以算是吧。”
说话时他们正各自在那堆断肢里捡回自己的武器,亚伦的背包落到一边了,好在那黏液没有渗进背包弄脏那封信。而那老猎人在旁边发出了不太愉快的咂嘴声,亚伦朝他看过去,才发现刚刚救了他的是一把连着锁链的短柄镰刀,而镰刀刚刚被怪物的骨头崩断了一半。
“运气不太好。”老猎人说,“这家伙该送去修理了,正好遇上了这事儿。”他打量了亚伦,问他讨走了几把短匕,拆掉了刀柄准备做成绳镖。他拽下面罩,终于露出了横着两道显眼伤疤的脸庞。他往嘴里塞了一卷烟卷,坐到路边便开始做他的临时武器。他说:“很少有猎人用锤子,没有锋刃,很不好上手。”
亚伦也坐在一边包扎刚刚的伤口,它看上去不大,但比他想象中深许多,没那么快能愈合。“我用习惯了,”他不那么介意讲出自己的来历,只不过常常隐去些内容,“我以前是矿工。”
“最后天亮了”,亚伦的故事通常都是用这句话结尾的。天亮过很多次,但是他在矿井里并不知道。矿道是鳄鱼的喉咙,井口的天空小而遥远,像月亮高挂在黑夜,像一盏遥远的灯。但这一天他们重新出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城市里飘荡着不祥的怪声和隐约的惨叫或哭泣,云层太厚了,看不见月亮,两旁的房子里即使有人刚刚躲在窗口看他们,也不点上灯。恐惧和腐臭味一起在城市里蔓延。亚伦仍然想着他要送的信,问艾德蒙能不能顺便去一趟玛格街二十八号,但被告知了纳塔城根本没有玛格街;他该去齐马蒂那边找找这位“玛格”街的“诺利亚”先生,在那儿的方言里这是木兰花的意思。老猎人耸了耸肩表示遗憾,手上甩着新做好的绳镖测试它的稳定性,亚伦想他的武器分明也很不常见,不论是连着锁链的短柄镰刀还是绳镖,一次性造成的伤害都很有限,而且看上去比锤子难操控多了。他又想起老猎人此前是从高处跳下来的,动作敏捷利落,他应该是个更擅长在丛林或城市的高处来回穿梭,在对手的背后给出致命一击的猎人,那两种古怪武器确实更适合这样的战斗方式。艾德蒙在他前面带路,浑然不知自己在这“后辈”眼中已经是个虽可依靠却危险的人物——在更早以前,艾德蒙还很年轻,腿脚也没有被打坏落下跛足的时候,这才是那些死掉的朋友们记得的他。
对老猎人艾德蒙来说,怎样被人记得倒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腿脚坏了,他没法再像年轻时那样战斗;因为朋友们大多都死去或离开猎人行当,所以没多少人记得他原本的样子;但为什么非得成为“夜莺猎人”,他却是说不出来的。如果一定要他说出点什么来,他会说这全都开始于十三年前,帕斯玛街区的一个下雪的早晨,天还没有亮起来,冬天很冷,血液却因为不久前的战斗在他血管里狂热奔涌。他穿行在一条很少有人经过的小巷,血在他的斗篷上结成了脏污的冰凌,那是好几个人的血,那些人的猎人徽章则在他的口袋里叮铃作响。他看到一条很长的血痕,在薄薄的积雪上拖出了一条极长的血带,恍然间以为又回到了刚刚的夜晚的郊外,被血肉浸透成红色的雪地里。那是一个小女孩在落着雪的小巷里挣扎着拖出的蜿蜒血迹。前一个夜里,艾德蒙·斯宾塞失去了好几个猎人同伴,有一些是他的朋友,有几个他也第一次见到。郊外那雪地也变成红色的了,但是现在想必已经看不出来,被夜里的大雪重新覆盖了,他们的身体也被盖在新雪下面,到来年春天才能去收敛。他看到清晨的小雪慢慢落在小女孩的血迹上,血迹和女孩身上像撒了一层轻飘飘的糖霜。他把这个只剩一点微弱呼吸的女孩包裹在斗篷里,像用死者脏污的血肉包裹住一只落巢的小鸟,用尚有余温的内脏去温暖虚弱的幼崽,他说没有事了,夜晚已经结束了。夜晚还会再来,但有人会在夜里点起灯了。
隆冬傍晚的纳塔城里,天色渐渐昏暗到看不清街道了,东城区仍然没有多少窗户亮起来,仿佛一片寂静的死城。亚伦随着老猎人前往他的在东城区布置的安全屋,转过街道不用指路,他就认出了这临时据点:那小楼外显眼地挂着一盏燃着明黄灯火的提灯,整条街道上,乃至此外的好几条街道上,这是唯一一盏亮着的灯,告诉人们这里仍然有人在。暖黄的灯光照着地面,在这无月的夜晚,仿佛这街道上低低悬挂的月亮。
他远远看着那盏提灯,终于将老猎人和提灯联系到了一起,说:“我想起来了,在帕斯玛那里,你那盏灯是蓝色的。那是在葬礼上。”
“我们有很多时间让它变成蓝色。”老猎人踩灭了烟卷,说,“葬礼可以等以后慢慢做,现在该做点别的。”
————END————
——————
G夫人:指盖亚女士 CID8072
【关联作品】明灯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6078/
作者:轻拍拍
评论:随意(请粗暴些)
烈日炙烤着一条毫无生气的小路,小路上走着一名年轻的僧人。僧人脸上满是汗珠,一顶大草帽盖在粗短的发茬上,衣衫陈旧多处破损——他一定在外奔波了很久。
但说在外奔波并不准确。僧人不打算回寺院,也不清楚如今自己身在何地,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成佛。可成佛又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看法是,人的痛苦来源于欲望,欲求不满则生痛苦,他若斩尽自己的欲望,便能立地成佛。
住持评价过自己,“有慧根,浮躁心切,需见大风浪”。当时僧人有些不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他独自游行两年,恰逢大旱,各地收获不好,惨状频现。域外异族袭扰加剧,境内妖兽日渐猖獗,几支朝廷派出的机械除妖旅不但寸功未建,反倒听说其中一支溃败逃散。僧人刻意往穷山恶水走,想多见些世间苦难,好成全自己的不动佛性。虽还没见过大风浪,但小风小浪,像是偷盗抢劫、仗势欺人的事情见了不少,已经不再能把他触动。好在有一身寺里练的武艺,勉强得以保全自身。
小路的尽头出现一座村落。遥遥望去,村落就像一个土堆,与路边的土堆一致,除去了无生气的黄色,再没有半点其他颜色。没有炊烟,这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地方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煮饭。僧人猛然发觉如今已不必刻意寻找苦难,举手念了一句佛号。
机械人阿明站在佛像前,佛像立在一间破庙里。佛像缺乏修缮,彩漆脱落,阴森可怖。阿明并不是在念佛,也没有在许愿,机械人不应当有愿望。
但阿明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像一个真正的活人一样,获得拥有“欲望”的能力。
“你的欲望是什么?”阿明操着一口流利正宗的官话,询问面前的少年。
“……杀,杀了我……”细不可闻的声音从少年的唇缝间飘出来,一同流出来的还有混着血的涎水。他每次开口,都会有股臭味从嘴巴里飘出来。汗水和血污浸透他的面孔,寸许长的头发吸满了液体,塑成一个个沾满墨汁的笔尖般的尖顶。少年是被倒吊着的。
“为什么是杀你?按照预先植入和后天收集的人类反应逻辑模式,你的欲望应该是杀了我,为你和你的母亲复仇。”阿明没有听错的可能,几乎是在少年音落的同时回答。除非他的控制主板判断有等待的必要,他永远可以在人类眼中的一瞬间作出回应。
“……因为我……杀不了你……”少年始终闭着眼,但此刻他的面孔抽动了几下,眼角淌出两滴泪来。这两滴眼泪对少年而言足够珍贵,毕竟他已经被吊在这里半天,流了太多的泪和血。他体内的液体尚未完全流干,但他的母亲就没有这样好运了。
“求你了,我好疼,好难受,杀了我吧……”少年含混不清地说着,唇间涌出更多红色的泡沫。
不够强烈。他的欲望还不够强烈。阿明想。半天前他还能吼出猴子一般的咒骂,可现在他的声音那么小,一定是因为这不是他最深的欲望。阿明检索了六个时辰以内的日志,发现这个少年在肉体受到伤害时,发出的声音最大。于是他花费半分钟扫描了眼前的生物,决定依次剪掉少年的指头,从右手的尾指开始。
庙门口的阳光忽然被挡住一块,这立刻被阿明背后的传感器捕捉到了。他转过身,好让更多的传感器获取信息。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举起一只手,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僧人闻见血腥味,这味道在干燥的沙土味中很容易分辨。他跟随这股气味,悄悄来到破庙外,伸头就看见这样一副画面,命运在漆黑的底色上以暗红作画。这画面令他心惊不已。他的视力在两秒后适应了缺乏光照的环境,同时他确信机械人已经发现了他,干脆走进庙门,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阿明转身面对他,双眼红光稳定。AM059-9527,这串编号在机械人胸前未被衣物遮掩的部位显露。庙外骄阳似火,但庙里的气息足够冷,令僧人的汗毛竖过一轮。虽正处在极度惊愕与恐慌中,他仍认出这是朝廷某支机械除妖旅的编号,AM代表武装,059的第三位9代表高度智能型,以应对与妖兽作战时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名少年与妖兽有关吗?”僧人注视着阿明,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与心神一同抚平。据各方记载,妖兽控制乃至变幻人形的案例并不少见。
“我在尝试拥有欲望,少年与妖兽无关。”阿明双目的红光极罕见地闪烁了一下,代表他完成了某些复杂的运算。可那是什么呢?是在解释他的目的吗?
“那么我看到你在折磨一个无辜的人,”僧人厉声喝问,“你是哪支部队的,你们的人类统领在哪里?”他确实见过数不清的小奸小恶,但从未见过如此直白的残忍。邪恶的轻重并不能经由不同事件累加,自然也不代表他有承受当下遭遇的这种邪恶的条件。
“我只是为了倾听他的欲望。一路上我尝试过许多方法,这种伤害肉体的方法最有效,”阿明说,“何况现在我已经不再是除妖旅的一员了。”
僧人从未见过如此超脱机械人运行规律的机械人,那支部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敏锐地发现,对方似乎并未完全丧失理性和逻辑,目前还在进行的语言沟通证明了这一点。
“你为什么要倾听他的欲望?”僧人问,他打算从对方的回答中找出缘由。
“因为我想拥有属于我的欲望,”阿明反问,“你的欲望又是什么?”
僧人一愣。他的目光投向仍被倒吊着生死不知的少年,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正是救下这名少年。多年修行,欲望依旧能在自己察觉前孕育、生长、成形,如此,自己何时才能成佛?他站在原地叹了口气,念道:“阿弥陀佛。”
缺乏条件。阿明的逻辑运算器弹出警告,他没能理解声音传感器捕捉到的这枚震动信号,这令他感到像是某条液压线路堵塞,或是电子引线短路般的不快。“建议重复说明你的原意,”阿明的合成器发出声音。
僧人从对方缺乏感情的话中感受到一种威胁,于是他的心一瞬间收紧了。可没等他做出反应,一阵呜咽突然从倒吊着的少年喉咙传出。少年残破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两下,随后就像离了人的秋千,在无风的空气中逐渐止息。
少年死了。僧人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获得了某种安心。少年受了这么多苦,不知能否去往极乐?“阿弥陀佛,”僧人闭目又念了一声。
“建议重复说明你的原意,”阿明说。
“阿弥陀佛,是一位无量大佛 [1]。若能像他一样,抛弃欲望除尽烦恼,死后便能前往极乐。” 僧人嘴上回应,心里突兀地萌发出一个念头。
“你想要抛弃欲望吗?”阿明没有停顿,在僧人话音落的一瞬间便抛出新的问题。
“正是。求而不得为苦,无所求则无苦。” 僧人听闻过一些不入殿堂、却在民间流传甚广的轶事,讲的是佛陀震慑外魔、收服信徒。
“可你有欲望,我看到了你的欲望,”阿明不假思索地说。僧人哑口无言,隔了好一会儿,才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我替你想到了办法,但你也要替我想办法,”阿明说,“我也想有欲望,跟你们一样的欲望。”
“你已经有了。”僧人没指望机械人口中的办法。他感到自己胸腔一阵悸动,若是自己替佛祖除掉这样一个妖魔,世间能多出几人菩提涅槃?僧人打定了主意,可他预料不到这个主意的结果。
“与你们不一样,我的欲望,我的念想,我想获得欲望的欲望,都不过是一段随机组合的数据和代码,一种电信号的错觉。我想要你们炽热的、根植于肉体的、发丝般条缕分明的欲望。”阿明向僧人靠近了一步,僧人察觉到一个难逢的机会,那是一句足以驳倒对方的话。
一句话无法杀人,可足以令人分心。分心,就会有破绽。
“人类的欲望,或许也只是人脑中微电流带来的幻觉。我们并没有分别,”僧人盯着阿明的双眼。
阿明没有回话,眼中红光火星般闪烁不停。
机会!僧人冲向阿明怀里。他们先前距离不过三米,一转眼便已贴身。僧人举起双拳向阿明面门砸去,这拳毫无疑问可以将对方的铁脑袋打个对穿。
可在僧人的拳头撞进阿明脑袋的前半秒钟,阿明双眼的红光忽地停止闪动,重又变得平稳,“你说得不错,我同你们并无分别”。阿明猛然抬起一对机械臂,打偏了僧人的拳头,“作为感谢,我可以告诉你我先前替你想到的办法。”
阿明化掌为拳,攻向僧人前胸,僧人连忙向后撤步。
“替佛祖除魔不过是打着佛祖的旗号,行自己的欲望,”阿明说。先前主意的后果开始显现,僧人后撤的动作慢了一拍。这个瞬间,僧人潜藏的连他自己都尚未察觉念头被揭破了,于是这句话成了他所闻的最后一条箴言。
“只有消灭自己才能消灭欲望,”阿明的钢铁拳头切切实实地命中,僧人喷出一大口血,倒在地上。
自己终究败下阵来,这个念头在年轻僧人脑中一闪而过,不但在武艺,也在佛法。但机械人的回答确实令他在这瞬间有了新的觉悟,将他在找到的路上向前推了一步。或许,如果他的生命再长些,他会发现这条路是一条不通的死路,又或许,他会沿着这条路披荆斩棘,最终在某一天抵达更加璀璨的真理。但这些都成了或许。
阿明在破庙里站了很久,站到太阳落山,星空浮现。他在星空下看着满地狼藉,走出庙门,开始用铁铸的双手挖坑。挖一尺,还是两尺?他的动作渐渐变得不那么顺畅,开始偶尔出错,左手撞到右手,右手又打到左手。坑挖好后,他从庙里扛出两具尸体,此时他的身体不再保持出厂后便一直拥有的完美平衡,手脚也失去了协调,像个横冲直撞的孩子。他将尸体扔进坑里,用土掩埋。终于,这一切都做好后,机械人颤抖着站直身体。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真的人了。
[1]有不同释义,此处选无量佛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