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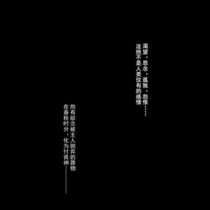

同场景下的艾洛尔和青年特雷。
====================
艾洛尔Ver.
谢尔盖拉着希尔的手,看着汽车旅馆的引路人给他们打开了301号房间的门。
那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很讨人喜欢,炫目的亮金色卷发在脑后简单地扎成一束;他的T恤衫和牛仔裤洗得有些发白,散发出一股洗衣粉特有的人造香味。“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他说,夸张地扬起手,展示这间狭小的房间,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上衣磨毛的边角:“欢迎来到——全多宁角最奢华的——温暖舒适的——滨海旅店301号房间!”
谢尔盖看着这间位于走廊尽头、又狭窄又破旧的小房间,毫不掩饰地嗤笑一声。
“您将享受到——超级酷炫的海滨美景!噢,白沙、美女,湛蓝的大海!我爱海景——”
谢尔盖一把将窗帘拉上,遮住了怒涛翻涌的黄绿色大海和堆积着海藻的褐色海岸。
“感受到如家般的温暖舒适!看看我们时尚又高档的装修吧——”
那泛黄的壁纸毫无疑问是二十年前的流行款式。
希尔把背包放在床上。床褥洗得很干净,可是那床太破旧了,一根不老实的弹簧硬邦邦地戳在那儿,把床单顶起一个鼓囊囊的包。
“我们提供24小时热水和热情周到的客房服务!”
谢尔盖恰好想要洗手,却发现热水龙头的旋钮早就锈死了;他回过头,看到客房电话的线是断掉的,电话旁的墙上有一个擦不净的污迹,看上去像“FUCK”。
“来吧,让我来帮您挂起大衣——”他从椅背上取下黑色的呢子大衣。谢尔盖夺回大衣,目光犀利地瞪着对方手中那个熟悉的黑色皮夹。
“噢!噢——我很抱歉,不是故意的——”那年轻人毫无诚意地说,把皮夹丢在桌上,摊开双手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我们的餐厅五点半开餐,欢迎来品尝全阿勒蒙德最、最、最美味的新鲜柠檬汁淋盐浸鲱鱼,由和蔼可亲的罗斯妈妈亲自主厨~”
但愿他说的不是楼下肮脏的小厨房里那个满脸脓包、疯言疯语的夫人吧。希尔想着整个楼梯下面飘散的那股臭咸鱼味儿,不由得嘟着嘴拉了拉谢尔盖的衣袖,用口型说:我们可不可以出去吃?
“都听你的。”谢尔盖说,揉了揉希尔的头发。他转头看到那侍者还待在房间里,一副翘首期盼的模样,于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可以走了。”
年轻人立刻露出一副天塌了似的惊恐表情。“噢,您!您不能这么对我!”他用一种受害者的腔调嚷嚷,句尾带着委屈的颤音:“我母亲常告诉我说辛勤的蜜蜂会赢得最香甜的蜜——我是如此辛勤地为您们服务,我的好先生们——”他伸出手,搓着指头比出一个“钱”的手势。
谢尔盖冷着脸打开皮夹,抽出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拍在桌上。“出去。现在。”
“好的,先生! ”年轻人鞠了个九十度的躬,欢天喜地地挟起那张钞票。“请尽情享受吧,先生们~”
他抛了个媚眼,把门关好,哼着歌儿跑下楼去了。
.
.
.
.
=====================
特雷斯特Ver.
谢尔盖拉着希尔的手,看着汽车旅馆的引路人给他们打开了301号房间的门。
那年轻人长着一张苍白的俊秀脸庞,微卷的黑头发用发油打理得一丝不乱;笔挺的西装显得和这破旧的小旅店格格不入——他很可能是被从哪个经营不善的星级宾馆打发到这里来的。
发现谢尔盖用毫不掩盖的审视目光盯着他瞧,那侍从微微颔首,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把他们让进房间。这间位于走廊尽头的小房间既狭窄又破旧,泛黄的壁纸是二十年前的流行样式。“滨海旅店,301号房间。有点老旧,不过在这个街区,您找不到性价比更合适的屋子了。”
他把手里希尔的背包放在床上,遮住一根不老实的弹簧在床单上顶起的鼓包;然后又从谢尔盖手里接过黑色的呢子大衣,拂掉上面的浮灰,恭恭敬敬地挂在衣帽架上。
“外面的景色好像和宣传画上的不太一样……”希尔说,跪在窗边的扶手椅上,失望地看着窗外怒涛翻涌的黄绿色大海和堆积着海藻的褐色海岸。
“尊敬的客人,”侍者露出一个亲切的微笑,“美丽的海景需要等待一个绝妙的好天气。”
“没有热水。”谢尔盖的声音从厕所里传来。他想洗手,却发现热水龙头的旋钮早就锈死了。
“事实上,我们这里提供24小时的免费热水。”年轻的侍者彬彬有礼地欠了欠身子:“一定是老糊涂了的里尔斯还没来修理。您看,孙女儿分娩,让他忙得什么都忘记了。——这是我们最后的空房——我这就打电话喊他来修……”
“不必了。”谢尔盖简短地说,用冷水洗了洗手。“你可以走了。”他回到房门前,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小面额的钞票。
青年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毕恭毕敬地接过那钞票,深深地鞠了一躬:“鄙店的餐厅五点半开餐,提供新鲜的柠檬汁淋盐渍鲱鱼,由怀特夫人精心烹制。——祝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先生们。”
他关好门,整了整领结,轻手轻脚地走下楼,动作优雅得像是正穿过哪座宫殿铺着华贵红毯的走廊。他径直拐进了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顺手把门锁好。
“打发掉了吗,特蕾西宝贝儿~?”一个油腻腻的声音在他身后说,语气里带着种露骨的饥渴。这房间比301号宽敞很多,摆着张半新的大床;一个赤裸的年轻男人等在那里,肥胖的胸部垂落在肚子上,看起来活像只白里透红的猪猡。有什么东西直直地挺立着,把盖住他下身的被子支起一个鼓囊囊的肿块。
“嗯哼。”叫做特雷的侍者回答道。“一个装模作样的恋童癖俄国佬,带着他的娈童。”他转过头,露出一个满是恶意的微笑:“十岁出头的小崽子,哭起来一定很动听。——幸好不是我洗床单。”他往床边走去,一边扯下纯白的手套、规整的领结,脱下笔挺的黑色上装,一件一件地丢落在褪了色的地毯上。
“宝贝儿,你刚刚放我的鸽子,准备怎么补偿~?”细皮嫩肉的男人喘息着说,看着特雷斯特在床边坐下,并且慢悠悠地点起一只烟。
“你想让我怎么补偿,里尔斯?”他从嘴里吐出一团淡蓝色的烟雾,轻佻地挑起唇角;扯开衬衫的头两颗扣子,露出紧实而匀称的胸肌。
猪猡似的男人发出一声难耐的呻吟。“特蕾西,宝贝儿,你这小恶魔!”他油腻腻地嚷道,像只嗅着了臭肉的苍蝇似的,眉开眼笑地扑过去,一口咬住那青年坚实的脖颈。
侍者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冰冷的杀意汇聚在他眼中,像是把磨利了的凶刃——它若是把真正的利器,塞进他高高抬起的手里,怕是当时就会要了对方的小命。杀气很快消散了。半空中的手缓缓落在男人肥厚的脊背上,轻轻地拍打着。
“你还要走开吧,——甜心?”男人放开青年的脖子,用那豆子大的眼睛瞅着他:“你们这里五点半还要开餐呢。”
特雷斯特噗呲一下笑出了声。“得了吧,里尔斯。”他说,把烟卷儿叼回嘴里:“你闻不到整个楼里飘散的那股臭咸鱼味儿吗?没人喜欢令人作呕的腌鲱鱼——更别提做菜的是满脸脓包的疯婆子罗斯了。”
“我可怜的宝贝儿……”猪猡样的男人把他拽进怀里,让身下的器官紧贴在他身上:“别担心,我很快就能让我爸在政府里给你找份工作的。”
特雷斯特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民政部的艾尔文·康拉德。”他轻柔地说,仿佛在慢慢咀嚼这个名字:“别忘记——我要做他的上司,猪宝贝。”


谢尔盖·菲奥多罗夫用手指拈着厚麻布的边沿,掀起织花窗帘的一角。
雨滴猛砸在窗玻璃上的声音突然变得震耳欲聋。夜色已深,那盏不太灵光的老路灯伫在街角,忽明忽暗的辉光几乎难以穿透厚厚的雨幕;大街上空落落的,连一个形色匆匆的影子都没有。
时间已经很晚了。谢尔盖对自己说——那个男孩不会来了。
这样很对,谁也不该在一个这样糟糕的夜晚离开家门。麦金斯——坏天气会让那孩子生病的。他理应留在家里,就着睡前故事喝下整杯热气腾腾的果茶。
谢尔盖放下窗帘踱到桌边,把刻意摆好的几罐橘子汽水推进角落——礼赞街42号楼的走廊上依然静悄悄的,只有男人自己的脚步声沉甸甸地跟在身后,合着雨水冰冷的噼啪声敲击着耳膜,迫得人几近发疯。
然而他刚把一盘冷透了的速食意面倒进垃圾桶,敲门声便突兀地响了起来。
盘子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把他自己吓了一跳。这位在职的冷血杀手飞快地走过去捉住门把,等到想起自己该再谨慎些的时候,厚重的铁门已经被拉开了。一股挟着潮湿霉味的寒意从门外闯了进来,走廊上昏暗的灯光勾勒出一个孩子瘦削的身形,他深黑色的影子哆嗦着,在满是污渍的斑驳墙面上缩成小小一团。
——真是他的麦吉。
眼前的男孩活像只差点儿溺死在汤锅里的鸡雏儿,冰冷的雨水顺着褐色卷发的发梢一个劲儿往下流;水滴滑过他满是雀斑的圆润脸颊,趟过有些短小的、浸透了雨水的深红色呢子外套,又从裤脚吵吵嚷嚷地跌下去,在小羊皮靴周围堆积成一汪混浊的水潭。
“快进来。”谢尔盖忙把麦金斯揽进门厅,脱下对方沉甸甸的湿外套。他的视线在男孩沾满泥渍的双膝和脏兮兮的小手之间逡巡,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你真不该来。雨这么大,路一定难走极了。”
他握住麦金斯冰冷的小手——可却被对方轻轻挣开了。
“我……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哥哥。”麦金斯的声音小得像只冻僵的蚊子,紧攥着衬衫的手指绷得骨节泛白——他的毛昵外套的确短了一截儿,以至于衬衫的下摆也被污水沾染得泥渍斑斑。
谢尔盖看了他一会儿,脸色重新缓和下来。
“你得先暖和过来,宝贝儿。”他柔声说,不由分说地打横抱起麦金斯,把他湿漉漉的小脑袋搂进怀里:“先擦干头发——我该给你洗个热水澡。或许一杯热的橘子汁白兰地……”他抱着麦金斯往屋子里走——也许是错觉,男孩好像抖得更厉害了。蜷在他怀里的小身体冷得像块融水的冰。
公寓楼制式的客厅千篇一律,只在角落里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装饰壁炉。初春雨夜的寒冷湿气从墙纸后面渗出来,不怀好意地充满了整间屋子。谢尔盖在沙发最软的一块垫子上放下水淋淋的男孩,脱下他泡得发胀 的靴子和短袜,扯过沙发罩巾,捂住冻得通红的小脚。
“哥哥,我……我其实……”麦金斯突然说。
谢尔盖抬起头,可是对方并没有说下去。他青紫色的嘴唇徒劳地翕张着,瞪着谢尔盖的眸子里掺了很多孤寂又冰冷的东西——可怜的孩子,他一定被这雨夜给折磨坏了。
“别怕,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了。在这里等我一下。”谢尔盖揉了揉男孩的头,然后站起身走进卧室。他拉开刻着过时花纹的大橡木衣橱,拨开一整排黑黢黢的大衣和衬衫,露出叠放在深处的一大摞灰白色褥单。一条暂新的、印着小鸭图案的嫩黄色绒毯躺在那灰白黑的荒漠中央,看上去既温软又乖巧,像一抹明亮的光。
他把那束光搭在左胳膊上,心满意足地合上了柜门。
这时候,他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卧室——紧接着,一双细细的手臂从身后抱紧了他。巴在他胸口的指头上紧紧箍着一只白漆的木头指环,正中横着一道熟悉的暗红色缺口。
这可真有趣,谢尔盖有些好笑地想。麦金斯是个瘦削的孩子,可衣着物事总是比他自己还要小上一圈儿,简直像是错穿了弟弟的衣服。
“不论你想说什么——我在听,麦吉。”谢尔盖忍着笑意说。
男孩没有说话,脸颊紧紧地挤男人的后背上,让人不禁担心起他圆乎乎的鼻子尖儿。
过了好一会儿——也许躲开男人的目光终于让他鼓足了勇气——麦金斯的声音虚弱地响了起来:“非常、非常、非常对不起,菲奥多罗夫先生……其实我——”
更猛烈的敲门声炸雷似地响了起来。
麦金斯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他像只不堪重压的弹簧似的,猛地从男人身边弹开了。
谢尔盖忙转过身,可麦金斯已经跑出了卧室。他追着对方蹬蹬蹬的脚步声后面,在门厅的旧衣帽橱后面找到了吓坏的男孩。
“麦吉?——”谢尔盖抖开毯子裹紧男孩的身体,捏了捏对方的肩膀——他的手像是捏在裹着棉布套的沙发扶手上,没有得到丁点儿回应。男孩湿润的眸子一直动也不动地瞪着铁门,背脊随着门外的巨响痉挛似地颤动着,仿佛那拳头正一下一下地捶打着他幼稚的脊梁。
谢尔盖皱起眉头,大步走到门边。他的拳头铛地一声砸在铁门上,声音里渗着冰冷的怒意:“滚!”
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那不请自来的家伙轻声笑了起来:“晚上好,银发的伊万。”
门镜里只能看到一个光滑而俊郎的下巴,在公寓走廊的灯光中显出一种冰冷的青白,皮质夹克衫的领子一直拉高到了喉结。
“蒙您关照,我来接我可爱的羊羔回家。”他笑着说。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谢尔盖提高音量:“滚开——不要考验我的耐心,狗!”
门外的人笑得愈发开心了。
“你在里面对不对,希尔?——”他用一种出奇柔和的语声哼着说:“开门,开开门,我亲爱的小羊羔。”他哼起一支轻快的调子,乐音混杂着雨声回荡在走廊里,听得人心烦意乱。
一只小手轻轻地拉住了谢尔盖的胳膊。他回过头,看到裹着小鸭毯子的麦金斯正一脸惊恐地往他脸上瞧——泪水从幼鹿般温顺的眸子里大颗大颗地涌出来,无声地划过他涨红的双颊。
“别哭,我的天使。你认识他?——他是你的搭档?”谢尔盖低声问。
男孩湿润的眸子惊恐地张大了。他把头摇得像个暴风雨里的风标——可是随后又咬住嘴唇,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是特、特雷……特雷斯特。”他抽泣着说。
“神慈科的特雷斯特!?”谢尔盖低声骂了一句,表情看起来像是门外堆了什么肮脏的东西。他弯下腰,平视着麦金斯闪烁不安的眸子,笃定地说:“我不会让他带走你的。”
他顿了顿,然后换上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你的名字叫希尔——其实你不是麦金斯?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对吗?”
男孩猛地瑟缩了。
“我、我不是……对不起——不想……”他着急地说,可那些字句被抽噎生生梗在了喉头,愈发含混不清起来;他徒劳地捂住嘴唇——泪水像串儿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看得人心里发颤。
谢尔盖的手指拂上了男孩肿胀的眼角。
“就算你不叫麦金斯,也没关系。”他柔声说。“我不在乎你叫什么,也不在乎你打哪儿来——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这儿抢走。你就是麦吉,我的天使。”他把嘴唇轻贴在男孩光洁的额头上,在仍湿漉漉的褐色卷发间落下一个吻,表情专注得像在举行某种神圣的仪式。然后那银发的杀手转身往门边走去,一边反手握住了腰间的枪。
枪栓的咔嗒声强硬地穿透了雨夜。一种锋芒般锐利的气息从他漆黑的背影里迸发出来——可是当他把手放在门栓上、回过头对着男孩眨眼睛的时候,看上去又不像是个老练的职业杀手了。
别怕,我的天使——有我在。他用口型说,紧接着一把拉开铁门,独自走进了门外的森冷寒夜。
闭合的大门只在男孩眼中留下了一道模糊的铁灰色暗影。“可我根本不是你的天使……——”他绝望地小声呜咽道,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的脚垫上,变了调的哭腔很快便被凄厉的雨声撕扯着淹没无踪。
====================
感谢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