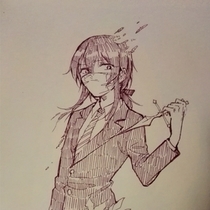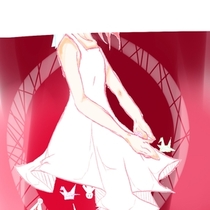-0-
雨点打在地上润湿了一小块痕迹,击打声逐渐掩盖了脚步的声音,一场莫名其妙的大雨将赶着回家的人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感染到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们一同逃避。
不知不觉就已经赶上了第二天的凌晨,太阳还深藏在地平线下不肯轻易挪位,静谧在蛐叫蝉鸣的交织中恍若隔世,更是为这夏日增添了几分烦躁的气息。
带着身上暂未散去的血腥,混杂着几缕消毒水的味道,一行人不动声色的移动着。
视野在建筑物的逐渐减少中不断扩大,最后进入眼帘的是一座庞大的工程——萨法丽丝娅湾跨海大桥。
透过早已褪去全黑的夜色,扫过桥面看到的,是点点微光和无尽的黯然。光芒在脚步的挪移中不断扩散着,当世界完全充斥着那抹红色时,太阳已经准备好从地平线上攀起。
在将夜空分割的最后一束月光下,红瞳与世界的颜色交织着。各占据一半桥面的双方阵营,均向对面缓慢侵蚀着。
-1-
细密的雨丝润开了薄薄一层衬衫,也同样打湿了路面和栏杆,落脚的地方变得发滑,一些武器由此变得脆弱。
“笛芙尔的各位,不如我放你们一条生路,交出你们的巧克力就好了,何必那么死板。倒不如说,笛芙尔本身就是德拉库拉的一部分。”有声音化作空气的一部分,弥漫在四周,令人不悦。
“说出这话之前不如我们先堵住你的嘴?贵族们。”相反的频率刺激着彼此的心情,谈判在这两三句言语中就猛然塌陷了,此时笛家的心里都有一个速战速决的想法,因为晨曦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是十分充裕了。
亚诺在私下中做出判断,家族中少有的纯血在此刻正发挥着作用,她必须首先干掉对非纯血最大的不利,精神方面的压制。
蝙蝠翼此刻在脊椎骨处快速生长,背部的血管由于快速新生的细胞被冲洗殆尽,嘎吱作响的骨骼保护内部的脏器不受压迫而爆裂,沸腾的血液流动在薄膜般的翅面而缓慢舒张到全身各处。
被众多纯血的气息压制到无法正常喘息,在恍惚间一闪而过的,是一位温润美丽的少女,长相甜美的她带有一头粉红色的奶油卷发,松松软软的搭在肩头,巨大的斗篷上装饰着挂在脖颈的蓝宝石,被华丽的粉色丝带固定着,宝石的光辉在夜晚的映衬下如同落下的尘星。
无视这精致的美丽,眼神扫过可以隐匿武器的地方,同时将她卷入自己的怀中,小刀的刃尖指在不断耸动的大动脉上,少女几乎没有反抗便服从了对方的行动,这令亚诺此时心里沾染了几丝不安的情绪。
在确认了当下人没有佩戴武器的时候,少女低劣的肉搏能力也不断刺激着亚诺的脑回路,直到她注意到那淡淡的清香从何处传来时,她便知道对方的身份了。
亚诺此刻来不及清嗓子,带着几丝沙哑的喘息声,快速说到:“rosa小姐,作为艺人战场不适合你。”
“在这里能遇到认识自己的吸血鬼,rosa感到十分荣幸。”对于自己的处境,rosa的声音没有一丝因为恐惧而扰乱的波动,反而愈发从容镇定,就当亚诺的小刀将要涌入到血液的潮水之中时,脑袋突然传开的爆炸感侵袭了四肢,神经无法传导到在手指的任何一处,小刀置地的声音尖锐清晰,使亚诺浮在脸上的笑容变得痛苦不已。
血统真的决定一个人的力量吗,亚诺不曾一次这么想过,当自己的抗体逐渐形成了时候,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瞳孔的黄色逐渐褪去的时候,就在此时两种精神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殆尽可是血统仍在身体里不息的运作着。
rosa的愁容一抹,扶着额头感叹着。
“就算我不能控制你,也就请你在你自己的梦境里沉睡吧,我会在背后看着你。”
暖黄色的记忆从眼神中渗出,顽固的攀岩在时间轴的终点。
-2-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回家的时刻。“
儿时的“我”,被这样告诫着。
从我出生开始,父母一直都在强调我一件事情,其实我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先天会对太阳与热量的恐惧愈发强烈。
在之后的生活,烧伤扩大的腐烂皮肤时时提醒着自己的不同,被光茫禁锢在屋里的时候,只有在无期限的轮回中等待着下一个黑夜的到来。
家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屋后还有一座小山,每至晚上我便沉浸在花香弥漫的山间,跟萤火虫倾述我的故事。
可是在这宁静生活的不久之后,当有人发现我时,我就被禁足了。
后来,读书、写字、绘画、音乐……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这些东西变成了我唯一的慰籍。记忆中的其他东西仿佛只剩下四面墙壁和几件桌椅罢了。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是人类,只是有些不同。
我一次一次用绷带包裹自己的身体,当我认为自己不会传染别人时,便会向父母提出出门的请求,可是被一次一次的回绝了,在那之后,父母带回来一台收音机,对我说。
“其实我们并不是人类,只是上帝遗弃的产物。”话语中残留的悲伤和内疚第一次摇瀚了我的世界观,心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
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收音机的操作,我每天的生活就变成了呆坐在床上,抱着收音机听里面嘈杂的声音互相解说着我从来没有接触的东西。
“人类和吸血鬼……”
“……”
因为它能说话的缘故,我不断尝试着与它交流,调换着不同的频道,希望有一个频道赋予了它生命,不过它只是像那只萤火虫一样,仅会嗡嗡作响和发出它自己的细语罢了,所以我就像对待那只死去的萤火虫一样,慢条斯理的学着父亲的样子,给它做了手术,可是它也像萤火虫那样,再也没对我说出任何话了,我把“它”拿给作为医生的父亲,但是父亲只是遗憾的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拆掉它呢?”
“因为我想赋予它生命,成为我的朋友。”
第二天,我趁着父母不在家出了门,用绷带遮住身体上会暴露的皮肤,为了辨认方向而不得不露出了眼睛的部分,将“它”埋在了院子里,但视网膜被灼烧的痛苦使我逐渐失明,只好利用手摸索着回到家,傍晚母亲回家时看到地面拖拉的血痕,焦急的顺着那条干枯的红色在卧室看见了靠卧在床脚的我,生理性的透明泪水和渗出的血珠混杂在一起,在锁骨绽放朵朵晕染的昙花。
自我愈合的那些天我安静的像具毫无生气的尸体,病态的苍白脸色衬托我眼窝深陷的酒红,血统不断抗争着死去的细胞,恍惚的精神却再也没有激起一点波澜。
当眼睛再一次充满光彩时,镜子中折射出的颜色却让我感到许些惊讶,那只伴随我出生的黄色眼睛中,覆盖了一层灰蒙蒙的血红。
“我要变成一只完美的吸血鬼了吗?”当我在餐桌上问着父母的时候,父亲只是宠溺的将手揉进我的发丝,洗发水的香气跳跃在我的鼻尖上。“哈qiu!”血浆撒了一地。
那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来自父母的第二份礼物——墨镜和拐杖。
收到这份礼物之后,在被允许出行的那一刻,是在成人礼的晚上。那时候父亲只是凝视着我已经褪去黄色的那只眼睛,递上行李箱微笑着,母亲也不知该言语什么,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丝温情。
“对不起。”在母亲回到房间的时候,父亲淡淡的吐出这句若有若无的话语,挥手关上了房门。
那一夜,家里的灯一直都在亮着。
-3-
在漫长的出行之后,我再也没回去过。
对于吸血鬼来说,年龄早已是在岁月的齿轮中被磨合的一部分了,只剩下感受记忆的流逝和人类的悲欢离合。
在茫茫人海中,只有隐藏着红瞳和嗜血的本能,才能不被人类当成异物一样处理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视觉从感知中遗忘,带上了隐藏身份的墨镜和拐杖。
秋天是一个让悲观人感到难过的季节,而我恰好撞上了这一点。静静的坐在城市的中心塔楼上,倚靠在塔尖。离成人礼已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适应了这座城市的频率之后也不由得开始享受生活,拿着所挣得的钱在某条街上开了一家小店,人客稀少却都是熟人,其中一位就是给这家店起了一个奇怪名字的警察,说起这位先生倒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十年前。
当我乘着火车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是在砖瓦的角落里度过的,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声音不由得令我吃了一惊。
“我叫salgado。”自己面前突然传来了低沉的问候语气,强烈的亲切不由得让人感受到潮水般的压迫感。
由于正下着一场秋雨,清晨的温度又偏低,原本冰凉的体温被迫又降了几度,
不能暴露身份而用绷带遮住的双眼看不见眼前人的模样,只好用声音判断所处的情况,听得到雨声而感受不到身上湿漉漉的感觉,想必是对方用雨伞为自己遮了一夜的雨。
“我是警察,你不用害怕,小姑娘是迷路了吗?”带有磁性的声音和温柔的语气让原本就很感激的心理带上了几分卸下防备的感觉。
“是的,刚来到这个城市,由于自己眼睛不方便而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住。”随便编了一个借口便想混过去的我,很快就被对方的责任心给拦住了。
“那我先帮你安排住宿吧。”听着对方咬定要管定自己的语气,心里突然产生一种人类都很好的错觉,到最后才知道自己蠢爆了。
当拿到住宿的钥匙和一系列各种信息之后,我才缓过神来感受这些东西,心底泛滥的温暖和众多不解让人感觉痒痒的,想说的话又欲言又止,可不久之后,那个人就直接推门跟着进去了。
“这里其实是我家,因为房子很大想合租。但是我看你躺在那种地方太可怜了,就不如把你接过来,就当养个女儿了。”sal开玩笑似的说出这些话之后,一百多年没感受到的体温逐渐升腾起几分热度。
我要收回我之前的感情了。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