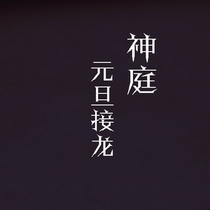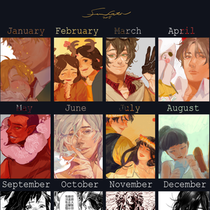矮桌不停地發出好像馬上就要壽終正寢的哀鳴,紙筆在指間不斷地摩擦,五十張桌椅和五十個學生。記不清楚姓氏究竟是什麼的老師站在講台前,嘴唇一張一合,不知道究竟是在講什麼,我也沒興趣去記。
明明是充滿朝氣的初春,我卻無論如何都提不起勁,嘛,就算不是初春也提不起來勁就是了。與我不同,坐在我的矮桌旁邊的傢伙正充滿朝氣地在課本上塗鴉,雖然很想起身來看看他在畫什麼,但是還是算了。春困夏乏就是指這種情緒吧,話說回來,這句話的後面接的是……秋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所以說,一年四季下來,根本就沒有能清醒地度過的時間。這可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啊,而是從人類這種生物還是猴子的時候就領悟的道理。
老師講的話就是最好的催眠了,冗長的文科講課根本不需要舒緩的配樂就能讓人產生“想睡!”的慾望,我將從家裡帶來的被子裹得更緊了點,用課本做了枕頭趴在矮桌上。嘶,真冷,雖然已經是早春了,但還是不及夏天,要在班裡的教室睡著太勉強了。
——如果是我們班的話。
二年F班,是笨蛋中的笨蛋的班級。說是不會讀書也好,不會考試也好,或者只是單純的笨蛋也好,總之就是這樣被稱作“差生”的學生待的班級。
而文月學園的等級制度,是利用學生的成績將少年少女們分成三六九等,接著再給不同的等級相應的設施,其結果就是——A班的同學待在設備最完善的舒適教室裡,而我們F班的學生則要坐在沒有供暖和冷氣,連椅子都沒有的教室。
真的很艱苦呢。
另外還有一點令我睡不著的是,從四處射過來的視線。
“喂……那傢伙啊,是不是就是傳聞中那個分班測試上睡著的超級大笨蛋啊。”
“嗯,我比他要高二十分呢。”
“嗚哇……這還真難得,你不是一直都沒考過及格嗎。”
“因為那傢伙交的是白卷啊!”
——所以比零分高二十分也不是什麼好得意的事情吧。我在內心中吐槽著。
是的,我,淺井良仁,不幸在分班測驗的時候睡著,並且交了白卷,分班測驗中的年級最低分是我……我有自信比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更低分。說我是笨蛋中的笨蛋也無可厚非,畢竟再蠢的傢伙也不會在分班測驗上睡著吧。
“懈怠啊……”喃喃感慨著,我將自己的頭埋在歷史書的紙頁間,逼迫自己進行再一次睡眠,直到旁邊的傢伙發出叮鈴桄榔的聲音讓我不得不起來看看他才做什麼。
這位同學穿著袖頭和上面縫了兔子媽媽團的圍裙,在矮桌後攪拌著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粘稠物質,還時不時伸出食指沾一下嘗嘗味道。再仔細一看,這傢伙旁邊竟然還有便攜式電磁爐和保溫箱。
……不會吧。
在教室裡做點心也太誇張了吧。
……雖然卷著鋪蓋卷,脖子上掛著飛機枕的我也沒什麼資格評價這件事就是了。
只見我的同桌雙手飛快地在鐵盆裡面攪拌著什麼東西,同時輕輕哼著我根本沒聽過的歌,大概是他自己原創的吧,過了會兒,大概是攪拌完成了,他把手上的鐵盆放下來,打開電磁爐。
不會有老師過來管的。因為是已經被放棄的F班嘛,F是failed的F。大概同桌也知道這件事,(當然很可能是單純地想做點東西吃)所以並沒有停下來他的手。不知道是在煮什麼東西,過了會兒,空氣中散發出點心發甜的香氣。
“……在煮什麼啊?”我輕聲問道,對方聽到這句話,似乎很高興有人在乎鍋裡的東西是什麼。
“是布丁喵!”那是說是沙啞的女聲或是較高的男生都可以的聲音,語尾刻意地加了一句小動物的語氣詞。搞啥啊,我抬起頭來,想看看對方的臉——和聲音差不多,說是可愛的男生或是英氣的女生都可以的長相,唯一能證明性別的東西是校服穿的是男生的西褲,即使這樣,按照普通的標準來看也絕對是個容貌上佳的少年。
我在被子中蠕動了一會兒,看著他準備的便攜電磁爐和保溫箱:“那個保溫箱裡面放的是什麼?”
“冰塊哦!待會兒要用來冷卻布丁!”同桌似乎在解釋什麼讓自己頗為得意的事情,點頭說道,末了想起來漏了語氣詞,又加上一句遲到的“喵!”
“哦哦……”大概是因為餓了,或者確實對對方的行為來了興趣,我看著電磁爐上的鍋子,問起對方的名字:“你叫什麼?”
同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來:“八尾巧哦?已經連著做自我介紹好幾節課了,淺井君的記性真差啊喵!……啊!煮沸了!”正說著,鍋子中的氣泡噗嚕噗嚕地沸騰了起來,八尾同學動作十分嫻熟地將攪拌好的布丁粉丟了進去。
……嗯,如果是指今天的前幾堂課的話,我都睡過去了。
“感覺八尾同學很擅長做這個啊。”
“嘿嘿。”完全沒有裝腔作勢地謙虛的意思,八尾很坦然地接受了這個誇獎。再過了會兒,他又把那些液體倒出來等待它們冷卻,放入裝滿冰塊的保溫箱裡。這傢伙準備得還真是齊全。
“這樣就算完成了嗎?”
“哎呀,還要再等三節課左右吧!在那之前要不要來玩井字棋喵!”八尾用動畫裡美少女翹頭的動作敲了敲腦袋,還沒等我答應就在課本上畫了個井字,仔細一看,這傢伙已經在課本上畫了不少東西,這才是開學第一天啊……我小心翼翼地不去碰旁邊畫的兔子媽媽,在棋盤上畫了個圓。
接下來的幾節課,我就在睡覺,偶爾爬起來記下筆記,和八尾玩中度過了。到了午飯時間,八尾滿臉幸福地去了食堂,回來的時候拿著炒麵麵包和蜜瓜味的果汁,我沒有在午飯的時候吃東西的習慣,所以在午飯時間就用飛機枕睡了一覺。
醒來以後不出所料地落枕了。
下午的課有數學和物理,許久不見地睡得很飽,我維持著落枕的姿勢,在矮桌上撐著下巴記筆記。八尾似乎也對理科比對文科興致要高,有在聽老師講課的樣子,到了最後一節課日本史,八尾又在桌子上玩起了瓶蓋跳棋。我因為對累人的競技運動沒什麼興趣,就趴在桌子上看他自己和自己下棋——寶礦力的瓶蓋明顯得到更多的偏愛。
八尾玩膩了之後,從保溫箱裡拿出來了早已被我遺忘的布丁。
“淺井君也來吃!”他用大勺子分好布丁,放在淺淺的紙質碟子裡面,再放到我桌子上。
我拿起他給我的小叉子,放在雙手之間,說到:“我開動啦。”
雖然只是布丁粉做出來的東西,但意外地很好吃。好好地向對方道了謝之後,我帶著八尾去了車站前的蛋糕店,請他吃了蛋糕作為謝禮。
我的家在和他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在車站前說了再見就別過了。道別的時候八尾十分又活力地在月台上跳著招手。
……這傢伙也太有活力了吧,完全跟不上他的節奏。
第二日,八尾帶著一套將棋來了學校,似乎還為了氣氛特意在校服外套了件羽織。我遲到了,所以在扛著被子進班的時候,已經快下第一節課了。順帶一提,寫在出勤表上的遲到原因是“男生早上不太方便的事情”。
八尾看到我來了,便拍拍我的榻榻米坐墊。
“這又是什麼啊……”
“將棋啊!”
“我不會玩。”我在同班同學和老師的目光下,攤開被子,披在自己身上。八尾對這個回答似乎並不在意。
“玩幾局就會啦喵!”八尾巧拉著我的手臂,把棋盤橫放在我們兩人的矮桌中央,側坐在矮桌旁開始了棋局。我一點也不會玩將棋,所以最初的幾局總是輸得很慘,另外就是側坐在矮桌旁對背部和腰的毀滅性簡直大得出奇,還沒玩上多少句,我就已經感到腰酸背痛了。
“高飛車——”八尾用手臂做出來飛車的動作,十分誇張地將棋子放了下來,“好啦,該你啦!淺井君——”
我低下頭來看向棋盤,知道自己又快輸了,剩下的幾步無論怎麼走都是死局:“八尾,你也太手下不留情了吧,我可是新手哎。”
“沒關係沒關係,不支撐到最後一刻誰知道是誰贏呢喵!”八尾擺了擺手,讓我繼續下下去。可是,就我看來,接下來再怎麼動王將,都不可能避免被八尾“王手”了。我左右顧慮之後,還是只好順著八尾額意思隨意地動了一下棋子。
“詰——”八尾將夾著棋子的食指輕輕點在棋盤上,“哇——下局我來讓一讓淺井君吧?”
“剛才那段演說非常不錯,你們兩人不打算把這種精神用在學習上嗎?”
“……啊。”“……喵。”
天女目濡羽先生教授的是古典文學,在我所聽到的有限的傳聞中,是位異常嚴厲的教師。一年級上半學期的時候,我的古典文學還能保持低空飛過的狀態,所以沒怎麼接受傳聞中的作業地獄洗禮,下半學期的時候則……
“那麼,八尾同學,淺井同學,又見面了,請兩位隨便坐。”天女目老師笑瞇瞇地看著我和八尾,哇,惡寒,有種不好的預感。我和八尾趕緊在老師的要求下就近找了位置,教師辦公室的地形我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天女目老師慢悠悠地從桌兜中拿出來茶具,再慢悠悠地泡上一壺茶,然後慢悠悠地為他自己湛上一杯,最後慢悠悠地抬起頭,露出一個看似溫柔的可怕微笑。
“兩位要不要喝茶?”
“不,不用了。”“不用了喵!”我和八尾異口同聲說道,天女目老師抿著茶水,聽到我們的回答後便將桌子上厚厚兩沓紙張遞了過來。
“那麼,就麻煩你們兩位將這兩沓卷子……”天女目老師又抿了一口茶水,我看向紙堆的厚度,猜測他大概只是罰我們將講義送到別的班去,還好,並不是嚴重的懲罰——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天女目老師將茶杯從唇邊移開了,“做完。”
“……這個再怎麼說,做完都有點……”
“沒關係沒關係,不會讓兩位在一天之內做完的,兩天如何?”
……兩天也做不完啊!
“不支撐到最後一刻,怎麼知道會不會做完呢。”天女目老師以溫柔的語氣說道,我第一次感受到語言的刺人,不知道八尾聽到自己的話被用在這上面,又作何感想。要說世上有人長著佛陀的面孔般若的心,大概就是天女目老師了。
事已至此,再做掙扎也於事無補,我和八尾認命地坐了下來,開始寫試卷。
“八尾,你有多餘的鉛筆嗎?我的那根筆尖斷掉了。”
“有哦喵!”八尾將筆袋放在胸前,做出誇張地翻找的動作,過了一會兒終於從裡面拿出來一根鉛筆。
“謝謝。”
我接過鉛筆,筆桿末端不出所料地刻著代表選擇題答案的字母。
接下來的時間過得飛快,八尾一邊抱怨著:“想回家想回家——”一邊寫著古典文學的試卷,注意力下降的時候就在試卷的角落上畫小花,我則像往常一樣緩慢地做著天女目先生給的卷子。試卷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厚,每每做完幾張新的,就交給天女目老師審卷。到了最後一張試卷做完的時候,墻上的指針已經是七點了。
快到該睡覺的時間了。
天女目老師還在低頭審核卷子,我將頭靠在飛機枕旁,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看八尾賣力地在辦公室的教師用黑板上畫小花。
說起來,懲罰學生的話,老師也要在學校裡留到很晚——難道就不覺得累嗎,當做沒看見,早點放我們回去,不就好了?
可偏偏就是有這樣的老師,他們就不會有片刻覺得累嗎——我是完全不理解,隨隨便便把事情混過去是我的人生信條之一,事情只要做到“剛剛好”就行了吧。
似乎是終於批改完了試卷,天女目先生從桌子後抬起頭來,招呼我和八尾過去看看:“兩位的問題有點多,還得再修改一下,把筆記本拿出來吧。首先,你們兩位的試卷都不及格。”
這倒是不意外。
“讀不下去……”我舉手投降。
天女目先生並沒有理我:“仔細地思考字句中的聯繫,必要的漢字的意思則要背下來,這些有好好地聽課的話,都不是很難,有條件的話,可以買一下這方面的字典在家看看。把這些話記到筆記裡吧,然後是你們兩個人分別有的問題。”
“是什麼呢喵!”
“首先,八尾同學,請不要在試卷上畫奇怪的東西,這樣會影響整潔。”
“喵……”
“其次,不可以用詞彙本身來解釋詞彙,用紅來解釋紅,用白來解釋白,這可不是這道題在問的事情。”天女目先生在試卷上勾畫著,“這個錯誤淺井同學也犯了,請下次多加註意。如果沒明白這篇文章的話,希望兩位能用字典和注釋自行理解一遍。”
“……嗯。”
“還•有•就•是•啊,”天女目先生頓了頓,在我的試卷上標畫了一下作文一欄的分數,“不會寫題目要求的短歌,也別拿演歌的歌詞來混事啊……!淺井同學!綜上所述,兩位明天還需要做幾張卷子再進行複習。”天女目先生將試卷還給了我們,隨後揮揮手,“明天見。”
“……”“……喵。”
我和八尾拖著身子,像兩隻史萊姆一樣在地上緩慢地蠕動著。八尾的語氣詞完全失去了朝氣,直到踏出校門後才稍有好轉,快到車站時則完全好了起來,一邊大聲說著“餓死了餓死了!”一邊在夜空下抻懶腰。路燈把街道照得明亮,我在車站前的自動販賣機買了兩瓶橙汁汽水,一瓶給了八尾。
站前的櫻花樹開得正燦爛,遠處,列車咬合軌道的聲音來了。






1、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赫西亚在积存着雨的水洼之间行走,肩膀和侧胁的伤口一直在渗血。水面上映出晴朗的天空,接着燃烧的灰烬和碎石落入其中,打碎它们,让它们泛起小小的涟漪。
枪口不断喷吐出火舌,子弹射入躯体,血液从伤口中向外喷溅,电流和火光在空中交错。天上下着火雨,周围建筑物上的涂鸦像建筑物上张开的嘴巴一样,露出狰狞的笑容。
虽然预料到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多能力者,他们似乎不知道疲倦和恐惧,只是想把侵入这一领域的敌人消灭干净。和岛上偶尔发生的骚乱不同,这是真正的“恩典”与武器的战斗,他看到有人倒下,有人被锐利的钢铁刺穿,有人被子弹击中头部,有人片刻之间就被烧成焦炭。
等这里恢复平静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不会觉得愉快吧。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违反教谕,放弃职责,背弃誓言,说谎、利用别人,白天黑夜不知疲倦地搜索、追寻,一刻不停地奔波,最后再踏入战场,毫不犹豫地伤害、杀死同样身为能力者的人类。
驱使他去做这些的,起初是说不清理由的愤怒,是因为“岛”一成不变的和平环境在一瞬间消失,秩序和安宁不复存在,之后是对离开的“岛”的住民的焦躁与恼火,不管花了多少精力去保护他们,引导他们,“岛”作为“家”的印象还是一下就在他们的脑海中消失干净,变成绑住他们的手脚,必须要挣脱与抛弃,让人不屑一顾的枷锁。
然而到了这里,愤怒与焦躁渐渐消失,笼罩在前面的是一片迷茫不安。
自己的坚持真是正确的吗?也许“岛”才是造成不幸的根源,不管是利维坦还是百眼巨人,那些能力者创造的组织才是那些天生被赋予“恩典”的人最终的归宿,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好的世界。
那么,这一切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自我满足而已。
——他是怎么想的?这是他想留下的地方吗?如果他拒绝回去,应该怎么做?
行动服裂了道口子,扯开的纤维被血和伤口黏在一起,好像有灼热的铁块贴在皮肤上,靴子下面传来水的阻力。
他感到身体被什么重物拖着,步伐越来越沉重,但是并没有感到痛楚。因为另一个高亢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疑问,从昏昧不明的地方、从混沌之中、从纠结繁杂的思绪里冲出来,不断向那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召唤着自己的,像是晨曦中的月亮一样的苍白影子传递着回应。
——在哪儿,你在什么地方。
——我要到你身边去。
——等着我。
2、
这片厂区已经废弃多年,布满管道与连接设备的建筑全是裂痕,爬藤植物爬满了整面墙壁,甚至有几个房间的天花板落下来,变成破碎的水泥块躺在地上。光线从破口射进来,被裸露的钢筋和碎木板切割成一块一块。只有从空间的大小才能勉强看出这里曾经被用作车间之类的用途。
周围到处都是灰尘,空气里弥漫着腥甜的铁锈味,还有什么东西烧焦的气味。地上散落着脚印,某些挨着墙角的门敞开着,而房间中央有不知名的仪器正在轰鸣,喷吐出白色的雾气,通过烟囱排向屋外。
赫西亚走进那台仪器,它像由钢铁构成的动物,正伏在那里发出沉沉的呼吸。这大概是净化污水的装置,白雾就是热气凝成的水雾,地上的铁管从远处另一栋建筑延伸过来,通过机器以后,流进下垂的水管,接着进入环绕厂区的河流。
他抬起头,看着那栋七八层的灰白色楼房,它建在稍微陡起的缓坡上,背对着一道深沟,沟渠里面是奔腾汹涌的河水,从厂区一直冲向大海。
他转身从钢铁管道和废弃机器、建筑垃圾之间挤出来,打算前往那栋建筑,突然,几步远的地方传来踢开什么东西的声音。
赫西亚闪到一边,他看到一个大块头匆匆走过,身上披着和外表非常不协调,沾着血污和灰尘的白色外褂。
——这就是“组织”的研究者吗?
赫西亚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身体隐没在机械背后的黑影里,悄悄跟随他的脚步来到外面。
3、
男人走出废弃厂房,步伐便加快起来,他的目的地也是那栋楼。两个人一同踏入了没有任何掩蔽物的水泥空地。
赫西亚一度有些担心对方会发现自己,不过不久,他从脚下的水面倒影里看到了那张面孔。那个人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是充斥着一种诡异的喜悦。他瞪着眼睛,嘴角勾起,对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好像肩负着什么伟大使命,而这使命就要完成了一样。
大约步行了两百多米,那个男人到达建筑物一侧的窄门前,用一张卡片刷了一下锈迹斑斑的老式密码锁,拧了拧门把手,接着用力拉开了那扇有些变形的铁门。
赫西亚环顾四周,岛上来的支援还没有到达这个位置,他欺身上去,猛地用手臂扼住了对方的喉咙。
出乎意料地,那个人做出了极为迅速的反应。他的另一只手甚至都没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扭转身体,用腰的力量顺势把从身后偷袭的人甩到前方,接着朝对方的右脸出拳。
这家伙的力气大得惊人,赫西亚躲过了迎面而来的一击,几百磅的冲击落在他身后的铁门上,把它撞瘪了一块。但与此同时,对方弯曲的膝盖朝他的胃部袭来。
赫西亚尽量弯曲身体减弱冲击,但瞬间传来的麻痹感以及恶心的感觉仍然席卷了全身。
胁下的伤口又被扯开了,他呛咳了一下,吐出带血的唾液。
这么近的距离已经无法拔枪了,他皱了皱鼻子,绷紧身体,仿佛有一阵电流通过身上的每块肌肉,他开始捕捉对方的动作,防御、出拳、踢击,攻击对方膝盖、脖颈、肘部、腕部脆弱的环节,而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里。
——他是能力者,而且被进行过身体强化,虽然不知道他的‘恩典’是什么,但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终于,对方无法移开身体,咽喉下面重重地挨了一拳,外褂下面的夹克拉链被压进他的胸口,胸骨被压扁了几寸,空气从他的肺部挤了出来,让他的喉咙里咯咯作响。
“牧羊犬”尽量保持一只手握住对方手腕的姿势,从腰际的搭扣里抽出匕首,向对方的腿猛力刺下去。
庞大的身体震颤了一下,麻醉药物从刀柄流出,沿着血线进入对方的伤口,男人摇晃了一会儿,接着重重倒在地上,像一头被放倒的犀牛。
赫西亚拖着那具躯体,试图把他关在门外,但刚才的铁门已经合不上了,于是赫西亚在一楼走廊挨个查看两侧的房间,终于找到了一件带着隔间的。
——气息。
他从翻倒的柜子和桌椅之间拔脚出来,反锁上门,拖着脚步向前走去。陈旧的水泥墙到处都是斑驳的污迹,天花板上的吊灯摇摇晃晃。他努力加快脚步,最后开始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小步快跑起来。
——那个人就在这里,而且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
走廊尽头是向上的楼梯,他握住扶手,用反作用力拉着自己的身体往上爬。带着霉味的空气让他感到呼吸不畅,平时很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变得如此困难。但“牧羊犬”还是坚持着走上二楼,走过走廊,接着是三楼、四楼,他在每一扇门后面搜索着,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
突然,脚下的地面摇晃起来。
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于是停下来靠近墙壁,但随后又是一阵摇晃,天花板上的灰泥簌簌下落,他感到自己站在船上,正被大浪托向高空。
——地震?
这个念头让他吃了一惊,他仿佛看到这栋本身就快要倒塌的建筑内部的钢筋摇摇晃晃地折断了,裂缝像藤蔓一样在地板和墙壁上爬行,大楼变成两半,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倾倒下去。
要怎么办,该怎么找到他,要怎么才能让他得救?无数个念头在“牧羊犬”的脑海中翻滚旋转,冷汗从他的脖颈上流下来。他拼命地向前走着,还有一层,还有……
终于,在五楼的走廊尽头,他看到了正匆匆朝自己走来的“黑羊”。
4、
光从走廊尽头的玻璃射进来,照在他身后,将他的身体埋在黑影里。赫西亚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但可以感到周遭退却和拒绝的气氛。
“牧羊犬”张了张嘴,但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好像稍微瘦了些,手伸进外褂的口袋里,一副迟疑和迷惑的样子。
下一瞬,他会拿出什么?解剖刀,手枪?他会发动“恩典”吗?他会朝自己伸手吗?还是会转身离开,背对着自己消失在刚刚出现的地方?
这好像十五年前,自己作为牧羊犬的能力被发现的时刻。赫西亚无法抑制地这么想着。
首先是伤害她的人,接着是照顾她的人,然后是无关的路人,最后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他们的身体从内部爆开,血液和内脏溅的到处都是,被暴走的“黑羊”撕碎再丢到地上。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像另外一种生物一样无法沟通,最后她选定了自己作为目标,一步步跟着自己走上楼,一直走到天台边缘,因为那里没有人,至少可以减小一些伤害。
——不,不,已经不会再出现那种事了。
“医生?”
他向前走去,“黑羊”轻轻地战栗了一下,但没有移动。
“文森特……医生。”
在吐出他名字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建筑再次摇撼起来,这次的震动已经无法停止,家具纷纷开始倾倒,日光灯从头顶落地摔得粉碎,墙壁和天花板开始往下掉。阴暗狭窄的空间发出轰响,木头和钢铁弯曲折断,地面变得像在风浪里起伏的甲板。
没有时间了,他从身体一侧拔出手枪。
这个动作似乎让站在走廊尽头的人向后退了一步,但之后他把视线移向一边,看着走廊一侧被子弹击中,碎成一片片的双层玻璃窗。
外面的冷空气冲进来,让人浑身为之一凛,赫西亚看着下面深暗的河水。湍急的水流形成一个个漩涡,卷着泥土和枯枝向远方涌去。
又是一阵剧烈的摇晃,大块水泥整个落下来,掀起一阵烟尘。赫西亚奔过去,抓住“黑羊”的肩膀。
对方的表情因为疼痛而扭曲了,他瞪大眼睛盯着面前浑身是灰尘和血迹的男人,赫西亚在他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你相信我吗?”
“牧羊犬”把手指插入对方的头发,用额头抵着他的,以清楚而不容拒绝的声音说。
“黑羊”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打了个冷战,似乎陷入了极度的动摇。他们现在已经一只脚踏出窗外,半个身体几乎悬在半空。
终于,蓝色的瞳孔放大又收缩,文森特以几不可见的动作点了点头。
5、
随着一声巨响,尘埃从建筑的窗口中喷射出来,其中还有隐隐的火光。
整栋楼像被浇上热水的刨冰一样逐渐垮塌,烟尘四溢而出,灰白色的墙体不断变矮,最后成了堆在地上的一片瓦砾。
接着,那景象消失了,他沉入冰冷的河水,黑暗一下包围了他们,耳边传来气泡和水流的汩汩声。
下坠过程中撞到了什么东西,赫西亚觉得自己的半边身体好像被扯断了,疼痛让他几乎昏厥过去。
“牧羊犬”竭尽全力维持着自己的意识,在湍急的水流中拖着和他一起坠入水中的人,一边流向下游,一边拼命向头顶的光线浮上去。
============================================
*上一篇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89018/
*我不管了!!!让我硬上!!!!
*下一篇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89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