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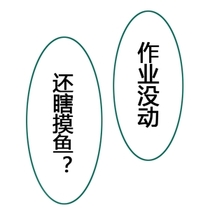
主线补档太沉重了让我摸个鱼【……………
*幻想工作搭档的if线
*091609,为了不被任何一方的群众打死我选择不表明立场xxxxxx
*很没质量的小鱼,随便看看就好【。
弗朗西斯不喜欢在工作的时候皱眉。作为一名优秀的商人,不管对面坐着的客户身份高低,性格如何,笑脸迎客都是基本的礼仪。更何况,从容淡然才是弗朗惯用的武器;在他行走的江湖里,不论是面对权贵人士或是市井小卒,一个自信的卖家形象是弗朗博取信任,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的第一步。双目失明带来两面的效果:在一场场见不得人的交易中,虽然能以不可能暴露买家长相为由,让买家安心,但同时也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不便。即便弗朗依靠听觉也能基本自保,但总是有个健全的人跟在自己身边会安心些——
明明这才是自己当时默许这个叫长居累的家伙缠着自己的理由。
弗朗轻轻在心里叹了口气。他现在坐在一桌佳肴美酒前,对面是来自当地黑帮的一位新晋干部和他手下的几个稍有些地位的喽啰。这并不是一笔大生意,但基于和该黑帮长时间以来的交情,弗朗找不到理由拒绝这次交易。原本只是抱着走过场的心理准备好了货物,打算速战速决的弗朗,听着身边传来的并不是投向自己的邀请,努力压着想绞到一起去的眉头。他在心里偷偷抱怨了几句,便一手举起手边的高脚杯,一手抓住坐在自己右边的人的肩膀,还没等对方开口就抢先站了起来,扯着一脸微笑道:“抱歉,这位长居先生只是我的护卫。”
此言一出,餐桌边的所有人登时都将目光投向了他——其中包括被他按住的,举着盛满了红酒的玻璃杯的“护卫”,长居累。
“先生不如直接和我喝几杯吧。”弗朗将他混沌的目光投向邀酒人的方向,控制着面部肌肉不慌不忙道,“作为坏了先生兴致的补偿……我可以把这两杯都干了,怎么样?”
对面的人似乎是没有料到这样的状况,一时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好在他很快反应过来,虽是语气里透着不满,也还是没有刻意为难,到是起了兴致似的打量了弗朗一番,悠悠地道:“哦?弗朗西斯先生看来是酒量了得?”
“不敢当。只是这点度数的红酒,还是能陪先生喝几杯的。”他说完,直接将自己的酒杯举到面前,抬头一饮而尽,接着将空杯往桌上一搁,从长居手里拿过另一杯斟满了的,朝着对面举起示意了一下,“这样先生应该就没有意见了吧。”
他微微眯着的双眼里闪着的精光如铁钉般将对方突然钉在了空气里——那人原本悠闲的表情在一瞬间里像石膏像凝固,然后被风沙迅速腐蚀,双眼微微瞪着,嘴角的弧度也禁不住降了下来。下一秒,他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狼狈,堪堪抬高语调答应了声:“弗朗西斯先生真是爽快……”
“呵,既然先生喜欢爽快些……”他的话音刚落,弗朗便笑了笑立刻接道,“那喝完这杯,我们就谈正事吧。”
对面的男人看着他干净的脸,突然有这么一刻怀疑起了面前这位有名的毒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双目失明。
长居累看着自己刚刚想去搀扶弗朗西斯却被拨开了的手。如果是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也许他会有点心伤;但是现在,他只是平静地将手收回了身侧而已:如果弗朗真的让他扶了,那就该醉得快不省人事了吧。
“别以为我酒量像你那样啊,长居。”果不其然,这位刚刚在饭桌上还满脸堆笑的商人此刻眉头紧皱,语气刻薄,“两瓶而已,又不是什么烈酒……”说到这里,他的嘴角却又高高吊起,那双蒙着雾的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线:“到是那些家伙,这么不能喝也能在道上混?真是笑死我了。”然后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顿了顿,接着将虚无的目光投向长居,听起来却是愉快地说道:“像你,就只能做个混混嘛。”
“混混?我不是你的‘护卫’吗,弗朗西斯君。”长居不慌不忙地,重重地念道。
“哈,我正要说呢,有你这么个麻烦的护卫,真是给我增加工作量。”弗朗毫不掩饰地一甩手,大肆表达着憋了一晚上的不满,“这么不能喝,给你挡也麻烦,不给你挡更麻烦……我看你还是最近别跟我出来,自己去好好练练酒量吧。”
长居闻言,却也还是轻松得很。自和他相处以来,弗朗早已把“不带你出来”作为口头禅挂在嘴边不少时日了。他微笑着跟在弗朗身后——这条狭窄的胡同,连月光都照不到些许,却确实是回弗朗家的近路。比起臭名昭著的毒贩的身份,弗朗住的地方到是普通得很,不过是出租公寓楼里的一间罢了。话虽如此,夜晚在这样的小路里穿梭,就算是良民也该有些危机感;明明清楚道上套路的弗朗却毫不避讳,大摇大摆地走在这里,实在是不能让长居安心——
“谁?”
随着弗朗一声尖锐的发问,长居反射性地跳起,贴到弗朗身边摆开了架势。
黑暗中没有传来任何长居能听到的动静。但这样的安宁只持续了几秒;嗒嗒的脚步声像是突然放弃了隐藏自己一般肆意响起,伴着一个毫无波动的音色:“还是这么敏锐啊……”
弗朗西斯闻声一呆,然后大声笑了出来:“什么啊,太久不见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他拍了拍长居的肩膀,拨开他想向来者的方向走去,却被长居一反手拦住:“等一下弗朗西斯君,他是谁?”
弗朗没料到长居会有此行动,不禁愣了愣,接着哈哈笑道:“不用这么紧张……刚好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老朋友。”
“我可没兴趣做你的老朋友。”黑暗中的声音依然波澜不惊,“狭路相逢而已。让路。”脚步越来越近,此言一出,从混沌中浮现的人影终于开始渐渐清晰。长居盯着黑暗里一双血红的眼眸,实在是无法对他有任何正面的印象;更何况他说出的话里,满是锋芒毕露的恶意。
“弗朗西斯君,这个人很危险,你让开。”他固执地杵在原地。
对方的脚步片刻不停,嘴上不耐烦地说:“……我对你们没兴趣。让路。”
“这位先生……”长居回以礼貌地一笑,“您走您的便是。”
只听那人切了一声,嗒嗒的脚步声突然加快了节奏。长居终于慢慢看清了他的脸:西方人的脸型,细长的双眼,紧抿的嘴唇,一头杂乱的金色长发,和长发下的额头上,若隐若现的伤疤。一件只扣了三颗扣子的素色衬衫,一条颜色相配西装裤,一双手插在裤袋里,腰间的手枪别得肆无忌惮,展露无遗。长居看着他朝这边瞪了一眼,接着满脸冷漠地靠近,自己便得以在很近的距离内直视那双凶狠的眼睛,用镇定的凝视回应,然后盯着他从自己面前走过,直到那个背影消失在另一端的黑暗里,也确实再没有其他任何行动了。
突然有些许月光卡着那人离开的时点投射到小巷里。大概是月亮的高度变了,长居这么想着松了憋着的一口气,顺势就想说——
“咔。”
他的后心突然被堵上了一口冰凉的枪。
呆愣了一阵,长居累才下意识地举起双手,大脑一片空白,只得怔在原地。待金属的温度让他稍微清新过来理解了状况,他立刻开口:“……弗朗西斯君?”
“转过来。”
枪口突然被挪开。长居疑惑着,还是听话地迅速转过身——
于是那枪这次便正正贴上了心口。
冰冷的压迫下,长居的大脑中回荡起自己心脏咚咚咚的跳动声。他的表情呆滞了,但在转为惊讶前被定格,终于什么明显的变化,甚至在片刻挠人的沉默后舒展开来,恢复了以往的微笑。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长居。”弗朗便在此刻开口。他的手很稳,手里的枪身没有丝毫抖动,结结实实地抵在长居胸前。然后他像是享受这番沉默地笑出了声,带着些许怒气些许得意:“就算看不见……我也知道心脏在哪里。”
长居打量着弗朗狡黠的笑脸。
“是。”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直说。”弗朗又将枪往前递了递。
长居便一动不动地站着,许久没有回答——直到终于灌满小巷的月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我就当你是明白了。”
胸口的压力消失了。长居眼见着弗朗头也不回,大步流星的背影——
“平时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他跟了上去。


搬家太忙了实在对不起,只能出来流水账一波【哭唧唧
对不起07,我这边完事儿了补图给你呜呜呜呜呜呜呜
但是我嫌弃了大姐姐,我巨爽【靠??!!!
待在没有阳光的房间,会对时间的流逝感到麻木。
但弗朗西斯并不是如此。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偶尔会捕捉到一些悉悉索索的衣物摩擦声,哒哒哒的脚步声和门的开关声,都来自墙的另一边。在那之后,世界已经安宁了不少时候;他知道自己混混沌沌地从另一个世界回归,在黑暗的宇宙中游离,最终在这个充满了酒的醇香的空间坐下,那就已经是深夜了。空气中飘着让人迷醉的味道,与他而言异常强烈又怀念。他坐在高脚椅上,侧靠着吧台,一只手撑着自己沉重却清醒的脑袋,另一只无意识地敲着手杖的握把,咔咔地甚至有些微弱的回声。
他记得自己并没有品过多少酒。他是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普通的孩子,顶多父母并不是他出身地的本国人罢了。在他的记忆里——更准确地来说,是“前半生记忆”里——他根本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也没有机会接触那些昂贵的洋酒。然而他却记得一个跳跃了时间的最近的自己,过着还颇显富贵的生活,自由自在,好像是在整个人的成长过程被砍掉了一截,完全找不到这种变化的缘由,不用说像是一夜暴富,甚至是直接换了个人在生活,而被清楚铭记的“现在的自己”的形象,也只是一片从火灾中被抢救出的残页,徒有零零散散的词句却拼不出完整的文章:这让他对自己感到陌生,无法对自己付诸信心与信任。
他想起了我妻真二,那个从称呼来看确实与自己熟络,又听起来诚恳地告诉了自己那些难以置信的“幕后故事”的人。
他不喜欢和我妻真二有交集,虽然这种讨厌的感情并不是针对在我妻这个人身上。他讨厌现在这种从别人口中了解自己的感觉,那让他更深刻的明白自己对自己的陌生,即便他其实已经有些被我妻的故事说服。就算单单理性地来考虑,这个人本身也有太多的疑点,不用说突然的出现,没有编号和住所,强势地想要引导裁判的走向,和他一副知道一切真相的嘴脸,就光从自己和他的交流来分析,如果事实确实如他所说,那为什么这里的人中只有他是不一样的?这方面的“差异”,直接指明了他必然是受了“背后的组织”什么“恩惠”,否则为何选择他成为“特别的那一个”?比这些越理越乱的重重疑惑更要命的是,弗朗内心有一种无法自控的想相信我妻的直觉,无凭无据,令他浑身发凉,不禁对我妻真二这个人更为警惕和在意。
“从这方面来说,如果我妻先生跟你一样好懂就好了……”手指敲打拐杖的声音突然停了,弗朗西斯眼珠都不转一下,直直地对着面前的空气说道,“是吧,长居累先生。”
短短一阵时间内,无人应答。片刻后,在静如深海的酒吧里才响起一阵沙沙的衣料摩擦声,合着脚步和轻快的语调:“晚上好,弗朗西斯君。”他不对弗朗没头没尾的招呼做任何评价,只是结束了问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弗朗将重心移正,原本靠在吧台上的手取来一边的高脚酒杯,坐直了对着长居慢悠悠地问道:“这么晚了,也来喝酒?”
“如果弗朗西斯君邀请我的话,我很乐意。”从容,干净,直接。如他一直以来跟在自己身后的脚步一样,随性而为,毫不遮掩。弗朗西斯心中暗暗评价着,自己其实并不讨厌他的这一点——
“但是,很可惜,长居先生。”他从高脚椅上跳下,平视前方,“我并没有那个打算。”
“我喜欢直白的人。你确实也是这样的人。但是,长居先生。”
他往前迈步,知道长居累就站在他几步远的地方;他早已凭方才的对话推断了距离,于是毫不犹豫,准确无误地从对方身旁擦过——
“你让我很烦。”
一步不停地,弗朗西斯往酒吧门口走去。
“……我听说,广崎君和我妻君,约好了明天来这里喝酒。”
等弗朗走过了拐角,才听到酒吧里飘出这么一句幽幽的话语。
还没待弗朗走下二楼的楼梯,一阵热闹的脚步声轰轰烈烈地迎面奔来。
“啊!终于有人在了!”不管跟谁比,这脚步都过于活泼,让弗朗不敢断定来者身份,好在对方立即热情地开口了;虽然并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他的音色还是被刻在弗朗的记忆里:是超高校级的甜点师,雨宫安里。
雨宫一溜烟哒哒哒地跑到弗朗面前,兴奋地叫道:“哈哈哈!请尝尝我刚完成的甜点吧!新品种哦!”
弗朗被这股狂风暴雨般的热情掀得有些尴尬,好在对甜品也小有兴趣,便应了声“噢”,从雨宫端着的大盘子里摸起一块放进嘴里。
“嗯。很好吃。”超高校级的称号果真不是空穴来风,雨宫制作的甜点被切成了刚好一口一个的试吃份,口感细腻入口即化,各种材料的香味和甜味被完美包容在一起,或互相调和或互相增味,确实是一种无法多得的美味。
雨宫闻言,又快活地憨笑起来,接着问道:“嘿嘿,附近还有人吗?我再找几个人试试!”
弗朗将手里的牙签放回盘子里:“嗯……楼上没什么人,我只知道长居先生一个人在酒吧里。”
“哈哈哈好的!那我去啦!”弗朗的话音刚落,雨宫就和来时一样热闹地跑上了楼梯,没多久就没声儿了。他来去如风的样子让弗朗不禁想起了熊田……
电视屏幕上鞭炮处刑的场景突然占领了大脑的频道,爆炸,燃烧的引线,被殃及的金属支架……弗朗的心没有任何恐惧的机会,却被单纯的厌烦与喷怒支配了情感。他不畏生死,却只是对于被限制行动,居与他人控制之下的现状感到不悦;而当他抛开外界的环境审视自己,他就被更深的迷惑和不安包围,就好像自己的身体里住了一个不认识的危险灵魂,随时会把“我”吞噬,取而代之。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疑惑,让弗朗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没有把握——
——如果能出去,我就能搞懂现在的我自己了吗?
他冷不丁地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