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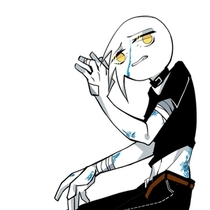
陌生人把烟凑到他嘴边说这东西能让你感到好一点。刘军拒绝了,他闻到温暖的,清淡的烟草的味道——香烟没有被点燃。
他还是血肉之躯,承载着微不足道的灵魂。但很显然这点灵魂对他来说已经太沉重了。
他感到自己躺在陌生人的臂弯中,血蹭的到处都是。“你快走。”刘军对他说。一小时前为了让部队脱离困境他独自一人去吸引敌方的主意,然后被大口径的子弹右肩。迫击炮的炮弹在身边爆炸,至少有六七块弹片卡在肺叶,剩下的则切断了腿骨或者胸骨,又或者嵌在他的头部。
总而言之,以当代人类的知识水平与科学技术来判断,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在北边森林里冬天又是那么冷,地上只有薄雪一层,更多的是枯枝败叶,冻得干脆了,又浇上了粘稠的蓝色的血。血液渗透进地里,蒸腾起白色的雾气。他快看不见东西,感觉不到疼痛,也没余力思考更多的事情了。甚至不想知道自己身旁的人是谁。
自己必死无疑,部队的奇袭取得了胜利,没什么好挂念的了。
陌生人将他抱得很舒服,对方的体温很高,让刘军的头贴在自己胸前并抓着他冰凉的,不完整的手。可能是因为快死了感官都停止运作了,他没听到对方的心跳。“这里危险……”他拼命拼出几个单词后彻底失去了呼吸,嘴边的肌肉被烧烂让他口齿不清,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注意到。陌生人伸手合上他的眼睛,用衣袖简单擦了一下他脸上的血后将他从地上抱起。
他的手无力的垂下,脑袋歪向一边,再也没有了呼吸。
这期间他醒了一次,将他唤醒的是剧烈的疼痛,除了从伤口传来,几乎将身体撕裂成两半的痛,还有仿佛大脑被一万条蠕虫啃食的痛苦。
眼前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概是伤口波及了视觉相关的区域。刘军蜷缩成一团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听到有人赶来将他扶起,把类似咖啡的东西递到他嘴边,他嘴唇粘到那清苦的液体就忍不住地干呕,后来是怎么喝下的也不清楚。等他像度过了漫长但普通的梦境一样,在林间的晨光中醒来,已经什么也不记得了。
北方的森林在冬天常有人来打猎,这时候无论熊还是鹿皮有最好的皮毛。在这片覆盖北部大陆的森林里散落着不少猎人的小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搭建的也没有主人,谁遇到了就打扫打扫住进去,走的时候或带走或留下一些物资。
他盖着好几条毯子躺在沙发上,沙发靠着石头砌的壁炉,炉里火焰还烧得正旺,壁炉上方则是巨大的麋鹿砍头。窗外晨雾还未散去,一点白光照在他身上。屋子很简陋,只有一套沙发几张桌子,没有床和多余的家具,猎枪斧头和柴火都堆在墙角,并不是被随意丢弃的。但对长时间在山林中打猎的猎人,和在战场上厮杀已久的士兵来说是一种奢侈。
陌生人不在屋里。周围太安静了,连鸟叫声都没有,只有燃烧的木头时不时爆开发出的声音,以及窗外某人一下下,悠哉游哉劈着木柴的声音。
刘军有些害怕,他昨天还在战场上,耳边充斥着炮火和枪声,以及战友中弹受伤倒在地上的哀嚎声。就连晚上也有零星的炮火以及伤员小声的啜泣声。
这里太安静了。
他翻身下床,双脚踩在地上垫着的巨鹿皮上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完整,他仿佛从没受过伤。除了一些擦伤与小面积的烫伤还在隐隐作痛,那些断裂的骨,纠缠在一起的肌肉血管以及支离破碎的肺部似乎已经回复如初了,而就连那些细小的伤口也被人包扎过,手法比战地医生要仔细一些。
他披上大衣走出门去,男人早已解决完了一堆木柴,正抽着烟把锅架在一个小炉子上,悠闲自在。看到裹着大衣的刘军站在门口冻得直哆嗦,男人冲他扬了扬眉命令道:“回去,外面冷。”
可他分明在笑。刘军听话地向后退了几步,努力把一肚子疑问憋回去。
男人定是知道了他在想什么,冲前脚已经踏回门内的刘军吆喝:“有什么问题吃了早饭再说。”
呲啦一声,又是他在煎什么东西了。
剩下的二十分钟对刘军来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难熬,在屋里站也不是躺也不是,走两步又踢到地上散落的木柴,只能坐回沙发上重新裹上毯子,老老实实把手放在膝盖上。直到男人推开门,把煎肉和炒蛋摆在他面前。应该是鸟蛋,刘军想,这种地方他哪来的鸡蛋。接着他不顾形象地狼吞虎咽起来,男人就坐在对面微笑着看着他。
“慢点吃,小心胃疼。”士兵带着歉疚的眼神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又把脑袋埋进盘子里。
刘军一个月一来第一次吃到一顿像样的饭。和木屋一样简陋,但热量与营养都刚刚好,更何况陌生人厨艺惊人,在这种贫乏的环境下做饭,连他都不能挑出什么毛病。
男人看他快吃完的时候出门去了,等他扒完盘子里的最后一块炒蛋的时候提着一壶咖啡回来。刘军闻到那香味想起昨晚似乎发生了什么,但记不起来。
陌生人给他跟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将咖啡壶随意放到地上:“我叫阿尔萨德,阿尔萨德•亚维奇。”
“刘军。”刘军紧张地看着他,觉得这个姓氏有些耳熟。
“是东方的盟军吗?”男人眯起狭长的眼睛,“你的名字像是来自那里。”
“是的。”刘军喝了口咖啡,紧攥着的手是要把杯子捏碎。
“亚维奇先生,如果您也是盟国的人,能不能告诉我部队在哪……”
“你的部队,正在把胜利的消息带回祖国。”阿尔萨德悠闲地喝着咖啡。
“那我……”
“以及你的死讯。”





它引他们走进那山洞。几个牧犬的勇士便开始推或者拉动那石扇。
石扇是牧犬常用的简陋机关之一,将洞穴凿成工整的方形通道,将巨大的石板排列并凿出供人出入的缺口,只有推送到合适的位置才能将洞连接成通道进入。伊格尔顿蹲下来看,石板与地面之间塞了许多坚韧的木制圆棍,估计用来减轻与地面的摩擦。
阿奎拉打头,结果长老手中的油灯带领天外来的贵客进入石扇,白川害怕,说要是外面在这时候推动石板自己就被夹死在里面了。阿奎拉伸爪对着他脑袋就是一下说你说什么呢,肉垫打在脑门上却一点也不疼。
终于通过石扇来到牧犬口中的星海,没想到却是一间昏暗的圆形石室,石室大得出乎意料,仅从脚步与说话的回音就能判断,阿奎拉特地嘱咐两个年轻人一定要放轻脚步放低声音,白川与卢洵听罢面面相觑用手捂住了嘴。不确定室内有没有其他的出口,氧气却还算充足。阿奎拉说这里有向上向下各八条通道通往外界,这就是为什么星海要建在半山腰。墙壁上燃着长明灯,大概是巨蟒的脂肪炼的灯油,隐约勾勒出石室的轮廓。墙壁与地面之间被挖出一条很深的沟渠,如果是听觉极其敏锐的人能听见细碎的水声。
刘军抬头看了看低声问阿奎拉石室顶上悬挂的是否是丝线,雪豹笑着点头道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接着带领一行人走上圆台。
她走回去拉下门边的绳子,长明灯逐渐上升到看不见的位置。现在唯一的光源只有她手中那一盏小油灯。
昏暗中刘军跟剑主自觉护在了两个相对年轻的家伙身旁,直到那点火光走到面前。
雪豹眯眯眼,琥珀色虹膜被灯火照地透亮,瞳孔还没有完全放大。
“准备好了吗小伙子们。”
“熄灯了!”
随着油灯被吹灭,天花板上三个幽蓝的球体奇迹般亮了起来。荧光通过无数极细的线不断闪烁。那些线交织在天花板上,以三个光点出发不断向外扩散盘旋,交织的地方正如星光闪烁。随着人的移动高光沿线的轨迹不断跳跃,白川恍然大悟道:“原来这就是星海。”
“三个球体代表主恒星以及牧神的两个卫星,牧神传说不认为牧神星是地球的中心,而认为一切行星围绕白鹿的三只眼睛不断盘旋转动。星海便是按照这轨迹造成的。”
“螺旋菌,”刘军小声道:“在天黑后才会生长发光的菌类,以及地面上这是……”
“牧神蓝藻,同样会发出荧光的物种。”阿奎拉接过话茬。几人这才看见沟渠中的星星点点,以及台面上用蓝藻画出的一个个套在一起的圈。
“看来蓝藻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氧气,石壁里充斥的二氧化碳则可以溶解到水里……”
“主要还是通风啦。”阿奎拉解释道:“其实星海并不是什么神秘严肃的地方,只是因为星海太过精密,修补起来也过于麻烦,就减少无关人员的访问了。”
“还有因为雪豹夜视力的原因,大姐是看不到这副场景啦,也就没法帮你们解答。”阿奎拉又用肉垫拍了拍白川的脑袋。刘军发现了,一切外星生物或者具有外星血统的生物都对白川的脑袋特别感兴趣。从上次那射手揉他脸揉了大半天就能看出来。
“白川,你的星图呢?”领航员沿着地上蓝藻流动的轨迹走着,突然抬起头。“在这儿,怎么了?”白川手忙脚乱掏出那个核桃,打开星图投影。
“看这个。”刘军带着他绕着蓝藻圈圈走着,对照星图看着丝线上的高光:“这几个比较粗的线都能看出来的,矿场,雪山,牧神本身,他们对星轨的预测已经相当准确了。”
离去的时候刘军在队伍末拦住了阿奎拉,让剑主带白川和卢洵先出去。“那不是普通的丝线,到底是什么材质的。”
“我也不知道啊。”阿奎拉眯眼,嘴角列开雪豹特有的微笑:“听老人说,是什么时候在秦大荒原捡到的,水晶砖呢,用热的石头蘸那砖头,就能拉出极细的丝线……于是就有了星海。”
“那是……”刘军皱紧眉头道:“难道真的是……”
“塑料原料。”阿奎拉收起笑容严肃道:“在大荒原发现了塑料原料。”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不及时向总署汇报?”
“上一任不知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刚接手,所以来找你们看。请及时把消息汇报给总部。”


千井千灯:
牧神语的“井”一字符由两竖两横构成,与中文相雷同,作为词组的部首之一不但指“从地表下取水的装置”更有万千河流源头之意。
秦舟地区作为牧神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处于通讯与交通都不发达的大山之中。不仅如此,特殊气候还经常导致瘟疫的流行。
千灯王,纯黑的神犬,在纯白的药王的帮助下协部族首领以药材制灯,每逢牧神夏季来临便以投在“井”中,灯火带药物顺流而下,灯火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系,药物也治愈了族民。千井地区得以成为牧神文明的第一个发源地。
两人在每年最干旱的季节制作药材,每个牧神年派遣不同的医师,七年一轮回,每组7人,带兽头面具将灯舟投入水中。久而久之发展成一种习俗。据说这就是说戏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