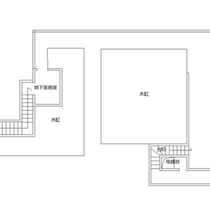一
枫华庆典开始的时候,也是塔恩回来的时候。
理由很简单,这是全年最容易买到好材料的好时机、好地方。
她已经在一家裁缝店外看了许久。
直到店里摇着羽扇、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人们离开后才推门进入。
店员很高兴,因为面前这位乡下丫头指向了店里最贵的墨绿丝绒。
店员也很难过,因为这位客户指着最昂贵的布料却只想做一条颈带脖链。
这实在不是一笔好生意。
“不行吗?”
女子翠绿色的眼眸望向他。
店员一怔,那绿色如同远东商人带来的玻璃碎石,竟让他一时之间有些发怵,拒绝的话语没有说出口。
“自然…自然是可以的,”店员摸摸鼻子,“只是要做好,不免要搭上一些金银丝线、还有一些晶石…”
店员话语间便见女子从随身兜里掏出了金银碎石和一枚祖母绿晶石。
“这些?”
“咳咳…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店员说着便伸手将东西拢到怀里。果然店长说的人不可貌相是真的!这样寡言又出手阔绰的客人也不错!
二
庆典的味道是芬芳的玫瑰味,是刚出炉的面包香,是武器碰撞间的烧焦味,是冒着泡沫的啤酒味……
暗处的窄巷,会让味道预加浓郁。
总之什么都比面前男人涂的香水味好闻。
塔恩此时此刻是这么想的。
“束缚之笼,你的大作,”面前男人将生锈的圆球丢到塔恩脚下。那圆球凹凸不平,是用锁链捆绑而成,上面的铭文已经模糊不清,明显是已经用完之物,“两年前,那低劣的龙化佣兵就是用你的东西困住兄长。我永远都记得他割开了兄长的喉咙。那血,已经没有温度了。你说说 ,我是不是该找上你?如果不是你,那龙化佣兵又怎么会得手?”
塔恩闻言,视线由那圆球拾级而上,略过正用手帕擦拭双手的黑色铠甲骑士,计算着离开的步骤。
“你不打算为自己即将到来的的死争辩一番?”手帕被丢弃在地。
“不是我杀的。”塔恩回到。
“是你!你们都是些没有原则的叛离者、没有底线的投机之徒、没有道德的、、、、、、肮脏事物!”
啊、、、、、、不太会骂人的贵族。
他真该跟黑市那些喝着啤酒互相谩骂的人们学学怎么骂人。
塔恩撇撇嘴。
便见她伸手摸进兜里掏出一物掷向骑士。
“你!”骑士见状抽剑运气抵御来物。
那物体滚落在地,竟是一把木质汤勺。转动的汤勺仿佛在嘲笑骑士刚刚被欺骗的愚蠢。
在回头看,已经没有了女子的身影。
“塔恩.希别克!你给我等着!”
三
远离城邦,塔恩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过骑士了。
所以她突然做了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面大镜子前。
南方家族一贯喜欢用绸带和珠链编织女眷的秀发。
服饰要用薄纱做最繁复的样式,珍珠翡翠也必不可少。
盈绿如同潭水一般、镶嵌在手杖上的晶石是她作为钟塔学徒的象征。
“你叫塔恩。”
“我来自南方的切斯特家族。”
“我们将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我们的家族将为我们自豪,你是我切斯特的塔恩。”
镜中模糊了面容的男子做了一个标准的骑士礼,向身着礼服的塔恩发出邀请。
镜面泛起涟漪,一群妇人在宴会中窃窃私语。
“希别克就只有塔恩了。”
“衰落的希别克出了一个天才塔恩。”
“她将来一定是一名优秀的魔法师。”
“希别克因为她而崛起。”
“塔恩.希别克......”女子歪着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手杖掉落在脚边。
“希别克的塔恩......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串串珠链被女子扯落在地。
“切斯特的塔恩......”
咚!咚!咚!
是学堂的钟声。
“塔恩,宴会就要开始了,可别让大家失望!”
镜中伸出骑士附着着手甲的双手。冷冰冰的触感包裹住她的双手。
“快走啊,跟我切斯特一起。”
咚!咚!咚!
“塔恩小姐!塔恩小姐!”
一声呼喊将她唤醒。
塔恩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少年浅蓝色的秀发。
“塔恩小姐,你怎么跑到我们的货仓里睡觉?”赛楠完全想不到到货仓里取货会碰到塔恩。
“果汁。”刚醒来的人迷迷糊糊吐露出话语。
“什么?”赛楠听得不太真切。
“开店大吉。”塔恩将一枚钱币放到赛楠手上。
“好嘞!我们的果汁一定让你满意。”
商队在庆典上做的果汁生意,似乎还不错。
塞恩如是想到。


邻里间都公认,埃尔维斯·福克纳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这种安分并不仅仅体现在他平日循规蹈矩的作风当中,还体现在他每天几乎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上——曾经有好事者试图完美地按照埃尔维斯的日程表生活一个月,以证明此人能有今日的优渥生活主要是靠运气,与他本人严苛刻板(或者说,努力上进)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关系。最后此人仅仅坚持了三天便放弃了,并发表感言:怎么会有人数年如一日地过着这种枯燥又疲累的生活?日子里一点有滋味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不管尝试过的人是怎么发牢骚的,这都侧面证明了一点,埃尔维斯·福克纳尽可能循规蹈矩地重复着的是一张日程排得过于密集的无聊时刻表。邻里间的人之所以会将之当做“福克纳安分守己”的例证,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埃尔维斯和他的店附近,时刻都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因此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清楚地知道那张时刻表上显然没有包括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也没有给类似的事情留下任何空余时间。
只是在邻里间,与“福克纳安分守己”这一条一同被公认的,还有“他性情有些古怪”这一点。人们因此不是很愿意与他交往过密,只维持着礼节上没什么错处的普通关系。这并不很难理解:像是埃尔维斯·福克纳这样的一个成年男性:身材算得上高大,面容称得上俊朗,银白色的短发与烫金般的虹膜都因少见而显得神秘。除此之外,他的四肢俱在,头脑明晰,最重要的是,此人坐拥一间定价颇高的炼金用品店,毫无疑问地颇有家资。这样的人正常来讲是不应该数年如一日地过着那种苦修士一般的生活的。
街坊们在他搬来这个街区后的几年中不知几次地议论过,福克纳已经到了该娶妻的年纪了。也不乏年轻漂亮的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一次又一次从那间店的门口走过,或暗示或明示地表示自己对炼金商店的女主人一职抱有兴趣,但就是没有结果。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他也合该在余暇的时间里往酒吧之类的地方转一转,喝喝酒,打打牌,甚至做些寻花问柳的事情——倒不是说这些是好事,只是一个正常人总得有些打发时间、愉悦身心的爱好。如果大家都知道埃尔维斯会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便只是个享受单身的浪子,算不上有多奇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埃尔维斯不这样做。
除了进货时或者有必须要出门完成的工作之外,他几乎从不踏出店门一步。哪怕是贵族小姐的禁足也没有这么严格。
这些足以证明埃尔维斯·福克纳确实是个性情古怪的人。但人的思维又很奇怪,当人们见到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时,如果这种怪异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这个古怪的人的来到会显而易见地对整个社群产生益处时,他们便愿意接受这一点奇怪的地方,并擅自为这个人不合群的地方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这条街附近的人为埃尔维斯找到的理由是当事人本人脖颈上明晃晃的那一圈烙痕——瞧啊,法师被封魔逐出钟塔后留下的痕迹。很有趣的是,说这些话的人没一个是法师,没一个曾经从自己的手指尖上释放过半个法术,也没一个在拥有过那样的能力之后又被剥夺了念诵带有玄奥力量的文句的资格。但他们依然会因此露出怜悯而遗憾的表情,摇着头轻叹“也难怪”,并在埃尔维斯本人不愿提及个中具体缘由时表示理解——就好像他们真的明白什么似的。
至于埃尔维斯·福克纳本人,虽然在暗地里会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但鉴于邻里间的这种风评对他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于是并没有去刻意纠正这些人自以为是的错误认知:
他之所以像现在这样“性情古怪”,并非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
或许可以说,他天生如此。
***
埃尔维斯·福克纳那“严苛刻板”的日程表,是从每天清晨五点钟水壶的尖叫声里开始的。
这种会用锐利的哨声提醒主人“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虽是从黄金之家当中走出来的,却并不是什么炼金产物。只消听说过其中简单的原理——水烧开的蒸汽穿过壶盖上的哨子,发出尖锐的哨音——的人,只要是稍有水准的普通工匠也能轻松制作。当然,价格显然会高一些。至少是足以让一般的平民家庭在购入一只后,向左邻右舍炫耀一番的程度。
不过,对于能够堂而皇之地把炼金用品店开在闹市区的埃尔维斯·福克纳来说,不论在能力或是财力上,都自然比“稍有水准的普通工匠”或者“一般平民家庭”高出很多。因此于他来讲,水壶本身没什么特别的。让水壶在恰当的时间尖叫起来充作闹铃的行为,也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炼金小把戏而已。
虽说要是按技术含量来衡量价格的话,后头的那部分显然比前者贵了十几倍,但这间房子里是由主人埃尔维斯·福克纳说了算——他觉得无所谓,那么这就是无所谓的事。
一般来讲,说了算的福克纳先生不会让水壶的尖叫声持续超过一分钟。他的睡眠不算很浅,但也总是能在壶盖的哨声响起来的几秒钟之内清醒过来,然后同他那只每日里准时开始加热的炼金炉台几乎一致的响应速度从床上起身,关掉已经完成了今天使命的炉台,让尖锐的哨声缓缓平息。
这种行为不论寒暑,每日如一。不论前一天夜里埃尔维斯·福克纳是在几点钟睡下的,他都会固定在次日一早五点钟的水壶尖叫声中醒来,分秒不差。这种毅力有些难以解释,几乎让人怀疑驱动这个人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意志,而是同那只炉台一般机械而稳定的炼金程式。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埃尔维斯的程式里显然还写了“只要从床上起身就算是醒了”、“只要醒了就得开始一天的工作”之类的东西。这人从来不睡回笼觉,在每天例行的“关掉炼金炉台”这个动作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洗漱、穿衣,准备早餐等等环节,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开始运转起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就仿佛他对这样的规律有什么偏执一样。
但这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值得称赞,故而也从未有人试图阻止他。埃尔维斯得以数年如一日地在清晨五点钟起床,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打理好自己并吃好早餐,然后下楼清点货物存量、做营业的准备,在八点钟准时把开店的标牌挂在门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店主出门的安排的话,“福克纳的店”就会在除周四之外的其他任何时间如此运行。
今天不是周四,所以“福克纳的店”一如往常地在八点钟准时开始营业。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间单从名字来看完全搞不清具体是卖什么的商铺是个炼金用品店,这就已经证明了店内的商品定价不会是家境普通的平民负担得起的。所以,这家店平时虽算不上门可罗雀,可人头攒动的景象也从来不曾出现过,会一动不动地杵在外头等着开店的人自然也少见。
不过这一天里有一个,只可惜不是客人。
“狗男人。”这位栗色长发,生着青黑色的不对称双角和尾巴,面上零星缀着龙鳞的佣兵女性风尘仆仆、显得有些狼狈。她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台阶上开了门、正拿着标牌准备往门外挂的埃尔维斯,“我回来了。”
饶是性情古怪的埃尔维斯,在这个过于冲击性的称谓下也不禁一时语塞。他那机械钟表般精准的日程表在此时此刻难得地卡顿了几秒,才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谁教你这么喊我的?”
这大概不是问话的好时机。任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位年轻的龙化症佣兵身上的疲劳已经快要溢出来了,几乎站在原地都能睡着。在这样的情况下,伊莱·布罗沃尔德自然已经没有精力进行多余的思考,只顺着埃尔维斯的话蔫答答地回答:“是斯黛拉。”
啊,当然是斯黛拉。埃尔维斯这么想。不然还能是谁呢?
他叹了一口气,伸手把门牌挂好,然后拉开大门,把这个有点脏兮兮的佣兵姑娘放进店里,同时还在一边说:“你怎么还信斯黛拉说的话?这不是什么好词。”
“我猜到了。”因为疲劳,伊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恹恹的,“所以我第一个拿你试试。”
“你知道这样讲话很容易惹人生气的,对吧?”埃尔维斯关上门,让深秋的寒风不至于一股脑地涌进温暖的室内,一边这样问。
这个反问句换来了伊莱莫名其妙的一瞥:“我知道,所以我先拿你试试。”她这样说,“你根本不会生气。何况,即便你真的生气了,你也打不过我。”
“本来我确实不至于生气。”埃尔维斯在门口拧着眉头说,“但在你加上后头那句之后,就显得我这样还不生气是不太礼貌的了。”
***
到最后,埃尔维斯还是没有生气,只是把这个风尘仆仆的佣兵小姐撵到了最顶上的阁楼去,叫她把自己弄干净之后再休息。
伊莱·布罗沃尔德勉强算是这家店里的帮工,或者跑腿,或者杂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她不是本地人,早年在荒野间长大,因此行事讲话都像是荒野间的狂风一般直来直去,也对人情世故之类的问题比较钝感,本人倒并没有什么坏心。
不好说是不是因为埃尔维斯清楚这些,才能有意识地在她做出一些令人血压上升的发言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又或者是他在这四年里已经习惯了这位几乎与野生动物差不了多少的佣兵小姐能造成的各种事故,并已经在这个过程里对所有叫人生气的事情麻木到无动于衷。不过确定的事实是,因为这个不会说话也看不懂气氛的毛病,伊莱在银顶城中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长期相处的朋友。所幸她在荒野中早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因此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熬的。
只是这样的缺陷自然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不便:伊莱·布罗沃尔德在四年前决定离开荒野,来到银顶城,然后立刻就因为不通人情(换句话说,很好骗),经历了一些很难说是故事还是事故的波折,最后幸或不幸地被埃尔维斯收留下来,在阁楼上原本被用作杂物仓库的一小块空间里得到一张床。
再然后,这位纯天然野生的荒野猎人与城里土生土长的炼金术士之间当然发生了一些包含经济损失在内的龃龉,以致于那段时间的埃尔维斯很少见的一整天都愁眉苦脸——但他最终还是没把这个可以说完全不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人从自己的店里赶出去,于是见过那段日子的人,没有不觉得福克纳先生心善的。
两位当事人都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伊莱是觉得没必要管其他不相干的人怎么想,反正碍不到她的事;埃尔维斯则是因为,旁人这么想对他平静的生活也是一种利好。
事实上,这种“收留”只是单纯出于一种利益交换:埃尔维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伊莱在银顶城生活的基础需求,包括提供少许薪资、简单的三餐和一个睡觉的地方;相对的,伊莱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埃尔维斯做事,以劳务来支付这些待遇。这种简单的利益交换中并不带有任何善恶倾向或者感情色彩,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哪怕四年后的今天伊莱的栖身之处已经从一片硬木板进化到一个阁楼上温馨的小房间也是一样——这只表示,被雇佣者的价码提升了。
总而言之,伊莱就是因此成为了炼金商店的帮工,或者跑腿,或者杂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平日里她为这家店做的事情与这些“职位”倒也相称,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会接受其他的、“更加佣兵”一些的工作,只不过那是另外的价钱。
除开在店里打工之外,她也在余暇时间里频繁地拜访下城区的黑山羊酒馆,打听消息(成果存疑),接取合适的任务,然后在需要离开银顶城的时候头也不回地把埃尔维斯和他的店扔在一边。不过本来,在伊莱到来之前,“福克纳的店”已经单靠店主一个人毫无差错地运转了两三年,一位帮忙的佣兵潇洒地离开几天对埃尔维斯的营生并没有什么可见的影响。
在这种双方默认的生活方式之下,埃尔维斯早上一开店门就看见一个做私活回来的风尘仆仆的伊莱,其实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也正是因此,他才会因习以为常才从容不迫地将当事人赶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去休息。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伊莱稍微离开几天对商店的营生并没有什么可见的影响,店主也无意探究对方是为什么离开的,又在离开的那几天里具体经历了什么。埃尔维斯的好奇心向来如此匮乏,这在与伊莱相处时令这位自由惯了的佣兵小姐感到舒适,但对于一个炼金术士来讲则有些要命了:他在炼金术一道浸淫近十年,只学习、吸收了他人的经验与技术,自己从未开发出任何完全属于自己的配方、公式或者铭文。学术上的毫无建树让他在黄金之家籍籍无名,不过他本身也并不在乎,反正他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让他的商店长期盈利了。
没有独创技术并不代表没有独创产品。埃尔维斯显然是更加擅长截取、拼接,优化他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长地制造自己的产品的那种术士。福克纳的店所出售的东西总是与其他炼金术士做出来的同类产品相比占点优势:或者更结实耐用,或者更便于携带,或者装饰得更为华丽、符合贵族的品味,或者操作上更为简单、适合完全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大老粗佣兵。
这让店里的营收总体而言一直稳健地上升,直至被埃尔维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大产能所限制。事实上,最近几天里,他一直在为了赶工一批节日用的炼金小彩灯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枫华庆典在即,主办方需要大量的类似装饰,因此委托了许多承接制造类似产品的炼金术士。倒不是说工期多么紧,或者银顶城中除了福克纳之外没有其他人能批量做出这样小得可以挂在绳子上的精致炼金彩灯,只是在计件工资的诱惑之下,怎么会有人拒绝多赚一点呢?
也并非没有人试着劝他收个学徒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来提高效率,但都被当事人以“伊莱这么一个帮工就够我头痛的”回绝掉了。所幸,肯出言劝说这些话的人往往都已经与埃尔维斯有了一定的交情,而与他有了一定交情的人又往往会听过邻里间的那些风言风语,将他如此的回复与他古怪的性情,乃至脖子上的那圈烙痕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又不像是伊莱——他们自认为是“文明人”,当然看得懂气氛,于是这些人总会在自己臆想中的那种气氛里点点头,再不做声,就此让这个话题无疾而终。
这就是埃尔维斯·福克纳不去纠正那些人错误的想法所带来的好处之一。
***
当日的营业乏善可陈,只陆续有几波佣兵打扮的人进来,都是问野营用的暖炉怎么卖。埃尔维斯不冷不热地招待,来的人也不咸不淡地挑拣,最后只成交了一笔,卖给了装备看起来最齐整的那个。鉴于佣兵大多更倾向于把钱花在自己的武器和铠甲,而非生活用品上,这是福克纳的店里的常态,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除此之外,就是庆典的主办方派了人来,按照之前商定好的数量查验小彩灯的质量并结算尾款。交割很顺利,对方表示这次合作非常愉快,如果还有类似订单的话,将会优先考虑埃尔维斯的商铺。对于市政、大商贾或者贵族这类花钱只为图省心的客户来讲,这也是福克纳的店里的常态,因此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真正值得一提的部分在五点钟商店打烊后:埃尔维斯刚刚掐着点换掉了门外挂着的牌子,关上门,还没来得及落锁,店铺的大门就被一股相当大的力气从外面猛地推开了——差点撞到可怜店主的鼻梁。
一个生着银白色的单侧旋角,有着晨光般青白短发的女性就站在门口,那张龙化症带来的鳞片也无法遮掩其美貌的面孔上一如往常地带着那种雾气般捉摸不定的微笑:“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埃尔维斯还能怎么说呢?只能在心底暗道一声晦气,然后请她进来——根据经验,将这个女人拒之门外是没有用的。她几乎要比埃尔维斯本人更加熟悉这家商店的一砖一瓦,乃至每一个可潜入的缝隙。如果在她的面前关上大门,她只会为自己寻找,或者创造一个别的入口,在进来的同时更带来一些无谓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斯黛拉·格林温尼斯。是那位前些天里教伊莱用“狗男人”来称呼男性并绝口不提这相当无礼的斯黛拉;是在四年前怂恿初来乍到、还不通世故的伊莱给埃尔维斯造成了更多非必要经济损失的斯黛拉;也是在更之前一点的时间里、伊莱所经历的不知故事还是事故的一连串波折当中担任另一位主角的斯黛拉;更是埃尔维斯自幼相识、又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将孽缘延续至今的斯黛拉。
虽说本人坚称自己只是“稍微有点自我中心,又稍微有点自由自在”而已,但这些自我申辩并不会影响到别人对她行为的评价——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坏女人斯黛拉。
总之,坏女人斯黛拉成功通过和平的渠道登堂入室,耀武扬威地自顾自发表了自己的莅临让这间平民店铺蓬荜生辉的开场白,并颐指气使地叫埃尔维斯端出待客的热茶来,随后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往二楼的贵宾室走去。
埃尔维斯无奈地长叹一口气,重新关好门,插上门闩,认命了一般也跟着上了楼。等他穿过二楼安装的诸多定制家装类炼金道具的样品,来到专为接待有身份的大客户而设置的贵宾室门口时,斯黛拉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最当中的那个待客用的昂贵真皮沙发上了。
其实论理,斯黛拉的血统倒也值得埃尔维斯启用这间贵宾室。格林温尼斯在银顶城中也算是排的上号的老牌贵族,其中数位家族成员也在戴诺斯钟塔的校史当中留下过自己的姓名。如无意外,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斯黛拉本应成为一个让这间贵宾室的格调配不上她的贵族大小姐,即便做不了法师也合该成为骑士——但很可惜,现如今她头上的角与身上的鳞已经明晃晃地将残酷的现实昭示了出来,上述一切的光辉坦途已经在她十九岁那年症状出现端倪时被毫不留情地截断了,成为一个她原本不放在眼里龙化佣兵反而成了最好的出路。
若是一般人,或许会像把埃尔维斯的性情古怪归因到他脖子上的那一圈封魔烙痕上一样,将斯黛拉现如今的横行无忌与她的未来被龙化症唐突粉碎联系在一起。不过,就埃尔维斯在这个话题上可以与斯黛拉相提并论这一点看来,他并不算是一般人,因此他清楚,这个女人现今如此行事与她为了活命被迫逃离家族乃至她的龙化症都毫无关系,她这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她天性如此,打出生起就是这样的人而已。
他与她是极为相似的人,否则二人也不会在尚年幼时仅有一面之缘的情况下便沆瀣一气。这点化学反应归根结底不过是物以类聚罢了。
只是当年的斯黛拉毕竟年幼(她比埃尔维斯小四岁),破坏力有限,因此比成年之后更加具有一些欺骗性;那时的埃尔维斯也还不够成熟,还不懂得世事无常这个道理,盲目地认为格林温尼斯森严的家规足以束缚这个托生在貌美女童躯壳当中的小恶魔,于是毫无芥蒂地与她狼狈为奸。等到他意识到为时已晚的时候,自然已经追悔莫及了——孽缘的种子已经种下,自此后,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就在似是而非的朋友和模棱两可的敌人之间不停地无序震荡。
在876年深秋、枫华庆典前夕这个时间点,斯黛拉与埃尔维斯的关系还是偏向轴线上“朋友”的那一侧的,因此商店的主人最终还是屈尊端出茶具,为前贵族小姐现龙化佣兵倒上了一杯白水,顺便嫌弃地表示:“没有茶给你。”
“没有茶?”斯黛拉带着笑意反问,每个音节里都透着十成十的“我不信”。
“不是没有茶,是没有茶给你。”埃尔维斯在这位不速之客的对面落座,摆出一副毫不退让的姿态,“要知道,我正在牺牲自己的时间坐在这里陪你聊天,每分每秒都在耽误出货的进度。我建议你有话快说,不然我会按时间收费。”
二人之间有着经年的孽缘,故而斯黛拉自然也是清楚埃尔维斯那个堪比苦行僧一般枯燥无趣的时间表的。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他会在商店打烊之后再次清点货物的数量,然后根据需求开工新炼制一些相应的核心部件,然后在白天店里没什么人的时候完成那些剩下的“有手就行”的简单拼装工序。这也是店主嫌弃客人“耽误进度”的主要原因。
换个一般人在这里,或许就会在埃尔维斯浑身上下都写着“快滚”的气氛当中识相地迅速说完自己要说的事情,然后告罪一句便匆匆离开。但斯黛拉不是一般人,她显然非常有在别人不愉快的区域中跳舞的能力和兴趣。于是,这个女人反而相当放松地靠在沙发背上,一副要久坐的姿态,揶揄道:“那么赶做什么?或许别人不知道,但我清楚,你早就挣够了足够你挥霍一辈子的钱了,还会在乎自己多卖少卖的那一两件东西吗?”
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埃尔维斯在乎的不是那一点,他的主要目的是把眼前的这尊大神赶紧送走。而在场的人又都清楚,在这一点上详细辩解的话是起不到埃尔维斯想要达到的那种效果的。于是炼金术士冷哼一声,顺着佣兵的话往下说:“或许在你看来,是这样的。毕竟你满打满算只剩十年左右的时间好活,当然会按这个期限来规划其他人的财产与支出。”
虽说这两人间互放狠话也算是正常情况,但这句话的攻击性也依旧过于强了。斯黛拉的面上还一如既往的笑着,但天青色的瞳仁间已经渗出了冷意:“是什么叫你产生了这种错觉?难道你觉得自己的命会比我的长很多吗?我倒不介意做个善人,就在今时今地身体力行地叫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斯黛拉,你今年二十八岁。”面对死亡威胁的埃尔维斯毫不露怯,反而倒打一耙,“在这个年纪里,你也应该明白有些话揣在心里比说出来更合适的道理了。”
龙化佣兵嚯地自沙发上站起身来,铿地一声抽出了腰间的细剑:“难道这话不该我对你说吗?”
但她终于还是没把剑尖指向埃尔维斯的面门。阻止她的是自脊背一直攀上后脑的一股寒意,这种奇特的、昭示着危险的预感在各种场合之下很多次救了斯黛拉一命,因此,她会无条件地顺从这种难以言说的预感。
她顺着自己的直觉向着贵宾室的门口瞥去,在见到伊莱被隐藏在黑暗当中、因龙化症而微微反射出绿光的双瞳时,反倒生出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原来如此,你的小保镖回来了,怪不得说话这么硬气。”斯黛拉嗤笑着,用力将自己的细剑插回到刀鞘里,故意让二者之间刮擦出刺耳的声音,“就不怕我们俩真的在这儿打起来吗?且不说你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我知道你其实不在乎这个——单就打坏这间屋子给你造成的损失,你能接受吗?”
她几乎是咬着牙,把下一句话从齿缝间碾出来的:“毕竟你一介平民,想迎合贵族的品味攒出这么一个房间,很难吧?”
这话问得埃尔维斯有些莫名其妙,但他很好地掩饰住了这种莫名其妙,平淡地做出了合理的应对:“如果真的变成这样了的话,我会把账单寄给马提亚尔先生。我非常确信这位体面的老爷是不会漠视自己的侄女儿因肆意妄为而给无辜群众造成的损失的。”
——奥卢斯·马提亚尔,斯黛拉·格林温尼斯同样受龙化病所苦的远方表叔。拜他们之间经年的孽缘所赐,埃尔维斯很清楚,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制住斯黛拉这个无法无天的女恶魔的话,那就只有马提亚尔这位真正仁善体面的老先生了。
果然,在听到自己表叔的名字时,斯黛拉的表情不自然地僵硬了一瞬。虽然她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让脸上的微笑重新回到原本那种雾蒙蒙的、叫人看不分明的感觉当中,但埃尔维斯很清楚,至少在今天,此时此刻,她已经歇了自己四处捣乱的心思了。
“行吧,今天就算你赢。”斯黛拉总结陈词道,“但只是今天你赢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话对埃尔维斯来讲不痛不痒:难道没有今天的事情,她就会放弃来折腾自己、在自己身上找乐子吗?当然不会。对他来讲,这只不过是一句“你的生活还会原汁原味地进行下去”的预告,听来甚至令人身心舒畅。因此,他依旧端坐在原地,只是往忙着撂狠话的那一位的方向摆手赶客:“不送。”
斯黛拉哼了一声,昂着头转身,柔软的披风随着她的动作飘扬起轻柔的弧度。只看她的神态,她全然不像落败,反倒如同凯旋。她没有走向门口,反倒往临街的窗子那儿去了——这人今天来店里,就是为了给埃尔维斯找不痛快的。哪怕现在她略输了一手,她也坚决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
当在场的人都意识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窗子被打破的一声巨响,及接下来玻璃碎片落地时发出的叮当声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斯黛拉敏捷地跳上刚刚被她制造出的那个出入口,半是成功给埃尔维斯添了堵的满足,半是觉得少了些旁人尖叫作为调剂,令她的这个行为本身少了些滋味的失望。
她在房间内的一片寂静中从二楼跳到了街上。这里多少也算是个主干道,傍晚的街上仍有行人,因此这一举动令四周路过的无辜者连连惊呼,多少满足了小恶魔的一点虚荣心。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再次计上心头,回过身去,冲着福克纳的店二楼上的那个空荡荡的窗口喊道:
“要是你敢把账单寄到家里,我就把自己在庆典上的所有消费全都寄给你!”
大喊大叫是真的很解压,不论喊的是什么。再次这样意识到的斯黛拉好整以暇地在深秋傍晚的寒风中裹紧自己的斗篷,叫寒气不会挤进她因为病变而不得不穿得单薄的衣服里,才终于心满意足地走了。
***
“等定损之后,我们把账单送给马提亚尔家。”埃尔维斯看着贵宾室中的一片狼藉,认命地准备去拿工具开始打扫。不过在他真正离开之前,还是转过头去,向门外的伊莱确认道,“你还记得那位先生住在哪里,对吗?”
睡饱了的,干干净净的伊莱点了点头,又迷惑地看了看那个正呼呼地往屋子里灌冷风的大窟窿,提问:“可她不是说,如果你把账单寄过去,她就要把她在庆典上的所有消费全都寄过来吗?那可不是个会给人省钱的主,修窗户的价钱肯定更便宜。”
“难道你还天真地以为,我们不把窗户的账单寄过去,她就不会这么做了吗?”埃尔维斯没好气地说,“我把账单送过去,只不过是要告诉马提亚尔先生一声,他的侄女儿又仗着别人打不过她在外头作威作福了。至于她在庆典上的消费,就当是我花钱买她倒霉。”
“你不在乎具体的花费吗?”伊莱追问,“我这次给商人当了护卫,他们好像都很在乎这些,拼了命地想要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要花很多钱才能得到一点好处,那他们宁可不做。你也是商人,你不这样干吗?”
这话稍微有点词不达意,但四年的接触让埃尔维斯可以顺畅地理解她的意思,并在此后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所以我算不上商人,只能算是个卖灯的。”他说,“要是我真的像一般的商人那样在乎什么钱不钱的,当初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你扔出去。”
这是在翻当初伊莱初来乍到时毁掉埃尔维斯整整三批货的旧账。但不论是说话的人还是闯祸的人,现如今都一副理直气壮浑不在意的样子,因此这个话题没能被深入延伸下去。
他们在沉默当中清理了一地碎片,然后用几块木板勉强堵住那个巨大的窟窿,但木板的缝隙之间依旧在不停地漏风。埃尔维斯看着这个贵宾室墙面上丑陋的补丁,再次长叹了一口气:且不说它多么有碍观瞻的问题,单说银顶城深秋的冷风会从木板间的缝隙当中坚持不懈地钻进来这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房间里的温度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哪怕他多少也算个暖炉商人,也得为原本规划好的取暖用火耗精打细算一番。加之庆典在近,各行各业都在向城中心的集市里集中,想来能修缮房屋的工人近几天内都在为那边的临时店面忙碌,很难腾出手来,为一个普通的炼金商店安一扇新的窗户。
“不如这两天干脆把店关了吧。”埃尔维斯说,“反正枫华庆典期间,这么干的店铺不在少数——你来银顶城四年,是不是还没去过庆典上的集市?”
他的后半句话是冲着他的帮工说的,而其中的言外之意,甚至连这位跟野生动物比也差不了多少的女性佣兵也能心领神会。
伊莱立刻点头如小鸡啄米一般,然后反问:“老板,报销吗?”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