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在剧院舞台上见过的芭蕾舞首席女演员光着脚,踩着碎瓦残砾朝我冲过来,用口型大喊道,“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我听不见她的声音。除我之外的世界一片寂静,而我的神经、我的血管与我身体之内的一切在寂静中发出阵阵轰鸣。
是了,数分钟之前一颗炸弹就在我们近旁爆炸,现在我除了耳鸣之外什么都听不见。
应该赶快逃跑,毫无疑问。我自动跑了起来,披肩一角掀动着划过视野的角落。黑白相间的花纹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莫名的恶心感浮上来,五脏六腑好像都胀住了一样。心脏加紧泵出血液,我在平缓的下坡路上持续奔跑,皮肤表面的温度不断升高,我在无声的世界里几乎脚不沾地地奔跑,好像在期待什么,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
一个地势低下的广场里挤着许多人,大约聚集了几个街区的住户。中产阶级模样的男女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神色如常地交谈,或者打着手势激烈争论。
广场中心随便搭了一堆帐篷,走过去依然是一路下坡。周围的人群陆续开始轮流高举手臂形成人浪,当我钻进帐篷时这一活动已经变得极富秩序。
帐篷里是另一位为观众熟知的女演员,担任过许多歌剧的主演。我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席地坐下,专心盘算着如何向她索要一个签名或者几页原始台本。这里有纸笔吗?我不经意抬起头,看到她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已经写好了一个名字。
太幸运了,我想。
……等等,那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和……一个被揉皱的六芒星。
她接住我惊讶的视线,勾起唇角报以一个微笑,然后不再看我。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听觉已经恢复,人浪的动作开始伴随有节奏的叫喊,从外面压迫着这个小小的帐篷。一股深刻的恐惧攫住了我,使我动弹不得,我徒劳地盯着她修剪好看的指甲,心里什么都没想,只有血液在冲击般地奔腾,合着人声的节奏,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肩膀到指尖一片冰凉。
大脑还没能理解视网膜上映出的天花板。
我迷茫地抬起一只手,注视了好一会,这只手的影像和刚才那个记忆尚鲜明的画面交替出现,交叠几次之后终于固定下来。
没有圆润的长指甲,也没有泛光的指甲油,周围的空间里只有自己,和一双极其普通的手。
认识到这件事之后,全身慢慢地放松了。心脏还在卖力地跳着,塞回被子里的双手开始回温。阳光从天鹅绒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给室内铺上一层均匀的薄光。看得出天色已经大亮。
人类意识之海的深处沉睡着恶魔。恶魔不属于人类本身,它是一团巨大的蛛丝,缠入人类诞生以降各种黏黏糊糊的人际关系的沉淀,以基因以外的方式被代代继承。仇恨,战争,血与火,无论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它们都会在梦里不断闪现。就像刚才的梦境,虽然十分凌乱,但它所象征的事件一定真实地发生过。
那样的恐惧,甚至更深刻的恐惧,也一定真实地发生过。
在历史的某个节点,或者说,所有的节点上。
刚才的噩梦持续了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三秒钟?
恰好在大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将要开始思考答案之前,抓住那一点停顿的时机,潜意识向空白的大脑抛出了一个名字。
“奈特妮丝……”
无意识的呢喃几乎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奈特妮丝是谁?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昨天早上,不是从别的人那里,而是来自自己脑海中的声音。虽然昨天因为早起而低血压,脑子一整天都不大清楚,但今天一回想,立刻意识到其中包含的意义。
作为神秘体验而言,“脑海里响起不属于自己的声音”实在太典型、太明显,与小概率事件的巧合不同,既明确地超出了常识范畴,又在客观上留有怀疑余地。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是说现实中不会发生超自然事件——也有其他看起来更科学的理论可以聊作解释。
无意识中的沉淀极其广袤。比个人无意识更深层,两者深度好比地壳与地幔。我们所称的“自我”,即人类,都浮在地壳之上,过着我们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我们所称的潜意识像大地一样,是肉眼所不能及的混杂,源源不断地向地表翻上资源。而在此之下,视野之外,炙热的岩浆蠢蠢欲动地翻滚,酝酿着彻底的毁灭之源,也酝酿着炽烈的热情之源。无意识之火在所有艺术中跃动。
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领域。
无论是广为人知的神话原型还是微小的意象碎片,多少都会在世界文化中留下蛛丝马迹,恐怕奈特妮丝这个名字也是。这样如果查阅一些古代文献,说不定能找到它的出处,从而从相关背景出发,尝试解释自己潜意识的部分活动。
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这些事,宴拉开窗帘看向外面,发现今天也有几位邻居在公园闲聊。阳光这么好,一会儿出门散散步吧,说不定会遇到一两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与小姐,能够一起探讨一下这些想法呢。
……
不过另外那种可能性就是,真的有什么超自然的事情正在发生。
--以上正文--
OMAKE:
“请诸位不要迷茫……”
(现在唯一让我迷茫的就是这个谜之天之声。)
“请诸位勤于思考……”
(现在最值得思考的只有这个谜之天之声究竟是啥。)
*一切逗比吐槽与失败的装逼属于中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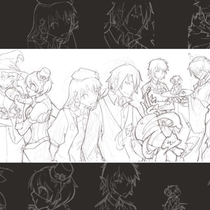
.
.
有一个乐天72黑巧的盒子被丢弃在地面上。
少年影魇停下脚步,就像所有的熊孩子一样、他用脚踢了踢那个圆柱形的盒子。
盒子里已经没有任何巧克力了、但是还是散发着甜甜的、工业世界的味道。
感兴趣的围着盒子转了一圈,Zaczof蹲下身用树枝戳了戳。
确认了他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盒子上的瞬间,一张大网悄无声息的在他身后展开。
小小的影子领主只来得及发出一个惊讶的单音就被巨大的渔网拖倒在地,想要撑住身体的时候胸口又被猛的一踹。
紧接着一只穿着白色长袜的脚就狠狠的踏上了他的胸口,被高跟鞋的鞋跟碾压的部分传来激烈的痛觉。
在逆光之中的是,轻飘飘的格子裙和染着极彩色的围裙,和指向自己的被宝石和雕花铺满的漆黑枪口。
绘空事看着被推倒在地的少年,浅蓝色的发丝噤若寒蝉的环绕着脸颊,蓝紫色瞳孔仿佛冻结长河一般毫无生机的冰冷,嘴唇紧紧的抿着。
“把我的东西还回来。”她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否则弄死你,死小鬼。”
两天之前还用能够当成礼仪范本的优雅温柔动作行礼的少女居高临下凶狠的说。
.
呜哇这位小姐今天魄力全开啊。Zaczof没有半点害怕的这么想着。
“小姐你丢了神马好东西呀?我也来帮你找找嘛~”
逆光的脸面无表情,踩在胸口的脚却又加了一分力,但是少年还是用惯常的戏弄人的语调说着话。
故意装出来的、小孩子一样甜甜的自来熟语调,对现在巧克力不足的少女来说只觉得神烦。
“美丽的小姐你看起来就不像会找东西的样子,但是人家可是很擅长哟~”
“怎么样呀~要借助我的力量吗可爱的小姐?人家只需要一个抱抱就足够了哟?”
一边说话还一边手舞足蹈的少年,终于让绘空事的头上成功冒出了数条青筋。
少女的耐心和巧克力一样用尽了、她瞬间扣下手枪的扳机!
然而那里没有预计会有的血肉飞溅,而只有子弹击中石板地冒起的青烟。
绘空事的耳边响起了懒洋洋的戏弄人的声音。
“这样的玩具可不适合你这样可爱的小姐哟,如果碰伤了手我会很心疼的呀~”
现形到少女身后的小小的影子领主用手指旋转着绘空事的手枪,说着足以被称为性骚扰的言语;然而他马上又分解了身体以逃过匕首的一击。
绘空事扭曲了表情,很不满的歪着嘴“切”了一声、将匕首向重新现形的少年掷去。
“好危险啊这位小姐!”装得好像要碰瓷一样的,Zaczof夸张的张开双手,“如果伤到我这张帅气的脸……呜哇!”
正说着话的时候、绘空事从身上又抽出一把小刀、然后是针、苦无、菜刀、镰刀…不用多久、这条无人的小巷就布满了刃物。
少年蹲坐在镰刀的刀把上托着脸颊、认真的看着用阴暗恐怖的眼神盯着他的少女。
“呜哇小姐你好厉害啊,带这么多不觉得沉……”
.
…总觉得有点熟悉啊。那两根呆毛…还有眼睛…啊。
Zaczof感兴趣的眯起眼睛。那个时候、的确是变成了尸体…虽然没有亲眼确认过,但是已经被分解到那种程度…
…所以那个大小姐才选上她的是吗……?!的确是个、有趣的旅行团呢…!
少年再次分解成影子,绘空事投向他脑袋的美工刀白白穿过了空气、和其他的道具一样不甘的落到地上。
再次聚合的时候,他贴着少女的耳朵,用低低的像影子一样的声音低语。
轻飘飘的、月影浮动一样的声音,在空旷的小巷里轻微的摇晃。
“…我想起来了…小姐的东西是在我手里没错。但是可不能白白给小姐你哟~?告诉我你的秘密吧、可爱的小姐?”
轻微的笑声、让人联想起浮动在暗影里的莲花,小小的影子领主用指尖卷起少女的一缕头发,作势像是要亲吻发尖。
Zaczof用暧昧的眼神看着绘空事,像恶魔一样诱惑的提问,用听到的人会献上祭品的甜美声音。
“…你为什么不会死呢?”
回答是反手刺向眼睛的尖利小刀,却和他的前任们一样只刺向了空气。
绘空事用冰冷的眼神盯着再次在不远处聚合的少年,双色的单瞳中看不出愤怒、却更显得恐怖,像是千里冻结夺走无数人生命的冰原。
“看来小姐你也不知道呢。”Zaczof看不出遗憾的说着遗憾,再次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唔~那、小姐、如果拿心脏来交换的话就还给你啦?”
他无赖的摊开手耸耸肩,用轻佻而戏弄人的玩笑语气说着可怕的话,
“不过我不想弄脏这身衣服,能不能麻烦小姐你自己挖出来给我呢?”
.
.
.
.
.
.
稍微被吓到了啊。
少年很感兴趣的研究着用魔力浮在空中的,十分钟之前还在少女身上的器官。
没想到真的会有人毫不犹豫的就能挖出自己的心脏…就算是不死之身也不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吧?
既然这样也没办法,遵守约定吧。
大量的、闪耀着高价光芒的宝石落下、填满了少女尸体心脏部位被挖出的空洞。
小小的影子领主在装着宝石的匣子上灌注魔力,记录下他的话语——
“不死之身的技术,我也很有兴趣。如果什么时候那段记忆启封、我愿以百倍珍宝与之交换——那么下次再见啦,美丽的小姐~”
.
“…咦、绘空事你换了个装宝石的盒子?”
“恩…是的。原先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抱着一盒六花亭的绘空事往嘴里填着草莓巧克力,周围浮动着甜甜的柔软气氛。
.
.
.
.
.
.
.
.
不知什么时候、Doodland开始流传起一个都市传说。
在河底有一个会说话的盒子、如果能够打开它、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当然、这是旅行团离开这里很久之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