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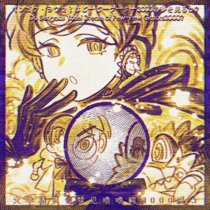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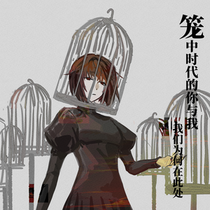



?陈述?
我提笔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基于演出的审讯已经结束,我被集团放回了位于街区的公寓,在那里进行半强制性的闭门思过。正是午夜十二点,缺乏睡眠的疲倦感来回击打着我的眼皮,但大脑却不愿意让我睡下。
我在无灯的走廊里徘徊,意识到继续让自己入睡是一种折磨,于是就起身回到了书桌前继续修改我的艺术陈述。在写作时,我听到公寓隔壁的阳台上传来均匀的风铃敲击声——在我受审时,邻居家似乎已经换了住户,我于是没去打扰。
自由后的这个夜晚让我感到陌生。我同时清晰地意识到,今后的每一个夜晚都会让我感到陌生。
夜晚于我将会变成一种清醒的酷刑,无论如何,痛苦总比让思绪溜走要来得更好。
我于是开始写作。
最初开始创作的动机相当的简单,我同这时代大多数人一样,诞生于集团所管理设立的养育院,是集团所培育的人工胚胎产物;也同这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并没有所谓的“父母”。
在育儿所里我接受了基础的教育,慢慢长大了。大抵是为了方便在成年时进行的职业测算,又或是完成某种指标,大部分的育儿所在最初的几年里都会为儿童进行多种不同方向的培训。
“舞蹈艺术”……这是我最初接触了行为艺术的契机,早期的行为艺术可以说与表演艺术、舞蹈艺术紧密相连,甚至说是托生于达达主义的舞蹈表演也不为过。
可实际上,我的舞跳得并不好,即便是一向持鼓励态度的老师,在看到我的舞之后也说:“虽然跳得很用力,但动作全错了,奈同学就不能看着我的示范跳吗?你再这样我就要让你去那边罚站了,该认真点。”
我否决了,并不是因为不想跳着和所有人一样的舞,而是因为我的舞蹈就是正确的。但老师并不这么想,她坚持让我复制她的一举一动。我抗议道:“我已经努力了,如果只是完全重复老师的舞蹈,那不就只是乏味糟糕的健身操了吗?和舞蹈有什么关系?”老师笑了起来,但还是让我走出教室。
我从此有了充裕的时间。当你脱离集体,不再沉湎于规则所制定的“常规日程”的必要性时,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时间是如此的充足。多数时候,我在图书馆里看书——养育我的那家育儿所还留有一栋旧时代的纸质书图书馆,现在已被拆除,用作游泳训练。
集团似乎认为人的才能主要来自于基因和与之配合的教育,但如果问我构成人格和才能的东西是什么,我会说是许许多多的巧合层叠而上。在那家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十分奇迹的留有关于行为艺术和在两次旧世界大战前后艺术史的书籍,我全部读完了,这就是起点。然后,我开始以我的朋友们为观者,向他们表演行为的艺术。多数的结果相当糟糕,说出来都有些招笑,这里就不再提及了。
在育儿所里,我认识了几个还算说得上话的朋友,但如今都不怎么联系了。不过,我还与同样被评定为超演算级的砂金红联络,现在仍维持着会向对方说新年快乐的关系。话虽如此,我也不知道这种同窗关系在发生“那件事”后是否还能长久。
如果要说我们时代的人有什么特性,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在这个被过度的演算人工构建的社会里,信仰已式微,亲情也已溺水,“我”和“你”之间相隔了过于过长、过久的距离。
社会不再具备鼓励点对点交流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相隔着系统、网络和屏幕,为何在交流并不需要成本的年代,交流反而正在消失?为何不再具备阶级的时候,人之间的距离反而越远?一些人将这种疏离归咎于人们过于仰赖身份,我认为对身份的信仰只是一种结果的体现。
因为这个世界不再有真正的神明,我们对“自己所在之处、自己所归之处”缺失的恐惧于是越发明显——说到底,如果没有神明和天堂的话,我们该归于何处?又该从属于何处?在信仰破裂的21世纪过去后,能够决定人命运的系统应运而生。为了缓解这种迷失的恐惧和痛苦,最初的系统能够成功运作,可以说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时局和集团的合谋也不为过。演算系统看似中立的表象,近一步促成了一种伪信仰式的迷信,这种盲目的相信和崇拜本质并没有任何精神乃至教条可言,只是人们放弃自我的产物。
结果是,正如“你”“我”所看见的那样,演算人生系统的出现导致的是人对自我的近一步割裂。在以往的世界里,“职业”构成了人们的“人格”和“身份”,人们却在演算系统诞生后被剥夺了这一点。
丢失了自我的集团社会下的人们,比以往都要沉默且孤独。因为人工智能审核机制地诞生,所有真正反抗的思想在表达出来前就已经消失。人们不得不学会那些隐秘地、不痛不痒的反抗方式,却也因此丢失了表达和交流的欲望。
在这个意义被高速迭代的电子化社会,语言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散,人格成了能随时替换的东西。不少人也鼓吹过人工智能伴侣可以解决这种情况,但实际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抚慰并不能解决这种失语的疼痛,而更像是一种麻药,只能缓解,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在大多情况下还会让情况更糟糕。说到底,为何人们总是期待整个社会依赖已久的药品没有毒性?这于我而言是未解之谜。
也正因如此,在这个原子化已久的社会里,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发生过多变革,因为“我”和“你”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形成“我们”。如果有,那一定是因为一个足以连接“我们”的“他”的出现。
在集团的语境下,这个“他”是系统、是数据、是主体由网络构成的监管,而在一般人的语境下,这个“他”是被寄托希望的面目模糊的连接者和破局者,在其真正出现前,都还没有具体的模样和名字。
——那么,“你”和“我”能回到最初的联系吗?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能互相感知到吗?作为观者的你,能注视我吗?能相信我吗?能理解我吗?能与彼此共享眼中的世界吗?
——这种关系,能成为新的“信仰”吗?
这就是我上一场表演,《静默中的我和你》的构想,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临场表演时演讲的内容,不过这里就不做过多展开了。
在我的预想中,那是一场在公开场所进行的行为艺术表演。所以在表演前,我向集团提交了表演基础的介绍和内容——任何形式的公众活动都需要经过集团的审批和采纳,否则便只能在画廊或是博物馆这一类“小范围内传播的空间”内存在,这点在集团的社会下已经是一种常识。
现在想想,那其实是败笔,在集团的容许下进行的反抗表达,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怀柔的表演、一种小丑般的玩闹独角戏罢了。
整个艺术审查的过程相当繁琐,一共进行了三次,几乎用了半年才成功落定。行为艺术表演本身就伴随着政治目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表演开始前的那次审查,我还被集团叫去安全保障部谈话。谈话者是超演算级的心理学家西寺惠,他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给人中性感觉的青年心理医生。
不知为何这段记忆相当清晰,在被集团的工作人员带到心理诊疗室的时候,西寺穿着白大褂问我道:“这位朋友,你马上就要开始进行表演了,如何,紧张吗?”
我告诉他我并没有太过紧张,毕竟在那以前,我就表演过多次了,人群带给我的紧张感,并不比过去每个个体带给我的多。
“但是,这一次表演大概会比以往的表演人都要多哦?真的没问题吗?对了,我在申请书上看到了你写的想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壁障,这个具体来说是怎么表现呢?我读申请书的时候,觉得这个构思很像我的工作,感觉会很有意思呢。“
我说我会在表演当天穿上镜面材质的衣物,然后在人群中引发互动。互动的开始时,观者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在那里就行了。这和申请书上的内容并没有太大区别。
“是吗?这听起来有点难懂啊,不过,我倒是能猜到,朋友你其实是想‘不需要做出什么,在场就是表达的开始、就是一种发言’,对吧?看你在申请书上写的东西,你似乎认为在这个时代传达本身已经无限接近于失效,有大量的人‘倾听’就已经成了一种‘表达’。”
嘛,不知道呢,如果把自己的所有构想都说出来艺术就没意思了吧。
“这种模糊对当局可是很头疼的哦?告诉我你的故事吧,我很乐意倾听。”
演者的故事就是没什么故事,如果有,早就作为艺术的素材吐露了。比起我的事情,我更好奇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为什么会穿白大褂呢,那种服装对心理治疗和审查都不是必须的吧?
“啊,那只是为了建立一种印象而已,这样更方便大家放下心来和我谈话。”西寺说,“就像朋友你也会通过服装建立自己是艺术家的印象吧?总之,希望你的演出能顺利按照申请书上的描述内容进行哦。”说这话的时候,他眯起眼,以一副相当人畜无害的神情注视着我,可是那双黑色的眼睛后却投来审视和观察的视线,我大抵已经猜到了他和他背后的集团的意图,这毕竟还是审查和警告。
嗯,当然了。我回答,然后就离开了审查室,继续准备表演。
之后的故事相当简单。我在演出中脱离了计划,稍稍做了点“即兴表演”,成果也相当斐然。具体的演出不在此处复述,因为这不是本篇陈述的重点,我想现在境外的网站和区块链上应该还在传播着那表演的内容。我也是之后才知道的。
说一下表演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发生的事吧。
那天上午所聚集的观者,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多些。大概是因为节日临近,加上天气意外的好,表演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在表演快要结束时,我听到了远处的人群中传来了尖叫声,随后人群就像水面下受惊的鱼那样四散而逃。画廊的助理让我拿上东西快点离开,不过那时已经晚了,我们租用的准备室里已经站了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之后的事都有点像电子游戏一样失真,我被戴上手铐,押送上警车,最后带到了自己并没有见过的陌生建筑里。一个穿着制服、态度冷淡的女警让我在房间里老老实实待着,不要轻举妄动,接着我又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然后是下一个房间、再下一个房间。期间,有好几个着警服的人问着我相同的问题,一直问到我有点听不太懂他们的意思。最后,我被丢进了一个除中央的桌椅和白炽灯外空荡荡的房间。
灯光亮得有些刺眼。
或许是有意设计成让受审者孤立无援的情况吧,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时间是漫长的,并没有人理会我的存在。我能听到门外有人在走动,步伐还很重,恐怕拿了枪,但并没有人开门进来查看我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人明面恐吓我。在房间里,白炽灯的光线仍在刺痛眼球。
等到我的思绪开始困乏的时候,房间里走进来一个衣着相当古典,留着长发的中年男子。那张脸,我曾在翻阅书籍和旧新闻氏见过,他比照片上的自己要年长一些,但整体的气质和风貌却没什么变化。
此时代并不缺少批评者,而缺少批判者;正如此时代并不缺少反对者,而缺少反抗者。岛津明成氏就曾是一位这样的反抗者,关于他的诸多事迹,以及鹿儿岛“争取”到独立自治区的历史,我曾经通过书籍和境外网站了解过。因此在集团请出他来到我的审讯室时,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他似乎并不意外自己被派遣来作为一个询问者,又或者说,集团需要一个调解矛盾的“和平大使”。至于集团的意图并不难猜到——让一个久负盛名的“反抗者”作为一个“臣服者”来谈判,本身就相当有劝服的力度。
我头脑的疲倦消失了,在对方开口之前便称呼对方为岛津氏。他似乎吃了一惊:“您很年轻,我没想到现在您这个年龄段的人还会认识我呢。“
是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吧,我小时候就在图书馆里看过您。啊,不过具体的事迹倒是之后道听途说的。我没想到集团会让您来问询我,那么您想问什么?
出乎意料的,岛津氏的语速相当平静和缓:“奈能大人……您的表演,是刻意违背了公开活动申请书的内容吗?或者说,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您在表演前就计划好的?集团似乎想让我搞清楚这一点,这会影响到您之后的审判结果。”
我们互相观察着对方。然后我说,如果我真的这么计划的话,我就会先问岛津氏你社会研究部的福祉待遇如何了。岛津氏温和又不置可否地一笑。我注视着他黑色的、如鸦羽的双眼,试图从中分析他与鹿儿岛的“故乡守护者”之间相隔的距离有多远。我不信任时间和强权,那么,可以信任“岛津氏”吗?我无法判断。
“那么谈谈别的事吧。”岛津氏说,“您是为什么要将表演的题目定为‘静默中的我和你’呢?“
我问他,岛津氏现在和我,我们中间相隔着什么呢?提示是虽然回答桌子和灯光也可以,但是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岛津氏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随后告诉我:“我年轻时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时,曾在一家法语剧院里看过一出戏剧,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萨特大师的《禁闭》……他的观点是,他人即地狱——只要被人的视线所观察,人就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无法正视自己的本质,不过,那是两个世纪前的看法了。”
嗯,岛津氏很敏锐呢。我们的时代和萨特的时代相当相似,在萨特的时代,冷战的阴云久久不散,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背负着不同思想的间谍,国家机器之间彼此怀疑且明争暗斗,文学家和哲学家们也是谍战的一环,萨特就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但我们的社会与加缪时代不同的是,自诞生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就是缺失的,植入的芯片过于轻易地操纵我们的思考和记忆,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代替了真正的交流,集团过多地介入任意两者的人生。就像我和你,现在在此刻交谈着,只是因为集团的演算系统横在我们之间。
“所以是‘我和你’吗……?”岛津氏抬起眼来问道,“我并不认同萨特大师的观点,以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看法似乎太悲观了。”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再说下去,那思绪就会成为系统和集团攻击我们两人的武器了。万幸的是,植入我们大脑的芯片虽然能观察到其刻录下来的记忆,却无法完全侦测我们的思想。
岛津氏又问了我一些其他问题,我意识到他应当仍是那个保卫鹿儿岛的英雄,可惜的是,我们在集团构筑的审问室里信任彼此,却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不久之后,岛津氏被一个工作人员带出了房间,另一个审问者被叫了进来。
砂金红在我对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她比上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又高了一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天她穿着矿工用的长靴吧。这回集团是想通过熟人劝说得出点结果吗?我看着红的一举一动,等她开口。
“你搞砸了。”这就是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大笑了起来。
嗯,我知道,所以你是怎么打算的?集团派你来审问我?我们是要开始一起回忆往昔了吗?然后我感动落泪、大声忏悔?
“打算……?”她停顿了一会儿,随后说道,“听不懂你的意思。我在网络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那是你的手笔,对吧。”
什么?
“不要装傻,尽早坦白从宽吧,再这样下去,集团会把你丢到社会研究部去的。那时候可就没狡辩的机会了。”红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希望我说点什么,“现在社交媒体上四处都在传播你那场带来麻烦的表演的视频,还有人用那东西做成了NFT,通过ai自动化铸造继续发行,这种失控的状况,大概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
所谓的NFT,是指在上世纪曾风靡一时的非同质化代币,通常以插画或视频一类的数位资产作为基础,收藏价值在于其艺术性和独特性。不过,这种代币早就成了经济泡沫的一部分,现在也只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几乎不具备什么持有价值了。
我问红传播的NFT里面有没有在元数据嵌入我的演讲内容,她没有回答,反而继续说了下去。
“那玩意都搅乱市场了,最接近原始视频的NFT拍卖出了惊人的高价,其余的则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病毒性地传播,更不要提随手把文件保存下来的人有多少了。你的目的也该达到了。拘捕的时间很短,你应该没机会做那些,你有同伙,对吧?他们在哪里,是谁?是画廊的人吗?你是怎么逃过芯片侦测的?”
原来如此。你并不是来看望劝说我,而是以集团的审问者的身份来的吗?但是为什么是质问我非同质化代币的事?
“我在挖掘方面很在行,恰好挖到了相关的信息而已。”
……哈,也是啦,我并不了解你。但是,我不能回答我没做过的事。你说的NFT什么的,在你走进这个房间之前我都还不知道呢。不过,这让你和集团很头疼吧?看来我的表演传播得很广,我为这意料外的状况感到高兴呢。
“别撒谎。”她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似乎是想辨别我话语的准确性。但正如我不了解她一样,她也不了解我。“这件事会很糟糕的。”她又说。
在你知道之前,它就已经很糟糕了。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啊。
之后又来了四五个人,逐一审问我所知道的所有细节,试图从我嘴里撬出点我不知道的东西。审问又持续了三天半,期间我每天有大概四个小时的睡眠,三餐只有基础的水和三明治。食物倒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平时就不喜欢进食,只是在入睡时时常能感觉到房间角落里的摄像头仍在运作。
但我不可能承认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在第四天的时候,我被集团的负责人从社会研究部释放了。当然,这其中免不了媒体的大肆报道和宣传,可我都是事后才了解到的。集团并未允许任何记者或是自媒体从业者与我见面,而官方的通稿早已准备好了。报道的实质内容只有三行字,来自各方的背书倒是洋洋洒洒。网络上此起彼伏的声音一片,但没过多久就淡化了,最后像大部分事情那样被人们遗忘,只听说以我为主人公的NFT还在地下市场不停地传播着。
除了缺乏睡眠、来自摄像头的监管视线和长时间的对话外,集团并没有对我做出更过激的“惩罚”。我想这一部分是律师和岛津明成先生明里暗里协助的成果,一部分是因为我终究还未越过那条“边界”,在舆论上拘留无法服众,所以过度的惩罚只会变成我的“创作素材”。
在一个关怀的社会这些惩罚似乎就已经能构成罪行,但在一个麻木的社会这些举措不过是人们每天在经历的,换言之——“你的发言权不重要,因为那是常态!”苦难叙事在表达上已经难以服众,我也清楚集团大概不会再给我公开表演的机会,更不会随意放任我的表演在互联网上传播了。这件事甚至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举措,在这个被人工智能所构建的社会里,一切都可以隐秘地达成。
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在踏进门的那一刻因突如其来的恶心痛苦流涕,扒在玄关的门柱上干呕。我头痛得厉害,就像有绣花针刺入大脑,直到喉咙开始干涩疼痛才勉强停止。我的思绪如同一团乱麻,几乎无法停歇地思考着过往的一切。
我想到许多。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是可以在玩弄概念中被否定的吗?我的道路是否也是演算的设计?我的思绪又来自于哪里?我的表演,仅仅是被允许的“安全演出”吗?我的天赋,也如这社会的大部分人一样,只是被程序“收编”的存在吗?
如果个人的呐喊对整体而言有计划性,那还是呐喊吗?兴许只是一种助兴了吧。
思考的疼痛感几乎要将我的大脑凿除。但如果在这里停下思绪,也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退缩。我于是向空空荡荡的房间内、那无名无状的假想敌喊道:
“……我将破坏你!”
没有回音。
少一个艺术家这个社会也不会怎么样,但如果多一个革命者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如此地惧怕一个表演,那就让这表演的存在成为你的眼中钉,肉中刺吧!来、来,注视我,轻视我,否定我,杀死我吧!
我不知道我还能维持这想法多久,或许只维持到天亮时。但至少此刻,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如此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