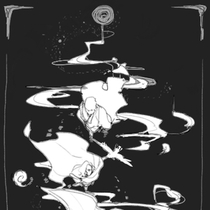架空黑手党paro,老唐存活结局。
想说大概就是“没有你,就没有世界”这种矫情的感觉。
死亡结局走http://elfartworld.com/works/70216/
“Dalle stalle alle stelle.”
“From the stalls to the stars.”
八月的星期天晚上。
佛罗伦萨的暖风仍旧吹得人面颊发红,夜色下红色地毯映照着仍旧绯红的天空,落山的太阳不再守护着这片阳光充沛的土地,黑衣与红裙混迹在软质的地面上,高跟鞋一脚踩碎黑头皮鞋所占有的空间。
日光还烧灼这大地,余温尚未从这片土地上退去。唐·璜隔着玻璃看了看窗外,回手整了整自己脖子上的领结。
“我得再跟你说一次,这不合适,这样真的不合适,这么正式!我几乎想揪掉领结破门而出了!”
“哦,但你不行。”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笑着说,“今晚大家不只是想认识那个风流贵公子唐·璜,他们应该更愿意看到费奥拉万蒂的得力助手唐·璜。”
唐·璜瞥了他一眼,愤恨地扯了扯那勒得他喉咙发紧的领结。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你已经可以面对一整个费奥拉万蒂家族了吗?给我回答,唐·璜。”
推开门的一瞬间,灯光、喧哗混合着鼎沸的人声一同向唐·璜袭来。
“啊,这是拉蒂默家那小子中的花吗?这倒真是不错,现在的年轻人也逐渐上来了嘛。”
“你别说,那个拉尼·拉蒂默,最近好像和罗雷莱家的小公子走得很近啊,既然如此恐怕也不会向着那边吧?”
“那边?哦,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边一直都斗志缺缺,只有这点儿地,他们也不会特意出手来抢吧!”
一群蠢蛋,唐·璜心想,连罗宾·罗雷莱的性别都没有搞清楚的家伙。可事实上,也就是这些人真正盘踞在家族的中上层。
忽然,有人用胳膊撞了他一下。
“哦,唐·璜,唐·璜,你的名字太放肆了,哈哈,唐·璜,唐·璜,这可真是个好名字,难怪大家都喜欢你。”
那是个醉汉,唐·璜皱着眉头想通过他那通红的面颊认出他的身份。
他退后两步,这才接着酒会偏黄的灯光认出那是费奥拉万蒂家族的三公子,法比奥·费奥拉万蒂。
唐·璜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从他进入家族的那天起那他名字开玩笑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有大半都是意大利人。生来讨厌意大利人的他当然一拳就把它们撩趴下了,但现在的情况太过尴尬,他总不能在家族酒会上以干部身份狠狠揍自家三公子一拳吧?
法比奥拎着酒瓶,早已微醺得站不住脚,于是他伸出手一把勾住唐·璜的脖子,像是吊在高树上一般,他摇晃着,凑近唐·璜的耳朵,扯着嗓子说道:“哥哥他看上去挺喜欢你的,哈,我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认同你,想要进这家门,你好歹得有点说得出口的成绩!”
唐·璜一把圈下他的手,抬手就拿过旁边送酒员托盘上的酒瓶,咕咚咕咚地灌满了法比奥的杯子,又抬起那杯子,用一整杯甜酒堵住了对方的嘴。
一杯酒下肚,法比奥拖着迷醉的眼神,呼出一口酒气,有点微喘地说道:“你,哈,你果然跟卡尔维诺哥哥一样,是个怪人。”
“不敢当,”唐·璜淡淡地说道,“你们两兄弟才是真的一样惹人讨厌。”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混乱得让人讨厌,刚摆脱法比奥,唐·璜就正面碰上了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
该死。他在心里骂道。
“我们有事找你。”卡尔维诺说道。
“谁?”唐·璜没有听清,酒会的嘈杂超出他的想象。
“伽利略·费奥拉万蒂!”卡尔维诺加重语气说道,唐·璜觉得他有些生气了,“我的父亲,唐·费奥拉万蒂要找你!”
“海鸥港的事情,你知道吗?”与酒会仅有一房相隔,但此刻唐·璜所处的房间安静至极,唐·费奥拉万蒂的声音掷地有声。
海鸥港是离这里两条街外的一个破旧小港口,因为港口正对的咖啡厅白墙上总是停满整排的海鸥而得名,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个无名的小港。唐·璜熟悉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他所负责的街区,每周五晚上,都会有几艘小船停靠在港口,费奥拉万蒂家族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船上进行的赌马活动。
唐·璜听到问话,对此毫无印象,他负责的街区还不曾出过什么事,于是他摇了摇头。
“跟他说说。”唐·费奥拉万蒂指了指站在一旁的奥古斯托·费奥拉万蒂,要大儿子把海鸥港发生的事情告诉一无所知的唐·璜。
“具体来说,”奥古斯托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道,“你负责的海鸥港在半个小时之前刚被条子查了,不仅是我们家族的人,埃斯波西托家族的人也被抓了,他们现在都蹲在皇后街的警局里。”
唐·璜有点不知所措。他有点担心自己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失去自己的小拇指。
一直不说话的卡尔维诺忽然站起身来,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卡尔维诺问他,你是费奥拉万蒂家的人对吧?
仅仅就这一句话,唐·璜就明白,这不是一个小指头可以解决了问题了。
“所以,唐·璜,”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转过头,面向唐·费奥拉万蒂和奥古斯托·费奥拉万蒂说,“到了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了。”
/
谁说浪子不惧怕死亡呢?相反他们可能更怕死,对世间玩乐的留恋会更深地缠着他们,比死亡更加窒息。
“至少我来了。”唐·璜这样想着,用同样颤抖的左手握紧右手。
火车持续着有节奏的声响。
他记起自己十七岁离家,几经辗转,整个大陆西岸都有过他踩凹的泥土。北飞的
燕鸥从他头顶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去,他的衣尾指向它们的翅尖;灰尾燕落于他所爱恋的地方,但秋风只赠与他最微弱的气息,法国的浪漫早已被腐朽所代替;再往下,美人鱼正在海对岸对他微笑,转过身来,施塔恩贝格湖底还游荡着他所不可见的亡魂。他在哪儿都没有停留,除了罗马。
唐·璜最为讨厌的就是意大利,不仅是因为意大利佬爱跟他抢妹,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他骨子里讨厌对方的说辞,什么“你美得像我家乡的星星”,情话说出口根本不经大脑,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老家根本连星星的影子都看不见。
但他还是在罗马做了一个一生最为悔恨的决定。
许愿池边的老牌冰淇淋店的小女孩儿跟他搭讪,他本不想吃,但看在那姑娘是在漂亮的份儿上——又是一双绿眼睛,他在那一刻就敢肯定他这辈子肯定要栽在绿眼睛上面——他点了他们家的招牌口味开心果。当然要的是碗装的,一个爷们儿独自一人还拎着个甜筒在大街上舔着未免有些可笑,他可不想还没走出两条街就被路边的意大利小男孩搭讪。
五分钟后,从窗口递出的却是一个载着两球的脆皮甜筒,就那两个冰淇淋球的大小来看,唐·璜确信他接手后迈开第一步就会弄脏自己的西裤。
“我只点了开心果,还是碗装的。”南欧的太阳火辣,他用带着西班牙口音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说道。
“我知道,”那姑娘笑着说,她那双漂亮的绿眼睛眨呀眨,看得唐·璜真怕自己下一秒就要冲上去吻对方的手,“甜筒和酒葡萄都是我送你的,这紫色跟你的眼睛可真搭。”
“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没法儿拿着它边走边吃,再有一刻钟我的火车就要开了,换成碗装的行吗?”
“哦,那个,”绿眼睛的姑娘眉角一弯,“我就是想留你在店门前多坐一会儿,好让我再仔细看你几眼。”
结果,唐·璜没能赶上那趟班车。
泡到漂亮姑娘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传来海风的呜呜声,紧接着是厚重男声,宣告着他一脚踏入一个糟糕的世界。
接连着回忆的中断,火车在空无一人的站台边停下。
这还不是终点,唐·璜深知这点,但他还是走下车,一脚踏上木制站台,脚下的旧木板发出吱呀声。他忽然发现这站点里架着一台电话机。
硬币在西装口袋里作响,他看了看电话机,手已经触及到听筒,耳已经听见长音的嘟嘟声,另一只手在硬币和纸片中游走,他脑后有夏末的风吹过。
此时正是静止,唐·璜知道整辆列车上为数不多的活人都在看着自己。抛开看好戏的车长以及几个漠不关心的列车员,还有费奥拉万蒂早就安插好的眼目。他权衡了一下,在脑中回想着他究竟能够给谁打上一个临终通讯。
他本想打给好友,可在脑中搜寻了一圈,仔细一想能够分享家族秘密的朋友似乎是没有;再转念想要打给家人,但当他费劲地摊开自己记着号码的小纸条时才发现这号码并不能联络到那个遥远的西班牙庄园。
记在小纸条上的号码清晰,一个个数字圆润而整齐,但他已经忘记了这究竟是谁留下的号码。身边经过的女人很多,但最后都像水,转瞬之间就流尽了。更何况,他也下不了决心把她们扯进麻烦事中。
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记起了这个号码的主人。
他记起那是属于威尔逊家的姑娘的号码,他们还一同出去看过电影。
来的时候,唐·璜迟到了二十分钟,家族的收尾工作稍稍拖迟了些,票早已售尽。为了弥补迟到而造成的坏影响,他单手撑着售票台,让鬓角的头发随着他头低下的弧度滑落。给我两张中间排的票,好吗,他轻轻勾起嘴角问道。于是售票小姐只得红着脸解释着他们票已受罄。得了吧,他一声嗤笑,凑近对方的耳边说道,谁不知道你们总会留上那么两个好位子等着大人物来,不知今晚的票是留给埃斯波西托还是费奥拉万蒂呀?
听到那两个名字的下一秒,售票小姐颤抖着递出了两张票。
唐·璜满意地接过它们,不出所料,的确是正中的好位子,于是他牵着威尔逊家的姑娘摸着黑进了场。
坐下之后他才有空转头看着隔壁座的水晶。
她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出更深的色彩,唐·璜不禁想起自己无数次跌倒在绿眼睛上的事。但那又何妨呢,唐·璜想到,这不是绿眼睛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可世间的美却常常犯错。
事实上他讨厌看电影,他根本无法忍受一个人坐在黑暗中那种寂寞的感觉,像是整个世界离他而去,他却无能为力。
屏幕上的女主角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红发,一对蓝眼睛看得人心醉。然后她一手插腰,伸直手指指着男主角的鼻子,指责他太过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嗬,英雄主义。唐·璜想起初学英文时,他记得他家乡那眼角带痣家庭教师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简单词语的意思。英雄,男主角,hero,三个意向浑然天成,英雄果然是男主角应该成为的角色。
主角当然不可能是他。电影也好,生活也罢,他都不可能成为那个hero。
他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他唐·璜可以是疯子,是懦夫,是半途而废不负责任的罪人,可他就是不能成为英雄。一个人又不可能因为长得像英雄就成为英雄,这样的假象或许能够迷惑外人,但内心中他很清楚,徒步行走至此,他什么也没有获得。梅西耶生前说过,几近努力最终仍是失败,只得承认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他甚至连这样的追求都没有,在十一岁的那个晚上他就很明白,他最终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世上完美的人千千万,就是不可能是他唐·璜。外表上的无懈可击并不能弥补缺失的内在,他紫色的眼眸中没有凯撒的英勇,他只是个帐下的逃兵,哀嚎着逃离战场。英雄是留给漫长未来的头衔,不适合他这样将亡的生命。
身旁水晶的呼吸声平稳安静,像极了路边的一株雏菊,浅浅地经过,淡淡地离去,不留一丝痕迹。
有那么一瞬间,唐·璜很想在黑暗中握住对方的手。
准确地说,电影的第二幕之后他就握住了水晶的手。对方有一瞬间的慌张,然后极快地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
唐·璜一个人在黑暗中度过了接下来的第三幕和第四幕。
从回忆里抽身,他又打量起那电话机,光滑漆面的中央有一块白色的划痕,破坏了美感。他又吸进一口空气,热度随着气息进入他的肺部,他在怀念薄荷烟清凉的那一瞬间不自觉地摁下了纸条上的数字。电话被接通的那一瞬间,他仿佛听见自己的心跳也随着那声清脆的应答声而盖棺,脚几乎要离地,投入那闷热的黑暗中。
“喂?请问是哪一位?”他从听筒里听见了水晶细细小小的声音。
他忽然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在电影院时那样,他呆坐在黑暗中,而此刻水晶的声音忽然穿透那层黑暗,仿佛突然降临的第五幕,水晶细细的胳膊忽然碰上黑暗中的他。
他忽然就下定了决心。
唐·璜挂掉电话,转头去看那列车。那是一辆漂亮的红色列车,三十年前应该也有过帅气的处女行,金色外框装饰虽有些掉漆,但留下的黑色轨迹仍旧勾勒出一幅繁华的景象,让他想起曾经在博物馆看过的洛可可风格的装饰画。
呼吸在此时显得沉重而多余,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开踩得吱呀作响的木板,踏上火车。
他睁大眼睛看着窗外。
无数相似的树木和山丘闪过,无数相似的红房子出现在视野尽头,他认真地看着,投入全力,像是新生儿初识世界那般投入全力。
他已经不能思考更多。已经出现的东西充斥着他的大脑,水晶的面容久久挥散不去。
我怎么会这么傻?为什么要给她挂电话?家族的人会不会知道她?我会不会让她深陷麻烦?他的脑子全都是这些垃圾,堆得快要溢出来。
他开始无比想念水晶。
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时的情形。一切都与往常无异,楼下的猫咪趴在垃圾箱盖上,奋力地划拉着箱底的食物,房东大妈抄起炉铲赶走厨房里又一只的肥老鼠,扯着嗓门骂了一通。哪里都是这样,生存来之不易。
他走出公寓时,隔壁房的奥提斯·帕西诺啃着充当早饭的三明治与他在街口碰面,简单打招呼的时候,对方手中三明治的香味反倒牢牢地窜入记忆,挥之不去。奥提斯嚼烂一片生菜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转过街角,没吃早饭的肚子不争气地在三明治前败下阵来,他也选了一块同样的三明治。嚼着硬邦邦的生菜叶的时候他想了很多,最多的还是关于接下来的事情,他才刚出门就已经见过很多人,但却没有一个知道他正攥着一张去比萨的单程票,一个钟头之后汽笛就会响起,车轮裹着费奥拉万蒂的希望一同驶向最终的西端。
紧接着他想起梅西耶之前的话,也没有谁会注意到他的离场,不明真相的姑娘小姐们或许会在三次舞会之后才想起他,但多半也只是口头的关心,三个月后她们可能会在另一场舞会上听到他身亡的消息,一个夜晚的泪水流尽后,两周转瞬而逝。她们很快就会有新的舞伴,他送出的那些礼物随着花瓣一同枯萎,被丢进再也不会打开的抽屉底层。而她们,她们将转手戴起其他男人送出的银镯,花裙泛起新的涟漪,一切又复如往常。知情者或许还会帮他办个像样的葬礼,黑衣黑伞黑棺,配上几朵简单的小白花,就像电影中的那样。但他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为了他而放慢脚步,模仿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情愿的慢镜头。
没有人还同他在一起,除了刚刚跟他对话的水晶,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跟他说过话,每个人都一如往常,没有人知道他唐·璜的往常就要在今天结束了。
刚加入家族时,他们问他是否信教。他知道家族的年轻人大多都不愿信教,他们相信自身多余相信上帝。
他信。
他并没有勇气和自信,他宁愿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飘忽的上帝保管。他不是虔诚,他不过是害怕承受责任,自身的责任。
于是他们又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天主。
他并不清楚基督和天主的具体差别,在他看来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忽然想到家乡盛传的施洗约翰的比喻,于是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在灯光下看着十字架上的苦像,心中想着它或许多耗费了零点几克的纯银。
从那之后他并不常去教堂,偶尔去时也只是看着圣母像发呆,他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够想些什么。现在他有些后悔,或许他应当带上一本圣经,最后的最后当一回虔诚的信徒,走得神圣一点。
他只能回想起圣经最初的故事,创世,亚当和夏娃诞生,然后是诺亚方舟,再往后他就记不清了。带起的是另一段回忆,他想起儿时窝在被窝里,他们家的约翰给他缓缓地读着圣经故事,阿方索的声音轻柔而充满磁性,他总是支撑不过三个故事便沉沉睡去,梦中似乎还有人在他身边读着那些故事,沉睡的人将醒来得永生,沉睡的人将醒来得永生,他听到有人这样说着。
似乎有什么超越他自身的东西出现了,他张开眼睛,他很明白地看到周围景物逝去的速度减慢了,他睁开眼睛,坚定的眼神出现在他脸上。他探出头去向窗外看去。不远的站台上,站着两个黑西装的男人。
他坐回位子上。
他明白他不应该这么不明不白地就迎来结束。
坐立不安的时刻被消除,他仿佛能够清楚地看到接下来的路途。
应该高声朗诵阿门?还是说应该抓住这最后反悔的机会,跃出火车开始逃亡?应该接受死亡,还是应该为了一些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人而努力活下去?
他已经有了答案。
再不需要什么人来指点迷津了,他的未来早已了然于心。
忽而一阵急促地汽笛声响起,他抬头向外看。
列车到站了。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因兴奋而颤抖着,就连咬牙也无法使其停止。他站了起来,迈开微微颤抖的步伐走向车厢口。
他扶稳车把手,深吸一口气,踏上站台。
他看到比萨的太阳,依旧灿烂,日光在他的视网膜上投下深色的阴影。
所以我才讨厌意大利,他这样想着,咧开嘴笑了笑,一时间他感到浑身轻松,女人、挚友、上帝和童年全都从记忆中脱离了出来,他们环绕在他的周围。
此地,绝不只有他唐·璜一人。
他转头,露出他自认为此生最美的一个笑容。袖兜中,一颗早已准备好的子弹正飞向远处。
架空黑手党paro,老唐死亡结局,BGM推荐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493835/
存活结局走http://elfartworld.com/works/70217/
“Dalle stalle alle stelle.”
“From the stalls to the stars.”
八月的星期天晚上。
佛罗伦萨的暖风仍旧吹得人面颊发红,夜色下红色地毯映照着仍旧绯红的天空,落山的太阳不再守护着这片阳光充沛的土地,黑衣与红裙混迹在软质的地面上,高跟鞋一脚踩碎黑头皮鞋所占有的空间。
日光还烧灼这大地,余温尚未从这片土地上退去。唐·璜隔着玻璃看了看窗外,回手整了整自己脖子上的领结。
“我得再跟你说一次,这不合适,这样真的不合适,这么正式!我几乎想揪掉领结破门而出了!”
“哦,但你不行。”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笑着说,“今晚大家不只是想认识那个风流贵公子唐·璜,他们应该更愿意看到费奥拉万蒂的得力助手唐·璜。”
唐·璜瞥了他一眼,愤恨地扯了扯那勒得他喉咙发紧的领结。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你已经可以面对一整个费奥拉万蒂家族了吗?给我回答,唐·璜。”
推开门的一瞬间,灯光、喧哗混合着鼎沸的人声一同向唐·璜袭来。
“啊,这是拉蒂默家那小子中的花吗?这倒真是不错,现在的年轻人也逐渐上来了嘛。”
“你别说,那个拉尼·拉蒂默,最近好像和罗雷莱家的小公子走得很近啊,既然如此恐怕也不会向着那边吧?”
“那边?哦,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边一直都斗志缺缺,只有这点儿地,他们也不会特意出手来抢吧!”
一群蠢蛋,唐·璜心想,连罗宾·罗雷莱的性别都没有搞清楚的家伙。可事实上,也就是这些人真正盘踞在家族的中上层。
忽然,有人用胳膊撞了他一下。
“哦,唐·璜,唐·璜,你的名字太放肆了,哈哈,唐·璜,唐·璜,这可真是个好名字,难怪大家都喜欢你。”
那是个醉汉,唐·璜皱着眉头想通过他那通红的面颊认出他的身份。
他退后两步,这才接着酒会偏黄的灯光认出那是费奥拉万蒂家族的三公子,法比奥·费奥拉万蒂。
唐·璜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从他进入家族的那天起那他名字开玩笑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有大半都是意大利人。生来讨厌意大利人的他当然一拳就把它们撩趴下了,但现在的情况太过尴尬,他总不能在家族酒会上以干部身份狠狠揍自家三公子一拳吧?
法比奥拎着酒瓶,早已微醺得站不住脚,于是他伸出手一把勾住唐·璜的脖子,像是吊在高树上一般,他摇晃着,凑近唐·璜的耳朵,扯着嗓子说道:“哥哥他看上去挺喜欢你的,哈,我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认同你,想要进这家门,你好歹得有点说得出口的成绩!”
唐·璜一把圈下他的手,抬手就拿过旁边送酒员托盘上的酒瓶,咕咚咕咚地灌满了法比奥的杯子,又抬起那杯子,用一整杯甜酒堵住了对方的嘴。
一杯酒下肚,法比奥拖着迷醉的眼神,呼出一口酒气,有点微喘地说道:“你,哈,你果然跟卡尔维诺哥哥一样,是个怪人。”
“不敢当,”唐·璜淡淡地说道,“你们两兄弟才是真的一样惹人讨厌。”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混乱得让人讨厌,刚摆脱法比奥,唐·璜就正面碰上了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
该死。他在心里骂道。
“我们有事找你。”卡尔维诺说道。
“谁?”唐·璜没有听清,酒会的嘈杂超出他的想象。
“伽利略·费奥拉万蒂!”卡尔维诺加重语气说道,唐·璜觉得他有些生气了,“我的父亲,唐·费奥拉万蒂要找你!”
“海鸥港的事情,你知道吗?”与酒会仅有一房相隔,但此刻唐·璜所处的房间安静至极,唐·费奥拉万蒂的声音掷地有声。
海鸥港是离这里两条街外的一个破旧小港口,因为港口正对的咖啡厅白墙上总是停满整排的海鸥而得名,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个无名的小港。唐·璜熟悉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他所负责的街区,每周五晚上,都会有几艘小船停靠在港口,费奥拉万蒂家族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船上进行的赌马活动。
唐·璜听到问话,对此毫无印象,他负责的街区还不曾出过什么事,于是他摇了摇头。
“跟他说说。”唐·费奥拉万蒂指了指站在一旁的奥古斯托·费奥拉万蒂,要大儿子把海鸥港发生的事情告诉一无所知的唐·璜。
“具体来说,”奥古斯托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道,“你负责的海鸥港在半个小时之前刚被条子查了,不仅是我们家族的人,埃斯波西托家族的人也被抓了,他们现在都蹲在皇后街的警局里。”
唐·璜有点不知所措。他有点担心自己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失去自己的小拇指。
一直不说话的卡尔维诺忽然站起身来,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卡尔维诺问他,你是费奥拉万蒂家的人对吧?
仅仅就这一句话,唐·璜就明白,这不是一个小指头可以解决了问题了。
“所以,唐·璜,”卡尔维诺·费奥拉万蒂转过头,面向唐·费奥拉万蒂和奥古斯托·费奥拉万蒂说,“到了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了。”
/
谁说浪子不惧怕死亡呢?相反他们可能更怕死,对世间玩乐的留恋会更深地缠着他们,比死亡更加窒息。
“至少我来了。”唐·璜这样想着,用同样颤抖的左手握紧右手。
火车持续着有节奏的声响。
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时的情形。一切都与往常无异,楼下的猫咪趴在垃圾箱盖上,奋力地划拉着箱底的食物,房东大妈抄起炉铲赶走厨房里又一只的肥老鼠,扯着嗓门骂了一通。哪里都是这样,生存来之不易。
他走出公寓时,隔壁房的奥提斯·帕西诺啃着充当早饭的三明治与他在街口碰面,简单打招呼的时候,对方手中三明治的香味反倒牢牢地窜入记忆,挥之不去。奥提斯嚼烂一片生菜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转过街角,没吃早饭的肚子不争气地在三明治前败下阵来,他也选了一块同样的三明治。嚼着硬邦邦的生菜叶的时候他想了很多,最多的还是关于接下来的事情,他才刚出门就已经见过很多人,但却没有一个知道他正攥着一张去比萨的单程票,一个钟头之后汽笛就会响起,车轮裹着费奥拉万蒂的希望一同驶向最终的西端。
紧接着他想起梅西耶之前的话,也没有谁会注意到他的离场,不明真相的姑娘小姐们或许会在三次舞会之后才想起他,但多半也只是口头的关心,三个月后她们可能会在另一场舞会上听到他身亡的消息,一个夜晚的泪水流尽后,两周转瞬而逝。她们很快就会有新的舞伴,他送出的那些礼物随着花瓣一同枯萎,被丢进再也不会打开的抽屉底层。而她们,她们将转手戴起其他男人送出的银镯,花裙泛起新的涟漪,一切又复如往常。知情者或许还会帮他办个像样的葬礼,黑衣黑伞黑棺,配上几朵简单的小白花,就像电影中的那样。但他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为了他而放慢脚步,模仿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情愿的慢镜头。
他记起自己十七岁离家,几经辗转,整个大陆西岸都有过他踩凹的泥土。北飞的
燕鸥从他头顶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去,他的衣尾指向它们的翅尖;灰尾燕落于他所爱恋的地方,但秋风只赠与他最微弱的气息,法国的浪漫早已被腐朽所代替;再往下,美人鱼正在海对岸对他微笑,转过身来,施塔恩贝格湖底还游荡着他所不可见的亡魂。他在哪儿都没有停留,除了罗马。
唐·璜最为讨厌的就是意大利,不仅是因为意大利佬爱跟他抢妹,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他骨子里讨厌对方的说辞,什么“你美得像我家乡的星星”,情话说出口根本不经大脑,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老家根本连星星的影子都看不见。
但他还是在罗马做了一个一生最为悔恨的决定。
许愿池边的老牌冰淇淋店的小女孩儿跟他搭讪,他本不想吃,但看在那姑娘是在漂亮的份儿上——又是一双绿眼睛,他在那一刻就敢肯定他这辈子肯定要栽在绿眼睛上面——他点了他们家的招牌口味开心果。当然要的是碗装的,一个爷们儿独自一人还拎着个甜筒在大街上舔着未免有些可笑,他可不想还没走出两条街就被路边的意大利小男孩搭讪。
五分钟后,从窗口递出的却是一个载着两球的脆皮甜筒,就那两个冰淇淋球的大小来看,唐·璜确信他接手后迈开第一步就会弄脏自己的西裤。
“我只点了开心果,还是碗装的。”南欧的太阳火辣,他用带着西班牙口音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说道。
“我知道,”那姑娘笑着说,她那双漂亮的绿眼睛眨呀眨,看得唐·璜真怕自己下一秒就要冲上去吻对方的手,“甜筒和酒葡萄都是我送你的,这紫色跟你的眼睛可真搭。”
“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没法儿拿着它边走边吃,再有一刻钟我的火车就要开了,换成碗装的行吗?”
“哦,那个,”绿眼睛的姑娘眉角一弯,“我就是想留你在店门前多坐一会儿,好让我再仔细看你几眼。”
结果,唐·璜没能赶上那趟班车。
泡到漂亮姑娘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传来海风的呜呜声,紧接着是厚重男声,宣告着他一脚踏入一个糟糕的世界。
接连着回忆的中断,火车在空无一人的站台边停下。
这还不是终点,唐·璜深知这点,但他还是走下车,一脚踏上木制站台,脚下的旧木板发出吱呀声。他忽然发现这站点里架着一台电话机。
硬币在西装口袋里作响,他看了看电话机,手已经触及到听筒,耳已经听见长音的嘟嘟声,另一只手在硬币和纸片中游走,他脑后有夏末的风吹过。
此时正是静止,唐·璜知道整辆列车上为数不多的活人都在看着自己。抛开看好戏的车长以及几个漠不关心的列车员,还有费奥拉万蒂早就安插好的眼目。他权衡了一下,在脑中回想着他究竟能够给谁打上一个临终通讯。
他本想打给好友,可在脑中搜寻了一圈,仔细一想能够分享家族秘密的朋友似乎是没有;再转念想要打给家人,但当他费劲地摊开自己记着号码的小纸条时才发现这号码并不能联络到那个遥远的西班牙庄园。
记在小纸条上的号码清晰,一个个数字圆润而整齐,但他已经忘记了这究竟是谁留下的号码。身边经过的女人很多,但最后都像水,转瞬之间就流尽了。更何况,他也下不了决心把她们扯进麻烦事中。
他紧盯着那黑色的电话机,光滑漆面的中央有一块白色的划痕,破坏了美感。他又吸进一口空气,热度随着气息进入他的肺部,他在怀念薄荷烟清凉的那一瞬间不自觉地放下了听筒。与坐台接触的那一瞬间,他仿佛听见自己的心跳也随着那听筒啪地盖棺,脚几乎要离地,投入那闷热的黑暗中。
他转头去看着列车。那是一辆漂亮的红色列车,三十年前应该也有过帅气的处女行,金色外框装饰虽有些掉漆,但留下的黑色轨迹仍旧勾勒出一幅繁华的景象,让他想起曾经在博物馆看过的洛可可风格的装饰画。
呼吸在此时显得沉重而多余,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开踩得吱呀作响的木板,踏上火车。
他穿过前几列空座位,在第七列座位停下,侧身坐进那有着厚绒垫的座位。
列车重新开始摇晃。
他转头看向窗外。
佛罗伦萨灿烂的日光和连绵的山脉逐渐被平原代替,路途向下延伸,地势逐渐转缓。他抬手看看表,距离比萨还有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
他不知道这车上有多少家族的成员,或许他们早已事先关照过,因此这辆车才如此空荡,他还没有见过第二位乘客。于是他顺势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十指都完好无缺,他进入家族后也没少犯错误,但上头几次三番没有追问,他本还以为自己是被偏爱者,而此刻火车轰隆,他身边却空无一人。
受到惩罚的也只有他一人。
他不知道此行对于费奥拉万蒂而言究竟有多少重量,他一人的生命似乎什么都换不回,最大化利用的结果不过借刀杀人,以此要挟埃斯波西托罢了。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做成,自十七岁离家开始,他自始至终都是两手空空。枉费一头金发和一汪紫眸,枉费母亲的期望,枉费一切盼望他成为英雄的奢望。
他早该知道的,他唐·璜可以是疯子,是懦夫,是半途而废不负责任的罪人,可他就是不能成为英雄。一个人又不可能因为长得像英雄就成为英雄,这样的假象或许能够迷惑外人,但内心中他很清楚,徒步行走至此,他什么也没有获得。梅西耶生前说过,几近努力最终仍是失败,只得承认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他甚至连这样的追求都没有,在十一岁的那个晚上他就很明白,他最终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世上完美的人千千万,就是不可能是他唐·璜。外表上的无懈可击并不能弥补缺失的内在,他紫色的眼眸中没有凯撒的英勇,他只是个帐下的逃兵,哀嚎着逃离战场。英雄是留给漫长未来的头衔,不适合他这样将亡的生命。
他睁大眼睛看着窗外。
无数相似的树木和山丘闪过,无数相似的红房子出现在视野尽头,他认真地看着,投入全力,像是新生儿初识世界那般投入全力。
刚加入家族时,他们问他是否信教。他知道家族的年轻人大多都不愿信教,他们相信自身多余相信上帝。
他信。
他并没有勇气和自信,他宁愿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飘忽的上帝保管。他不是虔诚,他不过是害怕承受责任,自身的责任。
于是他们又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天主。
他并不清楚基督和天主的具体差别,在他看来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忽然想到家乡盛传的施洗约翰的比喻,于是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在灯光下看着十字架上的苦像,心中想着它或许多耗费了零点几克的纯银。
从那之后他并不常去教堂,偶尔去时也只是看着圣母像发呆,他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够想些什么。现在他有些后悔,或许他应当带上一本圣经,最后的最后当一回虔诚的信徒,走得神圣一点。
他只能回想起圣经最初的故事,创世,亚当和夏娃诞生,然后是诺亚方舟,再往后他就记不清了。带起的是另一段回忆,他想起儿时窝在被窝里,他们家的约翰给他缓缓地读着圣经故事,阿方索的声音轻柔而充满磁性,他总是支撑不过三个故事便沉沉睡去,梦中似乎还有人在他身边读着那些故事,沉睡的人将醒来得永生,沉睡的人将醒来得永生,他听到有人这样说着。
似乎有什么超越他自身的东西出现了,他张开眼睛,他很明白地看到周围景物逝去的速度减慢了,他仰着一张流满泪水的脸探出车窗向外看去。不远的站台上,站着两个黑西装的男人。
他坐回位子上。
坐立不安的时刻现在才来临,他几乎不知道双手该如何安放。
他应该高声朗诵阿门吗?还是说应该抓住这最后反悔的机会,跃出火车开始逃亡?他应该接受死亡,还是应该为了一些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的人而活下去?
他不明白。他不明白。
没有人能帮他指点迷津了,他已走投无路。
忽而一阵急促地汽笛声响起,他慌忙抬头向外看。
列车到站了。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颤抖不已,就连咬牙也无法使其停止。忽然他站了起来,迈开颤抖地步伐走向车厢口。
他扶稳车把手,深吸一口气,踏上站台。
他看到比萨的太阳,依旧灿烂,日光在他的视网膜上投下深色的阴影。
所以我才讨厌意大利,他这样想着,咧开嘴笑了笑,一时间他感到浑身轻松,女人、挚友、上帝和童年全都消失了,此地只剩下他一人。
只剩下他唐·璜一人。
他转头,露出他自认为此生最美的一个笑容。五步开外,一颗早已准备好了的子弹向他飞来。
差一点就要变成狮院的叛徒了……
依旧借用了一点朋友家的孩子,ooc了的话请务必敲打我(。
奥提斯并不写日记,当然这是在五月之前的事情。一切的成习都能在美食的诱惑前改变,奥提斯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金发的大姐姐端着一盘起司鲜奶骨饼,笑着拜托他看看不靠谱的学长再记记日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七月之后,日记经由莎伦•肯特之手交给了柯莉斯特尔•威尔逊。
她翻开第一页。
上面只有一些骨饼碎屑。
第二页,依旧是骨饼的碎屑,其中还夹杂着干透了的紫红色葡萄汁。
第三页,奥提斯浑圆的字迹终于出现在纸上,留下的信息却只有“5月5日,晴,今天唐学长也不知所踪。”
柯莉斯特尔继续向下翻着。
5月14日,多云,今天午饭的时候见到唐学长,他跑去跟拉尼学长还有罗宾说话,然后一转眼就飞了出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5月20日,阴,今天唐学长抢走了我的棒棒手指饼,我只好趁他不注意咬了咬他的魔杖。魔杖不好吃。
5月26日,晴,今天唐学长在魁地奇训练的时候跟拉尼学长撞到了一起。虽然唐学长坚持是拉尼学长的错,但我可以保证他们两个人相撞的时候都没有看路。
5月27日,小雨,突然想起来,昨天唐学长和拉尼学长相撞的时候,训练场边观看的人有柯莉斯特尔学姐和罗宾。今天没有见到唐学长,但是我听到高年级魔药课的教室里好像有唐学长的惨叫。
5月29日,晴,刚刚经过唐学长的宿舍,听到他在里头很大声地说“啊,我怎么如此罪恶,又让一个好女孩儿爱上了我。”,然后我就看到他被其他学长赶了出来。他抱着我哭了一会儿,好像还有点眼泪蹭在我围巾上了,因为它尝起来比平常咸。
5月31日,多云,今天我去问唐学长,爸爸说过穿裤子的都是男生那为什么罗宾是女孩子,唐学长给了我一块罗密亚西饼之后就把我赶回了宿舍。
“呃,或许我们不应该拜托这孩子……?”莎伦•肯特在一旁看完之后不禁苦笑。
柯莉斯特尔眨眨她的绿眼睛,没有说话,接着又翻开了下一页。
6月1日,阴,唐学长说今天是我的节日,送了我一盒花生杏仁小圆饼。我就顺带问了他大家一直说的女朋友究竟是什么东西。可是女朋友不能吃,为什么有人喜欢呢。唐学长说女朋友就是像小圆饼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也喜欢上女朋友了。
6月3日,唐学长说话不算数!说好了去霍格莫德玩之后会给我带蜂蜜公爵的糖的!我很生气,只好咬了咬他的围巾。我觉得还是赫奇帕奇的围巾更好吃一点。
6月10日,多云,我原谅唐学长了,他跟我说没买糖果是因为要陪他的小女朋友,我想了想,小圆饼的确很容易让人忘记事。当然,今天他送给我的鱿鱼圈也一样容易让人忘事。
6月15日,晴,唐学长今天趴在草坪上的石椅子后面一直在看着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还吓了一大跳。他说他在看他的小女朋友,可是四年级里头没有人长得像小圆饼。
6月23日,大雨,我好像有点明白唐学长说的小女朋友是谁了,可是柯莉斯特尔学姐跟小圆饼究竟有什么关系?
6月30日,阴,唐学长今天来找我,问我他摆出哪个姿势会更帅一点。我如实说了“给我咸味玉米培根麦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很生气。
再往下便是今日还未来得及写上的日记,莎伦•肯特看着柯莉斯特尔变红的脸,意味深长地闭上眼睛。
看来一盘起司鲜奶骨饼并不亏。她这样想着,不禁笑了起来。

2568字
虽然欠着很多互动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谈起了恋爱!(打死
我家小水晶真可爱prprpr
文风出走写得很烂,还借用了朋友的一些孩子,希望不要介意(emoji闭眼
跟前文echo教授送老唐茶包有关。教授送的是黄玫瑰茶包,花语是友谊,也就是传说中的ntr之花………
上帝总是不适时地给他的子民打开了窗。
唐·璜就在这个不合适的时刻推开了窗。他承认也好拒绝也罢,上帝的的确确就在那里,在他已经几近崩溃时对他耳语,给他指令——“打开窗”。
于是透明玻璃就带着不小的重量,哐地一声,硬生生地撞上了什么东西,接着是跌坐声。唐·璜支起上身看向窗外,柯莉斯特尔·威尔逊的身影一点点地从隐形衣后显露出来。
那是唐·璜第一次见到柯莉斯特尔,一双似曾相识的绿眼睛尴尬地眨了眨,不等他开口询问对方的伤势,她便飞快地批起隐形衣,一下子便不见了。
唐·璜只得再坐回位子上,被打断了的思绪重新集中在手边那一袋茶包上。
底料用的是今年的新叶,锦上添花的辅料是被晒干了的玫瑰,一朵一滴黄,无声地诉说着他的失败。
热水倒入茶杯,白色的瓷杯中茶色弥漫,在光下显出一丝柔和的金黄。
那是黄玫瑰染上的色泽,柔和中夹杂着金色的闪光,唐·璜愈看它愈像刚刚那女孩儿的秀发。
但他确实不曾见过对方,至少没有面对面见过,否则他是不可能不记得少女的面容的。可他细细思索着却又觉得少女面熟得狠,像极了某个他所熟识的人。
茶香勾起回忆,唐·璜一皱眉,脑中闪过艾寇教授的面容和她的绿眼睛。他没有记错,她们的确相像,但又有些不同,对于少女,他总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
这种感觉持续到晚餐时分都还未结束。
唐·璜坐在晚餐长桌上,正当他把切片面包抹上果酱时,他感觉身后似乎有目光正在注视着自己。
他一向对于这种目光习以为常,但近日的经历令他悄悄有些神经紧张,于是他默默地调转头。
身后,拉尼·拉蒂默坐在一堆赫奇帕奇中抬起头冲他笑了笑,唐·璜第一时间发现今天罗宾·罗雷莱并没有坐在他身边。
真希望这家伙能早些开窍,不然迟早被甩,唐·璜转过头叹了口气。
而那目光再次向唐·璜袭来,方向改变到了右后方,他转过头,除了奥提斯·帕西诺哧呼哧呼地嚼着一大盘椰蓉奶球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在意的东西。
于是他只得再转回头,面对着他的切片面包。当他终于放弃寻找,挺起背任命地无视那目光时,他忽然瞥见一抹熟悉的金黄。
他当然知道学校中的金发不在少数,就连他自己也是金发,但唐·璜很清楚的知道每头金发都有不同的色泽。打个比方,如果说他唐·璜的金发璀璨而张扬,同是金发的麦伦·洛佩兹却显出了腼腆和乖巧,而这发色再放到莎伦·肯特的身上便显出一股贤淑大气的气质,每头金发都有些它自己的表达方式,使它自己与其他金色区分开来。
而唐·璜此刻瞥见的金色,像下午时分的花茶,淡淡地晕出一圈金色,透出一股清雅安静的气息。
他转头过去,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一般,他看见了下午出现在他窗前的那个姑娘。
/
上帝有的时候的确挺糊涂的,不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犯的错误多半都被解读为了试炼或神谕。
“别总跟我说这些无聊的话题,”梅西耶用眼神示意着唐·璜翻至下一页,“我对此毫无兴趣。”
“但是、但是,”唐·璜失意地趴在桌上,“她这样搞得我真的很在意!而且她那头金发还有那双绿眼睛……啧啧,我跟你说,我这辈子估计都得栽在绿眼睛上……”
梅西耶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指的‘她’是指那个金发绿眼睛一直喜欢出现在你周围的那个姑娘的话——”
唐·璜屏住气质等着他吐出那最为关键的一句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告诉你,她已经这样很久了。从你在图书馆睡得不省人事到强迫我做无聊的听写训练再到向我哭诉被哪个教授无情挂科了的时候,她应该都在距离我们两个长桌的距离外看着你。”
“真是罪孽啊”唐·璜一拍大腿,随即甩开他的秀发,单手扶额一边摇头一边开口,“此等重罪恐怕到最后审判时都难以赎清,啊,如此罪孽的我,竟然又让一个女孩儿为我沉迷!”
“如果你不看书,那么就不要总是来图书馆,”梅西耶冷冷地说道,“就算要也请不要挑我在图书馆的日子来。现在,翻页。”
唐·璜漫不经心地再翻过一页,嘴却片刻不停地继续说着:“你说,既然她都这样迷恋我了,我是不是该直接去找她比较好?还是说我就保持现状,让距离衬托出我别样的美丽?”
梅西耶没有回答。
“那这样,说好了哦,如果你的下一句话是‘翻页’,那我就去找她;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听你的意见,如何?”
“我只希望你还我一个清静,翻页。”
梅西耶话音刚落,唐·璜的身影就蹿出好远,直落在那金发少女身边。
然后,尽管梅西耶不愿知晓,但唐·璜还是用他也能听见的音量说道:
“正式介绍一下,在下唐·璜。这位美丽的小姐,不知这个周末你是否有打算前往霍格莫德呢?尽管很唐突,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务必允许我做你的旅伴。”
/
“来,看我的多味豆。”唐·璜抽出一颗豆子就向柯莉斯特尔的口中丢去。
“啊,”对方有些吃惊,好容易接下了怪味豆,少女认真地尝了尝味道,“呜哇……草味的。”
唐·璜又抽了一颗多味豆,将它高高抛起,仰头去接的时候豆子狠狠地砸在了他的鼻梁上,还来不及低头躲过一旁尴尬的视线,多味豆从唐·璜的鼻梁上蹦跳而下,顺势落进了他的口中。
“哦,”他伸出手摸摸鼻梁,又耸了耸肩,“呃,不知你有听说过吗,据说如果两个人在蜂蜜公爵的店里尝到了同样味道的多味豆,他们多半会成为情侣。”
柯莉斯特尔睁大了她那对漂亮的绿眼睛,此刻那玻璃珠一般的瞳孔中正写满了好奇。
“真、真的吗……?”她急于得到答案,脚尖轻点着地,微微前倾地问道。
唐·璜眯起一只眼睛,食指在空中左右摇晃着:“当然是真的了,千真万确,我怎么会骗我可爱的小水晶呢。”
“那……”柯莉斯特尔不好意思地眨了眨眼,目光有意无意地轻瞥着唐·璜的唇,多味豆还在唐·璜的口中,散发着旁人不可察觉的味道。
“哦,这个那当然是……”唐·璜上前一步,弯下腰,轻轻凑到柯莉斯特尔的耳边说道,“当然也是草味儿的。”
柯莉斯特尔还未回神,手便被唐·璜牵住,力量沿着手臂传来,她被带出了蜂蜜公爵的店。
在街道上重新找回步调后,她紧跟在唐·璜身边,牵着的手让她的脸颊升温,耳边传来男性沉稳的脚步声,她仰起头,沿街商铺玻璃窗里的小饰品此刻一齐黯淡,除了那飞扬的金色外,一切都没了颜色。
忽然唐·璜放慢了脚步,柯莉斯特尔这才发现他们在三把扫帚酒吧门口停了下来,歪斜的尖角下,三把扫帚围成一个三角,稳固而和谐。在唐·璜伸手拉开那老店木门光滑的手把之前,他转过头来看着柯莉斯特尔说道:“关于刚刚那个多味豆的传说,我忽然想起它的第一任传播者的名字了。”
“那么,是谁呢?”柯莉斯特尔问道。
唐·璜看了看她的绿眼睛,没说话。他自顾自地裂开嘴笑了笑,绿眼睛真的是个漩涡,唐·璜这样想着,随后拉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