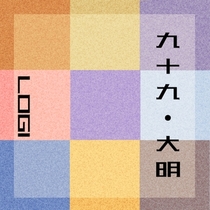时至隆冬,天地万物仿佛都凝固了。一年到头的这个时节,承载的多半是寂寥和终结。
八重,你又想着死了吗?阿香问我。
这次只差一点。我告诉她。
可不要死在我的屋子里,老板接济你,也是因为你有才华却又不会长命。他是一个喜欢焰火的人。阿香说。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说道。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放弃了所有一切的嬉笑怒骂,最后剩下的才是真实。
但人们总是更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就算是痛苦的事,不包裹在一层华丽外表下就没人吃得下去。
殊不知最深远的痛,是生活。
那一天我在姑苏的石桥上遇到了清海。他拄着竹棍,看着远方。这完全不像他平日里的为人,我以为他会和我说昨晚听到的笑话,不然就是那家神秘店铺的事情。
但清海只是问我,爱情有多少种?
爱情只有两种。和尚说,不是狗娘养,就是至死不渝。
世间的一切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又特别简单。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遁入红尘,又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转身离去。
和尚说,装疯卖傻到今天为止吧。
我说好。
我想讲一个故事了。
前朝再前朝的时候,有一位倾国倾城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数百年才会有一位,围绕她的全都是神秘又优雅的故事。正因为她是个奇人,所以她身边的器物也沾染了她的灵气,有一枚凤头金钗更是如此。这枚金钗到了能幻化的时日,便幻化成女人的样子,作弄宫殿中的人。她模仿女人的步伐姿态,但却因为是器物,并非活人,无论如何都差了些许。
非要说的话,大概是不懂人心。
如果盛世一直下去,那凤头金钗最后可能会与寿终正寝的女人一同入土。然而金钗并不想如此,一想到自己会随葬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就感到气恼。我也如此雍容华贵,我也不逊于你,我甚至比你更加永恒。肉身早晚会腐坏,但我却不会腐朽,我可是真金而制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凤头金钗竟然萌生了逃走的念头。
那年的长安,天龙寺的僧人正在为皇帝念经祈福。上元节皇帝想要安排一些盛大的宴席,每个人都能吃好玩好。他当然有资本这样做,现在的国家比任何时代的国都要强盛,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凤头金钗在一天晚上溜出了皇宫,赤脚踩在皇宫外的石板路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自然的,它,或者说她毕竟是真金而制啊。
她遇到了一个和尚。
下了晚课,点着烛火,走过天龙寺的墙。
小和尚,你看我一眼可好?凤头金钗觉得有趣,便学着故事里的妖精那样同和尚搭话。
和尚点了提灯,抬眼看见“娘娘”趴在墙上,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然而不过是一眼的功夫,瞬间山河崩塌,乱世来。
那个倾国倾城的女人香消玉殒。
凤头金钗不知去向。
天龙寺的小和尚,藏经阁着火的时候,他抱着经书被一根横梁砸断了脊梁。往生而去时,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城南没有去看过的花,还是那惊鸿一瞥间所见的美。
前朝的时候,兵荒马乱。都说乱世就会有妖物作祟,因为人心也跟着仿徨。
旧都不再是首府,随没有没落,但就像容颜老去的女人,不再受到眷顾。而这妖物正盘踞在旧都的城里,已经取了十几条人命。
官府不承认有妖物,如果承认有,那岂不是更加证明自己的不可靠。但私下里却四处寻找能降妖除魔的人才。
方才说了,乱世妖物频现。当然也会出现以祛除妖物为生的人。其中不乏各种骗子。那个僧人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
这个僧人说不清道不明自己的来路,连自己出家的寺庙都说不清楚。一进城就因为打架滋事被关进了大牢,虽然事后证明和他并无关系。
他说自己前世因为被横梁砸断了脊梁,所以这辈子不想再弯腰下去,结果招惹了地痞流氓。我来此处是闻到了妖物的气味。这位看起来像骗子的僧人说,妖物的种类不同,而这边作祟的这位,正好是小僧擅长的领域。
那妖物本是器物,却因邪念而化为对凡人有杀意的存在。僧人如此解释道。信不过小僧也无妨,姑且让小僧一试。天亮之后,如果小僧还活着,就请做个法事超度那些亡灵,再以你们官府的名义救济灾民。
如果小僧死了,那就请准备一张破席,卷裹尸身随意埋了吧。
旁人说你这是什么都不要吗?
小僧连自己是何许人也,从何处来都忘记了,何必在意这些。僧人说。
既然他都这样说了,那么就姑且一试。
当夜僧人便独自一人前往城北的前朝宫殿废墟处。那废墟早已被铲平,盖上了其他房屋。但就因为如此,那妖物在这原本是废墟的遗址上各种作祟。
当天夜里,有人说听见凄厉的嚎哭,也有人说听见女子的欢笑,有人听见诵经的声音,也有人说那和尚与妖物讲了一夜的道理。
众说纷纭,却没人真正看见。
天亮之后,人们看见那僧人端坐在大殿中,已然断气。
果然是骗子啊。人们这样想。拿来了破席子,裹了僧人的尸身埋去了乱葬岗。
但那夜之后妖物也不再出现了。人们这才觉得,这僧人看来是真的会祛魔。只不过用的是自己的性命。
过意不去的人们再去乱葬岗想要寻回高僧,是的,他们开始称其为高僧。想要寻回高僧的尸身,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
只留下一张破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人们于是说,高僧羽化而去。便向着西天的方向叩头跪拜。
哪有什么羽化而去。清海说,只不过是被野狗啃食叼走了。
呃。我回答他。
你我相见的第一天,其实你确实想寻死的吧?清海问。
确实如此。
你也没有前去鬼市,那不过是你摔倒之后的臆想,对吧?
确实如此。
唯独八重这个名字,确实并非你所有。清海笑了,你我都是无名无姓之辈,来处,去者,不过是一片白茫。
我无法反驳。
你在心中所想的世界是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还是哀伤遍野无人之境,都由你决定。只是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也许还有时间思考。
没错,这个世界很快就要结束了。用他们那个常世的时间来算的话,差不多还有两个月。
结束以后要往何处去呢?
不知。
一切皆虚妄啊。清海说。
还是来说故事吧。清海说。后来啊,也许你会觉得,这是最后一世。与她与我都是如此。但可惜并不是这样。
清海睁开双目,那对眼睛只有两个空洞,在空洞中我什么都见不到,只有无边黑暗。
我不是清海,清海早就死了。他早就脱离了轮回,不在此处很久了。
那是她编给自己听的故事。因为这样才能好过下去。
那真实的故事到底是如何的?
没人知道。
就满足她吧。
毕竟也算是有灵性的器物了,再回到平常不容易。
每个人的劫数,只有每个人自己知晓。
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个和尚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也是他在骗人。真相到底是什么,无人知晓。只有雪落无声,和在隆冬中静谧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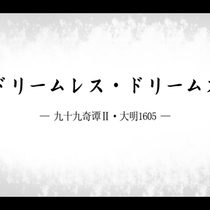
这次的故事,是关于三个男人的午夜大冒险。依然BUG很多,请海涵!
————————————————————
都说冬季是个好季节,我却不知它好在哪里。一年的终末,万物归于寂寥,只会让人想起诸多唏嘘的往事。
姑苏这种南方城市,就算降雪,也只会是一层薄薄的意思。所谓落雪之音,结果就跟下雨没什么区别。
至于我,只要进入冬季就好像立马就会睡过去,除了抱着暖炉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在下名为八重,乃是一名流落到此地的倭国作家。说是作家,其实也不过是替青楼姑娘们写些唱词糊口罢了。
在下寄居处,正是姑苏城内一座名为“闲月”的青楼。有旖旎环抱,衣食无忧,简直就是身为作家的梦想,而我正踏在这梦想之阶上……
“我搁炉子边上的红薯上哪去了!”吼声犹如虎啸,名为阿香的姑娘从暖炉边上揪出一个我。
“我说阿香啊,红薯就是要给人吃的嘛,如果烤过头就很可怜了呀。”我如此说道,然后看到阿香冷笑一声。
如果不是这么火爆脾气,应该会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才对。
于是我就在这种连鬼都能冻死的天气里,再一次地,被扫地出门了。
“这也太凄惨了吧?”清海说。我俩一同坐在避风的廊下,各自对冻僵的手哈气。清海乃是一名云游僧人,光凭法号是绝对想不到这个和尚是什么秉性的。
对我表示了差不多百部经书那样分量的同情之后,清海马上转折:“小僧我最近每晚都会被接引去一个奇妙的地方,温暖又有很多人吵闹,非常有意思呢。”
“……你该不会是冻到极致产生幻觉了吧?”
“如果能在这样的幻觉中西去,也是幸福啊。”
“…………”
要详细询问他是怎样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清海是个标准的,双目失明的僧人。根据他的说法,自己打出生就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样子。
世人所见之物,其实都是皮相。听见的,闻见的,也都并非真实。清海认真地表示,所以我这是佛缘。
……如果人人都能像他这么豁达,那世间怕是根本不会存在不幸了。
“难不成是你口中的那位娘娘干的好事?”
“施主真是聪慧。小僧确实每晚都在纷繁嘈杂中听见她的声音。”
“……她到底是人是鬼啊!”
“实不相瞒,每次都忘记问。”
“……”
事情就是如此。这位僧人似乎一直在与一位只有他能感知到的女子交流。
时常对着空无一人的方向说着“阿雨说得对啊”,“小僧我也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对方到底说了什么。
…………根本就是一个疯子。
路上行人匆匆,蓑衣斗笠与伞往来接踵。飘过来的雪那可是相当漫不经心。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不禁开始担心今晚到底要去哪里过夜。
要是冻死在街头的话,不知道阿香会不会肯拿出一点钱来为我买口棺材。……不可能的,那个女人比铁公鸡还一毛不拔。
“大师今晚有着落否?”我询问道。
“阿雨说今晚也可去她的住处叨唠,夜宵是素食果馅酒酿小圆子。”
“……”
“看来我俩如此合得来的份上,大师有没有考虑让我也沾点光呢?”我倒是要看看他每晚蛰居的住处是他的幻觉还是真有其事。
“你的话……”和尚突然转过头来对着我,他双目紧闭,并未睁开。但我不禁心里有些发毛,觉得确实是被人注视着。
“你的话……”清海说,“恐怕去不到那里。”
“哈?!”
“我是说真的,你去不到那里。”
“……那里究竟是哪里啦!如果是你的幻觉的话,我确实进不去就是了!”
“如果施主是担心今夜天气过于寒冷,可能会出人命的话……”
“怎样?”
“反正都是皮相,舍去了便是~~”
“…………”
“啊呀,施主是舍不得吗?”
“废话啊,我还想多活好多年呢!最好能儿孙满堂地在床上死去!”
“儿孙满堂地在床上死去啊……”和尚突然沉吟起来,“那真的是你的期望么?”
我被他一问,竟然语塞。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一阵巨响,有什么东西从屋顶上砸落在地。
……
“施主,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地了?”
“大师好耳力,确实有东西掉下来。”
“……听起来还挺沉。”
“那可是相当地沉。”
摔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一个活人。只不过因为落地姿势太过难看,很难形容给和尚听。这个人背着一个看起来精巧复杂的箱子,如今结结实实压在他身上。如果要去报官,恐怕只能对仵作说出“可能是被自己的箱子压死的”这样的死因来。
那个从天而降的角色动了动,突然飞快地爬起。 “二位真是好雅兴,竟然在这飘雪时节于廊下促膝相谈。
本来就肚子饿,还很冷。当然是没好气的。“这位道爷有何指教啊?”此人虽然穿得莫名其妙,但确实是一位道士没错。
“贫道听到你们在说些有趣的东西。”这位道人随随便便行了个稽首礼。
“没钱,不会找你算卦的。”我十分冷漠地说。
“……我还没说什么话呢!”道人说。
“出门在外最要小心四种人,女人小孩,和尚道士。”话是这么说,但这四种人我基本都碰上了。
所以也可能就因为这样,我才至今都境遇凄惨。
“真是至理名言!”这位道长由衷地说。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会随着麻烦一起来的角色啊。
“贫道唐隐,除了算卦捉鬼,最感兴趣的便是好好过日子,最后幸福地寿终正寝。”道长说。听起来根本就是与主线无关的人生履历。
“……难不成你觉得和一个穷作家外加一个疯瞎和尚搭话,也算是好好过日子的一部分吗?”
“事实上……因为我听到了你们谈论的有趣事情。”这位唐道长说,“这位大师,你可否听到您那位阿雨姑娘谈论起关于她们这个族类中,有其他存在也在此城中活动?”
“您这样一说,倒是有耳闻……”
“如何?”
“需要小僧帮忙打听一下吗?”
“再好不过了,唐隐拜谢。”
“只是道长想要寻找的是怎样的呢?”
“请大师附耳过来……大约是这样。”
“……………………喂你俩不要当我是透明的啊!”也不知道这俩人的脑波是怎么突然搭上了线,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就这样相互交流起奇怪的事情来。
“嗯嗯,我也觉得兴许去了那个地方。”
“毕竟是青楼女子……”
“要是惹了麻烦就糟糕了……”
“………………都说了不要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我拼命抗议,但是毫无效果。这两个人仿佛前世早就认识一样。
“施主,听说你是住在一座名为’闲月’的青楼里是吗?”和尚突然回过头来。
“……居然蛰居在这种地方,这位施主真是人不可貌相。”道长也跟着帮腔。要你多事。
“怎么?你们是要怎样?”我问他俩。
“贫道有一个不情之请……”那道长突然十分正经地说道。
“所以这就是你带着两个吃白食的回来的原因?”阿香倚着门,襦裙退到胸口,正想借口这样很冷啊去给她提上去。
和尚道士站在我身后,一副正经出家人的样子。
“呃,这位道长说近日这附近有些诡异之事,乃是一非同寻常的精怪所为,掐指算来,兴许会在今夜叨唠此处,所以……”
具体的事情要形容起来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干脆这样说就好了。
“……你信么?”阿香看着我。
“……当、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如果你出事要怎么办?”
“想不到八重你这么关心小娘子我啊~”阿香笑面如花,伸出手指戳我心口,“果然只有你这个男人最有良心了~”
接着阿香表情一沉:“不要以为用这种话哄骗老娘,老娘就会收留你们这几个穷要饭的!”
“…………这样说二位大师道长也太失礼了!”
“失礼?那你倒是告诉我,怎样才算有礼数呀?”阿香凑过来,她身上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真是叫人酥麻。
“呃……这个嘛……”未等我整理好语言,阿香顺势将我一推,我立马从台阶上滚下。大门铿锵有力地在我眼前关上。
真是个懂得捉放手腕的女人,就算是这样被扫地出门,我作为男人的那部分竟然也喜不自胜地对着空气欢呼。
“果然不会像计划中那样顺利……”道长说,“那照目前来看,只能在此蹲守了”
“…………说不定会冻死啊,看你的表情还以为会有什么高见,隔着一堵墙,里面是暖炉和酥胸,外面是天寒地冻。未免也太惨了吧!”
“有的时候,人就是需要拼一下的。”道长十分严肃地说。
“这和您之前所说的为人处世之道似乎不是很符合……”
“为人处世之道就是用来打破的,不然还叫什么人生。”
“…………”
我不禁为这句话鼓起掌来。
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三人顺着墙根坐下,开始等待。“和尚,你今天很沉默啊。”我对身边的清海说。
“阿雨说小僧是榆木脑瓜,只知道蹚浑水,一气之下已经先回去了。”和尚如此说道。
“那还真是有点惨。”说起来这种情况难道不就是,为了兄弟义气和女人吵架的桥段么?不过为何连和尚都有青睐的女人啊,虽然不知道是人是鬼罢了。
“八重先生,清海师父与那位女子的因缘很深,不是旁人所能道哉。”道长说。
你这个人,是有读心术吗?
“我可以看到两股纠缠许久的线,没有尽头。不过也许,在今世会有一个截断。”道长说,“不过那与我等都没有关系。至于你的话……”这家伙凑过来端详老子的脸,距离近到可以完全看到他的胡渣。
“你的话……嗯……”
“我的话,是要怎样?”
“……你这个面相,是个薄情之人。”
“…………要你说。”
“除了会让人伤心之外,别无用处。这种面相真应该张贴在大街小巷,让姑娘们离远一点。”
……够了喂。
如此闲聊着,三个勉强算是无家可归的男人靠在青楼的外墙边。雪时停时下,不久天暗了下来,青楼上下点起了灯笼,每个窗户里都透出了温润的橘色灯火。
姑娘们此时应该已洗漱装扮完毕,坐在有暖炉的屋子里,等着老鸨招呼。那些恩客要等天色再暗一些才会来,这隆冬季节里头,女人的体温怕是再好不过的抚慰。
……总觉得这样一想,在外墙的三人看起来更加凄苦了。
“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冻死了。”我说,“眼前已经出现了幻觉。”
“……既然都知道是幻觉,那一定还不会死吧。”道长说。
此时青楼大门已开,人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可那幻觉未免太过真实。”我指着街道尽头说。“那里……好像有个人。”
不禁如此,我似乎听到了幽幽的歌声。那歌声如泣如诉,一字一句。却并非我所熟悉的那些个唱词。
生……生……死……死……
未……忧……而……获……
只……晓……歌……舞……盛……不……知……伶……人……苦……
歌声幽婉,有着不同凡响的邪性。我听着那一句“生生死死”,突然眼眶一热,以为是流泪,用手一摸竟然是血。
“善哉,有邪气。”和尚说。这话音刚落,道长突然蹿了起来。“今日终于等到你了——!”
那歌声骤停,我颓然倒下,这冰冷的雪地瞬间让我清醒了大半。
“……!?!怎么了?!”
眼看着道长使出了雪上飞功夫,背着他的箱,一路蹿去。
“施主您自个儿保重~”和尚说,他拄着跟竹杖,竟然一边敲着地一边也速度不俗地往前快走而去。
独留我在青楼的墙根,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就好像魂儿随着先前的歌还没有归位,所见所闻所听所想都隔着一层纱。
我恍然转过身去,却见青楼往来恩客与姑娘,犹如群魔乱舞,面容扭曲,谈笑狰狞。我大骇,不由倒退几步。
“清海!道长!你们……你们等等我!”如此追着另外两位消失的方向,落荒而逃。
如果在平时,我一定会击掌庆贺,在这个异国城市里所遭遇的怪谈,绝对是写作的好题材。但此时我只觉得见什么都十分恐惧,在街上狂奔疾走,连连摔跤。和尚与道长也不知所踪,只有不小心被我撞着的路人,咒骂和尖叫钻入耳中。
后来想来,那一准是那奇异的歌声所带来的效果。但此时我根本无暇去推断,又一个趔趄,彻底摔进了雪里。
这雪堆竟比别处深了许多,我花了好久才从中爬出,却被雪迷了眼睛。眼中冰冷胀痛,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睁开,就这样摸索着想要站起,脚底则连连打滑怎么都没法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四周的声音渐渐褪去,就好像雪越下越大,终于淹没吸走了所有的声响,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寂静。
然而这寂静并未持续多久。
紧随而来的是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嘈杂的喧嚣。就好像我突然被扔在了一个人声鼎沸的集市上一样。
眼睛依然睁不开。我无从辨认自己到底在何处,也因此更加恐慌。这就是那个和尚平时的感受么?只有声音和触感的世界。
“哎呀,又是一个生人。”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从我耳边溜过。
“看他这样子,怕是没有来过此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今晚真是热闹呢,先是有个邪气的玩意过来了,刚才又跑过去一个道士,还撞进来一个和尚,现在又来了位俊俏小哥。”
俊俏小哥是说我吗……
不过听那人说的,难道道长和清海也都在这个方向?
“呃……劳驾诸位,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
听了我的话,那些人沉默了一下,突然都笑开了。“什么地方……这厮真是没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闯进来,看来是活腻了~”
“该说不幸还是万幸呢。与那和尚不同,这个俊俏小哥儿可是没有主的。”
“没有主的话,那就好办了……”
我只感觉到气息的临近,却又不是很对劲。寻常人的气息凑近,会感觉到实体。然而在此处,除了忽远忽近的人声,和这些男男女女的说话声,我竟然感觉不到半点“真正有人站在身边”。
一定是脑子坏掉了。
此时突然有人捉住我的袖子。“八重,你竟然在这里!”未等我反应过来,我就被这人拽着跑了。
“等等……!这是?!”
那人却并不理会我,只顾拽着我跑,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只能拼命跟上脚步。腾出来的一只手只想把眼睛扒拉开。
“不要睁开眼睛。”那个人说。
“哎?”
“如果睁开的话,就会从这个地方消失,回到生者的世界。”
“生者的世界……难道说这里是死人的国度吗?”
“说是也并不是。只是一些对尘世还有留恋的家伙,找借口留下来的地方罢了。”那人说道。
如此说着,对方的脚步慢了下来,终于完全停下。喧嚣依然在,但比起先前这些吵闹的声音好像已经跑到身后去了。啊,这就是所谓的灯火阑珊处了吗?
“你还是像过去那样,遇到奇怪的事情就义无反顾地追着寻找答案。”那个人说。
“……说得你好像认识我一样。”
“没错,认识哟。”那个人说道。
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喂,你这家伙……”他说,“为什么要顶着我的名字行走在世上啊?”
这一句话落下,我的心好像被重重地锤了一拳,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是你……?”挣扎着说出这几个词,却受到了对方明快的反应:“对,是我。”
双手被对方捉住,冰冷的触觉蔓延上来。
“以我的名字,八重出道,在江户那边写些私下传阅的故事,然后交给画匠作画,到今天也有十多年了。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写出与《平家物语》齐肩的作品,但到头来也只能写一些怪谈故事,讲述武士和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他说。
“写不出的时候简直想要自杀,而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觉得手中的笔在背叛自己,明明自己想要的不是这样的,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保持着人前的光鲜,只是为了遮掩自己窘迫的灵魂。故作洒脱的样子,也是因为自己不能为任何事情负责。这样的你……”指尖的冰冷温度已经浸透了手臂,“不觉得很辛苦吗?”
“……”
“非常辛苦啊。”我仰天长叹道,就与古往今来所有被忘记的失败者一样,终于找到了那个同样也不会被记住的,长叹的时候。
“但那不是你的梦想吗?”我说。
对方沉默了,指尖的冰冷竟然停滞了蔓延。
“我是武家的长子,原本这双手是要拿起武士刀的。”我说,“我对父亲说的是,时代不同了,接下来是不用打仗的时代了,就算没有武士的名号,我也能够以别样的方式有尊严地活下去。”
“结果被老人家狠揍了一顿。老顽固真是不懂顺应潮流。”说到过去的事情,我坦然起来,“如果你还在的话,一定会竭力阻止我老爹揍我这件事吧。”
对方仍旧没有说话。
“可惜那个时候你已经死了啊,八重。”我喊出了曾经并不属于我的那个名字。
八重樱花,结果你的命运也如樱花般在尚未盛开时就凋零了。
“借用了你的名字,决定以一个出道作家为人生目标的傻瓜,就是我了。”
“…………”
“总要有人记得梦想。”我轻声说。
“虽然我做得并不好,根本比不上你啊。如果是你的话,在我这个年纪,早就成名了吧?就算拼命努力去做也不可能达到你的程度,要说辛苦的话,这样内心的煎熬才是最痛苦的。”
“真是个愚蠢的傻瓜。”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对方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是吃力不讨好,我都这么努力了,结果还要被正主抱怨。”我说。
“并非抱怨,只是叙述事实。你就只能是个傻瓜,除此之外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
“呃啊,出现了!毒舌八重的灵魂击打!”我大声喊道。
……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这是我的梦想吗?”青年对我说道。
“哎?”我不明所以。
“事到如今,就算如此辛苦也没有想过放弃的你,真的只是因为,那是我梦想?”
呃啊,这家伙,比活着的时候更加直击人心了。
“…………因为感觉到了幸福。就算卖不了钱,就算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我也会感到幸福。”我认真地回答他的询问,也算是认真地回答着自己。“但又觉得那样是对你的背叛,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向前走追寻幸福而去了呢?”
我听见了笑声,那是一个十八岁的,兼于男孩和男人之间微妙年纪,清脆的笑声。
“并没有背叛这种事,你这个笨蛋。”我的鼻尖被人用手指戳了,“看到你找到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东西,我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不知何时开始,指尖的冰冷已经无影无踪了。
“死去的人的时间已经停滞,而活着的人得奋力向前。”他对我说,“就这样一直跑下去吧,八重!”他拽住我的手,重新飞奔起来。
喧嚣声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开始奔跑,飞奔过时间和记忆,飞奔回到了最初的原点。那不过是两个少年,在夜空下的田野间,萤火虫飞舞的时刻。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想象的事情,需要有人记录下来呢。我想成为作家,写出不亚于《平家物语》那样的作品的作家。
那一定是很棒很棒的事情。另一个少年说。
……
雪几乎已经不飘了。
“看样子会回暖。”坐在廊下的道长说,他拿起酒壶敦敦敦,衣衫上多了些口子和血迹。“喂,你这小子,瞪着我的样子好像在说‘这家伙好像一条丧家犬’啊?”道长冲我说道。
“呃……”
“看样子,道长这一整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和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倚在竹杖上,一副很没所谓的样子。
“你要怎么‘看’啊喂。”道长回敬道,接着敦敦敦。
“……你们两个。”我突然有种脱力的感觉。
“鬼市好玩吗?”清海突然说。
“……鬼市?”
“在这个季节很容易撞进鬼市。”道长补充说明,“人鬼殊途,只不过在某些时刻,两个世界会交汇在一起。”
“据说能够见到故人。但如果哭泣的话,就会再也无法梦见对方。”清海说。
“哭泣啊,怎么可能嘛。”不过就算如此,我也不会再梦见他了。
“啊,果然是见到了。”清海高兴地说,“我就说过施主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不要一直念叨我!你们两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吗!”我指着僧道二人的鼻子,“那个奇怪的人影到底是谁啊!我好像差点就被他害死了!”
“是狂百器。”道长说,“人类生前所用的物品如果沾染了邪气就会变成糟糕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样子很帅就是了。”
“如果放着不管的话,会出大乱子。不过……”道长三度敦敦敦,真是好酒量。
“恐怕也是到此为止了。”道长将酒壶立于脑门上,看不出来这家伙对杂耍还是蛮有天赋的。“人生又不是故事,哪来那么多必有回响的结局。不过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想留有遗憾而已。”
“…………”
“道长您悟到了。”清海双手合十。
“到你了大师,别想蒙混过关。”道长毫不客气地指着和尚,“中途你去了哪里?”
“小僧梦见了前世。”
“哈?”
“”
“原来我这一世依然在轮回中的原因竟然是女人的眼泪,啊哈哈哈哈~”
“…………”
“…………”
我就说这和尚才是最深不可测的。
道长说,“啊呀没酒了。喂你,有没有十文零钱?”
“什么鬼!我怎么可能有零钱!”
“只能去讨饭了吗?喂大师,我们一同去讨饭吧。”
“讨饭这种事也能勾肩搭背一起去的吗!”
“不想饿死的话,你也一起来啊。”
“…………我才不要!”
雪彻底停了,天也开始放晴。冬天终究是会过去的。
第二刻,完。

你要问那个瞄准镜的另一边是什么颜色的。
“全是废话,不是那边红就是这边红。”玉梢呸的一下吐掉了自己嘴里的那根棒棒糖,糖分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脑进行活动以及提高注意力,烟草?那众筹的要命的东西死了都不要去碰。
“冷静点,那里有那这种暴躁的狙击手。”耳机里传出来的是慢悠悠的责备,当然了在他耳朵里听起来那根本就不是责备,更像是平日里的闲聊。
“啊——我说娘娘啊,能不能下次不选这么不愉快的时间进行交易啊,冷的要死啊。”玉梢咂了咂嘴,舔掉了嘴角边残留的棒棒糖,黏腻的触感让她感到了不适,但是一分一秒那只眼睛都没有离开过瞄准镜。
“别这么说啊,不选在深夜,你还要选在条子门口光天化日大喊大叫?”
“我也没这么说啊。”玉梢反驳,“但是现在和光天化日没多大区别啊,对面早就知道这里的行动了吧。”
透过瞄准镜能够看见的是对面高楼的玻璃后面和自己一样看着瞄准镜的男人,身姿整个融入了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只有头上那一小撮红发才能让玉梢勉强看见那人的位置。
在头顶染红发那不是靶心么,哪有这么傻的条子。
翻了个白眼,玉梢拆开了另一个包装纸,里面装着的是几块饼干。
手表上的指针终于是划过了12这个数字,玉梢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对准了那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晚风掠过已经被废弃的工厂,即便是在这秋日,也让人感到一丝凉意,沁人心脾是不能比的,白寒给自己裹了一条围巾还在拿了搓了搓手臂。
横刀也一言不发,指尖夹着的烟头一明一灭,直到烟灰落下在,掉在了他的皮鞋上才想起来自己在抽烟这件事。
实在是过于无聊了,在这里干等人什么的,这个阵仗完全不像是要干坏事的样子,反而像极了古惑仔和他马子。
“我说,我作为组织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怎么半点优待特权都没得。”白寒用胳膊肘戳了戳横刀,用眼角瞄着放在仓库里的行李箱。
“别废话了,明天的菜单还没定下来呢,有什么抱怨你先看看楼顶玉梢再说。”
“我听见了哦。”
通讯器里悠悠传来这么句话,横刀浑身一颤,也不知道是被风吹得还是被玉梢吓的。作为一个狙击手这女人是格外的暴躁直接,半点不像是能在极端环境下连续观察目标大半年的老手。
“说好了不要用通讯起呢。”
“真烦,通讯器好用啊,什么蓝牙无线通讯器,还没个上世纪的机器信号好。”
白寒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赞同了玉梢的意见,“于是?有人来吗?”
“没空看。”撂下这句话,玉梢那头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说起来,不是约的一点么。”横刀•盲生,是终于发现了华点。
白寒裹紧了自己的衣物,接下了话茬,“守株待兔呗。诶,明早记得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
“不要说得好像我是你们大厨似得。”横刀也不可以,给了个白眼,拍了拍自己的哈雷,“这伙计都快成菜场搬运用小推车了。”
“守株待兔?我们不是守株待条子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祸云穿了件短款的皮夹克,带着银链子,一条红色的紧身裤在夜晚格外的显眼。
“呜哇——你是从哪个夜店出来的?一晚上多少钱?”
这次玉梢的通信是从耳机里传出来的,祸云还没听完就把那玩意从耳朵里抠出来扔在地上踩了个粉碎。
“好歹是公费啊——”
这次是三个人的对讲机。
或许组织里除了娘娘,最恶劣的就是这个女人了。
“啊啊——情报通知情报通知,对面的狙击手看着我了,你们自己解决问题哈。”
顾炎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对面的人,透过瞄准镜,能够看见那个女人一会按住自己的耳朵一会拿起对讲机,也不知道在和几个人对话,没一会又朝自己比了个不雅的手势。
“我说,真的不能爆头吗。”
“不能。”
“不能。就医学上来说你这个距离爆头,死相很难看的。再说你又不是第一次互相爆头,子弹在空中碰撞的次数还少?”朱杏,撅了撅嘴,一身白风衣,里面一件粉色的绒线衫配上不长不短的裙子和便于活动的平跟鞋,怎么看怎么像大学生。
要说这两个狙击手,也是特异中的特异,谁见过狙击子弹互相打架的?
逐魂倒是撇了撇嘴,自己明明还是个实习的怎么就被拉来了?自己本来应该在食堂里面吹着空调享受阿姨多加给自己的腌萝卜一边和小女友聊天的。
“你们装样子装的像点啊,这样只像是同学。”赵衍总指挥官终于是发话了,本来他就是坐阵大本营的,怎么还被卷进这种无意义的口角之中?
“今晚的情报确定准确吗?”觉拉扒拉着自己的夜宵,咬了一口藕盒感叹着今天这顿饭的火候是正正好,“不会只是个幌子吧。”
“谁知道呢,人家只已经在那里待机一个小时了,教母的影子是半个都没有。”就在这时,顾炎发现自己瞄准镜中那个人的影子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了架在那里的武器罢了。
“全体注意!对方狙击手不见了!高度戒备!”
“不是,我们都还没到地方,你担心什么鬼。”逐魂骂了一句,拉着朱杏便跑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陪你们,一起做这种高危险的体力活嘛!!”
“因为警局只有你一个女的!我实习生都来了就别抱怨了!”逐魂反驳着,尽可能的让自己身后的朱杏跟上。
“话不是这么说啊!愿意做法医的女孩子很少的!我应该是你们的宝物!”
觉拉没来得及把最后一口白饭送进嘴里,就匆匆忙忙站起来收好了饭盒,也往案发现场跑。
“啊,那啥,我在做任务,钱一会再说。”玉梢摆摆手,昏暗的灯光下,空调开的温度过高,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很。
“别废话,你在这住了三天了我的姐姐啊,开了几瓶威士忌了自己数数。”
“那又不是你的钱。”玉梢给了白川一个白眼,死不承认自己开的就是他冰箱里那几瓶。
“我说你一个干偷窥的,喝那么多酒干嘛,不怕伤肝啊?”白川拿他那烟杆点了点玉梢的脸,“看看你自己,还说是个女的,肤色暗沉的更泥潭似得,我看你已经不是肤色暗沉了,是印堂发黑快要被条子捉了去吧?”
玉梢一下拍开了那烟杆,手背一阵发疼,拿起对讲机就是一通抱怨。
站在空旷仓库前头的三个人不得不关掉了对讲机。
“怎么,你们家狙击手又发牢骚了?” 虞老板姗姗来迟,事实上两帮人约定好的时间是零点一刻,什么一点,完全就是给条子的假情报,让他们扑空的做法。
“啊,是这样,不过速度要快了,条子可能已经有动静了。”祸云挠了挠自己的头发,“东西呢。”
“在医生手里。”虞老板也不含糊,压低了自己的帽子,似乎是从帽檐里摸出了根女士香烟递给了白寒。
“人员编号在里头。”他瞧了瞧四周,“我要的东西呢。”
横刀看了看白寒的脸色,确认了滤嘴里确实有相应的号码,也没有多怀疑就打亮了打火机烧了纸条。
这时,白寒眼前一亮,脚边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弹坑,是条子和玉梢。
没有时间了,脚步声抓紧的靠近这个废弃仓库,横刀跨上哈雷一把抓过虞老板,扔在了后座上。
“——西南——子,朝——走!”对讲机里是玉梢的声音,但是因为电波不太好,几个人都没听清楚她讲了什么。
横刀啧了一声,开向了仓库里头,祸云和白寒两个人则是朝着东面跑。
“唔!”白寒一声闷哼,手臂上就多了个洞。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
“切!一定是那个家伙教的!”顾炎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要害,对方在过小的瞄准镜前采取的走位方式和躲避方法怎么看怎么映照了狙击手最讨厌的方法。
“唐叔!把东面的路封了!他们朝你那里去了!朱杏逐魂!你们绕到仓库后面去!”
“呀吼——你好啊,狙击手先生。”
顾炎的通讯被中断了,就连着觉拉和剩余人员的耳机里都出现了这个声音。
是杨雨霖。
“我说娘娘,你这么和人打招呼不好吧。”如璋缩了缩脖子,刚刚破译的通讯密码就这么被自己的BOSS抢去打招呼用了,坐在一边的绯也没办法地摊了摊手。
“今天晚上挺冷的,去街上吃碗热乎的馄饨怎么样——?工薪阶层?”
“呜哇——真气人。”拉下了脸,坐在办公室里的赵衍都听不下去了。
“这,仓库后面没门啊!”
急忙赶到的觉拉和逐魂他们会和了,但是绕了一整圈都没找见像样的通道。
“这回没法联系空和阿芷,他们那里的旅馆和医院不知道查的怎么样了。”
白川把玉梢揪下来之后便扔进了密室里。转头去看门口铁三还在和那个实习生的小警官周旋。
“都说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你看,营业执照还挂在那呢。”铁三双手抱胸,任由那个小男孩乱翻,就连前台里头的备用计生用品都被翻出来了。
“这!这是什么!”空涨红了脸,指着塑料包装的东西质问道。
“怎么,还不允许旅馆有这些卫生用品了?”白川走下楼梯来,一脸的好笑。看了看空,又看了看铁三,接着一句话让空落魄而逃,“小伙子长得不错啊,要和我试试吗?”
“老板啊,怎么说这个讲法都……”
“闭嘴。”
阿芷的电话几乎是在同时响起来的,穿着黑色长西装裤和小高跟的女孩坐在诊疗室里翻查所有的记录,愣是没找着奇怪的点,看了监控和所有的房间也没找出半具身份不明的尸体来。
“把,把所有的药物拿出来!”阿芷鼓着脸颊,挂掉了电话。
反观恭弦笑着点点头,手里捧着老厚的医学教材满脸微笑,一头黑色长发被束起来拢在一边,“小姐这边请。”




【时间有限,BUG很多……海涵-L-】
要说这个世界是由故事组成的也不为过。人们喜欢讲故事、听故事,为故事付出金钱和其他代价,这大概就是人的本性。甚至有人因为听了故事而开始编造自己的故事,也是常有的事。岁月之下,就好比风沙和流水蚀掉岩石,留下来的故事也许与当时的真相大相径庭,但好歹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遗物。所谓当时的人、事、情感存活过的证明。
当然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人也是有的, 只不过他也不能阻止自己活在一段故事中。
“我说你啊!吃闲饭也好歹有个限度啊!”如此粗暴地打断了我对人生思考的怒吼,出自一位女子之口。
“别人逛妓院都是花钱,只有你啊!在我这里白吃白喝也快一个月了吧!不要以为你是个倭国作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再不拿出钱来的话就把你当做倭寇送去报官!”
……这个国家的女人也如此彪悍,难怪大明是泱泱大国,立于不败之地呢。相较之下我们国家的那些诸侯一旦统一了天下就开始猴急地要封赏,结果不小心把手伸到了大明这边,被狠狠殴打的事迹,简直作为本国人都感觉丢人。
啊扯远了,容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乃是八重,以大明这边的称呼来说,大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的倭国文学家”。
史无前例的意思,大概就是“从来没有哪个笨蛋因为船沉没了抱着一块门板漂到了泉州港之后又凭借狗屎运没有被当做贼人抓起来反而北上谋生成功”。
只不过却因为好多天没有灵感而没有写什么东西,只顾吃饭喝酒,把寄居处的姑娘给惹毛了……
啊呀,顺便一说。我所住之处并非客栈,而是姑苏的青楼“闲月”。如此风雅的名字,想必老板也是个不俗之人,打着“我愿为您麾下的姑娘们写一些有趣的唱词”的旗号拜会之,又约了数位姑娘聊人生,干脆把藏在裤腰里一路从故乡陪伴自己到现在的琉璃金步摇给当了出去。等等……这好像可是京都某位舞伎赠予我的信物。
不过大明前前前朝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句,作为作家,自然是不需要考虑钱财这种俗气的事啦。
结果。
“阿香~老板都说了可以让我住你这边,你这样赶人不太好吧?”
“哦呵呵,住是可以住,不过要拿银子过来啊。你以为老娘是济世的女菩萨吗?”
“在我眼里何尝不是呢?”
“滚!”
如此这般,这便是我站在桥头遥望那河岸上的柳树,哀叹命运坎坷的原因了。说道姑苏城还真是古时吴国风范不减啊,客来人往,一派精致繁华景象。正发呆之际,冷不防就被人推了一把。
回过神的时候,发现推自己的是一个年轻和尚。
“施主请不要想不开!就算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淹死的,只会摔个半身不遂而已!”
“这种算什么安慰方式啊!不对!我不是要跳河啦!就算身上没有一文钱也绝对不会想到死的!”
“哦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年轻和尚显得很宽慰。
“好个屁!你到底是在阻止我跳河还是要把我推下去!”
“哎?方向错了吗?我以为那个方向才是……”
“你瞎吗!”
“……小僧的眼睛确实是看不见,施主真是敏锐呢!”
“那你怎么知道我要跳河啊!”
“有位姑娘附在我耳边说的。”
“………………”
“‘和尚你看,那边有个穷人要跳河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听起来也是个很不客气的女人。
“少来了,这周围根本没有女人经过啊。你不会是听到卖菜大妈的怒吼了吧?更何况我根本不穷!只是暂时钱财在别处罢了!”
“非也非也,小僧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其他感觉可是很敏锐的。比如现在,那位姑娘就在您的……呃,您的身边才对。”这个和尚,伸出手去摸索,摸来摸去,摸向一团空气。
我向他摸索的方向看去,空无一人。
…………这个和尚不仅瞎而且疯。
“施主请问您相信器物都是有灵性的吗?”
“……如果有灵性的话,那支琉璃金步摇怕是会化身武家后裔天诛我。”
“哈?”
“……咳,想起了一些往事而已。大师为何突然说起这个?”
在解释了自己只不过是想要寻找一点灵感来混饭吃后,我与这位疯瞎僧人攀谈起来。谁说文学家写稿是为了追求高境界,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为了下一餐的着落而已。只有求生欲望才能激发人的潜力,饱食终日的家伙根本不可能写出震慑灵魂的杰作。
“因为啊,小僧正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疯瞎僧人说道,“你说有没有一间店铺,存在于此又不能存在于此呢?”
“大师所说都是佛理,在下愚钝,不是很懂。”
“呔!”僧人突然抽出竹杖挥向某个方向,“哪里来的妖怪!离这位姑娘远一点!”
“………………”
“你不要突然就发难啊大师!”
“抱歉啊,突然感觉到了奇怪的气息。”
“这里最奇怪的人就是你吧!说是和尚,倒是从一开始就在教唆别人赶紧恋爱!”
“因为我觉得施主您最缺乏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
“我可是常年万花丛中过的,不想罢了。”
“是嘛~?”
“呃……”
“说到这个啊,小僧倒是有一件事想问,施主身上最为贵重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啊?自然是我的脑袋瓜了。”
“说得好,只不过小僧如果提头去见,怕也是没法继续以活人的姿态留在世上了~”
“……大师您还是去看一下郎中抓一帖药吧。”
“没钱呢。”
“………………”
“你身上的脂粉香倒是很浓郁,施主看来果然是戏耍万花中的好手。”
“用不着你来夸奖我,不过托您的福,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可以混饭吃的点子。”
“哦豁?是什么?”
“不可说不可说~”突然想到了故事的框架,为了避免忘记,我从石桥上径直跑回住处,不顾阿香的怒骂“猪回来了”,一头扎到书桌前,提笔开始写。
这个故事就叫做《姑娘》好了。
说是南宋年间,一位书生在石桥边遇到一绿衣姑娘,不知其是妖,与之交好许久的故事。之后兵荒马乱,乱军即将攻入城中,书生想同姑娘一起逃走。绿衣姑娘哭着说妾身真身乃是这棵柳树,扎根于此,无法离开。公子若有情谊,就折下妾身的一根枝条,权当妾身与公子相伴,速速逃命去吧。
书生大惊之下悲从中来。说柳妹你待我不薄,人妖殊途这句话我是不信的。奈何桥上你可要记得我,说着便在柳树下自刎而死。书生的血渗入树根所在的土壤。那柳树竟然在无风的时刻颤抖摇晃起来,树冠上泣出血来,顺着柳枝往下淌。就如同妇人哭泣一般。
后来呢?后来乱军破城,百姓死伤无数。这棵柳树也在战火中被烧成焦炭。
奈何桥上可记得?烟花三月杨柳青
我写完这个故事,舒畅不已。再动笔改成一首唱词,乐颠颠地去找阿香。结果找了一圈,恰好阿香在接客,只得作罢。将稿纸放在窗下书桌上。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扮相华丽的美艳女子瞪着我。
梦里的我承受着她的视线,却不知何故。“想必姑娘一定是哪路的神仙,不知在下哪里得罪了,惹的您竟然跑入在下的梦中……”
“那位小和尚说,他原本用于和我结缘的重要物什,被你取走了。”
“啊?”
“那东西在哪里,快还来。不然可不要怪本宫不客气。”
“哪有那种东西啊!”
“看来你是不吃点苦头就不知道痛的顽固男人……”那位女子虽然美艳,但此时隐隐有了杀气。
“…………且慢。”我伸出手来阻止,“那秃驴……”
“不许叫小和尚秃驴!”
“…………那那位大师,说过是什么东西吗?”
“小和尚说,与你的脑子有关。”美艳女子伸手过来就要摘我的头。
“姑娘何至于此啊!在下真没得罪你!”
“你把头拿来,本宫就能与小和尚结缘,你若不同意,本宫就强取!”
“………………”不知道神仙杀人算不算翻天条,就算犯,我这颗脑袋也装不回去了。说不定因为白死,在当地当个城隍之类。呃啊啊啊,还是不要了!
“且慢!虽然头不能给你!但是这里有一个在下从头中取出的故事,不知姑娘可否拿走交差。”真是佩服自己,在梦中居然如此睿智。
我不知从何取出了一叠稿纸交予面前的女子。女子将信将疑的拿了过来,看了几行。“哎呀,这故事好生可爱。那书生定然是长得极其英俊的,不过柳树精是怎么回事,那种脚下生根的乡下妖怪真是一点品位都无啊,连霓裳霞披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算幻化成人形也肯定是个村姑!”
“是是是……”我看着这位女子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读到故事最后是不是打算把我的脑袋拧下来。
不过好在她并没有读完。“那这个我就收下了。你还蛮可爱的嘛。”如此说着,女子飘然而去。
我猛然惊醒。再一看窗前书桌上,已空空如也。
…………眼花了吧?
不,真的空空如也。
这个时候月上树梢,阿香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八重重~听说你有好的唱词给我?”
“呃……”
不知道现在翻窗逃走是不是来得及。
第一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