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是黑暗的,世界又是苍白冰冷的,直到被挖掘出来,我对世界的感知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已死去多年,内里的液体在受精之前就腐败了,出生时姐姐都不愿蚕食的卵,毫无价值,不会诞生生命也没有意义。
我该沉寂于泥土之中,我的意识可以感知,那时候对寂寞这种情感并没有太大认识;树木生长,菌类在它的脚下冒出;虫子在它体内繁衍消亡,我听着身边的一切,随后的一日,几声尖锐的鸟鸣后,身边的声音都消亡了。
流云从身边穿过,我在越鸟声旁见了千山万水,忽来的下坠,急剧的寒风吹破了鸟阵,我被抛下了。
雪接住了我,我想摔碎了也不错,我的身体会回归到泥土之中,植物会篡取我的养分再度生长出来,生命的循环莫过于此。
我记得榻榻米底下死掉的飞蛾,它下坠之前摇曳着,挣扎着将鳞粉扑得到处都是,蚂蚁欣喜地用触角点碰着它,随后成群的蚂蚁排着队来了,绿色的汁液在破开禁锢后涌了出来,不久飞蛾就只剩下了没有价值的翼。
秋天的末尾,我身边死掉了一只松鼠,最后的雨淹没了我们,它的身体一半裸露在水面上。冬雪来了,水被冰封,松鼠裸露的尸体被鸟兽啃食,一半的枯荣一半虚假的生机。
冬日太静了,静得听得到雪落下的声音。狂风呼啸的怒吼,无情地带走所有生机,像一座苍白的牢笼,一望无际,放眼就是世界的尽头。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所谓“寂寞”的情感,我只是看着,无法理解,也无法感触。
当冰雪消融,蚯蚓蠕虫把剩余的尸体带入泥土,连同我一起,世界又回归了黑暗。
四季的变化在泥土中并不明显,虫子从我身体爬过,带着泥土细微的沙沙声,我听到地底的脉动,树木窃窃私语着什么,这种声音在风穿过树叶时我也听过,但却从未如此强烈。
树木的根须颤抖着,像是激动又神经质的老鼠,它们靠近我,缠绕我,冬日过后它们都活过来了,我想我的命运也会和那只飞蛾、松鼠一样,我会回归于大地,然后重新被塑造,像千万年以来一样。
如果是一个生灵被如此缠绕会如何?这种问题在我不能称之为“思想”的思想中闪过。
它会痛苦,它会挣扎,最后哀嚎死去?
可我本就是死去的,生来就死去的,不及见识一抹阳光,不曾感受过,我都快有被称为“气愤”的情绪。
不知道过了多久,树木又沉寂下来了,我知道冬天来了,这样的生活不知已经几个春冬,我的意识越来越薄弱了。用不了多久树木就会完全吸收我的身体,一切就要结束了,连同未见识过的一切,这难免有些遗憾,或许是这些多愁善感的树木感染了我。
它们总是唱着歌,诉说着森林中发生的故事:
猎人为了他的羊群捕杀狼, 猎人的孩子被狼吃掉了;美丽的贵族女子和穷小子私奔了,最后被抛弃,女子就吊死在西角的桦木上;革命的年轻人追赶着贵族,他们殴打他们,血就溅在树根下......
它们总是喜欢唱一些血腥的故事哄我入睡,唱完还舒适地砸吧砸吧根须,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死者会有梦吗?树木又会不会呢?
我在黑暗中也来越迟钝,想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某天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最高大的树木轰然倒下,震得大地都抖了起来,根须松开了我,我向下坠落着,一只没有温度的手抓住了我。
黑暗中映射出一束光,阳光的温暖和冰冷的手,这些我都感受不到,但低落在灰色蛋壳上血却是滚烫的,真真实实。
第一次我感受到了。
生命的律动,血液渗透进了我的卵,卵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心脏开始跳动。
扑通,扑通——
越来越快,抓着我的手铿锵有力,他带我离开无尽的黑暗,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寒意,冰雪的气息,但比冰雪更冷的是拖着我的人。
我看见了,透过蛋壳朦胧的光,周身漂浮着浓厚的花香,冬日里应该是没有花的。
第一次我有了渴望。
我想见到他,那迫不及待的心情,多一刻我的心脏都会在身体中爆裂开,我敲打着禁锢我的保护壳,我太过急迫以至于没有发觉自己的变化,蛋壳破碎了,阳光漏出来,我见到了他。
那是漆黑的光,充满了迷惘,萦绕着死气,漫漫雪原中唯一的颜色。我深爱他,那发自灵魂的情感再也抑郁不住,想要冲破躯壳,大声呐喊出来,就算是世界全部玩完也没关系,只要他,只有他!
其他事物怎么样都无所谓,就算他不在乎我也没关系!他可以杀死我、唾弃我、蔑视我,我全盘接受!
千千万万的胚胎中,有千千万万个苍白的躯壳。
在被你触碰的刹那被赋予了灵魂。
“给我......名....字。”
“苍。”
我伸出手想去抓住他,但这幅身躯太过薄弱,近乎透明的,看得到绿色的血液在其中流淌。
我第一次产生了羞愧的情绪,雪冻得我落泪,体液滚落到雪地里的时候,我被急剧疯长的植物淹没。
会被植物杀死的。
这样的念头在心中环绕,会被吞噬掉,它们在生气,我没有遵守约定。
那光亮就在这些植物的掩盖中消失了,我张开嘴想要呼喊,植物就进入了我的身体,它们快速疯长着,纠缠我的五脏六腑,一颗椿树从我眼眶中冒出来开了花。
救救我!
我的手胡乱的向前伸去,植物将我的身体裹得更紧,我的骨头碎了,和身体里的植物摩擦着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在我快要死去的时候,身体里的植物枯萎了,一朵朵红色的花开了,吸取了养分炫目至极。
禁锢着身体的植物枯萎粉碎,我站在雪地里,那个男人依旧站在那里,红色的花从他的脚底蔓延开来,我一时失声,不知如何是好。
他走向我,冰冷的手将我抱起,疲惫感席卷整个躯壳。
也许藤蔓约束的是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于此永远禁锢在这片雪原中,我的名字是苍。
苍白,残酷又冰冷,只要被你需要,我将献上所有。
只为抓住那一点光,黑暗中唯一的希望,什么都可以忍耐,现在我学会了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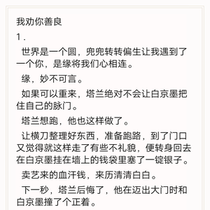

三头老虎各自盘踞屋檐,压低着身子,喉咙里发出警示的低吼,其中一虎动了动爪子,瓦片翻飞,掉在了地上。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像是一种信号,三只凶兽缠斗在一起,从屋顶撞落到了室内,在普通人眼中像是房梁支持不住瓦片的重量,倾倒了。
塔兰看得真切,引发这现象的那三头老虎,其中身形最大的白虎是觉拉,外表和寻常老虎无异的是这家主人造的业。
那凶虎是从一幅画卷中生出的灵,凶虎的主人已经被它杀害,但这灵却不肯离去还伤了无辜的人,先前觉拉和它打斗时占了上风,但突然出现了另一只白虎,对方敌我不明,现如今都打作了一团,觉拉显得有些吃力。
凶兽之间的战斗不是人类可以参与的。
塔兰在被凶虎袭击时伤了腿脚,一时无法起身,他的身旁躺着被开肠破肚吃了一半的富商,那人的肺腑和血散在地上把塔兰的白衣污了个透彻,看架势手在巧的洗衣妇都洗不干净了。
这趟浑水可不是自己找上来的,塔兰并没有义务救人,他不是道士,不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因果报应,这人种了什么因便得什么果。
但波及旁人就不应该了。
这家主人是个富商,生性爱虎,家中物件十件里面有七件是和老虎有关的,虎骨,虎牙这些都是寻常收藏。他出钱雇佣猎户去捕杀老虎,乡里称他是个大善人,当猎人给他送去一只未断奶的小虎时,富商睁大了眼惊呼一声,连忙让猎户杀了小老虎,做了件玩物。
这人若是真的爱虎便不会做出残害老虎的事来,人对喜爱事物的表现真是矛盾,颇有叶公好龙的架势,想必他收藏的那些“虎”的来路也不全是光鲜的,背地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外人不知道,他自己可清楚。
只可惜这个人不会在睁开眼睛夸耀他得到收藏物的故事了。
受邀到富商家里塔兰并不情愿,往日里塔兰也很少接受这种邀请,之所以会蹚这趟浑水还是为了拿回自己遗落在虎丘山的物件,东西虽小但意义重大。
那是姐姐的遗物,也是她留给自己唯一的东西了。要是普通东西丢了,那就丢了吧,说明他命里该有这一劫。
塔兰回忆那日虎丘山,正是佳节,民间自发组织了庆典,富家子弟们邀请了许多乐坊到搭建的歌台上展示才艺。自己安身的乐坊也受到了邀请,他原想推脱,结果被管事姑娘连人带着琵琶轰了出来,觉拉笑他连一个姑娘都可以将他抱走。
住处不让回,只能跟着自己的师傅们一同前往。
在节日里朝廷放得宽,没有夜禁,夜里倒是热闹,货郎捣弄着稀奇玩意儿,小贩也吆喝着小吃,师傅们带着塔兰四处转悠让他开了眼界,待她们游玩够了才一个个不情愿地拿起吃饭的家伙站到台上,和对家赌气似的比起了手艺。
美人抚琴争艳,尽管已是秋日,叶正黄,百草枯,但自她们的琴下却生出了春意。
塔兰坐在乐师的队伍里轻轻拨撩着管事姑娘给他的琵琶,琵琶虽说不合他的手,但也不影响演奏,他听身旁的人热烈地讨论着新得来的琴谱不禁笑出声。
台上有一女子,伴着乐师的独奏,翩然起舞,姣好的面容犹如盛艳牡丹,一双含着笑的凤眼将台下的男子的心魄都勾去了,惹得女伴们不满地扯紧手绢。
乐坊之间的比试也算是商品展示了。
自家乐坊收场后,塔兰被独的推出去试了本事,这倒也不困难,他的天赋不言而喻,着实是惊艳了一把,更有登徒子想问管事买他一夜,有特殊喜好的人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塔兰卖艺不卖身。
现在安身乐坊也只是暂时的,兴许过几日他就会离开姑苏城,起初到乐坊他只是想住几日而已,没有身份住店可是很难,幸好那些烟花柳巷不要什么身份证明,乐坊的管事看他对乐器颇有研究,便留了他,但塔兰提出了不签卖身契的要求,管事应了。
再者塔兰也没有卖身契可以签。
在收拾家伙回乐坊时一人将塔兰拦下,来人一副纨绔子弟模样,语言却意外的切实,塔兰静静的听着那人说话,觉拉在一旁告诉他个大致。
公子哥讲他父亲近日得来了一幅珍贵的虎啸山林图,想邀请宾客到家中欣赏,于是就想邀请塔兰到家里为宾客表演。
公子哥讲完后塔兰投以微笑表示回绝,在场乐师不少又何必只请邀自己一个人呢,再者,近期事物如此之多,塔兰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听罢,被拒绝公子哥好似喝醉一般撞到了塔兰身上,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耳坠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掉的,不排除是那人有意为之。
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自己已经是落在脏水沟里的鱼了,结果也在这里,自己果然不是番僧。
觉拉跟着自己去了富商家,进门不久就表示出了对这家人喜好的厌恶,任谁都不会喜欢一堆和自己形态相似的死物,塔兰对觉拉的不满没有任何表示,这和自己进出红室没有什么区别。
富商的儿子对塔兰热情,在宾客入席前带着他在院子里走了一遭,也不管塔兰听不听得懂讲了许多自己父亲藏品的故事。宾客到席之后这些故事又在被说了一遍,众人闲谈之际话题引到近期城中的一件怪事上。
近期城里的打更人总是说在巷子中看见大型猛兽的身影,有胆大的人凑上去看却是发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内脏,混着泥土染着斑驳的血迹,兴许是野狗互食也说不定。
一时众说纷纭,但还没有结论闹得人心惶惶。
众人戏说是不是富商家养的老虎们化作精怪跑了出去,所以才没有人发现城中野兽为何物。
富商笑罢,叫小童到书房里取今日宴会的主角,小童久久不来,富商面露难色自己领着客人到书房。只见房门大开,富商踏入房间惊叫一声便跌坐在了地上,好奇的客人跟着进来瞄了一眼吓得慌了神,居无一人想起要求报官。
那小童被刨开了胸膛,仰面倒在地上,头颅不翼而飞,血落在了展开的画卷上,画上赤竹颜色艳丽唯独不见应该在画中的老虎踪迹。
混乱中一滴粘稠的液体落在一位客人的头上顺皮肤着留了下来,他疑惑地摸了自己湿润了的脸。
血。
客人抬头望向房梁,对上了一双惊恐的眼睛,血液自眼睛的主人鼻尖低落,入了客人的眼。烟云凝结,一头虎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它松开口随后头颅坠落。
旁人尖叫着跑开,富商在听到尖叫后才回过神,连滚带爬地往门外逃,在半个身子都出了门槛时又被拖回了房中,门槛外的地上留下了一串绝望的血色抓痕。
————————————————————
想要杀死灵就需要杀死器。
不出意料凶虎的本体就是那副画,两条人命是个麻烦事,在解决完这件事之后自己又要踏上旅途了。
塔兰笑得勉强,画卷在离自己三米外的地上,先前自己还可以正常活动,凶虎察觉到他的意图后一掌将他拍出几米,现在他算是半个伤残想要靠近更是困难了。
大意了这是他自己问题,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觉拉。
塔兰看不到觉拉和其他的老虎去了什么地方,但是耳边的兽吼还在,属于觉拉的声音还在,他稍微可以有一些底气。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觉拉这样和人或者物打斗着,自己一次次的陷入危机,对方又怎样一次次的解救自己,如果自己不从那片竹林里把他带出来,他会不会更自由......
或者还是在那里一直无声哭泣。
塔兰摸上腰间的萧,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划痕,有新有旧,新的划痕还在凭空增加。
自己不是累赘,至少要为觉拉做些什么。他深吸一口气,手指触着满是血污的地面慢慢的移动到柱子旁,靠着柱子站了起来,他的五脏和四肢都在作痛,仿佛要散架一样。
他一步一步地挪着步子,在房间里找着从自己手里飞出去的耳坠。
觉拉和另外两头老虎战场又回到了书房,拉开距离后,觉拉警惕地护在塔兰身前。
“你还可以对付吗。【藏语】”
塔兰觉得他的声音此时此刻一定很难听。
“很难对付,但不是不能解决,你的东西找到了没。”
“找到了,接下来怎么做。”塔兰指着凶虎掌下的一抹朱色,镇静地说到。
觉拉鄙夷地呲牙没有说话像是在思考问题,一张虎兽的面孔也能有那么多表情,放在平时绝对是很逗趣的。
“你要命还是遗物。”
“我都要。”
“麻烦!早干什么去了,”觉拉凶道“只有一次机会,一刻间!你拿到了我马上带你走,扰乱大了,会有人来处理烂摊子的。”
塔兰默允,朝着柱子后挪了挪,觉拉勾起爪子,猛的扑向前,卯足力气朝着一只老虎的脸挥去。
三虎各自为立,否定了塔兰一开始想的画卷中有两头虎的构想。
又是一阵野兽的撕咬声和低吼,三只老虎又打作一团,塔兰抓准凶虎挪开步子的时机,跑到到耳坠的附近一把捞起那物件。
算准时间,觉拉从战斗中脱身,巨大的虎型化作男子姿态,他快速的揽过塔兰的腰,带着对方冲出书房......
“小子,作何感想。”
“......疼。”

横刀和大哥离了乐坊又不知道跑哪里快活去了,不过他也不在意,塔兰并不在意器和器主是什么关系,他不会去使用他们,在自己看来那很别扭,对大哥他们也是。
一个人的时候塔兰总是喜欢发呆,望着街上来往的游人,坐在乐坊的窗框上吹奏自己制作的竹笛,竹笛的声音盖不过姑娘手下琵琶,他也不气索信合调衬了那琵琶与歌声。
游人驻足望向高台不见一位歌女,却只见年少白头的塔兰荡着腿吹着笛子,熟悉这乐坊的人都惋惜――这年纪轻轻就盲了目,哑了声。
冬日早已过去,小贩在街头叫卖着粗粮小食,姑娘们换上了新衣,在院子里比较着那家的公子哥送的礼物最为贵重,那个最合自己心意。
绿柳抽枝,压抑了一个冬天只埋汰在店里着实可惜,小姑娘扯着塔兰的衣服偏生要他伴着出去添置铅华胭脂,这一趟吧,自己的脸又要造罪了,不去呢,自己的耳朵要遭罪,定夺下来还是去了比较好。
说起来这女子的兴趣来的快,去的也快。前一秒还欢喜的拉着自己购置胭脂布匹,下一秒见那初春桃花,要自己为她折花,自己不肯,便不顾女子风度折下花枝恼怒地塞进了自己怀里,拉着姐妹们走远了,完全不顾自己是否还回得去乐坊。
自己在这人群中手里捧着枝桃花,难免有些奇怪,塔兰微微睁开闭着的眼,看着手上开了花的桃枝。
“你在干什么?”玉梢望着在人群中不动的塔兰,忍不住出了声。
玉梢又向人要了可以出入的符了,想趁着春色望望花,可惜的是她时间算早了,百花还没有开,今天她唯一见到的花,就是塔兰捧着的这支。
“哪些姑娘丢下你走远了,不去追吗?”玉梢看着姑娘们离开的方向,转头对上了塔兰满含笑意的眼,一蓝一金和那家养的波斯猫一样,也和店里的哪位娘娘一样,漂亮的打紧。
这人果然的不盲,对他的关心可是多余的,玉梢想到。
“你要回去了?”
玉梢有些扭捏,难得遇到一个见过的人,对方可能马上要回家去了,这一趟自己又得是一个人了。
想要一个人陪而已,这样的话无法对人说出口。
不知是不是被对方看透了心思还是什么,只见塔兰闭上眼侧头,用手点了点自己的头发示意玉梢,玉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发髻,摸下了一片桃花。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自己一直在看人群都没有留意过路边拿来的桃树,让别人提醒自己头上有东西,失态了。
玉梢的表情有些绷不住了,塔兰还是那幅笑眯眯的样子,活脱脱是一只猫,她再次伸手想要确认自己头上还有没有花瓣,手却被塔兰握住了,玉梢愣了神。
塔兰松开玉梢的手,挨近她,将落在她发间的花瓣取下,放入了自己刚刚被乐坊姑娘塞给的香囊里,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将开了桃花的桃枝稍加修理,当做簪子插入了玉梢的发间。
“这可有够傻的。”
待塔兰弄完,玉梢推开他。
“......美人桃花面,很漂亮――”
到底是人漂亮还是桃花美说不清楚,看吧这人果然不是个哑巴,说起话来油腔滑调。
“比起桃花我更喜欢,梅花。”
可惜这个天里见不到梅花了,梅花开都时候自己还在店里积灰。
玉梢摆手作势要把头上的花枝取下,在塔兰的注视下又放下了手,换得了塔兰又一个微笑。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除了笑就没有其他表情。
塔兰从腰间抽出笛子,握着笛尾,玉梢握住了另一头。
“接下来呢?”
塔兰不做答,只是用笛子牵引着玉梢,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虽然乐坊的师父们很少会关注这些,但入乡随俗,对人太过逾越就是冒犯了。
“你不回答我,我可要走了。”
塔兰松开手,玉梢握着笛子不知道该干什么。
【等我一下――】
塔兰张开,没有声音出来,玉梢还没有反应过来,塔兰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这个人要是就这样丢下自己,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一定把他送上天,她保证。
玉梢呆呆的站在原地不是,她走了几步,街旁的豆浆小贩招呼着她过去。
“姑娘在等人吧,来喝碗豆浆暖暖肚子吧,我家豆浆可是老字号了!”
玉梢摸了摸身上,钱袋没有带,不好意思的回到:“抱歉呀,我身上没有带钱呢。”
“没关系,算我请你的,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等着,怪可怜的。”
一个人等着嘛......对啊,自己一直在等着什么。
温热的豆浆不添任何佐料,一口下肚暖意便升到了心里,玉梢放下碗,坐在小贩摊位的椅子上,计算着塔兰离开了多久。
半个时辰了。
自己真傻,居然真的等了这么久。
“谢谢店家的豆浆,我想我等的人不会来了。”玉梢起身拍了拍裙子。
“要走了嘛?下次再来呀,你说着小伙子气不气人呀,让你一个大姑娘等了那么久!”小贩替玉梢打抱着不平,玉梢再次谢过店家,朝着徒然堂的方向走去。
“店家,如果他回来了,请告诉他,桃花也很好。”
自己出来太久了,该回去了,不过下一次,下一次见面一定要狠狠教训这个放自己鸽子的混小子。
玉梢摸着头上有些不精神了的桃花,晃动着手中塔兰留下的笛子。
卖豆浆的小贩歇了精神,塔兰回到了遇到玉梢的地方,他手里攥着一支做工细致的梅花头簪,不见玉梢,游人依旧。
1.
离开寺庙的那天,无情的风肆虐,吹过枯黄的草地,雪花铺天盖地袭来掩埋了雪地中的足迹,风声盖过世俗杂音。
什么都无法传达,声音被风吞噬,喉咙嘶哑了。
什么都看不到,一望无际的纯白刺痛了眼睛,如果流泪的话,会失明吧。
姐姐一直都是这样的感受吗?
奔跑啊,奔跑啊,向着迷茫的荒原。
怀中的器好像在说着什么?寺庙里面的器是不是已经全部被自己摧毁了?解脱了吗?痛苦的一生,活着的时候作为奴隶,随意买卖的附属品,死去之时的苦痛折磨,死后成为“圣洁”的法器,这样的一生,结束了吗?
2.
进入寺庙时,塔兰失去了一切。
姐姐的眼睛看不见,姐姐无法说话,最合适的材料,纯洁的少女。大喇嘛拜访主人家,发现了珍宝一样的姐姐。
塔兰一无所知。
【我们希望和主人家交涉,这是一份荣誉。】
大喇嘛如此说到。
制作阿姐鼓需要纯洁的少女皮,不受世俗污染的少女少之又少,被选中的少女会被夺取眼睛和声音,在合适的年纪剥去皮。
姐姐不需要被人夺走这些,神明拿走了它们,现在大喇嘛要带走姐姐,将她献给神。
奴隶不是人,可以随意处理。
主人用姐姐从喇嘛手中换取了去世七年之久的活佛的“万能灵药”,主人的夫人生病了,需要神明的力量才能恢复。
姐姐不见了,塔兰回到主人家遇上大喇嘛来为主人赐福,他抬头望着大喇嘛,异色的瞳映入大喇嘛的眼。
【主人家,这孩子出生在什么时候?】
大喇嘛问主人。
【我记得是在活佛死的那天。】
主人回道。
【是遗漏的吗...您应该感到高兴,是我们遗漏的灵童,恕我冒昧,我们可以把他带回去吗?很有可能是活佛的转世,如果在佛学上造诣领悟比得上其他人,他就一定是了。】
【这是真的吗?我实在太荣幸了。请您将塔兰带走吧。】
3.
没有人会在意奴隶的人生过得怎么样,奴隶的孩子还是奴隶,和牲畜无异,老奴隶生小奴隶,小奴隶长大了又会生下新的奴隶。
塔兰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在奴隶堆里孩子混杂,久而久之大人们也都忘记了谁生了谁,不过这没关系,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是姐姐,只有姐姐,姐姐是亲人,不可质疑,塔兰这样想着。
姐姐是黑暗中的光,是灯,在寒冷的夜中紧抱着自己,她瘦小,但总是很暖;她的长相是什么样塔兰早就遗忘了,在绵长的记忆里只有她的温度无法忘记。
寺庙里有很多和他一样被称作灵童的孩子,他们在同一天出生,同一个时间,上一位活佛死的那一刻。他们学习经文,只为了成为那一个唯一。
寺庙和主人家没有什么区别。
学习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记住东西的内容并不难,塔兰九岁成为了“唯一”。
大喇嘛告诉他要怜爱众生。
他看着一个个富人,朝他们伸出了手,为他们赐福。
没有一个穷人,他想到,穷人如何得到祝福。
大喇嘛告诉他要不悲不喜,大彻大悟。
天井上尸骨堆积,秃鹰啄食着亡者腐烂的肉,展翅抓着无法吞咽的骨头飞向高空,骨头落下,摔个粉碎,强酸的胃液消化了稀碎的骨头,什么都没有留下。
无论什么人,死后什么也无法留下。
塔兰环视周围,高台上,只有他一个人,台下两侧的喇嘛逐渐举烛离开,最终只剩下他一个人与一束暗淡的烛火。
清风拂过,熄灭那微弱的光。
4.
姐姐在这里。
他能感觉到姐姐的抚摸,她的体温,她在这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姐姐还是姐姐。
黑夜中无数的声音从玲珑塔里跑出来,钻进他的耳朵。
【好痛啊――】
【不要在敲了】
【我的皮!!!我的骨头!可恶啊!可恶呀!】
【救救我啊――】
......
塔兰记得那玲珑塔是喇嘛们用来存放法器的,这些祭拜神明的器具,一个个都是由活生生的人身上取下的材料做出来的。
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终结,灵魂的死亡才是,哪些死去的人以器的形式被困在了这里。
姐姐也在这里,她微笑着,在黑夜中出现,穿过寂静的走廊,来到自己面前,和昔日一样,从身后抱住自己。
【什么都不用怕,我的灵魂会永远在你身旁。】
姐姐堵住塔兰的耳朵,隔绝玲珑塔里传来的声音,塔兰第一次听到姐姐的声音,轻柔得像风,和姐姐的名字一样。
是不是只有自己才听得到这些声音,他没有去细思,只要姐姐在就好。
【他们很痛苦,阿姐你也一样吗?】
【能陪在你身边我很幸福,塔兰。】
活生生剥皮的痛啊,怎么会不怨恨呢,他看过许多人被大喇嘛带进了红室,再出来就换了另一个样子。
【姐姐,我想看看你,为什么你只愿意在烛火全部熄灭的时候到我身边。】
【......】
姐姐哑然,她身上不断滴落下的血污落在地上又消失,塔兰看不见,这样最好了。现在的她完好的只有一双手而已。
能触碰他的只有一双手而已。
5.
塔兰不合常理,他出生血统低微。
大喇嘛为什么会选择他,对此他一无所知。
他无法离开莲坐,寺庙就仿佛是他的整个人生,什么宗教领袖?政治,都与自己无关,在成年之前摄政王会打理好这一切。
大喇嘛是他的老师,也是另一位活佛,大喇嘛说塔兰是化身,只要稍加修饰,又是一位大悟的尊师。
在大喇嘛身边,塔兰失去了孩子该有的情感,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会压垮人,但他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塔兰见过寺庙外来朝拜的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虔诚朴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孩子看着风中飘扬的彩旗,雄鹰翱翔天际,牧人高歌,庆祝着, 如果自己的存在可以让人快乐,那真是一件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事.....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本性无我。
要悟到这种境界,还是人类吗?
但是,自己的存在真的可以让人快乐嘛?
6.
他以为自己早已入化,脱离了俗世的苦与乐,但现实还是告诉塔兰,自己和俗人无异。
姐姐失踪了,姐姐的鼓被人偷走了,大喇嘛抓住了那伙盗贼中的一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都忘记了。
一个念头一直在他脑海里打转――要疯掉的,没有姐姐的话,很快就会疯掉的。
塔兰远远的望着大喇嘛,浓厚的香烛味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让他窒息。
自己该怎么做?现在该干什么?
【阿拉,您怎么了?】
大喇嘛注意到塔兰存在,平淡的问道,塔兰不理会他转身跑过悠长的走廊,没有人会给他堵上耳朵了,哪些器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听到我们!】
【带我们离开!】
【我不要在这里,带我离开――】
【烧掉我吧!我不要这样!好痛苦――啊啊啊啊!】
.......
刺耳的尖叫还在耳边回响,是那个窃贼的声音还是别的,这些声音让他头昏脑胀,前方的阶梯在眼中模糊,脚下的红色地毯像被踩着的鲜活内脏,为什么要奔跑?自己在躲着谁?谁在追着自己?
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自己为什么才肯接受姐姐已经死了的事实啊,只是一个物件而已,那面阿姐鼓,只是一个用姐姐的皮做的物件而已――
阶梯消失,塔兰摔到了地上,鼻腔内有温热的液体流出,落在地毯上被吸收了,留下了深红的印记,血液混合着眼泪充斥着他的口腔。
今后的人生该怎么样?自己都修行还不够,修行,自己是否更像人了?
悲伤已经无法抑制住了,心脏快要裂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