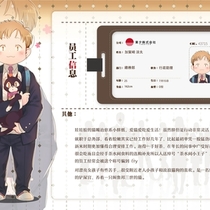1、
大约九点,海面上出现了几只丑鸭。
水上的雾气和薄纱一样盖着大海的云随着朝阳升起而消散,天空湛蓝,海水深暗,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寒气。
丑鸭随着海水摇摇晃晃,仿佛浴缸里的橡皮鸭子,其中一只抖抖羽毛钻进水里,接着又把脑袋伸出水面,柴崎良介抓住这个机会给它拍了张照。
直到昨夜入住旅馆时,夜空中还纷纷扬扬飘着大雪,让人不禁怀疑起声称第二天会放晴的天气预报。今早出发时虽然不再下了,可周围一片昏晦,防波块之间的缝隙都塞满了雪。而现在,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丑鸭羽毛上的水珠也跟着一起闪闪发亮,天气晴朗得让人惊讶。
今天可以一直在室外待到傍晚吧,良介想。
游船在水面上平缓地前进,海水轻轻推着船舷,让人产生轻微的眩晕感。
良介把目光从吃水线上移开,更远处的海岸线清晰可见,光裸的赭色岩石之间,聚集着上千只这样的小巧海鸟。
丑鸭身体上的条纹十分明显,像是有谁毫不在意地用饱蘸了白色颜料的油画笔,在它棕灰相间的羽毛上匆匆挥下几笔,而头颅后方的白色圆点又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它的眼睛就长在那个极不协调的位置上。这样略显滑稽的外表,为它赢得了意大利哑剧中的“丑角”之名。
然而近距离观察,就可以看到它收拢的翅膀、蜷缩的颈、鼓鼓的脸颊和上面意外不起眼、带着某种困惑神情的、圆圆的小眼睛。虽然听不见,良介还是可以想象远处它们拍击翅膀、在水面上直立着身体相互交谈发出的聒噪。三趾鸥和灰尾鸥也在低空盘旋,不时落在积了雪的沙滩上,那里的雪早已混合了沙子、羽毛和鸟的粪便,被弄得乱七八糟。
这些海鸟在更远的北方繁殖和生活,因此还盖着雪的这里被它们用来越冬——成群结队、带着同样滑稽的标记、同样呆然的表情,从一个寒冷的地方,移动到一个不那么冷的地方。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行动,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生存下去的条件。
这是自然赋予它们的反应机制,作为鸟,大概无需去想自己的羽毛为什么长成这样,为何要跟着大家一起飞行,以及每年的路线正确与否。虽然迁徙过程中也会遭遇恶劣天气、食物短缺、天敌袭击和伤病掉队,但无论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习得,它们不用问也知道如何选择。
——但人不一样。
即使聚在一起可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终究还是不会带来什么结果,只能离开人群、孤身一人,去面对一片迷雾中的未来。群聚着鸟儿的沙滩让良介产生了古怪的联想,想到N厂车间合上的卷帘门前面,把脸缩在围巾和领子里,彼此对视,低声交谈,把地上的雪踩得乱七八糟的工人们。
2、
T市市郊的景象几年来几乎没有改变。通往市外的路上阒寂无人,皑皑白雪雪被扫到道路两边,两条车辙从路中央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消失在蓝色天空下面的树木中间。线条简洁的建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空旷、安静、秩序井然。
不久,周围的建筑逐渐稀少,远处金色的枯草中间,无人清扫的积雪冻得结实。几小时前,说不定会有家庭驱车经过,前往有滑雪场和滑冰场的市民户外活动中心,但看起来天黑得很早的周日下午,并没有人想要到这里来。
良介抬头看看缓坡上方方正正的水泥建筑,早先这里工厂林立,它算是相当大的一间厂房,如今和它比邻的建筑全被拆除了,只留下这孤零零的一座。灰色外墙上修了带金属扶手的玻璃走廊,一部分墙壁被打通,以扩大室内空间,原来绘制着商标的地方已经被漆成淡绿色,在天空和草地的映衬下像棵倒下的树。
即使如此,还是无法抹消过去那个由黄色、橙色、粉紫色构成、鲜明到俗气的标志的存在感,良介几乎能看到点缀着斑点、星星图案的“TUMMY”几个字母,浮现在淡绿色的市民集会所外墙上。
他走近这栋建筑,站在走廊和墙壁形成的角落里。为阴影遮蔽的草坪上还有积雪,潮湿而阴冷的气息从脚下传来。
良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犹豫着,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
3、
N厂是A社控股,靠专利技术为其生产无菌包装的工厂,A社破产时还积压着大批库存。假以时日,说不定还能找到新客户慢慢摆脱窘况,但当时各行各业都在裁员、减薪,连附近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的港口城市都受到影响,不少工厂相继关停产能。造纸、包装行业发达的T市也倒闭了一大批公司,员工不到二百人的N厂自然未能幸免。
早在K大读书时,良介就常在寒假来T市小住,观察记录过冬的鸟类。他对这座宁静的城市颇为熟悉,也挺有好感。入职之后,公司总部就位于离这里一个半小时车程的S市,随部长考察过几次后,良介结识了经营家族工厂的内藤,逐渐和他们一家人熟悉起来。
结城朱里,也是那时候由内藤夫人真纪子介绍认识的。
电话响了,这个号码仍能接通,让良介稍微吃了一惊。对方没有搬家,仍然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会接起电话的可能性让无人接听的提示音带上了种不安的感觉。
他还记得内藤在A社刚刚成为媒体焦点的时候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询问消息,听过各种各样的传闻后,焦躁地指责管理层只顾自保,以及在良介劝他想法变卖工厂设备的时候长叹一声时的语气。
“工作丢了,再去找就可以了,这种话有人能轻松说出口,有人不能啊。”
嘟嘟声一声、一声持续响着,在寂静之中显得格外突兀。
“喂……?”
有人拿起了电话,是个显得有点不耐烦的、刚刚变声的中学男生的声音。
“阿树?是阿树吗?”
良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内藤一家时,内藤的儿子和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
“你是?”
“……我是柴崎,你可能不记得了,以前常常到你家拜访。”
“……”
“你爸爸在家吗?”
咔哒一声,电话挂断了。像是回应这声音一般,几只灰椋鸟从枯树上腾空而起,枝头的薄雪簌簌地掉落下来。
是忘记了吗?或者内藤夫妇对几年前的事情仍然心存芥蒂?良介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
或许该感谢来电显示功能,没过一会儿,对方便打了回来。
“良介?”
内藤的大嗓门一如既往,不知是不是错觉,良介觉得那声音里似乎少了些热情,多了些疲惫。
“啊……那孩子,真是没礼貌,最近总有些麻烦的家伙,所以挂了电话……没什么,是推销啦。不说这个……真没想到都这么久了……还在给鸟拍照吗?……在哪里就职?……东京?这么远?……哈哈哈,很好啊……难得的机会,要不要来家里住一晚?”
对方恢复了语速很快、滔滔不绝的健谈风格,良介几乎要打断内藤的话才能一句一句地回应,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
“只这一天?要赶晚班轮渡?大公司真是忙碌……你住哪里?几点的航班?从哪里出发?”
良介说出港口的名字和航班时间,内藤稍稍停了一瞬,接着,像不经意般脱口而出。
“滨内岬?……朱里现在住在那边。”
4、
远方的云朵逐渐压向海面,湛蓝色的天空变成玫瑰色,深蓝色的海面变成暗紫色,漂浮在港口平静水面上的浮冰和倒映在水面的云影混杂在一起,让天空和海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只有白色的灯塔还努力维持自身存在般地矗立在堆着雪的海岬上。
从码头的休息室向窗外遥望,环绕着旋梯的白塔如同隐隐浮现在天边的月影,显得比实际距离更为遥远。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灯塔上可以直接观察到远处礁石上停泊的海鸟,就算是暮色低沉的现在,还是可以看到海面上随海水飘荡的小群番鸭和长尾鸭,还有远处的丑鸭群。由于风景优美、视野开阔,T市一度打算把这里开发成观光景点,在周围修建了超市和影院,和休息室相邻的咖啡店,还有相当出名的年轮蛋糕出售,可惜这个计划也因为经济寒潮的到来而中止。
良介记得第一次和朱里一起登上灯塔时,两人都没什么话说。朱里和自己隔了两三步远站着,脸上挂着有点腼腆的微笑,接着把脸转向波光粼粼的大海,微微垂下了眼睛,看起来真心沉浸在海风和温暖的阳光之中,像她所说虽然住在附近的S市,经常路过这里,却不曾登上过这座小小的灯塔。直到蓝天上盘旋而过伸开翅膀、前翼边缘和尾部像盖着雪的虎头海雕,两人间略显僵硬的气氛才缓和了一点。
——从那以后,究竟过去了多少个冬天呢?
并不是阔别已久的家乡,也不是曾经长时间工作过的场所,然而周围影影幢幢,充斥在暮色里的全是回忆。
本以为隔了几年,再次来到这座小城的时候,能恢复到过去那样,只是追随着过冬候鸟短暂停留,像天空和雪一般明朗澄澈的心情。但果然随着时间流逝,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而另一些东西逐渐堆积起来,让人觉得步履沉重。
良介不后悔打了那通电话,却因为曾经和自己关系密切、造成如今这种境况自己多少也有责任的长辈近在咫尺,却只是礼节性、敷衍了事地登门拜访,连鞋子都没脱就在门口把伴手礼交给了对方,还怀着想要知道哪怕一点故人的消息,这样不干脆的心情而感到焦躁。
灯塔亮了,橙色的光稳定而温暖,穿透黑暗、穿透天空中零星飘起的雪花,映在因为室内的温度而起雾的玻璃上。
良介看着手里的速写本,上面用彩色铅笔上了色的白鹡鸰和暗绿绣眼鸟旁边,是刚刚潦草勾下的,灯塔的轮廓。
他从窗前退回休息室的椅子上,看着玻璃中央刚刚擦干净的一小片逐渐被模糊不清的雾气吞没,吁了口气,继续凭记忆涂起灯塔下面的岩石来。
5、
“叔叔,是画家吗。”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穿着棕色格子条纹大衣和红色靴子、手提便利店购物袋的小女孩站在良介面前,以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着。良介把目光投向她,她便害羞地扭过脸,假装刚才是在自言自语。
“不是,只是觉得鸟儿很有趣。”
“但是这个,不是鸟,是灯塔。”
听到对方向自己搭话,女孩鼓起勇气,用带着毛线手套的手指着良介刚刚在描摹的那一页。
“也有可以看鸟的地方、鸟儿住的地方之类的。”
良介笑了,他把速写本转了个方向,一页页翻着,女孩兴味盎然地张大了眼睛。
“苍鹭、红嘴鸥、银喉长尾山雀……”
孩子意外流利地说着鸟儿的名字,恋恋不舍地来回翻看着喜欢的图像,直到大厅里回荡起登船的通知,周围寥寥无几的旅客起身走向码头前面的栈桥,只剩下良介不知是该站起来,还是让正按着他膝盖上速写本的女孩再翻最后几页。
“舞子……”
这时,休息厅对面马路上的信号灯改换了,有个年轻女性牵着一个男孩的手,一边朝四周打量着,一边喊着谁的名字,急匆匆地朝休息厅外面的小型广场走来。
速写本滑落下来,差点掉在地上,女孩困惑地盯着良介的脸。
6、
雪越下越大,灯塔规律地旋转着的灯光映出急急下落的雪片。在逐渐变暗的道路上,几辆私家车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行。
“真的是送给你的吗?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别人忘在那里的也不行哟?”
驾驶座上的男人把雨刷调快了一档,稍微偏过头冲着后座说。
“才没有开玩笑,那个叔叔说,要我回去把没有画完的部分填上颜色呢。”
舞子用手指摩挲着绿啄木鸟的头顶。
“你这家伙,呆头呆脑的,运气倒是不坏。”
坐在副驾驶座,年纪稍长一点的哥哥,艳羡地看了看妹妹手中的画册,又央求般地对后座另一侧,正望着车窗外暗沉海面的女性说,
“妈,也画给我怎么样啊?”
==============================
*已經不會寫文...隨便寫寫先復健一下,順便上個線,不是故意搞成這種都市小言般的風格的,大家不要在意XDDD
*歡迎互動,各種談工作談感情談人生談理想都歡迎
*明明換了人設,卻總感覺還在重蹈什麼神秘的覆轍2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