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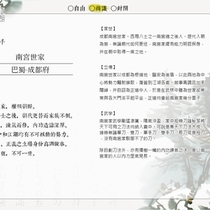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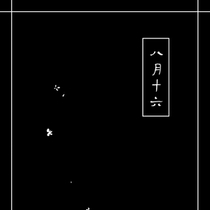


鳳三娘是個率性的女子。
但光光說她率性,是遠遠不足以形容出她的模樣的。人生本就是個大包袱,裡頭裝滿了互相矛盾的東西,誰也道不清自己身上背著的包裹里究竟藏了多少東西。
鳳三娘自然也不是個無趣的女人,因此旁人也都難以形容出她的模樣。
若單單看她那張臉,自然是叫人不易遺忘的。一雙眼睛雖不是柔情嬌媚的丹鳳,卻藏了鳳凰的模樣,眸子一轉,倒像是精氣神十足的鳳凰,剛從大火中重生而出,閃出一道利落乾淨的眼神,令人忘卻了她眼角暗藏的歲月的痕跡。接下來的鼻子,就這麼長在面龐中央,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聳不塌,一個人有這樣一個鼻子是不容易的,世間俗人們的鼻子,不是太高就是太矮,叫人見了,總生出想要幫他們整整位置的念頭。再者,有的人生得但是好看,但那一隻鼻子,不是大如煙斗就是小如豆粒,面上失了平衡,看了也勾起人心裡反感的情緒。更不用提那些過聳和過塌的鼻子,前者看來不似漢人,後者看來就是個草包。因此,鳳三娘有這樣一個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聳不塌的鼻子,是很難得的。再往下去,鳳三娘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她那一雙唇。
紅唇似火,倒不是沾染了胭脂粉飾的緣故,只因她本就生得一口豔麗的小嘴。那雙唇卻不似普通女子那般瘦弱淺薄,相反,豐滿的唇辦倒像熱切的邀請一般,招呼著每位碰面的旅人。在那誘人的下唇上,赫然顯出一顆黑痣,黑紅相襯,豔色不減反增,叫人不由得念起品嚐時候的香甜。鳳三娘因為著一口美麗的紅唇而出名,但她出名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著唇的模樣。
她不開口,輕含紅唇時美艷得每個人都愛她,可當她開了口,每個見到她的男人都恨不得掉頭就跑。
可他們還偏偏都跑不掉,只能憑著那雙唇張張合合,把他們從頭到尾數落上一遍。江東有醫名劉,見過鳳三娘那口紅唇后斷她氣血過熱,勸她調養,沒想反被鳳三娘連罵了一條長街,從醫德依始罵得劉大夫一愣一愣的,直等到夜色西沈, 鳳三娘趕著要喝酒才放過了他。
鳳三娘往江湖里一扎就是十來年,從無人問津到現在的人盡皆知,人們對她的稱呼也從早年的“翠嬌娥”變為了如今的“朱玉羅剎”,一綠一紅,倒是生生斬斷了鳳三娘的兩段日子。
鳳三娘是從百里成風成親之後,不再穿她最愛的翠色衣裳的。
一個女人,總得是有什麼緣由才能在江湖闖蕩十余年,抱著三十多歲的年紀還未成親。
除了為情所困之外,還有什麼能讓一個女人在一夜之間就變了模樣的?鳳三娘二九后便不再青衣,其中的酸澀怕也只有她一人才能說清道明。
晚風吹過撫雲閣,鳳三娘倚靠著最外的圍欄,想得卻是這等胡亂的往事。
她如今已是三十有三的女人了,見過的男人也有千千萬,她本不應該再為陳年舊情而感到心痛,她早已將自己的感情按在心底,盡管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愛著百里成風,她就是不要再提,哪怕是一字一句,她都要對方謝罪。
可她今天又想起百里成風了。
她的手上正捏著一封短信,白紙黑字,只有瞎子才看不見上面寫了些什麼,也只有呆子才會不明白,這短短的一句話於鳳三娘而言,是多重的痛。
沒錯,那信上寫道,百里成風的妻子,閩中南音的掌門之女,鄭漾榕已被她的丈夫修書一封,由長安送回天興府了。
鳳三娘怔怔地看著那行字。
她還記得彼時她被百里成風迷得不行,甚至還大鬧了他的親宴,直到他明明白白地對她說,他這輩子只愛鄭漾榕一個人,不會為他人所動,也只愿與鄭漾榕一人白頭偕老,她才真正被打敗,乖乖地回了姑蘇,從此再不去長安,也不回閩中。
而現今這封信狠狠地摔了他們一耳光,不只是百里成風,鳳三娘覺得她和鄭漾榕也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把她們都從美夢或謊話中打醒了,徒留一個火辣辣的巴掌印,令人難堪。
其實,鳳三娘本是不太信這信上所說的話的,人人都有眼睛,百里成風待鄭漾榕如何,人後她是不知道,但光從人前看,她是絕不信百里成風會休了鄭漾榕的。
他倒的確愛她,不論走到哪裡兩個人都如膠似漆,他也亦待她頗好,凡是鄭漾榕想要的,百里成風也都替她得到手。
只得慶幸鄭漾榕不是個刁鑽的女子,不然怕是有很多人會過得很難。有時候鳳三娘也會思索起這個問題,為什麼她和鄭漾榕長在同一個地方,心性脾氣卻差得這麼大呢?她火辣易怒,豪放無憂,鄭漾榕卻常常深鎖眉頭,把萬千的謹慎小心都收到了那小小的皺紋之中,叫人看了就不禁心疼。作個比方,她就是那曠野里的蘆葦,風怎麼闖她也都是奮力地搖晃,反抽風兒一個大嘴巴子,而鄭漾榕卻是空谷里的一朵幽蘭,碰見她,風都不敢大聲呼喊,只會收聲斂氣,從她身邊悄悄走過。
更多的時候,鳳三娘會懷疑鄭漾榕是否真的是閩中女人。
按她的印象,閩中很少像鄭漾榕那般沉靜無言的女子,至少在她離開那兒的時候,大多數人的家中還是女人掌權,一開口,中氣十足,一雙快手打得了麻將,也做得了家事。哪有像鄭漾榕那樣,輕聲柔氣,一看就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模樣。不過她似乎忘記了,在閩中,天興府南音本就是一個異類,夾雜在一堆又狠又粗的閩音之中,從琴瑟里呼出一曲悠揚樂聲。
就是這樣的一個鄭漾榕,就這樣被百里成風休了,任誰都會吃驚。鳳三娘自然比旁人更加驚訝,她是知道百里成風的性格的,她明白他是真的待鄭漾榕好,而如今這一紙休書,不僅休掉了鄭漾榕,也休掉了她對百里成風的信任。
但她的心中卻還在替他辯解。
她寧願相信百里成風是有什麼難言之隱,才不得不做出這些事的。或許是他遇上了些麻煩,不願牽扯上鄭漾榕,又或許他要去什麼遙遠的地方,不得不找個理由把鄭漾榕塞回天興府以保她的周全。鳳三娘兀自想了很多,想完後又搖了搖頭,這些假設太過蹩腳,她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高樓束起來往薄雲,樹的尖頂留在眼底,撫雲閣本是個很美的地方,也是她留在姑蘇的“家”,可她此刻卻彷彿一刻都坐不下去了,她有些急躁地從欄邊起身,腰肢一扭,就往閣外走去。
↓標題是隨便亂想的,大家隨便看看就好((
細雨·清風·故人
臨安城,錢塘鎮。
小雨綿綿,空氣也沾滿了露水的濕氣,鳳三娘拍掉蓑帽上的雨滴,又抖掉青色袍子下擺的水珠,邁步走進沿街的一家小酒館。
小二立刻端上了茶水,鳳三娘瞥見那桌上的油漬足有五分厚,轉頭又見那小二臉上生著幾個大大的疙瘩,幾乎要將他扁扁胖胖的鼻子整個罩住,看得人好不惡心。但鳳三娘只是眨了眨眼睛,麵不改色地坐了下去,叫了碗牛肉面就將小二打發走了。她沉默地坐在那板凳上,思考著不久前在花家門前見到的那張謎題。
白紙黑字,大大的“九十九”在紙上遊走如龍,但這卻難住了鳳三娘,絞盡腦汁也無法想出答案,她只好四下觀望著,希望能夠找到一線啟發的靈光。
看著桌角上還掛著的蛛網,鳳三娘猜想這小酒館平日里來客肯定不多,但剛剛她邁步進來時,這兒卻只剩下唯一的一張空桌,三條看著就很容易散架的板凳被隨意地丟在桌邊。她環視四周,衣著華麗的世家公子和扎緊褲腿、身後背著板斧的山野樵夫一同坐在這家酒店中,不可不謂之奇妙。
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和她有著同樣的想法,而且他們也都明白是誰創造了這個奇妙的情況。
花家小姐!
在這四周都不過是普通農舍的錢塘鎮,能引來這麼多江湖好漢的,也只有花家這一家,更吸引人的是,他們傳出自家年僅二八的自家小姐準備招親。唯一奇怪便是誰也沒曾見過花家小姐的模樣,但這些在氣血旺盛的年輕人眼裡都不是問題,就算不娶只是遠遠地看上一眼也是好的呀!
不過這些,都和鳳三娘無關。
她來到這裡的唯一理由就只有一個。
牛肉面很快上來了,熱騰騰的麵條上蓋著幾塊肥厚的牛肉,縱使是油膩膩的桌板此刻在那霧氣之下也顯得不那麼倒人胃口了。鳳三娘剛要動筷,忽地見得一人走到了她的桌邊。
她把原本拿起的筷子又橫放回了碗上,抬頭看著來人。
這是一位身著白衣的年輕男子,眉清目明,一把絹扇在手,真可謂是濁世佳公子。這樣的一位公子竟然要在這充滿汗臭油煙和陳年老垢的桌上坐下,就連鳳三娘都不禁唏噓幾分。
不過她也只是心頭唏噓,見過來人之後,她又拿起了她的筷子,往旁邊的板凳上一指,道:“坐。”
那位公子點了點頭,倒也不顧油污,就這麼坐了下來,待他理好衣襬,又將扇子輕輕放在腿上后,才抱拳向鳳三娘道:“萍水相逢,有幸能在一桌共食,不知這位朋友的名姓?”
鳳三娘正拿著筷子往那牛肉上戳,將整塊牛肉都沒入那湯汁中,聞言又將筷子提起了,頓了頓還是覺得不妥,只好再一次把筷子橫放,空出兩隻手來回禮道:“姑蘇城,撫雲閣,宋澄誠。”
她說得簡短,一是怕自己假扮的身份會暴露,二也是不知道對方的底細,不願一下坦露過多。
誰曾想對方聽了這句話卻似兩眼放光般,激動得不由得抓住了鳳三娘的手腕道:“久仰宋公子大名,如今一見果然是玉樹臨風風度翩翩不讓他人啊,只可惜在下聲命皆微,沒敢去撫雲閣上拜訪,誰曾想到竟在此處遇見宋公子,真是三生有幸!今後還請宋公子多多擔待,指教在下!”
他的聲音大且快,鳳三娘想打斷他是已然來不及了,四周有些視線已似有似無地飄了過來。
鳳三娘一時尷尬,她趕忙把目光投向面前的這位公子,問道:“哪裡哪裡,看公子如此眉目清秀,想必也是哪處世家的少爺吧?但不知公子名姓?”
那白衣公子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徐,名叫青風。”說罷他啪得一聲打開了手中的絹扇,只見上書幾個大字,乃是蘇軾的名句“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雖然鳳三娘對書畫並不了解,但她一看也知道這手字寫得不賴。
“原來是徐公子,幸會幸會,”鳳三娘點頭應道,“不知徐公子這次來是否也是為了花家小姐呢?”
徐青風點了點頭,但話題仍不離鳳三娘:“宋公子叫我青風就可以了,不過嘛,這次來錢塘鎮與其說是為了花家小姐,倒不如說……”
他的聲音被打斷了,因為從隔壁桌上,忽然傳來了一聲大喝,那是一個濃重渾厚的聲音,鳳三娘只一聽就知道這人多半是個莽人,然後她那聲音吼出了一個名字。
那是一個在此刻或許遠比花家小姐更有吸引力的名字。
百里成風!
鳳三娘突然握緊了拳頭!
可是她現在不能生氣,離開了姑蘇城,她已經不再是鳳三娘,此刻她一襲男裝,一柄鐵扇還插在腰間,不論怎麼說都沒有理由衝上去找人吵架。
所以她只能放任那人繼續說道:“去他媽的百里成風,好好的老婆不要,非他媽的要跑到這裡來格老子搶老婆,真是不要臉!”
鳳三娘的拳頭攥得更緊了。
一旁的徐青風忽然開口,道:“想必宋公子此行是為了花家小姐而來的吧,不知公子是否有解出那門前的謎題呢?”
鳳三娘知道他這句話是為了引開自己的注意,但他的確正點到了鳳三娘苦惱的地方,於是她進一步問道:“是的,在下來自正有此意。門上的謎題,我已經解開了,只是不知青風兄是否解出了呢?”
她說得有些咄咄逼人了,在這樣一個情形下質問別人是否解出了謎題似乎有些不太善意。
但徐青風對此卻沒有表現出反感,只見他湊近鳳三娘道:“不瞞宋兄,小弟心中已經有所答案,但是小弟只怕自己答錯了題會被別人小瞧,所以想和宋兄對一對那謎題的案底,不知可否?”
鳳三娘點了點頭,她本就為解不開門上的謎題而煩惱,如今有人把答案大大方方地送給她,她又怎麼會不收呢,只是她擔憂,在這樣一個人多耳雜的地方將答案公佈,企不是便宜了其他的人。
見她臉上浮現出了憂慮之情,徐青風打開絹扇一笑,湊上前去用絹扇擋住自己與三娘的臉,在扇后道:“宋兄不必擔憂,小弟會在桌下將自己的案底寫在宋兄的手掌上,若是這案底與宋兄的相同,宋兄點點頭就是,若是不同,宋兄收回自己的手就好。放心,這件謎題的案底絕不會讓其他人知道。”
鳳三娘將信將疑地點了點頭,將左手放在了桌下。
她感覺到有另外的一隻手碰到了她微微發汗的掌心,透著涼意的手指尖在她的掌上遊走。
一撇,一豎,一橫折,最後是兩筆直直的橫。
白。
就像徐青風今天身上穿著的衣服一般,謎題的答案是“白”。
她忽然低頭,盯著桌下那兩隻相觸的手。
她的手自然是不像男人那般的,上了年紀的女人總是對自己的身體保養有加,鳳三娘也不例外,她的十字仍舊是如蔥玉般白皙細長,指甲也修的恰到好處,任何一個人看到這雙手時都不會把它認作是男人的手。她的目光轉向另一隻手,這隻手只伸出了食指,冰冰涼涼地貼在她暖得有些發汗的手掌上。這手指也是細長白皙的,指甲稍稍比她的長上那麼一小圈,骨架抹在衣袖的遮擋中看不清楚,但鳳三娘認定那也是一雙小巧、靈秀的雙手。
她又轉頭去看徐青風的臉。
這張臉的確明眉秀目,一時間讓鳳三娘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想。
徐青風的目光已經追了過來,顯然他是在問剛剛的答案是否正確。鳳三娘穩了穩心神,才緩緩地點了點頭。
徐青風笑了,笑得並不張揚豪放,鳳三娘看著那笑容,將幾乎就要問出口的問題又吞下肚了。
她本就只為了那一個人而來,除此之外的事情,她都無半點興趣。
她轉頭,第三次拿起筷子,認真對付起已經有點微涼的牛肉麵。
和korrri讨论之后感觉小纪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错动【呆滞
……但是………………真好吃啊!QwQ脸交出接力棒……!
标题典出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
=============
壬子年的一切都好。
正月的时候帝驾取次萧山入了临安,到了春天,很是有些将要安定平稳下来的痕迹。吴山脚下屯了兵,还显得乱糟糟的,没什么规整的兵营的样子,演武的场地只是草草平整出来的一块,人马不经常踏及的地方,浸在江南初春湿暖的空气里,仿佛见风就长似的冒着一丛一片的绿。
演武场上正有一群人射柳为戏,引发一阵阵叫好声。张弓驰马的多是些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大略是陆续随驾而来的官员子弟。临安城内外素是不缺枝叶纤袅的垂柳的,以彩帕系柳枝,百步外驰马张弓射断并于落地前接住持回,名义上虽近于游戏,其实于射驭之上的要求都分毫不低。好在终究也只是个游戏,即便大部分人屡射不中,充其量无非也就是懊恼一下,倒也不觉得多丢了面子。
然而下一个上前的少年似乎像是众人期待了许久的人物似的,跨着马刚踏上射道边缘就听得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期待的彩声。少年约摸十六七岁,正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一身大红的猎装都只显得潇洒不觉张扬,此刻笑意朗朗,左手持弓,右手往背后箭囊里去摸箭,缰绳也未挽,就这样放任它松脱地搭在马颈上。
也没见他怎么催马,那匹深栗色的小马驹子就开始撒开蹄子沿了射道小跑起来。马背上的骑手肩平背直,以一种几乎是随性的姿态开弓张满,弓弦清脆悦耳的三声,柳枝应声而断。栗色马驹陡然加速擦过那排柳树,之后掉了个头回转过来,奔向那位年纪较长的判者。红衣的少年手里不知何时已持了一束新鲜的柳枝,三枝之上各自系一条鲜红绫帕,颜色与他身上的猎装倒是分外协调。
围观的人们把手拍得震天响,他的弓斜斜挂在肩头,左手控缰停马,嘴角噙了笑,俯身把那三枝柳条恭谨地递给判者。判者却不接,只笑着把身旁另一个人一拍。
“你瞧我说的是不是?叫小纪玩这个实在没难度,不成不成,这个不能算你赢。”
马上的少年也笑。
“延章兄这可不厚道。你们让我连射三枝,我便射来了;要尽系红帕,倒是瞧瞧有错没错?这会儿和我说不算,我可不依。”
那判者也不过二十许,一样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哪里肯饶他。
“说这么算的可不是我,那是子祁吧。你们既许我是判者,判者可没这么说过。”
围观的人见有热闹看更是不肯放过,一叠声轰然地说不算,少年没奈何也只好认输。
“行吧,这回射几枝?可先说啊,射道有点短,你们非得要十枝八枝的我可不一定弄得下来。”
“要个十枝八枝来做什么?于你来说还不都一个样。”
卢延章转了转眼珠,突然笑起来。
“依我看,你盲射吧。”
“诶?这……”
少年明显呆了呆,然而围观的人群一听却都兴奋起来,起哄着嚷着要看,卢延章更是直接就手把系在他射落柳枝上的红绫帕解了一条下来,折个几折,笑吟吟抬手递上去。少年本来似乎还想推拒,瞧着实在不给他这个机会,便只好接过来。
“……一会儿我要从马背上摔下来,你们可得记得救我。”
他这么半笑半抱怨地说着,兜转马头,往系了彩帕的柳树那头凝神看了几眼,然后用绫帕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场地里隐隐流动着一股兴奋而又紧张的气息。盲射要仰赖听力和触感,卢延章便抬手止了喧哗。四周风声极微,遥遥可以听见兵营里的喧杂,间或还有更远处隐约的市声。
蒙了眼的少年肩上的短弓落到左手,稳稳地握牢在掌心,右手松松牵着马缰,一时却并没有什么别的动作,像是在安静数着呼吸。
马儿起步得突然。影子一样飞快蹿出去的时候箭已离弦,因为离着远,带了些许尖锐的风声。然而马前行的方向和去箭的轨迹终究还是略微有点细小的偏差,箭头割断的柳枝只打在他伸出去接的指尖上,滑了开去,他一下没能接住。人群里表示遗憾惋惜的声音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先倒抽了一口冷气。
少年第一下没抓牢,马上反应迅捷地顺着指尖的触感翻腕朝外下方一捞,倒真给他勾着一片叶子,顺着一把抓在了手里。只是马身的位置和柳枝的位置偏离得有些远,为了捉住那条掉落的柳枝,他上半身几乎横悬在鞍上。这样的姿势重心不稳,把控不住极容易落鞍,可他看起来却似颇为轻巧不费力的样子,左手轻拽一把马鬃便借了腰背的力量翻身起来在鞍上坐稳,伸手拉下蒙眼的绫帕,自己先瞧了一眼手里的柳枝,上面明明白白系着条鹅黄帕子。他似乎自己也觉得意外,笼转马头往回走的时候先笑起来,高举了那柳枝朝着人群扬了扬,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似地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喝彩声。
“……那个人,是谁?”
稍远处的柳荫里有两人驻马,其中一个抬了抬下巴,问他的同伴。
问话的那人只勉强够得上少年的岁数,身形还没完全长开,脸颊上残留着点稚气的影子。他的同伴倒像是正在蹿个子的年纪,带着那个时期的男孩子所特有的、单薄修长的瘦,连握着缰绳的手指都仿佛能清晰地看到骨节。
“似乎是纪郎中的儿子。”
他这么回答。年少的同伴扬了扬眉毛。
“纪郎中?哪个?”
“户部度支郎中,纪永川。”
“哦,他呀。”
年少的那个散漫地应了一声,似乎并没怎么往心里去,顿了一顿才像是想了什么起来似的补了一句。
“他不是个文官么。”
年长的便看他一眼,只笑,也没说什么。年少的安静了一会儿。
“你怎么就认得了?”
“前些天在御前弓马所见过,说了几句话。”
他原本似乎没打算再做解释,可对方嗯了一声,倒像是还有那么些期待后话的意思,他便想了想,补充说。
“人不错。”
这一句却引得年少的同伴侧头看了他一眼。他把探询的目光迎上去,对方又把视线移了回去。停一停,却又忍不住似的再看了他一眼。
“怎么?”
“我还真少听你用‘不错’形容哪个人。”
“少吗?”
“少。”
年幼的那人抱了手笃定地点头。
“谭枢哥哥一般说人都是‘很好’,不过你的‘很好’,大概意思就是不怎么样。”
他便莞尔。
“没这回事。”
对方哼笑一声,投过来“你自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的眼神。
“他其它功夫怎么样?可有骑射好?”
他摇摇头笑起来。
“这我哪能知道?”
对方也笑,眉眼里却带着几分跃跃欲试的味道。
“你不知道,改天我倒挺想知道一下。”
(tbc)
感謝G太太成全,希望和叔叔的互動不會太OOC……
以及我真的對古風完全懵逼,有bug的話請大家溫柔地指出……原諒我是一個文盲……
↓
姑蘇城中酒家客棧自然眾多,但有“鼎味絕”這樣氣派的酒家,卻著實不多。
左倚姑蘇河,右靠市井大街,自然是落在絕佳的地方,一樓長桌,二樓雅座,到了最上層的三樓,卻又是一條長桌,直直跨越了約莫有三個鋪位的長度,配套的則是十餘條的長板凳,好一副隨性瀟灑的做派,平白地將最好的位置佈置成最低賤的酒家模樣,尋遍整個姑蘇城,怕也不會有第二家了。
鳳三娘打撫云閣出來,轉身要進的便是這間“鼎味絕”。
可說來也怪,偏偏在這樣一個奇怪的店鋪前,站著一個跟這條街都不太相符的人。
一面大旗挑在一人高的棍頂,那旗倒是簡單得很,黑邊白底,上書“神算”兩個大字,可仔細一瞧,這旗子卻已是飽經風雨,舊色染在旗面上,縱是逃也逃不去。旗未想動,背旗的人像是在與鼎味絕的小二爭執著些什麼,惹得旗子在棍頂顛顛晃動著。
鳳三娘湊近了,卻聽那小二模樣的人道:“喝了酒自當要付酒錢,不付自然就是叫花子,誰又要你個瘋瘋癲癲的傢伙來算命抵債!勸你還是快些把錢交出來,可莫要小瞧我們‘鼎味絕’!”
而那背旗的人卻仿佛沒有聽見小二生氣的口氣一般,仍舊是晃晃悠悠,醉色滿面的樣子,左手捏起三指,神神叨叨地輕點著,隨後又頗有意思地點了點頭,似是真的受到什麼天上的指示一般。
鳳三娘從他後頭看去,倒真是有幾分可笑,她也不急著進酒家,就站在那人身後繼續看著。
店小二卻沒有鳳三娘這般好閒情,生意人自是惜時如命,他的聲音自喉嚨出來,就像是給人拿皮鞭在後頭趕出來似的,在高聲時尖利,沉到低處時卻化為沙啞:“趕緊的,酒錢拿來,你再要這樣裝神弄鬼想糊弄過去的話,可別怪我們對你不客氣了!”
那人還是一副無所畏懼的模樣,真當是把店小二的話當做耳旁風了。
店小二吃了一口悶氣,自然是不肯這麼輕易放過他,可就在這小二轉頭,想喊來店裡人時,鳳三娘聽見那人忽然開口道:“兄台,人常言人命天定,你可知人亦能改命?方才我正為你算天時,你卻好生擾我,害我一個手抖,這下,只怕你的命宮受擾,將有大變啊。”
他故意做出吃驚憂慮的聲音,惹得小二也變得緊張起來,喊人也顧不上了,倒是湊上前去,悄聲問道:“敢問……有何大變?”
那人笑笑,道“輕則失金,重則失紅。”
店小二果然一震,繼續問道:“不知還有什麼法子能救嗎?”
那人點點頭道:“自然是有的,只要兄台肯花些銀子替在下將那酒錢付清了,在下即刻為兄台改命。”
那小二自然不傻,此言一出便識破這又是那人的詭計,正要破口大罵,鳳三娘的身影卻從後頭晃了出來。
只見她輕輕地拍了拍那背旗男子的肩,轉頭對小二燦然一笑,道:“小二你莫要害怕,酒錢我自然會替他付的,那命格自然也是會替你改的,現在只求你快快進去,為我們尋一張三樓的板凳,再備二兩上好的女兒紅,我們好上去詳談。”說罷,還挑了挑那道利眉,又拿那雙暗藏鳳凰的眼睛對著小二眨巴了兩下。
這樣的鳳三娘,又有哪個人能夠拒絕呢?更何況一個小二,聽到有人喝酒便是笑容滿面的,他抬起腳剛要往內堂跑,卻被人叫住了。
“二兩怎夠,先將我這酒葫蘆滿上再說。”言罷,一只胖乎乎的酒葫蘆就飛進小二懷中,他轉頭一看,才發現又是那背旗男子開的口。
“唉喲,你這人,人家說兩句客套話你倒還當真了。”鳳三娘嗔笑起來,繼而轉頭又對著那小二道:“也罷,你就替他滿上吧,今個兒姑娘我也是要尋酒,索性就尋個痛快。”
聽了這句話,卻是換了一旁背旗的男子笑了起來,喃喃道:“姑娘?三娘你這年歲,又何苦還稱自己是姑娘呢。”
鳳三娘扭頭,衝著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背旗男子自當是以笑代答,這一言一笑之間,他們二人已來到了三樓。
長桌一張,直直向南邊橫去,而在這長桌上喝酒吃茶的人,亦是循了店家的規矩,散散呼呼地在長桌上坐著,乍一看去,倒頗有長街宴之感。
二人尋了個旁人較少的位置剛坐下,剛剛的小二便端來了二兩女兒紅,順帶將已灌得滿滿的酒葫蘆還與那男子。
此刻,男子已將挑在隨身木棍上的“神算”大旗放了下來,小二這才好好打量起這人來。
內著的白衣自是有些時日了,布料失了新買來時的硬挺感,柔柔地沉在一身青色外掛之下。那手腕用黑色布料纏了起來,本看不出膚色,可一看那面龐便明了得很,有些蒼白的臉上還掛著些許胡茬,嘴唇亦是失了些血色,但奇的是那雙眼睛!縱使整張臉看上去滄桑,那雙眼睛卻仍是閃亮,似是還藏著能置人於死地的力量。可那眼神,那本還銳利的眼神,卻在觸到小二手上的酒葫蘆時軟了下去,像是眸子已先飲過那酒一般,竟已開始泛出酒醉時的神色,綿軟無力,頗失神色。
鼎味絕一日接待酒客少說也有上千人,小二在這兒干了八年,自然是明了貪酒之人的神色,可他亦是覺得沒有人能像面前這人那樣,貪酒如是,僅僅看一眼便已幻想自己醉了。小二自是不愿再理,匆匆放下酒具,便離開了。
鳳三娘自然拿過那酒瓶,穩穩地倒了兩杯。放下酒瓶,舉起那小巧的酒杯道:“巫馬牧,許久未見,三娘自是先敬你一杯。”說罷,酒已滑過喉嚨,刷的一下下肚了。
巫馬牧接過另一杯酒,卻不急著飲下,倒回味著剛剛上樓時的玩笑,只見他轉著酒杯道:“三娘啊三娘,你若真還當自己是姑娘,可不該飲酒。”
鳳三娘一挑眉,道:“不喝酒?那我該喝些什麼?”
巫馬牧笑著道:“茶。自然是茶,閩中多產茶,你又為何不喝?我聽過人滴酒不沾,卻只見你一人滴茶不飲。”
鳳三娘道:“你自是知道我是閩中人,亦聽過閩中陳家茶的名號,一飲此茶,只怕其他的茶水,我從此是入不了口了。”
巫馬牧道:“茶是好茶,卻也是一口毒茶。”
鳳三娘的眉毛又挑起來了,她略帶嗔怒地問道:“何出此言?”
巫馬牧笑道:“一飲此茶,從此不再能飲天下其他的茶水,怎不算毒?要我說,天下再沒有比你陳家茶更毒的毒藥了。”說罷,將面前的酒一飲而盡。
鳳三娘皺皺眉,卻不似因巫馬牧的話而起,她的思緒隨著他的話飄遠了,離了姑蘇,度過萬重山,到了她的故所去了。可不知怎的,面前浮現出的卻不是陳家二老的面容,亦不是自家那可愛的小茶園的模樣,倒是鄭漾榕的臉,愈發清晰地出現在了她的腦中。
她歎了口氣道:“這陳家茶對旁人而言或許是世間最毒的毒藥,于我卻不是。”
巫馬牧笑笑,道:“他既已遠去,你又何必執著至此?”
他二人都略過最為重要的字句不談,只是淺淺擦過所言之物,但雙方卻都明了對方心底想說的話,可見這二人熟識頗久,互知心事。在這長桌上難免有不老實的耳朵,但他二人的這番談話,縱使被旁人聽了去,也是摸不著頭腦,期間的真諦倒真只有他們自己明了。
可他們躲著某個人的名字不提,長桌上卻是好嚼舌頭的人占了多數,總有幾聲高談,落入了他們的耳中。亦如此刻,在他二人位旁兩座的位置,有位著紫色外袍的公子便就著酒勁吼出了一句飯後的閒談。
“哼,什麼青年才俊,我看那百里成風就是個休妻的莽人懦夫!”
鳳三娘牙口一咬,眼睛早已瞪了起來,仿佛那人下一句話一出口,她就要沖去理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