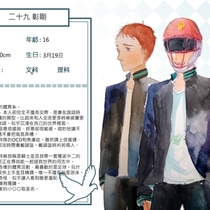

材料:
二百五十毫升左右酒精或汽油
酒瓶
水松、塑膠、蠟、橡膠或軟木塞
布料少許
火種
添味:一點父愛和殺意
蟬聒噪得要命,吵得人受不了。
那加•蓋拉背著他的行李,跟在教父佛朗西斯身後——後者在這大熱天裡面還穿著一身西裝。奧凡托河的水波在艷陽下猶如魚鱗,掀起層層疊疊的浪花,可當那加走近一看,卻發現水是綠的,讓人很掃興。
“還沒到嗎?”那加咽了口唾沫。
“還沒到,再忍一下,到了就能吃午餐。”他那沒什麼表情變化的教父搓了搓鼻子。河水聞起來一股腥味,叫人倒胃。
“哈,那還真是振奮人心。”
他們穿過稀疏的木叢。那加調整了下他背上的東西,佛朗西斯點了根煙。河岸,皮膚曬得發紅的孩子裸露著上半身,在沙地上堆起堡壘。那加向他們招手,得來這些小當地人們好奇的目光。
“阿伯特——他是個怎樣的人?”那加突然問起來。
教父只是繼續走著,用腳攆斷擋路的灌木,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你不需要知道。”
“我還以為你們的關係很好呢——”那加說的你們包括他父親。
“現在不了。”
他們停在一個好位置,這兒恰好能清楚看到那間屋子,但周圍的環境叫他們不那麼容易被發現。那加擦著額頭上的汗珠,盯著他教父看。而沙場老手只是嫻熟地從背包裡面拿出來酒瓶。至於期待已久的三明治,那是那加的哥哥做的,裡面放了肉丸和起司,還有對三明治稍稍有點過量的番茄醬。唯一的遺憾就是在背包裡放得太久,導致起司有點冷了,但味道仍然不錯。
“快吃吧,吃完了就該幹活了。”
那加大口吃著肉丸三明治,他看到他的教父掂量著手中的酒瓶,并將布條塞好。佛朗西斯的那根煙已經只剩一節,掉在當事人掌心裡,被他自己捻沒了。
“你不吃?不是馬上要幹活了嗎?我哥做了你的份,味道很棒,是他自己捏的。”那加問。佛朗西斯拍了拍手,叫那加打開他的行李。酒瓶被擦乾淨了。他們在樹蔭下看著行李箱裡面的三竿槍,黑色的槍桿在正午的陽光下閃著暗淡的光。佛朗西斯拿上他慣用的那把伯萊塔,那加則將剩下兩把拿起來。
他們盯著那棟木屋,直到從裡面走出來一個中年、肥胖的女人。看打扮,或許是附近的主婦吧。那人抱著一筐衣物走了出去,過一會兒,奧凡托河河畔的小屋又恢復了平靜。那加知道他們該去了,他看到他教父的眼睛裡已經燃起了什麼東西。
手上的槍把在夏日發燙。
他們走過去。佛朗西斯一語不發,那加想說點什麼,但又覺得不是時候。隨後,佛朗西斯一腳踹開了門——阿伯特坐在屋子裡,還在吃著午飯,好像沒明白過來有人闖進來似的。他們四目相交時,那加從對方眼睛裡看到了恐懼。
沒等佛朗西斯開口,子彈就已經射進了阿伯特的腦門。然後是第二槍、第三槍。
“夠了。”
那加感受著手上槍支的熱度,他聽到他教父的手拍在肩膀上的聲音。
“我殺人啦……我殺了阿伯特了。”他說著,不知是出於喜悅還是懊惱,是出於悔恨還是解脫,“我殺人了……但他該死。”
“作為第一次,做得不錯。”佛朗西斯將他的酒瓶拿了過來,示意他也過來幫忙,“來吧,讓我們把這房子燒了。”
他們點燃了燃燒瓶,把尸體拖到火裡,然後在更多的人被槍聲和煙霧吸引過來之前離開了。佛朗西斯腳步輕快,那加只好跟著對方。燃燒瓶都用沒了,回程要快上不少。他們走了幾里路,最後停在一個公交車站前。那加低下頭彎著腰喘著粗氣,淚水和汗留得滿身都是。不該穿這麼多,他胡思亂想著。
“太熱了,我得把衣服脫了。”
“車子快來了,還是別脫了。”佛朗西斯看了眼表。
“阿伯特,我想起來了,我小時候和阿伯特在一起過過生日呢。為什麼現在才想起來呢……啊……”那加說著,隨即感到他的教父寬厚的手掌重重地、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背,那動作笨拙得要命,絲毫感覺不到做炸彈時的靈巧。
“好孩子,好孩子。”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