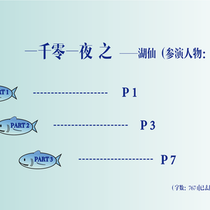




太难了我太难了(摇头)和蒙雅克聊天随时担心会踩雷,小心翼翼挤出字和他讲话,十八快快乐乐傻嗨,亲妈愁断肠
字数:2636,写出5k字的同担好强大
太阳懒散地落在甲板上,王马十八难得穿上了他的卫衣,向上45°角,望着天空,慢慢吐出烟雾。他的眼神像是被丢在菜摊上的咸鱼干,就是隔壁案板上剁成两半的草鱼也比他能跳。
青唉声叹气着来到甲板上,因为这脚步声,王马转过头来。
“青小姐?好巧。”
“哎哟,巧。”
王马刚想掐了烟,青摆摆手,也站到了一起,将双臂摆上栏杆。她的眼神比较像翻车鱼。
“你刚从蒙雅克那儿聊天回来?”
“可不是。”
“啥感受?”
“什么感受?就那样啊?你没和人聊过天吗?”
“嗨,难啊,和蒙雅克聊天太难了,难于上青天啊。”
王马再吸一口,凝视着远方,重重地长叹。
为什么会是蒙雅克呢?
硬要说的话,他比叶菲姆更像个孩子吧。这是王马真诚的想法。
他会擅自地对别人下定义,然后坚持,直到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他对于“孩子”的定义很奇怪,叛逆又笨拙的人是“孩子”,乖巧而懂事的是“小大人”。
船主先生是“事业有成的大人”,叶菲姆是“看起来像孩子的圆滑大人”。只有蒙雅克,是“孩子”,没有干劲又刻意保持距离的“孩子”。
王马十八喜欢和“孩子们”相处,他是回形针,“孩子们”是磁铁,只要出现在合适的范围里,他就会不由自主地靠过去。而这就是他选择主动向蒙雅克搭话的契机。
这不礼貌,让人感到尴尬,然而他向来是个怪人。
但是现在,他不后悔的同时,沉痛地谴责当时天真可爱的自己。
和蒙雅克聊天,难,太难了。
初次见到他的人,就凭那张脸,一准儿会啪啪啪啪把“认真”“负责”“严肃”“可靠”几个标签贴脸上。但蒙雅克只需要走几步,不,甚至只要呼吸一次,这些标签就会掉在地上。
想出一个话题,然后被蒙雅克敷衍,再想出一个,继续被敷衍。可恶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热衷于把天聊死的男人!
和他!聊天!实在是!太难了!
一切的开始是,王马在免税商店,看到蒙雅克与叶菲姆短暂地交谈了一次。他实在是好奇,一从商店溜出来就跑去找蒙雅克,假装不经意地——但谁知道蒙雅克有没有看出来呢——搭话。
前半段极其尴尬,蒙雅克直接承认船上扒手随人潮增加,不是“嗯啊哦”就是“大概或许可能”。王马一度开始怀疑自己的社交能力,并且事实上,可悲地,他的聊天水平确实很差。
“哎……看起来你已经很适应这种(对于小地方出身,连东京横滨都没去过的土狗来说的)大场面(指人满为患的昂贵游轮)了,真不愧是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啊。”十八发自真心地如此慨叹。事实上他的内心很绝望,他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如果蒙雅克再沉默,那我就要去……呃……吃个雪片糕以纪念浪费的时间!正当他在这么想的时候。
——蒙雅克笑了。
他的嘴没动,他在用他的眼睛笑。王马知道自己一准儿又多想了,但如此少见的“笑”实在是有趣。
“想笑就笑呗?笑又不会扣工资。”王马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泛黄的牙,心情甚好,“哪像我在的地方,白大褂解一颗扣,校长就要把我的头拧下来装点校园。”
“噗。”
那只是一个瞬间而已。一潭死水泛起涟漪,雪地里唯一的小木屋冒起炊烟,清晨刚醒的猫伸伸懒腰。这是王马在三秒内能想到的,与蒙雅克的笑一致的美好事物。他是做梦也想不到,如此没意思的笑话能让对方嘴角上挑。
他想,值了值了,我要是有雪片糕,我现在就要为了庆祝这一秒请全船人一人一片。
但王马果然是想太多了。
他无语哽咽,他心如死灰,两罐啤酒下肚,他在酒精里和麦芽小妖精大跳交涉破裂舞。他不仅多想,思绪还从地表飘出银河系,对着黑洞就是七百二十度托马斯大回旋外加战略性猛男冲刺。现在他的思绪回来了,哈哈,他人也没啦!
这船游客开放部分已经摸得差不多了,而距离目的地还有个把天。没劲,嗨呀,真的没劲。大清早地,他浑浑噩噩满船乱走。年轻人哪里有他起得早?想狼也不是这时候。
就在这时,他眼睛一亮!不错,拐角处面无表情走来的正是蒙雅克。
“早上好啊蒙雅克先生!”
“早上好。”
“今天天气真好啊蒙雅克先生!!”
“嗯。”
“接下来几天也会是好天气吧蒙雅克先生!!!”
“大概。”
王马手舞足蹈乐不可支,蒙雅克面色如常像在看一个弱智,这视线让对方硬生生克服了“哎嘛总算有人来唠嗑了”的亢奋,一阵尴尬的沉默后,王马试着找到一个新的话题。
“常年航线在海上的蒙雅克先生有没有什么难忘回忆?特别的旅客,不一样的风景,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么长的航线,啥都挺新鲜!”
“第一次的话,希望……您能有美好的体验。”蒙雅克抬眸看向对方,不知是否有意,回避了对方的问题。他向来一句话直白地从嘴里脱出,随时准备好结束对话,但这次却有奇怪的停顿。王马似乎听到对方吐出了某个音节,又咬回嘴里。这情况他也有过。
“哈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为了工作改变语气本身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似乎是错觉,蒙雅克突然变得警觉。
不可言说的过往?隐姓埋名用新编的身份生活?王马的脑海里出现了无数可能。根据轻小说定律,这个人很有可能过去不是什么好人——多么让人兴奋啊!在想象之中,自己的血液缓缓沸腾起来。
他在努力克制自己。是的是的王马十八,你又没由来地猜测了无道理莫须有的东西了,但是你好兴奋啊!真的好兴奋啊!好怀念!太多年了,实在是太多年了!他是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人了啊!
——或许十几年前的自己会这样想呢!王马冷静地这样想到。
那个人已经不会回来了,这点他心知肚明。他已经是合格的成年人啦!把毫不相干,相距甚远的人当成亲友的替代品,这不是轻小说男主角才会干的蠢事吗?他已经过了那种年纪了。
手指没有发抖,表情也和刚刚的相似,心绪的变化几乎不存在。至少面前的蒙雅克还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生。他摊开双手,露出苦恼的表情,说道:“我刚刚进学校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见人都蹦敬语,现在还不是和学生一起当狗逼?习惯了就好了,时间是很厉害的东西嘛。”
“……也许吧。”
蒙雅克闭上双眼。他可能在想什么,也可能没有。
说到底他和自己是异国他乡陌生人,下了船便永不相会。所以一时脑热想要了解对方的自己没有任何进步。
……吗?
才不是啊!因为是一期一会,才更加值得珍惜,要好好对待船上所有与自己点过头的人,然后快乐地玩,带上将行李箱撑爆的土特产,再回归自己的生活。
从那个人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享受当下!
虽然这么想了但是!!!
“那你在的这个职场对新人也挺友好的,工作体验还不错吧?”
“嗯。”
他面无表情,甚至没有点头,只是将这个音节从喉咙中吐出,完全没在意对面到底问了什么。
蒙雅克还是那个蒙雅克,改变的只有脑回路上蹿下跳仿佛飞天小女警的王马十八。
“哎,你说怎么会有这么难的事情呢?”
王马结束了回想,将烟头丢入海中,郑重地看向青。
“啥?”对方显然没理解这吊人的脑回路。
“难啊,和蒙雅克聊天,真是太难了。”
星期二我不杀人
壹、第二个故事。
几个世纪以来,水手都极为迷信,这样的迷信与宗教截然不同。它是经验、忌讳、仪式、灵感和征兆的组合,它是流动的、有生命的,从海上讨生活的人的口里成型,随着洋流和季风漂洋过海,每一年与过去都有不同的地方,而多年之后流言可能就成为了传统。
在我的养父杰罗姆闯入图克托亚图克之前,他的征兆就早已经出现了。
“那东西从海里爬出来……跟着我。”
2009年的冬天,杰罗姆在荷兰港罗斯玛丽号捕蟹船上当水手,一旦出海他们就得不分昼夜地干活,而螃蟹总是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这个移动的金库会出现在哪里,于是水手们要不停地把重达363公斤的捕蟹笼推进海里又捞起来,若是再加上北极的海上风暴,那可就真是要人命。但无论如何,只要抓到螃蟹就能赚钱。
他们撞大运遇上了螃蟹潮,每次捞起来的笼子都有70只以上的帝王蟹,一大堆螃蟹从笼子里被倾倒到分蟹台上,硬壳落到铁皮上“哔剥哔剥哔剥——”,对水手来说就像听见了钱落进了钱袋的声音。他和他的同伴量出螃蟹的大小,小的扔进海里,大的才能带回去。
他动作飞快地捡起在台子上乱爬的美金,这时,他注意到其中的一只,它的蟹盖是正常的朱红色,也足够大,那是非常标准的帝王蟹尺寸,但——
它在空中四处摆动的蟹脚灌满了鲜艳夺目的彩色荧光液体,里面的水光在蠕动,而越是到蟹脚末端,那种混合的色彩就更鲜亮更诡异,没有一种自然里的光和色彩是这样的形态。
邪门,他只看了一眼就感到背脊上窜过一阵凉气——尽管他现在已经在冬天的白令海上了,头顶飘雪,又湿又冷,但那阵凉气比什么鬼天气都厉害,让他从骨头缝里结出冰来。
那是从蟹脚倒灌进螃蟹的什么液体吗?海洋污染导致的见鬼的感染?但它看起来活力十足。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反胃。
或者说那色彩是活的?它悄悄从螃蟹脚爬进螃蟹壳,把血肉掏空,可能在那朱红盖子底下的身体已经融化了。螃蟹没在里头——
它完啦——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可不妙,这——
水手马森抬手就把那只晃动着魔鬼脚的怪物扔进了水槽。
你瞎了吗——杰罗姆差点放声大叫,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他想要怎么办,一只螃蟹而已为什么不把它扔进水槽?海里什么东西没有?或许只是一种新的寄生物罢了,只是会给螃蟹脚上染个色。
船舷旁的克劳得一边大吼小心,一边把另一笼满满的螃蟹倒了出来,哗啦一声,把之前的螃蟹推挤到了边上,它们个挨个,个挤个,个个都晃动着肢节想要逃跑,敦促催促他们加快收货的进度。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杰罗姆机械地把小螃蟹抛进海里,他身上因为干活而冒出的热气儿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
——来不及了,它已经上来了。
它上船来了。
它现在就待在水槽里,水槽下面有数百只活的螃蟹,等盖上盖子,它就可以在里面大杀特杀。
他们自以为满载而归,但等他们打开水槽盖子,海水里说不定飘满了蟹脚——
全是蟹脚——
水槽里除了蟹脚,只有那荡漾着的鲜艳夺目的彩色液体。
“一只螃蟹,哈哈哈,杰罗姆你真是尿裤子先锋。”水手们哄然大笑,“你是怎么一眼从上百只螃蟹里把它选出来的。”
不,根本不用选,是它选中你。
只要见到,就知道什么是它,只要见到,就知道它是冲你来的。他们疯狂地嘲笑自己胆小的伙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杰罗姆说的没错,每个人在第一次碰到它的时候就能认出来。就好像你总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影子。
从那之后那征兆无处不在,它化身六尺高的疯狗浪弄死了罗斯玛丽号的船长和三个水手,化身乳腺癌让他老婆躺进棺材并使他背上巨债,它一步都不肯停地跟着杰罗姆上了冷锋号,上了夏季湾号,上了皇家号……
直到他找到我。“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讨海人来说父亲的祝福总是管用的。” 以及那个更隐秘的期望,用新鲜的血肉填满它、喂饱它,让它找到新的饵料、钻进新的蟹笼——
“那么或许……有一天它会跟我说再见。”
他盯着啤酒杯,那双喝得通红的眼珠透过橙黄冒泡的液体看向我。
船舱又闷又热,散发着一股潮湿、难闻的发酵气息,汗湿的背心和鞋袜的臭气、喝了一半的超级波克精酿的酒酸味、过了一个捕蟹季的被褥的怪味。
杰罗姆倒头呼呼大睡,我多少已经有些警醒了:
第一,从2009年征兆出现到2012年杰罗姆一头扎进图克,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显然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都像女人似的喜欢慢慢来,毕竟婚后的生活都是逐渐变得糟糕、变得难以忍受的,不会一个照面就拿碎冰锤往你脸上招呼。
第二,我怀疑——
老早就怀疑,那只怪物为什么没有一口吃掉他?除了笼子,当然要给它吃饱。吃饱了以后,野兽也能变得斯文起来。
因此他必须要带人一起出图克,这是关键,但我父亲给了他惊喜。
第三,现在,按照那个传说——我说过所有水手都很迷信,那么从他们迷信里脱胎出来的怪物也应当遵守《大洋公约》不是吗?这就是说只要我和他呆在一条船上,它就拿他奈何不得。
回过头想想,是的,除了我第一次航行以灭顶告终以外,我们确实再没出过大岔子。2012年我们最终没有把那艘多灾多难船开进荷兰港。
那时我们刚刚行驶到红眼雪蟹渔场1141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我差不多已经习惯像只小海豹般仰躺在狭小床位上被海浪摇来摇去,而不会吐得一塌糊涂了。我还靠强记学会了一些常用的单词拼写,用来辨认仪器。认错当然是难免的,毕竟英语不是因纽特通用语,因纽特人要到16岁以后才可能通过和成年人交谈学到英语,我几个年长些的兄弟就要比我好得多。
但我也能听懂杰罗姆简单的命令和脏话——我每次犯错,他都会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而我和所有菜鸟水手一样容易犯错,所以婊子养的是我最快学会的语句之一。
然而越接近目的地,他越显得心神不宁,四处找茬、疑神疑鬼,总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做检查,我们在船上爬上爬下,被他操得疲累不堪。哈布恩——我那四个兄弟之一——私下里提起这事儿就皱鼻子,说只有新生儿才像他那样善变又需索无度。
不过杰罗姆该死的又对了,他的疑心病是有道理的。我不得不摆明这一点:渔船灭顶是由于防撞舱不知为何进了水,重心前移。
但——难以置信的部分是——在灭顶前负责检查甲板和开船的人都没发觉任何异常,考虑到我们频繁检修的次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事实如此,晚上风浪一起,船就被浪推着一头扎进海里。我们无计可施,只好放了救生艇,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了很久,差点被冻到失温,最后一艘路过的渔船发现我们,把我们捞了起来。
恐怕我的处女航就是它的反抗,它透过那艘船蒙蔽我们、影响我们,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毕竟那时候它徘徊已久,即使杰罗姆找到了学徒护身符,它也要放手一搏,享受这最后的大餐,但即使它没有得逞,它也不会消失。
它只是围着将死之人团团转,等待时机。
可打那以后杰罗姆和我从未分开过。他在哪儿我就必须在哪儿,他甚至逼得船长同意一个未成年在船上打杂。雇佣未成年在美国是个挺严重的罪名,所以我只能又多了一个船长叔叔,亲戚的小孩来船上过假期听起来就好多了是不是。
第四,让我喘口气,第四,现在——
它是螃蟹,我是水槽,我替水手杰罗姆盖着那个盖子呢。
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个征兆会不会找上我?我这会就在琢磨,它打碎盖子从水槽里爬出来是早晚的事儿,而这种结局杰罗姆理当早就知道,因为近两年,是的,自打2016年年底,他脾气变得暴躁、时常酗酒,尤其是,他又开始做噩梦。
那是种什么感觉?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杰罗姆的那个惊悸的晚上。那就是他的征兆,即使并不是我的,我也本能地感到恐惧。
这是个漫长的夜晚,酒精让他短暂地得到了安宁。
我靠着舱门,烟头被海风吹得忽明忽亮,港口的喧闹隐约传过来:那些乌七八糟的吼叫和哄笑,那些颠三倒四的船歌和口琴声——
我要当面问个清楚,尽管我已经差不多算把自己说服了。但我需要他正式地说出来。即使他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账、恶贯满盈的凶徒,但我当他的跟班已经四年,我也分担过他的恐惧、欣赏他娴熟的技艺,而且大部分时候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他还至少救过我两次,当我在甲板上犯下愚蠢又致命的错误的时候。
是他而不是别人,把我从那地方带了出来,教我手艺,使我不至于饿死。我甚至有点好笑地想,假如他是我的弓头鲸,那么至少我应该为他做一道鲸骨门。
总之,星期二我不杀人,至少现在不。
一切等到天亮吧,天亮再说。
字数641
致亲爱的青(绝密)
希望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懂得保持这封信的隐蔽性,如果遇到了你不认识或不理解的词,千万不要把这封信交给你的家人——事实上,我不知道那是你的第几任家人,但我由衷地希望他们是最后一任。
虽然这样的话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有点难以理解,但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告知于你,你也应该享有知情权。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孩子,我敢说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儿童像你这般奇特。
说真的,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真的没想到我的行李箱会在你的手中被修复完成。
也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如何才能避开宰客的店铺。作为回礼,我们最常去的那家店老板那里保存着我赠予你的一份小惊喜。
然后我必须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相当有问题。
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亦从未称呼过你的真名,你们几乎互不干涉,但你每次都被要求面对邻居说出关于父母的谎话。
这很难不让人产生不妙的联想。
你应当远离你现在的父母。事实上,他们似乎涉嫌某项不合法的特殊活动,你不过是他们明面上的挡箭牌而已。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稀里糊涂的原因成为无法回头的人。
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近期内无法再次与你见面,希望再次见面时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名字。
最后,我想说,如果你做出了你的选择,并且十分坚定地想要跟我走的时候,请拿着这封信去找码头的琳,她会暂时妥善地安置你,直到我再次见到你为止。
如果你最终没有见到我,那么我希望你最终不会被任何人束缚,这个世界远远比你想象中的模样要神奇,希望你能代替我认真的看看这些神奇的地方,当你确定你的确有能力独自出行之后。
你永远的朋友,(字迹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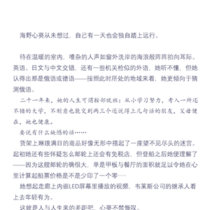
字数:2616
出演者:海野心葵
*剧情的发展,时常并不如观众所愿。
===============================================================
壁灯亮起,音乐断续,立足处正在起伏。
这起伏极其轻微,如不知间隔多少狭长过道的乐曲。
摇曳的灯火打亮驻足者的轮廓,照在摊开于页码42的书籍上。
弥生仁垂着眼,均匀地将书页后翻。
他几乎贴着墙站,食客们往来的身影穿不透书壳,无从打扰到他。他自在极了,像身在自己的房间。只在翻页的间隙抬头,隔着玻璃向餐厅内投去短暂一瞥。
——海野心葵端坐在餐厅一隅,细嚼慢咽。
她在他将离开时来,因此他来得及返回这里,将书交给她。
这比傍晚去敲她的房间门,或相反,要合适得多。
一页,又一页。
弥生仁要等的人在第4个三分钟后站起身。
他维持着这副姿态捏住书脊,等待对方从餐厅的唯一出口迈向自己。
而方才还自在独处着的心葵在看见他的一刹那便“呀”地一声站住了,身体与神情都紧绷了起来,像被上了发条的玩偶般僵硬地弯下了腰脊。
“您——您怎么还在这里?”
“我刚回来。”弥生仁合上书。他像是没听到女性毫无遮掩的惊呼,神情自若地将书递给她,“我想应该来得及,就去把它拿来了。书签在扉页,请随意使用,要折角也可以,不用顾虑。”
“什么?……啊,谢谢您,我会尽快看完还给您的!”
她看上去好像又忘记了一些东西。虽然一转眼就会想起来,但考试或将来答辩的时候这样可不太妙。
她自己知道吗?是不是该找个机会提醒她?
仁为此稍感担忧,看向她,而海野心葵笑得像揣进怀里的是刚被宣布中奖的彩票,连耳廓都泛出细细的红晕。
这可真是……傻笑。
不过,快乐总是好的,不该受到打扰。
“纸质书慢慢看才好,”仁礼貌地避开视线,转身站到她的侧前方。“旅行才刚开始,不赶时间。”
这句话也提醒了他自己。他把步子放得小些,向心葵确认,“海野小姐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吗?”
——从餐厅到电梯之间有好几条岔道,很容易迷路,视线也不开阔,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好选择。既然遇上了,他就该为她指明更好辨认的方向。
“有!”心葵回答得很及时,不像在走神。 “您也是么?平常吃完晚饭以后就在邮轮里四处走一走?”
“是的,”仁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照逃生路线踩点无疑也是种“走一走”。他已经摸清楚了大致的脱离路线,正以每天一层的方式仔细查看每层具体都有些什么。而昨天所弄清的场所里,有身旁的女性应当感兴趣的。
“——说来,海野小姐知道船上还有电影放映室吗?”
“啊?电影?在邮轮上?这层?……天啊,真齐全,我都想找个时间去看看了。”心葵眨着眼连声追问,她镜片后的眼满是好奇,脚步也不再刻意地与仁保持距离。
他们并肩而行,她像索食的雏鸟,叽叽喳喳地探出头。
“那除了电影放映室呢?我好像只会去甲板上走走……”
“地方不大,放的都是些旧电影。不是这儿,是阅览室那层,出售音响制品的店好像也在那里。这层最多的则是餐饮,有几家店出售点心,我打算回程时捎些回去。”仁一点、一点地回答她。
他们在交谈中踏过第一个岔口,飘忽的音乐声稍微清晰了些,顺着地毯蔓过来。
——“放映厅外面是个小小的圆形门厅,我见过有人在那里跳舞。”
仁回忆起第一天下午所遇见的情侣。
他们面对面无声地微笑,面对东洋人突然间的请求害羞地牵着手应允。
于是他得以将那一时刻藏入心间,照进相片。
“海野小姐有试过双人舞吗?”
仁想推荐这位易于羞怯的女性试试——去舞蹈,去相信自己的舞伴,但不仅仅是跟随,而是与之共谱舞步。
“大一的时候倒是选修过交际舞,可从没有在课外跳过。”心葵说。
“那海野小姐或许更熟练些——那对老人不像常跳。”仁继续回忆着,“也是交谊舞。city of star…那天放的是爱乐之城,他们跟着曲子起舞,很慢,步子也跨得很小,而且不时暂停。”
“那样也好啊……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上课时学的舞步了,只是记得有一堂课上,老师带一个学生跳了一支探戈,一开始只觉得惊艳,后来在一部电影里听见了才知道,那首曲子叫《一步之遥》。”
满心热切的曲,将人溺毙的爱。
海野心葵的声音是向往的。
他沉默地和她转过第二个岔口,而后接上话。
“我只记得女步。”弥生仁笑着说,“还是大学的活动内容丰富啊,高中里即使学生有兴趣,也没有相应的指导老师。”
“女步?这么说,您会在班里教学生跳舞么?”
“每年的圣诞会在校内举办舞会,在那之前会划出几节课来培训——人数不对等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师就得加入了。”
那是难得的,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彻底放松的时光。
心葵听起来更加神往。
“圣诞节舞会啊,我以前的高中从没有举办过,一定很有趣。能和您跳舞也一定很——呃”忽然间她又打了个嗝楞,“很……很好,我,我的意思是,学生们这么喜欢您,一定都抢着想当您的舞伴吧。”
“抢着让我跳女步,即使是女孩子们。所以我至今没怎么用过男步。”
仁毫无负担地说。
他扮演“跟随者”,实质却依旧在引导他们。
“好开心呀。既然这里有舞厅,也有人跳舞,说不定……说不定这次旅行也会有舞会……呢……瞧我都瞎说些什么呢。”心葵的声音渐渐低下去,
她又落后于仁了。
他们穿过走道,到达小小的门厅。
乐曲声从脚下的地毯涌来,像有支看不见的乐队。
仁意识到身侧这位年轻女性的憧憬。
她努力学习,认真生活,在充满幻想的高中阶段大概也落在地面。
好孩子,乖孩子。
“确实有可能。不过就算没有也没关系。”他顺着她的话说下去,鼓励她“这里有音乐、场地和人,已经足够起舞。”
——也许叶菲姆愿意组织一场小小的舞会。
而心葵突然停止前行。
“这里?您的意思是……现在?”
她依旧小心翼翼,却没有因这想法的荒谬而将言语半路吞下,假作玩笑。
“……?”
而仁偏过头,立即发现自己想传达的意思出了差错,心葵正因此产生期待。
她的双手捏紧了书籍,面上的红晕在灯光下无处藏匿,她的雀跃与快乐是如此生动,就像……
“……也许海野小姐愿意陪我练会儿男步?”
他笑着,落实她的猜想。
“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她说得没多少信心,细弱得如同梦呓。
——既然这么不确信,为什么不索性咽回去呢?
仁微笑着想,向她递出手。
心葵将它握住。
“海野小姐,书。”
仁听见自己的声音,它平稳得和在课堂上念诵课文时一样,制约着好奇心与其它一切不该展现出的情绪。
女性的眼睫飞快地颤动着,湿润的双眼仿佛要因浇下的灯光要沁出泪。
她的皮肤也如要烧起,握着仁的纤细手指用力蜷缩着,使他感受到一点疼痛。
接着,她瞠目结舌地抬起另一只手——掌心里还攥着那本巴掌大的书——用一种快哭出来似的腔调问他,“……书?”
她握得是这么的紧。
仁于是维持着这姿势,用另一只手自然地抽走那本书,将它搁在一侧的壁灯上。
在这之后,他轻柔地回握她,包裹住她因过度用力而颤抖的指尖。
“海野小姐,你看起来像被抓到作弊的学生。”
远处的乐曲停下,换了舒缓的新篇章。
仁依旧是安静而平和的。
他接着说,“没关系的,这场考试不扣分。”
与此同时,他已心知肚明——
【我当远离她。】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