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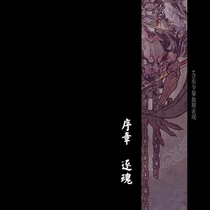

你要问那个瞄准镜的另一边是什么颜色的。
“全是废话,不是那边红就是这边红。”玉梢呸的一下吐掉了自己嘴里的那根棒棒糖,糖分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脑进行活动以及提高注意力,烟草?那众筹的要命的东西死了都不要去碰。
“冷静点,那里有那这种暴躁的狙击手。”耳机里传出来的是慢悠悠的责备,当然了在他耳朵里听起来那根本就不是责备,更像是平日里的闲聊。
“啊——我说娘娘啊,能不能下次不选这么不愉快的时间进行交易啊,冷的要死啊。”玉梢咂了咂嘴,舔掉了嘴角边残留的棒棒糖,黏腻的触感让她感到了不适,但是一分一秒那只眼睛都没有离开过瞄准镜。
“别这么说啊,不选在深夜,你还要选在条子门口光天化日大喊大叫?”
“我也没这么说啊。”玉梢反驳,“但是现在和光天化日没多大区别啊,对面早就知道这里的行动了吧。”
透过瞄准镜能够看见的是对面高楼的玻璃后面和自己一样看着瞄准镜的男人,身姿整个融入了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只有头上那一小撮红发才能让玉梢勉强看见那人的位置。
在头顶染红发那不是靶心么,哪有这么傻的条子。
翻了个白眼,玉梢拆开了另一个包装纸,里面装着的是几块饼干。
手表上的指针终于是划过了12这个数字,玉梢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对准了那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晚风掠过已经被废弃的工厂,即便是在这秋日,也让人感到一丝凉意,沁人心脾是不能比的,白寒给自己裹了一条围巾还在拿了搓了搓手臂。
横刀也一言不发,指尖夹着的烟头一明一灭,直到烟灰落下在,掉在了他的皮鞋上才想起来自己在抽烟这件事。
实在是过于无聊了,在这里干等人什么的,这个阵仗完全不像是要干坏事的样子,反而像极了古惑仔和他马子。
“我说,我作为组织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怎么半点优待特权都没得。”白寒用胳膊肘戳了戳横刀,用眼角瞄着放在仓库里的行李箱。
“别废话了,明天的菜单还没定下来呢,有什么抱怨你先看看楼顶玉梢再说。”
“我听见了哦。”
通讯器里悠悠传来这么句话,横刀浑身一颤,也不知道是被风吹得还是被玉梢吓的。作为一个狙击手这女人是格外的暴躁直接,半点不像是能在极端环境下连续观察目标大半年的老手。
“说好了不要用通讯起呢。”
“真烦,通讯器好用啊,什么蓝牙无线通讯器,还没个上世纪的机器信号好。”
白寒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赞同了玉梢的意见,“于是?有人来吗?”
“没空看。”撂下这句话,玉梢那头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说起来,不是约的一点么。”横刀•盲生,是终于发现了华点。
白寒裹紧了自己的衣物,接下了话茬,“守株待兔呗。诶,明早记得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
“不要说得好像我是你们大厨似得。”横刀也不可以,给了个白眼,拍了拍自己的哈雷,“这伙计都快成菜场搬运用小推车了。”
“守株待兔?我们不是守株待条子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祸云穿了件短款的皮夹克,带着银链子,一条红色的紧身裤在夜晚格外的显眼。
“呜哇——你是从哪个夜店出来的?一晚上多少钱?”
这次玉梢的通信是从耳机里传出来的,祸云还没听完就把那玩意从耳朵里抠出来扔在地上踩了个粉碎。
“好歹是公费啊——”
这次是三个人的对讲机。
或许组织里除了娘娘,最恶劣的就是这个女人了。
“啊啊——情报通知情报通知,对面的狙击手看着我了,你们自己解决问题哈。”
顾炎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对面的人,透过瞄准镜,能够看见那个女人一会按住自己的耳朵一会拿起对讲机,也不知道在和几个人对话,没一会又朝自己比了个不雅的手势。
“我说,真的不能爆头吗。”
“不能。”
“不能。就医学上来说你这个距离爆头,死相很难看的。再说你又不是第一次互相爆头,子弹在空中碰撞的次数还少?”朱杏,撅了撅嘴,一身白风衣,里面一件粉色的绒线衫配上不长不短的裙子和便于活动的平跟鞋,怎么看怎么像大学生。
要说这两个狙击手,也是特异中的特异,谁见过狙击子弹互相打架的?
逐魂倒是撇了撇嘴,自己明明还是个实习的怎么就被拉来了?自己本来应该在食堂里面吹着空调享受阿姨多加给自己的腌萝卜一边和小女友聊天的。
“你们装样子装的像点啊,这样只像是同学。”赵衍总指挥官终于是发话了,本来他就是坐阵大本营的,怎么还被卷进这种无意义的口角之中?
“今晚的情报确定准确吗?”觉拉扒拉着自己的夜宵,咬了一口藕盒感叹着今天这顿饭的火候是正正好,“不会只是个幌子吧。”
“谁知道呢,人家只已经在那里待机一个小时了,教母的影子是半个都没有。”就在这时,顾炎发现自己瞄准镜中那个人的影子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了架在那里的武器罢了。
“全体注意!对方狙击手不见了!高度戒备!”
“不是,我们都还没到地方,你担心什么鬼。”逐魂骂了一句,拉着朱杏便跑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陪你们,一起做这种高危险的体力活嘛!!”
“因为警局只有你一个女的!我实习生都来了就别抱怨了!”逐魂反驳着,尽可能的让自己身后的朱杏跟上。
“话不是这么说啊!愿意做法医的女孩子很少的!我应该是你们的宝物!”
觉拉没来得及把最后一口白饭送进嘴里,就匆匆忙忙站起来收好了饭盒,也往案发现场跑。
“啊,那啥,我在做任务,钱一会再说。”玉梢摆摆手,昏暗的灯光下,空调开的温度过高,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很。
“别废话,你在这住了三天了我的姐姐啊,开了几瓶威士忌了自己数数。”
“那又不是你的钱。”玉梢给了白川一个白眼,死不承认自己开的就是他冰箱里那几瓶。
“我说你一个干偷窥的,喝那么多酒干嘛,不怕伤肝啊?”白川拿他那烟杆点了点玉梢的脸,“看看你自己,还说是个女的,肤色暗沉的更泥潭似得,我看你已经不是肤色暗沉了,是印堂发黑快要被条子捉了去吧?”
玉梢一下拍开了那烟杆,手背一阵发疼,拿起对讲机就是一通抱怨。
站在空旷仓库前头的三个人不得不关掉了对讲机。
“怎么,你们家狙击手又发牢骚了?” 虞老板姗姗来迟,事实上两帮人约定好的时间是零点一刻,什么一点,完全就是给条子的假情报,让他们扑空的做法。
“啊,是这样,不过速度要快了,条子可能已经有动静了。”祸云挠了挠自己的头发,“东西呢。”
“在医生手里。”虞老板也不含糊,压低了自己的帽子,似乎是从帽檐里摸出了根女士香烟递给了白寒。
“人员编号在里头。”他瞧了瞧四周,“我要的东西呢。”
横刀看了看白寒的脸色,确认了滤嘴里确实有相应的号码,也没有多怀疑就打亮了打火机烧了纸条。
这时,白寒眼前一亮,脚边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弹坑,是条子和玉梢。
没有时间了,脚步声抓紧的靠近这个废弃仓库,横刀跨上哈雷一把抓过虞老板,扔在了后座上。
“——西南——子,朝——走!”对讲机里是玉梢的声音,但是因为电波不太好,几个人都没听清楚她讲了什么。
横刀啧了一声,开向了仓库里头,祸云和白寒两个人则是朝着东面跑。
“唔!”白寒一声闷哼,手臂上就多了个洞。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
“切!一定是那个家伙教的!”顾炎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要害,对方在过小的瞄准镜前采取的走位方式和躲避方法怎么看怎么映照了狙击手最讨厌的方法。
“唐叔!把东面的路封了!他们朝你那里去了!朱杏逐魂!你们绕到仓库后面去!”
“呀吼——你好啊,狙击手先生。”
顾炎的通讯被中断了,就连着觉拉和剩余人员的耳机里都出现了这个声音。
是杨雨霖。
“我说娘娘,你这么和人打招呼不好吧。”如璋缩了缩脖子,刚刚破译的通讯密码就这么被自己的BOSS抢去打招呼用了,坐在一边的绯也没办法地摊了摊手。
“今天晚上挺冷的,去街上吃碗热乎的馄饨怎么样——?工薪阶层?”
“呜哇——真气人。”拉下了脸,坐在办公室里的赵衍都听不下去了。
“这,仓库后面没门啊!”
急忙赶到的觉拉和逐魂他们会和了,但是绕了一整圈都没找见像样的通道。
“这回没法联系空和阿芷,他们那里的旅馆和医院不知道查的怎么样了。”
白川把玉梢揪下来之后便扔进了密室里。转头去看门口铁三还在和那个实习生的小警官周旋。
“都说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你看,营业执照还挂在那呢。”铁三双手抱胸,任由那个小男孩乱翻,就连前台里头的备用计生用品都被翻出来了。
“这!这是什么!”空涨红了脸,指着塑料包装的东西质问道。
“怎么,还不允许旅馆有这些卫生用品了?”白川走下楼梯来,一脸的好笑。看了看空,又看了看铁三,接着一句话让空落魄而逃,“小伙子长得不错啊,要和我试试吗?”
“老板啊,怎么说这个讲法都……”
“闭嘴。”
阿芷的电话几乎是在同时响起来的,穿着黑色长西装裤和小高跟的女孩坐在诊疗室里翻查所有的记录,愣是没找着奇怪的点,看了监控和所有的房间也没找出半具身份不明的尸体来。
“把,把所有的药物拿出来!”阿芷鼓着脸颊,挂掉了电话。
反观恭弦笑着点点头,手里捧着老厚的医学教材满脸微笑,一头黑色长发被束起来拢在一边,“小姐这边请。”

坂本真绫和能登麻美子的历史性合作【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听得是个节日,玉梢立于月下,伸手去摘那还未开花的月季,得了店长的许可,明日又能出门取看看外头的景色,在这花丛中摘得些这日子少见的花儿去,明天也算得上是有点事情可以做了。
现时秋日,先不说着四季如春的徒然堂也吹起了风来,外面的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要凉,终是不见那日放河灯时各家小姐穿着的绫罗绸缎,路上的新人不是披上了外衣就是穿着厚实的衣物。
玉梢或许也能觉得冷,只是对于她而言这些似乎都不怎么重要,只不过是气温稍稍下降了一些罢了,很快的,就会有漫天飞雪也说不定了,对于雪天的记忆玉梢也没有多少,想着总要在冬日前找着个能带自己出门去的主人,又想着自己得寻着什么能做的事情,不然这冬日就太过于无趣了。
自己从不是什么能言之人,更没有那巧舌如簧的技巧,在这世上也没几个能够正常的交谈之人,玉梢想要得到的消息和传闻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想着只能靠自己又没几个人能见着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也就只好听着人的闲聊度日。
她不羡慕那些有着明确目标的人和灵器,也不嫉妒那些已经找到归宿之人,只是怨自己过于无能罢了。
伸手去碰那花枝,带着茧子的手心倒是被刺扎得有些痒,用剪子咔嚓一声剪下放进篮子中,玉梢手边的提灯又灭了,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根蜡烛,她只是彻夜在这徘徊找些能被剪下的花儿来。花篮里的蜡烛逐渐逐渐地被花枝代替,月亮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隐去身形,夜到了最深的时候,玉梢终于是停下手来,拿起打火石点上最后一根蜡烛塞进提灯之中,离开了这花田。
即便自己的身影不能被人所见,但是自己拿着的东西似乎是能够被看见的样子,又或许被自己放开之后会被见着,玉梢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只是想着趁早也就能躲开人们的视线,借了店里的笔墨纸条,揣上一个布袋子,也就带着花篮出门去了。
提灯照亮着身前的路,自己的影子随风摇曳就像是要被吹散的蒲公英那般摇摇晃晃,玉梢停下来,蜡烛没有被吹灭,反倒是提灯被吹得微微晃动,指尖也被风的力气带得有些累了。
是晨光。破晓了。玉梢回过头去看被山峦挡住的那个火球、那束白色的光芒,她低了低头,似乎是在躲避那耀眼过头的光,又似乎是在沉思。
吹灭了蜡烛,玉梢继续前行,路上偶尔的能够遇上几个樵夫或者渔夫,农民似乎还没有起来看看地里的收成,只是路过田地的时候玉梢折了一根麦穗捏在手中玩,稻米累累,对于那空心的麦秆来说实在是有些重了,但是也不断,只是低着头随着玉梢的动作摆动。
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玉梢是终于到了街上,那些个店家还没有开门,玉梢找了个转角放下了手中的篮子,那不是什么必经之路,也不显眼,只是若是细细去看了便会发现那墙上的裂痕似是被果实压塌了的枝丫那般垂下的样子。
找了几块石头压住了自己写的纸,玉梢不知从哪找来了一个还算干净的小马扎,嘴里叼着那刚折来的麦穗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曲调。
那些个公子小姐路过之时玉梢看看他们的衣角,有些厚实的料子下头穿着的都是舒适布料制成的内衣,有时有人停下弯下腰来看玉梢写的字时玉梢也就抬眼去看看那人长得什么样貌,也凭着样貌在心理去猜猜这人是何籍贯,若是有人并肩而行说着这世间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玉梢也就停下哼曲的声音,去细细听那些个故事。
有说近日有人见着鬼,也有说在过山时被奇妙的男女拦下了,玉梢有一句没一句地收集着信息,倒也是把近几日奇怪的事情听了个全部,终于是到了正午快的时候了,行人变得多起来了 ,就连这样的转角小路也人流不断。
一支一回眸,一文一时节。
玉梢没学过什么诗词歌赋,最多也就是看见过两眼那些个墨宝书画罢了,毕竟自己最新的记忆是和那些个书画装饰在一块,也是在提笔写字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原来也算得上是会写几个大字,白纸黑字的,没几个人来拿自己篮子里的花,倒是来看这字条的人越来越多,玉梢斜眼去看,自己也没写错字来,只是字体可能不符合这个朝代罢了,墨汁因为季节的关系有些晕开,笔锋也被掩盖了一部分。
只看了两眼字便掏出铜板来的人也大有人在,不一会,玉梢篮子里那些已经开了的花是没几个人拿走,倒是那个小布袋子已经被装了一个底。
到了正午,太阳挂在最顶上的地方,玉梢躲在墙后的阴影里打了个哈欠,摸了摸指尖自己似乎是在打颤,歪了歪头,黑色的长发也就落下来盖住了自己的手。
这时候玉梢眼前又有人弯下腰来,袋子里响起了同板的声响,终于是有人拿走了篮子里的一支月季。
玉梢也就抬头去看那人,似是个文人样貌,衣物打理得整齐,手上的茧子也是握笔才会有的东西,只少不是农民也不是那些个舞刀弄枪之人。
侧了侧身子,玉梢见着他身后立着个穿着鹅黄色衣物的姑娘,肤如凝脂,眸如晕墨,伸出来接花的手也如那被雕刻出的供奉起来的石像那般优美。
便是有情人吧。玉梢撅了撅嘴,心底也不知是祝贺好还是一阵泛酸。只是现在才觉着自己做这事本身似乎就是在给自己添堵。
那小姑娘是笑得开心,花枝乱颤的样子看得玉梢心理一阵发毛,本以为是什么可人儿,一开口她都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那是因为玉梢你太不像是女孩子家了。”
“.…..有吗?”玉梢抬头去看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侧的慕双,那抹红色在自己眼里显得像是火那般的在烧,也不知她怎么得空出来也不知怎么就找到自己这里来了,玉梢没有去多问,只是从花篮里挑出一小束铃兰来招招手让慕双蹲下,自己则是一边看着那纸条不要被吹走了一边拿着铃兰的花枝绕着慕双的长发做了一个简单的编发来。
“哪有姑娘家大半夜的出门摘了花一大清早的在路边摆摊的,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什么家世。”慕双双手撑着脸,声音听上去有些闷,似乎是在抱怨玉梢多少有些过于不想寻常女子。可玉梢也不懂慕双口中说的平常女子平日里到底应该怎样,对于她来说随着自己的性子来似乎是最舒服的事情,既不碍着别人也不会出格,她没有被教导过的记忆,只是生性使然,就这样玉梢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究竟是哪里的出生。
“平日里的你看上去倒像是个大家小姐的样子,怎的一出手像是个洒脱的剑士似得。”
“我不会劫富济贫。”玉梢冷冷道,手上的茧子似乎是有些被那花枝勾破了皮,缠上了一根黑发不经意之间把它挑出了发髻垂在那铃兰的小花上头。
“你不会,你当然不会。”慕双也不去在意玉梢一瞬间的动作的停顿,只是接着说,“但是有人求助你也一定会去,你真的是个奇怪之人。”
“你很温柔。”玉梢定论着将那发丝重新塞进发髻之中,动作轻柔。
“你一点也不像是从墓里出来的,总以为你会和冥器那般性子。”慕双拍了拍自己的裙角,从口袋里摸出几文钱扔进了布袋子里,“真是好手艺,别人见不着你是有些亏了。”
玉梢敲了敲太阳,可能已经过了正午有些时候了,花篮里的花也有些蔫了,不过大部分是已经被拿走,路上行人多的是有情人,玉梢也就一个人挎着篮子手拿提灯袖子里装着那些个同伴。
路过遇见了什么独自前行的姑娘便是悄悄地往她们发上别上一支,看见了孩子也就塞个同板在那衣服的小袋子里。
一路上走着,玉梢听着他人交谈的声音,隐约的又听见有人说哪儿的山上下来了两个大盗,衙门似乎正在拟作捉捕令,路上巡查的人也变得多起来了。话语间漏出的信息似乎是在说那两人专挑着名贵的东西下手去。
玉梢也算听过就罢,也没有过于地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只是见着前头似乎是有丧队路过便是退到一边去,走在前头的是垂垂老矣的女性,或许那棺材里头躺着的是她的丈夫或者小辈吧。玉梢摸了摸自己的花篮,捡出一支样貌还算好看的白菊抛在了那棺材上头。
路边的人纷纷让路,也有人说这里头的似乎是暴毙而亡之人,平日里也算是个善人,只是不知怎的就这样没了。
玉梢等着这队伍走了也依旧停留在原地不知失神了去怀念什么,她低着头,也叫人看不清表情。
夕阳西斜的时候终于是回过神了的样子,有人拽了拽玉梢宽大的袖子,是个小孩,他指了指自己篮子里的那支茉莉又递上一颗糖来。玉梢不喜幼儿,只是这样诚恳的样子也叫人不好拒绝。
只见那孩子拿着已经有些谢了的茉莉别在了女童的衣领上,样子有些歪斜却也透着童真。
玉梢长叹,自己或许连个孩童都比不上吧。
又有人拽了拽玉梢的衣角。这回篮子里是什么都没有了,玉梢或过头去看见的是熟悉的面孔。
“你在这里呀。”是阿芷,“店长说你今日出了门来,我也就来找你了。”
玉梢没有说话,只是垂着头去看那笑得开心的姑娘,猛地想起自己还有颗糖在手里,也就剥了糖纸塞进了阿芷的嘴里。
“咬废库吗?”
因为嘴里喊了糖,阿芷咬字有些不清不楚的,玉梢把手中的竹花篮递给了阿芷,另一只手也就隔着衣物牵着阿芷的手,拿着提灯慢悠悠地朝前走,路过的茶馆都已经准备打烊了,饭馆和旅店倒是生意兴隆的样子,半点不像是有那种不好传闻出现的样子。
“瑜晓?”糖似乎还没有被吃完,阿芷也就跟着面无表情的玉梢往前走,左看看右看看,有时候偶停下来去看那些绣娘的样子,玉梢也就以为阿芷对那些个绣娘手中的帕子有兴趣,看了看那些个好看的料子,从布袋子里拿出合适的铜板数放进了绣娘的口袋,拿走了那块绣着腊梅的帕子递给阿芷。
阿芷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样子,但是看着玉梢是认真的也就这么收下了帕子去。
时值傍晚,路边家家都飘烟袅袅,传出饭菜的香味,玉梢沿途也买了些个梅花糕什么的,一个劲的往阿芷手里塞。
阿芷摆摆手说不要,只往自己嘴里塞了几块桂花糕去,剩下的也就全都进了玉梢的肚子里,玉梢生不逢时,虽说出生时的点心也不少,但是也没那实体能吃上几口,后又直接进了墓里去,怎么说也没得机会尝尝各地美食,到了今日也就一边朝外跑,一边买着各式各样点心。
这花钱的样子要是叫店长看了去怕不是要训斥一番才是。
玉梢在路上边走边看,也不买那些贵族小姐要用的香囊粉黛,只是一个劲的去买吃的,每个只买一点尝了味道就算结束,就这样玉梢一天下来的收入都被扔进了那一屉屉蒸笼里去成了那缥缈白烟,自己倒也是吃了个七八分饱。阿芷是被塞得几乎走不动路。
总觉得自己像是被当做什么可爱的小动物投喂了,阿芷多少有些闹起了脾气,但是看着玉梢手中那盏提灯和就算吃了好吃点心也毫无变化的表情,也就消了气跟着接着逛。
直到月亮都出来了,那花街到了最繁忙的时候,玉梢才想起今天听到的那些个传闻,直拉着阿芷往回走。
“玉梢?”
“回去了。”想了想着这么一句或许不够,又补上那么一句,“最近别出来,要出门也最好挑上午,人多的地方去。”
阿芷笑起来,玉梢也不知这姑娘在笑些个什么,只是随着她去,全当是自己说了什么奇怪的话或者真的只是开心罢了。
“玉梢的字是真好看,下次便是一块练字吧。”
玉梢没有回话,不答应也没得拒绝的意思,沉默着带着阿芷回了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