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冷刺骨的海水是他一辈子的噩梦。像是一根鲨鱼骨磨就的锥子,被冰山的尸体狠狠钉进大脑里,疼得死去活来,硬生生钉出了另一个人来。
-
每天的清晨,利利安准时准点地在闹钟响起的前一秒醒来,迅速拍下将要扯着嗓子开始尖叫的闹钟,起床将自己打理好。
镜中的人的长发如火,涂上了口红的双唇衬得她的脸色越发苍白。
利利安理了理衣角,走出了房间,来到隔壁房门前,伸手屈起手指敲了敲房门。
许久,屋里才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进来。”
利利安轻轻转动门把,推门走进屋里。屋中装修十分华丽,地毯几乎铺满了整个房间,衣柜占满了一面墙,从落地窗投进来的阳光铺在极大的双人床面上,撒在床上人摊了一大半床面的头发上。
“今天穿什么?”利利安来到衣柜前问道。
“唔……跟昨天一样就行。”
利利安从衣柜中取出一套裙子来,来到床边将裙子放在了被子上,把还迷迷糊糊的没睡清醒的女子从床上扶起。
“不要赖床,快起来。”利利安垂眸道。
她打了个哈欠,慢吞吞地趴下床,将睡衣换下,穿上了里衣,接着便在镜子前站定了,张开双臂。
“利利安,过来。”她勾了勾唇,笑道。
“姐姐,你已经……”
“给,我,过,来。”
利利安叹了口气,拿起床上的裙子,认命般走到她身后,替她将裙子穿好,扣好链子,最后理了理领口。
“今天口红涂得不错嘛。”她伸出右手来,用大拇指蹭了一下利利安的唇角,将口红蹭花了些。
“嗯,昨天姐姐教过了,就记住了。”利利安面无表情道。
她的心情不错:“挺好看的。今早吃什么?”
“简简单单的烤土豆、长棍面包、培根煎蛋不好么?”
“啧,有点腻,”她撇了撇嘴,“不过还不错。”
-
利利安是拉菲的母亲捡到的。
在夏日的烈阳下捡到的。
当头的太阳几乎要将这可怜的孩子晒成了人干,夜间将她冲上海滩的海水当时堪堪蹭到了她的脚趾尖儿。
拉菲说不清对她的感情——有时候讨厌她,有时候又不想对她说些恶言恶语。
利利安是很听话的。听话到让她有时会有些不爽。
利利安的听话不是那种让人舒服的听话。她说话做事,只要并非自愿而是被命令,就总会以一种诡异的笑容对人。表面温和,然而却让人毛骨悚然。
“今天……”
“今天还是赌场吧?”利利安头也不抬地说道,“要是逛街我是不会帮你提东西的。”
“正好,我也不想看你那样笑。”拉菲回道。
利利安皱了皱眉,刚想开口说什么,最后还是抿了抿唇,抬起头对拉菲笑道:“好的姐姐。”
-
利利安用眼角看着拉菲在桌上用手指敲了几下桌面,将手中的一张牌扔了出去。
两个人一起目送对手垂头丧气地走出去后,利利安起身去替拉菲倒了一杯红酒来,低垂着脑袋看着手指,坐在她身边。
“越来越熟练了嘛。”拉菲道。
“那要谢谢姐姐的栽培,”利利安笑道,“真成地。”
“我记得有人约你。”拉菲没接他的话,喝了一口酒,看向在赌桌边疯狂的赌徒们。
利利安看了眼钟表,起身道:“等我的好消息吧,亲爱的姐姐。”
拉菲看着她拿着手杖走进一道被红布遮掩住的门。她还是太小心了,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带那种手杖呢?
可没过多久,她就被一阵枪响吓得手一抖,红酒洒了一半。
她愣怔了半晌,这才跑向那道门,挤进聒噪的人群。安保人员已经来了,先开枪的人也已经被制住了,她的妹妹倚在墙上,左手捂着右肩上还在汩汩流血的伤口,右手中死死握住的被伪装成手杖的长刀已经出鞘了半寸。
“有没有伤到什么重要的地方?”拉菲扳住她的左手,问道。
“没有……姐姐,我们先回去,好不好?”
-
“脱衣服。”
“姐姐……”
“给我脱,利利安。”
两个人在客厅里死死盯了对方一分钟左右,最后是利利安认了输,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避免扯到已经有些凝固了的伤口。
层层衣物褪下后,露出的却是平坦的胸部和男性才该有的胸肌,以及从颈侧蔓延至胸口的血红的纹身。利利安虽然瘦,肌肉却还是挺结实的。
“这个伤口……有些深,但应该只擦到了骨头……你忍忍。”话音刚落,拉菲就拿起了一瓶消毒用的酒精,凶残地倒了上去。
利利安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难得地咬牙切齿道:“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血流这么多,温柔什么温柔。”拉菲没好气地说道,拿绷带给他包扎好,“到底怎么回事?”
“要泡我,”利利安翻了个白眼,“我不要,就说玩俄罗斯轮盘,如果我输了我就跟他玩玩,他输了就活该。”
“……你倒是上道的。”
“他同意了啊,”利利安抱怨道,“结果最后一发就是他嘛,他不乐意了,就拿枪打我了。”
“你不出刀?”
“来不及啊,右肩受伤了,换左手都难……嘶,怪疼的。”
“活该,”拉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道,“不过你今天的确很美丽,我亲爱的弟弟。”
-
一片黑暗中,利利安坐在发着亮的棋盘一侧,伸手将主教移动了一格。
“我演技不错吧,”坐在利利安对面的人笑道,声音与他无二,却是更加温柔些,“你看,她根本看不出我们两个的区别。
“你这个胆小鬼,为什么不拔刀?
“我看只有等人把你上了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后悔了。”
“莉莉安,到你了。少废话。”利利安淡淡地说道。
莉莉安笑了笑,把棋子都扫下了棋盘,站起撑在棋盘上,俯身看着他,两人的红发都纠缠在了一起,分不出彼此。
“利利安,我看你就该被溺死。无论是维淇淇·乌姆奥汀还是拉菲·萨克瑞尔,都会对你失望的。”


“待帆过千山,鸦骨已作土。绕梁久不去,终为野戾魂。”
卜寒州微微一愣,抬头将冷冰冰的视线压在御巳的脸上。
昏暗空旷的屋内,两人之间正横着一张两丈左右的画卷。卜寒州跪在正对着画面的那一侧,长发披散在肩上,御巳站在他的对面,脸上仍是带着那万年不变的微笑。
“御巳,你不该管你分外之事。”卜寒州咬牙道。
突然,自那画卷上传出一声凄厉的鸟鸣。御巳微微睁眼,低头向着那幅画卷,皱起了眉。
“公子。”
卜寒州没有低头看向手下的画卷,仍是死死盯着额前已经冒了冷汗的御巳。
在卜寒州的手下,此时正有一滩血迹印在画卷上,还染了他的手。卜寒州默默抬起手来,自那血液中掉出一两根白色的羽毛。而画卷上,晴天碧空中,一行白鹭正扑扇着翅膀挣扎着往远处飞去,只是本应该整整齐齐的一排队伍中,竟是打中间缺了一两只。
“……提长亭。”
“……是。”卜寒州低下头,微垂眼帘。
“这是你为数不多的儿时的东西了。”
“方才你怎般说的?‘待帆过千山,鸦骨已作土’?终是要成一抔黄土,何必在意那么多。”
“可那是浑龙峰。”
“浑龙峰有给你什么吗?”卜寒州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字一句敲在御巳向来平静的心上,像是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却卷起了一场风暴。
御巳的呼吸开始急促,平日里笑眯眯的他此时几乎要哭了出来:“我、我只想……只想回……”
“御巳,你冷静一下。”卜寒州看着他几乎要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叹了口气,“你能回去的。”
“可是浑龙图……”
御巳说的是卜寒州手上的这份画卷。这原先只是一份普普通通的画卷罢了。后来,卜寒州在其背面加了一层壳,中间贴满符咒,再托了提长亭辅以三千棋灯的三千变化,使得画卷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鹿都好似活了过来一般。
卜寒州若有所思地用血红的指尖抚摸着浑龙图,仿佛要透过这薄薄的一张纸看到远山云雾下的那道山门去。
“不过是留个念想罢了。”
-
月上中天,自蜀山上浮起千万盏明灯,悠悠往夜空中飘去。
卜寒州坐在廊下,往外伸出的手还没收回,就那样愣怔地看着从他手中离开的那盏灯。
他想起了他扔出去的那根骨头。
只是一根普通的、有些大的骨头。
他丢出去后,那条大狗飞快地奔了出去,后腿发力,在空中一个漂亮的扭身,张口把骨头接了下来。
“乖孩子!”男孩揉了揉冲过来扑在他跟前的大狗的脖颈,一把抱住了它。
大狗的尾巴左右甩得起劲,舔了舔男孩的脸。
男孩身后的屋里走出一美貌女子,只是面露疲态,平添了几分忧色。她将耳侧的碎发捋到耳后,唤道:“寒州。”
卜寒州回过头去看她,喊道:“娘!”
女子笑了笑,张开了双臂。一人一狗顿时默契地撤开,跑向女子。卜寒州扑进她怀里,抱紧了她白皙的脖颈。大狗在女子脚下边叫边摇尾巴乱窜。
“寒州,今日是十五,我们去做灯好不好呀?”
“好呀!”卜寒州兴奋地喊道,接过女子递给他的麦芽糖,塞进嘴里,“还要吃猫儿糕!”
“好好好,猫儿糕猫儿糕。你看看你,都快成一只小馋猫了。”
卜寒州咯咯笑了起来,偏过头避开娘亲戳过来的手指。
日头西落后,女子将一盘小糕点搁在了在厨房里呆了一下午而变得灰头土脸的卜寒州面前。盘中的几块糕点都是猫的形状,可爱又软糯,入口冰冰凉凉的,是卜寒州这总安分不下来的孩子最喜欢的零嘴。
卜寒州刚想伸出爪子去拿糕点,女子就突然一掌拍在桌上,截住了他:“寒州,今天你学了哪些,都告诉娘亲。”
卜寒州缩了缩脖子,老老实实地把这日所学得的东西都捋了一遍,这才从娘亲手里接过糕点,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娘,为什么只有每年的八月十五您才给我做猫儿糕哪?”
女子看着嚼得一本正经的卜寒州,笑了笑,除了揉了揉他的脑袋外没有说什么话。
-
“娘……为什么只有每年的八月十五您才给我做猫儿糕哪……”
卜寒州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掌心,攥紧了,叹了口气。
“寒州,我不能继续呆在这里了,你……”刚从西北城的魔爪和云想的调侃下逃出来的良英撇了撇嘴,道。
卜寒州盯着他微微泛红的脸,道:“司马遥星?”
这下良英的脸更红了。
“加油。”
对卜寒州来说,算是相当诚恳的祝福了。
良英离开后,接着来的是提长亭。她手里提着一坛酒,脸上飞红,伸出手来不安地递给他。
“师兄……这是碧月,你尝尝。”
卜寒州双手捧住那略沉的酒坛子,笑道:“如今我比你年纪小了,别再喊师兄了。”
提长亭却避开不答,道:“碧月是你……之后,夫人酿的,我用术法封了一坛在墓中,这坛还是夫人的手艺。”
卜寒州的睫毛颤了颤,覆在酒坛上的手指微微蜷缩起来。
提长亭在他身边坐下,看着他开封,在浓郁的酒香间斟了一杯酒,仰头将酒尽数倒入口中。卜寒州把酒含在嘴里,好一会儿才咽了下去,喉头上下滑动了一番,道:“苦。”
“苦?”提长亭皱起了眉,“怎么会苦呢?明明就封得好好的……”
“但是香。”卜寒州道,“是好酒。”
“是我不好。”卜寒州低下头去,手中捏着那只酒杯,慢悠悠地转着,“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师兄?”
“若娘在怀我时就把我堕了,就不必殚精竭虑地把我护到出事之前了。”
“师兄,”提长亭轻轻握住了他的左手,顿了顿,“红蝉星不是你。”
“是我,也不是我。可还有什么意义吗?浑龙峰终究是……”
“师兄,中秋快乐。喝酒吧。”提长亭打断他道。
-
提长亭被卜寒州哄回去后,来的是西北城。
卜寒州跟西北城不大熟,硬要找些关系的话,只能说是提长亭和御巳都与他认识,他还老喊良英“大侄子”。
西北城拿给他一个不小的食盒,竟是沉得惊人,应当是满满当当的,放满了吃食。
“你不去陪你的伴儿么?”卜寒州接过食盒,闻到了一股有点熟悉的香味。
西北城笑道:“就替鱼丝儿送个东西罢了,顺路。”
“御巳?他怎么不亲自来?”卜寒州打开食盒,愣住了。
“他说先前同你小吵了一次,怕惹你不快,就让我帮忙把东西送来了。没事儿,别介,他也答应下次泡人时帮我打掩护了。”西北城笑眯眯地说道。
食盒里有两层,上头的一层是一大堆的普通糕点,以桂花糕黄金糕居多,旁配一小壶月蓉酒,下层却是放了一盘猫儿糕。
西北城抱着手臂往里看了一眼:“这是什么糕点,他居然做了这么可爱的样子给你吃?”
卜寒州沉默着拿起一块猫儿糕,咬了一口。虽然与母亲所制的猫儿糕有些许不同,可与记忆中几乎一模一样的味道口感还是逼得卜寒州憋不住从眼眶中滚落的泪水,鼻子发酸,几下把猫儿糕啃了。
“你怎么哭了还?”西北城被他吓愣了,俯身问他。
卜寒州一边啃着猫儿糕,一边道:“没什么。”
御巳急急忙忙地赶到时,就听见卜寒州抽噎着,西北城在一旁陪他聊天。
“鱼丝儿来了,我先走了。”西北城拍了拍他的肩,起身离开了。
“……你怎么哭了?”御巳攥紧了伞柄,紧张问道。
卜寒州抓住了御巳的衣角。御巳不得法,只得在他身边坐下。
“你为什么会做猫儿糕?”卜寒州已经缓了过来,只是鼻尖和眼眶还红着。
御巳抿了抿嘴:“夫人教的……”
“你恨不恨她?”
“我为何……”
“你恨不恨我?”
“公子。”
“你恨不恨我爹?”卜寒州盯着他,一字一顿地咬牙切齿地说道。
“……”
“我爹是你现在这模样的元凶,我娘是把你弄成这样的人,我是让你活到现在的怪……”
“公子。别说了。”御巳按住了他的手,道,“事既已成,何必再去悔恨硬要求个结果。既来之则安之,等报了仇再说也不迟。你说的,我能回去的,你也一定能。”
-
回去?
回哪?
卜寒州看着食盒与那坛酒。
我是无家可归之人。
御巳曾说,他当平心静气,只管报仇便是。
他虽说一切都是他的错。可若没有那个人,他还能好好地同家人过完一生。
剑修杀气重,戾气重,最易滋生心魔。他虽并非单修符,却也以符修为重,剑是根本没碰过几次的。恨意难平,生了心魔,倒是可笑。
一次八月十五,竟是让他心中千般心绪翻涌。
-
再晚些了的时候,卜寒州想了想这些年在山头上认识的人。左右不多,也就那两位九月初时一道坐车的了。
方才和好后,御巳说,让他跟别人多来往。卜寒州便收拾了东西,将酒并上层的糕点分成了三份。
一份他送到了墨华章门外,一份送到了祁云窗头下。
还有一份,他放在了院里,正对着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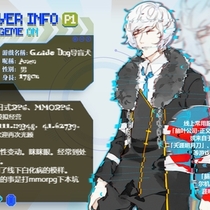
一道如花般的人影立于山巅上,腿上缠绕的杏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他攥紧了手中的伞柄,脸上展开一个使人如沐春风的笑容来。
-
“一个人?”
“一个人。”他淡淡说道。
那人欲言又止:“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
“我已经八年级了,师弟。”他摆了摆手,打着那把伞就往深山老林里走去,脚步轻快,哼着歌,像极了一只小雀。
他走后不久,一个少女走了过来。她咬了咬右手的指甲,左腋下夹着一柄提灯。
“啧,贱人。”她恶狠狠道,“方才这里是不是有个跟个娘们儿似的混球走过去了?”
那人歪头想了想。虽然那位师兄的确能称得上美丽,但也不至于如她所说,像个“娘们儿”。
见他摇头,少女愣了一下,面色复杂地纠结了自己的措辞,又道:“顶着伞的。”
“啊,那是有一个。顺着那条道走就可以啦。”
他指的那条路有阳光从树叶缝儿间洒落下来,虫鸣鸟啼一个不落,美极了,也确实是那个人的风格。
少女撇了撇嘴,摸了摸那人的脸,笑笑走了过去。
留下那人在原地红透了自己的脸。
-
他伸出手,一只蓝色的小鸟自空中俯冲下来,轻轻落在他带着淡淡香气的指尖上,亲昵地蹭了蹭他。
他停了下来,站在原地。
“提长亭。”
那少女在他身后站定了,静静看着他。
“你几年级了?”他回过身去,笑眯眯地问道,一双睫毛浓密的眼睛仍然没有睁开。
“六年级。”提长亭回道。
“那你藏得挺久啊,现在才出来。”
“但我可是一直看着你。我记得你有个狐朋狗友,怎么没一道走,好像叫……叫西北城?”
“他可不会按时到啊。”御巳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藏了?”
“我入筑基后期了。”
“你想同我打?”
“……我打不过你。”
御巳笑道:“亏得你活了这么久,终于有些自知之明了。”
“师兄呢?”
“怎么,我以为你会一直盯着。”
提长亭皱了皱眉。她一直专心躲着御巳,甚至连自个儿师兄的宗门都没搞明白过。
“他是怎么出来的?”
“有个小辈,撕了符。他就出来了。你手臂和眼睛怎么回事?”
“你他妈……果然是装瞎。”
御巳不置可否,只是持伞站在远处,静等着她的回答。
“被洞里的石头砸了身子。只是这样。”
“嗯……”御巳眯着眼睛望向天空,一手捏着下巴,指尖上的那只小蓝鸟展翅飞起,“不过这回可当心着点,有动静。”
提长亭正纳闷儿,道上突然冲过来几个黑衣人,其中一个跌跌撞撞,似是受了伤。
御巳飞身掠向那黑衣人,眼疾手快地扯了把那黑衣人背上贴着的一张黄纸符篆,接着迅速将其拍回那黑衣人背上,转身将提长亭拦到身后,往后退去,跃到山石上。
“你个贱人你做什么!”
“趴好,要炸了。”
他话音刚落,那黑衣人就被紧附在背上的黄符在背上炸出了一个洞来,其威力之大恐怕是声儿能传出个好几里。
“这是符宗的……”
“是寒州。”御巳淡淡道。
“啊,师兄他……”
“走了,还有几个。”
话音刚落,那只蓝色的鸟儿便在空中引颈长啼一声,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御巳自山石上跃下,伞上黑白棋子碰撞,烦得提长亭心神不宁。
显然,反感那黑白棋子的也不止提长亭一人。听见那碰撞声几个黑衣人纷纷摆出了戒备之姿,显然已经准备好了要打上一架了。
御巳将他那柄伞一抖,那些棋子便同绸带缠在了一块儿,大团大团的棋子撞在一起,声音更大,烦人的程度自然也更甚。
“死贱人,你他妈的给我安静些!”提长亭咬牙道,也跃下山石,手中提灯往前一置,瞬间抖开一副硕大的黑白棋盘来。
那棋盘上生出多枚白棋子,齐齐朝黑衣人砸去。
三千棋阵三千变化,网生者囚死尸,克轮回灭人道召万象。
“师妹,三千棋灯当真是好用啊。”御巳打趣道,手中伞柄一转,尖针瞬时飞出,直逼黑衣人脑门,“五万罗鬼盘在哪儿,真想见识见识。”
“鬼盘不在我这。”提长亭道。空中那棋盘织就的大网罩住了在场之人,且正往下逼。突然,她叫道:“坎位!落子!”
御巳飞身而起,收伞投向提长亭坎位,一刚持剑冲上来的黑衣人便被他生生逼了回去。
“艮位落!布阵!起刀!”
御巳毫不犹豫地落至艮位,手中白伞往地上一戳,起身一手按伞柄底部,将人撑起,在空中绕了一周,甩出去多把锃亮的刀片,薄得竟是刀片飞到了眼前才感觉出了那点寒意。
那几个黑衣人一惊,正欲侧身躲过,却重重撞上了那压过来的棋盘,同时一股力量将他们的脖颈死死扼住,正被刀片嵌进了手臂上的血肉里。
棋盘蹭了点血也不再动了,御巳已是顶着伞凭空坐在了那里,笑眯眯地看着黑衣人。
“取叶,声入乾位,配子击,封其精神。”
御巳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一片玉叶,一手甩伞,让伞转动起来从而带动棋子碰撞,同时唇间逸出美妙清音。
这音虽舒缓,却在每次转音时猛地变为尖锐刺耳之声,颇为折磨人。
虽说如此,这声音却因提长亭的阵法而有了走向,径直扎进了黑衣人耳中,一丝也没漏进提长亭耳中。
御巳停下了口中动作。
那些黑衣人有一两个还能勉强撑住,其他几个已经跪在地上起不了身了。
那站着的其中一个看了看自己的同伴,大喝了一声:“破!”
这提长亭粗粗布下的阵法竟然逆向运转起来,瞬时土崩瓦解。他与另一人提起自己剩下的同伴,取出一把剑捅破了棋网,掠身出去,消失在树林间。
“啧!都——”
“停下,收网撤阵。”御巳挥伞拦住她,“你的阵法刚破,棋网也损,眼下应当好生修整。左右他们也未纠缠不休,别为一时之气做出什么冲动之事来。”
“……啧。”提长亭收起了灯,别过了头。
御巳复又撑起了伞,几步踏开:“师妹,我先走一步。你可慢慢晃悠吧先。”
“喂!你给我站住!!!”


卜寒州睁开眼睛。
校车还在山道上颠簸,这车子上不止有他们这些老生,还有不少新生,因着新鲜味儿还没过去,现在正吵闹得很。
卜寒州的头发披散在椅背上,肩膀上,摊了一大片。他在自己褪色的头发上蹭了蹭,有些昏昏欲睡。
“啊,你已经到了啊。”
卜寒州微微睁开眼,看了眼来人,拢了拢自己头发,侧身让他坐到了临窗的位置上,打了个哈欠,继续闭眼打瞌睡。
“这么困?”良英把剑匣抱到身前,摘了一边的耳机下来。
“前日,”卜寒州顿了顿,不紧不慢地说道,“前日夜间,卜二拉着我要打牌,卜大要把他拖回去,两个人在我院里闹得鸡飞狗跳,一晚上没睡好,昨日又忙着赶路,眼下疲得很。”
“待会儿我叫了我一朋友一道坐马车,你来么?”
卜寒州抬起右眼的眼皮看了他一眼:“你也有朋友?”
良英皱眉道:“就一个。你来么?”
“来,”卜寒州抱紧了自己的头发,“左右我就你一个熟人。”
“你已经五年级了吧?”
“五年级又如何。”卜寒州嗤笑道,微微偏过了头。
五年又如何,就算是过了千八百年,他还是会做个独来独往的人。该习惯的总归还是要习惯的,他们这些人一旦筑基,注定最后要与亲朋好友形同陌路,漫漫修行路上若有一两个修士相陪倒也是极好运了的,大多最后是孑然一身。若要为了生离死别哭爹喊娘,倒不如一开始便一个人看着这人间百态,时光飞逝。
“你也交些朋友吧。”良英嘟囔道。
卜寒州没有回话,看了眼窗外,眯起了眼睛。
-
下车后卜寒州叼着自己那根长得要命的发带将自己的头发绑了起来。这些年他并没有剪过几次头发,因而这头头发也同样是长得要命。
卜寒州带着的行李并不多,里头仅有一件蜀山上统一的道袍、几件替换的衣物,剩下的只有几大沓家里给他写着玩的符纸了。
他不慌不忙地跟在良英身后,进了蜀山里头后随着上了一辆马车。
“里面还有个姑娘,就这么坐外边儿吧。”
男女授受不亲嘛,他自然懂的。卜寒州点了点头,算是应了良英。
良英是坐在他左手边,右手边是一个体宗的青年,手有些不安地抓着身上的衣物,喉结上下滑动了一番。
“墨华章。”良英努了努嘴,示意道。
卜寒州“嗯”了声,抱着手臂窝成了一团。
“华章哥,这是卜寒州。”
墨华章兴许是点了点头,反正卜寒州没有听到他回话。卜寒州打了个哈欠,继续车上没能打完的瞌睡。
山里树木参天茂密,虫鸣不断,不时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投下一片阴影。
三个人呆在车厢外的车板上,良英抱着他那剑匣兀自望着天空,卜寒州睡得几乎无声无息,墨华章还在四处打量着树林。至于车厢里那孩子,则是没什么动静。毕竟是个女孩子,喜静也是正常。
走了一阵,卜寒州突然皱了皱眉,抱着手臂的双手一紧,却仍是没有睁眼。
约莫一分钟后,四下竟突然掠出几个黑衣人来,黑布裹满全身,看不出一点模样。
最先跃出去的是良英,同时他的剑匣也“咔”地开了一道缝,千雪剑应声而出,顺势出鞘,不带一丝犹豫、夹着一道凛冽的剑风斩向其中一名黑衣人。
随即,墨华章也跃出了车板,自空中挥拳打向另一名黑衣人,同时出腿,狠狠踹向一自他背后攻过来的黑衣人。
“这搞的什么幺蛾子?!”墨华章咬牙道。
良英拎起剑匣,直往余下的一黑衣人脑门敲去,吼道:“别管那么多!先刚了这波再说!”
“那小学弟呢?!”墨华章躲过一次攻击,一个后空翻跃到不远处,擦了擦嘴角的一丝血。
“你去把他拎醒——靠!卜寒州!”
正在围攻良英的一名黑衣人突然转向,抽出一把长剑劈向马车车身。
眼见着那剑将要连车带着两个孩子劈作两半,只见一道黑影掠过,落定时那黑衣人已经摔在了远处,胸口的衣服像是被什么炸开了一般,胸口还有黑乎乎的一团。而卜寒州则一手拎着那惊魂未定的女孩子,一手的指间夹着他那两根血色且看着就邪气肆溢的血花毫,两瓣几近苍白的薄唇抿着一沓尚未动用的符纸。
最令人无语的是他还气定神闲地用胳膊夹着他的那只箱子。
“你他妈竟然装睡?!”良英不敢置信地喊到,抄起剑匣恶狠狠地砸向那复又攻上来的黑衣人,似是要将他的那些怒气尽数撒在上头。
卜寒州斜了他一眼,含糊不清地说道:“打你的架。”
“师兄你放我下来!”小姑娘委屈道。
“什么师兄,他五年级!”良英插嘴道。
祁云傻了眼,被他放下来后躲在他身后愣愣看着他。
“你在这里乖乖呆着,”卜寒州用牙齿咬脱了左手半边手套,置于右手下方,右手中血花毫在他指间翻转了一番,一道寒光闪过,他的左手手背上便出现了一道红痕。
那是一道细长的伤口,血液不多时便溢了出来。卜寒州拿血花毫的笔尖沾了血,拿了那沓符纸,迅速写了几张,塞给祁云:“拿着,防身用,小心着别炸了。记得看好我们的行李。”
语毕,卜寒州便掠了出去,挥出一张符纸,正对上那名胸口开花的黑衣人奋力砍下来的铁剑。
那符纸牢牢贴上了剑身,竟是自那之下出现了道道血痕,攀住剑身,将其分割为数块。卜寒州嗤笑一声,伸手在剑身上挥指一弹,那剑身居然登时四分五裂,落在了地上。
黑衣人迅速后退,静静看着他。
“阁下分明还有招数未用。不知究竟是何目的?”
此时,良英那里已经挥剑砍在了对上的那黑衣人左肩上,鲜血争先恐后地从那开了口子的血肉里涌出来,顺着剑身滴落在草堆里。那黑衣人低头看了眼,突然抬肩低身,硬生生将剑身从他身上抽离。
而墨华章两手各抓一黑衣人的脖颈,将他二人的脑袋狠狠撞在一起,撞得人眼冒金星。墨华章却并未打算就此放过他们,而是稍一用力,将他们猛地拽起,抡在地上。
“哇哦,”祁云小声道,“骨头裂了诶。”
那声脆响传入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卜寒州面前的那黑衣人正欲动手,却是顿了顿,飞身隐入了树林间。墨华章手下的那两个黑衣人抓住他的手腕往上一提,迅速抽身随着另一人离开。
良英甩了甩剑身上的血珠子,收剑入鞘。
“可有受伤?”卜寒州一面问道,一面转身从祁云手中收回符纸,数了数,面色一僵。
“没什么问题,就是手腕有点疼。”墨华章回道,站在几步外没有靠近。
“你就不能对女孩子温柔点?”良英凑到他身后问道,这才察觉他有点不对劲,“……怎么了?”
“姑娘,这符纸你对谁用了?”
祁云捏着衣角扭扭捏捏说不出话来,就在此时,远处的树海中突然传出一声爆炸的声响,四人脸皆是一黑。
“……哦。”卜寒州淡然收回符纸。
感情是贴人身上了。
“这些人突然跑出来是干嘛啊……”
良英去寻了卷绷带递给墨华章,回道:“也许是……‘测试’吧?”
卜寒州扯了扯嘴角:“走吧,去学校。”